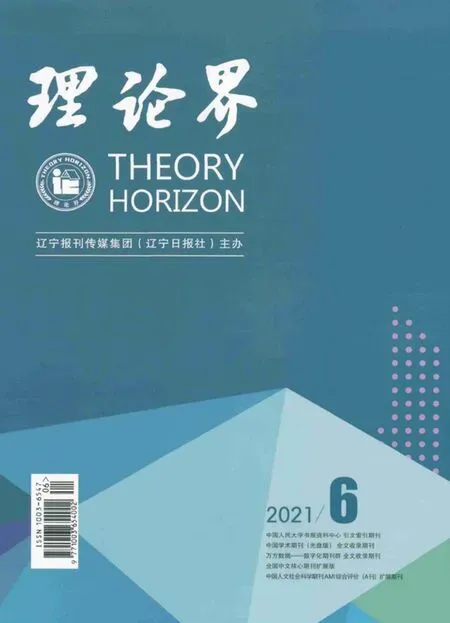从“心性大小之辨”看陆象山心学的展开
2021-12-26席玥桐
席玥桐
陆九渊,世称象山先生,是南宋时期重要的哲学家。董平认为,象山学说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以本心作为其理论基石,开创具有本体含义的心学理论。〔1〕陆象山关于心学的思考,源于孟子。孟子之“心”有许多表现,如存心说、四端之心、“心之官则思”等等。但是,他的学说尚未形成以心为本体的理论体系,而在道德情感方面着墨颇多。一些学者认为承接此传统的陆象山也赞成“‘本心’就是‘仁’心,进一步地说,就是促发道德行为的诸情感以及指导人的各种道德行为的行为准则或根本原则”,〔2〕陆象山亦难逃经验之维。即使他的心体思想存在先验层面,但仍存在“包含人的情感和欲望在内的气血之心”。〔3〕根据这样的观点,陆象山虽然预设了心之本体,但因夹杂经验的不确定性,并未形成一个融贯的道德体系。事实上,陆象山一方面未放弃甚至拓宽了孟子关于道德实践的经验层面;另一方面,通过把心“提升为具有本体意义的道德本体之心”,〔4〕构建了以心为本体的独特学说。
陆象山的思想简洁明了,从其来源可见一斑。陆象山自称其思想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5〕王阳明也曾说“故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6〕他的发明本心,重视心体等思想,无不与孟子的思想息息相关。孟子曾以“心之官则思”的功能联系到“大体”的层面,而陆象山由此转出,进一步发明他的“先立乎其大”的意涵。
关于“大体”思想,缘起于孟子对公都子问题的回答。在关于“心性大小之辨”的问题上,孟子点出其宗旨,但是并未完成他的答案。在宋代,心学依然被认为“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无伎俩”。〔7〕从现实层面出发,人性既可呈现善,也会呈现恶,心学需要回答如何在善恶不明的实际中贯通本心之善。陆象山并未规避问题,而是从本心出发,旨在回应具体伦理情境中的“心性大小之辨”问题,以完成对“先立乎其大”的演绎和发展。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陆象山进一步确立了他的“先立乎其大”的宗旨和本体思想,为今后阳明心学的发展奠基。
一、“心性大小之辨”的提出
“心性大小之辨”是陆象山心学中贯穿终始的主题。而这一主题最开始出现在《孟子·告子上》的一段对话中: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从现代道德语境看,公都子关注的“大小”问题可看作善与恶的形成问题。一开始,孟子提出的“大体”与“小体”分别点出了善与恶的存在根据,回答了“大人”为什么是“大人”、“小人”为什么是“小人”的问题。而公都子进一步追问“从其大体”与“从其小体”的原因,即大人(小人)如何成为大人(小人)的现实成因。孟子以“心之官则思”作为立论,描述了大小之别的产生。
通而观之,“心性大小之辨”的讨论中存在两条问题线索:第一条是大人(小人)为大人(小人)的存在本质,即为什么是的问题。第二条则是大人(小人)何以为大人(小人)的原因,即如何是的问题。孟子以“大体”与“小体”为根据,对第一个问题简要回应。在回应第二个问题时,“心之官则思”与“先立乎其大”都鲜明地点出了心学的核心义理。可见,相较于第一个问题,孟子对第二个问题更为敏感和重视。
在如何成善的意义上,“心性大小之辨”说明了人性存在“大”与“小”两种可变的情况。孟子坚持“性善论”的观念,由此出发而有“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尽心下》)的合理推断和理论延展。然而,荀子与此相对,他基于经验的观察而大加阐发“性恶论”:“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8〕孟子与荀子各自代表了两种人性观念。但是,从人性的发展整体看,他们其实揭示出人性存在可变化的不确定性。人性既会有善的发显,也存在腐化堕落的可能。再来审视公都子的“心性大小之辨”,其实他在追问人应当如何应对善恶变化的不确定性问题。
陆象山承继孟子“大体”之心的立场,进一步回应“心性大小之辨”中人性的不确定问题。陆象山通过“德伪之辨”和“同异之辨”来回应善恶的变化性,使“大体”之心在不同的伦理关系中锻造自身的向善性和明理性。善与恶的评判不再拘滞于固定不变的人性预设,而需要历经实际伦理情境的考验,这意味着心学逻辑向实践领域的展开。所以,陆象山意义下的“心性大小之辨”问题是:在不同情境的冲击下,一个人如何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中坚持性善、成就大体。
二、德伪之辨
孟子提出“先立乎其大”,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成就一个人稳定的品格。陆象山则在修德工夫中发展了“先立乎其大”。他们的共同点是:一切道德品质的推进和扩充都在于发挥此心的功能。不同的是,陆象山更加重视从反身明理的功能层面来思考。正所谓“积善者,积此者也;集义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进德者,进此者也”。〔9〕“积”“集”“知”“进”是依循本心的实践,善、义、德等德目并非与我无关的条例。一切德目须从本心出发,成为内在的德性。因此,一个人在自修德性的环节中,须注意到身心中的问题,时时把握住“德伪之辨”的界限——本心。一个人如果主动放弃本心,则会陷于“心逸日休,心劳日拙”〔10〕的极端状态中,一切成德之事终将废弃。能否立此心之大,能否充分发挥本心的功能是德与伪的分界标准。
立其本心表现为在蔽累常显的环境中,主体持久地涵泳本心。从人格树立的角度看,陆象山也如孟子般认为,君子异于人的地方在于君子能存此心。心这一独特的官能是每一个人生而有之的,孟子拈出“性善”之论,以四端之心作为人之善性的基石。但是,从个体发展的不同境况看,一个人本应从此“四端”生长,如何会走入截然相反的方向?正如孟子“牛山之喻”的警醒所示,日日废弃不作为,端倪终将不见踪影。陆象山从本心能否发挥的工夫论视角再做延展,给出两条路径来阐明君子与小人判然两分的现象:君子的人格树立是他能够日日存此心,但是小人则放其心、去此心。前者保守此赤子之心,时时在四端之心上做工夫;后者陷溺于蔽累中。相迥异的路径造就了君子与小人两种人生。
在涵泳本心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虚假和实有的分别。陆象山强调:“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实。言理则是实理,言事则是实事,德则实德,行则实行。”〔11〕这里提到“古人自得之”的对象包含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也包含良知良能、天爵等。善端之心能够存在于经验世界之中的根据来自实践,而且这种实践是笃实的践行。如何是笃实的践行?“然开端发足,不可不谨,养正涉邪,则当早辨。”〔12〕笃实地践行在于“开端发足”,也就是其行事的动机来源于本心,以纯粹之善心实践,而不是出于偶然的、偏狭的选择,也不是出于功利的行动。
充足地涵泳纯粹本心无法一蹴而就,主体须克服“怠惰”和“急迫”两种极端情况。“但所谓怠惰急迫两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稳之地,不以动静而变。”〔13〕在涵泳之中,既不可借主静之机而养成怠惰的习惯,也不可只知常动常变,而不知本心之定,以致慌乱、失却头脑。涵泳本心的状态是中道的实现,是一种“美在其中,不劳外索”〔14〕的理想状态。
主体在发明本心时还应做到克服私心的遮蔽。孟子曾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陆象山则进一步强调本心受遮蔽的原因,那就是“人之有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15〕从“可以是”到“能够是”之间往往存在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就是“自贼”所致。“自贼”的病因是“己私安有不可克者?顾不能自知其非”,〔16〕“己私”的遮蔽让人无法自知。陆象山同意孟子的“仁”是“人之安宅”(《孟子·公孙丑上》),然而他也不断强调,在“己私”遮蔽的情况下,人会离开“安宅”,陷于两难境地。“今己私未克之人,如在陷阱,如在荆棘,如在泥涂,如在囹圄械系。”〔17〕如若不克服“己私”,每个人只会离“安宅”越来越远,南辕北辙,不得不“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18〕因此,克服“己私”是保证本心能够推进、而不是被私欲击退的底线要求。
持守本心不是无根源的,其根据在于坚持此理为一,而不是为二。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至于孟子有:“夫道一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上》),如果出现“道二”,那就是“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所以,无论是先知先觉的,还是求得的,都只是这一个理,此理是善恶分立的准则。在此理之一侧,是“爱其亲者”“敬其兄者”以及“怵惕恻隐之心”;〔19〕在此理之另一侧,则是“可羞可恶之事”。〔20〕由此可见,既明此理,则明善恶之别。以仁理为本根,才能够一以贯之。
立此本心,每个人方可确立起生命赖以存在的本根。如若舍弃此本根,而狃于闻见之中,则会出现“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别。
夫子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古之所谓小人儒者,亦不过依据末节细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许浮论虚说谬悠无根之甚,夫子犹以为门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谬悠无根而可安乎?〔21〕
在陆象山看来,“君子儒”是在此心本根处着力,小人儒是“依据末节细行”。而更有次于小人儒的“今人”,于“浮论虚说”处用力。随着偏离本根处的方向增大,人的精神越来越容易消耗殆尽。人无本根,便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只能终日患得患失,处于“终日营营”“盈涸荣枯无常”〔22〕的劳碌中。陆象山强调本心的作用,其实观照的是每一个人生命存在的本真。
总之,人心之恶既不源于自身先天设定,也不源于外物存在。“用心多驰骛于外,而未知自反。”〔23〕在世之中,人人都在与他者打交道,但有的人在此过程中能持守本心;有的人却陷于周旋,放弃真实的生活。
德与伪有“可辨”之处,意味着二者不是两个事物,而是一体的。德与伪都是心的状态,而且都有天理贯穿其中。有德意味着自己能够依循道,专一恒久;伪则意味着心在道中摇摆不定,会被己私、俗见等干扰。在“德伪之辨”中,若不想失去大体,须在保持大体上用工夫。因此,在德与伪的讨论中,陆象山强调的是“先立乎其大”中如何去“立”的方面。他从工夫论角度理解道德,把道德扎根在实践之中,而不是浮于表面的空谈。在终极意义上,道德是成就生命本真的必经之路。
三、同异之辨
陆象山对“心性大小之辨”的发展还表现为“同异之辨”。“同异之辨”关乎的问题是主体如何对待他者。在“同异之辨”中,所同者为大智之明,所异者为自私小智。
人人皆可成尧舜,而舜之所以是圣贤在于他的明觉大智。舜的大智表现为“善与人同,乐取诸人以为善,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4〕在舜的例子中,“大智”是指一个人能够见一切善,并且将善时时刻刻发挥出来。性善者能够客观察知善的存在,是因为他能超出主观视角。这种视角既不是出于我本身,也不为他人所规定。对于陆象山而言,大智之明是一种能够不偏不倚地去见善闻善的客观立场。
基于客观化的立场,性善论不是为我的中心主义,而是一种“有所同”的状态。孟子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与“反求诸己”的担当精神,但这些宣称也遭遇着其道德行动只有自我的主观化质疑。事实上,心学中的“己”不是指只见己之是,而见他人之不是。而且,陆象山讲道:“今人所患,在于以己为是,归非他人,虽有显过,犹悍然自遂,未尝略有自咎自责之意。”〔25〕在这个意义上,心学中的性善意味着什么?正是“善与人同”之善。具体而言,“善与人同”的自己会有如下表现:(1)能见己善与他人之善。善之存在不是肯定自己而否定他人,而是平等地看待善的普遍存在。性善论肯定人人都有“天之所与”的本心,这正是对每个人存在价值的肯定和尊重。(2)“善与人同”仍在于个体自身的努力,自己能够推扩己善。善于“推扩”是一个很重要的为善能力。在学习中,善推扩的人能够举一反三,能够“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同样,在道德实践上,善于推扩的人能够将自己的善心不断地充实。这也正是君子比普通人高明的地方。(3)“善与人同”还表现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如舜一般“乐取诸人以为善”,好学他人之善。保持这种积极乐观的学习态度,一个人对于善的理解才会不断地丰富和深刻。
“明理”则是小人能成为大人的枢纽。当小人“蔽于闻见,以陷于恶而失于本心者”〔26〕之时,在陆象山看来,这并非真正的小人。因为小人若“见善而慕,知过而惧”〔27〕也能够转化为君子。这样的转化说明人能够自觉善的存在,“善与人同”的实现在于每个人都能够自觉此善心,亲近此善理——即有“明理”之心。“明理”则在于自己反省检查自己,如果“反己未切,省己未深,见善未明”,〔28〕则会陷于小人的深渊中。孟子认为,这样的自觉善意之心便是良知良能,陆象山进一步提升此心以达到与理相合的本体层面。当此心能够源源不断地照显此理的时候,则有“心即理”的通达明觉。
由于心是“至灵”的,知理之心自能消除私意俗见。正所谓“此心之灵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习,如见晛之雪,虽欲存之而不可得”,〔29〕此心明理则能立德,私意自会消散。因此,“明理”之心是消除私欲遮蔽、建立德性、恢复本心之同的最终根据。
在陆象山看来,能够发挥本心至灵意味着“知至”,“知至”指一个人自觉、自知以及自明天理。“此乃谓之知至,乃谓之先立乎其大者”,〔30〕由此可见,“先立乎其大”意味着人能够成就基于客观天理的大知,而脱离狃于闻见的小知。
四、陆象山意义下的“先立乎其大”
孟子的“先立乎其大”点出“大体”作为人的主宰这一主题。然而,这直接简明的心之思需要历经考验才能完成。陆象山在德与伪的辨析中,思得涵泳人格的力量;在同与异的辨析中,思得善与人同的公理心。陆象山的所思所得无不是对“先立乎其大”的进一步发明。
从主体角度看,“先立乎其大”意味着主体之“知”的明晰。在“德伪之辨”中,陆象山强调要“涵泳”和“寖明”,以去除遮蔽和保持本心明朗。而在“同异之辨”中,则强调“知至”,这种明朗之本心须以客观之知为根据,本心才能真正确立。基于大体的本心既不拘囿于经验的纷杂,也不执守于四端之心的原初状态中。“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31〕在应对具体伦理情境中,他透析出背后的心学规律,须“收拾精神,自作主宰”,〔32〕而不是去诉诸他人、求之于外、狃于听闻等。
从客观角度看,“先立乎其大”的根据在于秉持天理的客观性。“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33〕人在自我修身中,所坚持的善方向只能是一,不能是二。此“一”体现对天理客观性的诉求,而不是累于矛盾的偏隅之见。“典礼爵刑,莫非天理,洪范九畴,帝实锡之,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34〕事物虽有千变万化,然而其中都包含客观的天理。依循天理的人能够理解世间的包罗万象,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所。此理塞宇宙,天理公平地遍布在一切事物中,“天覆地载,春生夏长,秋敛冬肃,具此理”,〔35〕此理是宇宙秩序的根源。
至于陆象山,“先立乎其大”已然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行为端倪中发展为具有本体层面的意涵。一方面,“先立乎其大”表现为一个人的本心之明。依于本心,世间之人可透过声色、利用和文章技艺,而不失却自己生命的本根。另一方面,“先立乎其大”并不指涉主观的内心,而包含对生命规律的遵循。“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36〕按照天理的秩序,人与万物可在宇宙间各得其所,生生不息。
展望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此天理承继古代先贤的智慧,依循此天理是一个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像西方世界充满神话性。天理并非来自神的命令,而是由中国先贤在实践中一步步凝练而成。现在的人能够与天理相通,便会觉得“古先圣贤常在目前”。〔37〕与古代圣贤相通,不是厚古薄今,而是指向古人学习“盖他不曾用私智”〔38〕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从公理心出发去对待世界,能够经受得起时间和世事的考验。“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千古圣贤不能异此”,〔39〕在历史的淬炼中,人凭借自身的智慧探索着生命的规律,不因偏见、偶然性和外在浮华而中途易辙。因此,天理早已灌注在每一个人的切身体验中,是每一个人应当继续传承的价值。
五、总结
从哲学意义看,通过进一步回应“心性大小之辨”,陆象山拓宽了性善论的内涵。孟子拈出心之思的官能以回应公都子的“心性大小之辨”,但是孟子的回答是未完成的。在经验世界中,“心性大小之辨”的问题展现多样的形态。从性善论立场出发,如何处理在经验世界中从其大体的问题有待回答。陆象山为发展心学立场,从两个方面回答该问题:一为德伪之辨,一为同异之辨。从前者出发,性善论从先天之性善转变为修德之性善。在修德工夫中,保持此善心之本是判别德与伪的指向标。故而,性善论在修身工夫意义上没有规避恶的问题,反而为识别善恶问题而阐明了原则。从后者出发,性善论表现为“善与人同”,而不是与人为异。“善与人同”须从大体之心出发,推扩己善,见人之善,觉一切善。最终,个体能够超越主我的立场,而以客观立场觉知善。这便是心能明理,故而为“心即理”。
陆象山从“心性大小之辨”中突出了“立”与“大体”的优先性和本根性。通过对“心”的本体化处理,“先立乎其大”成为他回应具体伦理情境的根据所在。值得关注的是,一个人能够克服私意,便可作为“心害苟除,其善自着”〔40〕的成善状态。虽然陆象山并未将“克私”发展为一套成体系的工夫论(这一点由王阳明的工夫论发展完成),但立本心须克私的理念已然树立。另外,陆象山的“先立乎其大”最终落实到“知至”。心以“至灵”之明觉而能通理,故有“同此心,同此理也”意义下的“心即理”。这一论断为王阳明继承,他将心发展为良知,将明觉之心进一步客观化,心与理最终走向合一。
陆象山在处理“心性大小之辨”的问题上,一以贯之地阐明着他的心学宗旨——“先立乎其大”,他的贡献对于心学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陆象山改变了性善论主观化、忽略恶之存在的印象,使性善论思想客观地面对人性中的不确定问题,从而扩充了孟子的四端之心以及大体思想的意义,在本体层面确定了心的位置,展现出性善论客观合理性的一面。另一方面,陆象山开启了王阳明良知学中的以知来解心的理念。故而,陆象山的心学思想是心学历史中重要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