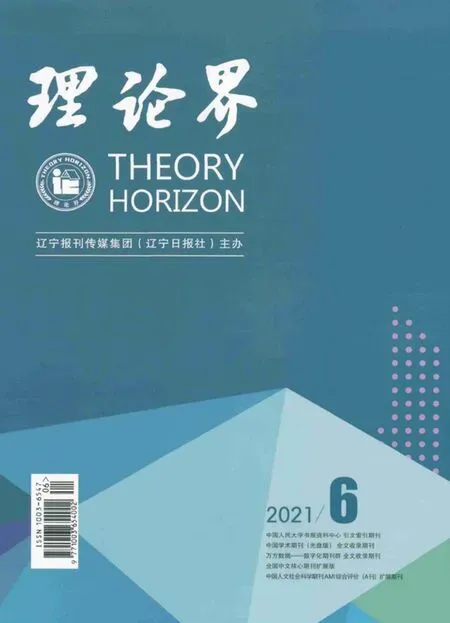纳尔逊·古德曼隐喻理论视野下的诗歌隐喻新探
2021-12-26王胜男
王胜男
精神不是抽象的,它借助各种形式现身。此时,形式与内容、语言与意义、物质与精神恰似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严丝合缝、难解难分了。艺术是有形的精神,是精神的外化。诗歌是语言的艺术,通过语词新的组织,意义在诗中流动起来。通过语词的“反常”使用,诗歌显得含糊、怪异、不合逻辑。在诸种“反常”方式中,隐喻占据重要地位。隐喻是诗学、修辞学、语言学、哲学等共同关心的主题,它常被看作修辞格,与语言的偏离、反常使用、范畴错误画等号,这意味着文学语言仿佛只是借助技巧使语言偏离了“正常”轨迹。日常语言以交际为目的,已固化为单义、强指称的模式,科学语言准确、清晰,追求一种中性的客观语言。而艺术语言往往多义含混,其中诗歌最具代表性。它通过创造丰富、新颖的意义空间,展现语言的深厚韵味。诗歌中常见隐喻,德里达认为诗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1〕因此,暂时搁置作为修辞方式的隐喻,转而对语言自身隐喻性质的探索是诗歌语言研究的重要方面。
一、哲学视域下的隐喻之思
1.相互冲撞的语言隐喻观
语言学探索隐喻的意义生成机制,而哲学家更关心隐喻与实在、真理等的关系问题。一些哲学家对隐喻抱有警惕或敌意,这缘于他们偏爱清晰、准确的字面语言,认为“纯字面语言乃是最重要的语言使用之所在,而隐喻之类只有歌谣或谜语中的相对不常用的边缘地位”。〔2〕如以卡尔纳普(Carnap)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将艺术、诗歌等排除在外。这种对语言“缺陷”的拒斥在莱布尼茨(Leibniz)那里就已显现,他认为思想的模糊不清与争论主要在于语言的模糊性。然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却将语言置于某种本体论的地位,海氏反对将言说当成人类的一种功能,更反对人类对话语的操控,他主张人类需对语言保持敬畏,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我们唯有倾听语言,才能领悟存在的秘密。海德格尔说,“语言说话”,若要获得语言之说,必须在“纯粹所说”也即诗歌中获得,“纯粹所说乃是诗歌”。〔3〕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揭示存在的真理,“诗”和“思”是语言——道说之发生的两个基本方式。〔4〕因此,诗歌隐喻不是反常的话语样式,而是蕴藏存在的秘密。与海德格尔类似,当代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运用符号学的方法,揭示了隐喻在构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他竭力为隐喻正名,指出了隐喻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重要地位。
2.纳尔逊·古德曼的隐喻观
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在艺术哲学的视域下构建了其隐喻理论。他基于一般符号理论分析了隐喻的本性,不仅从符号运作的模式出发解释了隐喻的发生机制,同时更将隐喻作为某种符号超越的方式,赋予其重要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意义。隐喻不仅不是世界的装饰品,恰恰是重构世界的重要方式。它通过标记图式的迁移,给予人类崭新的看待世界的视角,增加了人类对世界的洞见(Insight)。优秀的艺术使艺术变成了“物”一般的存在,使我们可以不断感受与体验它。诗歌不应是封闭的文本世界,而是人们通过读诗,获得了更丰富的体验世界的方式,而隐喻是创造这些方式的重要手段。如何(How)说与说什么(What)从来不是割裂的,隐喻绝非仅仅是手段,因其参与构成话语的内容,并由此重构了世界。古德曼的隐喻观揭示了隐喻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重要功能,为分析诗歌中的隐喻问题提供了哲学语义学上的视角与启示。
二、古德曼标记“图式转移”的隐喻理论
1.超越“语言工具论”
随着20世纪的“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对语言重要性的认识已成为一种共识。然而,摒弃语言工具论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将文学看成遵从“思想—语言—世界”这样的关系链,不仅仍然落入了语言表达思想的窠臼中,也偏离了文学的本意。语言并不是贴在已经完成的思想上的标签。〔5〕“我们分析思想,好像在找出表达思想的词语之前,思想已经是我们的句子试图表达的一种理想的原文。但是,作者本人并没有他能与其著作进行对照的原文,也没有在语言之前的语言。”〔6〕即便声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依然难逃被动描述世界的宿命。世界如此坚实,语言的日常状态早已将语词与事物牢牢地捆在一起,即便世界本就是语言(符号)所建构的。古德曼隐喻理论的深刻性,在于其语言观的自觉。他坚信,没有脱离语词与符号的世界,符号代表与指称世界,而世界是符号活动区分的产物与结果。语词与符号在古德曼眼中,不是表达世界的工具,而是建构世界的重要媒介与养料。正是基于这种新的语言观,古德曼才完成了其艺术哲学及哲学重塑的目的,才使其隐喻理论显现强大的生命力。隐喻不是多余的装饰品,而是重构世界的重要认知方式。
2.艺术是构造世界的方式
纳尔逊·古德曼从本体论、认识论上消解了“实在”,将“世界”消融于多种“世界—样式”(World-version)即符号系统(Symbol Systems)中。他主张世界是被构造(Made)而不是被发现的,世界是通过构造多种适合的符号系统而被构成的,其中艺术、科学、哲学等均是构造世界的不同方式。艺术不再是低级的感性领域的对象,而是如科学一样,服务于真理的发现与发明。然而,此真理已非传统符合论真理观下的真理,而是某种依循特定符号系统及多种因素的正确性(Rightness),它反映了符号系统的状态与特征,并成为符号运作之中的某种动态的稳定性。理解(Understanding)作为别样的真理成为认识世界的目标。符号系统并非一成不变,新要素的加入或旧有符号秩序的调整都会引发符号系统的变化。唯有流动与变化,才有新鲜的活水涌现。唯有对传统、习俗、惯例的超越,才会产生新的认识与洞见。在艺术中,符号最有活力,艺术家以其敏锐的感受与直觉不断发现新的关系与关联。诗歌是语言的艺术,隐喻是诗歌语言的惯常样式。与传统格律诗不同,当代诗歌自由舒展的语言表达,往往使诗歌本身显得晦涩含混。原因在于,当代诗的书写给予了我们一种崭新的看待世界的视角。用古德曼的话来说,是诗歌隐喻打破了标记(Label)的惯常适用(Application)方式,以标记运作的反常规性进行了领域(Realm)的重新组织,更新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
3.作为标记“图式转移”的隐喻
索绪尔的符号学为意义的符号学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路径,然而对诗歌隐喻的理解无法单纯局限于符号学的维度,虽然隐喻涉及意义运作的奥秘,然而“语言系统”从来都只能在具体的话语中显现。谈论语词对世界的区分和组织,便是谈论古德曼意义上的符号指称(Reference)活动。“话语指涉事物,而符号仅仅指涉系统之内的其他符号。符号与符号相区别,话语则指称世界。差别是符号学的差别,指称则是语义学的指称。”〔7〕因此,语义学通过与符号学和平共处,将探索的触角指向世界,并深信唯有通过对语言及其他符号活动的理解,才可能理解世界。
在古德曼看来,隐喻与人们区分世界的方式有关。他以外延语义学的方式,在艺术哲学的框架内,重新解释了隐喻的运作机制。他以谓词(Predicate)的隐喻性适用(Metaphorical Application)为切入点来阐释隐喻的机制。古德曼认为,事物拥有某种属性(Property)便等同于将某个谓词适用于它。说“这个灯是绿色的”等同于说这个灯具有绿色的属性。将一个谓词成功地适用于某个事物或某类事物,就是完成了谓词的一种成功的投射(Projection)。谓词到世界的投射过程,推而广之,便是标记(Label)适用于其对象(Objects)的过程,是符号指称(Reference)世界的过程。这种广义的符号化(Symbolization)行为,同时也是建构(Construct)现实的过程。世界不是预先存在的中性客体,而是符号活动构造的产物和结果。古德曼较为侧重描述属性、特征的隐喻性语言,如“这幅画是悲伤的”。不过,如下句子同样是隐喻的:“The lake is a sapphire”(那汪湖水是一颗蓝宝石)。其中,“湖水”“蓝宝石”通过与其通常的指称领域建立指涉关联,使世界得以区分与范畴化。而当它们试图为别的领域分类时,就可能产生隐喻。比如,“蓝宝石”通常指涉所有蓝宝石,而隐喻的适用,却将“蓝宝石”分配给其他对象或领域,比如用“蓝宝石”指涉一些湖泊。由此,我们通过标记新的适用,获得了对湖水的新的感受与体验,比如湖水是清澈的、晶莹剔透的、湛蓝的、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的,是小巧的、精致的,等等。可见,隐喻会打开一个广阔的理解空间。
三、古德曼的隐喻理论对诗歌隐喻的诠释
1.诗歌隐喻中的标记“图式转移”机制
一首好诗通常给人不一样的世界体验,诗歌语言的非字面使用可以从古德曼的隐喻诠释中获得解释。如“你们以为麦粒就是你们/为女人迸溅的泪滴吗?”(伊沙《饿死诗人》)“到了夜里,我可能是一头食人鲸/也可能是被信心击溃的乌鸦。”(朵渔《窗》)这里头,隐喻的构成主要是“泪滴”“食人鲸”“乌鸦”的新颖适用,即通过关联于新的指涉领域,从而完成了新的分类活动。“泪滴”建构了对麦粒及其相关物的重新分类,“食人鲸”和“乌鸦”则实现了对人及其领域相关物的重新组织。然而,上述分析仅仅点出了隐喻过程的一部分,似乎隐喻仅仅在单独的词语中完成。事实上,语词从来不会孤立地起作用。索绪尔的符号学,已将意义归于关系的产物。语词与事物间贴标签似的对应关系,和语词与固定意义的一一对应同样不可理解。语言更像一张隐形的大网,意义世界在其中清晰与显现。语言是“在人的心灵或‘精神’结构中充分形成的功能系统”。〔8〕
在隐喻中,“标记不是孤立地起作用,而是作为属于一个家族的成员而起作用。我们通过一些可选择物(Alternative)的集合来加以归类”。〔9〕标记的集合(Set)构成一种图式(Schemata),它可以包含两个甚至更多的标记,且随语境而变化。而图式中标记所适用的对象集合便是其领域(Realm),实际上也就是被图式分类的对象(至少包含其中一个标记所指涉的对象)。〔10〕标记并不属于某个固定图式,而是可以归属于许多图式。比如,“红色、非红色”与“红色、蓝色、橙色、粉色、紫色”便构成两种不同的图式,当它们都用来指涉一堆彩球时,被我们看成红色的彩球会随着两种图式的不同而存在微妙的差别。这意味着图式不同,相同的标记可能区分出有差异的对象领域。标记在此成为一种非实体的功能性存在。较极端的例子是一词多义现象,比如“红”在“这个苹果比那个红”与“他的思想又专又红”中,意义便不同,相应由“红”作出的区分领域也不同。因此,在语言使用中,每个标记的使用既得益于既有的图式,同时又可能开创新的图式。标记与指涉领域的复杂关联,给语言的创造性开启了广阔的空间。
2.标记图式的建构与诗歌语言的创造性
标记依赖所属的图式获得意义及特定的身份。因此,诗歌语言更注重标记图式的探索与创造。如“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通过语词并置,勾画了一幅别有意味的简笔画。也可以说,上述语词构成了一个标记图式。某种程度上,每一个词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可能的标记图式。我们说“羊”代表我们学会了运用“羊、狗、牛、猪”等区分图式。实际上标记图示依然依赖差异起作用,这与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殊途同归。因此,理解隐喻既需要将诗歌文本作为整体,看成一个复杂的标记图式,同时更依赖对个别语词潜在标记图式的搜索与建构。
读诗并不像日常交流那么容易,诗歌标记图式的建构不仅依赖字面用法,且需联系诗歌上下文,并且往往因隐喻语言的大量存在,加重了读诗的难度。诗歌是标记图式与领域间复杂关联的产物。因此,标记图式不仅打破了日常语言的惯用模式,也因众多复杂的标记图式转移,造成了图式关系的交织性与传递性。按照古德曼的符号指涉链,我们原则上可以将一个语词关联非常遥远的领域,如“花”—花—“美丽”—美女—“小脚的”—脚—“金莲”……指涉链往往并非如此单一与简单,而是以更复杂的方式连同整个标记图式发生变化。
3.诗歌隐喻与重构世界
以谓词为核心的隐喻阐释方式,实际上贯穿着“X是Y”的隐喻理解模式。〔11〕我们说“爱情是甜蜜的;屋檐是忧郁的;天空是孩子的眼睛;白菜是伤心的”等等。谓词“Y”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适用于主词“X”的领域,由此我们体验到了“X”领域的无限丰富性。将“X”领域置换成世界,那么“Y”就是各种各样的符号系统,它们构成不同的“世界—样式”来言说世界的丰富内容。这既是古德曼的哲学精髓,同时也道出了诗歌重构世界的重要价值。然而,诗歌隐喻并不总是呈现为“X是Y”的模式,如“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顾城《弧线》)既可看成拟人,也可看成海浪退潮与人耸起的背脊建立起的隐喻。此时是“耸起的背脊”所属的某个图式向海浪的某种转移。事实上,拟人在古德曼看来也已属于一种隐喻了,涉及不同领域(如生命领域的标记转移到无生命领域)的标记图式转移。诗歌在某种程度上都潜藏着“X是Y”的隐喻模式。“是”不一定在诗歌中显现,而是以更加复杂的词语组合样式呈现隐喻的意味。如:
那是我们不能攀登的大石
为了造出它
我们议论了六年
我们造出它又向上攀登
你说大约还要七年
大约还要几年
一个更长的时间
还来得及得一次阑尾炎
手术进行了十年
好像刀光
一闪——
(多多《那是我们不能攀登的大石》)
对于读者来说,建构标记图式即追寻其所指领域。这首诗,被隐喻者X十分隐晦,诗人通篇都在捕捉这个东西。我们对它的感受与体验,全部以“Y”的丰富展现为基础。“不能攀登的大石”作为标记图式的一员通过指涉X,使其在诗歌开端处露面。“大石”“攀登”“不能”的多重修饰,使它初现饱满。从第二句“为了造出它”直至“手术进行了十年”都反复呈现了漫长、艰难和等待的永无尽头感。借此,X所带来的上述感受继续在诗中凝聚与锤炼,然而末句出现了一个爆破点,“好像刀光/一闪”一下子如一道堤坝,将前述它的艰难、漫长的时间特征斩断,只化为疏忽即逝的一瞬。而“阑尾炎”“手术”“刀光”的引入,又构成多种可能的隐喻空间。“阑尾炎”可能成为疾病标记图式中的一员重新组织我们对X的体验,此时“手术”可能构成了另一被说者X的体验内容。而“刀”的出现,既可作为体验十年时间的隐喻标记,同时又在和“阑尾炎、手术”的碰撞结合中,构成另一重对X的重新体验。被言说者在诗句中游移,像一次漫长的生病,也像一次永无尽头的手术,又如一把刀,切碎了那段光阴,也使那时的诸般情境染上了刀的色彩。而末句的“刀光/一闪”不仅构成了可感对象在时间上既漫长又短暂的悖论性特征,同时也因“刀”所沾附的凶残、血淋淋等意味,间接地将其传递给了X,使其染上了与之相关的凶狠、暴虐的特性。本诗通篇构成了一个隐喻,尽管中间几句未必算是隐喻性的。对被言说者的体验全部基于从Y到X的谓词描述之环,要理解诗句,需要我们不断建构可能的标记图式,从而打开丰富多样的对X的体验。对标记图式的搜索与建构,使我们对隐喻主体的丰富想象与体验成为可能。
4.标记“图式转移”与诗歌隐喻的张力空间
隐喻充斥标记图式的转移,加重了我们理解标记区分过程的困难。隐喻的发生是标记图式与领域间的复杂关系。旧有领域通过标记的重新指派获得新的组织,标记图式通过向新领域的转移与“远征”而征服了其他领土,从而获得了标记新颖的区分能力。然而,诗歌语言并非任意的语词自动机,隐喻发挥效力依赖新奇性与日常性的张力状态,隐喻不是标记的错误指派,而是“重新指派”(Reassign)。〔12〕由此,诗歌给予了我们不一样的世界与体验。从理想状态来说,标记的重新分配能力越强、越活跃,诗歌语言越鲜活,也会创造较大的意义空间。日常语言标记与所指对象的关系已固化,因此,逐渐丧失了生命力。诗歌的语境,限定了标记图式的种类与范围。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诗歌的内容。诗歌的意味再浓,诗人的创作与接受者的解读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诗歌确立了某种界限。标记图式的区分能力,并不意味着语词是被动贴到事物之上的标签。“领域依赖于标记于其中起作用的图式”,〔13〕基于这种领域对标记的依赖性的唯名论主张,古德曼强调符号活动对世界的建构性与创造性,强调前者范畴化、系统化的能力。他认为,可以有脱离世界的符号与词语,但是不存在脱离语词与符号的世界。〔14〕
布鲁克斯(C.Brooks)认为,诗歌的语言是悖论的语言。“诗人表明真理只能依靠悖论。”〔15〕这意味着诗歌总是某种迂回,诗意不像日常语词,直接穿透能指到达所指,而是犹如走上一条曲折不平的山路,意义被语词不寻常的关系击碎,需要不断在系统中重建和延宕。隐喻打破了语词的旧有规则,或者说是踩着惯例的肩膀实现新的跨越。在字面用法中,标记图式遵从“惯例”,与所指领域的对应关系相对稳定。隐喻的产生“似乎是一种给旧词语传授新花样的问题,即用一种新方式来应用旧标记的问题”。〔16〕隐喻涉及“图式的转移”,是“一种概念的移民,一种种类(Category)的异化”。古德曼不无幽默地说隐喻“是一次愉快而新生的再婚,尽管犯有重婚的罪名”。〔17〕
诗句“一片叶。这宇宙的舌头伸进/窗口,引来街尾的一片森林”(张枣《云》),“叶”与“舌头”本来均有其字面的指涉对象,隐喻使“舌头”及其相关的标记图式对叶子及相关指涉领域进行了重新组织。隐喻同时显现抵抗与吸引,结果是带着武力的言和。舌头与叶子及其相关者,因隐喻的使用展现了不一样的面貌。叶子与舌头的形似,伸出舌头与叶子落入窗口及二者偷偷摸摸、悄无声息的状态等都在隐喻中涌现。标记受到新奇性的诱惑,要冲破旧有的藩篱,然而,旧有的适用痕迹并不会消失,而是与新奇性共同促成了隐喻中的张力。旧有的标记适用过程一方面抵抗着标记的新的适用,同时又作为一种符号运作的“痕迹”与“历史”暗中引导着新的适用方式的产生。
诗歌是对日常语言的反叛,后者透明、单义,已使语言变成某种“习俗”。在日常语言中,世界的多样光芒被遮蔽了,诗歌隐喻试图恢复语言的生命力。在张枣的诗中,作为字面适用带来的对伸出舌头这一过程的理解,似乎也能成为隐喻合理性的依据之一。因为隐喻的关联尽管原则上是任意的,然而相隔太远太新奇,也不利于隐喻的产生。比如,“一片叶/这宇宙的头颅”便不适合,因为叶子与头颅较难建立适当的类比关联。符号活动的运作依赖先前的符号活动及其所建立的世界知识与背景。这些都将作为某种“前见”与“框架”成为诗歌隐喻成立的限制因素与条件。完全排除对象或过程的相似性或者仅仅以上述相似性作为隐喻的基础皆不可取。前者摒弃了人类活生生的体验,似乎使语言从零开始言说,后者削弱了语言的创造性,有使语言沦为工具的危险。语言、世界、意义、体验是流动循环的关系。
四、余论
古德曼的隐喻理论,凸显了语言的创造性及语言对世界的重构功能,为诗歌隐喻的阐释提供了哲学语义学上的补充与启示。在古德曼看来,隐喻与字面语言二者同为标记的区分方式,并无常规与怪异之分。隐喻的真实并不比字面的真实更不真实。“隐喻并不仅仅只是装饰性的修辞工具,而是我们让我们的语词从事多种第二职业的一个途径。”〔18〕对于“堂吉诃德”之类的空外延标记,古德曼同样依据谓词的适用性及符号指称链的复杂编织,使其具备了组织世界的能力。隐喻内在于符号的指涉活动中,古德曼对符号活动的探索,看重符号运作机制本身,而非符号的使用者。符号活动好比拍皮球,谁拍的、为什么拍都不重要,皮球弹起的过程及弧线运动才有趣。他对标记图式的重视,是看到了系统的价值与意义。从符号活动的内在运作机制出发理解隐喻能捕捉到其重要特征。然而,基于诗歌语言自身的复杂性,古德曼源于谓词逻辑的语义学考察,可能对于复杂的隐喻解释力较弱。对诗歌隐喻问题的探索,必须继续在修辞学、语言学、哲学等的协同努力下前行。隐喻是意义之谜、语言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