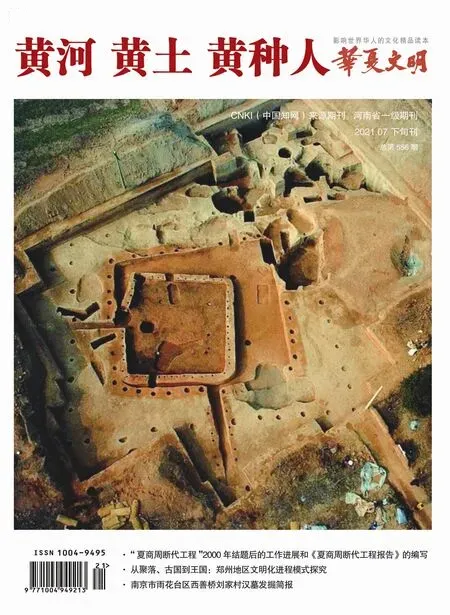从聚落、古国到王国:郑州地区文明化进程模式探究
2021-12-26刘丁辉
□刘丁辉
郑州地处华夏腹地,自然和地理环境优越。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开始,郑州地区就是人类理想的栖息地,环嵩山地带是全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仅在嵩山东南麓就发现300多处旧石器地点[1],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人类演化、发展以及农业起源的关键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郑州地区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与早期发展的核心区。本文拟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郑州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演进路径及成果做系统梳理,以期更加深入和全面地探究其演进模式,进而对郑州地区在中原乃至中华早期文明起源和发展延续中的作用及地位有一个更加清晰和精准的定位。
一、郑州地区从聚落、古国到王国的演进
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发展变化,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提出“邦国—王国—帝国”这一中华文明演进的轨迹,有效推进了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2]。实际上,在邦国文明形成之前,还经历了从聚落到城邦的漫长过程。原始人类从走出洞穴,到聚族而居,再到构筑城邑、建邦立国,经历了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漫长岁月,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走出洞穴——郑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的萌芽
在各种考古遗迹中,聚落遗址所能提供的有关社会形态的信息量是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考古发现表明,不同时期的聚落有不同的形态特征,这种聚落形态的演进,直接体现了社会生产、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推移与发展[2]。
中原地区史前聚落的演变可以分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是中国聚落演变线索最为清晰的地区之一。其中,郑州地区作为中原地区的核心区域,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连贯,可以清楚地刻画出中原地区的史前文明化进程,即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聚落的萌芽,新石器时代中期得到发展,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分化,并在龙山时代出现都邑级别的城邦,其文明之路经历了聚落—王国这样典型、完整的华夏早期文明演进阶段。从都城演进阶段来看,属于五帝时代的有郑州西山、巩义双槐树,属于夏代的有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属于商代的有郑州商城、小双桥,充分体现了郑州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传承性和连续性。
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是早期人类文明的孕育阶段,也是史前聚落的萌芽阶段。以新密李家沟遗址[3-4]为代表的环嵩山地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过渡遗址群是中原地区史前聚落的萌芽形态,这一时期的居民已经发明和使用了陶器,制陶地点很可能就在居住区的原地或居住地附近。陶器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器具。陶器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李家沟陶器的发现,还暗示了当时的人们极有可能已经定居下来,具备了较高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为农业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李家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发现的石器有锛、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磨盘等。从工具的组合看,它们是适应农业生产活动的。李家沟所在的环嵩山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居民,已经具备了原始农业生产的条件,开启了华夏农耕文明之源。
2.聚族而居——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聚落
经过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发展,郑州环嵩山区域形成了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文化聚落群,聚落数量显著增加,是同时期考古学文化中最为成熟的一支。裴李岗文化以嵩山地区为中心,遍布河南全境,无论是聚落布局中的房屋建筑、墓地制度,还是出土器物组合、形制特征都显示出其内部高度的一致性,第一次在时空框架上展现了早期中原文化的聚合力[5],并与同时期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发生了广泛的交流与互动。
就郑州地区而言,它是裴李岗文化的最早发现地,也是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目前在河南发现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有160余处,其中60余处在郑州地区,多分布在新郑、新密、巩义等县市境内。以发现地命名的新郑裴李岗村裴李岗文化遗址,位于嵩山东麓,双洎河转弯处。自1977年发现以来,裴李岗遗址陆续发现有房基、墓葬、陶窑、灰坑等,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其中,典型器物有锯齿石镰、两端有刃的条形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近年来新发现的新郑唐户遗址位于潩水河与九龙河两河汇流处的夹角台地上。遗址面积140余万平方米,其中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6-7],在遗址范围内发现了60余座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文化的房址,这是国内首次发现数量多而集中的裴李岗时期的房址,这些房址分为4个组合,呈圆圈状,中央为大片的空地,这种圆圈状的房屋布局方式开启了仰韶文化时期向心式聚落布局的先河。此外还发现了排水系统、石器作坊、灰坑、窖穴等重要遗迹。郑州地区的新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对研究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房屋建筑方式,特别是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家庭组织结构、农业文明的起源等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3.古国初现——郑州地区仰韶时代聚落的发展
在裴李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在郑州地区分布密集,聚落数量急剧增加,规模急剧扩大,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和最新的考古调查结果,嵩山地区仰韶文化时期的聚落达563处。包括郑州大河村、西山、后庄王、站马屯,荥阳点军台、青台,巩义双槐树等,这些分布相对集中且存在着一定分级的郑州仰韶文化遗址群,是已经具备强大凝聚力、向心力的早期中原文化的核心部分,并促进了中华文明与早期国家在中原地区的形成与发展。
从距今5300年开始,中华文明走上了文明化的快车道,社会演进速度加快,地区间的差异越发凸显,区域文化整合明显,聚落群内部分化和中心聚落的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呈现出大型中心聚落、中型中心聚落、小型中心聚落3级形态,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还出现都邑性聚落或都城,逐渐进入古国(或称“邦国”)时代,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处在这一历史节点的郑州地区聚落有郑州大河村、西山和巩义双槐树遗址。
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内涵极为丰富,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延续时间达3300多年,以仰韶文化堆积为主,尤其是在仰韶文化中晚期,该遗址的发展达到了鼎盛阶段,发现有大量高规格房址、壕沟和彩陶等遗迹遗物,是当时一个规模较大的中心聚落[8]。
由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社会冲突的加剧,作为群体防御设施的“城”开始出现。位于惠济区古荥镇的西山仰韶文化城址,是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史前城址,距今有5300—4800年,面积3.45万平方米,现存半圆形城墙,墙体用方块版筑法分段逐层夯筑,四周有壕沟环绕,还发现有两座城门、一条道路,在城内发现有大量房基、窖穴、墓葬等遗迹。有不少学者根据西山古城的年代和地理位置,推断其为黄帝之都,或是黄帝时代的一处区域政治军事中心[9]。
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河汇流入黄河处的巩义双槐树遗址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双槐树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在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与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根据国内考古学界的论证结果,双槐树遗址是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10],揭开了河洛古国神秘的面纱。
4.走向王国——龙山时代晚期城址群的涌现及发展
龙山文化时期,聚落社会出现了分化,部族之间的纷争也频繁发生,最为突出的聚落变化就是城市群的出现,呈现出城邦林立的社会状态。这时已全面进入了邦国时代,是中国历史开始走向文明以至产生最初国家的重要时期。郑州地区的嵩山城址群是当时中原三大龙山文化城址群之一,也是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分布最为密集的一组,主要有新密古城寨、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新郑人和寨等。
古城寨城址位于新密市曲梁镇大樊庄村,处于豫西丘陵向黄淮平原的过渡地带,西临溱水,南靠丘陵,东面是一望无际的黄淮平原,北面岗地与平原相间。古城寨城址修建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距今有4200—3800年[11]。城址平面呈东西向的长方形,面积17.65万平方米,发现有城门、护城河、大型带回廊的宫殿基址等遗迹,在城内中部偏东北发现了中原龙山时代最早的宫殿基址F1。根据古城寨遗址的规模、位置和文献记载,它应与远古时期的祝融部落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有学者认为其是古史记载中的“祝融之墟”[12]。
一般认为,国家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同时还伴随着社会分工、阶层分化、都邑设置、战争等表征。经过龙山时代的发展,在距今4000年左右,地处“天下之中”的郑州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率先进入了王国时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夏王朝,开始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夏代的政治中心主要围绕嵩山分布,目前学术界一般将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作为夏代的早期都邑遗址。此外,在都邑周围还设置有荥阳大师姑、东赵,新郑望京楼等卫星城址,以拱卫都邑安全。
王城岗遗址位于登封市告成镇西北的岗地上,面积约50万平方米[13]。遗址东部为五渡河,南部为颍河,向南眺望箕山和大、小熊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地理位置十分重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东、西两个小城和一座大城,3座城址年代均为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是目前河南境内发现的龙山文化最大的城址。发现有城墙、城壕、建筑基址、祭祀坑等重要遗迹。王城岗位于嵩山南麓,同历史上的夏部族与夏王朝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根据古史记载,夏部族首领鲧就活动在嵩山一带,鲧之子禹,既是夏部族的首领,也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他的早期居住地和政治中心都在阳城。研究结果显示,王城岗遗址的使用年代在龙山文化晚期,与鲧、禹的活动年代相吻合,当时已经进入了文明时期,出现了阶级分化,甚至出现了国家雏形和政治中心。王城岗小城和大城内发现有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和祭祀坑,还出土有玉石琮、白陶器、青铜容器等遗物,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遗址,显示出其中心聚落的属性。综合来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为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位置正处于夏部族活动的中心区域,规模大、规格高,与诸多文献所载的“鲧作城”“禹都阳城”的位置、年代相合。因此,有学者提出王城岗小城有可能是“鲧作城”,大城有可能是“禹都阳城”所在地[14],因而推断王城岗可能是夏王朝的最早都邑。
新砦遗址位于嵩山东麓的新密市刘寨镇,由外壕、城墙及护城河、内壕三重防御设施组成,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15]12。在内城中部发现一座大型浅穴式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规模宏大,建造考究,可能是一处大型露天祭祀活动场所。新砦遗址出土大批高规格遗物,有子母口瓮、簋形豆、双腹豆、玉凿、青铜容器等。从聚落规模来看,新砦遗址在新砦期聚落群中面积最大、防御设施最为完善、等级最高,应该属于中心聚落,周围其他遗址面积明显小于新砦遗址,属于次级聚落。文献记载“启居黄台之丘”,该“黄台之丘”位于今新密境内的洧水岸边,与新砦遗址位置基本一致。据研究,新砦遗址始建于龙山文化晚期末段,废弃于二里头文化早期,与夏代早期年代基本一致。因此,新砦城址极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权国家——夏王朝的都城,也即是启都夏邑[16]。
郑州地区还是商代早期的核心区域,考古发现的郑州商代遗址众多,比较重要的有郑州商城、小双桥、白寨,荥阳东赵、大师姑等遗址,其中郑州商城是商汤亳都,小双桥遗址是商代隞都所在地。商王朝在前期正是以郑州为中心,不断向四周发展,开疆拓土。
郑州商城遗址面积约25平方千米,城址位于遗址中部偏东,可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17]。内城平面略呈方形,城内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内城和外城城墙外发现有城壕遗迹。内外城之间分布着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包括铸铜、制骨和制陶作坊。在内城中部偏北和东北部一带,是总面积达4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先后发现了50多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在内城内外还发现有大量祭祀遗迹,其中有3处青铜器窖藏坑,出土有方鼎、斝、爵、簋、戈、钺等青铜器,其中以方鼎最为重要,这些青铜器很可能是商王室重器或为商王朝祭祀所用之器,是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都城的实物例证[18]。根据对郑州商城的年代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前后,可知郑州商城始建于商代早期。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的亳在郑国境内,郑州商城东北部的白家庄一带曾出土了大量东周时期带“亳”和“亳丘”字样的陶文。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为150—200年,很可能是商代早期都城商汤亳都所在地[18]。
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的石佛镇小双桥村,总面积为144万平方米,在商代前期遗址中,规模仅次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19]。小双桥遗址中心区为宫庙区,发现有宫城城墙基址和8处夯土建筑基址。在宫殿区南部的祭祀区内,发现有多处祭祀遗迹。遗址范围内还发现有青铜冶铸作坊和制骨、制陶作坊遗迹。小双桥遗址出土有青铜器、玉器、原始青瓷、卜骨等重要遗物。此外,还发现了朱书陶文,这些文字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一脉相承,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商代最早的书写文字。小双桥遗址的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435—前1412年,距今约3400年,是目前发现的处于郑州商城和安阳洹北商城之间的唯一的白家庄期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根据文献记载,商王仲丁从亳都迁至隞地,后世《水经注》《括地志》均认为隞地在荥阳、郑州一带,与小双桥遗址位置相符。根据考古研究结果,小双桥商文化的发展兴盛年代与郑州商城的废弃年代前后衔接,均属白家庄期。因此综合来看,小双桥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商王仲丁之隞都[20]。
二、文明要素在郑州地区的汇集与融合
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是适宜的自然环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领域的进步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的方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1]。从历史和考古研究成果来看,在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王朝的漫长时间里,占据着环境、地理等优势的郑州地区有着强大的聚合力和向心力,通过与周边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汇集融合了各地先进的文明要素,取得了华夏早期文明的核心和领导地位,最终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华夏早期文明高地。
(一)早期物质文明高地
在从聚落向古国、王国文明演进的过程中,郑州地区的先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开发了先进的筑城技术,引领时代的制陶和制瓷技术,发明了丝织法,青铜冶铸技术达到新高度。它们都成为华夏文明发展史中重要的物质载体。
1.中国陶瓷文化的起源地
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碎片[22],并显示出较为成熟的制陶技术,这一发现将中原地区制陶技术向前追溯到距今1万年前。陶器的出现是史前先人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的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证据,引发了农业产生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大变革,形成“新石器早期革命”。
在距今7000—5000多年前,以彩陶为主要特征的仰韶文化进入了黄河流域。作为仰韶文化核心分布区,以郑州大河村[8]和巩义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州地区,正处于彩陶文明发展的高峰期,并在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对外扩张中广泛影响了东方和北方地区,在这些地区的很多遗址都发现了花瓣纹彩陶。仰韶文化彩陶主要是用赭、红、黑和白等色绘饰陶器,彩绘图案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有些彩陶上还绘有太阳纹、月亮纹和星座纹等天文图案,引起了天文学家的重视。这些彩陶图案蕴含了先民们对生灵万物和自身的独特理解。
郑州还是瓷器的故乡。在郑州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夏代生产的原始瓷器,而更广为人知的是,郑州商城出土的商代早期原始青瓷[23]。郑州商城出土的原始青瓷以高岭土为胎,用人工配制的石灰釉施在器表及口沿内,光亮透明,呈现出深浅不同的青色,烧成温度在1200℃左右。该瓷器质地坚硬,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已经具备瓷器的基本特质,可以看作中国瓷器的鼻祖,其生产工艺为后来制瓷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2.中国版筑城墙技术的源头
位于郑州西北郊的西山城址是中国黄河流域最早的城址,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版筑城墙技术的源头。西山城址始建于距今5300年前后,由大型环壕和城墙组成,环壕为人工所挖,城墙是先于地上挖出倒梯形基础槽,然后再分段分层夯筑建造地面墙体[24]。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版筑城墙。随后,版筑技术便广泛扩散至燕山地区、海岱地区、长江流域、河套平原以及东南沿海等广大地区。这一发源于郑州的版筑与基槽技术,显示了巨大的进步性和创造力,在中国古代建城史和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揭开了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序幕,也开启了中国城墙建筑规制的先河,对后世的城市规划和规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还对探讨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和华夏文明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中国丝绸之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家蚕、缫丝织绸的国家,传说生活在郑州的黄帝正妃嫘祖最早开始养蚕取丝织造衣服,因而被奉为蚕神。丝绸与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四大发明一样,都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载体,丝绸起源一直以来都是许多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近年来郑州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早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就开始养蚕制丝,中国丝绸之源在郑州。
20世纪80年代在郑州青台遗址发现了一批距今5500年左右的纤维纺织物,经科学检测,不仅有麻织的布,而且还有蚕丝织的帛和罗,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丝绸实物[25]。最近在荥阳汪沟遗址的数个瓮棺葬中再次发现同时期的四经绞罗织物,又在同时期的双槐树遗址发现了一枚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距今已有5000多年,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造型与现代家蚕极为相似[26]。这一系列考古发现与古籍文献中记载的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的传说的时间、地点相互印证,使嫘祖“育蚕取丝、造机杼作衣”的传说得到实证。同时说明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家蚕饲养和丝绸生产技术,郑州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生产丝绸的地方,也是中国的丝绸之源。
4.中国青铜文明的绝唱
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地区汇集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其中就包括从西方传入的青铜冶铸技术,并迅速开始了其中国化的过程。青铜冶铸技术在中原地区迅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郑州作为当时中原的核心地区,是青铜冶铸技术中国化的桥头堡,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策源地之一。登封王城岗出土的距今约4100年的青铜容器残片[27],是目前在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容器实物。郑州牛砦遗址还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的熔化青铜的熔炉残壁块[28],后来又在稍晚的新密新砦遗址发现了红铜容器残片[15]223-224。这些发现表明,至迟在龙山文化晚期的郑州地区已经率先掌握了复合范技术,从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铸造青铜容(礼)器的先河。
经过夏代的发展,青铜冶铸技术在商代前期已经非常成熟,开创了将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标志的商周青铜时代,达到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第一次巅峰。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郑州商城已发现青铜窖藏坑3处,铸铜作坊2处,青铜器墓葬40余座,出土各类青铜器300多件,其中青铜容器130多件。此外,还有大量青铜工具、小件装饰品和生活用具。郑州出土的青铜器最大的有1米高,最小的仅至盈寸,其中的青铜大鼎有9件之多,为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王室青铜重器。
(二)早期精神文明高地
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郑州地区的先民还在精神文化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不仅占据了中华早期精神文明的高地,而且影响深远,成为华夏文明连绵不绝、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1.中国文字的滥觞地
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出现在商代晚期的殷墟甲骨文中,然而在殷墟甲骨文之前,中国文字的发展演变已经历经了几千年历史,距今9000—7000年的贾湖遗址就发现了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甲骨契刻符号,其中个别符号与商代甲骨文已有相似之处,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学术界普遍认为,按照殷墟甲骨文的成熟程度,至少在夏代或商代前期已经有了初步成熟的文字系统。
除新密市黄寨遗址曾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带有2个文字的卜骨外[29],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两片刻有文字的甲骨[30]。其中一片牛肋骨上有14处刻字,刻字较殷墟甲骨文字稍浅而略粗,表现出原始的契刻特点。由于这是安阳殷墟之外首次发现的商代刻辞,因此对研究殷墟甲骨文的来源和演变有着重要意义。
被认为是商代隞都的郑州小双桥遗址也发现了用红色朱砂书写文字的陶器,目前发现可辨识的朱书文字20多个[31]。用朱砂作颜料书写于陶器表面的小双桥朱书文字,是目前发现的第一批早于商代甲骨文和商周铜器铭文的书写文字,对研究中国古文字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有重要意义。小双桥朱书文字与商代甲骨文及商周金文关系密切,从字形、笔画、结构及表现手法分析,小双桥朱书文字与甲骨文、金文是属于同一体系且存在着承袭关系的古代文字,明显早于甲骨文和金文,是中国古代文字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小双桥朱书文字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435—前1412年,早于安阳殷墟甲骨文。它的发现至少将汉字使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年,即从商代后期提早到商代中期早段,被认为是目前商代最早的书写文字。
2.中国天文学的发祥地
天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当时的人们为了指示方向,确定时间和季节,就通过观察太阳、月亮和星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找出它们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历法,用于指导生活和农牧业生产活动。
郑州是中国天文学的重要发祥地。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上绘制的精美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彗星纹、日晕纹等图像,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生活在郑州的先民就开始观测天象,探索寰宇。这些彩陶上描绘的天文图像也是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种类最丰富的天文图录。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在荥阳青台、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了5000多年前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由此改写了中国天文学史[32]。
荥阳青台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一处大型环壕聚落,发现有三重环壕,总面积约31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有与天文相关的遗迹,其中有按照北斗九星形状摆放的9个陶罐,斗柄向北,东部发现有黄土圜丘,周边分布有同时期瓮棺以及不同时期的墓葬、臼类遗存及祭祀坑等相关遗迹。与青台遗址同时期的双槐树遗址在一处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巨型中心居址的前面发现了以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在建筑中心还发现有一头完整的麋鹿,位置在北斗九星上端的北极附近。这些融合了北斗九星图案的重要建筑等遗迹,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将中国观象授时的历史提前了800—1000年。这些北斗九星遗迹的发现,表明当时的先民已具备了一定的天文知识,通过观察天象指导生产生活,举行祭祀,用以观察节气、祈祷丰收等,并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文宇宙观。这些发现对研究早期天文学和中华文明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3.“天下之中”理念的诞生地
“天下之中”的观念是在中国先民宇宙观的基础上,融合大量的人文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理念[33],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已经发端。随后“中原”“中华”“中国”等概念由此而生,这种理念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行为哲学,以至成为中国古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至今还深为国人所奉守。“天下之中”还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态,古代中国王权非常重视利用“天下之中”观念巩固自身统治。这一理念对中国历史和文明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郑州嵩山地区是“天下之中”理念的诞生地,该理念初步形成于夏代。据文献记载和传说,嵩山一带是夏族先公建立夏王朝的主要活动区域,都城“居天下之中”。根据考古发现,王城岗遗址可能是夏鲧之城,后为禹都阳城,新密新砦遗址很可能与夏代早期都城夏邑有关,或为夏启之居,都在嵩山附近。
郑州嵩山地区“天下之中”的历史地位,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得到更明确的展示,嵩山被商、周人神化与崇拜。有学者认为,在殷墟卜辞中作为商人高祖而被尊崇的“岳”,有可能就是嵩山。西周初年青铜器天亡簋铭文记载“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是说周武王在克商后即来到天室,也就是到嵩山来举行祀天典礼,说明嵩山在周人看来,是人与天沟通的纽带。周公基于天圆地方的认知,以土圭测影而定地中。根据考证,周公测得的地中,极有可能是在阳城,也即是今天嵩山脚下的登封告成镇。考古发现的清华简《保训》与何尊铭文又进一步印证了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后确立以嵩山为天下之中的事实。与此同时,“天地之中”之“中”的观念的提出,成为国家认同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华民族的‘和合’思想则是‘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中’与‘和’形成的‘中和’理念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34]。
(三)早期政治制度文明高地
中国早期的政治制度通常以礼乐制度为核心,萌芽于尧舜时期,初步形成于夏代,发展完善于商代,确立推广于西周。作为夏商统治核心区域的郑州,是中国早期礼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地区。
夏王朝建立于礼制文明中心地位确立的时期,很多初见于陶寺、石峁等夏代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的礼仪性用具得以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出现了表示持有者高贵身份的大型礼仪用具和宫殿建筑,初步形成了具有华夏风格的礼乐制度[35-37]。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夏代早期都城都发现了玉石琮、白陶器、青铜容器等高等级的礼制用器,新砦遗址还发现了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礼制建筑。夏王朝的礼乐制度在以二里头遗址为都邑的时期逐渐丰富和完善,并对周围广阔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开启了传承数千年的中国礼制文明的先河。
在商王朝以郑州商城和小双桥遗址为都邑的时期,夏代开创的以青铜礼器和玉礼器代表持有者身份的礼乐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郑州商城已发现青铜窖藏坑3处,铸铜作坊2处,青铜器墓葬40余座,出土各类青铜器300多件,其中青铜容器130多件,仅青铜大鼎就有9件,为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王室青铜重器,制作精致,反映出商代青铜器制作工艺水平的显著提高。在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游和下游,甚至辽河流域,都有典型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发现,这表明商王朝已经把政治理念和礼乐制度通过青铜器这一物化载体,传播推行到周围方国。
三、结语
距今1万年以来,郑州地区在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这一漫长的文明化进程中,通过对周边各地文明要素的汇集与融合,逐渐显现出领先的态势,最终在夏商周三代文明达到巅峰。可以说,华夏文明形成于此,早期国家出现并发展于此,夏商王朝诞生并定都于此,郑州地区是中华早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的高地。郑州地区连绵不绝、完整有序的文明化链条,构成了中原乃至中华早期文明的演进轨迹,郑州地区在物质、精神和制度方面的文明化成就,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及持续领先做出了突出贡献,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得以延绵不断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