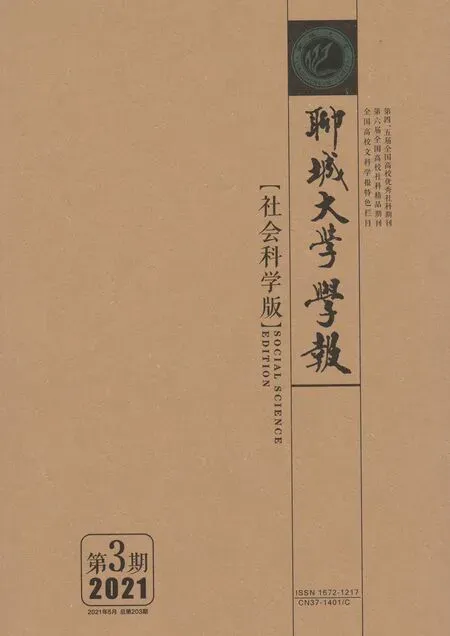“东洋史”及其在中国的回响
2021-12-23王庆婷
王庆婷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关于“中日史学交流”这一重要课题,学界成果斐然。就中日史学交流中的东洋史而言,以黄东兰的《东洋史中的“东洋”概念——以中日两国东洋史教科书为素材》①黄东兰:《东洋史中的“东洋”概念——以中日两国东洋史教科书为素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为代表。该文对东洋史在中日两国教科书中的概念认识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对东洋史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并未全面论及。本文以“东洋史”为考察对象,对其传入、发展和消失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重点探讨它作为一门历史课程的发展情况,以期展现中日史学交流中的一个面向,并进一步窥见影响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内外因素。
一、 “东洋”与“东洋史”
东洋含义的变化是东洋史产生的前提。清朝时,东洋在中日文献中主要指日本。日本从幕府时代中后期起,开始接触到欧洲的知识,并不断被其影响,明治维新后东洋逐渐被赋予新的含义。
在地理意义上,东洋的含义在日本发生变化与西洋含义的变化有关。西洋最初大概指今南洋的西部,而明清以来欧洲来华的传教士自称“西洋人”,“遂使原有西洋一义渐生混淆,而世人对西洋地域之观感亦逐渐变化”②王尔敏:《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6年第15期(上)。,鸦片战争之后,在中日两国,西洋开始专指欧洲,这为赋予东洋更深的含义提供了前提。
在文化意义上,东洋含义在日本的变化受明治维新的影响。明治维新后,日本广泛接触西方文化,赋予东洋新的含义,使其“成为与指称欧洲的‘西洋’相对应的概念,其空间范围也扩大到包括中国和中国文化影响所及的广大地区。”③黄东兰:《作为隐喻的空间——日本史学研究中的“东洋”“东亚”与“东部欧亚”概念》,《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由此,在日本的世界观下,“西洋”与“东洋”成为两大文化圈。东洋的地理意义逐渐淡化,文化意义开始凸显,而此时日本亦在东洋的范围中。
赋予东洋以政治意义与福泽谕吉有莫大的关系。福泽谕吉于1866年开始撰写《西洋事情》,使日本人士广泛了解欧洲文明。1885年他发表《脱亚论》,宣扬“脱亚入欧”的思想,在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脱亚入欧论”以及甲午中日战争的影响,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它将自己从东洋中抽离出来,构建出一种新的历史观。在这一历史观下,东洋代表了一种相对于西洋“文明”世界而存在的“非文明”世界,“日本和西洋有着同等的地位,是亚洲最发达的最高级的国家,而在文化、智识与制度结构上超越了中国。”①陈怀宇:《没有过去的历史:学术史上的日本东洋史——读〈日本的东方:将过去转化为历史〉》,《国际汉学》2009年第1期。这就形成了“日本在面对‘西洋’的时候,它同时还面对着‘东洋’”②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的政治局面。正是东洋概念在日本的衍变尤其是其政治隐喻促使了东洋史的产生。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日本未出现政治色彩浓厚的专门的东洋史著作,东洋史只在一些世界史著作中被提及,其内容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史。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东洋的文化与政治意义在日本的广泛接受,东洋学兴起。东洋学研究旨趣的奠定也离不开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对汉学有一定的修养,但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已经脱离了传统汉学的路径,而是用西洋文明的价值观来看待中国。受其影响,日本学界传统的汉学研究被采用西方研究范式的“东洋学”和“支那学”取代,历史学被包含在“东洋学”和“支那学”中,分别为“东洋史”和“支那史”。③钱婉约:《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这两个学派本质上都是日本在民族主义思想膨胀的背景下为侵华服务的。被称为“东洋史学”创始人的那珂通世是福泽谕吉在庆应义塾的学生,他吸收了福泽谕吉的思想,“从文明发展和停滞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④黄东兰:《书写中国——明治时期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叙述》,载黄东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新史学第4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37页。,提出了“中国文明停滞论”,这一论点影响了其后的东洋史学家,他们中的大部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多表现出批判之意。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为方便对中国乃至亚洲的扩张,日本学界研究东洋史的热情逐渐高涨。1894年那珂通世等建议在中学开设东洋史课程并得到认可,他本人也放弃《支那通史》的写作转而撰写《那珂东洋小史》。同时,日本出现了大量的东洋史著作,如1895年宫本正贯的《东洋历史》、藤田丰八的《中等教育东洋史》、1897年市村瓒次郎的《东洋史要》、1898年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等。东洋史学科在这一背景下诞生。1904年东京帝国大学的“支那史”学科独立,到1910年更名为“东洋史”。自此,日本历史学的学科建制呈现出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足鼎立之势。虽然东洋在地理意义上是指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在内的东亚甚至整个亚洲地区”,但彼时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与课程中的东洋为文化与政治意义上的东洋,主要研究和讲述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各国的治乱兴衰概况,其中并不包括日本。
二 、“东洋史”传入中国
晚清民国时期,中日史学交流频繁,中国派遣大量留学生到日本,亦请日本学者到中国来讲学,往来之间,大量的日本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东洋史由此传入。尤其是自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在政治军事上较日本处于劣势,国内出现了学习日本的高潮,“从甲午战后到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几年间,随着清朝大规模的学制改革,几乎这一时期的所有日本东洋史作品都被译介到中国。”⑤杨鹏:《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迎拒》,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第49页。
第一部被译介到中国的东洋史著作是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此书1898年出版,被用作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影响甚大。1899年,该书由樊炳清翻译并改名为《东洋史要》,由王国维作序①彼时樊炳清与王国维二人都在东文学社从学于藤田丰八。于东文学社刊印。桑原骘藏把亚洲分为东亚、西亚、中亚、南亚、北亚五部分,东亚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主体,东洋史研究范围主要是东亚的历史,兼及中亚和南亚历史中与东亚历史相关联者。王国维的序文写道:
吾师藤田学士乃论述此书之大旨,而命国维书其端曰: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抑古来西洋各国自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今日西洋之文化;我东洋诸国亦自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东方数千年来固有之文化。……其称东洋史、西洋史者,必自国史杂沓之事实中,取其影响及他国之事变,以说明现时之历史团体者也。②王国维:《东洋史要序》,《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页。
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将东洋史理解为把东洋各国作为一个历史团体来叙述的学问,这也代表了近代早期中国学者未明了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仅有对东洋史学理层面上的认识。
但是《东洋史要》全书,其内容以中国史为主体,并按照中国历史划分时代,论述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概况。所以,虽然日本学者对东洋史的定位是与西洋史对应的世界史的一半,在实际写作中却将其撰述为一部中国史。即在日本,东洋史与西洋史在学科性质上都是世界史,所以它不包括日本史,而东亚各国大都受中国的影响深远,日本将中国作为其侵略的主要对象,在撰述时自然以中国史为中心。而近代学者最初并未了解东洋史学科在日本产生的政治隐喻,在中日史学交流过程中直接将其引进。樊炳清翻译《东洋史要》之后,中国的历史课程和著作中开始出现东洋史。
值得注意的是,东洋在中国的地理意义并未随东洋史的传入而改变,习惯上依然称日本为东洋,而日本东洋史中的东洋则是指除日本外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各国,概念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来中国的东洋史研究内容的模糊与混乱。
近代的中日史学交流既有私人交往,又有官方授意。私人交往促进了上述日本东洋史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官方授意则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东洋史出现于学校的历史课程中。
东洋史课程的出现与清末学制改革是分不开的。在学制改革之初,清政府曾派官员赴日考察。其中1899年9月至1900年3月,武昌两湖书院教习陈毅奉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赴日考察,其间他非常关注日本的东洋史研究,并且见到了日本东洋史之父那珂通世,交谈多次。1902年张之洞又派罗振玉等人前往日本考察中小学教育及教科书,罗氏与那珂通世亦有交流。不仅如此,国内学者与日本学者在这些考察与活动中建立联系,也为日本东洋史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帮助。这些活动对于东洋史课程在中国学校中出现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学制改革之初,中小学的中国史课程教材短缺,因东洋史以中国史为中心,故而一些学者认为东洋史实则是中国史。以梁启超为代表,他曾开列“东洋史”书目13种,并根据对这些著作的了解总结出“日本人所谓东洋者,对于泰西而言也,即专指亚细亚洲是也。东洋史之主人翁,实惟中国,故凡以此名所著之书,率十之八九载中国耳。”③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8页。在这样的认识下,出现了一批改编日本东洋史为中国史的教科书,这反映出近代学科划分之后,国史教科书从无到有的历程。
三 、“东洋史”在中国的发展
东洋史的传入一方面解决了国史教科书编纂的燃眉之急,比如我国最早的章节体小学历史教科书,1901年出版的《普通新历史》,是由上海普通学书室据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东洋历史》增删改编而成。有一部分中学在东洋史课程设置之初,直接翻译日本的著作作为教科书,主要以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为主。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由于“惟以外国人而编中国史,则又并于太略,且多舛误”①王舟瑶:《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贰编),《论读史法》,京师学务处官书局印行,1904年。,受到中国学界的诟病,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既伤害民族感情,又不利于本国史的教学。随着国内教科书编写的成熟,中小学改编东洋史以作中国史的现象逐渐消失。
中学的《东洋史》教科书也出现了不同于日本的撰述体系。以秦衡江编著的《东洋分国史》和章赋浏的《东洋史》为代表,他们都将东洋史定义为“除本国史以外的亚洲史”。前者分上下卷,卷上为日本史,卷下为朝鲜史、安南史、暹罗史、印度史、波斯史,凡例称“现今东洋局面最有势力者首推日本,故叙日本独详”②秦衡江编译:《(教科参考)东洋分国史》“凡例”,育材学堂编译所校行,文明书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可见对日本史格外重视。后者作者因不满当时的东洋史教科书“非过于详,即失之略”,写作此书“折衷详略,以求切合教学之用。”③章赋浏编著,陆光宇校订:《东洋史•例言》,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叙述了东洋诸民族以及日本、朝鲜、印度、暹罗、缅甸、安南等国的历史。全书虽未叙述中国史,但仍以中国民族的盛衰作为划分东洋历史阶段的标准。
在大学,东洋史有不同的形式存在,从大的方面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一类课程的总称,以1930年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程为例,其中“东洋史类”下设日本史、日本近世史、朝鲜史、印度史、南洋诸国史、北亚史、回教民族史、欧亚交通史。④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26页,第264页。另一种是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而存在。
东洋史在大学课程中的出现得益于民国时期各高校历史学门与史学系的创建。1912年10月24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发布《大学令》,规范文理科目,后经讨论,完善、修订于次年1月12日公布《大学规程令》,详细划分大学科目,第二章“学科及科目”第七条于文科科目中将历史学门分为“中国史及东洋史学类”与“西洋史学类”。⑤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令(民国二年一月十二日部令第一号)《教育杂志》1913年第5卷第1号,第3页。这条规定说明当时东洋史有一定的影响力,在1940年民国大学教育全面实施统一课程标准之前,有相关教员的学校都开设了东洋史课程,如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厦门大学、大夏大学、成都大学、中央大学、广东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东南大学等学校。
据可见资料显示,这些学校的东洋史课程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各国关系史”,主要有北平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大夏大学、北京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学校。其内容可从以下学校的规定中窥见,如1928年中央大学“东洋通史”讲授内容规定,“本学程以国史为纲,通贯印度、西域、朝鲜、日本、北亚及南方诸国家诸种族史实。遇诸国家、诸种族与宗邦有关系时,即顺叙其前后,如衣挚领,纲举目张,亚洲全史除西亚外略焉可观,又注重其与中国文化上、政治上之关系及其相互之交涉与形势之今昔。”⑥《史地学系历史门课程规例说明》,《国立中央大学一览》,1928年,第9-10页。1931年大夏大学的东洋史课程强调:东洋史以汉族为主,而以满蒙、西藏、朝鲜、日本、安南、暹罗、缅甸、印度、中央亚细亚各民族为辅。其中多数与我国有密切关系,本学程详究其国与国之关系,及各国对文化上之特殊贡献。藉以知东方形式之大略焉。⑦《私立大夏大学一览•文学院课程》,1931年6月,第20页。1931年北京大学的“东洋史”规定课程目的在于“证明历史上中国在亚洲及世界所占之位置,及其对四维民族之关系”⑧《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1年度,1931年9月至1932年6月,第21页。。1934年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开设“东洋各国史”选修课,虽名为“各国史”,实则是“研究东洋各民族文化之演进及其相互影响,特重日本、印度、朝鲜及南洋诸国与我国之关系。”⑨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26页,第264页。这类课程的讲义以王桐龄所著《东洋史》为代表。
二是专指“日本史”,以暨南大学为代表。1930年暨南大学东洋史课程“讲述日本社会发展的各阶段,明治维新以前之社会及文化情况,维新以后的设施,最近资本主义之发展,及其对外方略。”①《国立暨南大学一览•学程一览》(1930年度),第20页。这类课程是采用传统的东洋概念,借用东洋史名称的日本史课程,在学科性质上符合东洋史为世界史分支的设置。
三是“综合的东洋史”,如卞宗孟在东北大学开设的东洋史课程,其内容分四部分:“(一)古代东洋各国兴亡史(二)近世欧人东侵史(三)现代亚洲独立各国史(四)现代亚洲民族复兴运动史。一二两部以国史为联系的中心,作系统的(纵的)研究;三四两部以各民族各国家为单元,作国别的(横的)研究,合之可称为综合的研究。”讲授者称“东洋史作如是之研究者,前无先例。”②臧启芳编:《国立东北大学一览》(1938-1939年度),国立东北大学,1939年,第73页,转引自尚小明:《民国时期的亚洲史教育》,《北大史学》第17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卞宗孟改变了日本的东洋史撰述结构,凸显了亚洲各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使他认识到了日本东洋史背后的蔑华情感与侵华意图。1930年卞宗孟与金毓黻同在东北学社,以共同反抗日本学者在学理层面上将东北同中国的联系割裂开来的企图。金氏曾说:“世界各国学者凡欲研究东洋史,东方学术或进而研究吾国东北史,必取日本之著作为基本材料,断然无疑。以乙国人叙甲国事,其观察之不密,判断之不公,本不待论。是其影响之巨,贻患之深,岂待今日而后见。”③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六卷),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第2页。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有意排斥,若干研究呈现针锋相对之势”④袁咏红:《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迎拒》,《光明日报》2009年6月2日,第12版。,在此形势下,卞宗孟完全摒弃日本东洋史的撰述体系,从民族兴亡的角度讲授东洋史,这是东洋史在中国发展的一大突破。
综上所述,民国大学课程中,东洋史的教学范畴并不统一,折射出中国学界对东洋史的认知差异,在日本留学过的东洋史教员大多接受“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各国关系史”的讲授体系,而本土学者则对其有一定的反思。1940年教育部公布《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实乃民国以来大学教育全面施行统一课程标准之始”。⑤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14页。在这一科目表中,已不见东洋史的踪迹,其相关的内容被列在“国别史”一类中,1944年,教育部重新修订《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科目表》将“国别史”分为亚洲诸国史和西洋国别史,至此东洋史完全被亚洲诸国史取代,在中国大学的历史课程中消失。
四、结语
东洋史是日本受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影响,在传统汉学研究内容的基础上,采用西方的研究路径,产生的一门学科。在清末学制改革中,东洋史由日本移植到中国,对中国历史教学与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其背后的侵华思想引发了中国学者对东洋史的集体抗拒。加之违背了学科分类的科学性,东洋史最终消失在中国历史教学之中。
东洋史中的东洋从来就不是地缘性的认知,这一学科在日本的产生有侵华的政治因素在其中,在中国的消失也离不开这个因素的作用。这门以日本视角构建的学科,本质是“夸大日本的主体性,进而使东洋非主体化”⑥[韩]柳镛泰:《从东洋史到东亚史再到亚洲史:走向认知体系之重构》,《江海学刊》2017年第6期。,而东洋史又是以中国为中心,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的主体性。1940年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其以侵华为根本的认知体系自然引起中国的抗拒。
受日本殖民的影响,朝鲜在1926年京城帝国大学开设的史学科分国史学(即日本史)、朝鲜史学与东洋史学三种。⑦参见[韩]金成修《清史研究在韩国——以东洋史学会与明清史学会为中心》,《清史研究》2015年第5期。朝鲜的东洋史不包括日本史与朝鲜史,可见日本与朝鲜(韩国)的亚洲史研究对象是相对固定的,都是以中国史为中心。相比之下,综观东洋史在中国的发展,则始终未见学者有相关学科建设意识,未能在理论上对这一课程的研究内容进行科学全面的界定,导致其在学科分类上既不完全是中国史又不完全是世界史。学科性质上的混乱成为它在中国历史课程中消失的一个内在因素。
虽然东洋史因种种原因未能留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但并不能因此对它全盘否定,它在近代中国史学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意义主要有二:第一,它对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中的历史分期更是影响深远。近代以来,西方有两种历史分期方法对中国历史学影响较大,其中文艺复兴以来按“上古”“中古”“近古”划分历史的方法,主要受《东洋史要》传播的影响,这一分期形式长期影响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以致傅斯年说“近年来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其纲者。”①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第三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第1225页。第二,东洋史的传入使中国近代学人开阔了历史视野,初步具备了世界意识。②参见朱洪斌:《王国维的第三次学术转向及其学术史意义》,《“中西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11月30日。它一方面促进了中国亚洲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使近代学者在中国史的写作中有意识的涉及亚洲各民族同中国的交往。受东洋史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论述“中国史之范围”时指出“至于二千年来亚洲各民族与中国之交涉之事最繁赜,自归于中国史之范围,固不待言。”③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六》,第2页。王桐龄后来撰述的《中国史》和《中国民族史》在视野上也受到其东洋史研究的影响。
总体而言,东洋史传入中国是近代中日史学交流的结果,它在中国历史教学中的产生与消失不仅仅反映了近代以来学制的变化,更与中国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迎拒密切相关。同时,也反映出近代中国学者不断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对日本乃至世界不断深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