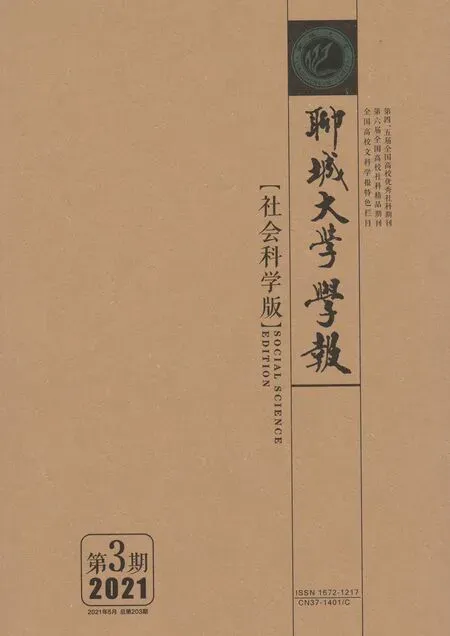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婚姻伦理叙事
2021-12-23宋雯
宋 雯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中国小说中的婚姻伦理叙事,是从五四开始才渐渐增多的。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和“人”的发现,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腐朽封建制度和家族制度的相通之处,因此家庭生活开始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家们的重点审视对象,以往被作家们忽视的婚姻生活也开始成为主要的叙事对象。
在封建社会,进入婚姻的女子往往被视为“传宗接代”,打理家务的工具,地位低下。现代文学时期的很多小说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迫害。此外,现代文学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书写“新女性”婚姻悲剧的小说,它们的叙事模式多为冲破家庭阻力,自由恋爱——进入婚姻,美好幻灭。这体现了作家对封建制度和婚姻的深层次思考,是否推翻了封建婚姻制度,拥有了自由恋爱的权利,就一定可以拥有美满的婚姻生活呢?五四时期的作家给出的答案多是否定的,美好幻灭的结局反映了作家们的悲观态度,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有关婚姻的思考局限。
“十七年”时期的到来中断了作家们对婚姻伦理叙事更深层次的探索。因为这个时期,政治革命话语取代启蒙话语成了文学主流,小说中的婚姻伦理叙事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现代文学作品所没有的“女强男弱”的模式,夫妻关系也都类似于革命同志的关系,婚姻伦理叙事中私人性的一面被完全摒弃。
经过了个人空间被公共空间极度挤压,政治意识形态统领一切的年代,有关婚姻生活的书写在新时期才重归大众视野。这一时期的人们刚从文革中走出,面对旧价值秩序崩溃,同心圆式的社会结构碎裂的现实,人们急需建立新的价值秩序,抚慰内心的创伤。这个新的价值秩序包括传统性别规范的回归,因此在这一时期,传统的贤妻良母型女性又大量出现在作家笔下。不过,新时期小说中的婚姻伦理叙事强调的最多的,还是爱情及两情相悦的重要性。因为爱情是人道主义话语的良好载体,而人道主义话语正是新时期的主流话语。戴锦华曾评价写于这个时期的《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这是一篇典型的‘伦理小说’,作者的旨趣不在控诉‘文革’对人性的戕害,而在于歌颂一个为了爱情放弃一生的物质享受和政治生命,至死不悔的女人。”①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此外,新时期小说中显现得较多的还有职业女性的婚姻困境。这种女性在十七年时期被称为“铁姑娘”,那个时期的小说对她们大加赞赏,她们的婚姻生活虽然没被具体展示出来,但总体来说都比较幸福,因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无形中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至于家庭生活和事业的冲突她们也不必担心,因为遍地开花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减轻了她们在养育儿女和打理家务上的负担。而到了新时期,人们对虚假政治口号和“铁姑娘”式的人物形象已经感到厌倦,职业女性家庭事业双肩挑的困境就被真实呈现出来。
总体而言,新时期以婚姻和夫妻关系为主题的小说数量猛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们对于婚姻、爱情及夫妻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不过,由于80年代的主流话语是以理想主义、人道主义及启蒙话语为主,所以新时期小说中的婚姻伦理叙事还是承担着过多的能指意义。
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比80年代更加宽松,商业大潮来袭,文学的地位逐渐从中心滑向边缘,随之滑落的,还有文科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身份和精英地位。这样一个时期,经济文化都在经历着剧烈的转型,小说中的婚姻伦理叙事又会发生一些怎样的变化呢?
一、“过日子”与平凡之美
在以婚姻为题材或主题的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我们能看到大量有关婚姻日常琐碎的描写,此前虽然也有不少小说写到了婚后生活,可是很少像90年代小说这样,如此不厌其烦地描摹着婚姻生活中的一个个平凡场景。有学者认为,这类作品“似乎少有文化蕴含,都是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但其实他们抓住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关心他们如何去解决身边一个个迎面扑来的矛盾和尴尬,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视角。”①汪政、晓华:《新写实与小说的民族化》,《文艺研究》1993年第2期。
《太阳出世》(池莉)开篇就从赵胜天和李小兰的婚礼写起,重点描绘了他们的婚后生活。新婚不久的意外怀孕,让这对小夫妻不知所措,因为养育小孩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过,两人在经过思想挣扎后决定迎接这个挑战,小说着重展示的,就是这对小夫妻如何在生养孩子带来的系列挑战中,逐渐走向成熟,生孩子在这里具有了成人礼的象征。《纸婚年》(方方)中,维扬和如影的婚姻始于维扬对如影的一见钟情,可是婚后,最初的新鲜感很快过去,原本你侬我侬的两人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过在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却发现,婚姻生活虽远不如想象中的美好,却能给人带来安定的感觉,尤其在见识了朋友轰轰烈烈却分分合合的恋爱之后,他们更加明白了平凡的可贵。从拒绝平凡到接受平凡,这是20世纪90年代婚姻题材小说的一个常见模式。
关于婚姻和爱情的关系探讨,20世纪90年代小说也表现出不一样的特质。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爱情作为人道主义的一个绝佳承载体,是超脱凡俗的诗性存在。因此80年代很多小说都表达了无爱婚姻的痛苦,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是随着商业大潮的来袭,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在社会盛行开来,人们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80年代小说中的婚姻伦理叙事普遍隐含着一种对此岸的排斥和对彼岸的憧憬,那么90年代很多小说中的婚姻伦理叙事则认可了此岸的庸常,认可了不够浪漫却充满烟火气的人生。在80年代的很多小说中,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难以忍受的,无论是作者还是主人公似乎都坚信爱情的存在,而在90年代的很多小说中,婚姻里有没有爱情并没有那么重要,作家们对爱情是否存在也持怀疑态度,踏实“过日子”,似乎就是婚姻的全部,如《不谈爱情》(池莉)中的庄建非和吉玲,虽是因自由恋爱走到一起,可他们之间并没多少爱情可言,吉玲打算利用婚姻实现阶层跨越,而庄建非结婚的原因竟是出于性欲。庄建非的知识分子父母对媳妇很不满意,小两口之间也小摩擦不断,可是当吉玲在一次争吵后赌气回到娘家后,庄建非的生活陷入混乱,因为吉玲虽有时会使使小性子,可是总体来说还算贤惠,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这种平凡却实际的温暖就像白开水,不能给人提供特别的惊喜,可是没它又不行。此外,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一个人社会形象的好坏与其婚姻状况有很大关系,若是婚姻出现问题,这个人的社会形象就会大打折扣,庄建非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出国机会很可能因为离婚而被剥夺,因此一直瞧不上亲家和媳妇的庄建非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会放下身段去亲家家里赔礼。婚姻的重要意义在这里显现出来,它是一个供人休憩的港湾,也是个人形象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些事业有成的精明男性对此认识得很清楚,他们明白,只有平凡的过日子式婚姻才能提供给他们所需的安稳和温暖,因此在选择妻子时,他们摒弃了爱情的因素,把贤惠、顺从当成首要的择偶标准,他们希望妻子能够牺牲自己的追求,以他们的前途和事业为中心,所以我们看到,在《首席》(张欣)中,野心勃勃的江祖扬拒绝了两位才貌双全的优秀女性的追求,选择了一个极其平庸的妻子,“以安家事,为的是不受琐碎之累专注于大事。”①张欣:《爱又如何,恨又如何》,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纪念》(殷慧芬)中的狄仁,不但事业有成,在情场上也是春风得意,可拥有不少情人的他,妻子却老实普通,对情人,他调情手段高超,对妻子,他也哄得很好,这不仅是因为婚姻出问题会影响仕途,还因为他的确需要一个让他感到安稳和放松的栖息地。在这些小说中,婚姻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意义,爱情的缺失并没让婚姻中的双方感到痛苦。从作家的平民立场以及他们在小说中流露出的叙事态度上,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种虽缺少爱情,却踏实安稳的婚姻状态的认可。婚姻是秩序的一部分,婚姻的稳定代表着秩序的稳定,对安稳婚姻的认可和赞赏,也是对秩序的礼赞。
二、“爱情神话”的建构与解构
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婚姻伦理叙事,大都从浪漫彼岸降落到了现实此岸,似乎大家都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婚姻,不过就是搭伙过日子。可是,依然有一些作家在凡庸的婚姻生活中努力找寻爱情的身影,他们似乎想要印证,爱情不一定都是惊世骇俗的,不一定只存在于诗意的彼岸,在烟火气十足的此岸,在平常的一粥一饭中,同样可以有爱情的存在。迟子建就是一个这样的作家,《亲亲土豆》中,秦山和李爱杰这对勤劳的农民夫妇夫唱妇随,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厄运突然到来:秦山患癌了。妻子并没有退缩,而是要找“看病最好的医院”给丈夫看病。秦山心疼妻子,找借口向妻子要了几百块钱,偷偷为妻子买了条漂亮旗袍,之后就独自离开了医院。过冬的时候,秦山把旗袍拿了出来,给了妻子一个意外的惊喜,“秦山说,‘明年夏天你穿上吧。’‘明年夏天——’李爱杰伤感地说,‘到时我穿给你看。’‘穿给别人看也是一样的。’秦山说。”②迟子建:《亲亲土豆》,《迟子建小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75页。简单朴素的几句对话,却蕴含了夫妻炽热深厚的情感。《清水洗尘》中,夫妻间的故事都是在儿子天灶的眼睛中展开的,夫妻感情在儿童视角下显得含蓄又有趣,村里有名的风流寡妇让天灶父亲帮忙去家里修理东西,天灶母亲不乐意但又不好直接表现出来,直到丈夫很快回家后才放下心里的紧张,而她的紧张正来自于对丈夫的爱。作者在最后用含蓄的手法写了天灶父亲回家后和母亲在洗澡桶里的恩爱场景,使得小说中洋溢着一种爱情的暖意。这些小说中的爱情都是构建在凡庸婚姻生活上的“爱情神话”,与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情相比,这样的爱情显得不够浪漫诗意,却自有一种温暖妥帖,这些作品告诉我们,简单平凡的日常生活,也是可以滋养着爱情的,就像不起眼的土地,也能开出美丽的花朵。
迟子建小说中的 “爱情神话”都建立在此岸的日常生活之上,平实安稳,充满着烟火气,而另一些作家,譬如北村,则固执地坚持“爱情神话”只存在于浪漫的彼岸,认为真正的爱情是天塌地陷,轰轰烈烈的,与一地鸡毛的琐碎日常毫不相关。不过这样的“爱情”因为太过理想化而显得脆弱不堪,它只适合生长在纯净的彼岸,一旦被移植到现实此岸,它就会像水土不服的娇艳花朵一样迅速枯萎。《周渔的火车》中,美人周渔和电工陈清的爱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显得超凡脱俗。在这个美女们纷纷想着嫁大款的年代,周渔却义无反顾地爱着资质平平的普通电工。这种超越功利的爱是生长在彼岸的“爱情神话”,比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都显得更纯粹。80年代小说中的人们可能在相爱和结婚的时候不看重金钱和名利,但是崇高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仍是他们所注重的,而周渔对陈清的爱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与那种婚前爱得死去活来婚后就激情褪去的婚姻不同,周渔和陈清在婚后依然延续了他们的爱情。陈清意外身亡之后,周渔仿佛也跟着死去了,如果不是陈清的情人李兰意外浮出水面,陈清和周渔的“爱情神话”恐怕会永垂不朽了。可是随着李兰的出现,陈清的另一面被揭开,我们发现陈清和周渔的爱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李兰一语道破天机:“那种看起来非常伟大的爱情是经不起轻轻一碰的。”①北村:《周渔的火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58页。《玛卓的爱情》中,班花玛卓之所以选择其貌不扬的刘仁,正是因为刘仁的浪漫。刘仁曾在三年间给玛卓写了一千多封情书,并在一个下午,坐在山上,把情书一封封读给玛卓听,这成了他们爱情的开始,也成了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记忆。可是,当他们修成正果走进婚姻后,他们却发现两人的关系变得尴尬,从婚后第一夜起就变得无话可说,婚姻生活中的做饭、买菜等日常事务好像对浪漫爱情构成了巨大的破坏,那个坐在山上读情书听情话的美好下午再也回不来了。正如刘仁对两人婚姻的分析:“我们仿佛是两个只适合于在山上过爱情生活而不适于在房间里过婚姻生活的人”。玛卓也对二人关系做了反思:“他的信一停止,我们的新婚之夜立刻出问题,看来,我们是无力生活的人,我们生活在纸上,生活在猜想中更合适一些。”②北村:《周渔的火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03页。作家在这些小说中思索了这样一个问题,不受世俗污染的浪漫爱情,究竟真实存在,还是人们心中的美好幻象?从故事的发展和结局来看,作者显然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
与上述小说相比,20世纪90年代一些小说中的“爱情神话”被摧毁的原因显得更加具体,这与90年代文学更加注重和现实的对话有关。90年代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物欲泛滥,拜金主义盛行,那些拥有爱情基础但缺乏物质基础的婚姻,在这样的社会显得不合时宜,曾经海誓山盟的爱情,在实实在在的物质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冬至》(张欣)中的“小米”和“大胡子”情投意合,他们的婚姻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两人原本都是超凡脱俗的理想主义者,信奉“爱大过天”,可是贫困使得两人的婚姻生活落魄狼狈,“小米”也不再相信“有爱就有一切了”,因为窘迫的经济状况让他们无法维持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因此这个曾经爱情至上的“小米”真诚告诫自己的女性朋友:“有钱会出现两种情况,幸福或者不幸福,没钱就只有一种情况,不幸福。”③张欣:《张欣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年,第36页。
在这节所列举的小说中,只有迟子建构建的“爱情神话”延续到了最后,这或许源于作者对爱情的日常属性的认可,而其他小说的作者就像一个玩积木的人,先是用五颜六色的积木搭起了一座辉煌巍峨的“爱情”城堡,然后再毫不留情地将其推倒。
三、各式各样的“围城”困境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自由伦理个体叙事”增多,与“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的“人民伦理大叙事”不同,“自由伦理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迹或经历的人生变故”。④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6页。因此比起以往,20世纪90年代以婚姻为主题和题材的小说不仅数量颇丰,而且在叙事形式和叙事内容上也显得更加多元,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各式各样的“围城”困境。
(一)“皮格马利翁”与理想伴侣的塑造
《逐鹿中街》中的英语教师陈传青,38岁才经人介绍和丧偶的市建局干部古子铭结了婚,在外人眼中,陈传青贤惠能干,她把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丈夫的穿着打扮也在她的精心设计下越来越有风度。最初,古子铭对这样的日子很是享受,可慢慢他就感到了不对劲,因为妻子似乎把婚姻做成了一个光鲜的模子,他的一切都要与这个模子吻合才行。他有种被控制的感觉,开始有意识地反抗,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到点就回家,宁可和单位里的小姑娘呆在一起互诉衷肠。控制欲旺盛却仍想保持自己贤妻形象的陈传青和觉醒了的古子铭开始了一场“逐鹿中街”的好戏,陈传青的跟踪和古子铭的反跟踪好像变成了一个夫妻间心照不宣的游戏。从岁月静好到风声鹤唳,这场婚姻的最大问题,在于陈传青过于想把古子铭塑造成她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可是她忘了,丈夫不是一个任由她雕塑的泥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大活人。
《周渔的火车》(北村)中的陈清也是一个外人眼中的模范丈夫,虽然相貌和能力都平平,可是深爱周渔。周渔也知道陈清不够出色,但对于把爱情看得重于生命的她来说,有情饮水饱。周渔习惯了陈清对自己的爱和付出,要求陈清按她的方式好好爱她,做个她心目中的理想丈夫。陈清出轨李兰,实际是他对周渔一直要求他扮演的理想伴侣角色的厌倦和反抗,就像他对李兰吐露的:“光靠我一个人是做不成好丈夫的,是周渔使我这样的,是她把我塑造成这样。”①北村:《周渔的火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57页。他之所以跟李兰在一起,是因为他可以卸下沉重的“理想丈夫”假面,享受做回真实自我的感觉。
《逐鹿中街》中的陈传青和《周渔的火车》中的周渔实际上都在不经意间充当了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她们对丈夫的想法和喜好毫不关心,只想把丈夫塑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样。由于一直活在妻子的塑造和期待中,一直活在模范丈夫的面具之下,丈夫的“原始自我”被深深压抑,这必然会导致最终的反抗。
(二)平波水面,波澜深藏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从一个“熟人社会”慢慢转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们的婚恋行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过去的“熟人社会”,婚恋双方大都互相知根知底,而随着“陌生人社会”的到来,人们对自己的婚恋对象可能了解并不多,周边同事的撮合或一次意外的邂逅,就能匆匆促成一段婚姻,他们结婚可能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为了符合世俗的期待,他们往往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感和好恶,就算真实的婚姻状况千疮百孔,也要维持光鲜亮丽的表面。
《云破处》(池莉)里的金祥和曾善美,是一对公认的模范夫妻,在同一家单位工作,在外人眼中,他们琴瑟和鸣,就像“一列安全行驶了十好几年的老火车。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开动,”②池莉:《云破处》,《花城》1997年第1期。可是命运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曾善美意外发现金祥是多年前毒死自己父母的凶手,笼罩在他们婚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随之揭下,两人多年来积压的对对方的不满像沉寂多年的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可是到了白天,他们依旧一起上班,一起在外人面前扮演着模范夫妻的形象。
《藤之舞》(黄蓓佳)中的陈兆华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富有奉献精神的能干贤妻,她帮汪齐云从一个小资料员一步步转变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副教授,“文革”期间她也不畏艰辛陪丈夫下放,并主动承担了大部分体力活,可是这种从一开始就不平等的“女强男弱”式婚姻让思想传统的汪齐云倍感压抑。他们回城后,汪齐云成了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陈兆华却风光不再,并因操劳过度成了一个外形粗糙的黄脸婆,两人在婚姻中的地位颠倒了过来,汪齐云开始反抗妻子对自己命运的操控,在柔弱女子李小娟身上找到了作为强者的自信,开始了他的“第二春”,与此同时,他和妻子开始暗藏机锋互相攻击,儿子一语中的:“你们是两根纠缠在一起的藤,彼此盘绕,又彼此依附,彼此仇恨,却彼此从对方吸精吮汁。”①黄蓓佳:《藤之舞》,《钟山》1992年第3期。汪齐云和陈兆华的婚姻,在外人眼中可能幸福美满,因为他们患难与共,妻子没嫌弃丈夫比自己出身低微,还一直尽心尽力帮助丈夫,而丈夫发达后也没把这个“糟糠妻”休掉。可是在表面的风平浪静下,却积蓄着丈夫多年来的不满和怨恨。
《云破处》和《藤之舞》中的婚姻告诉我们,风平浪静或许只是表面现象,不管下面暗流如何剧烈翻涌,作为岸边人的我们都不得而知。很多人为了符合世俗的期待,纷纷戴上面具扮演模范夫妻,甚至在家里,独自面对伴侣的时候也不摘下来,可是一直被压抑着的不满和矛盾都在双方心里越积越深,一旦达到极限,定会像火山一样爆发。但是他们的爆发也有可能是悄无声息的,因为他们习惯了伪装和掩饰,再痛苦,也不想让外人看到他们千疮百孔的婚姻现实。
(三)欲望的压抑
在经济不够发达的从前,人们普遍把生活视作人生的目的,把赚钱视作手段,而物质充裕的现代社会却将之颠倒了过来,工具理性战胜了人文理性,人们的生命力也在无形中被“阉割”了。如果婚姻中有一方是这样的人,而另一方依然保有生命活力,那么这样的婚姻注定不幸福。《双鱼星座》(徐小斌)中卜零和韦的婚姻就是如此。卜零是个富有浪漫气息的女子,和这个充满商业气息的世俗社会显得格格不入。丈夫韦在有钱有权之后,就越来越厌烦这个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妻子,比起夫妻间的精神交流,他觉得跟欢场女子直截了当的交换更加轻松。卜零处境很尴尬,在外人眼中,她是养尊处优的阔太,可在家里,她不但没有掌握经济大权,还伺候男权思想严重的丈夫。小说特意写到韦性欲贫弱,没有生育能力,他在家经常做的不过是看看电视,这其实象征了韦的生命力被阉割。面对这样的丈夫,生命力旺盛的卜零是痛苦的。小说细致描绘了卜零的性心理及被压抑的情欲,她之所以会对年轻帅气的司机动心,出现杀夫的幻觉,都是情欲被极端压抑的表现。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婚姻题材小说中,作者多借婚姻传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对于婚姻中“性”的问题却多避而不谈。而随着90年代逐渐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思考“性”与婚姻的关系。对于现代人来说,婚姻中的“性”绝不仅是一个传宗接代的手段,它关系着夫妻关系的和谐与否,关系着人的正常欲望是否得到合理释放。不过,一些人已习惯了压抑自己的本能欲望,他们的婚姻也因此受到影响。《桑烟为谁升起》(蒋子丹)中的萧芒深爱丈夫宁羽,可他们在性事方面并不和谐。因为萧芒幼年丧母,没人对她预先进行婚前性教育,少女时期的朋友小赖的那些给她留下肮脏印象的描述,便成为萧芒对这类生活的全部认识。这导致在做爱的时候,她总是带着一种难言的犯罪感。她“习惯了在黑暗的掩护下恪尽妻子的义务,除此之外她几乎从来没有沉醉其中。她只是静静地躺着,听任丈夫动作。”②蒋子丹:《桑烟为谁升起》,《收获》1994第1期。这样的性生活完全不能满足血气方刚,对“性”充满热情的宁羽,这正是他在外面找情人的缘由。可以说,“性”的不和谐是破坏他们婚姻的最重要原因,而这又是由萧芒对自己本能欲望的极度压抑所引起。小说清晰呈现了萧芒是如何一步步压抑自己的欲望,被传统性别规范的。她一直想维护自己的纯洁好女孩形象,殊不知这样的形象实际上是她的“伪自我”,她的“原始自我”已被压抑到她自己都看不到的地方。
(四)为自己画地为牢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传入,20世纪90年代的作家们对“女性解放”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中国的“女性解放”历来都不太彻底,“它始终与超越性别的民族、阶级的革命实践相伴生,”③杨永明:《女性解放的社会怪圈》,《海南师范大学》2006年第3期。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可很多女性的主体意识还没有真正觉醒,她们不但认可男权社会的性别规范,还把这些加诸在她们身上的规范都视为内心的道德律令。如《杀人》(万方)中的乡下女子六团,在父母做主下稀里糊涂成了亲,成亲后,丈夫很快回城打工去了,把六团留在乡下伺候自己的母亲。六团黑天白夜小心服侍婆婆,认为这是媳妇的本分;怀上的孩子不小心掉了,则把一切责任都归到自己头上,更加忘我地为这个家干活。丈夫鞠生从来都没有爱过六团,可是当他向六团提出离婚,六团却坚决不肯。因为世俗道德、舆论和娘家人都不允许她这么做。来自她身边的声音都是这样的:“这方圆百里的谁不知道老鞠家的六团,活得多有名分。”“就是死,你也要死在鞠家。”①万方:《万方文学作品选》,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在这样的声音下,“六团”像个狂热教徒一样,将封建礼教视为最高信仰来捍卫,她认定,活着或死都要当鞠生的媳妇。虽然她的婚姻早已有名无实,可为了一个“正室”的名分,她宁愿守活寡也坚决不同意离婚。六团对名分的执着,害了自己的一生,也害了丈夫的一生。
都市女性同样面临着女性意识尚未觉醒这个问题。如《冬至》(张欣)中的叶冰琦是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一个白领,可是她的思想和那些旧式女子并没有太大区别,她认为女人最重要的价值就是青春和美貌,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就是结婚生子,虽然她婚前就明白未婚夫是个爱流连花丛的花花公子,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和他结了婚,一是因为她依赖性强,认为婚姻可以满足她的物质需求和情感需求;二是因为她把世俗舆论看得无比重要,认为没有婚姻会让别人看不起。婚后的她温柔贤惠,却被花心的丈夫嫌弃不够野性,她的第一次婚姻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可是她并没有醒悟,又匆匆嫁给一个有钱的香港老男人,却没想到他在香港还有家。在小说最后,当叶冰琦的另外两个女性好友再次见到她时,她已不复当年风采,表面的风光下是无尽的辛酸。
上述小说中的婚姻悲剧都是因女性把男权文化规范内化为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甚至信仰而引起,她们缺少的不是外在的自由,而是内在的自由,因此她们在婚姻里给自己画地为牢,是那些把笼子打开,也不肯飞出去的鸟儿。这些小说深刻表明,若女性的主体意识不觉醒,“女性解放”永远也不可能彻底。
文学和时代从来都密不可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不断繁荣的大众文化与都市文化时,世俗意识开始走进历史舞台”,②梁鸿:《重回语文学——地方、空间、词语与当代文学》,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06页。以市民为主体的“个人生活”已经不再是某种“被遮蔽的空间”,因此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婚姻伦理叙事摆脱了意识形态重负,以往小说中被忽略或一笔带过的日常琐碎和各类婚姻困境被放大凸显了出来。这些作品没有负载过多的能指意义,却充满了对平民真实生活的人文关怀,具有很强的现实指涉性,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心态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