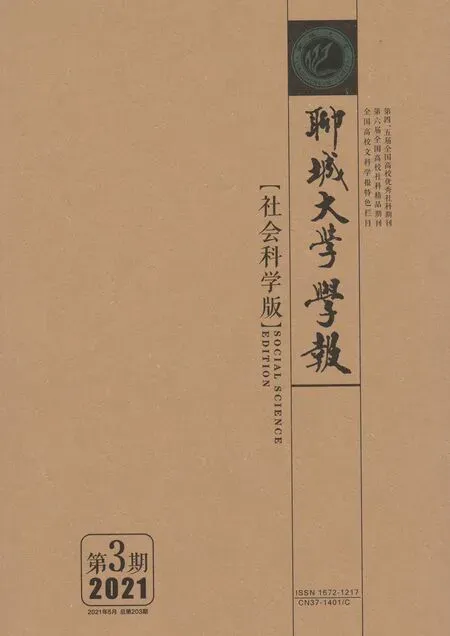天水与建康:南宋《选诗演义》对六朝作家的评论
2021-12-23卞东波
卞东波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选诗演义》(下简称《演义》)是南宋江西人曾原一编撰的一部《文选》注释书,也是现存宋代唯一一部《文选》注本,因很早在中国本土失传,仅有朝鲜古活字本庋藏于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学术界对其了解不多,近来始有学者对该书加以研究①参见芳村弘道:《孤本朝鮮活字版『選詩演義』と撰者曾原一について》,载立命馆大学中国艺文研究会《学林》第46-47号,2008年(中文版《关于孤本朝鲜活字版〈选诗演义〉及其作者曾原一》,金程宇译,《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南宋選學書『選詩演義』考》,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62号,2010年(中文版《南宋选学书〈选诗演义〉考》,金程宇译,《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選詩演義』考異—宋代『文選』版本としての『選詩演義』—》,载立命馆大学中国艺文研究会《学林》第53-54号,2011年(中文版《〈选诗演义〉考异——〈选诗演义〉所用〈文选〉的版本问题》,第九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南京大学,2011年8月)。卞东波:《曾原一〈选诗演义〉与宋代“文选学”》,原载《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后收入所著《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演义》对《文选》中39家诗人,165首诗,进行了或详或略的解说。《演义》的注文除了引用唐代的《文选》李善注、五臣注,还引用了宋代陈宗道、林实夫、曾醇、黄文雷、利登、黄应龙、敖陶孙、谢子允②芳村弘道先生对这些人有详细的考证,参见芳村弘道:《关於孤本朝鮮活字版〈选诗演义〉及其作者曾原一》。等人对《选》诗的见解,此外还有曾原一本人对《选》诗的评论,而且这部分评论较有文学批评价值,也体现了一位南宋学者对六朝作家作品的认知,是研究宋人六朝文学观的比较集中的材料。下文笔者拟对《演义》的六朝诗人评论略加探讨,以见其批评之特色。
一
《演义》是《文选》诗的再选本,从《文选》诗人中选择了39家作为典范,这些诗人大部分是曾原一等南宋士人欣赏的汉魏晋宋诗人。《演义》所遴选的诗人大部分仅选诗一首,选诗比较多的诗人是:阮籍十七首、曹植十三首、谢灵运十三首、陆机九首、颜延之九首、刘桢七首、郭璞七首、鲍照七首、左思五首,其中《文选》所选的阮籍《咏怀诗》十七首、郭璞《游仙诗》七首全部收入。《演义》入选作品的数量与这些诗人在《文选》入选作品的多少是成正比的,也与这些诗人在六朝文学史上的地位直接关联。
《演义》的选诗也受到文学史“经典化”的影响,即《演义》遴选的《选》诗绝大部分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认可。锺嵘《诗品序》云: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①锺嵘著,曹旭笺注:《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459页。
锺嵘本段所列的作品都是六朝时公认的名篇佳作,“陈思赠弟”即曹植《赠白马王彪》,“公干思友”即刘桢《赠徐幹》,“子卿双凫”即苏武《别李陵诗》,“叔夜双鸾”即嵇康《赠秀才入军》,“茂先寒夕”即张华《杂诗》三首之一,“安仁倦暑”或指潘岳《在怀县作》,“景阳苦雨”指张协《杂诗》十首之一,“越石感乱”即刘琨《重赠卢谌》或《扶风歌》,“景纯咏仙”即郭璞《游仙诗》,“王微风月”可能指王微《养疾》,“谢客山泉”即谢灵运的山水诗,“叔源离宴”可能指谢混《送二王在领军府集》,“鲍照戍边”即其《代出自蓟北门行》,“颜延入洛”即颜延之《北使洛》,“陶公咏贫”即陶渊明《咏贫士》,“惠连捣衣”即谢惠连《捣衣》。以上作品,除“陈思赠弟”“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王微风月”“叔源离宴”“陶公《咏贫》”,《演义》未选外,其他作品悉数入选。
皎然《诗式》卷三《论卢藏用〈陈子昂集序〉》:“若但论诗,则魏有曹、刘、三傅,晋有潘岳、陆机、阮籍、卢谌,宋有谢康乐、陶渊明、鲍明远,齐有谢吏部……”②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21页。本处提到的作家除陶渊明外,全部入选《演义》。秦观《韩愈论》:“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③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51页。以上提到的诗人,除陶渊明外,亦全部入选《演义》。于上可见,作为“选本的选本”的《演义》遴选作家作品的标准是建立在历代公认的经典作家作品之上,所选之诗亦是六朝诗歌中的精品。
曾原一对汉魏六朝作家评论的一个原则就是知人论世,不以人废言。《演义》选了旧题李陵所作的《与苏武三首》,李陵因为投降匈奴,很多人对其不齿,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白居易《汉将李陵论》:“忠、孝、智、勇四者,为臣为子之大宝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汉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四者无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④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89页。不过,即使如此,《演义》还是入选了其诗,并称:“其辞意悲惋,读之令人凄恻,亦得诗人兴致者,故不以人废言。”
六朝诗史上,有不少有争议性的诗人,除了李陵,陆机、谢灵运都因为卷入政治,最后死于非命,曾原一对他们都抱以同情。《演义》卷下评陆机《猛虎行》云:
夫机以孙皓暴虐之余,而远来于洛,犹不息恶木,不饮盗泉,而远寻也。太康以后,晋政日乱,奸慝四出,其猛虎、野雀乎?机之所作,殆有感于当时。吁!知其难为音矣。轻于择主,委身于成都王颖。颖岂可依息者乎?卒杀其身,亦可悲也已。
曾原一对陆机的评价还是比较平实的,对陆机“卒杀其身”的悲惨命运,发出“亦可悲也已”的同情之音。曾氏对陆机早年在东吴乱世之时,“犹不息恶木,不饮盗泉”表示赞赏,但对陆机到洛阳后,在政治上犯了幼稚病,“轻于择主”,投靠成都王颖则持批评态度,认为司马颖是不可“依息者”。相对于元人盛如梓的批评,曾原一的评论可谓平和之论,盛氏云:
陆机、云兄弟托身于成都王颖,叶石林《避暑録》云:“当危乱之世,贪权喜功,虽欲苟全可乎?”斯言是也。谓卢志称其父祖名,机怒,亦称卢之父祖名以报。河桥之败,志因谮之,父子兄弟皆诛死。余谓此说非也。使机当日无此语,亦被祸。不思机乃亡国人至中原,在贾谧二十四友之列,及诛谧,机亦有功,人得以议之。伦将簒位,机在中书,九锡文、禅诏皆与焉,减死徙边,遇赦而止。晋室多故,机不识时,昧乱邦不居之戒,欲取功名、图富贵,愚矣!①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上,《丛书集成初编》第32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5页。
盛氏对陆机兄弟的遭遇毫无同情,认为其悲惨的下场完全是由其“贪权喜功”自致的。在“晋室多故”的多事之秋,陆机既不能审时度世,如张翰等人抽身而退,又不能理解孔子所说的“乱邦不居”(《论语•泰伯》)的告诫,反而深度参与到西晋政权的政治搏杀中,其结果也可想而知。陆机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欲取功名、图富贵”的政治野心,最后只能身败名裂。盛如梓用“愚矣”二字对陆机盖棺定论,这应该是后人的普遍看法,但曾原一却能施之同情,这也是曾原一高于世人之处。
曾原一对谢灵运亦抱同情之态度,《演义》卷下评谢灵运《登池上楼》云:
读灵运诗,其归隐之意,锐矣。然决去不勇,卒至以诬谮死。能言而不能行,抑可悲也已。
曾原一对谢灵运的悲剧命运判断非常准确:“能言而不能行”,其评谢氏《登石门最高顶》亦云:“灵运此志高矣,惜其不能蹈也。”“不能蹈”也即“不能行”之意。可见,这是曾原一对谢灵运一贯的看法。“能言而不能行”也是六朝世族致命性的通病,虽然他们出身高贵,也掌握一部分政治资源,但其实他们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身不由己,特别是谢灵运所处的刘宋时代,次等寒族势力兴起,皇权有意识地对世家大族进行压制。这时的世族早已没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荣耀和实力,稍有不慎,便有生命之虞。谢灵运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亦是一曲门阀世族的挽歌。
《演义》卷下评谢灵运的《初发石首城》引用曾氏友人黄文雷之说,对身处晋宋之际的陶渊明、谢灵运进行了比较:
陶、谢二公皆晋大臣子孙,故于兴废之际,不无慨然之怀。靖节萧然远引,微见其意于纪年之间,遂获全其身名。康乐佯狂,盖亦自知其不免,而有不能不然者。观其诗,常若有彷徨之忧迫乎其后,夭伐之虑,盖自叹之。至于跨山越海,求避于世,卒之不能自脱于祸,抑可悲已!有客三诗,于二王之后来助祭也,曰:“在彼无恶,在此无斁。”盖易代之间,谗疑易构,彼其成周之盛际也,故能容二代之遗绪,而意爱形焉。否则恶斁生,而刑祸作矣。况乎世臣之家,挟才负气,如康乐者哉!必也以道自乐,情累俱遣,如靖节可也。
“抑可悲已”与曾原一使用的话语如出一辙,可见当时的江西地区诗学圈应是共享一套诗学话语与诗学理念②黄文雷为江西旴江人,与曾原一同为江西人,且曾结为诗社。刘壎《隐居通议》卷九载:“希声名文雷,自号看云……尤长于诗,诗尤妙于长歌行。同时乡里以诗名者,碧涧利履道登、白云赵汉宗崇嶓,俱为社友,然品格俱不及公。赣之宁都有苍山曾子实原一、抚之临川有东林赵成叔崇峄,亦同时诗盟者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4页。。黄文雷的这段分析有一定的深度,首先他指出“易代之间,谗疑易构”,是一个产生悲剧的时代。如何在此“兴废之际”出处,是对士人智慧的考验。陶渊明和谢灵运都身处改朝换代之际,同时他们的出身背景有一定的相似性,“皆晋大臣子孙”,故而对时局都“不无慨然之怀”。其实陶渊明在退隐之前,经历也比较复杂,他先入桓玄幕,后又成为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可以说比较深地涉入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之中,但他最后能够全身而退,其原因一方面是陶渊明的个性使然,“性本爱丘山”,无法拘縻于宦海的“尘纲”之中;另一方面也和陶渊明对政治的敏感有关,从他所作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等诗可见,他当时游走于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军事重镇荆州和京口,接触到不少政治内幕,他敏锐地感觉到政治风暴即将到来,果断地急流勇退,这比谢灵运贪恋官位、权势高明了许多,用黄文雷的话说就是,陶渊明能够“以道自乐,情累俱遣”。“道”既是抽象的天道,也可以理解为人道,即陶渊明所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情累俱遣”指的是,陶渊明能够抛弃外在的束缚,“萧然远引”,回归内心。谢灵运的悲剧则在于,因为其出身“世臣之家”,加之性格上“挟才负气”,故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很率性地“自免去职”(《归去来兮辞序》),所以处于政治磨心中的他,自然“常若有彷徨之忧,迫乎其后”,这些忧虑都呈现在他的诗歌之中。他也试图通过游山玩水,“求避于世”,分散刘宋统治者对他的戒心,但“卒之不能自脱于祸”。谢灵运的悲剧是时代和性格双重原因导致的,而最大的悲剧则在于谢灵运无法超脱命运的枷锁,诚如方东树所言:
陶公说不要富贵,是真不要。康乐本以愤惋,而诗中故作恬淡;以比陶公,则探其深浅远近,居然有江湖涧沚之别。①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29-130页。
其实谢灵运也是聪明之极的人,之所以不能全身而退,就因为做不到陶渊明的“萧然远引”——“不要富贵,是真不要”,只能“故作恬淡”。故他的境界与陶渊明相比,有“江湖涧沚之别”。吴淇亦云:
陶、谢齐名,于理各有所见。谢见得深,陶见得实。谢见得做不得,止于狂;陶见得做得,可称狷。论文各诣其至:陶诗和雅,《大雅》之才;谢诗悲愤,《小雅》之流。若以谢多涩句、晦句,以为不如陶之通陗,不足与言诗矣。②吴淇撰,汪俊、黄进德点校:《六朝选诗定论》卷十四,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第348页。
古人对谢灵运的观察还是比较透彻的,很多看法都有相似之处。吴淇也谈到谢灵运“见得做不得”,与黄文雷所说的“自知其不免,而有不能不然者”,异曲同工。吴淇也说到谢氏的“狂”,但黄文雷明确指出其是“佯狂”,故很多事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吴淇认为“谢诗悲愤”,方东树也说到“康乐本以愤惋”,他们都读出谢灵运诗中郁郁不得志的一面,从而与“陶诗和雅”形成鲜明对比。
陶、谢优劣论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公案,但历代的意见差不多一致,即陶优于谢。黄文雷扬陶抑谢还比较平和,而且也主要是从人格出发,而大多数宋人和清人对陶的揄扬要明显超过谢,而且认为谢的人品与诗品皆不及于陶③刘克庄:《戊子答真侍郎论选诗》:“世以陶谢相配,谢用功尤深,其诗极天下之工,然其品故在五柳之下,以其太工也。优游栗里,僇死广市,即是陶谢优劣,惟诗亦然。”(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一百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223页)则刘克庄认为,谢灵运在人品和诗品上都不如陶渊明。。其实在文学史上,陶在宋代之前,地位一直不及谢,谢的光芒完全掩盖住了陶,但到宋代陶的地位隆起后,谢的文学史地位开始下降。《演义》大量收录谢诗,可见曾原一对谢灵运的文学成就还是承认的,黄文雷对谢灵运的评论也比较中肯。
除陆机、谢灵运之外,曾原一对六朝文学史上其他因为政治斗争而早殒的诗人也抱以同情。《演义》卷下评刘铄《拟行行重行行》云:
年几弱冠,即中奇祸以殒其身。诵此诗谓不先察其几,不可也。文灿绚目,有俊气,可想其人。为世所疾,宜哉!虽然,是诗谓之“拟古”,则未也。
刘铄为宋文帝刘义隆第四子,文帝被弑后,支持元凶刘劭,后刘骏(即孝武帝)平定叛乱后,刘铄被杀,年仅二十三岁。据《南史》卷十四本传记载,铄“未弱冠,《拟古》三十余首,时人以为亚迹陆机”④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5页。,甚至不少学者认为其拟诗的成就超过了陆机,萧绎《金楼子》卷三《说蕃》称:“《拟古》胜于士衡矣。”⑤萧绎撰,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69页。《演义》所选的诗正是这三十余首拟古诗之一。曾原一对刘铄评价非常正面,不但对其悲惨的身世寄以同情,而且称其“文灿绚目,有俊气”,可与明清人所言的“姿态虽浓,要不失纤冶”⑥萧统编,孙鑛评、闵齐华注:《文选瀹注》卷十五,天启二年乌程闵氏自刻本。,“颇饶秀笔,异于时趋”⑦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95页。相呼应。在评语最后,曾原一认为,刘铄此诗虽名为“拟古”,但其气格则非古制。相似的看法也见于评鲍照《拟古》之语中:“今此诗气伟语俊,而谓之‘拟古’,非也。”也就是说,在曾原一心目中,“拟古诗”的气格应趋于古朴,用清人吴淇的话说就是:“拟诗必兢兢以古人之格调字句,寸寸摹仿。”①吴淇撰,汪俊、黄进德点校:《六朝选诗定论》卷十三,第331页。而刘铄的拟诗“有俊气”,鲍照的“气伟语俊”,与“古人之格调字句”并不相侔,故认为他们的“拟古诗”其实并非是真正的拟古。
二
《演义》对六朝作家的评论,颇有一些不同于主流看法之处,其中对曹植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评价非常高,锺嵘《诗品》曾云“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②锺嵘著,曹旭笺注:《诗品集注》(增订本),第118页。。这种评价主要是基于曹植的文学成就,但似乎也掩盖了曹植在其他方面的弱点。《演义》评曹植《杂诗》云:
皆植被罪时。“西北”一章,叹自己文华之美,而君莫我用,此心欲见君以自明也。“南国”一章,叹己之美,而人莫我里言也。“仆夫”“飞观”二章,李善引《责躬》诗“愿家矢石,建旗东岳”之句,谓与此同意,盖得之矣。读植太和二年上疏,言“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陛下出不世之诏,臣効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东属大司马”云云。植之诗,其作于此时乎?“仆夫”一章,言江介淮泗为吴而作。“飞观”一章,言西南望,兼吴蜀言也。吁!植岂能真慷慨为国任事哉?废弃无以自见,欲希功名,以庶几文帝之我进耳。独不思太祖时,尝因曹仁为关羽所困,以植为南中郎将,遣救仁。植将行,太子饮,偪至醉,不能受命,悔而罢之。夫文帝为太子时,犹不欲植司兵,以偪吾位。今兄弟正自蒙疑,乃欲得兵权以为用,文帝奚肯授之?子建亦痴拙甚矣。
曹植《杂诗•飞观百余尺》一诗幻想着能为文帝所用,征讨吴蜀。这种想法反映了曹植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曾原一对曹植的政治才能颇为怀疑,“植岂能真慷慨为国任事哉?”曾原一还认为曹植亦没有自知之明,曹丕未即位时,对曹植已经有所忌惮,现在即位后,更不授“兵权以为用”,遂毫不留情地批评曹植“痴拙甚矣”,芳村弘道先生认为曾氏的评论“十分辛辣”③见芳村弘道:《南宋选学书〈选诗演义〉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7辑,第354页。同时芳村先生认为:“由于《演义》将《杂诗》其五、六的创作时期定为明帝太和二年之作,故作出的曹植对文帝抱有期待是愚蠢的评价并不恰当。”。在《演义》中,曾原一对曹植负面评价比较多,曹植《赠丁仪》注云:
子建此诗,岂作于赞立之时耶?前四句言汉之将衰,如凝霜之秋。“朝云”而下,言魏诸人出为时用,因已讽仪之辅己也,意谓他日不忘仪,所以重结仪心也。事未成,而先出此语,宜益重文帝之疑,而至于杀仪也。史称子建任性而行,观此诗,信矣。
此处又批评曹植在政治上“任性而行”,这应指其早年的行为,与《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所言相同:“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④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57页。曾原一对曹植的评论主要是基于其性格,对于曹植在文学上的成就,他也是认可的,曹植《七哀诗》注云:“至于抑扬开阖,妙得三百篇之遗音。”在曾原一所撰的《选诗演义序》中,我们可知《诗经》是曾原一的最高诗学标的,此处评论曹植之诗“妙得三百篇之遗音”⑤大部分宋代学者对曹植还是持正面的评价,亦有其他宋人认为曹植之诗得《诗经》之遗韵,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观子建‘明月照高楼’‘高台多悲风’‘南国有佳人’‘惊风飘白日’‘谒帝承明庐’等篇,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与三百五篇异世同律,此所谓韵不可及也。”(陈应鸾:《岁寒堂诗话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18页),也是对曹植文学成就的承认。
纵观中国文学史,论者对曹植一般都持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对其创作成就有微词者鲜少,但对曹植的为人处世,也不乏批评的声音存在。最早在《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论》中,陈寿就说:“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然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①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第577页。陈寿一方面肯定了曹植的才华,另一方面对其不能“克让”②关于曹植是否“克让”的问题,古人有不同的看法,如王通就认为:“陈思王可谓达理者也,以天下让,时人莫之知也。”(《文中子•事君篇》,王通著,张沛校注:《中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3页)又说:“谓陈思王善让也,能污其迹,可谓远刑名矣。”(《文中子•魏相篇》,《中说校注》,第201页)刘克庄云:“曹植以盖代之才,他人犹爱之,况于父乎?使其少加智巧,夺嫡犹反手耳。植素无此念,深自敛退,虽丁仪等坐诛,辞不连植。黄初之世,屡有贬削,方且作诗责躬,上表求自试。兄不见察,而不敢废恭顺之义,卒以此自全,可谓仁且智矣。文中子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让。’真笃论也。”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前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刘克庄与曾原一差不多同时,但关于曹植的见解几乎完全相反。李梦阳云:“且以植之贤,稍自矜饬,夺储特反掌耳。而乃纵酒铲晦,以明己无上兄之心。”(《空同集》卷五十《陈思王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第464页)同是“纵酒”,古人视为“任性”“轻脱”,而李梦阳则认为是“铲晦”之举,而且曹植也根本“无上兄之心”。,最终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携隙”(即嫌隙),似有不满。类似曾原一式的批评,在历史上也不少,如明孙能传《剡溪漫笔》卷一“曹子建”条云:
曹子建才名甚盛,几于夺宗。今观其初得邯郸淳甚喜,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是何轻脱乃尔。只此一事,伎俩可知。阿瞒宠之,不过悦其浮藻,为丁、杨辈摇惑耳。其后屡经贬徙,犹上疏求自试,欲突刃触锋为士卒先,尤不解事。汉河间、北海,稍涉嫌疑,辄以酒色狗马自污。植乃高自矜许,撮风后之奇,接孙吴之要,欲持此安之乎?其制于忌兄,而郁邑发疾以死,无足怪者。③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1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26—327页。
孙能传此段对曹植的评论也是不留情面。他认为,曹植虽然“才名甚盛”,但其实为人“轻脱”,难成大事。其后“屡经贬徙”,但仍上疏希望被用,是其不识时务的表现。孙能传称其“尤不解事”与曾原一所言的“痴拙甚矣”意思差不多。曹植最后“郁邑发疾以死”,与其“高自矜许”的性格不无关系。这一点,明人亦有批评:“子建任气凭材,一往不制,是以有过中之病。”④陆时雍:《诗镜总论》,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05页。清人继续抨击曹植的节操:
东汉尚风节,子建之精光浩气长留天地间者,在文辞不在风节,偶持风节,要不因此增重也……子建德薄,于魏有罪,于汉无功,惟是自少至终,篇籍不离手,文则《两京》具体,诗为百代宗工,是能立言不朽,视立德、立功曾何悬别?⑤严可均:《曹子建集校辑叙录》,载朱绪曾:《曹集考异》卷十一,《丛书集成续编》第12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211页。
这段话也肯定了子建的文学才华,但对其“风节”,则持否定态度,甚至用“德薄”来形容他,用词不可谓不重。可见,在褒扬曹植的传统文学史书写中,也存在批评曹植的潜流,曾原一的《演义》则是这股潜流中比较早的代表性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曾原一对六朝诗人大多抱同情之态度,但对曹植却以批评为主。
三
阮籍是“正始之音”之代表,曾原一对阮籍的评论也有非常深刻之处⑥笔者曾在《曾原一〈选诗演义〉与宋代“文选学”》中对这一点有所讨论,但限于篇幅未及展开,本文在前文基础上进一步申论。:
世谓阮步兵酗酒废礼,往往斥讥之。余读步兵秋怀诸将(引者按:疑当作“诗”),率皆悼魏室之沦夷,疾权臣之奸宄。考之于传,司马昭欲为炎求昏[婚]于步兵,醉六十日不得言乃止。何曾欲杀之,昭又每为之曲护,盖拳拳于步兵者。步兵父文学决起,从魏世受主知,步兵之心盖在魏,伤时之不可为,而又惧昭之逼用己也,故为放诞,酗酒废礼以自昏污,步兵岂真不知礼哉?箕子佯狂,心乎仿之。论籍之心,当与渊明不书宋年号者同。渊明位卑,足易决去,步兵名父之子,名显魏朝,昭复知敬,决去未能,故曲自免。其视王蠋绝脰等事,则籍犹未勇于死矣。九锡之文,醉不欲为,强迫之甚,乃不得已为之。使籍能死,不举此笔,籍不得为全美乎?扬雄著《法言》,可谓明礼法矣;美新之作,甘为不道,又非籍之强为比也。而自韩昌黎、曾南丰诸公亦加敬之,无君果可以《法言》恕乎?步兵心乎王室而疾奸臣,顾乃以托酒自污者罪焉,视雄不当末减耶? (《演义》卷下《咏怀诗》其十七评语)
这段话可谓是知人论世之说,曾原一从阮籍诗歌中看到他的政治态度,“率皆悼魏室之沦夷,疾权臣之奸宄”,这其实也是需要一番勇气的,但“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阮籍只能“托酒自污”。世人从前从一种浅薄的意识形态角度指责阮籍“酗酒废礼”,其实未能探得阮籍的心曲,曾氏称“步兵岂真不知礼哉”,实际上认为阮籍这些破坏虚伪礼教者,才是礼的真正守护者①魏禧云:“然观藉呕血骨立,及沈醉六十日,却司马氏婚,则未尝不明于大义。”见《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一《阮籍论》,《续修四库全书》第1408册,第306页。。“故为放诞,酗酒废礼以自昏污”,实际上是阮籍在残酷的魏晋易代之际政治夹缝中的自保行为,宋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阮籍负英伟之才,生非其时,陆沉于俗,而世之论者遂以为放旷不羁之流,而礼法之士至于羞谈之,岂不过哉……籍于是时傥不自混于酒,崭然出其头角,则死于强臣之手也必矣。②谢逸《读阮籍传》,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3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卷2877,第255页。
曾氏又将阮籍与两位历史人物陶渊明及扬雄相比。阮籍与陶渊明同处易代之际,因为家世的原因,对旧朝皆持同情之态度。据沈约《宋书•陶潜传》载:“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③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8页。尽管沈约的记载不一定符合史实,但宋人特别是南宋人基本相信这一点。《演义》云:“论籍之心,当与渊明不书宋年号者同。”④后人亦有相似的看法,胡缵宗《阮诗跋》云:“籍也惓惓王室,立心略同于靖节,故与嵇叔夜并称。”(《鸟鼠山人小集》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79页)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张云璈云:“阮籍既为大将军从事,闻兵厨酒美,复为校尉。此阳欲远昭而心实附之,乃其用心诡谲之处……十七首中以为恐罹祸患、常怀忧思,此固籍之心事,以为绝不附司马,吾未能信。”张云璈《选学胶言》卷十“阮籍附司马氏”条,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3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09-310页。曾氏认为,阮籍“故为放诞,酗酒废礼”行为背后表现出的“心乎王室而疾奸臣”与陶渊明不书刘宋年号乃是同一心迹,其心理逻辑都是对现存统治秩序的不合作。这段话实际上也是为千百年饱受诟病的阮籍任诞行为正名,同时也深入到了阮籍痛苦挣扎的心灵世界。
在文学史上,宋人也经常将阮籍与陶渊明相比,同时看到他们行为的相似点,如阮籍与陶渊明皆嗜酒:
余尝疑阮嗣宗、陶渊明平生沉酣于酒,而出处去就之际,皆合于道。其为诗,虽汪洋澹泊,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是以知二子负英伟之才,而世不我用,托于酒以自遁者也。⑤谢逸:《黄君墓志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33册,卷2875,第235页。
谢逸观察到阮、陶二人“平生沉酣于酒”,但其背后则“托于酒以自遁”,就是通过饮酒逃避现实,避免与现实发生冲突。此论也是正确的,但观察似没有曾原一的深刻。谢逸认为阮、陶的嗜酒似乎是一种消极的避世,而曾原一视域中的阮、陶行为则明显有一种对现实的不满。
曾原一又比较了阮籍起草《为郑冲劝晋王笺》与扬雄作《剧秦美新》二事,并认为阮籍是“强迫之甚,乃不得已为之”,而扬雄“美新之作,甘为不道”,两者表现出节操与出处的高下之别。明陈德文云:“籍白眼睨俗,非苟禄之子云。”①陈德文:《刻阮嗣宗集叙》,《中华再造善本•明代编》集部第417册,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范钦、陈德文刻《阮嗣宗集》本影印本。亦是褒阮贬扬。对阮籍作《为郑冲劝晋王笺》之事,曾原一持一种同情的态度;在比较阮、陶时,也将阮、陶持平论之,而没有斥阮扬陶,这其实与宋人的看法并不相同,如刘克庄就认为:
自有诗人以来,惟阮嗣宗、陶渊明自是一家。譬如景星庆云、醴泉灵芝,虽天地间物,而天地亦不能使之常有也。然嗣宗跌宕弃礼法,矜傲犯世患,晚为《劝进表》以求容,志行扫地,反累其诗。渊明多引典训,居然名教中人,终其身不践二姓之庭,未尝谐世,而世故不能害。人物高胜,其诗遂独步千古。②刘克庄注,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校笺校》卷二十三《赵寺丞和陶诗序》,第4000页。
从上面的话语可以明显看出,刘克庄是抑阮扬陶,恰好他也论述到阮籍生平中“弃礼法”与“晚为《劝进表》”两点,但观点几乎与曾原一相反,都持贬斥的态度。他看不到阮籍“弃礼法”背后的人生坚守,而认为是“矜傲犯世患”,即对社会主流价值的侵犯;而作《为郑冲劝晋王笺》并非是阮籍“不得已为之”,而是为“求容”,即为了求得司马氏的宽容而主动为之,其结果必然是“志行扫地,反累其诗”,也就是说,其行为严重影响到了阮籍人格与文学的品位。曾原一认为阮籍其实是“真知礼”者,而在刘克庄的眼中,陶渊明才真正是“名教中人”。因陶“终其身不践二姓之庭”,故“人物高胜,其诗独步千古”,批评的角度仍然是政治道德及立身大节。
从曾原一对曹植、阮籍一贬一褒的评论可以看出,他评论六朝诗人能够不囿于传统之说,而且能从自身的视角或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从而做出独立的或具有同情心的判断。
四
曾原一《选诗演义序》云:“自渊明外,愈日以降,朓、约诸子,靡风遄起。”又卷下鲍照传注云:“《选》诗止于此耳,皆靡丽矣。”故他认为齐梁诗风“靡丽”,不是他欣赏的自然朴实的上古诗歌。在《演义》中未单列齐梁诗,但实际上他还是选了二位齐梁诗人,即谢朓和江淹。曾原一虽选谢朓之诗,但也是有批评的,《演义》卷下谢朓《高斋闲坐答吕法曹》注云:“渊明‘云无心而出岫’,平易中下字有精密工[夫]。玄晖‘窗中列远岫’,山谷尝证其非。求巧字过,则义多舛戾,大抵然也。”山谷之论见于《山谷集》卷二十六《书徐会稽禹庙诗后》中:“越州应天释希圆,姑苏人,避地甬东。所居小房琅琊山顶也,山下有井,井有鳗鲡鱼;水有盈缩,与江湖相应,甚多灵怪。按《尔雅》:‘山有穴为岫。’今季海诗云:‘孤岫龟形在’,乃不成语。盖谢玄晖云‘窗中列远岫’,已误用此字,季海亦承误耳。”③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第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58页。显然谢朓等人将岫理解为了山峦,为了刻意“求巧字过”,结果导致“义多舛戾”。这个批评可谓一语中的。又评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云:“诗语典丽,亦铺画有委折,然气则隘矣。”所谓“文章以气为主”(曹丕《典论•论文》),谢朓之诗虽然在诗语和描写上都很好,但诗歌呈现出来的格局,即“气”,则是狭隘的,这也决定了其诗歌的品格不可能成为上品。《演义》卷下评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云:
“天际”“云中”“余霞”“澄江”等句,属餍于人,玄晖盖以是名者。呜呼!美矣,丽矣!唐子西有言:“诗至玄晖,句益工,然渐有唐风矣。”允哉!“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其又唐之晚靡者欤?
此诗是谢朓的名作,特别是“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二句成为千古名句,曾原一亦用“美矣,丽矣”来形容,但他关心的问题是谢朓诗中已经出现唐诗的元素,其所引唐庚之语见于唐庚《唐先生文集》卷九《书三谢诗后》:“诗至玄晖语益工,然萧散自得之趣,亦复少减,渐有唐风矣。于此可以观世变也。”①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39册,卷3009,第341页。谢朓诗中有唐风在宋代成为普遍的见解,如赵紫芝《秋夜偶书》云:“玄晖诗变有唐风。”②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5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卷2841,第33859页。最著名的是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之语:“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③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张健:《沧浪诗话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52页。曾原一则在此基础上,认为谢朓另外两句诗“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已有晚唐诗的风味。这里“靡”与曾原一反对的“靡丽”意义相同,也是宋人所说的“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④吴可:《藏海诗话》,郭绍虞辑《历代诗话续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1页。;“晩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⑤《诗人玉屑》卷七“铢两不差”条引《诗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7页。;“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⑥《诗人玉屑》卷十六“诗小巧无风骚气味”条引《诗史》,第358页。。曾原一的观察非常犀利,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六朝》:“六朝句于唐人,调不同而语相似者……‘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晚唐也。”⑦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155页。清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谢玄晖集,佳句不一……‘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皆中晚入妙谛也。”⑧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58页。胡应麟、叶矫然应该不可能看到《演义》,但他们英雄所见略同,而且曾原一更早发现这一点。
江淹是《演义》所选的最后一位诗人,《演义》仅选择了他的名作《杂拟诗三十首》中的三首,即《拟陶彭泽休致归耕》《拟谢康乐游山》《拟休上人怨别》。在江淹小传下,有曾原一对江淹《杂拟诗三十首》的一段评论:
凡拟诗如学画,当识家数。然必得其笔意,运规制于胸中,自尔似乃可。若展己画,临貌虽似,亦下矣。诸拟作凡被所道字语,俱不用,而气味逼真,乃为佳耳。陆士衡,晋人也,拟作已不免用其语字,且引所历事迹。至文通不惟用字,且用其题,又用其意,其能酷似,是盗之,非拟也。然灵运以后,气日益漓,休文、希范辈靡浅不堪读,如玄晖者且作俑巧丽,以胚晚唐之风,而文通独欲追魏晋诸公逸驾。尚哉,斯志!姑用掇数章之尤以表焉。
“家数”是南宋人常用的一个批评概念⑨关于“家数”的内涵及其演变,参见蒋寅:《家数•名家•大家——有关古代诗歌品第的一个考察》,载《东华汉学》2012年6月第15期。又参见张健:《沧浪诗话校笺》引荒井健日译《沧浪诗话》云:“家数原有家传的术数、秘数之意。作为文艺批评术语,指形成个人样式或一家样式之文学家的等次。”(第491页)又引黄景进《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第五章《严羽的实际批评》:“所谓家数,应指各时代,各重要诗人之特殊风格而言。”(第493页),论诗当识家数也是当时诗学批评家一种共同的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严羽,他多次说到这个问题:“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⑩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张健:《沧浪诗话校笺》,第490页。;又云:“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市缣帛者,必分道地,然后知优劣,况文章乎?”[11]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张健:《沧浪诗话校笺》,第765-766页。严羽是从诗歌评论角度立论的,而曾原一提出“凡拟诗如学画,当识家数”则是从创作的角度出发的。创作拟诗时,“必得其笔意,运规制于胸中”,一定要对模拟对象的体性、气象、格调、风格等个性化的特征(“规制”)了然于胸才能创作成功,否则即使是语言上很相似,也终非杰作。曾原一认为,拟诗的最高境界是完全不用模拟对象使用过的语言,但是“气味逼真”,在风格上神似,就是最高境界。曾原一举出六朝文学史上的两位写作拟古诗的大家,一为陆机,一为江淹。陆机拟古诗已然不免用前人成字,而江淹则不仅用字,且蹈袭题目和诗意,故不如陆机,但相比沈约(休文)、丘迟(希范)、谢朓(玄晖)等人流于“靡浅”和“巧丽”,江淹独能拟古,意在追摹古风,故相比侪辈,仍有所长。文学史上,锺嵘《诗品》以降对江淹《杂拟诗三十首》评价一向比较高。不过,曾原一欣赏江淹拟诗并非是从其拟古成功的角度,而是因其模拟的对象都是“魏晋诸公逸驾”,与当时沈约、丘迟等人“靡浅”、谢朓“巧丽”的美学风格完全异趣。换言之,曾原一对江淹的接受完全基于其本人的文学史观与诗学趣味,这可以从《演义》所选的魏晋诗人与江淹模拟的对象多有重叠看出来。从曾原一对《演义》卷下所录最后一首诗江淹《拟休上人怨别》的评论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是诗轻俊,见者悦之,可知美矣。然古诗至此,体其极矣乎!寄之卷终,有识者于此焉感之矣。虽然,犹厚于“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等语也。
江淹的拟诗非常成功,以至于后人都以此诗为惠休原作,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二“江淹拟古”条云:“《遯斋闲览》云:‘《文选》有江淹拟汤惠休诗,曰: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人遂用为休上人诗故事。’仆谓此误自唐已然,不但今也。”①王楙撰,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2页。曾原一对此诗非但没有批评,而且认为“此诗轻俊”,并且将其作为“古诗”之体所能容忍的极致或极限,再模拟下去,将尽失所以为古体的特征了。细绎“体其极矣”之语,且亦含自江淹以下之诗无复足观之悲慨,古诗之比兴风旨自此以后隐没式微之怅恨。曾原一亦承认江淹拟古诗的“殿军”位置,从某种程度上亦可言达到极致,但仍从属于“退化”的诗学观,江淹的拟古诗是无法超越真正的古诗的。所以将此诗作为压卷之作,也体现了曾原一的一片苦心,即曾原一树立的“古诗”典范至此终结,以后的诗就走上了他所反对的“靡丽”之途,或者谢朓“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之类晚唐风格之路了。这里又和上文所引的曾原一认为谢朓之诗“作俑巧丽,以胚晚唐之风”相呼应,也和《演义》黄崇实序中所言的“近世推尊晚唐,往往盛唐已不读,建安、黄初,谁复睨之,况三百篇邪”之语相照应。
《演义》的诗学批评体现出一个环环相扣的内在结构。《演义》以汉魏晋宋诗为学习对象,正是对南宋晚期诗坛流行的晚唐诗的回应与反动;在实际的诗人与诗作批评中,曾原一也清晰贯穿着其文学史观与诗学理念。《演义》中未选陶渊明诗,但我们从《演义》的批评中时时可以看到陶渊明的影子,以其来作为衡量六朝诗人的一个标杆②《演义》未选陶诗,可能曾原一打算另编一部陶诗选注本。曾氏对陶渊明评价非常高,其《选诗演义序》云:“渊明于诗道渐靡时,卓然得天趣,盖中兴于诗者。”详参笔者《曾原一〈选诗演义〉与宋代“文选学”》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