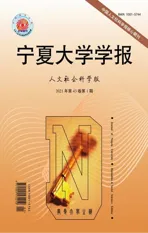马洛对戏剧人物个体性的建构:从神祇的衰落到自我的演进
2021-12-22周雪凝
周雪凝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戏剧人物的个体性建构是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相较于古希腊与中世纪戏剧呈现的新变革。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 年)作为“大学才子派之首”的重要戏剧成就,就在于他对人物“欲望”“意志”“潜能”的充分塑造。“个体性”是理解马洛作品和整个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特征的重要维度。所谓戏剧人物的个体性,本文主要指人物摆脱超验力量与世俗规训,以自我为参照成为独立行动的个体,并发挥意志能动性的本质特性。黑格尔(Hegel)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了个体所展现的“自在且自为”的存在性质[1],对个体性的阐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针对文艺复兴戏剧呈现的个体化趋向,20 世纪的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总结了“个体行动”[2]的概念、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提出了“自我形塑”[3]的理论,都指出了戏剧人物朝向个体自我的变革趋向。在国内研究中,最早研究马洛的学者冯国忠在文章《谈马洛的三部悲剧》[4]中论及了人物自我发展的强烈愿望,对本文具有借鉴意义。进入21 世纪,马洛戏剧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部分学者针对人物的“激情”“欲望”等领域展开探究,但视角大部分局限在感性经验领域,未涉及超验和经验、灵魂与身体、欲望与意志之间的转变关系,未触及“个体性”这一关键要素。本文力图探寻文艺复兴时期神学、哲学、科学等领域的变革所引发的戏剧革新,充分挖掘马洛如何依托时代语境,重新建构人物的精神秩序。首先,马洛试图通过新科学知识、世俗化理念重新塑造人神关系,剥离人物信仰中的超验支配力。其次,他尝试以感性经验代替超验精神,实现对人物身体的感官与欲望的探求。再次,马洛从塑造感性欲望的领域过渡到建构人物自我意志的阶段,创造出具有“绝对自我”的个体性人物,最终使人类超越神祇占据精神秩序中的绝对地位。马洛对戏剧人物的个体新建构印证的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追求无限自由与试图进行自我确证的现代化进程。
一 神祇的衰落:剥离人物信仰中的超验力量
戏剧人物如何认知环绕自身的外在力量,是马洛重塑人物精神秩序的首要环节。马洛对戏剧传统中支配人物行动的超验性力量进行了消解,这是个体性建构的首要步骤。他重塑了人物对于神祇的认知,并重置了人神之间的相对位置。
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戏剧中,戏剧中的超验性力量与人物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超验性力量主要呈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古希腊、罗马戏剧中源于神话传说的神祇,他们以神谕、预言、昭示等方式支配着人物,建构起超验性的宗教空间。二是命运观念,其自古代社会就已存在,在基督教一教独大的中世纪历史中也占据重要位置。命运一直呈现为超然于个别神祇之上的毁灭性力量。三是中世纪流行的基督教神学信仰体系,其主要体现在神秘剧和道德剧的创作中。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科学等领域对于人类主体性的发现,逐步使上述戏剧中的人神关系发生了变动。笛卡尔(Descartes)于1641 年出版的《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与霍布斯(Hobbes)1651 年出版的《利维坦(Leviathan)》等学术著作中都包含着对人类自我主体的发现。马洛作为英国近代早期具有先驱性质的剧作家,也顺应这一文化变革趋势。他在戏剧中利用新科学思维、世俗王权观念以及新教伦理观念,重塑了人物对于神祇的认知。
第一,马洛运用新科学思维改变了人物的思想观念。新科学主要指流行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基于新科技成果的哲学理念、科学思维与人文知识。玛丽·T.克拉内(Mary Thomas Crane)在《马洛与新科学(Marlowe and the New Science)》一文中指出,在16 世纪的英格兰,“新科学”首次出现在受过教育的伦敦人关于数学领域和科技领域的问题中,他们探讨在过去半个世纪拥有的新科技,并尝试去调和新理论与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原理的关系[5]。马洛作为剑桥大学神学院的硕士毕业生,正属于这类知识分子。他转变了“身体元素说”的宗教意涵,赋予其人类目的论的世俗意味。例如,在《帖木儿大帝》中,有一段著名的“元素论”称,“大自然构成我们的四大元素,在我们胸中彼此管制又相互冲突,教导我们所有人拥有进取精神(《帖(一)》,2.6.58-60)”[6](剧本引用参考《马洛戏剧全集(Christopher Marlowe,The Complete Plays),企鹅出版社2003 年》,为简洁起见,按照剧目中译的首个汉字进行标注,如《帖木儿大帝(第一部)》简称为《帖(一)》,《爱德华二世》简称为《爱》,以此类推)。这段文本表明,虽然戏剧中沿用了代表中世纪宇宙秩序的人体元素论,但马洛更强调的是人类的自主创造力与进取精神。除此之外,戏剧中频繁展示出天文、气象、地理的知识性元素,它们完全出自对自然领域的科学性观察,不再与古代神祇的宗教意涵相对应。
第二,马洛运用绝对王权逐步压制教权之后的世俗化社会背景,建构了人物对于世俗权力的欲望。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一世发动的一系列宗教改革,削弱了神权在国家与社会中的实际支配地位,带来了人们对于各项宗教事务的世俗化理解。相比于获得“天堂的荣光”、神祇的指引或上帝的救赎,马洛的人物关注的是世俗性权力与财富的获得。在《帖木儿大帝》中,波斯贵族特瑞达马斯(Theridamas)关于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对比性话语具有代表性:
“神灵未具国王那般光荣与辉煌;
我想他们所享受的天堂之荣光,
不及尘世君主享有的美妙时光:
去戴一顶镶满珍珠黄金的王冠,
它的光彩伴随着生与死的光环;
去命令,获得,统领与被服从;
当仪表获得奖赏,当容貌滋生爱情,
这种魅惑人的权力撩动诸侯的眼睛”。
(《帖一》2.5.56-63)
第三,马洛运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发展趋势,建构出人物趋向经济利益的倾向,并相应带来了戏剧中时间观念的变革。就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源头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7],新教的禁欲主义虽然谴责把追求财富作为目的本身,但他们认为如果财富是在履行天职的劳动中获得的,那它就是上帝赐福的标志。这种新教伦理精神在英国近代早期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不断进行财富积累的趋势。巴拉巴斯在《马耳他的犹太人》一剧中就解释了世界运行的动力:“是吹遍世界的风,是对于黄金的欲望(《马》,3.5.3-4)”。
对于世俗功绩的关注,相应带来了时间观念上的变化。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不同的时间认知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中世纪的时间观念是以神学思想来规范的,人类基本以稳定且静止的时间模式生活,扮演着由上帝分派给他的角色。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时间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神学的时间概念没有陡然消失,但是从那时开始,它就不得不同实际时间(行动、创造、发现、变革的时间)宝贵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并存”[8]。个人的、主观的私人化时间开始发挥作用。马洛塑造的众多人物都展现出对时间流逝卷走尘世价值的恐慌状态。例如,浮士德在剧终濒死之际的长段独白也显示了个体在时间飞逝过程中的精神挣扎。他以小时、天数、星期、月份、季节、年份等时间标记将生命流逝的过程描述出来,增强了人们对时间一去不复返的悲剧性感受力,彰显了个体对世俗荣誉的留恋,以及对信仰生活的偏离。
基于人物对神祇认知的改变,马洛在戏剧中重置了人神关系。他不仅将人神关系做了平等化处理,使人物等同于神,而且将人物放置在神祇之上,展露出对神祇蔑视、亵渎的姿态。首先,人与神的对等关系是马洛重置过程的第一步。马洛频繁使用古典神祇的相貌、力量、权威、情感来修饰人物,将神祇的超验功用降格为修辞性策略。其次,马洛塑造的人物不仅具有神祇般的卓越特性,还挑战神祇的权威,试图推翻神祇的政权。在《帖木儿大帝》上下两部戏剧中,帖木儿始终将自身放置在高于神祇的位置,他试图进攻天庭:
“来吧,让我们向着天庭的权威进攻,在天空中竖立黑色的幡旗,预示着对众神的屠杀(《帖(二)》,5.3.48-50)”。
“要叩响地狱锈蚀的大口,三头的刻尔柏洛斯将狂吠,让黑色君主向我屈膝下跪(《帖(二)》,5.1.96-98)》”。
帖木儿一系列强有力的修辞话语,烘托出人类力量强于神祇之力的戏剧景象。最后,戏剧人物还展现出对神祇与神学信仰的否定。马洛的无神论倾向不仅得到了史料的证明,而且体现在他的创作观念中。他塑造的人物不仅抨击神学信条、烧毁神学著作,还将基督教信仰当作实现世俗性目的的工具。《巴黎大屠杀》中的吉斯公爵(the Guise)以宗教作为手段残杀众人。《马耳他的犹太人》中的巴拉巴斯在第一幕就指出基督徒的怨恨、虚伪和极端傲慢。而在《帖木儿大帝》中,认为人的命运不是由神主宰的,而是由人自身所掌握。
以上一系列人神关系的颠覆状态,与古希腊或中世纪戏剧中的传统惯例形成了强烈对比。支配戏剧总体思想架构的超验信仰和神学问题,不属于马洛试图表达和解决的核心问题。超验力量的消解为马洛对人物感性经验的塑造打开了新的场域。
二 欲望的补位:探求人物身体中的感性经验
在清除神祇的绝对支配力后,马洛将作为感性经验的欲望填补进人物的精神空间。在灵与肉的二元斗争中,肉体的地位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提升。在马洛戏剧《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浮士德一语道破了感性经验对超验力量的取代:“你侍奉的神灵是自己的欲望(《浮》,5.11)”。在这里实质存在着一个重要转变,这是马洛个体性塑造的中间阶段。
身体观念的更新是指身体在戏剧中不再被贬低为与灵魂相对的低等存在,而是成为彰显个体生命感的创作领域。一般而言,人通常被看成身体与灵魂、自然元素和超自然元素的结合。与马洛创作时期更为接近的是英国中世纪的神秘剧、道德剧,这些戏剧呈现出明显的颂扬灵魂、贬低肉体的理念。身体因更贴近动物性以及更具有工具性,而被认为是灵魂的载体,居于形而下的位置。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尊重与肯定人类作为个体的生命需求,不再对其采取粗暴的克制态度。人类的感知、感觉、欲望等身体维度逐步进入了戏剧创作者的视野。
首先,感官享受作为个体性的世俗行为,在马洛戏剧中被充分塑造。马洛对于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的创新贡献之一,是对人类整体感官的诗意化的表达。无论是他的爱情史诗《希罗与利安得(Hero and Leander)》,还是他的戏剧《迦太基女王,狄多》等,都清晰展现了他对个体感官机制的探索。感官享受(voluptuousness)一词(《浮》,3.94)已经明确出现在马洛的剧本中,其他关于身体愉悦的词汇,如情欲(lascivious)、消遣(pastime),愉悦(pleasure)、取悦(pleasing)等,也频繁出现在戏剧中。马洛细化了感官的分类,触觉、视觉、听觉、嗅觉等领域都成为塑造人物的崭新途径。以视觉领域的刻画为例,马洛运用了视觉美学烘托出戏剧的整体氛围。他利用白色、红色和黑色三种颜色来形容帖木儿大帝的精神状态,“在他安营扎寨的首日,白色是他们的色彩,一根雪白的羽毛闪烁在他银色光亮的头盔上,显示出他平静温和的心绪(《帖(一)》,4.1.49-52)”,而当“他的装束红如血腥颜色,那时他被激起的怒火须用鲜血浇灭,不会宽恕任何试图挑战之人(《帖(一)》,4.1.53-57)”,接着“黑色成为他的色彩,漆黑的帐篷,他的矛枪、盾牌、战马、盔甲、羽饰,都乌黑发亮,威胁着死亡与地狱(《帖(一)》,4.1.58-60)”。通过三种色彩的视觉对比,马洛成功地烘托出人物从平和到愤怒的心绪以及戏剧从缓和到紧张的氛围。这些对于人物感官不断细化与诗意化的戏剧塑造方式,体现了感性经验在人类精神空间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
其次,马洛不仅扩展了感官的表现方式,还进一步扩充了身体欲望的样态。他注重对力欲、知欲、爱欲等多层面欲望的塑造。《诺顿英国文学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的编者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认为马洛的戏剧人物“分别追求统治权,金钱占有权或满足占有知识的欲望”[9]。除了他所阐述的力欲、知欲外,爱欲也在他的戏剧中得到充分展现,构成了欲望塑造的三个维度。第一,力欲主要指个体获得并持存权势的欲望,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欲望都属于力欲。这种倾向与马洛创作时代的英国殖民扩张背景相关。在戏剧中浮士德的殖民式联想中就体现了这一点,他说:“我要派遣他们飞往印度采金,为得到耀目的珍珠而洗劫海洋,去搜寻新大陆之中的每寸土地(《浮》,1.83-85)”。印度、新大陆等殖民性地理名词都是殖民扩张背景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第二,知欲作为认知的欲望,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人文主义特征。人物的求知欲望主要表现在对地理和天文两个知识领域的探索中。浮士德与梅菲斯特在戏剧频繁讨论星体的排列与组合的规律,他们在第七场用了长达34 行的对话来讨论天体知识,而帖木儿关于世界地图的丰富联想涉及大量的地理名词。可以看出,这些人物都将获取知识作为认知世界的重要途径。第三,爱欲描写属于马洛戏剧的典型风格,他不仅局限于塑造男女恋情的传统模式,还关注男性间欲望与友谊的描写,这主要反映在他的戏剧《爱德华二世》与翻译作品《希罗与利安德》中。马洛试图探寻人性情欲的多样化形态,反映了近代早期戏剧展开的对人性多层面的探求。
最后,在各类人性欲望的彰显中,马洛的人物呈现出纵欲特征,形成了具有近代特征的个人体验。学者乔吉娅·布朗(Georgia E. Brown)在分析马洛的诗作《希罗与利安得》时指出,这些纵欲类的人物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人物,他们嬉戏放纵、浮夸、没有节制[10]。戏剧中,狄多对于埃涅阿斯的情欲呈现出疯癫的病态症状;爱德华二世对加弗斯顿的同性情感也不顾国家责任与伦理约束,他被剧中人物兰开斯特(Lancaster)形容为“纵欲的头脑(thy wanton head)(《爱》,1.130)”;而浮士德甘愿向魔王交出灵魂:“只要延长他二十四年的寿命,允许他活得快活,尽欲尽情(《浮》,3.93-94)”。浮士德“尽欲尽情”的生命态度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性解放的典型体现。
马洛对于情欲的描写并不考虑道德禁忌,而是试图将其进行美化处理。戏剧人物体现纵欲倾向,是文艺复兴之前的戏剧作品中少有的书写经验。然而,个体欲望虽然是丰富充沛的,但却驱使戏剧人物将自己限定在单一的个人感情中,逃避社会的伦理、国家的荣誉、家庭的关系的行为约束。人物欲望在单一面向上的自发性和无节制的延展性,使他们频繁表现出精神失常的极端状态。这不能构成个体性人物稳定而完整的性格特征,因此这一阶段仍是马洛个体性建构的过渡阶段。
三 意志的推进:建构个体行动中的绝对自我
马洛对人物的个体性塑造未停留在欲望的阶段,而是融入了“意志”的概念。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了欲望与意志的递进关系,意志作为欲望的最后阶段,是个体经过斟酌后朝向行动的阶段[11]。作为个体的戏剧人物的存在基础,可分为外部和内部的两个层面。外在性的力量主要是指超验性、伦理性、血缘性的力量,它们形成了行动的外在性规范。内部性的力量主要指自我的冲动、欲望、意识等,它们表征出个体的自主能动性。在近代之前的戏剧惯例中,外在性力量始终对人物的存在意义予以规定。而马洛戏剧中呈现的个体意志概念,则为人物存在的基础找到了独立性的条件。
首先,个体意志作为马洛戏剧人物研究的关键要素,受到了众多研究学者的关注。学者凯瑟琳·施维茨(Kathryn Schwarz)所写作的《马洛与意志的问题》[12]一文指出,在马洛的戏剧中,“推动行为的个人意志(will)与语法上预测将来的将要(will)是相互一致的,暗示着一种压服一切的冲动,这种冲动推动着征服性的目的论”[13]。这种征服性与压制性的人格力量正是个体意志不断强化的表现。在这一个体世界之中,意志成为人物表达自身独立性的关键要素,从而摆脱了其他外在力量对行动的束缚。在《帖木儿大帝》第二部中,“这就是我的意愿,我愿意这样想(《帖(二)》,4.2.91)”出自帖木儿之口,马洛在简短的语句中运用了两个“will”表示意志,形成了个体存在的强势自信。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浮士德要求梅菲斯特“永远服从于我的意志(my will)(《浮》,3.98)”,在《爱德华二世》中,国王爱德华只在意自身的意愿,他说:“那是我们的乐趣,我们就愿意(will)这样做(《爱》,4.9)”。这里的人物依据意愿展开行动,也尝试让他人臣服于自己的意志,并通过意志的满足而获得愉悦。另外,“自我”“我的”等词汇被人物频繁使用,展现了他们内在生发出的崭新精神维度。当爱德华二世面对即将被放逐的加弗斯顿时说:“你被放逐出这片土地,我则被放逐出自我(myself)(《爱》,4.117)”,以及梅菲斯特回答浮士德的疑问时说:“不是,是我自愿来的(《浮》,3.44)”,这些话语都展现了人物自我主体性的特征。在《帖木儿大帝》一剧中,帖木儿临终前强调,他自己的精神将注入两位儿子的胸膛,他说:“我的血肉分化为你们珍贵的身形,它将继续保留我的精神,虽然我将死去,但是它将会世世代代永存不朽(《帖(二)》,5.3.172-174)”。这种对“自我的精神”的强调与对意志的注重,使近代早期的戏剧人物找到了独立自在的存在基础和行动来源。
其次,马洛未止步于独立自我的人物塑造,他更为明确地指向了对人物所具有的“绝对自我”的诉求。所谓“绝对”,意味着试图施展意志的个体将自身放在自己与他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中心位置,试图跨越人类的有限性境况,实现个体潜能的极限。格林布拉特将马洛戏剧中个体展现的行动模式归纳为“强迫性重复”模式[14],其主要指:戏剧人物依据个体意志在实现目标之后,不会因一次目标的实现而终止行动,而是在自我身份确证的驱动力之下继续进行重复式行动。这是人物对自我意志绝对性的强化过程。除此之外,马洛的戏剧人物还呈现出僭越式的行动特征。僭越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以绝对自我为中心的表现。这些戏剧人物都企图否定一些固有秩序、外在束缚的表现,将自身的力量与潜能施展到极致,占据宇宙与自然的中心。
最终,马洛建构出了具有“绝对自我”的个体性人物。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个体却在戏剧的终局都面临着精神的矛盾困境。戏剧人物最终的仓促而草率的死亡,反映的正是马洛无法解决的人类精神秩序上的矛盾所在。就像戏剧人物贝尔道克(Baldock)在《爱德华二世》中所说:“所有活着的都会死去,上升的都会堕落(《爱》,20.110)”,其中就散发出极限之后的虚无意味。具有绝对自我的个体,既处于自身潜能的巅峰,但又面临着极限中的虚空,这是以人类自我作为单一秩序后所陷入的虚无困境。
这种矛盾性情境产生于两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在于,文艺复兴是一个多元文化混杂与交锋的时代,蕴含着人类的多重精神危机。神祇不会被真正驱逐出精神世界,而是以各种姿态保留在宗教信仰中,也或藏匿在精神文化的载体中。宏大的必然性秩序作为隐形架构,也继续发挥着人类无法摆脱的支配性力量。马洛戏剧中出现的“神谴的变形”,就是这一文化特征的充分体现。原因之二在于,单一的个体秩序排除了任何关于秩序和正义的清晰思考,即将面对的就是戏剧广度的丧失,单一秩序之下的虚无。伊格尔顿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中指出:“如果主体现在被推崇到无限的状态,在它的怀抱中隐匿了一个无限的能力,同样可以声称(因为无限就是绝对否定)在它的核心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虚无”[15]。马洛戏剧中的人物没有太多的家庭、社会或国家的责任感,更加偏向个人特质,沉溺在自己主观意志之中。个体意志的无限重复,最终成为空洞的重复、对同一的延续。这种状况无法承载其宏大的必然秩序与普遍意义,终究沦为单薄而空洞的戏剧场景。
四 结语
马洛在人物塑造方面实现了从灵到肉,从欲望到意志的个体性转变,塑造出试图超越神祇、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个人,触碰着个体潜能的极限。马洛被誉为英国“第一位对人类力量之宏伟,之诱人,之显赫,之堕落的魅惑力量给予表达的剧作家”[16]。黑格尔在《美学》中总结了马洛生活的文艺复兴时期能够产生卓越文艺的根源,即:“每个人都能独立自主地根据他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行动。这就产生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卓越文艺”[17]。马洛在戏剧中对人物个体性的建构过程正是这一特质的典型体现。以马洛戏剧的“个体性”概念作为圆心,可以辐射到戏剧人物的神人关系、命运观念、感官欲望、自我意识、个体意志等诸多领域,展现了英国文艺复兴戏剧中不同以往的个体面貌与精神感知。但是,对于马洛“个体性”建构的思考不能止步于此,正如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Jaspers)在论述文艺复兴悲剧时指出的,虽然这些戏剧标志着一个鼎盛世界中自我认识的完成,但是人类的心灵正是由于潜能的丰富而衰萎困顿,每一种能力臻于实现的时候就会招灾惹祸[18]。马洛戏剧面临的终局困境,显示出单一的个体秩序的缺陷,这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类精神困境,也是日后现代化进程,以及后现代进程中人类仍然需要思索的问题。个体在试图达到潜能极限的同时,其与外在世界中各种力量的关系,以及其与内部自我结构的制衡状态,都是戏剧艺术需要始终思索与探寻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