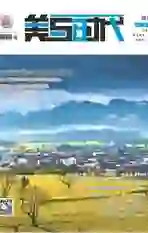辩证的“个体性”
2017-03-17赵晶晶
赵晶晶
摘 要:家庭分离、社区共同体弱化、社会合作减少、人际关系淡化、社会道德缺失和诚信衰退、个人无安全感和焦虑感增强,这些现象普遍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藏匿于其中的各种风险,对社会整合构成强大威胁。学者用“社会凝聚”这一概念为社会管理提供了与“个体化”相反的构想。通过对中国“个体化”现状的考察,并结合贝克等学者的“个体化”理论,探讨“个体化”社会再次实现社会凝聚的可能性。
关键词:个体化;风险社会;社会凝聚
当下的中国转型正在见证并孕育着一种新的个体化进程,这种个体化正在“公开地发挥着影响力”:炫耀型消费、理性计算和利己主义等占据着社会生活的主旋律,货币关系取代了人情交往,生活世界在经济原则下被殖民化,道德宣言空洞无力。再看小的社会单元——家庭,人户分家、青壮年外出、个人追求隐私都在不断瓦解着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与人际互动模式,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离婚夫妻使得“家庭”不再成为“心灵的港湾”,每一个个体都无着落地在社会中行动,孤独感在每个人内心不断增强。
本文从社会凝聚角度出发,从反方向考察中国社会是否具有“个体化”现象,分析中国“个体化”社会特点,并试图从学者关于社会个体化、社会团结等理论探讨实现社会凝聚的可能。
一、“社会凝聚”:对“个体化”的考量
家庭分离、社区共同体弱化、社会合作减少、人际关系淡化、社会道德缺失和诚信衰退、个人无安全感和焦虑感增强,这些普遍存在的现象已经对社会管理构成了强大的风险。
张海东等学者提出社会质量研究,其中社会凝聚是一个重要方面,从社会个体化的反面强调了社会凝聚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性。“社会凝聚,指以团结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揭示的是基于共享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能保有集体性并维系基本的价值规范……社会凝聚指向的是团结和整合问题,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分化或分裂[1]。”
在张海东教授的研究中,“社会凝聚”成为可量化的指标,指向社会整合程度。社会凝聚程度越低,越能说明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程度。社会凝聚主要受到社会发展和社区、群体、家庭相互作用的影响。从能动的行动者角度出发,社会发展同社区、群体、家庭相互作用产生社会认可,尽管在社会、集体共同构成的框架内,但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社会凝聚不仅仅关乎社会团结这一宏观的社会状态,也对个人的自我实现至关重要。因为社会凝聚连接着社会与社区,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行动都在社区中进行,都是在与其他成员的互动中实现其社会性的价值。
具体到“社会凝聚”中,有多个子域:信任、宽容、社会契约、社会网络、国家以及地区和人际关系认同。欧洲与亚洲国家在具体指标设置中会因为社会背景差异而做出细微调整,但大致看来,依然体现出社会凝聚在宏观社会和微观个人层面的共同关注,联系宏观与微观的是社会认可,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以社会认可为衡量标准。从个人——社区、群体的结构中强调个人的福祉和潜能,前提是基于人的“社会性”。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认可不可分割,只有在社会关系中、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得到自我实现。
二、中国:“个体化”的社会?
市场化改革,尤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众多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对诸多下岗工人而言,这不仅是组织纽带的断裂,也意味着生活世界的解体。即便是在血缘关系浓厚的农村,也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使个人回归家庭,但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出现了“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之人”现象[2]。住房、医疗、教育的一系列改革,使人们摆脱了对家庭、家族的依赖,而增大了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很大程度上也使得传统社会关系进一步瓦解,社会成员之间许多关系消失或弱化,愈发孤立。加上观念的转变,在个人权利得到尊重的同时,客观上也在弱化父子、夫妻等人际关系的信任。
贝克在解释“个体化”时,从再生产领域和生产领域两个角度展开分析,王春光延续贝克的这一逻辑,对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状况进行了详细考察。他从“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元入手进行考量,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和夫妻离婚率三个方面展开调研和分析,三者数据均呈上升态势。家庭,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论是其重要性还是其功能,都趋于弱化。
学者王建民指出,相较于贝克所提出的西方社会“个体化”,中国的个体化植根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社会事实,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自我主义传统、市场化改革进程、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以及互联网的兴起。
不同于王春光,王建民不仅从社会结构方面探讨了中国个体化的表现,也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以及个体极为隐秘的精神状态。但二位学者都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与西方福利国家的“个体化”存在诸多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现代化路径和制度的特殊性,导致中国的“个体化”社会存在传统、工业以及后現代多重时空压缩的特点。即使中国社会出现了贝克所谓的“个体化”现象,其形成路径和逻辑同西方社会也并不相同。
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个体化”社会的风险
“中国社会情境(指社会关系)的独特性在于兼具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者”[3],即团结的社群(传统)、工具性的联合(现代)和公民身份的联合体(后现代)。这种多重时空压缩的复合社会关系,使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并存,其中后现代的出现主要是伴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及单位制解体逐步产生的。
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传统对个体的控制与支持日渐丧失,社会成员必须作为个体来积极主动地创造自己的身份与认同。笔者并不认为“个体主义”等同于自我中心主义或利己主义,“个体主义”本身并不具有褒贬意义。当个体可以免受所处环境的消极影响、成为自身生活的积极塑造者的同时,个体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通过努力进取在竞争中实现自我。但是个体化在客观上导致社会关系网络不再为人们的社会成员身份提供有效支持,现代个体则在从传统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照顾与支持。
但需要强调的是,贝克关于“个体化”的提出是基于“福利国家所保护的劳动市场社会的普遍化、消解了阶级社会和核心家庭的社会基础”[4],在国家福利体制的保护之下,劳动者有充分的条件灵活就业,削弱了原有的以阶级和核心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基础。但在中国,福利国家尚未建立,“个体化”会出现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的后果,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切身感受到了“个体化”所带来的诸多风险与不安全性:“以社会道德环境、家庭婚姻和男女角色来应付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传统方式不断遭到失败。在同样的程度上,需要个体自身来应付焦虑和不安全感。或迟或早,对教育、咨询、医疗和政治的社会制度的新需求会从相联系的社会和文化的冲击与颠覆中产生出来。”[5]安全感的丧失与个人自由的增加相伴而生,但人对此的本能反应不是选择自由,而是逃避自由,寻求安全。
“个体化”强化了人们“为自己而活”的观念,但在缺乏安全感、充满风险的社会中,个体化造成的文化认同、社区认同及集体认同的缺失,人的精神陷入焦虑无着的状态,使得“为自己而活”从原本的一种单纯的生存策略变成了“只为自己而活”,不顾及他人利益,甚至铤而走险。
四、实现社会凝聚的可能
个体化理论是西方社会进入“第二现代性”阶段所提出,与风险社会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相联,但并非一个阶段性命题,因为个体化与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社会凝聚相背离,作为社会性的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则是永恒的话题。
社会凌驾于个体之上,道德意味着克己,社会的存在与延续有赖于个体之间的妥协与牺牲。而个体化的社会,强调对自我实现的肯定,每个社会个体都在努力遵循内在的自我。在这种社会情境下,是否还存在力量使得“社会存在”与“纯粹个体存在”相抗衡?涂尔干对此持辩证观点,“个体性”体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因而,“个体化”社会的“个体性”,也应当具有两层含义:个体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具有独立思想和权利意识的个体,同时承认和尊重其他个体的独立思想与权利意识,这是构成“个体化”社会关系的根本基础,也直接影响对于社会的整体管理思路。
一方面,肯定强制性权力存在的必要性。权力概念处于中心地位。权力作为“运作机制”将微观(个人行动)和宏观(社会秩序)连接起来,并体现在个人行动者的行动中。政府作为必要的恶而存在是启蒙运动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共识,而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是国家及各级政府应当致力的重点。建立健全平等的劳动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通过稳定劳动就业市场、确立公平法治制度增强社会安全感、公平正义感。
另一方面,建立个人与社会、私域与公域的沟通。大量的社会组织发挥“桥梁”作用,作为国家之下的“次级群体”的存在,是连接个体与社会、微观与宏观、公民与国家的中间力量,是社会个体走向团结凝聚的粘合剂,也是个体进行社会参与的主要途径,可以增强社会归属感和集体意识。但就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来看,各类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在社会领域尚未能够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第三方: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作用,需要社會组织体制改革以及政府的资源和政治支持,依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张海东.从发展道路到社会质量:社会发展研究的范式转换[J].江海学刊,2010,(03).
[2]王建民.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J].思想战线,2013,(03).
[3]王春光.个体化背景下社会建设的可能性问题研究[J].人文杂志,2013,(11).
[4]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87,188.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