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实现的“诗意地栖居”
2021-12-20汪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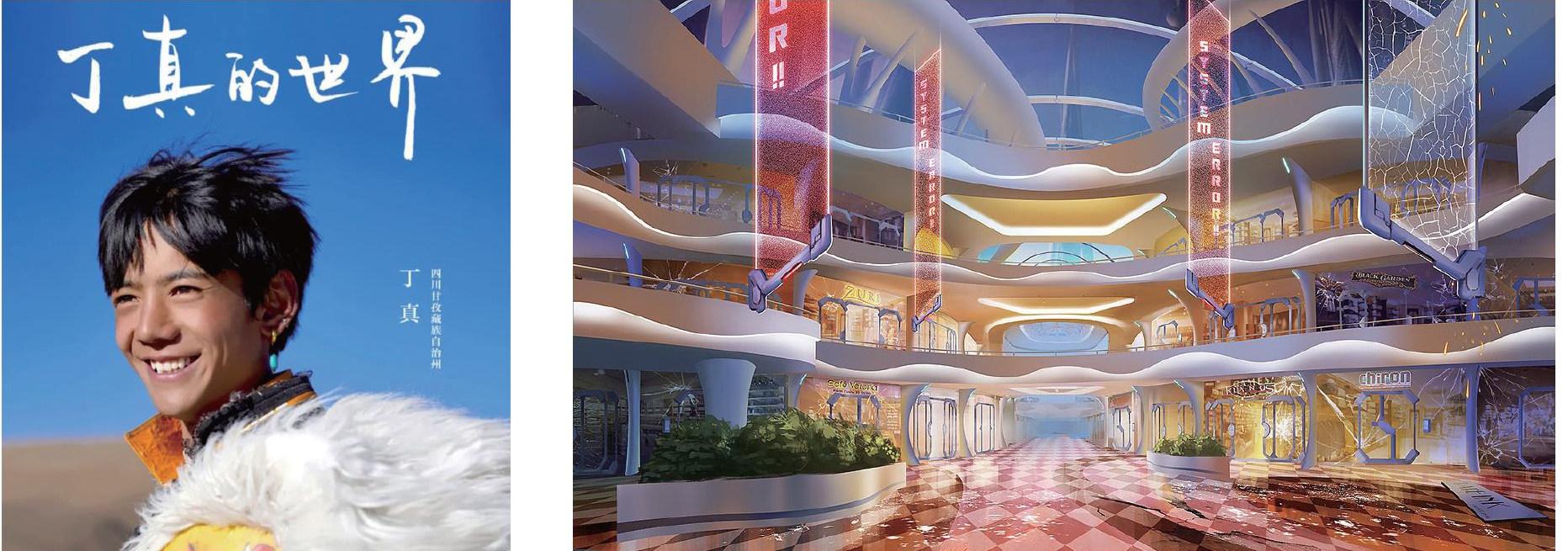
摘 要:“诗意地栖居”原本是指人在四重整体的相互关照中实现真正的栖居。在现实生活中,它离开了海德格尔的本意,成为人们标榜精神理想的口号。在遭遇了当下艺术和无力自律、生活的审美泛化、诗意的消解之后,这种审美理想难以实现。
关键词:艺术自律;审美;消费;诗意地栖居
“诗意地栖居”最初是在荷尔德林的诗作中出现,后来被海德格尔用来阐释他的存在主义思想,这一命题的提出背景是对现代技术遮蔽了人的本真存在的批判,他认为,“人把天空、大地、诸神、终有一死者——人自身这四重整体保护在其本质之中,由此而栖居”[1],即天、地、神、人按照其本质去存在,而存在本身又是在这四种整体中得以创建,人在四重整体的相互关照中实现真正的栖居。
在现实生活中,这句话离开了海德格尔的本意,成为人们标榜精神理想的极具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的口号。前段时间,四川甘孜藏族男孩儿丁真的走红,正是人们渴慕“诗意地栖居”的一种表现。“诗意地栖居”是一种审美理想,在传统意义上,也即代表着对日常生活的情欲需要、功利目的和理性意识的暂时性超脱,艺术能否承担人们诗意生存的重托?生活能否让人们实现“诗意地栖居”?
一、艺术的无力自律
艺术自律就是要求艺术获得独立自主性,即将审美作为艺术的伦理法则。“诗意地栖居”的生活理想和艺术的审美追求是相似的,它们都要求主体独立于现实功利目标之外,具有非功利的快感、“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特征。海德格尔将“诗意地栖居”的希望寄托在诗人身上,暂时“坐忘”“同于大通”[2]的精神理想也需要借助艺术的审美性得以实现。
审美并非艺术与生俱来的特质,在中国,艺术的自律以魏晋南北朝文学走向独立为开始的标志。在西方,康德第一次使得艺术以审美来为自己“立法”获得了伦理自主性[3]。他意识到理论理性的批判和实践理性的批判之间有一道裂痕,于是他找到了判断力来作为这两个形而上学共同的支撑点,判断力和理性、悟性一样都是先验的,是审美的先天原则,鉴赏判断就是诸心意机能的协调运动,即“想象力(作为先验诸直观的机能)通过一个给定的表象,无意识地和悟性(作为概念机能)协合一致,并且由此唤醒愉快的情绪,那么,这对象就将被视为对于反省着的判断力是合乎目的的”[4]。启蒙思想家们在推翻贵族统治的合法性、争取文化领导权时,为了宣扬人的自由意志和自觉意识,提出人性论系列命题,这一理论逻辑的延伸就是进一步把审美确立为艺术这一场域的伦理法则。浪漫主义强调艺术家的独立自主、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重视、审美批判理论将文化作品“审美孤立”等都是艺术自律的实践。席勒、阿多诺、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皆是艺术自律的捍卫者,他们将艺术视作黯淡现实中的精神净土。在“二战”后,先锋艺术、波普艺术等不断动摇着审美在艺术场中的特权地位,艺术逐渐回到世俗生活,日常生活经验被越来越多地呈现在艺术作品中,大众文化的出现则彻底将艺术自律体制推向了终结。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出现过艺术自律的短暂取胜,那就是朦胧诗、寻根文学、意识流小说、先锋派文学等组成的现代派文学潮流。随之出现的新写实小说,虽然借用了先锋派的一些创作手法,却以贴近日常生活的姿态和先锋派标榜的精英和前卫划开界限。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文学的兴起,艺术自律彻底灭亡,艺术在技术和消费的他律中丧失了本真的诗意。冯黎明总结了艺术自律的三个特征:“审美主义的艺术观念”“署名崇拜”以及“文本自足性”[5],在网络文学的场域中遍寻不见。首先,网络文学作品的优劣不再仅仅取决于其“文学性”,点击率、月票排名是决定作品成功的更重要的因素。“爽感”取代诗意体验、几十万起步的字数取代形式和技巧成为作者们一致的追求。虽然其中不乏坚持着人文情怀的作品,但大部分作品都缺乏诗意追求。其次,媒介的革新带来了写作狂欢。文学创作的门槛降低,人人都可以是作家。这不仅仅是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而是完全消弭了作者和大众的界限,取消了作者的特权。最后,网络文学作为一种大众文学,将作品当成工业制品来生产、销售和消费。作品如同复制品一般,出现了情节模式、人物塑造的大量雷同。传媒公司从体量庞大的网络文学作品中筛选出具有IP价值的作品,再开发成产业链,谋取最大的商业利益。读者想要阅读完整章节,要么就要付费成为网站VIP,要么就要被迫观看几秒钟的广告才能进入下一章。网络小说作者的成功也必然意味着作品的畅销和跨媒介转型的成功。
当艺术被消费裹挟,艺术创作者只是任何一个普通人,作品迷失了人文精神向度,艺术无力自律,那么经由艺术寻找“诗意地栖居”已不再可能。
二、生活的审美泛化
与文学泛化同时出现的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迈克·费瑟斯通认为可以从三种意义上谈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現:第一,以“一战”后产生的达达主义、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等艺术为代表的亚文化,它们一方面消解了艺术作品的神圣性,造成经典、高雅文化艺术的衰落,如杜尚的《长胡子的蒙娜丽莎》;另一方面消解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使得艺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呈现出任何事物之上,如杜尚的《泉》。第二,生活向艺术品转化。如福柯和罗蒂将生活视为艺术作品的策划,又如大众消费背景下唯美主义与消费主义相结合的“艺术人生”,塑造审美化的生活风格。这种对如何把生活融入到艺术或者如何把生活塑造为艺术的追求推动了对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的建构,而后者恰是消费文化的核心。第三,符号和图像渗透到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结构当中。比如城市里的随处可见的陈列橱窗、播放着广告的电子屏幕,都在以一种图像的方式给人带来视觉美的享受,同时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决不能把消费社会仅仅看作释放了某种一统天下的物质主义,因为它同样向人们展示、述说着欲望的梦幻图像,将现实审美化又去现实化”[6]。
审美泛化带来的是审美需求的层次下降,人们不会为曲高和寡的纯粹艺术享受买账,即便是去欣赏,也只是带着休闲的心态。人们满足于具有审美意味的非艺术品带来的愉悦,且这种愉悦已经不是形而上的妙悟,甚至不是情感的高峰体验,而是身体的快感。“以前,人们说到‘审美’,必有高远的要求需要予以达成;在今天,低层次的要求亦足以敷衍。故而取悦感官的某种安排,亦被称之为审美的。升华因素如此降尊纡贵,审美需求已经接近了本能领域,甚至是在此一领域中孕育而出。”[7]
审美需要催生了审美活动,审美活动也创造着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同时创造着主体的审美需要。消费社会的到来,使消费型审美活动成为了审美活动的主要方式。一方面,审美活动被纳入社会经济活动的链条当中,人们要追求片刻精神愉悦,就得看电影、听音乐、旅游等。想要获得精神享受就必须消费,不消费就无法享受到这些产品提供的精神愉悦。人们审美需要的各个方面,“都被精确地预计、设置和操纵,并‘被编排为可以消费的范型’”[8],以便商家生产出越来越“人性化”的商品和提供越来越细致周到的服务。另一方面,商家为了盈利,会在产品的设计上极度迎合感性需求,不停地制造热点和引发舆论,诱导人们意识到自身的审美需要,在本没有审美需要的地方创造出审美需要,从而刺激消费行为的发生。消费型审美活动让审美不再是难得的精神升华的时刻,而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个普通环节,挑选一支牙刷、逛一次服装店,都是在审美,也都是在生活。
在当下,“诗意”被商家设计进商品的外观和宣传标语之中,“栖居”的场所也以消费作为唯一入场券。喝着“大自然的搬运工”的水,吃着“纯天然、无添加”的食物,住着“生态宜居”的小区,欣赏着丁真纯真的笑容和他那蓝天草原为背景的生活环境,人们似乎更加亲近大自然了,而这一切现代工业的产物恰恰是大自然的破坏者,适应了工业文明的人们难以适应真正的贴近大自然的生活。当审美离不开金钱和色情,人们渴望的“诗意地栖居”只是一种有钱有闲的生活模式,而不是达到心灵的澄明和精神的自由、包容天地人神的本质,甚至不是对日常生活的情欲需要、功利目的和理性意识的暂时性超脱。
三、诗意的消解
人们在进行消费型审美时,获得了什么审美感受,在其中是否还残留着一点诗意?
当代审美文化,按照余虹的看法,“这种普遍化的娱乐性审美文化威胁着审美文化的精神性品质”[9]335。不论是读虐文、看韩剧而流泪痛哭,还是看脱口秀、喜剧类电影而捧腹大笑,本质上都是在追求单纯的享乐,绝不是为了关照现实、反思人生。可能在某些时刻,受众仿佛体验到人物或剧情的情感共鸣,或者感受到某一句明星名言的醍醐灌顶,亦或者顺应了文化产品中主流价值观的教化,都不足以达到震撼灵魂的深度,不能引领人们体验到“此在”。
甚至在审美活动中,情感的波动、思维的闪光都可以不在场。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件物品都可以被设计为美的、任何一场经历都可以包装成审美的,但是人们不再以严肃的态度去思考美背后的隐喻,落入符号和图像的所指即它们本身,看一场艺术展、听一场音乐会仿佛进行了一次美的饕餮盛宴,走出展馆和歌手驻唱的酒吧却什么也没有留下,美变得虚无而空洞。人们对美的接受止步于美的事物本身,制造美也指涉于纯粹形象外观自身。美的服饰、美的妆容、美的城市设计、美的形体,等等,它们背后绝没有什么“理念的感性显现”,也不是再现生活、表达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
美不再来源于生活,相反,它改造着生活。例如本来女性美只是一小部分的女性在一定时期内达到的理想状态,但是广告、影视荧屏等对于女性美的突出和放大,使得所有人都产生这样的错觉:女性美可以在每一个女性身上体现,并且可以突破年龄的局限。因此,觉察到想法和现实之间存在的落差,女性只好用化妆品、节食、外科整容手术等来予以填补,主流文化创造出来的女性神话完成了女性气质的构建。这种对美的追求只能带来持续的消费需求和永远填不满的变美欲壑,消费社会又一次成功利用了审美文化这一手段。审美带来的不是精神的愉悦和享受,而是让“颜控”更加理直气壮,造成人们尤其是女性生存的焦虑和压力。
审美活动还成为阶级的标榜,“在皮埃尔·布迪厄看来,人们在日常消费中的文化实践,从饮食、服饰、身体直至音乐、绘画、文学的鉴赏趣味/品味,都表现和证明了行动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9]346。不同的群体和阶层有着不同的审美趣味,审美趣味的选择既是人们自我表演的方式,也是人们将个人与所属阶层区隔开的方式。通过消费,任何人都可以复制其他群体或阶层的生活方式,从事反映着更高级的审美趣味的审美活动,或者在自己所属的群体里完成自我标榜和自我体认,或者获得短暂的优越感和进入更高阶层的虚幻满足。
在消费型社会里,既缺少以“诗意地栖居”为真正理想的主体,又没有可供栖居的园地,追随者寥寥。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审美文化和现象,至少能让人们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更自主自在地游走在环绕着商品的日常生活之间。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演讲与论文集(修订译本)[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43-144.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6:213.
[3]冯黎明.艺术自律与审美伦理[J].文艺研究,2018(11):29-38.
[4]康德.判断力批判(上)[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6.
[5]冯黎明.艺术自律与艺术终结[J].长江学术,2014(3):31-41.
[6]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89.
[7]韋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1.
[8]余虹.审美文化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8.
[9]祁进玉.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汪欣,中南民族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编辑:宋国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