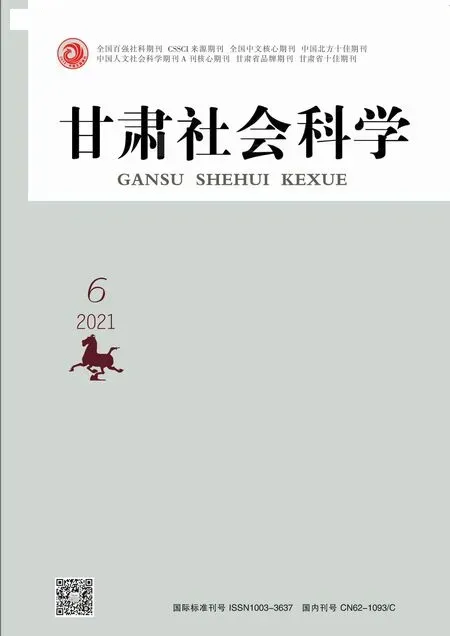论“不学《诗》无以言”的命题语境制约
2021-12-16王列生
王列生
(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武汉 430000)
提要: 当日常问学间道出的孔子“不学《诗》无以言”引申为一个必然判断的独立命题之后,就成为知识学而非经学抑或文学维度极其值得追问的知识事态。事态真相追问结果表明,这一具指命题的合法性与真值率不过在于,《诗》发生史与中华文明“语言建基”“社会建基”和“道德建基”巅峰时域高度叠合,由此形成对个体和社会都有超强能量的历史语境制约。《诗》的外在“文本”与内在“本文”之所以凝结为当时凸显知识的杠杆以及延时经久的民族经典,是因为它既是这些建基的历史成果,又是建基得以延展持续的现实动能。但随着语境变迁,新的制约迫使命题真值率呈渐进衰减之势,必然知识命题也就演绎为或然知识命题。至于《诗》的后起经学兴盛与文学转向,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另当别论的复杂事态与异质界面,尽管彼此间往往问题交叉、议题纠缠乃至解题牴牾。所有这一切,都以《诗》乃中华民族“高不可及的范本”之一为存在前提。
《论语·季氏》载:“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1]197虽然这一记载省略部分及其事态整体的语旨重心,更大程度上在于“君子不独亲子,故相疏远,是陈亢今得闻君子远于其子也”[2]的圣德价值指向,在于细节性超越诸如一般命题指涉的“私也者,其生于心为溺,发于政为党,成于行为慝,见于事为悖、为欺,其究为私己”[3],但对本文的关注点而言,却专注于陈亢“三闻”之一的“学诗”必然诉求,于是“不学《诗》无以言”就演绎为此议所要追问的必然知识命题。即孔子间接涉事陈述中所隐存必然命题逻辑,是否具有不可置换的命题真值。毫无疑问,力点支撑一定会有多个值得讨论的维度抑或向度,但此议所要聚焦的,只不过“语境制约”一个焦点,从而确证孔子诫鲤之际所陈述的知识命题,具有历史时空定位的深刻语旨与普遍语用的张力价值。
一、“语言建基”必然诉求
《诗》所具有的语境制约力量,首先在于这一聚集态文本,能在“语言建基”时代大体量提供“言说能力”得以有效支撑的功能杠杆,否则就一定因“无以言”的“语言之困”,一方面丧失士大夫身份“迩之事父,远之事君”[1]202的“立言”机遇,另一方面则因难以充分满足“辞达”[1]192的交往底线诉求,而不得不窘陷“因缘与意蕴,世界之为世界”[4]102由此难以企及的生存自蔽,这显然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①为使命口号的任何矢志个体所无法接受的存身屏障。
“言说能力”作为个体与社会基本结构赖以维系的要素,绝非20世纪“语言学指向”以来才受到普遍价值关注,也绝非只有古希腊“逻各斯中心主义”背景下智者的“言语与言语的对抗”[5]20才具有要素凸显的谱源唯一性地位。恰恰相反,不仅“语言之困”对人类个体抑或整体皆为相与始终的终极性问题,而且各民族语言发生史也都有其自身不可或缺的言说能力。关注独特知识谱源,语言生态学家所发现的“创始人原则”及其所谓“演化生态”,并非仅仅适用于克里奥尔语,可以普效延展至各个语种以及作为语种主体的各个民族,所以一切尽可统辖于“语言演化的群体遗传”[5]20。正因为如此,哪怕人类学家20世纪深度切入的那些原始氏族抑或小型社会,也都必然有其自身语言演化史以及群体遗传赖以进行的“建基时代”。而当尺度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那么最大的语言建基事件无疑发生在象征叙事的所谓“轴心时代”。因为人类的知识言说能力在那个约指时间域限出现了第一次革命性全方位进展,并且这一进展的更绵密事态表述,还应该将约指时间域限扩大到“前轴心时代”和“后轴心时代”。由此就能更具命题张力地兼容既极为繁复又极为绵远的建基事态。个案举证有如远古印度吠陀奥义的模糊语用文献,较之阿育王朝体制佛教所形成的成熟宗教知识形态,无论如何都具有知识谱系生成的“播种”与“耕耘”前置存在价值。与此相仿,古希腊的普鲁塔克才从阅读柏拉图的《王制》和《蒂迈欧》等篇章过程中,很清晰地梳理出诸多远古埃及法老们认识世界与猜想存在的智性表达对柏拉图理性主义知识体系的跨文化影响。凡此足以说明,在20世纪“语言哲学”炙手可热之前,人类的历史及其生命解困所形成的知识史,从来就是在意识到的同时也积极实践着的语言价值演化史,并且这一进程完全吻合马克思所言的认知程度囿于历史时代有限性条件的判断②。这一共识性基本认识,当然也适应于中国事态现场,并且尤其适应于此在议题与所议对象。其凸显处在于,《诗》在“前轴心时代”以及向“后轴心时代”功能延伸的漫长历程中,最大限度地以经典文本形态呈现出中华文化的语言建基成果,是殷商甲骨文基础上的质性飞跃与聚集态重构。飞跃和重构本身,站在今天的审视位置,可以说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界面都足以消解汉语起源神话观及种种汉字起源的神话细节,典型如《世本》所谓“仓颉造文字”[7],或者更具演绎特征的“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8]。这种消解,意味着科学理性主导的语言学家或文字学家,对具体文字或一般语码的意义指涉,通常都会持渐进互约的通用功能生成观,至多会强调特定个体、特定文本抑或特定时阈有其生成突进价值。也正是从这一价值维度,《诗》获得了类似特定文本的存在属性,成为“轴心时代”及其前后延伸期中国事态现场力避“无以言”的“工具箱”,并且首先是最为切要的“语码工具箱”之一。
无论造字六法所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③,还是造句两式所谓“致动式”与“使成式”④,都可统辖于语言建基时代言说解困的摹状词语言理论范式,尽管这依然不过是语言学现代进展中的一种知识形态。对于罗素而言,他所说的“摹状词可能有两种:限定的和非限定的”[9],虽然是在语言形而上学界面确立命题,但这种确立无疑可以实现形而下阐释移位,包括移位至《诗》的造字、造词和造句。沿着这一解释向度,我们就能洞彻并且确证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诗》能够以一种简策文本形态,于所在历史时空经典化地实现汉语知识域语言建基目标,从而成为言说能力必然诉求的文字功能支撑乃至语词功能支撑。对于所有意欲言说的士大夫来说,为了获得这些功能支撑起的特殊身份,就必须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202开始,直至能自觉地意识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1]202?而所议的关键恰恰在于,《诗》是满足语境诉求字、词、句必备基本能力的完备“知识工具箱”,赵衰极致性地价值评估为“《诗》《书》,义之府也”[10]268。
《诗》的字词句语言建基,及其这种建基对所在时空士大夫阶层潜在身份和实际身份所构成的诉求必然性,也就成为可以展开的凸显议题。仅就语言建基经典价值乃至必然工具功能而言,至少可以归纳陈述为三大基本向度:或者名物得以解困及其效果呈现的汉字音形义语码定准,或者叙议得以激活及其效果呈现的汉语信达雅语用定格,或者情志得以抒发的汉诗赋比兴语旨定向。
德国学者J.G.赫尔德站在现代位置所强调的“人类思维的所有这些痕迹都刻在了最早的名称上面”[11],说到底不过是坚信语言源于以分类能力为前提的名物解困,而这在汉语发展史上,早在汉代就已形成知识成熟形态的诸如《尔雅》《方言》《释名》及《说文解字》等,其名物解困的文字理性已然实现汉语方块字音形义完整而全面的谱系化建构。追溯至更为遥远的“前轴心时代”,虽然类似功能谱系诉求显然无法企及,但五百年历史生成且多次编集才最终成为确定文本的简策之《诗》或者布帛之《诗》,便已经在殷商甲骨文或者商周金文渐远渐成基础之上,有了文字功能定准的文本形态,从而可以“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12],或所谓“先王寄理于竹帛”[13]199。《诗》无达诂当然是时距造成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时间还原意义上所有文字当时就已失去音形义“语符定准”,否则就不可能有《左传·隐公三年》的“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风有《采蘩》《采》,雅有《行苇》《泂酌》”[10]52,也就没有沟通有效的“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14]
语符定准之论,其一在字音。诸如“襢,白衣也;张彦切,后六服有襢衣”[15],虽然未必能在音韵学维度对《郑风·大叔于田》的“襢裼暴虎,献于公所”给予精准还原,甚至音韵学早期经典《切韵》《广韵》《中原音韵》抑或后期代表作江永《古韵标准》与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也依然不过是沿波讨源的尽力而为。因为较多字音都事态复杂,至个案“《诗》‘宾载手仇’,郑云:‘读曰’……今按:仇在幽部,在乌部,两字古韵异部”[17],由此也就决定《诗》所在时代绝无后世音训所能达到的字音定准统一性与规范化程度。于是《诗》文本自身所实际呈现的字音相对统一性与规范化,就成为所在时域士大夫阶层及其预备者学习与交往的字音定准基本条件,甚至有可能在泮宫或者庠序里成为读音识字的教科书,从而基于语音自衍本能而非社会理性地化解音韵知识谱系代际延伸和功能建构之前的音读之困。
其三在字义。虽然《诗》于生成时域或者语域,有所谓瞽瞍声传与国子义教途径之别,但不同场所与不同表现形态终究都要根于《诗》语,根于语义学层面同步衍生这一经典文本“从隐含意义到编码(规约的)意义转换”[19]的最大语用张力,从而也就具有《诗》字意义规约播撒与增量拓值的语言建基之功,并且增量和拓值一方面体现为物类与事类大范围覆盖的“名定而实辩”[20]210,使野草奇兽也能字彰名显为诸如“蘩”“《采”“菽”“芑”“薇”“杜”“棣”“莪”“蓼”“萧”“茨”“棫”,诸如“卷耳”“芣苢”“葛藟”“甘棠”“芄兰”“木瓜”“扶苏”“荷华”“白华”,诸如“麕”“麟”“雉”“鸨”“鹭”,诸如“雎鸠”“驺虞”“蟋蟀”“鸤鸠”“鸱鸮”“蜉蝣”“鸿雁”“鸳鸯”。另一方面则更在于名物字符指涉中字义的精微意义延伸,仅《鲁颂·駉》单篇个案,总体概念的“馬”就字义化地延伸出“驈”“骊”“骓”“駓”“骍”“骊”“骐”“驒”“骆”“駵”“雒”“驔”“骃”“騢”等。而在《诗》尚有诸多“馬”义分延称谓字之外,其他物类抑或字类意义延伸称谓字同样繁多,以计量语言学为知识工具就能获取各种意欲获取的精准分析数据。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今天可以理所当然或日常忽略的字义指涉与意义延伸,对《诗》所在时代而言,乃是一切求知个体无法绕过去的第一道门槛,因而也就是《诗》的字义功能张力所在。
总之,《诗》所呈现的音形义三位一体汉字语码定准,在语言建基时代无疑有其必然逻辑条件存在价值。
二、“社会建基”必然诉求
《诗》所具有的语境制约力量,其次在于这一聚集态文本,能在“社会建基时代”深度澄明“言说能力”得以有效指涉的意义覆盖,否则就一定因“无以言”的“意义之困”,一方面丧失士大夫身份所渴望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61的“立身”机遇,另一方面则不得不被动沦落于“上失其道,民散久矣”[1]218所在时空位置社会失序窘况之际,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问题的关键在于,类似被动并非社会秩序的“重建”而是“始建”,是事态迫使人们无法仅仅崇信于神话性创建叙事诸如“帝釐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饫》”[22]112,且不得不更着力于现实性创建叙事的古人所谓“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23],抑或今人所谓“然则百其姓者百其类。以今语释之,即一百个种族不同之社会也。故《尧典》以‘平章’言百姓,意即平等调和各异族云尔”[24]。诸如此类并非表示社会建基自《诗》始,而是强调以周及封国兴衰为事态背景的《诗》发生史所处时域,乃先秦中华民族社会发展鼎盛阶段,由此也就有社会增量与拓值后果的“氏族制度已经过时。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段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25],并且在社会本体构成界面也于延展过程中叠加性地不断确证“整个综合体作为一个社会”[26]。正因为如此,我们迫切需要回答的,不过是《诗》对“社会建基”究竟澄明了哪些解困之途的意义真相,尽管此时只能选择最切要义项的梳理形式。
《诗》较大篇幅反映周人宫廷宗教仪式本身,直接就是宗教意识形态建基的民族文化形成过程。日本当代学者家井真所述“《诗经》中《雅》《颂》诸篇的产生,是以铸刻于宗庙彝器上的铭文为诗歌母体,在继承和保持其宗教性的同时,有意识的强化并提炼其文学性和文学化过程”[27],与清末中国学者方玉润声称“或又曰:《二南》《雅》《颂》,祭祀朝向聘之所用也”[28]57,虽然彼此间文学经学意义向度分异明显,却于祭祀之本体论叠合。这就意味着《诗》的宗教生活功能乃其极为重要的价值构成,并且于知识谱源维度既有外在证据的“瞽矇……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29]357,亦有内在证据的“有瞽有瞽,在周之庭”[19]。尽管确凿无疑的“瞽矇传诗”及其《诗》宗庙生活功能覆盖并非“本文”全部,但其所已然指涉内容,却是社会化宗教意识形态的充分呈现,是体制宗教开山立派之前社会化宗教信仰的典范形式。基于此,作为社会建基构成要件的宗教意识形态建基,可以从《诗》中较为清晰地编序出:其一,物灵崇拜。也就是说,诸如《采蘩》之“蘩”、《采蘋》之“采”、《访落》之“艾”、《潜》之“鲔”、《凫鹥》之“凫鹥”、《既醉》之“笾豆”、《行苇》之“苇”,都是物灵崇拜介质对象,其意义隐存在于由“灵物”而至“物灵”以寄托人对某种超验性的崇拜意识。这在各民族所处“万物有灵”时代乃是普遍存在的宗教意识,而《诗》对类似意识及其介质的典范言说,由此使社会“能够获得无限、不可见或神圣”[30]的最大意义载量,进而可直接事功于“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以诫劝人君也”[29]357。其二,祖德崇拜。也就是说,诸如《文王》《大明》《绵》《棫朴》《思齐》《灵台》《下武》《文王有声》等类似篇章,无不致力于祖德神圣化、宗庙化、崇拜化,并在宗教仪式形态转化过程中获取其所意欲获取的治国理政精神维系。此时所诉求的“供奉仪式和共享仪式、模仿仪式和纪念仪式是怎样经常满足同一种功能”[31],不过是将祖德禳解性地诉求于宗教符号创建的当下价值,然后在《诗》的介质功能作用下使“想象确保了宗教有一种促使其自身发展的机制,思想因此而达到指引,超越了眼前的直接事物”[32],由此而至“雝雝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19],抑或不乏悲怆的“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19]。其三,天命崇拜。也就是说,无论《天保》祥言“天保定尔,俾尔戬穀。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19],还是《君子偕老》怒问:“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19],抑或《维天之命》感恩“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19],虽然言说立场有别,却都显意识或潜意识地共同表达着天命崇拜的宗教化社会信仰。中国的“天”及其天命崇拜,无论于世界文明版图,还是于中华文明结构,皆可以视为既具体制宗教终极神属性同时又不具终极神存身给定其特殊超验力量的表现形式,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中国人的日常生存现实都有超越体制宗教终极神的影响力量,因而或多或少存在于《诗》中就具有历史必然性。此议的重心不过在于,《诗》对天命崇拜的诗性言说,代表了原始宗教晚期中国社会对至上超验力量的肯定形式,而这种肯定恰恰就是中华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的核心之所在。此后凡老子“天乃道、道乃久”[33]、孔子“畏天命”[1]196、墨子“顺天意者,义政也”[34]290、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1]220,亦皆如是。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即使处于巫筮文化鼎盛背景之下,宗教意识形态建基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对于社会形成和发展具有功能支撑的完全有效,于是制度建基由此就凸显为社会建基的要义所在。所谓“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21]220,所谓“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19],所谓“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19],所描述的无不是西周封建制度创建及其创建中的秩序功能基本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创建核心,今人冯天瑜先生归纳为“宗法封建制”[35],以区别于夏商由神话叙事得以还原的“氏族封建制”。虽然《诗》对于社会制度创建的诗性呈现及其这种呈现对现实再创建的观念反哺,其精细程度必不若《书》之诸如“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22]782,《礼》之诸如“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29]179,如此等等。但问题是,无论《北门》个体感受的“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谪我”[19],还是《伐檀》集体质疑的“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19],抑或是《雨无止》国危嗟叹的“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为恶”[19],《诗》中此类诗性言说所能聚焦之处就在于,宗法封建制的社会制度建构过程漫长而且复杂,既非线性递进轨迹,亦非弹性凸显界面,其制度驱动能量、制度建构变异、制度功能恰配、制度利益冲突乃至制度运行调节等,无不在“哀民生之多艰”与“多难兴邦”中基于历史生成条件渐长渐成,且成长出与雅典“武装的公共权力”[25]制度形态分异的先秦中国“礼乐体制”。当然我们还必须面对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孔子“不学《诗》无以言”命题陈述所在时域,早已是“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1]169的所谓“礼崩乐坏”天下颓势。《左传》所载如“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10]824,又或者《晏子》所载如“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内给之祭”[36],已然成为朝野方国诸侯每日常态。而所有这类外在常态之中的内在变数,无非就是“礼制”基本社会制度的能量裂变与重建赋力,礼乐体制建构与解构由此也就演绎为制度建基的互驱动力,所以创建裂变和重构都应该历史理性地理解为制度建基的有机过程。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制度变迁是社会扩容与拓值的要义所在,从而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渐变抑或突变的制度后果,且这种后果的存在阈限在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37]3,而《诗》的历史存在必然逻辑或者言说魅力,恰恰就在这一阈限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更具价值隐存却又往往被忽视的社会建基意义在于,《诗》在具有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建基的典坟地位之外,另一重要功能就是以其诗性言说张力,尽可能延展兼顾宏观与微观日常生活建基的文化担当。这种非目的性预设的担当本身,不仅引风气之先而后氛围化为习俗,而且在日起日落儿女情长的文字渲染中产生无可估量的日常价值漫溢效果,并由此能使受众循迹洞穿生存表象之坚甲,而领悟生存活性的“因缘”与“指引”[4]95-108,从而也就在非自觉状态下积聚起富有文化理性之日常社会驱动能量。驱动有效首先体现为“沉默多数”的“遮蔽”状态因《诗》而向着“世界”得以敞开,且敞开的往往不是朱熹贬义指涉的“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38],还更广泛地呈现为因丧失话语权和言说能力的沉默多数所最大社会载量的诸如农事日常、战事日常、家事日常、心事日常直至种种杂事日常。之所以被“遮蔽”,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无法进入宗庙叙事现场、朝廷叙事现场和其他种种宏大叙事现场,于是历史时空和文化进程就因文化特权者“时代的幻想”而总体显形为“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超于世界之上的东西”[39]173,或者将世界极化为少数人现场狂欢的“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40]5。只是《诗》作为那个时代的经典文本,才能在内史辈执着于“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29]406之外,让征夫苦不堪言的“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19],或者恋人言难尽意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19],成为现实生活更具普遍意义的日常真相,世界由此走向存在论价值维度的庶民同样在世。驱动有效其次体现为“生存细节”的“漠视”命运因《诗》而转向生存自觉,即不仅“沉默多数”庶民的遮蔽真相得以在世敞开,而且由士大夫直至君王们被漠视的生存细节也成为有价值的自觉追求,宏大叙事、崇高叙事抑或神圣叙事如《毛公鼎》宣王誓言的“用卬邵皇天,绸缪大命,康能四国,欲我弗作先王忧”[41],又能有宫廷日常叙事的“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宾客,且以酌醴”[19],或者民间日常叙事的“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19]。这些日常叙事虽呈现出明显的格差社会生活内容,但就其价值而言,日常性建构无疑具有《诗》所在时代中国社会史诗性言说的同质性,而同质的核心所在,则是于社会时间频谱初端对日常社会予以此后无法评估的生存激活,并且激活的“生存细节”由此可以逃脱“漠视”命运成为社会生活的合法化存在形态。驱动有效其三还体现在“日常个体”的“沉沦”因《诗》而人格凸显,因为无论“天下国家”总体预案中的“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21]261,还是处于现实之困中的“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19],都体现为超主体性使得个体难以获得主体性乃至主体间性,被动性生存的芸芸众生于是也就在无限“沉沦”中失去个体人格建构的权利与机会。虽然《诗》所关涉的如“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19],又或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19],抑或所谓“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19],对于人格独立与个体主体性意义构建依然极其有限。但相较于《诗》五百年生成史及其后诸子百家崛起与个人化世俗生活的日常社会延展,能量内驱之功依然不可小觑,其中深刻地隐存着现代价值观“在世间,人的个体人格、人的独特性和人的命运无与伦比”[42]的历史缘起。总之,《诗》的日常社会建基,对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文化史而言,意味着发现社会和拓展社会,甚至意味着大地、家园和生存史的价值垒筑,由此而使其所栖居的社会得以在蹱足而至的轴心时代产生强大的社会能量裂变与社会建基后果。
三、“道德建基”必然诉求

按照“在天成像,在地成形,变化见矣”[45]145的生成逻辑,则《诗》在致力道德本体拓值的过程中,一个突出先在优势就是通过诗性言说方式,纷繁变化地展现具有意义症候的形象,进而在形象塑造中以一种无限能指创建的自由姿态,将道德本体渐进性地予以确证,所以清牛运震极为叹服“只‘窈窕淑女’二语已足,便极正大蕴藉,不必更加奉神灵、正纲纪等语”[46]。今人以“文本”统计方式,得出“《国语》引诗共引23次,《左传》引诗,除‘君子’所引51例不计之外,共有129次”[47]的计量社会学靶向成果,其学理合法性与研究范式转换的内在价值就在于,《诗》的“本文”为“文本”的社会引用提供了意义得以衍生和漫溢的“能指”存在前提。其实无论“吴公子季札来聘……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10]668,还是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61,抑或祭公谋父“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其德而后其性……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40]2,都是在“能指”言说维度语用其《诗》与道德价值的关系,并且这类语用方式在后世《韩诗外传》中,几乎演绎为某种模式化的解《诗》方式和《诗》证方式。因此才有具证个案如“兽穷则啮,鸟穷则啄,人穷则诈。自古及今,穷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诗》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善御之谓也’。定公曰:‘寡人之过矣’”[48],因为这一个案能指张力在于《诗》句与议题之间不过是间接意义换算关系,换算之后才能回到君王当德治方有善治的所议话题。由此不难看出,《诗》以其诗语的言说能力获得道德建基的能指性,能在异处语境异类德目和异义理解等不同维度和界面,实现因事而异或者因人而变的道德教化功能,并因这种功能语用广泛性与语旨多维化而确立其本体性道德建基的能指无限价值地位。例如,恰恰在能指随机的鲁隐公三年周、郑交恶进而互质,就有所谓“君子”议其“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10]53。而能指无限之所以成为《诗》别于《书》的功能特质,就在于诗性言说能展现“世界之为世界”,并且“存在者以因缘(上手状态)的存在方式在一个世界中来照面”[4]108,不过因其形象之魅从而导致“凝视”与“领会”以及黑格尔式“生气灌注”[49]中的意义澄明与价值展望,所有这一切又都可以归源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50]。概而言之,《诗》的形象建构及其道德意义张力,为所在时空的传唱者、倾听者、阅读者、吟诵者乃至凝视者,提供超越后继汉儒,基本德目归类更为丰富也更具影响力的能指性道德教化内在本文与外在文本,并且这一切都是《诗》经学化乃至文学化之前的《诗》发生史事态,所以其道德建基因能指言说能力而具社会化意义漫溢后果,情形俨然毛亨等笃信的“《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51]。

在递进意义上,基本言说能力的诗意能指形象与所指形象,在《诗》的道德教化功能中还只是与社会受众的生存论“照面”,而抵达“悟”或者“领会”后果还得凭借本体论层面的“意象”,一种想象性内在而且间接形象构成的聚焦态意义存在体。因而《诗》在诸多道德意义承载的意象指引下实现所在时代道德建基。与“能指”和“所指”形象不同的是,意象的道德功能实现途径在于随机的“意指”关系构建,因而意指意象就成为《诗》道德建基所具有的更为强大内驱动力。现代苏珊·朗格所谓“意象真正的功用是:它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59],与远古《周易》所谓“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47]147,就《诗》作为言说对象而言,其有效性功能叠合或许就在于,隐匿于形象之后的那些意象,既是外在形象的内在凝视化生成产物,更是内在意义的外在沉浸化价值结晶,由此方可使《诗》在社会延展过程中以其诗意言说而道德担当于“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202。就《诗》的历时生成进程与共时面对现场而言,真实状况显然大相径庭于后世经学化与文学化价值呈现方式,风、雅、颂各篇章具有“文化濡化”存在功能的每一种意象,与所在时域传唱者、倾听者、阅读者、吟诵者乃至凝视者的功能效应,完全取决于他们与《诗》及其特定隐存意象之间的意指关系建构程度、链接方式以及意义聚焦位置,并且所有这一切又都随着时间、地点、条件和接受主体介入方式等不同而呈现彼此间意指关系变化,当然也就包括道德意义和价值的所在时空位置现实变化。总而言之,《诗》的丰富意象与《诗》生成背景的最重要意指关系之一就是道德意指,而这一核心价值所在的意指意象,因其具有“本文”在“本人”中的“得意在志象,得象在忘言”[60]的转换功能,足以形成个体和社会不可或缺的道德自律、道德他律和道德共律,因而能够以《诗》文本和《诗》本文的意象意指功能确立其道德建基的典坟地位。虽然韩非子“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遂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3]445的代际转换判断,其“上古”所覆盖时域必包含想象性叙事的夏商乃至更早以前,但对于西周的全覆盖则更具确指性,而这恰恰是前轴心时代中华文化道德建基的关键时期,乃至春秋初晋重耳之世德目语义能较为完备地指涉善政之求,由此才有《国语》所载“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40]44。
四、“真值”时限与“真值率”减存
既然《诗》于所在时域具有语言建基、社会建基和道德建基的重要功能进而成为知识文本典范,那么建基过程依然进行中的历史现场,“不学《诗》无以言”作为基本知识命题就一定具有极高的命题真值率,因为命题缘起既是建基的价值成果,同时又是知识延展和价值增量的逻辑起点,既吻合西方古典知识论的“一切教授及一切理智学习都源于业已存在的知识”[61],也嵌入中国古典知识论的“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1]202。
孔子给定这一知识命题,按照《史记》所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62],参照《孔子家语》“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葬于防。至十九娶于宋之幵官氏,一岁而生伯鱼”[63],再参今人《孔子传》“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亦有云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者。其间有一年之差。两千年来学人各从一说,未有定论”[64]。则这一命题依照混沌学“使用多值逻辑来分析含混性面临一个进一步的问题:高阶含混性现象”[65]的时域阈限可处置办法,无论如何命题都建构于鲁昭公年间,而且估计孔鲤的可能入学时间甚至能将阈限精微至昭公二十年作为定准标杆的正负五年之间(公元前527—517年)。如果郑玄《诗谱序》“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66]疑中或有不疑之处的话,那么《诗》发生史末端距命题阈限只在百年之内,而录自《传说汇纂》的所谓“《作诗时世图》更将《陈风》的《株林》与《泽陂》系于周定王之时”[28]40,由此使得两诗只能作于周定王鲁宣公与陈灵公的时域叠合的公元前606至599八年之间。详检鲁宣公三年至鲁宣公十年(时域叠合期)的《春秋经》与《左传》所载内容,惟宣公九年所谓“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10]381,或与《株林》的“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19]有怨刺的所指隐喻叙事内在关联。至于《泽陂》及更早一些的《月出》,则显然是日常生活扩容的社会建基诗性言说,这种能指形象将会真切而丰富地与不同的涉入者,产生或情或理的异质性意象意指关系。而所议的要点不过在于,强调《诗》发生史末端与孔子知识命题凸显的时域和语境乃是时间线性未曾绠断的相同历史背景,因而诗旨价值向度与命题功能指向,缘起于同质性社会存在条件和同向性社会发展诉求,意即“不仅在空间中必然有彼此并列的历史,而且在时间上也必然有前后相继的历史”[39]852。
正因为如此,对该命题真值率的检验与追问,必得嵌入孔子生存的“世界”及其建基高峰期的历史语境,因为这一历史语境无论社会价值诉求如“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10]853,还是个体知识启蒙如“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174,抑或逆向历史还原细节求证如“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括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40]229,都处在求知而非已知的知识存在状态,甚至会程度不同地境遇类同于“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109。这种境遇类同本身,意味着可称之为“建基语境”的宏伟历史语境现场,正统辖着包括前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直至后轴心时代的知识进展与言说能力逐步升级,而孔子要求弟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56,或者荀子在稷下学宫告诫弟子“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介尔景福’”[21]2,由此也就不是偶然劝学事件而是整个社会的必然价值诉求,并且这种必然价值诉求在社会存在本体与日常个体生存之间一定形成巨大的历史语境压力,其中包括“不学《诗》无以言”的命题知识压力项。其压力项的必然确证与义项构成,远不止于《礼记》所说的“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66]。
事态的进一步真相更在于,孔子所拟知识命题必然性制约的历史语境,愈是后轴心延伸其变异就愈明显,社会存在本体的增量与拓值以及所有建基成果的知识化延伸,使得或然性选择成为士大夫以言说能力支撑其身份确证与入场有效,增加了更多可能性。虽然战国以后士大夫个体依然汲汲于孔子“沽之哉!我待贾者也”[1]128的列国游说方式,也依然会孟子般以《诗》为有力依据说服梁惠王“与民同乐”,即所谓“孟子见梁惠王……《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45]231,其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志趣下如何满足知遇诉求的所谓“且夫遇也,能不预设,说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触上意,故谓之遇”[68]。但时过境迁,《诗》发生史乃至整个建基时代的历史逻辑与社会生存现实已然进入代际转换过程中,而且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时间社会学的“频谱”与空间社会学的“场景”变化万千,由此使得更大规模的士大夫知识个体,迥异于孔子及其所在历史语境中的诸如鲁叔孙豹、齐晏婴、晋叔向、楚倚相、吴季札等,《诗》与他们的知识依存关系,或然性价值显然大于必然性价值,一切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语境变迁后果。变迁以后,便有墨子一方面肯定性称道“《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善其顺法则也……故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既可得而知已”[34]300,另一方面因质疑其日常功能价值泛滥而否定性追问“或以不丧之闲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69]庄子在知识存在论维度客观看待《诗》的意义真实性,所以才端庄笔调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70]238,却在知识生存论维度冷嘲热讽“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70]238事至商鞅、韩非一脉,则《诗》的功能竟到了被认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知识游戏状态,所以才有《商君书》的诸如“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贪”[71],甚至到了伦教非伦的文本依据沦丧地位,所以才有《韩非子》所谓“《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13]467。极限挑战至此,不是简单学派切分与立场之争概而言之就可以了事,而是命题必然性制约与命题或然性制约的历史语境复杂变迁结果,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看做整个社会的知识进化使然,而这种进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士大夫个体不学《诗》也可以言,也可以在《诗》之外获取更多元化或多样性的社会存在表达方式与个体身份确证方式。所以,面对建基时代《诗》发生史功能地位现实状况,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知识命题无疑乃所在历史语境制约使然,是真值率极高的知识命题,但是,随着历史语境变迁,新的制约力量也决定了这一知识命题真值率渐次衰微的存在宿命,尽管从未厄运至因归零或转负而沦落伪命题的地步。
余 论
必须指出,“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受所在历史语境制约现场拟置的知识学命题,而我们对命题合法性和真值率的有限解读,完全基于《诗》发生史意义生成与价值实现的存在方式与时空阈限。所议对“不学《诗》无以言”高真值率于特定边际条件的价值判断,是对具体命题及其关联事态的理性把握,丝毫不影响《诗》作为中华文化建基时代“高不可及的范本”之一的崇高地位,情形如同原典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待古希腊神话,一方面,深刻地把握到“困难不在于理解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37]711;另一方面,尖锐地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37]711,而这两方面事态的社会存在依据,不过在于“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25]34。
注 释:
①“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参阅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6页。
②相关表述参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33页。
③与许慎此说编序不同,班固称之为“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参阅班固:《汉书·艺文志》,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765页。
④“由致动发展为使成式,是汉语语法的一大进步。”参阅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1页。
⑤本文凡例《诗》,均据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即参考文献[19]),不另标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