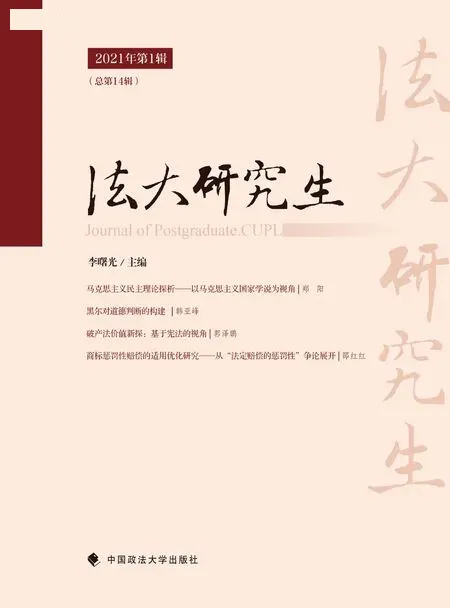论证型式:司法人工智能的希冀
2021-12-08朱赫夫
朱赫夫
人工智能与司法的联姻是近年来学界之兴趣所在。我们身处在一个各方面都蓬勃发展的年代,一方面是人工智能的“奇点”不断逼近;另一方面是法典化运动结成硕果。将两项激动人心的时代要素联结到一起,这是自然而然的想法。在浪漫畅想之余,不应只停留在描绘蓝图的阶段,还是有值得严肃探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公布后,对司法人工智能是否有益?在当今的科技水平下是否可行?若有不足,那么现阶段我们能做什么?
一、冷与热:司法人工智能在中国
(一) 司法人工智能的肇始
首先应当区分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人工智能与法律”和“法律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法律(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是一个学科概念,泛指研究法律中人工智能问题的学问,新兴于20 世纪90 年代,是计算科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有同名旗舰刊物《人工智能与法律》;而法律人工智能(Leg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一项技术概念,指各种处理法律问题的人工智能技术。法律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法律下辖的一个研究分支,两者之关系可类比于民法与法学。法律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很宽,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方面。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是“司法人工智能”(Jud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即由人工智能进行法律推理和裁判的技术,俗称“人工智能法官”。
法律界正式开始关注司法人工智能,起源于1970 年布坎南(B.Buchanan)和亨德里克(T.Headrick) 发表的《关于人工智能与法律推理的思考》。文中首次探讨了人工智能作为法官的可能性。〔1〕See B.G.Buchanan &T.E.Headrick,Some Speculation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Reasoning,23 Stanford Law Review (1970).1977 年麦卡锡(T.McCathy) 设计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动法律系统TAXMAN。〔2〕See L.Thorne McCarty,Reflections on TAXMAN:An Experiment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egal Reasoning,5 Harvard Law Review,837-893 (1977).随后学者们开创了人工智能与法律(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这一领域,1987 年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人工智能与法律大会(ICAIL)”,迄今已召开了29 届。人工智能与法律领域虽然有很多议题,比如人工智能的人格、权责等,但是“自动法律推理”一直享有重要地位。〔3〕参见郑戈:《人工智能与法律的未来》,载《探索与争鸣》2017 年第10 期,第78~84 页。此方向的开创者是梅德曼(Meldman) 和加德纳(Gardner)。理士兰(Rissland) 和阿什莉(Ashley) 构建了第一个自动推理系统“海珀(HYPO)”。在其基础上理士兰和斯卡拉克(Skalak) 开发了“卡巴莱特系统(CABARET)”。〔1〕参见[荷] 亨利·帕肯:《建模法律论证的逻辑工具——法律可废止推理研究》,熊明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 页。此领域现已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涌现出了一大批世界知名学者,如戈登 (Gordon)、帕肯 (Prakken)、萨托尔(Sator)、维赫雅(Verheij) 等。
(二) 冷:理论界的抵制
尽管“司法人工智能”这一论题在西方已蔚为大观,但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真正引起国人学术兴趣的是2016 年AlphaGo 横空出世,之后国内关于司法人工智能的讨论突然繁荣。〔2〕相关讨论参见贾章范:《司法人工智能的话语冲突、化解路径与规范适用》,载《科技与法律》2019 年第6 期,第59~67 页。司法人工智能的讨论可以划分为实然与应然两块。应然是理论界探讨“应不应发展司法人工智能”;实然是实务界关心“怎么发展司法人工智能”。
司法人工智能在国内理论界受到了一定的抵制。除少数“变革派”学者支持外,大部分法学家都属于“谨慎派”,认为司法人工智能的前景并不乐观。〔3〕参见马长山:《AI 法律、法律AI 及“第三道路”》,载《浙江社会科学》2019 年第12 期,第5 页。主要理由与西方知识界相似:其一,司法系人民主权之产物,不得为非公民(非人类) 所掌控,技术黑箱可能带来伦理问题;〔4〕参见[美] 卢克·多梅尔:《算法时代:新经济的新引擎》,胡小锐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 页。其二,司法系复杂之权衡艺术,AI 难探幽微人心,终究只能学得皮毛;其三,司法在于定纷止争,事关人与人的沟通,这是AI 无法替代的。〔5〕参见季卫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载《东方法学》2018 年第1 期,第131 页。
(三) 热:实务界的期望
司法人工智能在实务界却获得了非常高的期望,甚至可能有点急迫。西方对司法人工智能的研究存在伦理枷锁,技术先进而实践受限;我国则是实践追捧,而技术水平尚为不足。〔6〕参见左卫民:《热与冷:中国法律人工智能的再思考》,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 年第2 期,第53~64 页。
司法实务部门有客观需要。一是法院“诉讼爆炸”。现在一线城市的法官一年判案数可达到数百件。基层法院不堪讼累,此时司法人工智能似乎成了一条破解之道。〔1〕参见程金华:《人工智能与法院大转型》,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 期,第33~48 页。二是法律人也排斥劳动异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各部委的规章办法,总量令人生畏,任何一个法律人也不能全部掌握。这导致法律实务中,查阅、整理、搜集、文书等的机械工作占用了法律人的大量时间。对于劳动异化之抵触,也是催生司法人工智能的动力。〔2〕参见季若望:《法律的再生:人工智能时代的凤凰涅槃》,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4 期,第119~121 页。三是人工智能也许能更好地维护公平正义。克服人性之私与恶是永恒的难题,我国文化支持“圣人独断”。因而在未来,人工智能进行审判或者监督司法可能会成为常态。〔3〕参见潘庸鲁:《人工智能介入司法领域的价值与定位》,载《探索与争鸣》2017 年第10 期,第101~106 页。
国家层面予以最高优先重视。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指出:“建设集审判、人员、数据应用、司法公开和动态监控于一体的智慧法庭数据平台,促进人工智能在证据收集、案例分析、法律文件阅读与分析中的应用,实现法院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智能化。”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提出了各自的“智慧方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智慧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则深化“智慧检务”。
各地实践如火如荼。在东部地区,法院已经形成了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服务、智慧管理的“四智格局”。〔4〕参见袁春杰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法院建设中的应用》,载《人工智能》2020 年第4 期,第56~65 页。庭审阶段基本上已实现了记录电子化,“科大讯飞”开发的语音识别能达到一般书记员的水平。裁判环节出现了类案推荐、偏差预警、摘要提取、自动生成判决等技术。〔5〕参见帅奕男:《人工智能辅助司法裁判的现实可能与必要限度》,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4 期,第101~110 页。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的“类案推送系统”、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推出的“C2J 法官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信息管理系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江苏法务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睿法官”。〔6〕参见徐骏:《智慧法院的法理审思》,载《法学》2017 年第3 期,第55 页。那么,司法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在地平线上了?
二、“电子赫拉克勒斯”来了吗?
德沃金将完美法官称为“赫拉克勒斯”,那么司法人工智能就是“电子赫拉克勒斯”,它来了吗?很遗憾,司法人工智能在现阶段还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迄今声称成功者,要么是偶然的,要么适用条件苛刻。根据人工智能的技术定义:人工智能要能自主完成学习、判断、决策等人类行为。〔1〕参见杨正洪、郭良越、刘玮:《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2 页。以此观之,现阶段之“司法人工智能”大多只是噱头。
人工智能可分类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完全人工智能)。〔2〕参见李开复、王咏刚:《人工智能》,文化发展出版社2017 年版,第26~37 页。司法人工智能是否能达到弱人工智能呢?司法人工智能的关键在于自动推理(automatic reasoning),推理有四种:演绎(deduce)、归纳 (induce)、类比(analogy) 和溯因(abduction)。其中演绎推理最为简单,因为具有封闭性与必然性。那么司法人工智能能否做到演绎推理?我国各地的审判辅助软件和智能司法系统,以演绎推理为主,类比推理为辅,处理一些民事关系较为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14]要使司法人工智能通过演绎法实现自动推理,至少(且不限于) 要满足以下条件:法律规定足够细致和完备;人工智能能够准确识别语言;人工智能能够合理地匹配法律规范。
(一) 法律规定仍不够细致与完备
《民法典》的公布,毫无疑问离司法人工智能更近了一步,但和能作为人工智能使用的细致完备的需求仍有距离。
条文数量可以作为衡量法律完备的指标,《法国民法典》有2281 条,《德国民法典》有2385 条,即便是德法两国,靠2000 多条的民法典仍不足以应付法律实践,还会配套以汗牛充栋的“法典评注”(Kommentar),如著名的《施陶丁格(Staudinger) 民法典评注》共有44 卷之巨。〔3〕参见贺剑:《法教义学的巅峰——德国法律评注文化及其中国前景考察》,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2 期,第381 页。德法之法律规定尚不足以支撑其司法人工智能化,即便竭尽立法者之心智,也会有法律漏洞,总会有法律没有予以规定的案件。〔4〕参见[奥] 恩斯特·A.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153~156 页。若允许司法人工智能进行法律续造,且不说合法性问题,在技术上就超出了现有之技术水平。〔1〕参见王烁:《论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司法的态度、途径和阶段——以轻微刑事案件为契机的分析》,载《科技与法律》2020 年第3 期,第65 页。
(二) 法律语言识别还不可行
当代人工智能在识别自然语言上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已能识别一些相对复杂的自然语言。但是要对法律语言的识别,还显不足。
法律语言的识别进路与自然语言不同。自然语言的识别,关键在于谓词(predicate)。通过识别谓词可以把握句子的结构,就能解析句子的主要信息元,现阶段的语言识别技术都集中于此。〔2〕参见邱德钧:《人工智能中一阶逻辑的现代表达方法》,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6 期,第354~357 页。但对于法律文本而言作用有限,因为法规的关键信息在于概念,而谓词所含信息量较少,不足以把握法律语句的核心意思。
法律语言是裁剪性的。司法分为法的发现(discovery of law) 与法的证成(justification of law)。前者是推理出结果的过程,后者将结果进行充分说明。真正有经验的法官,都是在衡量是非之后,谨慎地“裁剪”事实,而得出法律语句组合。〔3〕参见方乐:《能动司法的模式与方法》,载《法学》2011 年第1 期,第30~39 页。通过对司法裁判书的自动学习,无法还原司法推理(发现)之过程。
(三) 人工智能无法合理匹配法律规范
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不能满足,那么合理匹配法律规范就是更加遥远的事情了。
司法人工智能的多解冲突是最大问题。立法过程中往往会设想规范对应的特定场景,然而实务案件可能并不如立法者想象得那样分明。因而很多案件会出现交叉特征,导致分类冲突,案件可以归摄到不同之法条下,且都是正确的。〔4〕参见雷磊:《法律规范冲突的逻辑性质》,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6期,第3~18 页。问题在于法律结果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在系统输入单一信息,却会输出多解。即便可以设定冲突规则,但也面对同等效力位阶的多解。〔5〕See Leenes R.&Lucivero F.,Laws on Robots, Laws by Robots, Laws in Robots: Regulating Robot Behaviour by Design, 6 Law,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pp.193-220 (2014).
司法人工智能也难以处理价值与利益。法律是承载价值与利益的,有的在原则中出现,但更多是非文字的,存在于社会观念中。现行的“人工智能法官”之预测,建立在指定信息库之上,但关于社会价值之考量还完全做不到。〔1〕参见白建军:《法律大数据时代裁判预测的可能与限度》,载《探索与争鸣》2017 年第10 期,第95~100 页。若人工智能设定特殊的算法,凌驾于一般规则算法之上,就可能会造成两种算法的混乱和规则的架空。〔2〕参见季卫东:《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议论》,载《法学研究》2019 年第6 期,第32~49 页。
而且司法人工智能所运用的“涵摄模式”本身就受到了挑战。与“涵摄模式”针锋相对的是“等置模式”,即司法审判并非只是将案件事实涵摄入法条之下如此简单,而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眼光流转”,事实的定性与规范的选取是相互扰动的。在法律实践中,判决是通过反复权衡达致的,还需要进行详尽说理,也无怪于有人认为法律是“艺术”。〔3〕参见郑永流:《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 年第1 期,第140~149 页。现阶段人工智能也许能做到人类的封闭性的技术,但对于开放性创造还捉襟见肘。
三、三条进路:司法自动推理如何可行
现阶段与其纠结于司法人工智能会怎么样?该怎么样?不如务实一些,讨论在现今之技术条件下,我们能做哪些工作?目前司法人工智能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司法自动推理,有三条进路:完全自主学习、限定干预学习和个案实践学习。
(一) 完全自主学习
完全自主学习又称法律自动推理机(legal autonomous reasoning machine)。这是司法人工智能的完全形态,所有法律问题只需通过一个系统或就可解决。这要求自动推理机独自完成全部工作,如解读原始资料、选定参考类别,证成结果等功能。〔4〕参见郑戈:《算法的法律与法律的算法》,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 年第2 期,第66~85 页。这种方法的优点自不必说,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全部问题。这样官员只需要进行最低限度的训练便可使用,大幅度提高司法效率,即使边远地区也能享受到现代的公正司法;缺点是,制作这样一个机器或系统几乎是不可能的,远超现在技术的能力。制作这样一个自动推理机,所投入的人力与物力也是天文数字。现实问题之外,还有封闭逻辑系统的噩梦——哥德尔定理 (Gödel's Completeness Theorem),宣判了自动推理机的死刑。
(二) 限定干预学习
限定干预学习(constraint autonomous learning) 需要人为选定数据库与设定标准,在个别情况下还需要对算法进行修改。人工智能需要在人为设定的界限与框架内进行学习,通过一定量的训练,从而逐渐接近人工处理的准确率。在很多领域中都使用限定干预学习,比如医疗、社会管理等,Alphago 也是限定干预学习。〔1〕参见何清等:《大数据下的机器学习算法综述》,载《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2014 年第4 期,第327~336 页。优点是:相对完全自主学习而言,需求的资源要更少。理论上只要学习量提高,AI 可以无限制地逼近人类法官;缺点也很明显:“过拟合”(overfitting) 现象,在样本不足或偏差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garbage out)”现象,瑕疵样本生产出无用数据。还有法律是“开放文本”(open-texture),不是限定的,这直接推翻了限定干预学习的预设前提。〔2〕参见徐娟、杜家明:《智慧司法实施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载《河北法学》2020 年第8 期,第188~200 页。
(三) 个案实践学习
个案实践学习是通过实践案件进行学习,而逐渐接近人类法官的判决。前两者都采取外在视角观察法律,将判决书和数据库检索视为法的本质。这是当代科学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即便是研究法律这种悠久与复杂的学科,也不关心其自身的特质,依然秉持外观主义。传统方法都是基于弗雷格的数理逻辑(形式逻辑) 之上的,然而数理逻辑只具有“保真性(truth-preservation)”,即前提为真,结论必为真。这是否能适用于法律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案件事实也许有真伪,但是法律结果(司法判决) 不具有真伪性。对于判决而言,更重要的是合法性与可接受性。这两个性质的传递被称为“保权性(entitlement-preservation)”,这意味着需要数理逻辑之外的逻辑工具,才能适用于司法人工智能。
法律本身系实践之产物,自然也要回归到实践中才能认识到法律之特质。这是尊重科学态度,也才有可能达成目标。当然实践非常复杂,需要法学家清理出“道路”,为司法人工智能提供一个适宜学习的“窗口”。这个“窗口”应最接近法律本质,同时又能降低人工智能的学习难度。
四、实践转向——论证型式
近年来,西方司法人工智能的研究也出现了实践转向,论证型式(argumentation scheme) 因为贴合法律本质,又易于人工智能学习,成为重要的新进路。论证型式又称论辩方案,它不同于逻辑学按照形式分类,而是依据论证的实质内容进行分类。论证型式是由不同论辩在某一原则作为共同项而形成的集合,并附带了一系列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critical question),以评估在特定案件中的应用是可以被允许的。〔1〕See Henry Prakken,AI & law,Logic and Argument schemes,19 Argumention,pp.303-320(2005).针对关键问题的回答,是检验论证是否能成立的关键。〔2〕See G.C.Goddu.Walton on Argument Structure,1 Informal Logic,pp.5-25 (2007).
论证型式符合真实的法律,节省资源,又不会遭遇技术黑箱与赛博极权的质疑。首先,论证型式最为贴合法律,符合法庭的真实过程。在实践中,法官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为了效率起见,法官往往会归纳“争点”,使得双方集中于讨论几个关键问题,而双方对于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才是影响案件胜负之要目。其次,论证型式最节省资源。法官是考量到法律中的要件规定,结合案情而总结出关键问题。〔3〕参见纪格非:《“争点”法律效力的西方样本与中国路径》,载《中国法学》2013 年第3 期,第109~120 页。既然司法中是通过此种方法可以降低工作量,那么人工智能同样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节省算力,开发难度也会大大降低。法官实践使用论证型式,人工智能通过论证型式来进入实践。多余的内容不需要再耗费资源分析,而只有合乎关键问题的内容才被采纳。从原先机器进行检索和挖掘,转由机器学习评价。最后,论证型式可减少合法性的阻力。论证型式从人的思维结构和文化背景中来,这意味着法官和普通人都能进行核验。〔4〕See Henry Prakken,On the nature of Argument Schemes,in Dialectics,Dialogue and Argumentation:An Examination of Douglas Walton's Theories of Reasoning and Argument,pp.167-185 (C.A Reed and C.Tingdale eds.,College Publications 2010).对于关键问题之回答是当事人自主的,人工智能并不会越俎代庖。
(一) 法学的实践转向
法律的本位在法庭,庭审之灵魂在论辩。司法的本质是“判断权”,由法官裁断双方论辩孰为合理。古希腊时期,法学还未形成,法庭论辩已然发达了,因此产生了修辞学。〔5〕参见刘兵:《作为修辞的法律——法律的修辞性质与方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9~62 页。修辞学要求演讲者掌握道德性(ethos)、情感性(pathos) 和逻辑性(logos),这些组合形成的固定模式,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恩梯墨玛(Enthymeme)。这种技术曾被人称之为“修辞三段论”,也被称为“常识论式”,此为论证型式之滥觞。〔1〕参见舒国滢:《西方古代修辞学:辞源、主旨与技术》,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 年第4期,第33~52 页。随着法律实践的积累,形成如何处理论辩的实用手册,这被称为“论题”(loci)。〔2〕参见舒国滢:《论题学:修辞学抑或辩证法?》,载《政法论丛》2013 年第2 期,第3~11 页。
近代法典化运动,使得法学约同于“立法学”,逐渐忽视了论辩。二战后,法律的实践性开始受到重视。法律不是纯粹客观或主观,而是依托于法律之论辩形成的“主体间的客观共识”。论证型式由佩雷尔曼(ChaÏm Perelman) 在《新修辞学》中首倡复兴,他认为论证型式是听众在其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定式认知模式。论证者只需给出前提,听众自动推演出结论。〔3〕See ChaÏm Perelman &L.Olbrechts-Tyteca,The New Rhetoric: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pp.26-30 (J.Wilkinson and P.Weaver eds.,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69).随后图尔敏(Stephen Toulmin) 提出了著名的论证图示(argument diagram),数据(data) 通过凭证 (Warrant) 而成为假设 (qualifer),而凭证需要支援(Backing) 予以支撑,假设需要经受反驳 (rebuttal) 之检验而成为结论(Claim)。〔4〕See Stephen Toulmin,Richard Rieke,Allan Janik,An Introduction to Reasoning,pp.349-368 (2nd ed.,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84).数据、凭证、支援等内容组成了论证型式,反驳作为关键性问题,因而图尔敏模式可以算作是论证型式的一般模型。菲韦格(Theodor Viehweg) 证明法学问题的处理是按照特定论题模式,而并非简单的演绎或归纳推理。菲韦格称这些法律运行模式为“论题学法学”(topical jurisprudence),诚为司法论证型式之先声。〔5〕参见[德] 特奥多尔·菲韦格:《论题学与法学——论法学的基础研究》,舒国滢译,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75~79 页。
(二) 司法人工智能中的论证型式
自20 世纪80 年代起,人工智能与法律被当作计算科学的一个分支。这一定性在21 世纪后,发生了“论证型式转向”。非形式逻辑与形式逻辑终于结合起来,而不再是对抗。〔6〕See Johan van Benthem,One Logician's Perspective on Argumentation,2 Cogency,pp.13 -26(2009).在现代学者看来,论证型式似乎是用以开发计算机来分析、评估甚至构建自然语言论证的最佳方法。〔7〕See Anthony Blair,Groundword in the Theory of Argumentation:Selected Papers of J.Anthony Blair,p.121 (Springer 2012).
沃尔顿(Douglas Walton) 为论证型式的发展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他认为,论证型式是非演绎推理的类型集合,由一组前提和假定以及推出的结论组成,评价者根据型式上的一组关键问题以考量其使用。在论辩中,使用者只要添加一个实例,就会自动产生一个支持推论。同时,也会为反对者提供一套关键问题,要求对方承担说明责任。若无法进行说明,则假定会被推翻,若成功则被赋予有效性。〔1〕See T.Gordon &D.Walton,Legal Reasoning with Argumentation Schemes,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137-146 (ACM Press 2009).沃尔顿在《假定推理的论证型式》中识别了29个基础论证型式,在随后的《论证型式》中细化为96 种论证型式。
董番明(Dung Fanming) 开创的抽象论证框架,从洛伦岑的《对话逻辑》(DialogischeLogik) 中获得启发,使法律人工智能从纯粹算法转向语用博弈。此框架的原理是这样的:论证框架(AF) 被定义为一对集合〈Args,Def〉,其中Args 是论证集合,Def⊆Args×Args 是双重论证交叠而成的子集。论证之间轮流攻击,经受不住攻击的被排除,最后仍站住的视为成立。〔2〕See Dung,P,On the Acceptability of Arguments and its Fundamental Role in Non-monotonic Reasoning,Logic Programming,and N-person Games,7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pp.321-357 (1995).与此类似的还有戈登(Gordon) 提出的“诉答博弈”(Pleadings Game),他的模型是基于阿列克西的“法律商谈理论”创设的。亚普·哈格(Jaap Hage) 将“法律融贯论”作为新的评价标准,提出了“基于理由的逻辑”。〔3〕See J.C.Hage,Formalizing Legal Coherence,ICAIL'01: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pp.22-31 (2001).
亨利·帕肯(Henry Prakken) 的重大贡献是将“论证型式”引进了人工智能与法律领域。他受沃尔顿的启发,认识到法律不是碎片的法条库,而是块状的论证型式。换言之,法律的核心不是法条规定,而是围绕着法律案件形成的实质型式,以及双方对于关键问题的回应。[32]他认为论证型式的本质是可废止推理(defeasible reasoning) 的规则,而关键问题是反论(counterargument) 的指示器。〔4〕See F.Bex,H.,Prakken,C.Reed,D.Walton,Towards a formal Account of Reasoning about Evidence:Argumentation Schemes and Generalisations,1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pp.125-165 (2003).于波洛克(John Pollock) 将反论分为两种,一种称为反驳(rebutting),即直接针对论点提出否定意见;另一种称为底切(undercutting),并非直接针对论点,而是切断前提与结论间的连接。〔5〕See John L.Pollock,Knowledge and Justification,pp.42-4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论证型式的关键问题,要么是针对前提的反驳,要么是针对前提间的联系(结构) 的底切,如此论证型式便可以进行建模。这样,实践至算法之间的桥梁就被架设起来。现代论证软件的原理均基于此原理之上,如ArguMed、Dialaw、Ararcaria、Rationale、Carneades。〔1〕参见武宏志:《论证型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200 页。
五、司法论证型式之构建
我国的司法人工智能研究起步较晚,有些不健康的研究趋向,比如凭空构建,或者一味排斥。法学学者现阶段能做的,不应直接自行着手技术工作(对于少数有跨学科背景的学者可行),而应考虑在当前技术条件下,能做到的又有前瞻性的工作。可以对论证型式进行研究,尤其是庭审论辩中的论证型式。
(一) 司法论证型式之作用场域
首先,确定司法论证型式的构建原则。理论上司法论证型式可以适用于整个法律阶段,从律师咨询至审判监督。但是这样从头至尾的构建没有必要,既耗费精力,作用亦有限。司法人工智能的构建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以缓解讼累为主。发展人工智能是为了帮助法律人,而不是消灭法律人。二是以法律论辩为主。法律是“语言游戏”的一种,要尊重人的主体性。三是以专家解释为主。法律专家对法律过程的阐释,优先于概率性统计。
其次,司法人工智能的适用范围应严格限定在法官工作领域。律师、检察官与法务工作者并不受诉讼爆炸之影响,只有法院才有此困境。另外,论证型式只作用于庭审环节。因为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等并不存在司法论证的诉讼构造。庭审环节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参见段文波:《我国民事庭审阶段化构造再认识》,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2 期,第87~107 页。起诉阶段,各方在法庭辩论开始前提交诉状与证据清单;质证阶段,当事人对案件所涉之证据进行举证,并发表质证意见;事实推理,各方依据之前质证的证据,在证据的基础上,进行事实的推理与叙说;法律适用,关于案件的定性,法律的适用与不适用,以及案件判决结果的意见;最终陈词。
最后,论证型式作用于质证阶段、事实推理和法律适用。之所以排除起诉阶段与最终陈词,是因为在这两个阶段论证结构是残缺的,而且几乎不存在对关键问题的回应,而且这两个阶段的主张在质证阶段、事实推理和法律适用会有重复。
笔者对建构有以下声明:其一,由于笔者之能力有限,只能进行粗略建构以抛砖引玉;其二,本文建构以法律要素为核心,偏离较远的论证不予考虑;其三,此研究仍属于非形式逻辑,仅有探讨之目的,投诸实践还不可行。
(二) 一般型式
前文已然提及,图尔敏论证图示作为一般论证型式,在庭审中也是有效的。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庭审的每个环节,细化而言都可以在图尔敏模式上有所对应,甚至每个单一论证都可以重构为此模式;其二,整个庭审过程也可视为图尔敏模式,质证与事实推理阶段为数据,法律适用阶段为凭证与支撑,而双方观点与争执为资格与反驳,最终判决为结论。在此先建构一般型式,但由于每一步重构为三段论过于烦琐,直接重建为关键问题序列。本节所有的型式构建,其原型可在沃尔顿等著《论证型式》中找到。〔1〕See Douglas Walton,Chris Reed,Farizio Macagno,Argumentation Sche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一般型式如下:
CQ1:数据是否可靠?
CQ2:凭证是否有依据?
CQ3:支撑是否能成立?
CQ4:数据是否有凭证做依据?
CQ5:凭证是否有支撑为支持?
CQ6:数据推出资格是否能成立?
CQ7:资格是否经受住反驳?
CQ8:反驳是否能有作用?
CQ9:资格是否能获得确证而成为结论?
大部分的关键问题都可以在上述9 个问题中找到原型。
(三) 质证型式
质证阶段一般都围绕着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展开。在我国,证据一般是在庭前提交的,质证环节由于证据众多,大多是一并质证的。我国质证环节的原则是,对方当事人或者法官没有异议,则证据视为通过质证。因而质证型式以“默认”为主,推定具有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但在特殊情况下会不适用一般型式,比如需要作证、间接关联与非法证据排除等情况。
1.关于证据真实性的论证
(1) 一般真实论证(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
大前提:一般情况下,A 提出证据a,在未经他人质疑或质疑不能成立,视为真的;
小前提:他人未进行质疑,或质疑未能成立;
结论:a 是真的。
CQ1:他人是否可以质疑?
CQ2:若他人质疑,质疑是否合理?
CQ3:提出的质疑是否有证据支撑?
(2) 特殊真伪论证(当事人陈述、证人、鉴定意见)。
大前提:A 处于了解S 领域的地位,该领域包括证据a;
小前提:A 断定证据a 真的(假的);
结论:a 是真的(假的)。
CQ1:A 真的了解S 领域吗?
CQ2:A 是一个诚实的(值得信赖的、可靠的) 来源吗?
CQ3:A 领域确实包括证据a 吗?
2.关于证据关联性的论证
(1) 一般关联论证(直接关联)。
大前提:对于案件G 而言,含有性质F;
小前提:证据a 有性质F;
结论:a 与案件G 具有关联性。
CQ1:是否可以切实证明a 有性质F?
CQ2:性质F 是否是基于个别性或偶然性?
CQ3:证据a 确实具有性质F 吗?
(2) 特殊关联论证(特殊关联)。
大前提1:对于案件G 而言,含有性质F;
大前提2:性质F 包括有F1、F2、F3等内容;
小前提:证据a 有性质F1;
结论:a 与案件G 具有关联性。
CQ1:是否可以切实证明案件G 包含性质F?
CQ2:性质F 是否包括有F1、F2、F3等内容?
CQ3:证据a 确实具有性质F1吗?
CQ4:F1与案件G 有关联性可言吗?
3.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论证
(1) 一般合法论证。
大前提:如果证据a 未受合法性质疑,则证据a 应视为合法;
小前提:证据a 未受质疑;
结论:证据a 合法。
CQ1:他人是否可以提出合法性质疑?
CQ2:他人提出的质疑能否成立?
CQ3:证据a 是否达到形式要件合法?
(2) 特殊合法论证(非法证据排除)。
大前提:如果A 的情况是非法的,那么与A 直接相关或获取的证据a 应不予采信;
小前提:A 是非法的;
结论:证据a 应当被排除。
CQ1:他人是否得提出合法性质疑?
CQ2:A 情况是否有明确法律依据为非法?
CQ3:A 情况是否有证据予以支撑,或线索予以开示?
CQ4:证据或线索是否可靠与有意义?
CQ5:法官是否对情况A 予以了审慎之考虑?
(四) 事实推理型式
事实推理一般先整理材料,材料有三种:质证后的证据、常识和惯习。质证后的证据可以直接用以推理,惯习需要进行证明,常识则默认适用。在材料齐备后进行推理,在我国认可的推理关系只有一种:因果关系。但实践中因果关系未必如此清楚,还会出现正相关(类比) 与溯因推理,后两者要重建为因果关系模式才能起作用。
1.关于推理材料的论证
(1) 证据假说论证。
大前提:假说认为,如果A 事件是真的,那么证据a 将会被观察到;
小前提:在质证环节中,证据a 被证明是真的;
结论:A 事件是真的。
CQ1:在此情形下,若A 事件是真则就会出现证据a 吗?
CQ2:证据a 被是否通过了质证环节?
CQ3:是否可能存在某种情况,不是由于事件A 的发生而导致证据a出现?
(2) 常识论证。
大前提:如果人们普遍接受某事为常识,无须出示证据或举证,即可视为真;
小前提:人们普遍接受事件A;
结论:A 应视为真。
CQ1:普遍接受为何可以作为豁免举证之理由?普遍接受与真之间有关系?
CQ2:有什么证据支持“人们普遍接受事件A”这一主张?
CQ3:即使普遍将A 当作真的加以接受,存在怀疑它为真的任何好理由吗?
(3) 惯习论证。
大前提:如果在某地,一种做法或实践是通行的,那么就应认为是可接受的;
小前提:在法律关系发生所在地而言,A 是一种通行的做法或实践;
结论:在此情形中,A 是可接受的。
CQ1:有什么证据或其他方式表明法律关系发生所在地的大多数人接受A?
CQ2:即使绝大多数人将A 当作真的加以接受,A 是否也是正当合理的?
CQ3:惯习做法是否违反法律基本原则?
2.关于推理形式的论证
(1) 因果论证。
大前提:一般地,若事件A 发生,那么事件B 将(可能) 发生;
小前提:在此证据下,事件A 发生(可能发生);
结论:在此情形下,事件B 将(可能) 发生。
CQ1:为什么事件A 发生会导致事件B 发生?
CQ2:证据是否能证明事件A 发生?
CQ3:存在其他会干预或抵消的因素吗?
(2) 正相关论证。
大前提:一般情况下,正相关关系可等同于因果关系;
小前提:A 和B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结论:A 与B 有因果关系。
CQ1:凭什么说正相关关系可等同于因果关系?
CQ2:在A 和B 之间真的存在正相关吗?
CQ3:可能存在某个既引起A 又引起B 的第三因素C 吗?
(3) 溯因论证。
前提1:D 是本案待证之事实或要件;
前提2:事件A1,A2,…,An都能合理说明D 的发生。
前提3:A1最能成功地说明D。
结论:A1与D 有因果关系。
CQ1:为什么A1最能成功地说明D?
CQ2:是否有其他备选事件比A1还好?
CQ3:最能成功说明,就能得出因果关系吗?
CQ4:是否进一步探索起因会更好吗?
(五) 法律适用型式
法律适用阶段,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是否适用X 法第X 条之规定?但是实践中又并非如此简单,法律之难点在于填补事实与规范间的落差,即当事人须将事实推理阶段之所证事实,归摄入法条规定之下。有的只需简单进行词义归类,有的要通过解释进行“归摄之含糊论证”。更有甚者,无法通过解释手段处理,则需要诉诸法条之外的手段(外部论证),比如先例论证(最近“同案同判”原则在我国被确认)、价值论证(诉诸原则) 和例外论证。
1.适用法条的论证(内部论证)
(1) 一般规则论证。
大前提:法律有规定,如果发生a 情形,则会导致A 法律后果;
小前提:本案属于情形a;
结论:本案将发生A 法律后果。
CQ1:规则要求A 这种情况作为要采取这类行动的事例吗?
CQ2:是否有其他规则与该规则冲突或会推翻它吗?
CQ3:本案是否是例外,是否有减轻的情况或不服从的理由?
(2) 归摄论证。
大前提:对所有x,如果x 符合要件D,那么x 可被归类为概念G;
小前提:a 符合要件D;
结论:a 属概念G 项下。
CQ1:存在D 是一个恰当要件的证据,按照其他要件可能排除a 属于概念G 吗?
CQ2:a 符合要件D 是合理的吗?
(3) 归摄的含混论证(解释方法)。
前提1:对于概念G,其构成要件为D;
前提2:要件D 通过操作方案F 进行解释,达至含义A;
前提3:事实推理所证之事实a,符合含义A;
结论:a 属于概念G 项下。
CQ1:操作方案F 是否是公认之解释,是否有更具有公信力之解释?
CQ2:通过操作方案F 解释,是否能达至含义A?
CQ3:事实a 是否符合含义A,是否能扩展至要件D?
2.超越法条的论证(外部论证)
(1) 价值论证(原则论证)。
前提1:在本案中价值V 被认为是更重要的;
前提2:价值V 在本法中属于原则P;
前提3:存在一个重要理由R,直接适用原则P;
结论:本案直接适用原则P。
CQ1:本案中的价值V 是否是最重要的?
CQ2:价值V 是否是被广泛公认的价值?
CQ3:这个理由R 是否足够重要,以至于需要直接适用原则P?
(2) 先例论证。
大前提:对于本案a 的情况,有类似先例判决E,E 与规则R 不同;
小前提:有恰当之理由R,本案应适用于先例E,而不是规则R;
结论:本案a 适用先例E。
CQ1:遵循先例在本国是否被官方公认为应遵循之法律原则?
CQ2:判决E 是否是有效的官方判决,是否类似于本案a?
CQ3:这个理由R 是否足够重要,以至于需要直接适用先例E?
(3) 例外论证。
大前提:一般地,按照已确立的规则,如果x 有性质F,则x 也有性质G;
小前提:在这个恰当的情形中,a 有F 但没有G;
结论:该规则的一个例外必须被承认,而且该规则必须适当修改或限制。
CQ1:已确立的规则真的适用这种情形吗?
CQ2:所引用案例是合乎惯例的或能被解释为只是表面上违反该规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