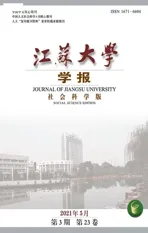赛珍珠跨国书写中的女性口述与文化记忆
2021-12-07王蕾
王 蕾
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1892-1973)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性作家。她在襁褓中就被父母带到中国,她的父亲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与母亲凯丽·斯塔尔廷(Carie Stulting)19世纪末来到中国传教,赛珍珠是听着母亲对美国的讲述、奶妈对中国民间故事的讲述、厨子和园丁们对天南地北传闻的讲述以及走街串巷的说书人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的讲述长大的。这种跨文化的口述传统深深地影响了赛珍珠接受文学的方式以及她成年后叙述故事的方式。赛珍珠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热情洋溢地强调自己对中国小说的感恩之心:“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一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1)赛珍珠.中国小说[M]//大地三部曲.王逢振,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956-976.。
赛珍珠的获奖感言揭示,她的写作更多秉承了一种口述传统。无论是她分别为父母写的传记《战斗的天使》(FightingAngel:PortraitofaSoul, 1936)与《异邦客》(TheExile, 1936),还是她的中国书写,都展示了中国小说与口述文化的鲜明印记。赛珍珠不仅通过传记讲述来华传教士父母的故事,而且为母亲凯丽代言,揭示她如何在跨文化空间中通过丰富的亲子口述抚慰思乡之情,通过与中国女性达成精神联结来缓释其遭遇的文化与性别创痛。
赛珍珠无疑继承了母亲启发的口述传统,并且在创作中将其与中国口述文化融会贯通。她的文学创作不仅继承了中国说书文化对普罗大众的关照,而且呈现了其对处于社会文化边缘的女性的历史责任感。《一个中国女人的叙述》(AChineseWomanSpeaks, 1926)、《大地》(TheGoodEarth, 1931)、《儿子们》(Sons, 1932)和《母亲》(TheMother, 1934)不仅揭示在中国男权文化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女性如何借助口述传统展示对男权文化的颠覆与指导力,而且呈现了女性对民族文化记忆的传承功能。这些女性虽然身处中国社会底层和主流文化的边缘,但这一位置却也提高了她们对伦理问题的宽容度,使她们在口述中既能表达女性的主体诉求,又能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通过激发交流与对话将传统文化记忆传承下来。梳理国内外的赛珍珠研究,可以发现很少有学者关注到赛珍珠写作中的女性口述与文化记忆。为此,本文从女性口述文化视角,阐析赛珍珠如何通过口述,为跨国跨文化的女性共同体“代言”,留下属于女性的文化记忆。
一、 口述文化的性别特征
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1883年携妻凯丽来华传教。他们通过口述讲故事的方式贴近中国大众,完成自己的传教使命。对比分析《战斗的天使》与《异邦客》,读者不难发现,两部作品揭示了赛氏父母如何在工作中努力援用口述文化与中国底层大众达成一种对话关系。赛珍珠无疑从这种跨文化的口述文化环境中汲取了充分的养分。无论是传记写作还是小说创作,都呈现了对社会底层人民视点的关注,对文学创作大众性的坚持。从某种意义上讲,传记相当于讲述他人的故事,是口述传统的一种书面留存形式。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古希腊的《荷马史诗》都是以演唱呈现的口述传记。赛珍珠为父母写的传记就是向他人口述父母的人生故事。
赛珍珠从小就看到母亲凯丽努力通过口述文化深入中国妇女生活,在救助这些妇女的同时实现自我救赎。凯丽不仅擅长通过丰富多元的口述形式传承故土文化记忆,还通过对人类基本生存体验的人文关注,激发劳苦大众对其信仰的兴趣。她的口述始终是跨文化的,推动着跨国的女性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中美两国妇女交流在男权夹缝中的生存体验和“第二性”的性别创痛。在跨文化交流中,凯丽将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故事化与生活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不仅表达了她的主体诉求、女性口述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承功能,而且展示了文化记忆的性别化特征。
在《记忆的性别》(TheGenderofMemory, 2017)中,美国学者贺萧(Gail Hershatter)通过陕西农村72位老年女性的口述记忆,重建了20世纪中期中国农村妇女生活的变迁史,并借此提出了口述记忆的社会性别特征。这些女性在兵荒马乱年代饱受战争与家庭离散的创伤,后来又被吸纳进国家建设,通过口述言说了战争灾变、劳作与生活的多重压力。贺萧发现,这些女性并没有像男性那样完全吸收国家话语,她们用贴近生活的语言描述这一时期的标志性运动(2)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M].张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5.。这些女性常年辗转于田野劳作与家务之间,同时被男权话语排斥在外,她们的口述因此难免偏离历史,缺乏时间逻辑与概念,从而呈现出口述记忆的性别化特征。
英国人类学家鲁思·芬尼根(RuthFinnegan, 1933—)认为,“口述”一词本身就有“口头的”(voiced)与“非书面的”(unwritten)的双重意蕴。因此,口述传统有时包括所有的非书面传统(所有往昔流传下来的未经成文的观念、实践活动和器物)的文化形式,有时则指通过口头表述存在的文化形式。如果说“口头的”代表了通过语言流传下来的文化形式,那么“非书面的”则是人间万象与人生百态的各种感官形式的呈现。女性的家庭组织经验更多地体现了人类基本的生存体验,因此能更好地将“口头的”与“非书面的”口述形式糅合起来。
如果说男性口述更多借助文字等抽象概念来辅助记忆,体现为一种遵循时间发展的“纵向”记忆,女性记忆则体现了对“人”的关注,呈现为一种突显人际交往的“横向”感官记忆。在男权社会,男性通常享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与社会话语权,男性文化因此更多呈现为借助文字形成的书面文化记忆。这一社会文化位置使男性更容易受到历史进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对民间文化传统的保存能力也相对不足。例如,孔子修订《诗经》时曾将大量民间口述诗歌删除。与此形成对比,女性的家庭建设经验使她们在口述中更擅长于援用外物或者是他人的辅助记忆,这使得女性口述更容易突破主流文化束缚与个体视角局限,呈现出按照具体情况裁切的灵活性,从而能够通过生活化的口述形式将民间文化传承下来。
朱骅曾经指出:“神性话语是男性执掌的教会体系的基石,对‘神性’的描述和定义从来就没考虑过女性,因此‘神性’话语的适用域从来和女性无关。”(3)朱骅.离散论视角下来华女传教士的天路历程——基于《异邦客》的文本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6(3): 92-100.这种神性话语的男权本质与《圣经》代表的书面文化,导致男传教士很难接受他者文化与视点。“他们对不相信或不能全信这些信条人的评判,简直残酷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他们不屑于结识这些人,更谈不上与他们建立友谊,对他们来说,这些人压根就不存在。”(4)赛珍珠.战斗的天使[M].陆兴华,陈永祥,丁夏林,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310.他们在工作中不关心那些中国人来教会前有什么困难,有何信仰,他们不顾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帝国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强制推行西方基督教文化与宗教伦理观念。在《中国印象》(ChinaasISeeit, 1970)中,赛珍珠提出,“只有当人们了解了这些西方人的生活与精神气质,才能理解他们试图解释的东西”(5)BUCK P S.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to the west[C]//China as I see it.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70: 10-15.。换言之,只有中西方达成一种平等对话关系,才能使传教工作顺利进行。这种双向理解的工作实际上更多的是女传教士通过和中国妇女的口头交流实现的。
西方传教界的两性社会职能空间分野,以及“妇女工作为妇女”的传教理念,使女性传教士只能贴近中国妇女,通过建立跨国的女性命运共同体传播基督教和异域文化。赛珍珠指出,教会对女性声音的压制促使与凯丽同时代的女传教士多以女性口述开展工作(6)赛珍珠.战斗的天使[M].陆兴华,陈永祥,丁夏林,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312-313.。女传教士更擅长于将女性家庭建设经验融入工作中,她们将“口头的”与“非书面的”形式融合起来。她们的口述文化展示了一种以善为基础的“圣母文化”,能够融入当地民众的集体记忆,将异域文化真正传播开来。
女传教士深受教会男权话语压制,因此更容易摆脱西方优越文化心理与视角,更容易贴近中国大众生活,达到传教的目的。这种口述传统不仅保留了女性的文化记忆,而且通过激发女性间的对话与思想碰撞展示一种跨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赛珍珠亲眼见到以母亲为代表的女传教士与中国妇女的性别宿命,以及这些女性跨越文化差异的生命交流与携手救赎的过程,坚定了为广大女性代言的决心。她不仅为被神性男权话语“噤声”的传教妇女代言,而且为被男权文化压抑而失去表达机会的中国女性代言。
二、 赛珍珠口述文化溯源
虽然赛珍珠在诺贝尔奖讲坛上深情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小说的感恩之心,她的传记写作却表明其首先深受传教士母亲的口述文化影响。凯丽性子急躁却情感热烈,擅长于使用富于感官体验的口述文化经营亲子关系。到中国后,不仅要实现宗教理想,还要开荒破土、重建家园。凯丽继承了祖辈落地生根的精神与口述能力,她借助丰富多样、触碰心灵的亲子口述传统帮助孩子触摸美国文化根脉。“她可以滔滔不绝地唱上百首小歌和讲杂七杂八的快乐的废话逗引小孩”(7)赛珍珠.异邦客[M].林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133.;当她想开玩笑并开始模仿某人的声音、步态和举止时,总能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8)同③:38.。
凯丽不仅通过一种口传心授的口述文化来展示自己的母性关怀,而且不惜一切努力重建故土的文化记忆空间,以抚慰自己对故土的绵绵思念,同时为孩子们打造跨文化家园。扬·阿斯曼指出,记忆术最早使用的媒介手段就是空间化(9)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5.。作为文化边缘人的凯丽积极“移植”故土文化元素来重建家园,从美国带来的床、桌椅、钢琴、风琴和炉子等家具随着她在山东、安徽与江苏各地辗转。凯丽利用“非书面的”口述文化因素使流动的家变成有吸引力的促进中美文化交汇的空间。她在自己精心布置的家中弹琴歌唱,熏陶自己的孩子,同时吸引当地中国妇女,“任中国妇女在家中走来走去,看看她的炉子、缝纫机、风琴和所有洋玩意儿的奥秘”(10)赛珍珠.异邦客[M].林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112.。由此分析,凯丽建构的美国文化记忆空间并非是与中国大众隔离的“文化荒岛”,而是激发中西方妇女跨文化对话的女性共同体空间。
凯丽实际上将“非书面”的女性口述文化发扬光大了。无论是居家布置,还是图画、歌曲、日用品,都能辅助口述交流,激发孩子们对母性文化的认同,同时通过激发中西方女性之间的情感互动,推进文化交流。她在居住的地方“聚集一群群的妇人和孩子,教他们识字、唱歌、编织和手工,在教这些的同时也讲授基督徒生活和行为的简单基础知识”(11)同①:159.。她将“口头的”与“非书面的”糅合起来,将传教工作、日常交际、女性文化经验紧密结合起来,使《圣经》故事通俗化与生活化,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慢慢渗透到中国大众日常生活当中。这种口述文化特别关注妇孺情感需求,能够满足女性的文化身份诉求,因此既能激发女性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又将基督文化传播开来,进而隐喻异域文化只有与中国大众,特别是女性口述相互交融,才能获得立足空间,才能成为一种可以流传下来的文化记忆。
凯丽对中国大众的关爱,特别是与妇女建立的精神联结,极大地启发了赛珍珠。妇女们在凯丽面前毫无顾忌,什么话都敢讲。凯丽听她们说李牧师向每个入会者收取三块大洋,还听说年老的李牧师偷偷纳了三个小妾,饶牧师是个鸦片鬼,等等(12)赛珍珠.战斗的天使[M].陆兴华,陈永祥,丁夏林,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305.。这种全知视角与女性家庭组织经验使凯丽更容易站在别人的视角看问题,进而展示出对伦理问题的宽容。例如,有位林先生要参加教会,但是他有两个老婆。赛兆祥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他把妾打发走。然而,凯丽坚持认为这种做法非常不人道,因为那可怜的女人没地方去(13)同①:144-145.。如果说赛兆祥是一名孤独的基督教卫道士,凯丽则是一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她关注生命,特别是女性的性别文化创痛,她的口述因此带着体温,通过与中国妇女的“横向”交际展示了可以按照生命裁切的灵活性,更加完美地呈现了口述传统以人为本的原则。
赛珍珠不仅继承了母亲的口述文化,而且将其与中国市井口述文化,以及中国小说融合起来,贯彻于她的文学创作中。家中保姆王妈为报凯丽的搭救之恩,对她的孩子视如己出。她给赛珍珠哼唱最委婉的曲调,使其脑中充满了中国韵律(14)同①:105.,她给赛珍珠讲充满伦理寓意的狐仙鬼怪故事。赛珍珠还听剃头匠、草药郎中、卖食物的小贩、木匠和各家奴仆间闲聊的八卦(15)彼德·康.赛珍珠传[M].刘海平,张玉兰,方柏林,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29.,从市井百态的“非书面的”口述文化中得到了最早的中国文化滋养,这些都成为她中国创作的不竭动力。
在诺贝尔文学获奖感言中,赛珍珠指出中国小说根植于普通民众生活,是在说书这种口述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决定了中国小说只有关注市井人生,与普罗大众对话才具有生命力。由此,赛珍珠非常形象地指出,小说家的位置在市井人群之中,“他在街上会非常快乐。街上充满了喧嚣,男人和女人表现自己的技巧也不像雕像那样完美”(16)赛珍珠.中国小说[C]//大地三部曲.王逢振,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956-976.。显然,赛珍珠从中国市井文化与中国小说中发现了文学的生命力所在,在她的描述中,小说家并非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高不可攀的艺术家,他的位置在大众之间,应该通过关注与吸引大众视点与读者达成一种基于人格平等的对话关系。换言之,小说只有与广大读者进行对话,为民生“代言”,帮助普通人“说话”(voice),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赛珍珠从母亲口述文化与中国小说中汲取的营养,使她坚定了为平民写作的方向。赛珍珠的写作实际上就是一种口述体文学,菲利斯·本特利(Phyllis Bentley)认为,赛珍珠文风“朴素平实,而不失庄重,具有《圣经》风格”(17)BENTLEY P. The art of Pearl S. Buck [J]. The English journal,1935,24(10): 791-800.。这种风格就是贴近普通人的“口述”风格——口语化,家常措辞,通过生动的故事讲道理。“像中国小说家那样,我受的教育就是要为这些人写作,如果他们有一百万人读他们的杂志,我愿意我的小说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而不想在只有少数人读的杂志上发表。他们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晰的法官,因为他们的感官未受破坏,他们的感情是自由的。”(18)同①.因此,赛珍珠坚持为广大民众创作,接受大众兴趣考验,展示大众视点。
三、 口述:为中国女性代言
在为父母所作的传记中,赛珍珠揭示了母亲如何援用饱蘸生命色彩的口述形式帮助子女触摸文化根脉,又如何与中国妇女进行思想碰撞与生命互助。凯丽的口述文化流淌着她对故土文化的生命记忆,同时突显为女性之间跨文化的生命记忆。这种女性口述帮助赛珍珠塑造了饱满自信的精神人格,激励她通过写作复活母亲的口述文化。赛珍珠的写作不仅是为母亲“代言”,而且为与母亲命运类似,被封建男权文化“噤声”的中国女性“代言”。
赛珍珠的第一篇小说《一个中国女人的叙述》,以一种带有中国本土特征的女性“口述”,呈现20 世纪初社会变革给当时中国私人生活带来的压力。彼德·康(Peter Conn)认为,题目本身就是一次绝对的女性主义断言,表达了赛珍珠要为无声的中国女性发言的先锋式愿望(19)彼德·康.赛珍珠传[M].刘海平,张玉兰,方柏林,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93.。从《一个中国女人的叙述》中的桂兰,到《大地》中的农妇阿兰,到《儿子们》中的梨花,再到《母亲》中的无名母亲,这些女性形象不再是男性视觉中被性感化、幼稚化、妖魔化的文化他者,而是具有一定独立与反抗意识,一定主体意识与精神诉求的女性形象。
赛珍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东风·西风》(EastWind:WestWind, 1930)是在《一个中国女人的叙述》基础上写成,以妇女之间讲私密话的“口述”形式,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过程,呈现了中西文化的对立与融合。女主角桂兰以书信独白的方式叙述了自己在婚姻中的蜕变过程。桂兰从小接受了母亲严格的女性规范教育,成婚之后留洋丈夫却坚持两性平等,要求桂兰放开在封建社会中象征女性完美的小脚。桂兰虽然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但还是按照母亲灌输的“男尊女卑”原则遵从了丈夫的要求。夫妻之间从此有了交际与对话,桂兰在新旧两种生活与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开始对自我有了认知。
桂兰的“讲述”揭示了女性口述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功能。在她的娓娓道来中,读者“听”到了等候升天的灶王爷、元宵节点亮的荷花灯、端午节河上的赛龙舟。在这些传统节日与文化记忆的背后,永远是紧紧牵着哥哥的手,或者跟在母亲身后的桂兰。成婚之后第一次回门,她用无限留恋的口吻描绘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娘家:“夜幕从弯弯屋顶落下,蜡烛在屋里摇曳闪烁,饭菜发出阵阵香味儿,小孩子们玩耍嬉笑,他们的布鞋踩在砖地上发出柔软的声响。啊,我是老式中国人家的女儿……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我感到安全可靠,知道该怎样行事”(20)赛珍珠.东风·西风[M].钱青,赵宇,余宁平,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419.,可以很明显看出,桂兰的“口述”重感官体验,擅长援用外物或他人辅助记忆,不仅向读者展示了五光十色的社会图景,而且揭示了长幼有序、母慈子孝的文化传统。这种女性口述更善于将官方的伦理价值观通俗化,通过生活化的描绘将民间文化记忆传承下来。
桂兰也代表了处于封建男权社会的边缘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东方女性。然而,这种边缘文化位置使她更关注他者视点,在口述中能给予处于不同阶层、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相同的关注。她的叙述中既有端庄稳重、才貌一流的母亲,又有无知无识、争风吃醋的姨太太。她既描述了固执于男权文化的母亲背后的无言创楚与忧伤,又呈现了那些任情任性的姨太太如何被父亲代表的男权文化盘剥、利用、轻蔑而枉付生命。桂兰从不同视角讲述父亲身边不同女人的境遇,不仅见证了女性口述对伦理问题的宽容度,而且为其后来在婚姻中形成跨文化视野铺平了道路。
桂兰与嫂子的跨文化“横向”互助与思想碰撞,体现了女性口述的跨主体特征。桂兰的哥哥留学美国后与白人女孩玛丽结为夫妻,回国后遭到所有人反对。然而,丈夫竭力灌输的两性平等理念,使桂兰逐渐明白婚姻的真谛在于两情相悦。姑嫂二人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努力沟通,这种跨文化的女性情感互动使桂兰能以批判的眼光反对恪守古训的母亲。由是观之,女性口述能够超越文化差异,拓展生命广度,以女性命运共同体突破男权文化的禁锢。
在代表作《大地》中,赛珍珠通过皖北农民王龙夫妇与土地的生死关系,探索了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出路问题。妻子阿兰代表饱受男权文化压抑而“失语”的女性。她命运多舛,儿时被逃荒的父母卖给大户人家做丫鬟。被王龙娶进家门后,她恪守封建伦理强加给中国女性的性别规定,在生养子女、奉养老人、料理家务之外还承担着与王龙几乎同样的田间劳动。然而,当日子稍有起色时,王龙开始厌倦相貌平庸、沉默寡言的阿兰,导致后者抑郁而终。
为了替这些无法摆脱性别宿命的中国女性他者代言,赛珍珠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这种叙事手法等于给了沉默的女性一个“文字”的声音,一种文字的“叙述”。发迹后的王龙娶荷花为妾,对阿兰“甚至还不如对一头垂下头的牛或不进食的猪那么关心”(21)赛珍珠.大地[M].王逢振,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221.。面对丈夫的情感背叛,阿兰选择了“沉默”。然而,赛珍珠的讲述给了阿兰一个“声音”,她以“画外音”的方式,解释着阿兰隐忍的默然的地母般的存在。换言之,阿兰的行动与赛珍珠的“声音”实现了跨文化、跨时空的配合,达成了一个无须挑明的命运共同体。在赛珍珠的口述中,读者意识到木讷的阿兰其实是何等聪明,能看出家中和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在逃难、买地、送长子进洋学堂等重大事项中左右着王龙的决定。虽然她没有说话,但却似乎余音袅袅。
赛珍珠也同样“代言”隐忍沉默的丫环梨花。阿兰去世之后,王龙将丫环少女梨花收为侧室。《儿子们》故事开始,王龙去世,梨花带着王龙的女儿与残疾驼背的孙子,在城外旧土坯老屋为王龙守墓,构成了被边缘化的,失去了任何表达权利的底层社会。但赛珍珠却帮助梨花在关键时刻打破被“噤”的女性声音。梨花坚守着丈夫对土地文化的信仰,当她无意中从驼背口中听说王大和王二正在偷偷卖地,就匆忙赶到城里王大家,在关键时刻勇敢地替墓中的王龙发声:“我真没想到老爷的儿子会这么不听他的话,我是个软弱的女人,你们谁也不把我当回事……老爷会替自己报仇的”(22)赛珍珠.儿子们[M].韩邦凯,姚中,顾丽萍,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101.!梨花在关键时刻不仅替王龙“发声”,而且让阿兰“复活”,因为她和阿兰一样都能在关键时刻发声,唤起人们对土地代表的中国伦理传统的记忆,通过激发对话将传统文化传承下来。
《母亲》是赛珍珠向美国读者讲述她所熟悉的皖北一带的农村妇女的故事,整个叙事手法就是一种简明易懂的“八卦”和唠嗑口述形式,具有典型的女性口述特点。“母亲”是一位备受生活碾压,却具有一定女性意识与精神诉求的农村女性。她先后经历丈夫失踪、村人歧视、女儿失明,以及女儿和小儿子的先后离世,然而她援用一种随机应变的女性口述积极应对世事无常与生活变故。丈夫失踪之后,“母亲”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家务,还要应对那些成群结队来打探她男人消息的村妇。面对这些农妇,母亲灵机一动,骄傲地说:“他有一个朋友,住在很远的一个大城镇里,那朋友告诉孩子他爹,那边有个很好的差事,工钱又多,所以他可不必再种田来养活我们了”(23)赛珍珠.母亲[M]. 万绮年,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50.。为堵住村人闲言碎语,维护自尊与家庭稳定,母亲一次次编造谎言,还不惜花钱请写信先生以丈夫的口吻给自己写信。由此分析,母亲的口述围绕家庭建设,呈现了能够按照具体情况裁切的灵活性。这种口述能突破性别与家庭带给她的双重压力,因此表现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活的口述文化。
母亲的口述通过对土地,及其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信仰呈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母亲勤劳恋土,丈夫失踪之后,她不仅在土地中寻求突破家庭困境的有效路径,而且通过在田中辛勤劳作来麻痹自己,释放肉体上的压抑与痛苦。当大儿子阻止上了年纪的母亲去田里做工时,母亲恼怒地说:“我又不怎样老!让我做做事,好安慰安慰我自己吧,你不觉得我需要这样才能让我自己好过些吗”(24)赛珍珠.母亲[M]. 万绮年,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164.?母亲虽然目不识丁,却将土地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念生活化与通俗化,暗示只有土地才能承载中国农民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只有接近土地才能获得修复创伤的有效路径,进而将土地代表的传统文化记忆传承下来。
赛珍珠通过阿兰、梨花、母亲等传统女性的接力“发声”揭示了女性口述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保存与传承。这些女性都代表了没有介质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展示了性别化的土地文化记忆。虽然她们的口述揭示了女性对于土地代表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坚守,对于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功能,然而她们却没有摆脱被男权噤声的命运。因此,赛珍珠力图通过写作替这些无法摆脱性别宿命的女性“发声”。这种女性声音以女性跨文化命运共同体的形式不断冲击男权文化的壁垒。
四、 结论
赛珍珠在中美两种文化的滋养下长大,母亲凯丽与保姆王妈的口述不仅给她提供了最长久的文学滋养,而且帮助她体味女性口述独特的包容性与开放精神。凯丽与身边女性通过交际互助达成了“横向”精神联结,她们的口述不仅呈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对世间万物的人文关注,而且表现出能够按照生命裁切的灵活性。这种口述不仅能够表达被男权文化压抑的女性主体诉求,而且通过其中蕴含的伦理价值呈现出对于家庭与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作用,进而展示出女性口述对于文化记忆的保存功能。
赛珍珠的写作秉承了这种女性口述传统,她的写作不仅表现为对母性口述文化的生命记忆,而且突出呈现了中西文化焦灼对话带来的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特别是对辗转挣扎的女性群体命运的思考。她通过写作代替美国妇女(凯丽及其同辈女传教士)和中国不同阶层的妇女(桂兰、阿兰、梨花、母亲)言说女性自己的故事。她以怜惜的女性视角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男权文化压抑下的女性群体,她的跨国写作因此成为中美两国性别记忆的留存档案,她的这些文字由此也成为跨文化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