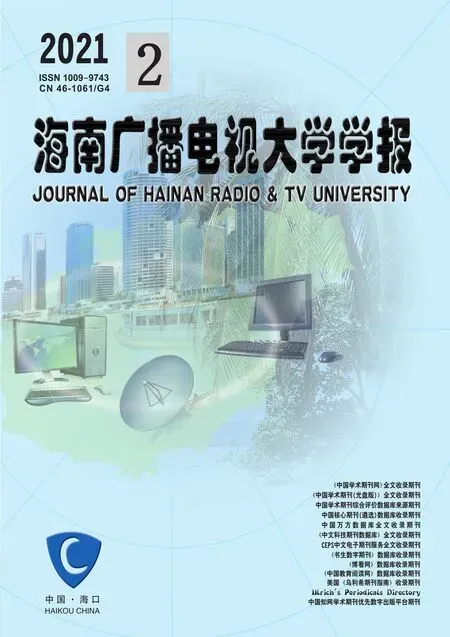论现代家庭伦理剧成功之道
——以电视剧《都挺好》为例
2021-12-07万咪咪
万咪咪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前 言
电视剧《都挺好》作为新时代家庭伦理剧典型代表至今热度未褪,该剧彰显着对传统家庭伦理剧老旧模式的自觉超越和对当代伦理新秩序的审美体现。它跳脱毫无技巧、稀疏平常的生活流叙述模式,将其匠心独运的艺术眼光聚焦于时代典型环境之下有关家庭文化变迁、性别意识较量等社会热点问题,并透过对苏姓人家家庭冲突的描绘来塑造艺术典型。二者相互融合,形成一个巨大的召唤结构,从而引发大众热议与其自觉填空行为。笔者试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其成功之道进行分析,为当代家庭伦理剧转型提供一定艺术启示和经验思考。
一、典型环境:时代的缩影与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型观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深刻揭示了有关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艺术问题。恩格斯在1888年《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就哈克奈斯的中篇小说《城市姑娘》和对巴尔扎克创作的相关评论,集中阐述了他对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的见解,他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思考创造性地提出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这一重要见解。在信中,恩格斯表示“所谓现实主义的内涵不仅是要表现细节的真实,更要注重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这里的人物就其本身而言已足够典型,但是环绕并促成这些人物行动的环境就不那么典型了(2)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页。”。人物与环境相互依存,典型环境是人物生存其中并能深刻体现时代生活本质方面的环境。
(一)典型环境的呈现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有机统一
就自然环境而言,多指促成人物行动的景物气候、空间地域等实际环境;社会环境则指人物生存其中并得以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总体形态的环境。二者相互协调,构成接受者对作品空间环境的主观性感知与诗艺性创造。在电视剧《都挺好》中,故事是以苏家老宅为自然环境铺叙开来的,位于苏州同德里的老宅承载着苏家全体成员的集体记忆,那灰褐色的瓦砾,斑驳的墙体,狭长的胡同和幽深的天井无不见证着苏家过往的历史,他作为记忆空间的存在揭示了苏家内在矛盾的根源所在。正是通过这个家庭场域的具象呈现,我们认识到苏母赵美兰重男轻女、偏心强势的典型性格,为了给苏家兄弟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她肆意剥夺苏家小妹明玉的生存资源,间接成为导致苏家兄妹反目成仇、矛盾深厚的始作俑者,于此,表面风光、令人艳羡的家庭背后涌动的滚滚暗潮跃然荧幕之上。其次,剧中不仅利用自然环境映射矛盾根源,还使得都市职场成为社会环境的镜像呈现。苏明玉作为老蒙的得力干将在众诚集团身居高位,其果敢刚毅的精英白领形象深入人心,但其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纠纷同职场应接不暇的工作任务相遇时,也时常令她焦头烂额。公司内部明争暗斗,家庭内部分崩支离,两个场域相互交错,共同勾勒出现代职场人在面对家庭纠纷与工作问题时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境。
(二)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典型统一是时代历史的缩影与具体化
环境的典型性呈现并非一系列生搬硬造的情节构造,也不是毫无生气的描摹客观现实的本来面貌,典型环境作为特定场域的存在不仅是促成人物行动、营造文本内部环境的客观条件,还蕴含着对文本外部世界的现实映射。恩格斯在揭示“典型”的内在本质时,尤其注重对文本的现实品格与历史品格的塑造,要求以独特、鲜明的具体环境去反映现实社会大环境中的必然规律,表现出一定阶级、历史时期的社会内蕴,从而达到以局部反映整体,以个性彰显共性、以现象凸显本质、以微知著的艺术效果。正所谓,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作为社会组织的最小构成单位,其成员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都挺好》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扼住了时代脉搏,它并未停留在对家长里短的表面叙述,而是引发了大众关于“家庭”内涵的深度思考,电视剧透过对苏姓小家内部矛盾的大胆陈述直面社会痛点,其议题涵盖了教育、经济、住房、养老责任等方方面面。首先,就养老问题看来,传统养老观念与现代价值产生了强烈冲突。长久以来,中国传统的养老理念便是通过“互养”途径形成的反馈模式,父辈作为资源优势方承担着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责任,子女成人后便接续这种模式,肩负着赡养父母的重任。然而,在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后,父辈随家庭经济主导地位的转移,逐渐丧失了家庭核心主导权,开始出现养老焦虑。他们将同子女的沟通策略转换为“以情感为主的沟通(3)袁一民:《养老焦虑与城市再融入——电视剧《都挺好》中的老年人口社会问题》,《中国电视》2020年第1期。”,以一种异化形式挥霍着子女的耐心来表现自我需求,证明自我的家庭地位,基于此,生活中便开始出现了一个个“苏大强式的作精父亲”。同时,由于老年人情绪的过度释放也使得子女面临忠孝两难困境。剧中苏明哲虚荣自大,为了对苏父尽孝,满足苏父买大房子的心愿而多次舍小家为苏姓大家,后经济实力不允,苏父便开始责备明哲不守信用。另一边,为了尽量守诺,明哲无度降低其妻子吴非与其女儿小咪的生活质量,导致吴非陷入一种丧偶式婚姻境地,万般无奈下吴非便提出离婚。一边是生养自己的父亲,一边是相濡以沫的妻子,明哲所纠结的、渴望协调却又无能为力的问题也正是时下年轻一代在赡养父母的过程中所两难的。
(三)就教育问题而言,《都挺好》直面现代社会由于原生家庭之殇给子女带来的心灵创伤而引发的家庭冲突
苏家兄妹之间苦大仇深、无可消解的恩怨矛盾、他们各自的性格弊病都来源于其父母的区别对待和教育差错。苏母作为饱受原生家庭无度控制和索取的牺牲品,在其成为父母后又变成了维护这种“重男轻女”畸形逻辑的卫道士。她强势霸道,极力压榨明玉的生存资源,为了满足儿子外出旅游的虚荣心,可以狠心拒绝女儿想买一本练习题的卑微请求;为了老大苏明哲出国留学她卖了一间房,为了老二苏明成结婚又卖了一间房,然而对于明玉,苏母从来都是冷眼以对,全然不顾明玉渴望守护自己独立空间的希冀,亦能罔顾明玉费尽辛苦渴望考上名校的梦想,且自作主张、肆意安排她的志愿,美其名曰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桩桩件件并非随意捏造的戏剧虚构,这种“重男轻女”“一切都是为了你好”的教育理念早早便在许多家庭生根发芽。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崇尚独立平等和强调精神关注变成年轻一代的迫切需要。子女们妄图挣脱这种“一切为你好”的老旧思想,跳出“重男轻女”窠臼。为了捍卫自我意识,他们开始思考父母作为家庭绝对权威的可靠性,向父母提出精神关注的强烈愿望,对家庭文化表达新的诉求。在他们看来,尽管亲情血浓于水,也不容许无节制的操纵和利用;家不仅是温饱线上的港湾,更应是心灵真正得以栖息的一方天地。
二、典型人物:符号人物的权力突围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235页。”。典型性格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离开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便失去意义;离开典型人物,便无所谓典型环境。同时,恩格斯在充分肯定典型环境塑造人物性格、揭示生活本质方面的优势之外,亦强调“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真实”,在对性格的要求中,恩格斯指出“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即典型性格既要具有鲜明的个性,又要反映所隶属阶级、阶层的某些本质方面(5)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236页。” “就人的现实本质而言,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物形成性格、采取行动的动机不只是个人欲望的作祟,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其行动的促成是从其所处的历史潮流中而来的(6)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236页。”。母系社会分崩瓦解后,男性凭借其先天生理优势,逐渐成为家庭生产资料的主要创造者,并通过对教育权力的性别垄断、经济基础的绝对掌控迅速占据了家庭话语权力的主体地位。就此而言,绝对威严、不容挑战的父权制度在传统文化中便根深蒂固。“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父,守三纲,遵五常”等“尊父权,抑女性”的陈规旧约致使女性被先天赋予了悲剧性附属客体的色彩,长此以往,女性被异化至边缘的绝对第二性的境地而解放无门。然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机器对人力的解放逐渐缩小了性别鸿沟,使平等独立的民主新风宣扬开来,为现代化男女平权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在这期间,女性透过对教育平等权、工作平等权的争取与社会价值的自我确立逐渐完成了自觉或半自觉的性别觉醒,他们对以男权为中心的话语体制发起挑战,变被动为主动,变客体为主体,着力尝试对传统父权的突围与逆反。
在《都挺好》的创作构思中,剧作者着力打破传统家庭伦理题材男强女弱常规,对男性作为家庭支柱、话语中心的伟岸形象进行解构,将固有性别认知抽离出去,构筑起以女性为权力主体的叙事语境,且对女性家长里短、柔弱而不堪一击的婆妈标签、歇斯底里的妖魔化符号进行颠覆和祛除,他们发现了女性形象,并创造了具有时代意味的女性形象。剧中,以苏家为核心建构起的叙事场域,相较于传统剧情女性以柔克刚、同强势男权进行对峙以实现权力转移、取得自我确证和主导地位模式不同,《都挺好》中权力移置是通过男性失语与女性强权的强烈对比来实现的,它所营造的是一个阴盛阳衰、父权式微的世界,强权女性作为突出符号成为剧情发展重要线索,承担着打破传统家庭文化秩序,引发大众思考的重任。就苏家的权力中心苏母而言,她一出场即存在于有别于现实世界的回忆空间,但是她在苏父和苏家兄妹心中一直实现着缺席的在场。她的凌厉与强势迫使苏家的男人们都对他言听计从:苏父在她压制下一生唯唯诺诺,小心翼翼,每当家庭发生冲突,儿女向他求助,要么面对墙壁一言不发,要么逃去厕所躲开纷争,全然被剥离到话语中心的边缘地带,他甘愿屈居苏母之下,成为苏母的附庸客体,以至于苏母离世之后,她的霸道和积年压迫仍令苏父颤栗不已。但是苏母对于父权制度的突围仍然是不够彻底的,或者说她在尝试突围的同时还在持续接受父权制的压迫。作为女性,苏母饱受原生家庭歧视,从小被父权制家庭男尊女卑思想荼毒,成年后,她作为维系父权制度的同谋者不但成为一个令人厌弃的“扶弟魔”,无节制地对其蛀虫般的无赖弟弟进行经济援助,而且还用这种落后思想继续麻痹、迫害自己的女儿。苏明玉在看清楚这强权表面之下隐匿的真相后毅然放弃了对苏家的期望,成为现代版出走的娜拉。她是一个民主意识、自我精神极强的现代女性,正统的教育理念、价值观念使其无形中被注入独立自强的主体意识。在认识到家庭无法拯救她的人生之后,便转向了自我解救的道路。她努力拼搏,在尔虞我诈的职场上叱咤风云、游刃有余,有一股男子气概,行事果敢凌厉,并仰仗其杰出的销售才能实现了对大部分男性话语权力的绝对碾压,并通过这种社会认定的有效途径,实现了对自我命运的完全掌控。与此同时,也恰是这个最不被家庭看好,家庭不舍投资的女儿最终却对苏家投入最多。苏母的丧事是明玉一手操办的;苏家兄弟的工作是明玉疏通的;苏父晚年患病最终也是明玉与之相伴。都说养儿防老,最不受待见的女儿最终却是最有孝心、付出最多的那一个,桩桩件件无疑都是对传统父权文化中心的绝地反击。她的存在直击“男主内,女主外”的老旧模式,将传统女性应当灶前台后,恪守本分的陈规印象进行颠覆,并凭借独立、理性意识的觉醒与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最终摆脱了作为男性权利附属品的存在,她不但自我弥补了童年时期家庭话语权力缺失的遗憾,而且成功实现了话语权力变被动为主动的突围。某种意义上说,她不仅是苏明玉本身,更是现实社会里千万独立女性形象的投影和典型聚焦,是时代观众最熟悉的陌生人。
三、历史趋势:“家”题材创作思维的构筑
《都挺好》在叙事内容上的精心编排与叙事技巧中的大胆创新使各个年龄层观众无不拍手叫绝。它一边行云流水,淡叙百姓日常生活点滴;一边或隐或显揭示社会重大议题。它的成功是建立在对真实家庭生活探索之上的艺术巧思,是符合真实生活逻辑的艺术真实。同时,它弥合了时代典型环境之下大众对假丑恶的厌弃,对真善美的向往审美趋势,其中的现实主义品格、人文关怀气质以及形式美的呈现都对我们探索“家”题材剧作的未来出路大有裨益。
(一)文艺创作一定要以历史理性求真
要能动地反映、理解与阐释社会真实,呈现出现实主义的美学品格。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是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其艺术表现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艺术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在对生活进行艺术变形、艺术加工的同时,创作者既要明确社会生活作为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理清楚生活与文艺的源流关系;又要兼顾细节、环境与人物的典型性,揭示出时代生活的历史真理与规律。作为2019年大获全胜的良心剧作,《都挺好》所呈现的生活真实不胜枚举,尽管剧作内容纯属虚构,但是创作者放弃了传统叙事文本对时空环境架空化处理方式,选取了苏州同德里这个现实场域进行文本叙述,虚构文本的拟真化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与情境带入感,使观众生发强烈共鸣。于此,时空环境不再是一种无关紧要的间性符号,同时也是引发受众真情实感的重要中介。此外,该剧在细节写实方面也达到了观众显微镜式欣赏的高标准、严要求。剧中的道具安排贴合人物真实,明玉作为苏家最不受待见的孩子,其家庭地位远在两位哥哥之下,明成和明哲的房间都有电脑,而明玉的卧室只有日常设施,宁静朴素;苏母去世后,明玉在车内独自回忆往事,她拼命扯去孝布,然而几番来回也没能拽下,她又急又气,无奈至极,取下之后却又理清皱褶、叠放整齐。这一系列的精细安排在逻辑合理之外又使得人物立体起来,暗含了明玉想要远离家庭,无奈血浓于水终不忍决绝的复杂情绪。
(二)创作者要具备尚善特征的人格力量
创作者要以高尚的品格和诚挚的情感对社会生活进行诗意的裁判。它要求作家运用内在尺度把伦理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和评价融入其中,并凭借“境(典型、意境、意象)”的审美形式与“理”的艺术诠释相交融,表现对美好事物、美好情操、美好理想的守望与追求,对丑恶、阴暗、腐朽事物的拒斥,呈现人文关怀的终极价值追求,从而激发受众的情感经验与审美思考,使之得到心灵的净化、情操的陶冶与境界的提升。诚然,《都挺好》所触碰的主要议题稍显沉重,其审美效果大多是通过“揭伤疤”形式达到的,创作者毫不留情地将部分观众潜藏在内心隐秘角落里的伤口一道道扒开,苏明玉所承受的不公和歧视观众与之同觞;苏明玉妄图逃离家的牢笼却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绪观众感同身受。反观自我,苏明玉即是观众最熟悉的陌生人。同剧中人物一样矛盾,他们一边心有不甘,企图冷漠到底,一边又渴望温情,想与家人和解,对过去释怀。剧作者敏锐地领悟了这些生活真实,并以艺术眼光对其投去深沉的人文关怀,他在伤痛与圆满中找寻一种微妙的平衡,最终通过幼有所爱、老有所养的温情呈现对创伤心灵进行修补,引发了大众对“家”更为理性、冷静的思考,使之在作品的余味中得到慰藉。这种循序渐进的情感治疗无疑彰显了创作者的巨大社会责任感,显示出为艺术为人的最高境界。
(三)文艺创作还要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形式创造
艺术创造之美植根于“真”,附丽于“善”,二者的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审美的深刻价值追求。然而,这种美尚处于内容状态,艺术家仍需对艺术内容的内在结构加以组织,即运用一定语言材料或艺术手段呈现为审美的艺术形式,它作为审美价值的最后追求,是艺术内容得以外化和体现,得以深化或升华的有效手段。近年来,规行矩步的影视桥段与因循守旧的情感对白已然成为时代的窠臼,大众对其嗤之以鼻,并呈现出对剧作配乐、台词等多元素材的独创性追求。《都挺好》并未抱令守律,采用了苏州评弹替代流行曲目作为背景音乐,评弹一现,苏州风情、婉约江南境界全出。其词调不仅贴近社会真实,符合剧作的情感走向,还生发出审美新质,引发大众对评弹这一传统曲艺挖掘、品鉴的兴趣。剧中,评弹多用语调,其词句与剧中场景一一对应,吴侬软语既不显得突兀,又使得故事氛围瞬间构筑起来。《白蛇传——赏中秋》原曲描绘的是许仙与白娘子的美好感情,因而总是为剧中的温馨场面做伴,当明玉与石天冬确定恋爱关系,明成一家主动承担赡养苏父的义务时都有出现;《长生殿——宫怨》情感悲恸,便伴以苏父与保姆分手情节;《玉蜻蜓——庵堂认母》巧妙地设计在苏父患病后,明玉同苏父共听评弹的场面,此曲伴此情,暗指明玉决心放弃过往恩怨,苏家终重修旧好的大团圆结局,此类巧用,数不胜数。
结 语
偶然之中隐含着绝对必然,试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都挺好》的成功原因理性剖析,为家庭伦理题材作品的成功转型提供可供参考的审美经验。《都挺好》以家庭为叙事核心,凭借社会真实直击转型时期大众对“家”的多元诉求和秩序表达,呈现出典型环境与符号人物的现实主义品格,表现为文艺创作向真、向善、向美的价值追求,形成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完美统一的召唤结构,引人深思,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