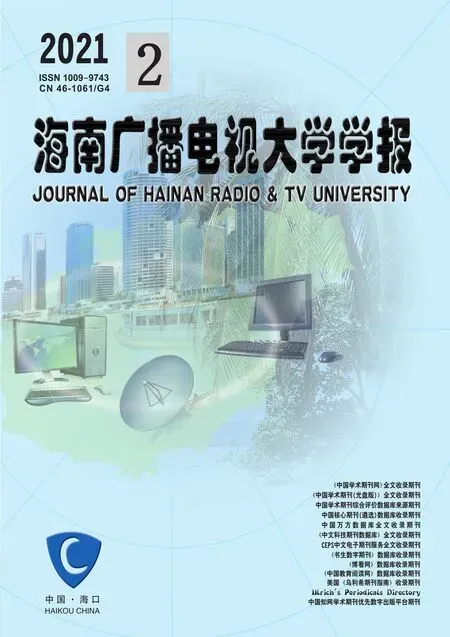游走在战争中的边缘童年
——《伊万的童年》与《通向蜘蛛巢的小径》的互文
2021-12-07周琳玥
周琳玥
(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部,北京 100083)
前 言
塔可夫斯基1962年的电影处女作《伊万的童年》(Ivan's Childhood)讲述了12岁的男孩伊万过早介入战争,当红军侦察员的一系列经历。影片为苏联夺得了第2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圣马可金狮奖,把这位日后将蜚声国际的年轻导演一举送入了电影艺术殿堂。
影片剧本改编自博戈莫洛夫(Vladimir Bogomolov)1958年的短篇小说《伊万》(Ivan)。塔可夫斯基对原著评价其实并不高,他曾表示:“纯就文艺学层面而言,这篇小说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内心冲击,它的创作手法枯燥,叙事散漫,就像小说主人公加尔采夫上尉的性格[1]11。” 博戈莫洛夫的小说有着很强的纪实感,如若遵循原著,很可能拍出一部出色的战争“叙事型”影片,但塔可夫斯基声明“我无法将这种风格搬到银幕上——这有悖我的信念[1]14”。塔可夫斯基坦言自己看重的只是小说中的三个特质——主人公的命运、叙述战争的节奏、小男孩的性格——正是这三点锁定了他的想象力。在电影改编中,他采用了与小说截然不同的视角,并且为这个故事创造了新的语言,一番脱胎换骨后俨然造就了另一种结果,使《伊万的童年》完全成为了“塔可夫斯基式”的作者电影。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Chingiz Aitmatov)曾评论道:“塔可夫斯基这个风格始终如一的艺术家,同现代文学有着极深刻的有机联系。尤其体现于《伊万的童年》的创作[2]2。”现代文学常见的创作倾向即是把人放在过去与现在的融合中来描述,力求以可见方式反映人的情绪记忆,在此过程中往往牺牲事件、现象和人物行为的外部逻辑,而深入地开掘它们的本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无意做影片《伊万的童年》与原著的比较;就创作题旨和现代手法而言,另一部小说与之有着更近似的联系,值得做一番探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1946年发表的处女作《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二者都是以20世纪40年代的二战为背景,以孩童视角讲述了一个有些另类的游击队的故事:从创作手法上看,与同时期的战争题材创作拉开了距离,在诗意与现实间开拓了战争叙事的新境界;从思想内核上看,探讨了儿童被“非儿童化”(异化)的题旨,以现代哲思方式表现了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一、空间建构与战争想象
空间是创作者以叙述形式在作品里建构起来的场所、建筑和景观等的总称,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伊万的童年》与《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均以战争为背景,但并未着意描绘前线上战事的激烈和残酷。传统战争题材中的厮杀、轰炸乃至作战过程均被一带而过,转而建构的是战争之间的空档。在这“空档”的建构中,聚焦于主人公的情绪与自我认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战争想象。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讲述的是一个在贫民窟长大,后来参加了游击队的男孩皮恩的故事。皮恩生活的地区是一条叫做“长街”的小巷,目之所及的景致是冰冷的墙壁、杂乱的窗户和路中间的一道骡子尿排泄沟;在他打工的彼埃特罗马格罗的修鞋店里,磨破底的鞋子堆成山,甚至会滚到街上来;而在家里,皮恩生活的空间仅为姐姐狭小房间旁边的储藏室。皮恩通过隔板缝隙斜眼向外看,最常看见的便是“两个全裸的身体互相追逐,互相厮打,互相拥抱[3]14”——他从此对世上所有事情的解释都来自于那块隔板后面。
母亲去世、父亲出走、姐姐做了妓女,内在家庭空间的崩塌将皮恩推向另一个空间——外向的社会空间。于是皮恩喜欢和混迹在酒馆里的男人们打交道:他唱男人们教他的淫秽歌曲,声音沙哑,像一个老小孩似的;他像男人一样吞吐烟雾,即使香烟对他这个小孩子的喉咙来讲还太厉害,让他拼命地流泪咳嗽;他与男人们谈论流血事件和杀人故事,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偷了德国水兵的手枪。偷枪这个非凡举动把皮恩送进了监狱,让他结识了“政治犯”红狼,两人成功越狱。之后,皮恩偶然被一个叫“表兄”的抵抗军收留,加入了树林中的德克托游击队。从长街、储藏室、酒馆到监狱、树林,在这一系列空间转换中,皮恩看似实现了一次从幼稚顽童到“英雄史诗”式的主人公的跨越,但其中却充满反讽:实际上,皮恩不是一个值得歌颂的小英雄,只是一个被战争裹挟、扭曲了心灵的儿童。长期浸润在暴力、性与政治的成人世界中,他变得粗野鲁莽,没有同情心,却有杀人的欲望。
《伊万的童年》中,主人公同样经历了一番从家庭空间到社会空间的转换。不同在于,皮恩是从逼仄、穷困的家庭空间被推向广阔而混乱的社会空间的,其间没有多少波澜,他加入游击队时对战争甚至怀着懵懂的憧憬;伊万则是从温暖的家庭空间被突然“抛入”到残酷的战争空间,这是一种对比强烈的逆转。自母亲和妹妹被战争夺去生命后,伊万在那个年纪应有的一切都无可挽回地从他生命中消失了,他活着只是为了复仇,一种拜战争所赐的邪恶在他身上聚集、膨胀——他变成了一个性情乖戾的“小怪物”,令大人们难以接近。
塔可夫斯基并未直接表现伊万的家庭空间,伊万对母亲和妹妹的记忆多是建立在井边、沙地这样的外部场景之上——原因在于他认为“记忆中那个我们成长于其间然而已多年不见的家,和现实中历经岁月沧桑的房舍,早已大相径庭。充满各种细节的回忆重现只会让我们失望而已[1]26。”但影片又巧妙地插入了一个他者的家庭空间,从侧面映衬了伊万的遭遇:伊万逃跑时遇到一位与公鸡为伴的疯老人,他徘徊于其住所的废墟间,喃喃地问伊万:“你妈妈在哪儿,她还活着吗?我那老太婆也是死在德国兵枪下”。伊万离开时,钻出车窗在井边留下了面包和罐头。井边,也是伊万母亲当初倒下的地方,这个极具意味的换喻完成了对伊万家庭经验空间的建构。
接下来,家庭空间的突然丧失将伊万不置可否地推向战争空间。在塔可夫斯基的影像中,为伊万建构的战争空间分为两个:一是淹水的白桦林,空中照明弹不时闪过,伊万小心翼翼越过铁丝网执行侦察任务,大远景画面极具压迫感;二是地下作战室,伊万与霍林大尉、加尔采夫上尉共处的室内空间,“L”形三人镜头传递了人物间的温情,缓和了战争的紧张氛围。在两个空间对照下,“世界被割裂成互不相容的两半——在其中的一半里,人是自由的、完整的人,具有美好的人类情感,是美好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在另一半里,人只是复仇者,是复仇的机器,为了复仇使命而放弃自我——这不仅是伊万身上存在的现实,这也是作者的主导思想和所有其他角色的共同感受[2]55。”
在皮恩和伊万的故事中,空间建构是其介入战争的外在导向,重心仍是以小主人公的内在思想为构思准则。其中,对战争的想象在他们的思想活动中占据关键一环;既然是儿童视角,那游戏便是最佳表现手法。《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皮恩视战争为游戏,这游戏很复杂,使人着迷,只不过是以生命为赌注。当他从德国水兵那里偷到一支老式P38型手枪时,他对战争的狂热想象便被彻底激发了——“一个人有了真枪就什么都能干,像大人一样。就能以杀人来威胁,让男人和女人为他服务[3]17”。接着他便开始以游戏来品舐战争之味:他紧紧地握着枪把,小心地不让手指动到扳机,首先瞄准屋檐靠近金属板的管子,而后瞄准自己的一个手指;找到一只旧鞋,便又瞄准旧鞋;后来他再也顶不住引诱,将枪瞄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感受眩晕;把枪管放到口中,感受在舌下的味道;将枪对着眼睛看里面,黑洞洞的枪管像一口井……卡尔维诺用极具视像性的描写再现了这一系列悚然的举动。从玩具到手枪,皮恩完成了从孩子的游戏世界到大人的战争世界的过渡。于是当同志们问若让他参加战斗他要干什么时,皮恩本能的反应便是把双拳靠近眼下,做拿机枪射击的姿势——“他激动了:想到法西斯分子,想到德国兵抽打他的时候,想到审讯室中那些没胡子的浅蓝色脸。哒,哒哒哒,都把他们打倒了,他们在德国军官的办公桌底下咬地毯,满嘴流血[3]79。”这其中包含的暴力快感使皮恩感到满足。《伊万的童年》中,伊万的游戏则是在地下的作战室里展开的:当霍林和加尔采夫离开后,伊万拿着刚借来的短刀和手电玩起了侦察游戏。塔可夫斯基用蒙太奇手法构设了长达三分钟的游戏情节:镜头晃动,忽明忽暗的画面造成眩晕,墙上刻满“为我们报仇”的字迹,配合着呼叫、哭喊的尖锐画外音,伊万的面孔逐渐扭曲,他推倒桌子,拉响钟绳警报,最终把墙上挂着的旧军装当作敌人,怒目控诉,进而哽咽、蹲下痛哭。
两部作品同是以游戏来表现战争想象,不同之处在于:皮恩不清楚有战争和无战争的区别(“自他生下来,好像就听人没完没了地谈论战争[3]102”),他自然地把战争视为一场掺杂着快感的成人世界的游戏;而伊万却清楚地知道战争与生活的界限,他的战争想象糅合了自己的切身经历,以至于游戏间轻易而不自觉地代入的,恰是最真实的恐惧与愤怒。
二、梦境探索与诗性隐喻
处于战争中的人内心往往保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支点,正是这支点使之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相较公共性的战争,这乃是绝对私人性的领域。可以说,找到这个支点便找到了人物内核的编码。在《伊万的童年》与《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梦境与回忆起到的就是这样的支点作用,它既指向战争之前的美好过去,又指向战争之后所憧憬的未来,现实中的战争反而成了一个空档,是与之相抗衡的存在。
在《伊万的童年》中,塔可夫斯基所作的大胆创新是在影片的现实时空之外引入了梦境时空。伊万的4个梦穿插在现实叙事中,成为艺术性的高光时刻:
(一)影片开头,蜘蛛网后出现伊万稚气的脸庞,林中传来布谷鸟的叫声。伊万赤裸着上身在林中奔跑,越过树冠,上升。画面中出现提水桶的母亲,伊万把头埋进桶里喝水,激动地叫道“妈妈,有只布谷鸟!”母亲微笑地看着他,但随之灾难发生,画面倒转,伊万从梦中惊醒。
(二)观众首先听到滴水声,水珠顺着伊万的手滴到盆里。镜头上摇,一口菱形的井,仰拍伊万和母亲。伊万把一根羽毛抛入井中,镜头叠化,出现近景双人特写和对话:“在一口深井里,即使在最耀眼的白昼也能看到星星”“什么星星”“任何星星”。接着俯拍二人井中倒影,再转回双人特写镜头,切到伊万单人,他伸手触摸水中的光亮,接着伊万视角回到井底,井口只留母亲一人。再转为仰拍,铰链拉动一只桶上升,枪声响起,母亲的披肩和桶同时落入井中,对井底的伊万形成强烈冲击和压迫感。岸上母亲倒下的尸体被井中溅出的水淋湿,伊万惊醒。
(三)运用负片展示和平时代的记忆。载满苹果的卡车从雨中驶过,伊万和妹妹坐在果堆上。电闪雷鸣间,饱蘸雨水的苹果映衬着两张湿漉漉的、童真的脸。女孩的特写镜头闪过三次,神情由明媚的笑靥逐渐转为阴郁,暗示着即将来临的悲剧。远景,卡车驶过沙地,满地的苹果浴着雨珠闪耀在阳光中。即将出任务的伊万被上尉叫醒。
(四)伊万受绞刑后的最后一刹那,通过其倒置的目光闪回到第一个梦境——他在母亲慈爱的注视下从水桶里喝水的镜头。之后场景衔接到海岸边,伊万与小女孩追逐嬉戏,两人脸部特写快速切换。他们在镜头中越跑越远,最终镜头只剩下伊万一人,他朝前伸出手臂,迎面而来的是枯树的黑色枝干——象征最后的死亡。伊万再也没有醒来。
全片在梦境中开始,也在梦境的隐喻中结束。在塔可夫斯基那里,梦境是一种诗的逻辑,是一种对世界的感受,一种看待现实的特殊方式。成为侦察兵之后,战争与暴力是伊万心目中唯一绝对的现实,而童年仅是梦境中回溯的短暂记忆。在两个时空对照中,伊万梦中被压抑的渴望恰恰反衬出他现实的生活被战争扭曲到了何种地步。
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为与现实的残酷相区隔,卡尔维诺用童话叙事笔法为皮恩构设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神圣之地——蜘蛛巢。一如梦境在伊万身上反复出现,蜘蛛巢也在皮恩心中反复出现:“有一个地方,蜘蛛在那里筑巢。这地方只有皮恩知道,整个山谷,也可能是整个地区就这么一个地方。除了皮恩以外,别的孩子都不知道蜘蛛筑巢这件事[3]22。”每当皮恩惹了大祸和笑过之后,心里总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便一个人顺着小路寻找蜘蛛筑巢的地方。在显性的一面上,蜘蛛巢是皮恩身上唯一仅存的童真:隐藏的蜘蛛巢,需要弯下身来悉心观察的蜘蛛巢,与政治的突进相对抗,呈现出一种超然的轻逸,挥之不去的感伤诗意氛围。但在隐性的一面上,这童真却又不那么纯粹,甚至遭到玷污:皮恩对动物很坏,认为它们是不祥之物——“用细长木棍可以捅到巢的尽头,刺穿一个蜘蛛,一个黑色的小蜘蛛,身上带有灰色的斑点,像老太太夏装上的一样。皮恩很高兴能拆下巢上的小门,将蜘蛛串在木棍上,觉得很好玩,他还喜欢逮蟋蟀,细细观看它们愚蠢的绿脸,然后把它们切成小块,在一块石头上拼成带爪子的奇怪图案[3]23。”蜘蛛巢无疑是孩童的场域,纯真透明,而在皮恩这里,却又包含着一些与童稚不相称的残忍举动——肆意杀戮。这种悖谬性附于蜘蛛巢上,一如皮恩早熟外壳与童稚内心的两面,二者形成一种呼应,使战争对儿童心性的摧残异化显得更加鲜明可触。
三、边缘身份与错位结局
塔可夫斯基镜头中的伊万与卡尔维诺笔下的皮恩都在游击战争中度过他们的童年,同属本不该介入,却被迫介入战争,一定程度上性格被异化了的“边缘人”。边缘人即对各社会群体都不完全参与,游离于各群体之外的人。对儿童群体而言,他们因过早介入成人世界的战争而异化,丧失了儿童的特质;对成人世界而言,他们心智尚未健全,无法真正参与。于是他们徘徊于两个世界、两种身份之中,哪一方都不能将其完全接纳。这样的边缘身份总是带有悲剧色彩。
在《伊万的童年》中,父辈军官们一次次把伊万送进后方的军校和儿童院,伊万又一次次回到队伍,气急败坏地向他们质问,并企图证明自己:“我知道敌军即将发动进攻,我会很有用处!”年长者可以用理智去理解战争的苦难,但对伊万这样心智尚未健全的儿童来说,战争带来的却是一场严重的情感裂变。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伊万和他那些父辈战友之间实际有着一条微妙的分界线:伊万不同于年轻的加尔采夫上尉;不同于勇敢的侦察兵霍林大尉;不同于头脑清醒的善良的卡塔索内奇;也不同于像父亲一样疼爱他的格里亚兹诺夫上校。因为“对于成年人来说,战争不仅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而且是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作。每个人都认真忘我地做着这件工作,必要时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但对伊万来说,战争中没有休息,没有假期,没有日常生活。没有后方,没有晋升和褒奖,除了战争本身,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对他来说,战争是一种绝对的需要,高于其他一切[2]53。” 自伊万加入游击队开始,残酷的战争便成为其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求他时时保持高度警惕;但属于伊万的儿童世界的记忆却又没有完全远去,反而通过梦境一次次召唤他。于是,现实中的伊万是面容冷峻的红军侦察员;梦境中的伊万是笑容纯真的孩子。这两种身份撕扯着他,使他每每从梦中惊醒回到现实世界后都感到——“我的神经快要崩溃了”。
伊万是一个战争的产儿,他完全适合战争环境,以致于绝对无法适应和平生活,其结局只能是毁灭——他在一次执行任务后再也没有回来。影片最后,塔可夫斯基用跳跃性剪辑表现了伊万之死:战争胜利后,红军从德帝国大臣官邸中搜出无数惨死的儿童尸体;镜头随着加尔采夫的脚步和视线移动,他在废墟的文件堆中发现了伊万的死亡报告,从上面的照片切入伊万被行刑前与守卫的对话,使加尔采夫的当下时空与伊万行刑的时空穿插并行;待伊万的尸体从绞刑架上跌落,从他眼睛的特写切入伊万的梦境,与伊万母亲关切的目光相对接;梦境的结尾伊万朝前伸出手臂,接着黑色的枝干覆盖了景框。在塔可夫斯基看来,原著中主人公之死有着特殊含义:“在其他作家笔下,这之后总还会有令人宽慰的情节。但这篇小说在这时却戛然而止了。通常在这种情形下,作家都喜欢表彰一下主人公的赫赫战功。艰难、残酷已经成为过往,它们只是生命中一段艰辛的历程。而在博戈莫洛夫的小说中,这一历程被死亡打断,并成为唯一的和最终的历程。这里浓缩了伊凡悲怆的一生。这一完结以出人意料的力量,让人体会到战争的荒谬[1]13。”塔可夫斯基用影像出色地传达了其意旨。
另一边,《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的皮恩同样游离在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边缘。同龄的男孩子不喜欢皮恩,因为皮恩是大人的朋友,他知道的事比他们都多;皮恩只能留在大人的世界里,但大人们也不欢迎他,他只被大人当作好玩的或讨厌的东西来对待。皮恩是个不会玩的孩子,既不会参加大人的游戏,也不会参加小孩的游戏,他只能在臆想中渴求认同:“他想像一帮孩子推举他当头领,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大家一起去反对大人,打他们,做出一番惊人的事情来。让大人们也不得不佩服他,并让他当头领,让大人们喜欢他,抚摩他的脑袋[3]15。”故事中,皮恩盲目地参与战争而不问党派,只为找到一个能够接纳他的地方,战争对他来说就是不断接触“西姆”“加波”“格伯乌”这类带着激情的名词的冒险,每个词语都好像是一个暗号,可以让他被懂得这一暗语的群体所吸纳。
战争中各方力量此消彼长,历经欺骗与失望后,皮恩被大家抛弃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不知道去哪里——“他发现自己对那些计划的热情是假的,预想的。发现他的幻想肯定永远不能实现,他继续是个迷途的、到处漂泊的可怜孩子[3]160。”但纵使现实中不断受挫,仍有一隅属于儿童的幻想之地在牵引着他——蜘蛛巢。皮恩从故事伊始就一直在自顾自地幻想:“可能有这么一天,找到一位朋友,一位明白事理和能够明白事理的真正的朋友。那时他就把蜘蛛巢的地方告诉他,只告诉他一个人[3]22-23。”皮恩没有把蜘蛛巢告诉酒馆里那群男人,他们只知谈论战争和女人;皮恩没有把蜘蛛巢告诉红狼,虽然他是一个杰出的青年,但他只对政治这样严肃的事情感兴趣;最后,迷途中的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分享蜘蛛巢的朋友——表兄——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最后一个人。但当皮恩领着表兄到那后,却发现法西斯分子佩莱把蜘蛛巢都毁了,只剩下了一个完整的巢。皮恩问“你相信它们能重新筑巢吗?”表兄答“如果让它们安静,我想会的[3]166。” 蜘蛛巢无疑象征着被摧毁的童年,而重新筑巢则是矫正战争流弊的希冀。小说最后,皮恩和表兄达成了温暖的情谊——“他们继续走着,大人和孩子,在黑夜中,在萤火虫飞舞中,手拉着手[3]170。”这个乌托邦式幻想使战争中被异化的儿童和疲惫的成人短暂地得以回归和解放。
相同的边缘身份,不同的错位结局。在毁灭和生存的两重境遇中,塔可夫斯基的伊万和卡尔维诺的皮恩提供了关于战争反思的两种不同范式。
结 语
生于1932年的塔可夫斯基与生于1923年的卡尔维诺都是在年少时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他们与自己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属于同一代人。《伊万的童年》与《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可以说都产生于时代的总体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凡是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见证者都会感到一种特殊的责任,有着迫切的表达愿望——“表达我们自己,我们那时经历的辛酸生活,表达我们自认为所知或所是的许多事情[3]4”。两部作品均一反当时正面的创作潮流,而另辟蹊径地从反面入手,表现战争中被摧残异化的儿童,其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的表现力在当今仍具借鉴意义。
此外,值得提及的是,《伊万的童年》与《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作为塔可夫斯基与卡尔维诺的处女作,在其各自的创作生涯中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塔可夫斯基将《伊万的童年》视为“对我创作资格的测验[1]24”,以这部长片为开端,他确定了自己做导演的能力。影片对梦境这一载体的青睐、长镜头的运用等可以说奠定了塔氏的创作基调。他之后的《镜子》《乡愁》《牺牲》等代表作,更进一步创造了崭新的、忠实于电影本体的语言,开始了形而上的生命探索。而卡尔维诺在自己的首部长篇《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指认出的个人特质是寓言写作和童话意味,这两点亦贯穿于他今后的写作。在完成了《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后,卡尔维诺亦像塔可夫斯基一样经历了转型。他由经验写作转向虚构写作,由新现实主义转向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作出了《看不见的城市》《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寒冬夜行人》等蜚声文坛的作品。
无论是在创作初期选择以孩童视角展现战争对人心灵的摧残和异化,表达现实人文关怀;还是转型后对诗性的追求与对哲学的思考,作为导演的塔可夫斯基和作为作家的卡尔维诺都有着令人惊奇的相似。跨越影像与文学文本的界限,在保护二者独立性的同时探究其共同内核,增进了解并互蒙其利,于文学于电影,都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