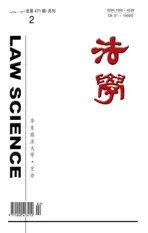区域协同立法的合法性困境与出路
——基于辅助性原则的视角分析
2021-12-07韩业斌
韩业斌
区域协同立法是我国地方立法领域出现的新兴概念,它是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及跨区域社会治理需要而提出的一种法治对策,是在特定区域范围内跨行政区的地方立法机关之间就区域性公共事务,在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同展开区域性规则的制定、认可、变动的立法活动总称。区域协同立法依托于享有立法权的各个地方立法机关,强调多个享有立法权的地方立法机关之间的协同配合。区域协同立法在欧盟地区及美国各州之间已经具有较为广泛的实践基础,欧盟法与州际协定可以看成欧洲和美国州际之间区域协同立法的代表。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区域内的各方在立法方面展开合作,成立共同的立法机构,该机构的立法权限、行使范围、行使方式均由各成员协商确定,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总体上看,欧盟区域内各成员国仍有立法权,但不得与欧盟法相冲突,欧盟法的效力优先于欧盟各成员国国内法的效力。美国在处理州际关系时,形成了州际协定模式,州际协定在美国已经具有上百年历史,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机制,可用以协调州服务的提供、管制政策和设施建设,也可用以建立新的地区间政府实体。州际协定相当于在缔约各州的全部或部分领土上制定了统一法,涉及政治主权性州际协定需要国会批准,其他州际协定只需要州议会批准即可生效。〔1〕参见[美]齐默尔曼:《州际合作:协定与行政协议》,王诚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35-42 页。反观我国,由于《立法法》只承认国务院各部门之间联合立法,没有规定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可以跨行政区域协同立法问题,这就导致了目前区域协同立法容易陷入缺乏合法性依据的困境。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依据的缺失导致立法实践过程中地方立法机关鲜于从事协同立法活动,协同立法成果较少,协同立法的功能和意义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如何破解区域协同立法的合法性困境呢?我们不妨转换视角,以辅助性原则理论为视角进行探讨。辅助性原则为我们解决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一、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困境的主要表象
合法性就其含义来说,有些学者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讨论合法性,主要针对公共权力或政治统治的合理性、正当性、权威性和实际有效性问题,即是人民群众对政权的认同态度问题,如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239 页。而在马克·夸克看来:“合法性即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3〕[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版,第10 页。这些观点都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也就是从人民群众对其统治认同程度的角度讨论合法性问题。有些学者从法学角度讨论合法性问题,即形式合法性问题,主要讨论一个行为或者制度是否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制度规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合法律性问题。哈贝马斯指出:“合法律性是不问法律承受者的态度和动机的,”〔4〕[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0 页。它只以统治者颁布的现行有效法律为依据进行判断。合法律性原则适用于所有的国家活动,不仅意味着限制公民个人权利的活动,还包括那些为个人和活动提供利益的相关国家组织。夏皮罗认为,合法性这一术语有时是指符合法律的或合乎法律的,有时又指一种价值或一组价值,尤其是那些与法治相关的价值。在直接谈及合法性的时候,他指的是可以被规则、组织、官员、文本、概念、陈述和判断等实例化的一种属性。〔5〕See Scott J.Shapiro, Lega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404.夏皮罗教授所说的前一种含义,也是合法律性问题,即指符合现有法律的规定。当然,在法律实证主义者看来,合理性和合法律性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重合的,只要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大部分情况也是合理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也会产生合理性和合法律性不重合问题,比如我们现在讨论的区域协同立法问题就是一个典型。就区域协同立法的合法性而言,主要面临着缺乏直接法律依据的困境。
(一)法律依据缺失导致区域协同立法的现有成果较少
法律依据的欠缺是导致区域协同立法进展不大的重要原因。〔6〕参见葛胜亮:《区域立法协作机制浅探》,载《人大研究》2016 年第8 期,第17 页。寻遍我国现行《宪法》《立法法》,我们很难找到区域协同立法的直接依据。《宪法》第99 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根据该条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只能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的地方人大无权保证法律得到有效执行,也没有能力保证法律得到有效执行。虽然近年来一些地方立法对区域协同立法进行了规定,如2020 年7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条例》第42 条规定:“北部湾经济区各设区的市建立区域协同立法机制,加强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和立法起草、论证、审议等环节的沟通协商,促进北部湾经济区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协调一致,引领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但是由于该条例的法律效力较低和实施范围有限,很难作为其他地区进行协同立法的法律依据。可以说,目前在国家立法层面上,跨行政区域的协同立法实际上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国内较早实施区域协同立法的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2006 年签订的《东北三省政府立法协作框架协议》,为三省政府间协同立法提供了制度框架,许多学者对此寄予厚望,认为此举必将有利于实现区域性立法资源共享,降低立法成本,消除立法冲突,维护地方立法体系和谐和国家法制的统一,〔7〕参见李林主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第47-48 页。然而该协议签订10 多年来,真正的协同立法成果并不是很多。除了东北地区之外,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也就区域协同立法签订了一系列立法合作协议,如2015 年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京津冀人大协同立法的若干意见》、2017 年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的《京津冀人大立法项目协同办法》和2018 年第五次京津冀协同立法工作会议通过的《京津冀人大立法项目协同实施细则》、2018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签署的《关于深化长三角地区人大工作协作机制的协议》和《关于深化长三角地区人大常委会地方立法工作协同的协议》,以及2020 年7 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签订的《关于协同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合作协议》等。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协议无一例外地都没有对外公布,人们只能从新闻报道中看到立法协议的签订情况。这些立法协议没有向民众公布,民众便无从知晓,更无法监督上述协议的执行情况,同时理论研究者无法看到这些立法合作协议的具体内容,理论研究难以深入下去,自然也无法为区域协同立法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南。虽然近年来一部分学者和地区对区域协同立法的呼声很高,并指出,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跨省域、跨市域之间的区域协同立法需求必将越来越迫切。〔8〕参见虞浔:《立法协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载《人民日报》2019 年1 月17 日,第19 版;周霄鹏:《京津冀打造地方协同立法新样本》,载《法制日报》2020 年3 月22 日,第1 版;秦建莉、范海杰:《淮海经济区十市人大共同建立立法协作机制 为设区市地方立法跨省协作提供新模式》,载《徐州日报》2019 年12 月13 日,第2 版;邱洁:《加快推动区域协同立法》,载《德阳日报》2020 年5 月15 日,第2 版。但是,目前区域协同立法活动大部分还是停留在立法信息、立法项目、立法程序的沟通协调上,真正协作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京津冀三地关于《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防治条例》、沪苏浙皖四地通过的《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以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通过的《酉水河保护条例》可以看成相对成功的事例,但这些协同立法成果往往集中在环境保护领域,其他领域协同立法成果仍然较少。
(二)中央政策与最高立法机关之间意见不一
针对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问题,中央国家机关也有不同的态度。近年来,中央出台了诸多区域规划文件: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这些政策性文件都是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的,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并没有参与其中。这些文件的颁布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态度和决心,而区域协同立法正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性策略,因而,我们可以推导出,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区域协同立法应该是支持和赞许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京津冀三地要打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建立地方立法和执法工作协同常态化机制,推动重点区域、重点领域跨区域立法研究,共同制定行为准则,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法规支撑和保障。该《规划纲要》还要求,要建立统一规则,规范招商引资和人才招引政策,以及建立重点领域制度规则和重大政策沟通协调机制,提高政策制定的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
还有,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指出,要加强区域立法工作的合作与协调,形成区域相对统一的法制环境。不得不说,这些规划纲要、指导意见对于立法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上述规划纲要、指导意见只能算作政策性文件,尚不具有法律渊源地位,因而不具有法律性质,不足以为区域协同立法提供合法性依据。另外,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通过颁布《指导意见》的形式,要求加强区域立法合作与协调与法理不符,区域之间是否需要立法合作与协调,应该由最高立法机关予以规定更为合适,最高行政机关予以规定有违法理。有学者认为,由于硬法的缺位,导致区域协同立法缺乏制度保障,不妨将上述政策性文件看成软法规范,使其作为区域协同立法的软法依据,但是由于软法的法律约束力较弱,无法突破地方政府利益观念束缚及各个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积极性主动性参差不齐,实施效果不佳。〔9〕参见陈可翔:《欧盟开放协调机制于我国区域法治协调之借鉴——以区域软法治理为视角》,载冯玉军主编:《区域协同立法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110 页。
就全国人大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人员也在不同场合就区域协同立法表示支持,早在2013 年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领导就表示,日前长三角、东三省等部分省份提出开展区域立法合作,全国人大法工委已同意地方可以先行先试,并认为,这代表了未来立法的发展方向,至于是各省共同起草还是各自起草、保持相对一致,可以做进一步探索试验。〔10〕参见陈竹沁、金可镂:《各省市可试点跨省区域性立法》,载《南方都市报》2013 年6 月30 日,第9 版。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就区域协同立法又有诸多会议讲话,充分肯定了区域协同立法实践。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在2018 年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地方人大在这方面有许多生动的实践和经验,也不断有新的探索。比如,近年来一些地方加强区域协同立法,建立完善区域协同立法工作机制,京津冀优先推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升级转移三个重点协同立法项目,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关于深化长三角地区人大常委会地方立法工作协同协议,地方立法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对我们做好全国人大层面的立法工作具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11〕沈春耀:《在第二十四次全国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上的小结讲话》,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zgrdw/npc/lfzt/rlyw/2018-09/20/content_2061462.htm。还有2019 年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省级人大立法工作交流会上指出:“地方立法要围绕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突出地方特色,抓好重点领域立法……抓好协同立法,依法保障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实落地。”〔12〕王萍:《吹响新时代地方立法工作“集结号”》,载《中国人大》2019 年第18 期,第9 页。另外,2019 年11 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在第25 次全国立法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对属于省(区)域内若干设区的市的共性立法问题,比如大气污染防治、流域性水污染防治、林业生态保护、旅游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可以加强设区的市之间的地方立法协同。”〔13〕李飞:《加强和改进省(区)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立法工作的审批指导》,载《中国人大》2020 年第2 期,第19 页。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讲话外,几乎每次京津冀协同立法会议和长三角协同立法会议都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同志参加,协同立法的文本最终也要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对于是否需要修改《宪法》《立法法》 赋予区域协同立法以法律依据问题,上述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们都没有作相关表态。可见,对于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尚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三)合法性与非法性争论相持不下
关于区域协同立法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法学界也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区域协同立法具有合法性,其主要理由为:第一,宪法序言的间接推导。虽然《宪法》和《立法法》都没有直接规定区域协同立法的内容,但是宪法序言部分却增加了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都要求践行可持续的、协调的发展理念,协调发展自然也包括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法治的协调发展,而立法是法治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是实现良法善治的前提条件,协同立法自然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14〕参见刘松山:《区域协同立法的宪法法律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 年第4 期,第64-66 页。第二,国务院部门联合立法的指引。《立法法》第81条规定:“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该条关于部门联合立法的规定,可以看成区域协同立法的指引。既然跨部门的事项可以通过联合制定规章来调整,那么跨行政区域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地方联合立法来解决呢?二者的实质都是立法权的行使问题,而非配置问题,对现行立法体制没有影响。〔15〕参见刘莘主编:《区域法治化评价体系与标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2 页。第三,依据地方立法权的推导。《立法法》第72 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跨区域社会治理也是地方发展的实际需要,因而,有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制定统一的地方性法规,只要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就可以了。〔16〕参见王腊生:《地方立法协作重大问题探讨》,载《政法论丛》2008 年第3 期,第71-72 页。
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区域协同立法缺乏合法性依据,主要理由在于缺乏《宪法》《立法法》上的明确依据。如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宪法》与《立法法》的规定中我们无从看到关于区域协同立法的规定。显然,在我国,各区域协同立法是缺乏法的依据的。〔17〕参见宋方青、朱志昊:《论我国区域立法合作》,载《法治与法律》2009 年第11 期,第20 页。由于《宪法》和《立法法》没有进行正式规定,地方人大和政府之间进行区域协同立法实践需要时刻面临着违宪违法的风险,包括违反《宪法》及宪法相关法规定的“不抵触原则”,以及立法协作中超越立法权限、违反立法程序等情形。〔18〕参见姚明:《地方立法协作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 年版,第129 页。由于缺乏合法性依据,还导致区域协同立法只能在一种相对松散、彼此约束力不强的条件下进行。〔19〕参见焦洪昌、席志文:《京津冀人大协同立法的路径》,载《法学》2016 年第3 期,第42 页。地方官员参与协同立法的积极性不高,更多地处于一种徘徊和观望状态,区域合作更多地体现在一些具体事务上和行政领域,现有区域协同立法成果不多。〔20〕参见陈光:《区域立法协调机制的理论建构》,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87 页。
基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支持论者的论证思路是根据宪法序言所反映的法律精神,以及《立法法》规定的国务院部门可以联合制定部门规章,地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间接推导出区域协同立法具有合法性,这种推论是比较勉强的,至少从《宪法》《立法法》中直接推导出区域协同立法具有合法性具有一定难度。但是从现有法律间接推导出区域协同立法具有合法性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如有学者认为,区域协同立法仅仅涉及地方立法权的行使问题,对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没有影响,因而不需要《宪法》《立法法》的规定也是可以的。还有学者认为,区域协同立法涉及立法权的配置问题,因而需要《宪法》《立法法》予以规定,笔者认为,所谓立法权的配置问题,主要是涉及立法权的有无,以及立法权的权限范围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宪法》《立法法》予以规定,比如设区的市能否获得立法权,设区的市的立法权权限范围是否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保护这三个方面,这些都是立法权的配置问题,需要《宪法》《立法法》进行规定,而区域协同立法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它仅仅涉及享有独立立法权的省市之间的相互配合协作问题,也就是立法权的行使方式或行使程序问题。反对论者的论证思路是,立法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才能行使,否则即是缺乏合法性依据,面临违宪违法风险,而现行《宪法》和《立法法》没有直接而明确的规定,因而就断定区域协同立法没有合法性依据,至于其他相关法律有没有区域协同立法的相关规定,学者们大都没有进行仔细考察。既然《宪法》《立法法》没有明确规定,又何谈违宪违法呢?这似乎是《宪法》和《立法法》的一个漏洞和盲点,是不是没有《宪法》《立法法》的直接规定就一概不允许区域协同立法呢,反对论者没有进一步论证。区域协同立法的合法性困境实质上反映的是合理性和合法律性之间的矛盾问题,也就是一项制度设计虽然具备相对充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依据,但缺乏直接而明确的法理依据,能否进行实践呢,这也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
二、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不足导致的法治风险
阿蒂亚说:“合法性的形式问题是有关特定法律或规则或命令的权威之形式渊源的纯法律问题。”〔21〕[英]P·S·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范悦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157 页。这里所谓的合法性其实就是合法律性问题,也就是一项法律或者规则的法律依据问题。区域协同立法是地方立法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面对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大潮中,区域协同立法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家立法层面上尚没有对区域协同立法的法律依据予以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区域协同立法仍然缺少合法性依据。由于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依据不足容易导致诸多法治风险。
(一)背离限制权力的法治原则
公权力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与约束,这是当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区域协同立法涉及两个以上地方立法权的共同行使问题,影响到同一区域范围内广大民众的权利义务,因而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与制约。在权力限制的各种理论中,通过法律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通过法律赋予政府机关的权力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政府机关必须作为,法律没有赋予政府机关的权力,则政府机关不允许作为。拉兹认为,狭义的理解法治,即政府受法律的统治并服从法律。〔22〕See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12.毛雷尔指出,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是国家遵守法律的约束。任何国家权力及其机关都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立法机关受宪法和宪法制度的约束,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受法律、权利和法治的约束。〔23〕参见[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106 页。塔玛纳哈也认为:“政府无论做什么事情,它都应该凭借法律行事。”〔24〕[美]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18 页。合法性原则也是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合法性原则主要包括 “法律至上”和“法律保留”两个方面的内容。“法律至上”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尊重法律,“法律保留”意味着除不可抗力外,任何国家活动都必须以法律规则为依据。〔25〕See Andreas Ladner et al, Swiss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king the State Work Successfully,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79.合法性原则不仅限制行政权,还应该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合法性原则根本来说是为限制立法机关制定的标准……立法机关制定的法案只是国家行为,因此其是否合法要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基础规范。”〔26〕[加]大卫·戴岑豪斯:《合法性与正当性:魏玛时代的施米特、凯尔森与海勒》,刘毅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174 页。因而对于同样作为一种公权力的立法权而言,对宪法赋予立法机关的权力,立法机关必须作为,宪法没有赋予立法机关的权力,立法机关则不可为,这要求立法机关必须依法立法,没有法律依据的权力,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力。权力始终存在异化和被滥用的可能,立法权也不例外,而且,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滥用相比,立法权被滥用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需要对立法权及其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以避免立法腐败和立法寻租现象的发生。〔27〕参见易有禄:《立法权正当行使的控制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45 页。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反复强调,“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的权力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界定法治,他把法治所要求的法律和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区别开来,他进而指出,“法治只在立法者认为受其约束的时候才是有效的。”〔28〕[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260、261 页。也就是说立法机关也存在违反法治的情况,立法机关也会滥用立法权,制定不适当的法律,从而违背法治原则,侵犯人民权利。
另外,“法无授权不可为”也是现代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 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8 年版,第388 页。那么这个制度之笼应该如何打造呢,这个制度之笼的四梁八柱应该包括哪些呢?“法无授权不可为”就是把国家公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支柱。这一点在李克强总理的讲话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李克强总理指出:“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30〕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14 年2 月24 日,第2 版。对于立法权也是一样,宪法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了立法机关的权力,宪法的列举既是立法机关行使权力的依据,同时也构成对立法机关权力的限制,即宪法没有列入的权力,立法机关就不能行使。既然《宪法》和《立法法》没有赋予地方人大之间跨行政区域联合立法的权力,则意味着法无授权不可为,立法机关必须遵守,否则限制权力的法治理念就会被虚置。〔31〕参见童之伟:《“法无授权不可无”的宪法学展开》,载《中外法学》2018 年第3 期,第583-587 页。
(二)导致地方立法权的滥用
《立法法》修改以后,地方立法主体的数量不断增多,地方立法权被滥用的风险也随之加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获得地方立法权的主体不断增多,立法权限也在不断加强。有学者认为:我们在生活中更多地关注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滥用,对于立法权的滥用感触不深,其实,一条法律、一项规则,影响的是某个行业甚至是一批人的利益,它带来的利益或不公都是整体的、普遍的,其危害性可能远胜于某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或者司法行为。〔32〕参见游伟:《立法权扩大落地须防权力滥用》,载《上海法治报》2014 年10 月20 日,第A06 版。尤其是大量设区的市获得立法权之后,享有立法权主体的行政层级越低,其与具体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的利益纠葛越紧,对公民和社会权益的损害可能越大,因此享有地方立法权主体过多过滥,也加大了设区的市滥用地方立法权的可能性。地方滥用立法权导致一些地方立法粗制滥造、重复立法、缺乏特色、可操作性不强、程序不规范等问题,破坏现有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就是近年来地方滥用立法权的典型一例,由于甘肃省人大把关不严,导致上述地方性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发生严重抵触,国家自然区保护条例明令在保护区内禁止砍伐、放牧等十类行为,但是《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则将上述十类行为缩减为三类,且都是近年来很少实施并已基本得到控制的行为,这对祁连山的自然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我们要深刻吸取《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部分内容严重违反上位法规定,在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水”的经验教训,守住地方性法规不得跟上位法相抵触的底线。要遏制地方立法权的滥用,就必须加强对地方立法权的监督,推进合法性审查机制,防止任性立法、越权立法。〔33〕参见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1 期,第10-13 页。
至于区域协同立法同样也存在地方立法权滥用的可能性。由于同级地方人大之间是否可以相互协作共同行使立法权,法律没有规定,这可能是《立法法》修订者始料未及的,这也对法治国家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立法法》只承认国务院各部门之间联合立法,未肯定甚至未认识到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协同立法的意义与功能。〔34〕参见崔卓兰等:《地方立法实证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年版,第505 页。在单一制国家,宪法中往往强调中央与单个地方之间的纵向关系,对于区域之间横向关系宪法没有规定,目的在于防止区域之间通过相互协议,从而达成利益同盟,危害中央权威。对于区域协同立法,由于法律没有规定,人们往往认为,区域协同立法就是存在一个跨区域的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之后可以适用于整个区域,这样容易形成所谓“立法联盟”,或者法律“独立王国”,形成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利益割据。这些都是宪法和法律所不允许的,也与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不相容。这也是地方滥用立法权的一种体现。
(三)地方保护主义再次强化
对于区域协同立法而言,除了违反法治原则和地方立法权被滥用的风险之外,还存在一种风险,即一些地方人大或者地方政府往往借区域协同立法之名,把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和正当化。地方保护主义一般是指地方政府以损害辖区外经济主体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其辖区内经济主体利益的各种不公平保护行为。它在我国有着深刻的体制基础和理念基础,由于分税制改革,地方获得相对独立的征税权力;另外,上级政府主要以下级行政区域的经济指标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选拔依据,也就是地方政府在所属辖区内有了自己的特定利益。当地方政府有了财政税收的支配权,从而能够发展自己所在辖区的经济;而当取得更好的政绩时,便有了进一步提拔升迁的可能,这是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最终会反映在本地企业的竞争力上。迈克尔·波特指出:“企业会通过国家、地区和全球战略来实施跨地域竞争。同时,国家和地区必须同其他地域进行竞争,从而创造出一个具有商业吸引力的环境。”〔35〕[美]迈克尔·波特:《竞争论》,刘宁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 年版,第10 页。这样一种地方竞争模式,在一些目光短视的政府官员看来,为了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往往封锁本地市场,以提高财政收入,这样就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在地方立法、行政、司法过程中均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立法过程实质上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立法者本来需要不偏不倚地考虑到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主张。〔36〕参见杨炼:《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3 页。但是一些地方人大和政府很可能以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为名义,把地方不正当利益纳入地方立法保护之中。地方利益影响地方立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立法项目的选择上,保护本地稀缺资源和市场成为地方立法的主要项目;其二,对主体规定不同的权利义务,通常本地主体享有更多的权利,承担更少的义务,而外地主体承担更多的义务,享有更少的权利。对于区域协同立法而言,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约束,若干行政区域的人大和政府之间往往通过共同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把本区域的市场相对封闭,从而在更大区域范围内保护本区域的市场主体利益,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也正是反对区域协同立法的学者所担心和忧虑的。以东北地区的政府协同立法为例,东北三省政府2006 年签订了《东北三省政府立法协作框架协议》,至于东北地区为何要开展区域协同立法,当地一位法制办立法处负责人表示,由于地方立法标准不一致,吉林全省货车往往“外逃”到黑龙江、辽宁等省份,导致吉林省每年损失大量养路费,这主要是由于各地的运输车辆收费标准不同而造成的。为了防止运输车辆外逃,增加当地政府税费收入,东北地区需要进行协同立法,制定共同的运输车辆收费标准。〔37〕参见钱昊平:《立法协作:东北三省的尝试》,载《人大建设》2006 年第10 期,第41 页。这一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理,但是人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收取运输车辆税费属于政府的自身利益,东北三省地方政府是否会通过协同立法的形式,达致三省政府自身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这也是从立法上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将整个东北地区政府税费收入的增加作为更大的利益加以保护。
三、探寻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困境的出路
鉴于一定区域的地方人大根据区域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共同协商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于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区域性市场共同体的形成,应对跨区域社会治理,提高相关地区立法质量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基础,因此区域协同立法势在必行。但是在区域协同立法过程中,合法性困境是其无法逾越的障碍,如何克服区域协同立法的合法性困境呢,我们不妨从辅助性原则理论中寻求解决方案。〔38〕关于在区域环境协同立法中引入辅助性原则理论,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该学者指出,在区域环境协同立法的推进上,可以考虑引入辅助性原则……基于辅助性原则的两面性,区域环境协同立法在方案设计上应有时间进程的先后,以上级政府主导为近程,以区域内政府间的平行合作为远程,逐步实现由 “被动式回应型协同”向 “主动式常态型协同”转变。参见曾娜:《从协调到协同:区域环境治理联合防治协调机制的实践路径》,载《西部法学评论》2020 年第2 期,第61 页。
(一)尊重部分区域的先行探索精神
辅助性原则兴起于20 世纪70 年代,90 年代之后发展迅猛。辅助性原则最早源于天主教社会哲学思想,强调一切社会活动,从其功能与本质上说,应该是为社会成员提供帮助,但是绝不是毁灭或攫取他们。“辅助性原则绝不是内容空洞的流行语,或者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口号……是一项明智的规则。”〔39〕[德]罗尔夫·思特博:《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陈少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5 页。在西方语境中,辅助性原则发展成为一项政治法律原则,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辅助性原则主要解决多层级治理体系中下级政府、地区政府与跨国组织之间的权力纵向分配问题。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辅助性原则特别强调将决策权力尽可能地配置到基层,发挥基层、社会组织和下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40〕See James E. Fleming, Jacob T. Levy, Federalism and Subsidiari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25-126.与之前的国家中心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理论相反,辅助性原则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权力要自下而上地配置和行使,尽可能贴近基层作出决策。有学者指出,在其语境中,辅助性一般被理解为,政府的各项立法与行政政策,应当由最贴近于受政策影响的人们所在的政治层级来决定。〔41〕See George A. Bermann,Subsidiarity as a Principle of U.S. Constitu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42, 1994, p. 555.还有学者认为,在一个由个人、家庭、基层社区、教会和国家组成的多层次治理体系中,中央集权受到限制有助于在尽可能低的层级上解决自身问题。〔42〕See Michelle Evans, Augusto Zimmermann, Global Perspectives on Subsidiarity, Springer, 2014, p.2.
如果从上述视角来看,区域协同立法是地方人大基于区域一体化和跨区域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自发构建的一种制度性举措,其首创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在《宪法》《立法法》未作修改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先易后难,先试点再推开的思路和原则,默许和尊重部分区域先行试点探索精神。在区域一体化较为发达的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等区域可以先进行一些探索,待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争取法律支持。在区域协同立法较为活跃的京津冀地区,近年来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经验,2017 年3 月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了《京津冀人大立法项目协同办法》,该《办法》主要围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核心要义,在环境保护、交通一体化和产业升级转移等方面优先展开协同立法。“无论在任何地方,稀缺的立法资源和有限的起草时间都迫使起草者必须决定起草法案的优先顺序。”〔43〕[美]安·赛德曼等:《立法学:理论与实践》,刘国福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年版,第64 页。在京津冀协同立法中,环境保护等方面将被优先安排。有学者认为,环保领域是京津冀协同立法的“富矿”所在,同时还是区域协同立法的“创新”之地。〔44〕参见冯志广:《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立法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法治保障》,载冯玉军主编:《京津冀协同发展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253 页。这是因为,在环境保护领域开展区域协同立法实践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依据,现行《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可以允许特定区域之内各地方人大之间先行探索,以便应对日益严峻的环保压力。〔45〕在环境保护领域相关法律中具有关于跨区域联防联控及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的诸多规定,比如《环境保护法》第20 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6 条、《水污染防治法》第16 条,等等。针对上述国家层面的立法规定,如何在地方层面具体落实呢?这就需要同一流域范围内或者区域内的人大之间协同起来,共同立法,通过建立统一的规划、标准、监测制度,以便发挥联防联控的最佳效果。也就是说《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的上述条文为区域内展开环境保护方面的协同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近年来协同立法成功的样本,包括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湖北省恩施州和湖南省湘西州酉水河保护条例及京津冀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器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均指出其立法依据是《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而没有指出立法依据为《宪法》《立法法》,这些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防治的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又如何解释呢?有学者认为,由于《立法法》中缺乏对于区域协同立法的具体规定,现有的区域协同立法实践无法从制度上突破地方立法机关跨地区进行立法并跨地区统一适用和执行的“瓶颈”。虽然宪法等相关法律并没有对区域协同立法进行规范,但是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却提出建立跨区域污染治理的联防联控机制,因而我们就不能片面地认为区域协同立法完全没有合法性依据。虽然上述立法对于区域协同立法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是具有部分合法性的。参见刘学文:《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区域一体化立法的困局与超越》,载公丕祥主编:《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第2 卷),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231 页。然而把区域协同立法仅拘泥于环境保护领域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环境保护领域的协同立法仅针对环境保护本身的跨区域特点,而不是基于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需求,也就是说环境保护领域的协同立法不是基于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求而出现的。如果要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就必须推动更高层次的协同立法,在市场经济秩序和营商环境、政务服务、社会信用、食品安全、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文化旅游发展等领域广泛开展协同立法,确保同一区域范围的营商法律规则一体化,从而消除行政壁垒,保障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好地服务于区域性统一市场的形成,更好地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但是营商环境领域的协同立法尚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困境,这需要转换视角,引入辅助性原则理论,为营商环境领域的协同立法开辟路径。
基于辅助性原则的要求,相对于中央立法来说,地方立法具有从属性和实施性,但同时也具有先行性和试验性的特点,凡不属于应当由国家统一立法的事项,在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之前,地方都有权根据地方的实际需要先行立法。〔46〕参见李步云、汪永清主编:《中国立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年版,第222 页。一些地方正在对区域协同立法进行积极探索试验,有些区域的地方人大之间展开积极沟通协调,签订许多立法合作协议,有些正处于立项、论证、审议阶段,有些协同立法项目已经获得了相应地区的人大批准通过。〔47〕《丽江市泸沽湖保护条例》是区域协同立法又一成功案例,该条例已经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泸沽湖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和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交界区域,为了共同保护泸沽湖,云南省丽江市《条例》起草班子多次赴宁蒗实地调研听取意见、反复论证研究,还专门征求四川省凉山州和盐源县人民政府的意见,把川滇两省共治共管共建泸沽湖体现到立法环节,《条例》明确要求丽江市、宁蒗县人民政府应当与凉山州、盐源县人民政府协商建立泸沽湖保护协调机制,构建泸沽湖共同保护治理工作格局,维护泸沽湖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四川省凉山州的泸沽湖保护条例也正在修订之中,可以预见通过两地的协同立法能够对泸沽湖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参见蒋朝晖:《云南首次实践区域协同立法 推动形成川滇共同保护管理泸沽湖新格局》,载《中国环境报》2020 年1月3 日,第8 版。在没有中央立法依据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坐等法律修改或者中央授权,错失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机。改革和发展都有一个机遇问题,不能等到法治完备了再进行改革,只要这种改革符合宪法的精神即可,并不一定要求每一项改革都必须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应该通过解释和论证,在实践中去发展和完善法治。〔48〕参见叶必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8 期,第129-130 页。综观我国的改革历程,几乎所有意义重大的举措都是首先在地方试验成功的条件下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假如不允许地方试验,那么中国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维持现状,或者在没有任何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贸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后果未知的改革,从而极大增加改革的风险和难度,如果一概以违法乃至违宪为由禁止地方试验,那么就很可能扼杀改革的种子,最终延缓全国从地方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受益的进程。〔49〕参见张千帆:《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另一种视角》,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3-144 页。同时,在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应该容许地方开展积极探索试点,理由还在于,对于区域协同立法而言,地方人大和政府对于当地公共事务更为熟悉和了解,因而通过各区域自行协商解决更为合适,我们应该尊重和肯定地方的先行探索、试错精神,只有在地方无力解决的时候,上级机关才能进行干预,对于地方探索中出现的失误或者偏差,可以予以免责或者减轻责任,这样才能有效激发地方的积极性,这也正是辅助性原则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学家格尔茨看来,法律是一种对特定地方的特定事物赋予特定意义的活动。〔50〕See Cliあ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Basic Books, Inc., 1983, p.232.因而特定区域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所在区域的立法事项更为熟悉和了解,通过区域协同立法的形式进行解决,也是法律对社会生活具有建设性作用的重要体现。还有学者在研究美国州际协定时指出,相比于联邦政府而言,联邦政府及其官员容易忽视各州的利益需求,对于各州的重要利益需求往往疏于作出反应,而州际协定的快速反应可以弥补联邦政府对于各州利益不甚关注的消极作用。〔51〕See Christi Davis, Douglas M.Branson, Interstate Compacts in Commerce and Industry: a Proposal for “Common Markets Among States”, Vermont Law Review, Vol.23: 143-144, (1998).因而,对于我国的区域协同立法而言,以区域协同立法的形式推动地方法治和区域法治的发展,待时机成熟再提请法律修改,这是辅助性原则对我国法治发展的重要启示。
(二)全国人大应尽快修改《立法法》,及时肯定区域协同立法活动
辅助性原则还有一层含义,即可以把中央立法对地方立法的授权看成为上级干预原则的积极行使。基于辅助性原则的要求,决策的制定实施主要用以保证更好地和更有效地实现目标,换句话说,只有在下级机构不能有效地履行某一特定职能时,上级当局才会进行干预。〔52〕See Anna Zielinska-Glebocka, Subsidiarity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あairs, Vol.7:35, (1998).在辅助性原则看来,承认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或基层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但是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或基层政府的干预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而不能任意、过度地干预地方事务。上级政府的干预必须满足必要性条件,按照欧盟实践,欧盟在处理成员国事务时,必须满足在欧盟和成员国共享事务中,只有在成员国无法令人满意地实现采取的行动目标,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能够很好地完成目标,共同体才能采取行动。有学者详细概括欧盟干预的具体标准:第一,通过成员国的行动,提案的跨国性方面是否得到有效的管控;第二,缺乏共同体的行动,将与条约的要求相冲突或者严重损害成员国的利益;第三,相比于成员国的单独行动而言,联盟的行动因其规模或效果而产生明显的益处。〔53〕See Barbara Guastaferro, Coupling National Identity with Subsidiarity Concerns in National Parliaments’ Reasoned Opinions, 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 Vol.21:324, (2014).从这一概括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在成员国无法完成行动目标时,欧盟才能采取行动,而且行动能够产生较好的收益,这就是所谓上级干预必须满足充分性条件。上级干预必须满足充分性条件这一要求对我们处理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区域协同立法本身无法完成合法性依据的证成,只有通过中央立法机关的及时干预,也就是对于区域协同立法进行积极的肯定和支持,才能使区域协同立法摆脱合法性困境,为此全国人大需要尽快修改《立法法》,增加区域协同立法的相关内容,从而赋予区域协同立法以合法性地位。
由于我国在区域协同立法领域尚属空白,在区域合作推进过程中必须同步推进立法建设,明确区域合作的法律地位,健全与区域合作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由于《立法法》是调整我国立法制度的根本性法律,区域协同立法涉及地方立法权的横向协调与配合问题,依据法治国家的基本原理,由全国人大修改《立法法》 将是一种更好的解决方式。全国人大不妨模仿《立法法》 第81 条的规定,在《立法法》第四章地方性法规部分增加一条,涉及两个以上省级行政区或市级行政区的事项,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上述区域内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可以协同制定地方性法规。这样区域协同立法的合法性困境就会迎刃而解。还有学者认为,也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门授权,采用授权立法的形式赋予区域协同立法以合法性,笔者认为,根据《立法法》规定,所谓授权立法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先行制定行政法规的行为,行政法规主要职能是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而区域协同立法的立法主体主要是地方立法机关,如果要规范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还是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为好。但是由于全国人大需要统领全国范围的立法工作,要求其就区域协同立法事项专门修改《立法法》,仍具有一定难度。另外,区域协同立法自理论构想变成立法现实以来,我们就期望《立法法》予以规定,但一直没有得到实现。拉兹指出,缓慢的改革步伐与立法程序妨碍了法律修改,即使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法律的缺陷。〔54〕See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2.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强调,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里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和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是两种平行的手段,共同实现立法和改革相衔接的目的,我们不能一味强调改革于法有据,实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我们也要强调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就是为了满足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积极立法或者修改法律,以达到于法有据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因而,当区域协同立法面临着合法性困境,且地方无法自身完成合法性证成时,中央应该尽快启动干预措施,通过修改《立法法》的形式,赋予区域协同立法以合法性,以立法促进改革,引领改革,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三)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赋予区域协同立法以合法性地位
根据辅助性原则的要求,上级政府在进行干预过程中,还需要满足比例原则,即采取的行动措施或手段应与预期的目的相平衡,也就是在上级进行干预时,可以有多种手段进行选择时,必须选择能给成员国、下级政府或个人最大限度自由的一种行动或举措,这就是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在欧盟实践中,比例原则的目的在于限制共同体的行动,不能超出实现目标所必需的范围,比例原则在保护个人自由和成员国利益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55〕See Mădălina Cocoşatu, Principles of Subsidiarity and Proportionality at European Union Level, as Express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Acta Universitatis Danubius,Vol.8:32,(2012).如果说辅助性原则提供了共同体行动的必要性,那么比例原则可以看成为共同体行动提供了一种标准。将比例原则放到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困境的破解问题上来看,也就是需要中央立法机关进行积极干预,但是中央立法的干预具有多种途径,能够通过直接修改《立法法》赋予其合法性自然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但是未必符合比例原则,考虑到《立法法》刚刚修改完成,再次贸然修改,会给人以朝令夕改的感觉,有损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因而根据比例原则要求,采用最低成本的方式达致满足合法性要求的目的自然是最好的,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妨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赋予区域协同立法以合法性依据,这也是区域协同立法获得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之一。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和法律进行解释也是一项重要的立法活动,是所解释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是完善和发展立法的重要途径,可以在不改变立法原意的前提下,赋予法律条文新的含义,以适应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需要。就区域协同立法的解释而言,首先应该考虑宪法的规定。卡尔·拉伦茨指出,“和其他法律一样,宪法作为成文法也是一种语言创作,也需要解释,宪法中的语句也具有规范的特质,宪法的约束力也绝不小于其他法律,毋宁还更加强大。”〔56〕[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236 页。《宪法》第3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这一规定是地方立法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的重要宪法依据。作为地方立法发挥积极性作用的重要体现,区域协同立法也属于地方立法的范畴,通过区域内部不同人大之间进行适当的协作,共同制定地方性法规,以便适应区域一体化的需求,这是地方立法权行使过程中的自主性制度建构,是地方立法权发挥积极性主动性的重要体现,不仅没有违反宪法,而且充分贯彻了上述宪法原则,是应该鼓励的行为,只要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即可,而不能仅仅宪法没有规定就简单地进行否定。
对于《立法法》而言,《立法法》第72 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这里面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前提是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不抵触是地方立法需要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一般而言,地方立法都是根据宪法和已有的上位法来制定的,一切形式的立法,在内容上都不得与正在生效的上位法相抵触,这是实现法治的必要条件。〔57〕参见江国华:《立法:理想与变革》,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192-193 页。对于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宪法、立法法里面没有进行规定,也就是说中央立法对于区域内部各地方人大之间能否进行协同立法,既没有说不行,也没有明确的授权,那么享有立法权的行政区域之间进行协同立法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呢?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的解释,对于专属立法之外的事项,考虑到国家处于改革时期,中央立法不能一步到位的,地方可以先行立法,在总结实践经验后,再上升为中央立法。〔58〕参见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导读与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年版,第243 页。合法性审查主要是审查下位法与上位法是否抵触,所谓“抵触”,标准之一就是对于上位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与上位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相反的立法。〔59〕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 年版,第303 页。也就是说对于专属立法权之外的事项,即使中央立法没有规定,也是可以允许地方先行立法的,不能一概指责其与上位法相抵触,关键要看其立法目的是否与上位法立法目的相一致。“不相抵触”不应当被理解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没有作出某项规定,地方性法规便一概不能就此事作出规定的意思。否则地方立法就无从属与自主两重性可言,就不能解决不宜由中央立法解决或中央立法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60〕参见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283-284 页。对于区域协同立法而言,按照辅助性原则的要求,通过运用法律解释赋予其合法性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妨通过对《宪法》中两个积极性原则和《立法法》中不抵触原则进行解释,作为协同立法结果的法律文本只要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精神相抵触,同时又不属于中央专属立法权事项即可视为具有合法性。
四、结论
作为我国地方立法领域新概念的区域协同立法,由于现行《宪法》《立法法》缺乏相应的规定,导致区域协同立法时刻面临着合法性困境,这给立法实践带来了诸多困惑。在立法实践中,一些地方囿于中央立法缺乏明确的规定而处于徘徊和观望状态,使得现有区域协同立法活动大多停留在立法合作协议的签署,立法信息、立法项目、立法程序的沟通和交流上,真正的区域协同立法成果较少,中央国家机关对于区域协同立法是否具有合法性亦有不同意见,法学界对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和非法性争论相持不下。由于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依据不足,背离了权力限制的法治原则,容易导致地方立法权的滥用和地方保护主义再次强化。在探寻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困境的出路上,我们不妨借鉴辅助性原则理论。基于辅助性原则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尊重和肯定地方的首创精神,允许部分区域的协同立法试点探索活动,尽量淡化对区域协同立法的合法性质疑,重点关注协同立法的实践效果,在区域协同立法的运作模式及协同路径等方面进行试点探索,待积累一定的经验之后,再考虑争取形式合法性支持。当然,区域协同立法取得合法性依据,最终还需通过中央立法机关的积极干预,仅通过制定政策性文件及领导人的内部讲话是无法解决区域协同立法合法性问题的。中央应该尽快启动干预措施,通过修改《立法法》赋予区域协同立法以合法性,这是区域协同立法获得合法性依据的最根本途径。此外,在上级干预措施的选择上,也可以基于比例原则要求,采用法律解释的形式赋予区域协同立法以合法性,这样既可以节省立法资源,同时又维护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通过上述措施,我们期望区域协同立法早日摆脱合法性困境,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跨区域事务处理和区域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