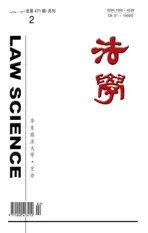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及限度
2021-12-07李夏旭
李夏旭
一、问题的缘起
在处理具体规则与诚信原则的适用关系时,通常的做法是具体规则优先适用,只有在没有具体规则时才能适用诚信原则。〔1〕参见王利明、杨立新等:《民法学》(第5 版),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22 页;梁慧星:《民法总论》(第5 版),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46 页。然而,现实中不乏不诚信一方滥用具体规则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例如,开发商明知自己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仍与购房者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房价上涨,开发商为获得商品房溢价,以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由主张合同违法无效。又如,宅基地使用权人明知宅基地禁止买卖仍与买受人订立宅基地买卖合同,之后房屋拆迁,出卖人为获得拆迁款,主张宅基地买卖合同违法无效。在这些案件中,现行法对涉案合同已经明确规定了无效的法律效果,依据“具体规则优先”的法律适用原则,法官应当优先适用具体规则认定合同无效,但合同一旦被宣告无效,似乎会产生有利于不诚信一方的结果。那么,在法有明文规定,但严格适用该规定将产生有违诚信原则的结果时,诚信原则应当如何适用呢?
针对这类“试图通过确认合同无效获益”的案件,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根据2019 年11 月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第32 条,法官既要“做到依法认定合同无效”,又要依据诚信原则对获益予以合理分配,使不诚信方无法因不诚信行为获益。〔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 年版,第260 页。这种做法表面上两全其美,理论上却难以行得通。具体而言,由于我国民法并未采纳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一旦债权合同被宣告无效,物权自始不发生变动,出卖人可基于物上请求权要求买受人返还原物。〔3〕同前注〔1〕,王利明、杨立新等书,第341 页;同前注〔1〕,梁慧星书,第170 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4 版),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320 页。在返还原物后,买受人虽然可以基于缔约过失责任要求出卖人赔偿损害,但缔约过失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信赖利益,尚不包括房屋溢价这类预期利益。〔4〕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481 页。据此,一旦合同被认定无效,不诚信一方获益的结果将难以改变。
理论界所给出的方案是,将一方主张合同违法无效的行为视为权利滥用,并据此禁止一方主张合同违法无效,最终达致“合同无效按有效处理”之效果。〔5〕参见夏昊晗:《诚信原则在“借违法无效之名毁约”案型中的适用》,载《法学》2019 年第6 期,第141 页;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 年第5 期,第66 页。此种做法本质上适用的是诚信原则的权利行使审查功能,有待商榷之处有三。其一,无效的法律行为属于当然无效,不需要当事人主张无效。合同无效之效果由法律规定产生,法官判决某一合同无效仅具有宣告效力。〔6〕同前注〔3〕,韩世远书,第213 页;同前注〔1〕,梁慧星书,第202 页。因此,即便禁止不诚信一方主张合同无效,合同也不会因此有效。其二,合同因违法而无效的事由属于事实抗辩,对于事实抗辩,无论当事人是否主张,法院都应在诉讼中依职权考虑。〔7〕抗辩可分为事实抗辩与权利抗辩。事实抗辩无需当事人主张,法院应依职权查明。参见尹腊梅:《民事抗辩权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年版,第36 页。其三,“合同无效按有效处理”存在逻辑跳跃,一旦法院依职权查明涉案合同确属无效,如何借助诚信原则矫正合同的无效性有待进一步说明。
综上,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均存在理论瑕疵,而且其所探讨的案型多限于合同违法无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领域。在其他领域,也会发生不诚信一方借助现行法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例如,消费者“知假买假”,援引惩罚性赔偿的相关规定,要求销售者“买一赔三”或“买一赔十”。现有理论尚无法对这类案件提供妥当的解决方案。不过,无论是哪一个领域,此类案件均存在共通之处,即现行法对相关事项已经作出明确规定,但严格适用相关规范将产生有利于不诚信一方的结果,由此产生了诚信原则在具体规则中的适用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首先回答诚信原则在法有明文规定时发挥的是何种规范功能。对此,我国有学者主张在适用既有规定将与诚信原则相抵触,并于个案中产生严重不公正结果时,诚信原则具有法律修正功能,法官可援引诚信原则修正现行法的不当规定。〔8〕参见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载《法学研究》1994 年第2 期,第27 页;雷磊:《论依据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律修正》,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 年第6 期,第11 页;韩世远:《民法基本原则:体系结构、规范功能与应用发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 年第6 期,第10 页。诸多立法建议稿也提到了该功能,如梁慧星教授主持的合同法建议稿第6 条第3 款规定:“法院于裁判案件时,如对于该待决案件法律未有规定,或者虽有规定而适用该规定所得结果显然违反社会正义时,可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9〕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第2 册),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 年版,第136-137 页。在原《民法总则》的制定过程中,也有学者建议规定:“适用具体规定将导致结果极不适当或极不公正时,可以直接适用基本原则。”〔10〕《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7 年版,第202 页。可见,在法有明文规定,但严格适用该规定将导致个案不公时,适用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似乎更为妥当。不过,现有研究在论及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时多是一笔带过,此修正功能的若干关键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第一,从名称上看,现有理论采“法律修正”或“法律限制”两种表述。然而,两者的涵义并不一致,法律修正意味着对规范作一般性的修改,而法律限制则仅是限制相关规范在个案中的适用,并未改变规范内容。那么,法律修正功能的实质是什么?当既有规定与诚信原则相抵触时,诚信原则究竟是限制既有规定的适用,还是直接对既有规定的内容进行修改?如果是对法律作一般性修正,则可能与法官受法律约束原则相抵触。为避免僭越立法权,法官在进行法律修正时应当受到怎样的限制?
第二,现有理论认为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前提为“适用具体规定将导致结果极不适当或极不公正”,那么,衡量结果公正与否的尺度为何,是否适用规则产生了有利于不诚信一方的结果就足以说明结果极不公正?除法官的法感外,是否存在一定的理性标准?如果法官基于自身的正义观认为某一结果是极不公正的,其是否有权推翻立法者的价值决定?
第三,在法学方法论中,除法律修正功能外,目的性限缩也可以限制某一具体规范的适用范围。两相比较,目的性限缩已有较为深厚的理论根基,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11〕参见于程远:《民法上目的性限缩的正当性基础与边界》,载《法学》2019 年第8 期,第30 页;陈兴良:《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的教义学分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6 期,第12 页。也有法院采取目的性限缩的方法矫正严格适用规则所导致的个案不公正结果。〔12〕例如,开发商为取得房屋溢价,以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由,主动诉请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在这类案件中,开发商虽然违反了诚信原则,但有的法院并未诉诸诚信原则,而是通过目的性限缩的方式矫正个案不公正的结果,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2 条的目的在于保护购房者权益,据此排除了该条在案件中的适用。参见“西安闻天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陈江玫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以下简称“陈江玫案”),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8)陕0104 民初2071 号民事裁定书。在此背景下,如果目的性限缩本身就可以达致与法律修正功能相同的效果,则没有必要再另行确认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因为法律修正功能容易导致诚信原则被滥用,损及法律安定性,这也是立法者不采纳相关立法建议的主要理由。那么,目的性限缩可否取代法律修正功能,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二、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的理论基础及适用前提
(一)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的理论基础
法拥有自身内蕴的价值即法的安定性,但法的安定性并非是唯一重要的价值,法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应当是正义。在极端历史时期,当实在法与正义之间的矛盾达到难以容忍的程度时,法官可以通过宣告法律非正义解除法律的约束。〔13〕参见雷磊编:《拉德布鲁赫公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24 页。但在正常的民主法治国家,法官并无此种对立法的抵抗权,即便适用法律会产生个别非正义的结果,法官仍应在现行法的框架内予以矫正。〔14〕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411 页。在法典具备详尽规则时,《民法典》依然保留了基本原则,正是为正义进入法律提供通道,使法官得以在现行法框架内化解正义与法律的潜在矛盾。不过,《民法典》第10 条并未指明当既有规则与诚信原则相冲突时,法官应当如何行事。根据《民法典》第7 条的文义,我们也无法获知诚信原则在具体规则中应当如何展开。这一制度空白亟待学界提供理论供给。从比较法看,德国民法面临与我国法相同的问题,《德国民法典》同样没有规定方法论规范,没有明确司法者应当如何解决具体规则与诚信原则的冲突。而且在德国司法实践中,不诚信一方滥用既定法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为妥善解决具体规则与诚信原则的冲突,德国法学界在解释论上发展出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在此有必要作进一步介绍。
《德国民法典》第242 条的文义与我国《民法典》第7 条类似,均是强调民事主体须“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德国法学界根据该条文义确立了诚信原则的“具体化”功能,即依据诚信原则将债务关系的内容具体化,以此确保债务关系的双方“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这也是诚信原则最初的功能。〔15〕Vgl. MünKomm/Roth/Schubert, 2012, §242 Rn. 83.然而,德国法学界对诚信原则的解释并未局限于字面含义,而是额外赋予“公平正义”的内涵,使之成为法官进行法律续造的依据。〔16〕Vgl. F. S. Bosch, Das Problem der Rechtsprognose, 1976, S. 573.其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欠缺法律规定时,法官援引诚信原则创设具体规定;另一种是在法律规定与诚信原则相抵触时,法官援引诚信原则进行法律修正。〔17〕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 §242 Rn. 51.
之所以对诚信原则作此种广义理解,是因为根据禁止拒绝裁判原则,法官有义务对法律漏洞进行填补,但《德国民法典》并未规定漏洞填补规则,法官在进行法律续造时欠缺法律依据。鉴于此,德国司法和理论亟需作为法律续造依据的明确规范,这一规范不能过分具体,因为法官在进行法律续造时不能仅仅考虑规范所提供的单一价值,除规范之外的其他价值也应当被纳入考量,唯有如此,法官在填补法律漏洞时所确立的规则才能真正满足公平正义的要求。而诚信原则由于内容模糊需要价值的填充,这种开放性使其能够成为吸纳多元价值的据点,特别适合作为法律续造的依据。〔18〕Vgl. MünKomm/Roth/Schubert, 2012,§242 Rn. 3.诚信原则为法官提供了一个灵活的工具,法官可以借此考虑事实和法律情况的变化以及社会主流价值观作出裁判。Vgl. Looschelders/Roth, Juristische Methodik im Prozeß der Rechtsanwendung, 1998, S. 198.因而,德国司法界和学界选择诚信原则作为法律续造条款。与德国民法相比,我国《民法典》虽然同样没有确立法律续造条款,但在第一章规定了更为多元的基本原则,这无疑为确立法律续造条款提供了更多选择。无论是何基本原则,一旦被赋予法律续造功能,其字面含义就不应再受到过分重视,而应当被理解为更为抽象的公平正义。只有这样,基本原则才能脱离单一价值维度成为多元价值的容器,才真正有资格作为法律续造的依据。
诚信原则的文义和公平正义共同构成该原则的两大支柱,其中,公平正义奠定了法律修正功能的理论基础,〔19〕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13.此点对准确把握法律修正功能意义重大。在法官依据诚信原则进行法律修正时,具体规则是否符合诚实信用的要求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应当是适用具体规则所产生的结果是否公正。至于结果公正与否,不能将诚实信用作为唯一的考量因素,还应将已经存在的立法者价值决定考虑在内,并通过利益权衡作出判断。须着重说明的是,当适用具体规则在个案中产生不公正结果时可能存在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法律本身就不公正;另一种原因是法律本身是公正的,只不过个别规范的适用范围过宽,没有对某些特殊案件作区别对待,由此在这些特殊案件中产生了不妥当的结果。这也导致德国法学界对法律修正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法律修正适用于法律一般性不公正之情形,在此情形,法官可以通过修改法律使相关规范“符合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公正标准”。〔20〕Vgl. J. Schmidt, Präzisierung des §242 BGB - Eine Daueraufgabe?, in: Rechtsdogmatik und praktische Vernunft, 1990, S. 231.然而,此种观点违反了分权原则,因为审查现行法是否符合社会公正标准,以及在出现偏差的情况下根据诚信原则进行一般性修正,是立法者的任务,而非法官的责任。〔21〕Vgl. Looschelders/Roth, Grundrechte und Vertragsrecht: Die verfassungskonforme Reduktion des 5 565 Abs 1 S 2 BGB, JZ 1995, 1038, 1043.假使法官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只能通过相关程序提交立法部门审议修改。
因此,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的目的不是要在成文法之外建立第二套更有道德感的秩序。〔22〕Vgl. Basler Kommentar/Honsell, 2018, Art. 2 Rn. 28.相反,考虑到法官受法律约束原则,法官在进行法律修正时,应当前提性地认定现行法是公正的,只不过其中某些规范的适用范围过宽,没有对某些特殊案件作区别对待,由此在个案中产生了不公正结果。〔23〕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336.法律修正的实质正是通过为这些偏离规范“正常情况”的特殊案件创设但书,使相关规范在特殊案件中不予适用,以此矫正严格适用具体规则所产生的个案不公正结果。〔24〕Vgl.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 Allgemeiner Teil, 14. Aufl., 1987, S. 129.据此,法律修正的实质并非是将法律修改成(在法官看来)公平正义的,而仅是限制相关规范在特殊案件中的适用。所以有瑞士学者认为,“法律修正”用语不准确,更准确的用语应该是“法律限制”,个中理由在于“规范并没有被改正,而只是确定了某规范不应被适用到特定案件中”。〔25〕[瑞]贝蒂娜·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瑞士民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纪海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98 页。韩世远教授也强调法律修正功能并没有改变具体法规则的内容,而只是使具体法规则在个案中不予适用。〔26〕同前注〔8〕,韩世远文,第10 页。实际上,法律修正和法律限制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当适用规范仅在个案中产生不公正结果时,援引诚信原则限制具体规则的适用即可,此时只能称为法律限制(法律突破),尚不构成法律修正;但如果相同问题多次出现,个案累积到一定程度,证明此问题具有典型性,法官就可以且有必要从案例群中归纳出一条限制性规范,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修正。〔27〕Vgl. ZK-Zürcher Kommentar/Baumann, 1998, Art. 2-A Rn. 21.
在判断某一案件是否偏离规范的“正常情况”时,适用既有规范在个案中所产生的结果是否公正成为最直观的判断标准。然而,由于法官正义观的不同,势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评价。这一方面会导致诚信原则被滥用,损及法律的安定性;另一方面,法官基于自己的正义观推翻立法者的价值决定会违反分权原则,不具备正当性。为保证法律修正不会僭越立法权,法官在评价严格适用具体规则所导致的结果是否公正时,不能仅凭自己的法感,而须从现行法秩序中提取出评价要素对诚信原则进行价值填充,以立法者的视角审视结果是否公正。〔28〕Vgl. MünKomm/Roth/Schubert, 2012,§242 Rn. 122.只有这样,法律修正才不会脱离现行法的框架,法官受法律约束原则才能得到保障。
此外,在德国民法理论中,相较于法律补充功能,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发展较晚,但在近代已经变得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德国民法典》已经老化,而立法机关又不愿意对其作出反应。〔29〕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204.我国《民法典》新近颁布,并不存在过于老化的问题,那么,法律修正功能对新的法律是否重要呢?德国债法现代化的经验表明,即使是较新的法律,也会出现立法者没有考虑到的情况,仍有必要诉诸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予以解决。〔30〕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338.而且从立法技术来说,立法机关在起草法律规范时必须以典型案例为主要方向,非典型的案例类型即使是已知的,也可以不考虑。这使得规则或多或少地具有一般性,如果原封不动地适用规则,难免会产生不当的结果。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作为矫正这种不当结果的手段发挥重要作用。〔31〕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399 页。尤其在我国《民法典》第10 条没有承认法律漏洞,更未指明在既定法与诚信原则相冲突时法官应当如何裁判的背景下,探讨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更显必要。
(二)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适用于填补隐藏法律漏洞
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适用的特殊之处在于法律中并不缺少可以适用的规则。相反,对系争案件存在可以适用的规则,只不过该规则与诚信原则相抵触,需要对规则的适用范围加以限制。德国法学界最初并未将此种法律续造视为漏洞填补,因为在此并无法律规则的缺失,不存在真正的法律漏洞。〔32〕Vgl. Zittelmann, Lücken im Recht, Rektoratsrede aus d. J. 102, 1903, S. 20.然而,法律漏洞并非仅指法律未为任何规定,规则的适用范围过宽也是法律漏洞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法律规定得太多意味着应有的限制规定之不存在,也是一种“不及”。〔33〕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293 页。有鉴于此,拉伦茨提出“隐藏法律漏洞”这一概念,当法律对某类事件虽有规定,但与法律目的相比该规定的适用范围过宽,法律应作限制而未限制时,即存在隐藏法律漏洞。〔34〕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254 页。就此种漏洞可通过添加合理且必要的限制予以填补。〔35〕参见[奥]恩斯特·A.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166 页。那么,依据诚信原则为某一规范创设限制性规定可否被视为填补隐藏法律漏洞呢?
回答这一问题的难点在于,在判断某一规范是否欠缺例外规定时,通常依据的是规范的主观目的,尚不清楚诚信原则这类客观目的可否作为隐藏法律漏洞的认定和填补依据。对此,卡纳里斯指出,应当在法律的整体关系和整个法秩序中查明单个规定的目的,而不能孤立地探究法律目的。〔36〕Vgl. Canaris, Die Feststellung von Lücken im Gesetz, 2. Aufl., 1983, S. 39.依此要求,在探究单个规范的法律目的时,应考虑的不仅包括立法者在制定该规范时的主观目的,对已经显现在法律之中的诚信原则亦须加以考量。只有在对诚信原则与规范的主观目的进行权衡后,才能最终确定单个规范的法律目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25 条规定,欠缺法定形式要件的法律行为无效。实践中发生了一方为获益而借助该条毁约的情形。在此情形,如果严格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25 条将使违反诚信的行为反而受到法律的奖励时,则应当认定诚信原则较该条的规范目的更为重要,该条在此便存在隐藏法律漏洞,可以依据诚信原则创设例外规定予以填补。〔37〕同前注〔34〕,卡尔·拉伦茨书,第272 页。瑞士民法也持类似立场,其中发挥法律修正功能的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瑞士民法典》第2 条第2 款)。〔38〕在瑞士民法中,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瑞士民法典》第2 条第2 款)具有法律修正功能,诚信原则(《瑞士民法典》第2 条第1 款)具有法律解释、法律补充功能。同前注〔25〕,贝蒂娜·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书,第97 页。按照瑞士传统学说,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可以通过法律修正的方式填补“隐藏法律漏洞”。〔39〕同前注〔35〕,恩斯特·A.克莱默书,第200 页。据此,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看,依据诚信原则限制某一规范的适用本质上是在填补隐藏法律漏洞。
不过,就隐藏法律漏洞的填补而言,目的性限缩是最为重要的手段,在此出现了目的性限缩与法律修正的方法论关系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常将目的性限缩与法律修正功能混淆。例如,在由同一开发商为获得商品房溢价而引发的多个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中,虽然法院最终都通过限制规则适用的方式确认合同有效,但在限制规则适用的方法选择上,有的法院用的是目的性限缩,认为《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2 条的目的在于保护购房者权益,据此限制了该条的适用;〔40〕同前注〔12〕。有的法院则认为开发商的行为有违诚信原则,而且援引诚信原则限制规则的适用。〔41〕参见“西安闻天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李琛茹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 民终8145 号民事判决书。
目的性限缩是由拉伦茨首先提出并广泛应用的一个概念,它是指法条的文义虽然清楚,但是与法律目的比较,该文义过于宽泛,因此将该文义限缩在与法律目的相一致的适用领域内。〔42〕同前注〔34〕,卡尔·拉伦茨书,第267 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拉伦茨的理论框架中,可以作为目的性限缩依据的,不仅包括法条自身的主观目的,诸如诚信原则这类客观目的也可以成为目的性限缩的依据。〔43〕同上注,第268 页。依此观点,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与目的性限缩似乎是一回事,因为两者本质上都是基于法律目的对规则作违背文义的限缩,从而得出一条限制性规范。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基于客观目的,后者多基于主观目的。但此点细微差异构成方法论上的重大不同,原因在于,依据主观目的所作的目的性限缩没有偏离法律规范的意义和目的,仍在立法者原意范围内;而依据诚信原则所作的目的性限缩则偏离了立法者原意,构成对规范主观目的的修正,法官若要作此种修正,须进行利益权衡。〔44〕同前注〔14〕,伯恩·魏德士书,第410 页。只有在个案中适用诚信原则比规范的主观目的更重要时,才可以适用诚信原则限制规则的适用。〔45〕Vgl. Larenz/Canaris,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3. Aufl., 1995, S. 211.
鉴于此,有瑞士学者指出,在真正意义上的目的性限缩中,法条是根据它自己的目的被限制的;但在用客观目的进行目的性限缩的情形,则是根据另一条文的目的进行限缩,不能算作真正的目的性限缩。〔46〕Vgl. Anke Schmidt, Richterliche Rechtsfortbildung in Deutschland und der Schweiz, 2017, S. 66.可见,目的性限缩中的“目的”应仅限于法条自身的主观目的,至于诉诸诚信原则而对特定具体规则不予适用的做法是否应当被允许,则属于法律修正功能所讨论的范畴。除上述不同之外,目的性限缩更注重规范目的,其所作的限制具有一般性;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则更注重个案的具体情况,只有在个案产生严重不公的结果时,才可以对规范加以限制,更具特殊性。〔47〕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345.为维护方法论原理内部的和谐统一,最好将目的性限缩回归本位,仅限于主观目的;一旦依据诚信原则进行所谓的目的性限缩,则构成对主观目的的修正,属于法律修正功能的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当相关规定具有多个规范目的,法官仅依据其中一个进行目的性限缩时,也难以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目的性限缩,仍属于法律修正的范畴。例如,在“陈江玫案”中,法官为惩罚背信的开发商,保护守信的购房者,将《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2 条的主观目的解释为“维护购房者权益”,并据此进行目的性限缩,将开发商损害购房者权益的情形排除在该条适用范围之外。〔48〕同前注〔12〕。但该条还有第二个立法目的,即维护商品房销售市场秩序。〔49〕由《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2 条的文义,我们无法直接获知其规范目的,但制定该解释的主要法律依据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后者在第1 条的总领条款中指明了立法目的,即“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地产的管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据此,《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2 条的立法目的不仅包括“维护购房者权益”,还包括“维护市场秩序”。如果依据第二个立法目的,目的性限缩将难以实现,因为只有依法将欠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合同认定为无效,才有利于维护商品房市场销售秩序。在此,法官实际上依据诚信原则剔除了第二个立法目的,构成对该条主观目的的修正。此种借“目的性限缩”之名行“法律修正”之实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逃避论证义务,由于目的性限缩坚守了立法者本意,法官负担较少的论证义务;而法律修正偏离了立法者本意,法官须承担较重的论证义务。
在适用顺序上,由于目的性限缩坚守了立法者原意,更加接近法律,因此具有优先适用性。对此,《施陶丁格评注》指出:“在限制规则适用范围时,首先要检验目的性限缩能否予以限制;如果可以,则不必也不应诉诸诚信原则。”〔50〕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445.瑞士学者也强调:“对于像禁止权利滥用这样的规定,尽管有法律授权,但法院在适用时仍应十分谨慎,只有通过法律解释(包括目的性限缩)无法避免权利滥用时,才能适用该原则。”〔51〕Vgl. Mader, 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 nemini licet, 1981, S. 123 f.可见,在限制规则适用方面,诚信原则仅具有辅助作用。此点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被忽视。例如,在“何丽红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支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52〕参见“何丽红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支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 年第8 期,第40-48 页。中,保险人在明知投保人隐瞒事实的情况下仍与其签订保险合同,之后又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保险合同。在该案中,法官完全可以通过目的性限缩的方式矫正个案的不公正结果,无需诉诸诚信原则。原因在于,2002 年《保险法》第17 条的主观目的是保护保险公司,使其免受由于投保人隐瞒事实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基于这一目的,该条不应当适用于保险人明知隐瞒事实的情况,因此可作目的性限缩,将“保险人明知投保人隐瞒事实”这一情形排除在外。但是该案法官并未采取目的性限缩,而是直接运用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以保险公司违反诚信原则为由限制了该条的适用,其适用顺序有误。
综上,目的性限缩虽然可以填补部分隐藏法律漏洞,但由于其依据的是规范的主观目的,不包括客观目的,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而法律修正功能在目的性限缩力所不逮之处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法律修正功能有着目的性限缩无法取代的地位,在我国法中确立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确属必要。然而,虽然理论界在相关立法建议稿中多次提到了法律修正功能,但最终并未获得立法者肯认,立法者的主要顾虑在于诚信原则会被滥用,立法者原意会被篡改。但法官借“目的性限缩”之名行“法律修正”之实的现象表明,只有确认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并辅以正确的适用方法,才能真正避免立法者原意被篡改。在此,立法者的顾虑反而成为确立法律修正功能的佐证。
(三)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规制的是制度滥用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因为一方滥用法律制度引发法律修正的需要。例如,消费者“知假买假”,并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48 条要求销售者予以十倍赔偿。〔5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第23 号指导性案例(法〔2014〕18 号)。又如,开发商在房价上涨之时,以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由,主动援引《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2 条诉请法院确认合同违法无效。〔54〕同前注〔12〕;同前注〔41〕。不诚信一方表面上滥用的是权利(如损害赔偿请求权、诉权),但本质上滥用的是法律制度。如果严格适用既定法,将可能与诚信原则发生冲突,产生有利于不诚信一方的结果。然而,在我国教义学语境下,权利滥用的对象仅指“权利”,而不包括“法律制度”。〔55〕典型表述有:“滥用权利,应当具备如下条件:首先,要有权利的存在。如果根本就没有权利,也就谈不上‘滥用’。”同前注〔1〕,王利明、杨立新等书,第152 页。这一理解似乎略显狭隘,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权利滥用不仅包括“个别权利滥用”,还包括“制度滥用”。〔56〕同前注〔4〕,王泽鉴书,第556 页。德国民法亦作此种区分。〔57〕Vgl. BGHZ 48, 396, 398; Palandt Kommentar/Grüneberg, 2019, §242 Rn. 40.
制度滥用与个别权利滥用的差异在于:在制度滥用中,规则的适用产生了难以容忍的不公正结果。要想矫正此种结果,须依诚信原则限制规则的适用,诚信原则在此发挥的是法律修正功能;而在个别权利滥用中,债权人的权利行使行为导致了双方间的利益失衡,于此须依诚信原则限制权利的行使行为,诚信原则在此发挥的是权利行使审查功能。〔58〕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217.比称谓更重要的是两者思维方式的不同,个别权利滥用仅需要考量双方间的利益状态,即一方行使权利所获利益与给另一方带来的损失是否相称;而在制度滥用中,双方间的利益状态并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对相关规范目的和法律确定性的考量。〔59〕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336.例如,多数劳动法强制性规定之法律目的在于保护雇员,如果雇员事先签署了无效的劳动协议,之后又宣称协议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此种情形不构成制度滥用。否则,雇员将无法受到强制性条款的保护。〔60〕Vgl. Basler Kommentar/Honsell, 2018, Art. 2 Rn. 44.
须着重说明的是,在这一例证中,从规范的主观目的来看,规范在该案中不应受到限制,不构成制度滥用。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果规范的适用因违反诚信原则而产生“绝对不公、严重影响公正良知的结果”,仍会构成制度滥用。〔61〕同前注〔35〕,恩斯特·A.克莱默书,第199 页。换言之,规范的主观目的是判定制度滥用的一般标准,但如果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而禁止性规定的主观目的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况时,依然有可能构成制度滥用。〔62〕Vgl. Staudinger/Sack/Seibl, 2017, §134 Rn. 188.依据规范主观目的所作的思考是目的性限缩的思维过程,而对个案非典型情形的考量则是法律修正功能的思维过程。因此,从理论应然的角度说,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应当具有目的性限缩和法律修正的双重功能,将法律修正功能归入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似乎更为妥当。
不过,由于立法体例的不同,各国相关理论发展与其存在差异。在瑞士民法中,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最初具有目的性限缩和法律修正的双重功能,但随着理论的发展,目的性限缩逐步被《瑞士民法典》第1 条第2 款所吸收,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最终仅具法律修正功能。〔63〕对于适用规则违反其规范目的时法官应当如何裁判的问题,《瑞士民法典》第1 条第2 款的德语版本并没有明确说明。但由《瑞士民法典》第1 条第2 款的法文和意大利文版本可知,不仅在缺少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而且在法律规定(目的性)不合适的情况下,都可以适用《瑞士民法典》第1 条第2 款。据此,《瑞士民法典》第1 条第2 款成为目的性限缩的规范依据。同前注〔35〕,恩斯特·A.克莱默书,第166 页。在《瑞士民法典》第1 条第2 款成为目的性限缩的规范依据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功能部分失效。同前注〔25〕,贝蒂娜·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书,第106 页。德国民法并未将法律修正功能归入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德国民法典》第226 条),而是将其归入诚信原则(《德国民法典》第242 条)。之所以作此种安排,主要是由于《德国民法典》第226 条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根据该条,只有行为人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才构成权利滥用。这使得很多权利滥用情形无法受其规制,《德国民法典》第226 条逐渐成为“死法”。〔64〕Vgl. Basler Kommentar/Honsell, 2018, Art. 2 Rn. 36.面对此种情况,德国司法多依据诚信原则对权利滥用(包括制度滥用)予以规制。据此,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多数功能被诚信原则所吸收,法律修正功能亦然。
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后,许多学者主张采用德国法律评注的方法发展中国民法解释论。那么,在撰写民法典评注时,我国民法教义学应当将法律修正功能置于《民法典》第7 条还是第132 条之下?比较来看,我国《民法典》第132 条并未附加“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这一限制条件,因此该条适用范围较《德国民法典》第226 条更宽。但将我国《民法典》第132 条的适用范围拓展至制度滥用仍存在体系瓶颈,原因在于,不同于《瑞士民法典》在“序言”(类似总则的“基本规定”)中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我国《民法典》是在总则编“民事权利”一章予以规定,这使得第132 条具有体系上的局限性,仅能规制权利滥用,而无法涵盖制度滥用。从这一角度说,我国《民法典》第132 条同样存在适用范围狭窄的问题。因此,本文建议仿效德国法教义学构造,将我国《民法典》第132 条所无法涵盖的制度滥用纳入《民法典》第7 条,进而将法律修正功能纳入第7 条的教义学框架内。
法律修正功能与制度滥用之间的紧密关系常为我国学界所忽视。例如,有学者在探讨开发商为获益主张合同无效这类案件时,参照瑞士法上的经验,认为应将开发商的行为视为权利滥用,并依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禁止开发商主张合同无效,最终达致“无效按有效处理”之效果。〔65〕同前注〔5〕,夏昊晗文,第152 页。但其忽视了瑞士民法的特殊教义学构造。的确,瑞士司法实践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常诉诸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予以解决,但其适用的是该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解决的是制度滥用问题。例如,有瑞士学者指出,限制一方主张合同无效并不能改变合同无效之结果。就法律方法而言,合同无效之结果是通过禁止制度滥用原则得以矫正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此发挥的是法律修正功能。〔66〕Vgl. Basler Kommentar/Honsell, 2018, Art. 2 Rn. 46.可见,禁止不诚信一方主张合同无效只能算作一种表面理由,其背后运用的仍是法律修正功能。
三、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方法
当适用具体规则与诚信原则相抵触时,法官须先检验可否通过目的性限缩实现合理且必要的限制。如果可以,则适用目的性限缩即可,没有必要诉诸诚信原则。只有经目的性限缩仍无法限制规则适用时,才可以考虑诉诸诚信原则进行法律修正。但这只是适用法律修正功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想适用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必须进行利益权衡。
(一)适用法律修正功能须进行利益权衡
需要权衡的是,在个案中适用诚信原则(个案公正)所带来的利益是否超过了严格适用规则(主观目的)所带来的利益。〔67〕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345.只有前者明显超过了后者、存在利益失衡时,才可以依据诚信原则为规则创设限制性规定,以此进行法律修正。须说明的是,并非每种利益失衡都会对法律适用产生限制性影响,只有个案不公达到“明显”难以容忍的程度时才可以进行法律修正。“明显”一词意味着如果法官对某一结果是否构成制度滥用存在疑问,则应推定为不构成制度滥用,此时不得进行法律修正。〔68〕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221.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份判决中也强调:“只有当适用规则会造成明显不公正结果时,法官才可以根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修正法律。”Vgl. BGE 143 III 279 E. 3.1.换言之,在进行法律修正时,法官应持保守且审慎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具有优先性,除非有特别重要的理由,原则上不得推翻立法者的价值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修正功能中的利益权衡程序不同于权利行使审查功能,就后者而言,在判断一方合同权利的行使是否构成权利滥用时,利益权衡更侧重于双方之间的利益状态,审视一方行使权利带来的利益与另一方所受损失是否相称。但在法律修正功能中,利益权衡的侧重点在于规范目的,双方之间的利益状态不起决定作用。例如,雇主与雇员签订了无效的非法雇佣合同,且雇主已经支付了大量的预付款。当雇佣合同被法院宣告无效时,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17 条第2 款之规定,由于雇主对合同违反禁止性规定同样有过错,雇主不得请求返还预付款。德国法院最初认为,考虑到预付款数额巨大这一情形,如果严格适用《德国民法典》第817 条第2 款,将会在双方之间产生显著的利益失衡,违反诚信原则,因此,应当依据诚信原则限制第817 条第2 款的适用。〔69〕Vgl. BGHZ 111, 308, 312 f.但德国新近判例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17 条第2 款的规范目的在于一般性地预防违反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如果允许雇主请求返还预付款,不仅无法预防雇主再次订立非法雇佣合同,也不能对其他社会主体违反禁止性规定之行为起到预防作用,不利于《德国民法典》第817 条第2 款规范目的之实现。因此,不应依据诚信原则限制该条款的适用。〔70〕Vgl. BGH NJW 2006, 45, 46; NJW 2008, 1942; NJW-RR 2009, 345 f.; NJW 2009, 984.可见,考虑到规范目的,即便严格适用规则会导致双方之间的利益失衡,也难以构成“明显不公正的结果”,不足以适用诚信原则进行法律修正。
那么,在个案中实现诚信原则的重要性何时会明显超过规范的主观目的呢?实际上,诚信原则作为一个有待价值填充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身不能为利益权衡提供有用的标准。〔71〕Vgl. Brox/Walker, Allgemeines Schuldrecht, 36. Aufl., 2012, §7 Rn. 3.我们也不能过分重视诚信原则的文义,因为诚信原则的字面含义充其量只能表示一种价值倾向性,并不能削弱在个案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立法价值决定,〔72〕Vgl. MünKomm/Roth/Schubert, 2012,§242 Rn. 16.其作用仅是“使个案的特殊情况得到考虑,即提示法官考虑个案正义”。〔73〕同前注〔36〕,Canaris 书,第20 页。要想让诚信原则在利益权衡中发挥实质作用,就需要依据现行法对诚信原则进行价值填充,也即在诚信原则的框架内,参考成文法规范,将由此产生的立法价值决定纳入权衡过程。〔74〕Vgl. MünKomm/Roth/Schubert, 2012,§242 Rn. 122.从这一意义上说,诚信原则作为一个“用于吸收多种原理的据点”,在利益权衡中发挥重要作用。〔75〕同前注〔31〕,山本敬三书,第399 页。默兹形象地将其称为概括条款的“通道功能”。〔76〕同前注〔35〕,恩斯特·A.克莱默书,第200 页。
例如,针对一方为获益而主张合同存在形式瑕疵之情形,如果一方仅是为获益而主张合同无效,尚不足以说明案件中存在显著的利益失衡。因为一般而言,人们多是为了自身利益主张合同无效,都在一定程度上滥用了形式要件规则,倘若人们不愿意一般性地容忍滥用形式要件规则的行为,那么必须完全放弃形式要件规则。〔77〕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334 页。形式要件规则的目的在于维护一种绝对的形式秩序,仅仅双方之间存在利益失衡,尚不足以构成偏离形式要件规则的理由。但是,如果一方不仅为获益,而且在此之前就形式要件进行了恶意欺诈,如开发商伪造预售许可证或欺骗购房者其已经取得预售许可证,则此时认定合同无效会产生有利于欺诈一方的结果。而从现行法“欺诈可撤销”这一规定中,可以抽取出立法者对欺诈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这一评价要素可以被纳入诚信原则的框架内,使诚信原则在与规范目的的利益权衡中占据更大权重。在此情形,才可以依据诚信原则对形式要件规则加以限制。〔78〕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338;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4. Aufl., 1992, S. 150.
由上述案例分析可知,如果适用规则仅产生有利于不诚信一方的结果,尚不足以构成难以容忍的不公正结果。结果是否难以容忍,应从立法者的视角审视。在此,诚信原则更多是作为一个“据点”发挥作用,用来吸收现行法中具体可证明的评价标准。法官在对诚信原则进行价值填充时,依据的应当是现行法规范所包含的评价,而非法官自己的评价。因此,适用诚信原则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适用法律规则及其所包含的评价的问题。〔79〕同前注〔46〕,Anke Schmidt 书,第67 页。从这一意义上说,依据诚信原则所进行的法律修正属于“法律内的法律续造”,并未僭越立法权。〔80〕“法律内的法律续造”与“法律外的法律续造”相对,前者指的是依据现行法识别、填补法律漏洞,后者则指依据法外因素填补法政策漏洞。同前注〔34〕,卡尔·拉伦茨书,第252 页。此点不同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在法律对某类事项完全没有规定时,基于禁止拒绝裁判原则,法官造法的空间更加广泛,可以将法政策因素纳入考量,进行“法律外的法律续造”。〔81〕同前注〔14〕,伯恩·魏德士书,第381 页。但在法有明文规定时,基于法官受法律约束原则,法官原则上不得依据法外因素修改现行法,基于法政策考量所作的修正只能由立法者进行。
(二)从“法律限制”到“法律修正”
法官在依据诚信原则进行法律修正时,应将上述利益权衡过程充分展现出来,而不能仅仅套用“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这一空洞的公式作出裁判。否则,诚信原则只能算作一种“外在的表象”或“虚假的理由”。〔82〕Vgl. MünKomm/Roth/Schubert, 2012,§242 Rn. 5.这一问题在德国法中屡见不鲜,由于《德国民法典》没有承认法律漏洞,这使得法官在进行法律续造时,往往直接依据诚信原则作出裁判,而不愿承认其在进行法律续造,《德国民法典》第242 条成为法官逃避论证义务的虚假理由。〔83〕同前注〔46〕,Anke Schmidt 书,第88 页。我国《民法典》第10 条并未承认法律漏洞,存在与德国法相同的问题。为避免法官借法律适用之名进行法律续造,法官在适用诚信原则进行法律修正时,应当指明其依据的是从哪一成文法中提取的评价要素。如果仅是提及“诚实信用”,则相当于法官自己进行评价,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完全自由的法律续造。
此外,诚信原则是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其本身并不能直接适用,但可以转化为法律规则适用。〔84〕Vgl. Larenz, Richtiges Recht, Grundzüge einer Rechtsethik, 1979, S. 23.依此要求,法官在适用诚信原则进行法律修正时,须在个案的基础上提取出一般性限制规范,而不能仅满足于个案决疑式的裁判。只有这样,“判决的妥当性才能以事后可检验的方式获得保障,个案裁判才能为同案类型提供可参考的一般规则”。〔85〕于飞:《民法总则法源条款的缺失与补充》,载《法学研究》2018 年第1 期,第46 页。有疑问的是,如果系争案件属于新发的孤案,是否有必要提取一般性规则;如果有必要,怎样保证基于个案所提取的规则具有一般性特征。实际上,当适用规范仅在个案中产生不公正结果时,援引诚信原则限制规则的适用即可,此种做法虽然构成了对法律的突破,但尚不构成法律修正;但如果相同问题多次出现,个案累积到一定程度,法官就可以且有必要从中归纳出一条限制性规范,以此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修正。
德国司法实践亦采取了此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在德国判例法中,如果事实证据与法律规定均清楚、明确,但严格适用既定法会导致严重不公正结果,则法官就此类案件所创设的裁判规则被称为“回应型裁判规则”。〔86〕参见高尚:《德国判例使用方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第133 页。就此类裁判规则的制定,当系争案件为新发的孤例时,法官只需从中提取“个案规范型裁判规则”,这类裁判规则主要是为了回应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就表现形式而言,这类裁判规则主要是作为判决理由存在的,缺乏概括性,法官往往不会将其总结为一条抽象规范。但如果某一类案件多次出现并形成判例群,法官就会在援引、对比和应用先例的过程中归纳出具有一般性的裁判规则,其也被称为“持续性判例的裁判规则”,由此构成了一种司法惯例,具备了习惯法的特征。〔87〕同上注,第136、185 页。可见,“回应型裁判规则”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形成之初,其主要体现在结合案件事实的判决理由中,欠缺概括性;当类似案件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法官才能结合判例群归纳出具有概括性的裁判规则,此时,裁判规则才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具体案情,从而具有一般性。
综上,在适用诚信原则进行法律修正时,如果系争案件尚无足够的先例可供参照,法官在充分说理的基础上依据诚信原则限制规范的适用即可,无需进行一般性法律修正。在此情形,与案件事实相融合的判决理由构成了个案规范,这类规范较为具体,但欠缺抽象性。在制定个案规范时,法官应当着重阐述对案件有实质影响的事实情节,以便于后案法官进行案件比较和参照适用。当类似案件逐渐增多,原本的孤案发展为典型性案例时,法官就可以且有必要从判例群中归纳出具有抽象性的例外规定,从而将某类特殊案型排除在具体规范的适用范围之外。
(三)诚信原则在我国《民法典》第153 条第1 款中的适用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方试图通过确认合同无效获益”的系列案件。问题是如果一方主张合同无效的行为违反诚信原则,可否根据诚信原则阻止不诚信一方主张合同无效。然而,主张合同违法无效并不构成实体法中抗辩权的行使,不属于权利抗辩;相反,合同是否违法无效属于法院依职权考虑的事实抗辩。因此,对合同违法无效的主张不可能违反诚信原则。〔88〕Vgl. MünKomm/Armbrüster, 2012, §138 Rn. 155.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应当是,认定合同无效是否会产生个案不公的结果。就方法论而言,问题的实质是,是否应当根据诚信原则限制相关强制性规定的适用,诚信原则在此发挥的是法律修正功能,而非权利行使审查功能。不过,强制性规定一般涉及公共利益,具有特殊性。那么,诚信原则可否修正强制性规定呢?
对此,早期德国判例持否定态度,理由在于,如果允许诚信原则修正强制性规定,会使相关规范变得毫无意义。〔89〕Vgl. RGZ 52, 1, 5; OLG Koblenz DRZ 1949, 40; BGH WM 1966, 518, 520.而且强制性规定是基于“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公共秩序目的”制定的,维护的是具有优先性的公共利益,因此,诚信原则不应适用于强制性规定领域。〔90〕Vgl. Soergel/Siebert/Knopp, 10. Aufl., 1967, §242 Rn. 44.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之处有二。其一,维护诚信客观上有利于弘扬诚信风尚,有利于构建诚信社会,这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表现。因此,在利益权衡中,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并不必然优先于诚信原则。其二,尚不清楚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将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相反,根据德国新近学说,保护其他合同伙伴或第三方的私人利益也可以成为阻止诉诸诚信原则(公共利益)的理由。〔91〕Vgl. Soergel/Teichmann, 12. Aufl., 1990, §242 Rn. 118 あ.因此,目前德国主流学说认为,不宜在强制性规定领域一般性地排除适用诚信原则,判断诚信原则可否修正强制性规定,需要在利益权衡的基础上,结合具体规范进行讨论。〔92〕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339.
在对我国《民法典》第153 条第1 款适用诚信原则时,应当指出,违反该款中的强制性规定不一定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由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 号)第14 条可知,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但合同当事人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93〕参见王轶:《行政许可的民法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5 期,第107 页。而在判断某一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时,《民法典》第153 条第1 款发挥的是概括条款的作用,授权法院在综合利益权衡的基础上予以确认。〔94〕参见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 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环节的“综合利益权衡”实际上与法律修正环节的利益权衡属同一思维程序。法官在此应首先考虑的是,相关强制性规范的含义和目的是否要求发生合同无效的后果。除此之外,法官也要将严格适用规范所导致的个案不公考虑在内。如果通过权衡,只有宣告合同无效才能维护强制性规定所保护的利益,而个案不公所导致的损失与之相比是无关紧要的,则该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以出卖人为了获得拆迁款主张小产权房买卖合同违法无效为例,禁止宅基地买卖的相关规定旨在维护出卖人的生存权、粮食安全乃至政治安全。〔95〕参见戴孟勇:《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纠纷的司法规制》,载《清华法学》2009 年第5 期,第8 页。此种利益保护较之纠正个案不公(买方无法取得拆迁款)更具优先性。因此,禁止宅基地买卖的相关规定应当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可见,在强制性规定的确认环节,个案公正已经被考虑在内。
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也需遵循上述相同的利益权衡程序,其所得结论理论上应当一致。即如果通过利益权衡得出某一规范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意味着个案不公相较于规范目的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此时便会同时得出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应被诚信原则修正的结论。《施陶丁格评注》也强调,如果通过利益权衡已经确认某一规范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补充适用诚信原则的余地很小。原因在于,在强制性规定的确认环节,如果个案不公相较于规范目的而言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在诚信原则法律修正环节,个案不公的权重也不应借助诚信原则被过度放大。在这种情况下,对信赖保护的考量也不可能有多大意义。因为对违法法律行为效力的信任,原则上不值得保护。〔96〕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486.依此要求,一旦禁止宅基地买卖的相关规定被确认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法官不得再以个案不公为由诉诸诚信原则改变合同的无效性。
可见,如果通过利益权衡,某一规定被确认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其所产生的无效结果原则上不应被诚信原则矫正。同样,如果某一规定被确认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法律行为有效,则无需诉诸诚信原则。然而,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存在误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确认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况。〔97〕如《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2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 条第1 款。同前注〔93〕,王轶文,第99 页。从立法论的角度看,这些规定本质上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如果其适用会导致个案不公正结果,则通过认定合同有效的方式予以矫正即可,而无需诉诸诚信原则。但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说,由于这些规定已经明确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因此,法官无权再依据《民法典》第153 条第1 款将其认定为管理性强制规定。〔98〕如果相关规定已经明确规定了无效的法律效果,则《民法典》第153 条第1 款不再具有概括条款功能,仅具有引致功能。同前注〔94〕,苏永钦书,第41 页。在此情形,如果认定合同无效会在个案中产生难以容忍的不公正结果,则只能通过限制相关规范适用的方式改变合同的无效性,此时便会进入前述“目的性限缩—法律修正”的矫正路径。需要说明的是,诚信原则只能作为矫正个案不公的最后手段,在此之前,应首先检验个案不公可否通过目的性限缩、不当得利、损害赔偿等手段得以矫正,如果可以,则没有必要也不应当适用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
四、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的适用限度
(一)原则上不得填补法政策漏洞
法官在进行法律修正时,表面上依据的是诚信原则,但其实质仍是基于现行法秩序所提供的评价要素。有疑问的是,如果现行法对某一事件没有提供评价要素,法官可否依据法政策认定某一结果是不公正的,从而进行法律修正。对此,卡纳里斯认为,考虑到法官受法律约束原则,如果法律对某类事件已有规定,法官在进行法律修正时,仍应受到现行法秩序的制约。〔99〕同前注〔36〕,Canaris 书,第24 页。换言之,漏洞存在与否是由现行成文法秩序决定的,也即以成文法已有的评价要素为依据,判断是否需要对某一事件加以规范或对某一规定加以限制。假使法律并无不圆满的情况,只是有法政策上的错误,那么不存在漏洞填补的空间。〔100〕同前注〔34〕,卡尔·拉伦茨书,第252 页。依此要求,法官在进行法律修正时,不能仅凭自己对法政策的理解,还需要现行法评价要素的支持。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当法院根据法政策对某一现行法律规定表示不满时,常常以法律存在漏洞为由对现行法进行修正。在此,与其说法官在“寻找”漏洞,不如说是在“发明”漏洞。这样,法官才能实现其偏离法律的法政策意图。举例来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退一赔三”,《食品安全法》规定了“退一赔十”,这些惩罚性赔偿规定的目的不仅在于补偿消费者的实际损失,更在于惩罚经营者的欺诈经营行为,并对其他经营者产生警示效应,防止类似欺诈经营行为再次发生,从而净化市场环境。〔101〕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4 页。而消费者“知假买假”乃至“职业打假”的行为客观上有利于净化市场环境,符合惩罚性赔偿规定的规范目的。因此,通过目的性限缩,我们无法从这些规范中得出“知假买假者除外”这样的例外规定,即便消费者“知假买假”,其惩罚性赔偿的请求也应获得支持。但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10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 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仅认可了食品、药品监督领域的“知假买假”行为,对普通消费领域的“知假买假”行为不予支持。个中理由在于,食品、药品是直接关系人体健康安全的特殊的、重要的消费产品,且在当时食品、药品重大安全事件频繁曝出,基于这一“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政策考量”,应当认可食品、药品监督领域的“知假买假”行为;但其他消费领域并没有此种特殊情况,且职业打假的行为浪费了司法资源,故“不宜将食药纠纷的特殊政策推广适用到所有消费者保护领域”。〔10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 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法办函〔2017〕 181 号)。由此可知,在诚信原则可否限制惩罚性赔偿规定适用这一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所依据的不是从现行法秩序中提取出的评价标准,而是依据自己的法政策考量,此种做法已经僭越了立法权。
就“知假买假”这一情形而言,只有在存在更为严重的情节时,法官才可以进行法律修正。例如,消费者以打假之名行造假之实,用化学试剂将商品的生产日期擦去,或将商品藏到货架深处,等到过期后再翻腾出来索赔。〔104〕参见罗培新:《恶化营商环境、伤害社会诚信——关于职业打假的一些法律问题(上)》,载《中国市场监管报》2019 年4 月30 日,第4 版。又如,竞争对手借该规则打击同行企业,以此取得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针对这两种情形,我们可以从《民法典》第148 条中抽取出立法者对欺诈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也可以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 条中提取出立法者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若不借助诚信原则予以纠正,就会产生鼓励欺诈方或不正当竞争方的结果,而此种结果是立法者不希望得到的。在此情形,才可以依据诚信原则限制惩罚性赔偿规则的适用。
综上,当适用现行法将导致明显不公正结果时,法律修正可以作为一种紧急措施或权宜之计,但不能用来填补法政策漏洞。原因在于,适用诚信原则进行法律修正的目的不是要对法律秩序与社会制度进行改革或现代化,〔105〕同前注〔14〕,伯恩·魏德士书,第379 页。而只是为了矫正个案中的不公正结果。如果法律规定仅仅是落后于法政策,不应当由法官进行法律修正,基于法政策所进行的法律修正只能交由立法者进行。
(二)不得推翻立法者的有意决定
在进行法律修正时,必须关注有关法律规定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考虑到特殊利益状态。一项规则规定得越具体,就越有可能在具体案件中产生符合当事人最大利益的结果,此时诚信原则不得用来推翻立法者深思熟虑的价值决定。〔106〕Vgl. Staudinger/Looschelders/Olzen, 2015,§242 Rn. 337.换言之,如果立法者已经预见适用规则可能与诚信原则相抵触,但有意不作限制性规定,则此种限制之欠缺就是立法者的有意决定,法官不得推翻这一决定。此种情形也被称为“立法者的有意沉默”,是指虽然法律对某事项未作规定,但该规定之欠缺是立法者有意为之,故此种欠缺不构成法律漏洞。〔107〕同前注〔34〕,卡尔·拉伦茨书,第249 页;同前注〔33〕,黄茂荣书,第330 页。例如,有德国学者认为本国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情事变更问题并有意不作规定,属于立法者的有意沉默而非法律漏洞,因此不应依据诚信原则对合同严守条款加以限制。〔108〕同前注〔8〕,韩世远文,第10 页。
问题在于如何判断某一限制性规定之欠缺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在刑法中,由于存在罪刑法定原则,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否则所有的行为免予刑罚。在此,可以从法律规定之欠缺反面推理出立法者有意对某类行为不予惩罚,也即“立法者的有意沉默”。但此种反面推理于民法并不适用,因为民法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一般消极原则。因此,如果法律对某一规则欠缺例外规定,并不当然构成“立法者的有意沉默”。相反,立法机关在起草法律规范时,常以典型案例为主要方向,在很多时候并未充分认识到具体规则与诚信原则之间的潜在冲突。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诸多司法解释中为合同规定了特殊形式要件,且同时规定欠缺形式要件者无效。这些规定的目的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但诸如开发商滥用形式要件规则谋取房屋溢价这类不诚信行为是立法者未曾想到的。直到2019 年11 月8 日,《九民会议纪要》第32 条才对这类情形作了特别说明:“不能使不诚信的当事人因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获益。”可见,立法者最初并未认识到其所制定的规则会成为不诚信一方谋利的手段,也就不可能对一个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作有意沉默。
但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当法官依据规范的主观目的进行目的性限缩仍无法获得限制性规定时,常会认为此种欠缺是“立法者的有意沉默”。如在最高人民法院第23 号指导性案例中,法院认为《食品安全法》第148 条可以适用于消费者“知假买假”情形。其核心理据在于“该条并未对消费者的主观购物动机作出限制性规定”,也即从该条的主观目的无法获得限制性规定。〔109〕同前注〔53〕。然而,借助目的性限缩无法限制规则的适用,并不能说明限制性规定之欠缺是立法者有意为之。相反,立法者在立法时很可能并未充分认识到消费者“知假买假”这一情形。因此,论辩工作到此还未结束,法院还需说明为何不能依据诚信原则限制规则的适用。且该案中被告已明确主张“原告明知食品过期而购买,希望利用其错误谋求利益,不应予以十倍赔偿”。对于这一诉讼主张,法官必须回应。显然,在该案中,法官并未尽到充分论辩义务,仍是违反禁止拒绝裁判原则的一种表现。只有经“目的性限缩—法律修正”双重检验后,才能最终确定十倍惩罚性赔偿规则是否应当受到限制。在该案中不得依据诚信原则进行法律修正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者并不存在欺诈行为或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使得诚信原则在与十倍惩罚性赔偿规则的权衡过程中无法获得现行法其他评价要素的支持。因此,在该案中适用诚信原则的重要性并不明显超过十倍惩罚性赔偿规则,法官应当推定消费者“知假买假”的行为不构成制度滥用,不得依据诚信原则进行法律修正。
五、结语
当具体规则的适用与诚信原则发生抵触,并在个案中产生难以容忍的不公正结果时,法官可以依据诚信原则进行法律修正。法律修正功能的实质不是要另行建立一套更具道德感的法律秩序,而仅是为那些偏离规范“正常情况”的特殊案件创设但书,使相关规范在这些特殊案件中不予适用,以此实现法律的“紧急制动”。在司法实践中,多是一方滥用法律制度触发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该功能在此被用来规制制度滥用。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看,之所以会产生制度滥用的问题,是因为法律存在隐藏法律漏洞,需要法官添加合理且必要的限制予以填补。在此,目的性限缩和法律修正功能作为填补隐藏法律漏洞的重要手段,呈现出前后递进的关系。当通过目的性限缩无法实现合理且必要的限制时,法官就需要尝试诉诸诚信原则的法律修正功能。
在适用诚信原则法律修正功能时,法官应当进行利益权衡,确认适用诚信原则所带来的利益是否明显超过了严格适用规则所带来的利益。在这一权衡过程中,如果适用规则仅是产生有利于不诚信一方的结果,尚不足以说明适用诚信原则的重要性明显超过适用规则。要使诚信原则在利益权衡中占据更大权重,还需现行成文法其他评价要素的支持。诚信原则在此发挥“据点”作用,用来吸收其他评价要素。如果现行成文法并未对某一事项提供评价要素,法官不得依据法政策或自己的法感进行法律修正,否则就违反了法官受法律约束原则,僭越了立法权。基于法政策所作的法律修正只能由立法者进行,法官无权作此种修正。因此,在适用诚信原则进行法律修正时,法官一方面须意识到滥用的危险,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分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