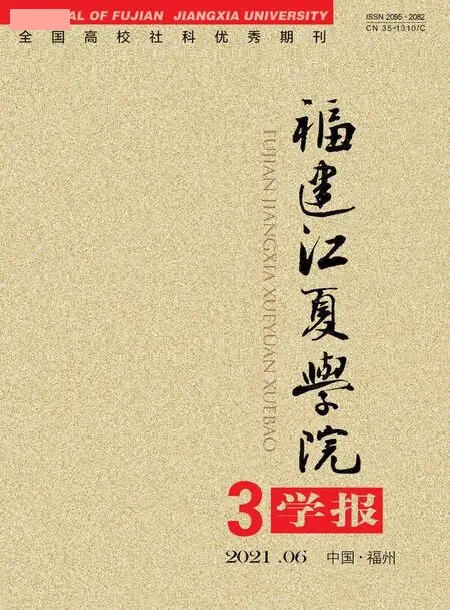冯梦龙文学思想探源
2021-12-07潘旭君
潘旭君
(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作为通俗文学的积极研究者和倡导者,冯梦龙一生致力于戏曲、民歌、笑话,尤其是白话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与编纂等工作。其通俗作品成就之大、作品之多是文学史上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而这些突出成就皆源自于他进步的文学思想。冯梦龙成长于封建时代,但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相比,他的社会观和文学观具有明显的先进性。他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对平民文学情有独钟。他切身感受到平民百姓对文学的真实需求,深刻地认识到通俗文学作品快捷而深刻的教化作用。他率先塑造了市民阶层的小人物形象,着力反映市民观念;宣扬济困扶危、诚信不欺、惩恶扶善,追求个性解放,重视市民友情和市民意识;着重描写市民阶层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表现他们的道德观念与理想追求,这些较为客观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充分显示冯梦龙文学思想的时代性、进步性与人民性。
研究作家的文学主张与作品,应该客观、历史、全面地了解作家的文学思想来源。冯梦龙的思想相当复杂,主要以儒家为基础,兼有释道,以及明代中期以降的哲学思潮和沿海一带的开放观念,其中,李贽、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主张对冯梦龙文学思想的影响较为深刻。李贽是一位主张“真情”的激进思想家,王阳明则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二者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哲学体系,但在思想理论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维系的纽带就是儒家的忠孝节义。可以说,冯梦龙文学思想是多种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儒家“仁义”思想对冯梦龙的影响
冯梦龙从小就接触并学习儒家思想,儒家经典烂熟于心。他不仅编著了大量的“治经”著作,如《麟经指月》《春秋衡库》《四书指月》《中兴伟略》等,还编纂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塑造了大量具有传统儒家思想的正面人物形象,强调儒学的价值观,如“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情史》《古今谭概》等。此外他年届六十还不远千里来到福建山区为官,实现“大济苍生”的梦想,体现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思想。
书院林立是明代儒家思想发展的一大特点。诸多知识分子通过讲学来表达政见和传播思想,其中就有东林党和冯梦龙参与的复社。他们以儒家思想为基准,倡导和传播儒家“经世致用”的积极入世思想,大力宣扬主张“兴复古学”。晚明沿海经济发达,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城市新兴市民阶层和农村富裕人群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在拥护儒家思想时也为自己争取利益。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冯梦龙敏感而又深刻地感受到这一思想变化,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之渗透在自己的文艺作品中。“三言”中诸多商人身上所体现的“诚信观”“义利观”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如《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卷二《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等作品中刻画的重仁义、讲道德、守诚信、以德报怨、平等互利的商人形象,他们秉承传统儒家道德,在社会剧烈变动的经济转型时期获得成功并提高了自身社会地位。
儒家的仁义思想成为冯梦龙思想的底色。但是明代社会思潮发生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宋代理学和元代的沉闷之后,明代文艺思潮蓬勃且复杂,各种思想汇聚争鸣,晚明出现了“儒释道”合流的倾向,这些思想倾向自然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在“儒释道”合流中对冯梦龙的影响除仁义思想外,还有释道的“尚真”和释家的因果报应等。从根本上说,这种释道思想在思想合流中并不违和,也可视为仁义的延展。
冯梦龙常将释道与儒并提,“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藉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1]冯梦龙崇尚道家“虚无”“尚真”思想,并将之贯通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如他所倡导的“真情说”,其主要哲学来源就是道家的“尚真”。在“三言”中,道家识心见性,蔑视功名富贵,追求逍遥自在等思想得以充分体现,如在《警世通言》卷九《李谪仙醉草吓蛮书》、《醒世恒言》卷四十《马当神风送滕王阁》等作品中,冯梦龙用极富浪漫色彩的笔法写出失意文人(李白、王勃)恣意洒脱的生活,以慰藉现实苦闷的自我。同时他还将自己率真的个性,真切自然地融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墨憨斋定本传奇》文尾的题诗“谁将情咏传情人?情到真时事亦真”[2]就是这种思想的直接反映。《醒世恒言》卷二十六《薛录事鱼服证仙》中薛录事的入梦化鱼、《警世通言》卷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庄子的假死试妻,以及搜集民间歌诗发出的“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3]等,皆可看到道家之“真”。这种“真”与文艺创作中“艺术真实”普适性相对应,对冯梦龙文学思想的生成与传播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冯梦龙编纂的“三言”120篇作品中,有20多篇内容涉及佛教的“因果报应”及关于“酒色误人”的佛家戒律等思想。如《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结语:“恩爱夫妻虽到头,妻还作妾亦堪羞。殃祥果报无虚谬,咫尺青天莫远求 ”[4]36,对王三巧儿的命运作了相应的评价;《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老大吕玉、老三吕珍无意中做了善事,最终一家骨肉团圆,而老二吕宝心怀鬼胎,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结语处点明了“本意还金兼得子,立心卖嫂反输妻。世间唯有天工巧,善恶分明不可欺”[5]62的“善恶果报”思想;《喻世明言》卷二十九《月明和尚度柳翠》中李源与僧人圆泽的因果故事,卷三十七《梁武帝累修归极乐》宣扬“有等善人,安乐从容,优游自在,仙境天堂,并无挂碍;有等恶人,受罪如刀山血海,拔舌油锅,蛇伤虎咬,诸般罪孽 ”[4]555的佛教思想,等等。这些虽然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蕴含封建宿命的因子,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受众而言,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震慑和劝诫的作用。
晚明时期的自由风气,追求个性开放、人性的解放等思潮也影响了冯梦龙对佛教清规戒律、禁欲色空等思想的认知。在《三教偶拈·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中,他将“喝佛骂祖”“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济颠和尚,立为“僧家之首”[6],体现冯梦龙对“袭其迹”的厌恶与“得其意”的认同[7]2。
二、王阳明“心学”对冯梦龙的影响
冯梦龙的后期作品更多偏向于王阳明的“致良知”,不仅讲求“真情”,还注重“知行合一”,可见王阳明“心学”对冯梦龙的影响。
第一,“心即理”影响了冯梦龙的文学观。王阳明作为儒家思想哲学化的重要代表,他提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8]13-14等重要命题,对世界本源、社会道德、人性等进行了考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和文学界。王阳明思想不仅影响了冯梦龙的人生道路,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冯梦龙的文学思想体系。冯梦龙极力推崇王阳明的军事才能、办案才能与治国之道等,在《古今谭概》《智囊》等中辑录了15个王阳明故事,他还在晚年创作了《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生靖乱录》,书中写到“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7]3,歌颂了王阳明的丰功伟绩,极力推崇王阳明的“心学”,冯梦龙的文学作品也因此具有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8]13的唯心主义观点。如在《警世通言》卷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开篇入诗即写到:“莫把金枷套颈,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5]14冯梦龙向往修心养性达到成己成圣境界的超脱由此可见一斑。庄子妻子死后,庄子鼓盆而歌则表达了其独特的生死观和“心即理”的哲学思想。
第二,冯梦龙的醒世思想与王阳明的救世思想具有同质性。“致良知”被世人认为是王阳明救世醒世的一剂良药。王阳明在不同的情境中,从不同的角度对“良知”进行不同的阐释,所谓“良知”,可以说是一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先天赋予的、不假外求的、人人具备的主观存在。具体指是非善恶之心、孝悌恻隐之心、真诚辞让之心、忠君爱国之心等。“致良知”即在实际行动中保持良知不为私欲所遮蔽、自觉自愿践行知行合一的道德规范。冯梦龙的醒世思想是认为自己可以通过通俗小说的劝诫,从而达到教人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效果。二者所宣扬的基本思想原则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在冯梦龙的文学思想里,更强调文学的情感作用,“致良知”表现为对“情真”的崇尚。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朴实忠厚,又有一种异于常人的向往和追求,无疑是古代文学世界中难得一见的一个人物形象。作品不仅正面表现了秦重的“良知”,而且通过邢权、老鸨的猥琐卑鄙反衬出秦重那光芒耀眼的“良知”。《醒世恒言》卷十二《佛印师四调琴娘》中佛印更是“致良知”量身定制的艺术形象,体现了冯梦龙教化劝善的思想。冯梦龙的“致良知”还体现在一些“小人物”,如商人、小手工业者的身上。他们有情有义、济困扶危、诚信不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养蚕人施复和朱恩,一个拾金不昧、分毫不取,一个知恩图报、济人之危,两人友爱互助,结下了兄弟般情谊。由此可见王阳明“致良知”思想和冯梦龙“以文教化”理念之间的同质性。
第三,王阳明强调个体价值,主张用独立的批判意识认识世界,促进了冯梦龙文学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明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品经济活跃,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出现了王阳明、李贽、徐渭为代表的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英雄式人物,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备受时人的推崇。冯梦龙通俗小说的情教思想正是王阳明“心学”影响下的产物,强调个体价值。在《情史》中,冯梦龙大胆宣扬“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化。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9]1,强调“情”的重要作用,认为“情”是可以脱离个人而独立存在,这些思想在冯梦龙的文学作品中均得到充分的体现。“三言”不但肯定了男女之情,也颂扬手足之情、朋友之情。《警世通言》卷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喻世明言》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等,表现情真实意的作品比比皆是,极力倡导情真,强调以真情感人、以真情教人。作品还首次反映了明代市井百姓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如《喻世明言》卷一《蒋兴歌重会珍珠衫》中的蒋兴哥与王三巧新婚燕尔,十分恩爱,但迫于生计,婚后不久,蒋兴哥便外出经商,在家无聊的王三巧却耐不住寂寞而红杏出墙。蒋兴哥获悉之后,忍痛将王三巧遣回娘家,“虽则一时休了,心中好生痛切”[4]28。改嫁后的王三巧碰巧得知蒋兴哥遭遇了官司,念及旧日夫妻之情,她想方设法搭救,几经波折,夫妻二人最终重归于好。普通百姓情感的自然流露、封建贞节观念的弱化等各种复杂思想意识,在这篇作品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生动表现了卖油小贩秦重和名妓莘瑶琴之间的爱情故事。在这里普通小商贩可以用真情感动花魁,而花魁娘子也并非只为从良而嫁人。为了追求自主爱情,他们敢于冲破传统婚姻门第观念的禁锢,关注自我生活,注重自我表现,说明了明代末年婚姻问题已经突破了封建门第等级观念的束缚,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正在萌芽等等,也显示了冯梦龙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当然,冯梦龙的这种主体意识还处于朦胧状态,因此,他的文学作品处处充满着矛盾与纠结,《蒋兴歌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痛恨妻子王三巧出轨而休妻,却又因旧情难忘而重归于好;《喻世明言》卷十《滕大尹鬼断家私》中的滕大尹有清明断案的能力和智慧,暗地里却设计私吞苦主的千两黄金。《喻世明言》卷十一《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主人公赵旭赴京赶考,科名因故被废而流落街头;却又因宋仁宗的偶然一梦而衣锦还乡,等等。
三、李贽“童心说”对冯梦龙的影响
李贽对冯梦龙影响深刻且多方面。李贽的思想主要体现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批判观、倡导男女平等观、尊重女性的进步妇女观,以及在文学作品中要表露真情实感的“童心说”等。冯梦龙不仅广泛阅读李贽的著作,而且虔诚地接受李贽的思想。在所编撰、评改的“三言”和《古今谭概》《情史》《智囊》等诸多著作中,冯梦龙大量引用李贽的言论,肯定李贽的多元化观点。
首先,在冯梦龙的著作中,不乏对孔子及其“六经”的嘲讽与质疑。如《警世通言》卷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以“二亲不允”否定了孔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5]7-8的观点;而在《广笑府序 》中则强调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大胆提出了孔子道学杀人的观点,“又笑那孔子这老头儿,你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10]其激进程度并不亚于李贽。当然,冯梦龙并未像李贽那样,对孔孟经书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批判,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李贽的观点,并将李贽的观点运用到他的文学作创作之中。
其次,受李贽进步妇女观的影响,冯梦龙认同、肯定、称赞女性的才智。在他的《智囊》专辑《闺智部》一卷中,刻意赞颂了古今才女。冯梦龙认为,“妇智胜男”,“即不胜,亦无不及”[11]。这与李贽的男女见识无长短之别的进步观点不谋而合。他同情、理解和赞美女性,在“三言”中塑造了一系列敢于抗争、追求婚姻自主、个性鲜明、才智卓越的智慧女性形象,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她们地位卑微,却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大胆追求自由婚姻,如歌姬杜十娘、花魁娘子莘瑶琴、团头女金玉奴、青楼歌姬严蕊等;她们的美貌与智慧并存,敢于追求并坚定捍卫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如苏小妹、喜顺娘、张淑儿、周胜仙等。这些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体现冯梦龙的历史进步性和现实针对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李贽和冯梦龙不但对历史上有作为的女性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且对寡妇再醮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他们都赞美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婚姻自主行为,李贽在《藏书》卷37中评价了汉代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一事,反映了他对卓文君私奔再嫁之事的赞扬。无独有偶,冯梦龙在《情史》也谈及此事,“相如不遇文君,则绿绮之弦可废;文君不遇相如,两颊芙蓉,后世亦谁复有传者。是妇是夫,千秋为偶,风流放诞,岂足病乎!”[9]86而且在《喻世明言》卷五《穷马周遭际卖媪》中,不但让寡妇王媪再嫁,而且嫁得很好。
第三,李贽的“童心说”影响了冯梦龙的文学价值取向。李贽“童心说”是从王阳明“心学”发展而来,两者之间一脉相承,但又有内涵上的质的差异。“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2]146-147李贽在提出“童心说”之前的思想皆是在此理论上建构的,这是“童心说”成熟前的思想准备与积淀,李贽后期的思想均围绕“童心说”而展开。李贽认为世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真情实感的表露。针对明代诗文创作的复古倾向,“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12]149-150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对复古派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12]145的理论提出了惊人的批评。明代之前,通俗小说始终被看作是粗野俗物,不能登大雅之堂,而李贽不但肯定了通俗文学的艺术价值,还极力推崇那些出自“童心”的优秀通俗文艺作品,认为它们是“古今至文”,至于“六经”和《论语 》《孟子 》等儒家经典则与“童心”无关;他还评点了《水浒传》《幽闺记》《红拂记 》等小说戏曲,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冯梦龙的文学价值取向。冯梦龙在继承李贽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大力倡导通俗文学,创作了大量通俗白话短篇小说,如“三言”等;搜集整理了民歌笑话集,如《挂枝儿》《山歌》《笑府》等;改编创作了戏曲文本,如《牡丹亭》《双雄记》《万事足》等,推动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发展。
四、结语
综观冯梦龙的文学作品,不难看出,“情教说”是冯梦龙文艺思想的核心,其主要来源于儒家“仁义”、王阳明“心学”及李贽“童心说”等思想,李贽对冯梦龙的影响尤为深刻。李贽是一位激进的思想家,他嘲讽和否定孔孟著作及其思想,抨击明代的假道学,但他又受到王阳明的影响,很多的精辟思想里都有王阳明“心学”的痕迹。王阳明的思想基调是儒家的,其中孟子和陆九渊的痕迹尤为明显。冯梦龙的总体思想是进步的,堪称文化杂家,他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和辨识力,又有兼收并蓄、运用自如的智慧;他总是能围绕“以情教化世人”这一目的,在不同的情境中恰如其分地表现不同的思想。比如,他一方面肯定卓文君为爱私奔,另一方面又在《寿宁待志》中为节妇立碑著传;一方面肯定女性、赞美女性的才智,有着进步的妇女观,另一方面又在《万事足》中严责高妻悍妒,不容丈夫纳妾,赞美心灵已被严重扭曲的不妒之妇梅氏;一方面嘲讽孔孟思想,另一方面却又埋头编撰《麟经指月》《春秋衡库》等经书。这种矛盾现象正是王阳明“心学”与李贽“童心说”思想碰撞的结果,而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则是儒家之以真情、自觉自愿地行忠孝节义之道的思想,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教化世人”“用情化人”。
此外,冯梦龙的文学思想还受到了释家和道家的影响。“三言”中的有些作品具有突出释道思想的倾向,但其大部分文学作品还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冯梦龙有时将释道与儒并提,但在编撰“三言”时,则不忘“喻世”“警世”“醒世”的教化功能,欲“以二教为儒之辅”,而且他还努力践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可见儒家思想早已深入冯梦龙骨髓并构成了其思想体系的基础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