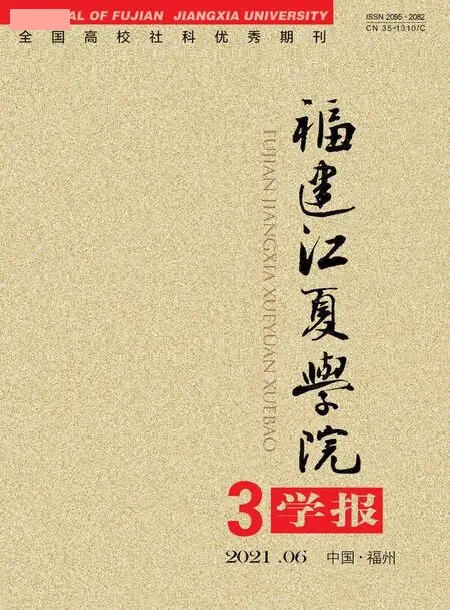高句丽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2021-12-07孙炜冉
孙炜冉
(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吉林通化,134001)
高句丽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尽管现存典籍所载疏略,但仍然可以从仅有的文献和遗存中看出双方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高句丽经过汉魏以来对汉文化长期的吸收,到隋唐时代已形成了相当繁盛的地方民族文化,隋唐高度发达的文化继续对高句丽产生强烈影响。虽然隋唐两代与高句丽战争不断,但双方还是在宗教、文学、音乐、教育等方面有着频繁而广泛的交流。高句丽灭亡后,大量的入唐移民又把高句丽文化带回中原,反哺了中原文化,使其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句丽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关系很早便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东北学者开始关注高句丽文化形成问题时,便已经注意到其对中原文化的吸纳及双方的文化交流,如魏存成先生便较为鲜明地强调,高句丽文化的形成相当程度上来自中原汉人文化的影响[1]。此后,又有多位学者注意到并倡导高句丽文化形成与中原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与联系[2],强调其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3]。21世纪以来,随着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拓展,许多学者从更为微观的视角对高句丽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因素以及双方文化交流情况予以研究,如以宗教信仰为视角的研究[4]、以古墓壁画为视角的研究①参见魏学辉:《浅析中原壁画对高句丽壁画之影响》,《东疆学刊》,2006年第1期,第49-51页;郑开法:《中原汉唐墓室壁画对集安高句丽墓室壁画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以神话传说为视角的研究②参见徐栋梁:《从开国传说看高句丽文化的渊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82-86页;孙炜冉:《〈三国史记〉高句丽始祖神话与建国神话的文献史源》,《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4-113页。、以服饰为视角的研究③参见徐晶:《从妇女装饰“花子”看高句丽文化的中原化》,《暨南史学》,2012年第7辑,第172-177页;李劲松:《论中原服饰对高句丽服饰的影响》,《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12-17页。、以婚丧习俗为视角的研究④参见史利玢:《谈高句丽民族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墓葬习俗》,《职大学报》,2011年第4期,第44-46页;刘伟:《中原文化影响下的高句丽婚丧习俗》,《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1期,第16-18页。、以文学为视角的研究[5]、以教育为视角的研究⑤参见张芳:《高句丽教育的性质与发展状况》,《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6-8页;宋欣屿:《高句丽教育制度中的中原因素解析》,《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8-14页。以及以人口流动为视角的研究⑥参见孙炜冉:《高句丽人口中的汉族构成小考》,《博物馆研究》,2011年第4期,第52-58页;苗威:《高句丽移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薛成城、李德山:《汉代中原人口向东北地区的迁移及其影响》,《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6期,第145-150页。等,可见中原文化对高句丽文化的形成有着极大的促进和影响,双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与互动[6]。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加验证了中原文化对高句丽文化的重要影响,汉人及其文化在高句丽文化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⑦参见李大龙:《辉煌的高句丽文化》,《寻根》,2006年第1期,第92-100页;于波:《汉文化对高句丽文化的影响》,《东北史地》,2006年第2期,第27-19页;王雁:《高句丽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同源关系》,《职大学报》,2013年第5期,第66-67页。
一、高句丽的汉学教育
高句丽第十七代王小兽林王在位期间,极为重视对高句丽的文化制度改革,其继位第二年(公元372年),便开始在高句丽施行大刀阔斧的文化改革,效仿中原制度,设立国家教育机关“太学”[7]221,以汉学为主要内容的高句丽教育事业开始有了飞越性的发展。⑧参见苗威、孙炜冉:《高句丽小兽林王考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41-45页;孙炜冉:《高句丽诸王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第154页。7世纪中叶,高句丽更是数次派遣贵族子弟赴唐,以直接汲取汉文化营养。
自小兽林王时,高句丽开始了系统地学习中原的汉学教育,但囿于文献阙遗,其发展状况和规模程度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隋唐之际,高句丽的汉学教育已经非常发达。据《旧唐书》载,高句丽人“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8]5320。文献表明,高句丽人非常喜好书籍,已经普及到“衡门厮养”这样的平民大众之家,并且建有专门的学校“扃堂”,用以教育高句丽青少年,在未婚之前,都要在这里读书习箭,显然是中原文化传统的“六艺”教育,因为所读书目均为儒家经典和前四史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这种汉学教育证明了高句丽人自幼便接受中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由此可知,高句丽因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教育具有同期中原社会教育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有了“扃堂”这样学校性质的专门的教育机构;其次,其教育体制是官学和私学并行;再次,高句丽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严格的等级性;最后,高句丽教育内容有儒学教育和汉字教育等内容。[9]
《旧唐书》所反映的内容是高句丽末期的社会情况,表明高句丽的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朝鲜半岛之后,仍在继续全面地吸收中原文化。这种汉学教育有着非常持久的连贯性,正是高句丽统治者注重对中原文化教育的学习,才造就了高句丽文化在海东地区的繁盛和昌明。
因为高句丽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而通行汉字,所以接受汉文化极为方便,特别是文献中所反映的,到了隋唐之际,高句丽对汉文化的吸收已达到相当的程度,中国的典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此基础上,高句丽的文学也因此有了极大的发展。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高句丽后期名将乙支文德的汉学素养。在与隋作战时,乙支文德曾写给隋将于仲文一首汉诗,云:“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10]1455全诗似乎是在恭维对方,实际却暗含揶揄,可谓绵里藏针,深得中华外交辞令之精华。[11]据《三国史记》称,乙支文德“资沉鹜,有智数,兼解属文”[7]505,颇有儒将之风。可见高句丽社会,尤其是贵族和上层统治阶级自幼便系统接受中原文化的汉学教育,深谙汉文、汉诗等,这也是后来高句丽人移民唐朝后能迅速融入中原社会重要的文化基础和深层原因。
另外,中原地区许多来自高句丽的学子、僧人也有很多汉诗佳作,如南陈时在陈云游的高句丽高僧定法师作的《咏孤石》:“迥石直生空,平湖四望通。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偃流还渍影,侵霞更上红。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该诗是一首十分成熟的律诗,格律较为规范,很难看出是中原之外的人所作。[12]陈、隋之际,中国的近体诗虽已出现,但还未在诗坛上占统治地位,这位高句丽的定法师却已得风气之先,作出了这样一首文字清新、技巧娴熟的律诗,若没有对汉文化的长期学习与积累,是不可能做到的。
此外,高句丽被唐击灭后,新罗扶立的高句丽王安胜(舜)遣大将军延武上新罗文武王表书,亦可为汉文学中表文典范。表略云:“窃以帝女降妫,王姬适齐,本扬圣德,匪关凡才。臣本庸流,行能无算,幸逢昌运,沐浴圣化,每荷殊泽,欲报无阶。重蒙天宠,降此姻亲,遂即秾华表庆,肃雍成德。吉月令辰,言归弊馆,亿载难遇,一朝获申,事非望始,喜出意表。”[7]101-102文字流畅,用典恰当,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汉学文化功底。
上述三个例证足以说明,高句丽有着成熟且成体系的中原文化教育,故而才有乙支文德、定法师以及延武这样汉学修养极高的人物。其实,在高句丽建国伊始,便表现出根源于中原汉学的文化趋势,如第二代王琉璃明王所作的《黄鸟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便是高句丽早期汉学诗作中的佼佼者。从该诗歌中既可以看出琉璃明王个人极高的汉学修为,同时,亦可以窥见汉学是构成高句丽文化的重要来源。[13]其实还不限于上述的高句丽统治阶层,一些底层民众亦表现出汉学素养在高句丽的普及情况,如高句丽底层流传的《人参歌》(“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椴树相寻”[6]543)等诗作,便反映了中原文化对高句丽文化的熏陶与影响。
汉学和汉文在高句丽社会的普及直接造成了高句丽在汉字书法艺术方面也有较高水平。《旧唐书·欧阳询传》中云:“高(句)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8]4947可以为证。现今发现的所有高句丽碑碣石刻、墓志墨书也均由汉字镌刻、书写而成,其中著名的《好太王碑》不仅史学价值极高,并且兼具书法和文学的艺术性于一身,其书法以雄浑高古、笔巧意拙的审美内质彰显了其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好太王碑》以其本身及拓本相关的书法艺术研究,一直以来便备受学界重视,甚至有学者以其与很多中原其他名碑加以比较。[14]并且,这种汉文书写的高句丽书法艺术并不限于好太王碑,还有诸如冉牟墓等一大批高句丽传世金石文献。[15]足证高句丽的书法艺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这种艺术熏陶要靠成熟的教育修养作为积淀才能得以实现,《好太王碑》便是其中汉字碑碣的杰出代表。
《好太王碑》是汉文化与高句丽文化关系密切的最好见证。石碑矗立在吉林省集安市城东4公里处的太王乡大碑街,建于高句丽好太王逝世第三年的公元414年。碑身用整块方柱形角砾凝灰岩略加修琢而成,高6.39米,幅宽1.34~2.00米不等,四面环刻汉字碑文,以东南为正面,共44行,每行一般为41字,计1775字。[16]学者们对该碑铭的史料价值、文章的笔法、书法的功力,均有高度评价:“铭词无韵,而文义简洁疏宕。叙事处有类范史之笔。字体八分遒浑。当为辽东第一古碑”(郑文焯:《高(句)丽国永乐好太王碑释文纂考》):“碑字大如碗,方严质厚,在隶楷之间。……所记高(句)丽开国武功甚备。此真海东第一瑰宝也”(叶昌炽:《语石》)。对与好太王陵碑有关之好太王陵砖,亦有高度评价:“好太王陵砖,……曰:‘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夕隶书朴厚,如两汉人,较《好太王碑》为精”(罗振玉:《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好太王陵砖跋》[17])。
高句丽自建国初期起,就利用汉文撰修本国史籍。有人用汉文记下高句丽史事100卷,名曰《留记》。公元600年,高句丽婴阳王诏令太学博士李文真,将《留记》整理删订为《新集》5卷。[7]244可见,其历史文本的书写亦是采用汉文完成,这就为后来金富轼撰写《三国史记》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而这些文献资料实际上就是汉文古籍。
从高句丽人对于汉文的广泛使用及汉诗的写作水平等情况,都可以看出汉文化对高句丽文化的重要影响,尽管高句丽地处东北边疆,但其却是中原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移植。
二、高句丽与中原宗教文化的交流
中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教,其中包括外来宗教“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而这两种宗教都被高句丽所接受,对高句丽社会文化影响极深。
佛教很早就传入了高句丽。公元372年,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至高句丽;374年,僧阿道自前秦至高句丽;375年,高句丽始建肖门寺,以安置顺道,又建伊弗兰寺,以安置阿道。[7]221此盖佛教以官方形式传入高句丽之始。此外,还有东晋经海路向高句丽传播的民间交流途径。[18]可以说,佛教一经传入便得到了高句丽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不仅兴建寺庙,还定其为国教,用以求福安民。[7]223迨至广开土王时,更是在平壤一次便建寺九座[7]223,可见佛教在高句丽发展之快,影响之迅猛。东北亚地区也正是经由高句丽为途径,才将佛教传播至周边地区,故所谓“海东佛法之始”[7]221即始于高句丽。
到了隋唐时代,佛教已在高句丽得到了充分且广泛的传播。但佛教义理博大精深,高句丽僧人在弘法时经常遇到疑义待析、经籍未备的困难。出于探寻佛法的热情和对佛法的崇仰,这一时期还有很多高句丽的僧人亲赴中原地区求教请益。如高句丽僧人释波若,南陈时来到中原内地求法,先在金陵听讲,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后,波若离开金陵游方学业。开皇十六年(596)入天台山师从智额大师求授佛法,不久即有所成,智额劝他到天台山的最高峰华顶上修头陀行,波若即于开皇十八年(598)前往此处,昼夜修行,不出山达十六年之久。大业九年(613)二月,他自知寿命将尽,下山至国清寺,向众僧辞别,数日后无疾寂灭于国清寺。[19]波若虽没有把天台宗传回高句丽,但他本身的事迹足以说明中原地区的佛教文化对高句丽的巨大影响,令无数求法僧人赴中原内地学习,相信还是有更多的人在求学之后返回高句丽,将中原地区学习到的佛教文化在高句丽乃至东北亚诸地发扬光大。
稍后来到中原求法的高句丽僧惠灌,他于开皇九年(589)至大业元年(605)间在内地学习佛法,先后在越州稼祥寺、长安日严寺游学,师从吉藏,学习三论宗。而三论宗对高句丽影响尤甚,其中新三论宗的创始人僧朗大师,便是高句丽辽东城人,在南梁时游学于中原地区,历住摄山栖霞寺、钟山草堂寺弘法。[20]
高句丽僧道登也于贞观元年(627)来到长安,师从吉藏,此二人后来均赴日本弘法。[21]高句丽僧智德则师从禅宗五祖弘忍。《楞伽师资记》记有弘忍对他的评价:“潞州法如、韶州慧能、扬州高丽僧智德,此并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21]可见其佛法造诣之高。
这些高句丽僧人不仅深研佛法,同时也弘扬了高句丽的文化。例如,高句丽乐就是由他们传入内地的。另外,他们还促进了佛教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22]此外,佛教建筑对于高句丽建筑亦有深远影响。[23]
在宗教文化交流方面,另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道教在唐初传入了高句丽。公元624年,唐高祖遣使前往高句丽,携有天尊像及道士,为高句丽讲《老子》,荣留王及道俗听者数千人;次年,高句丽荣留王遣使于唐,求佛老教法。[7]251-252公元643年,盖苏文奏请宝藏王遣使于唐,再求道教以训国人,唐太宗遣道士叔达等八人赴高句丽传道,兼赐老子《道德经》。[7]255道教文化在高句丽迅速崛起并盛行,直接影响了佛教在高句丽的地位和影响,于是在公元650年,发生了高句丽盘龙寺普德和尚以国家奉道不信佛法南移完山孤大山的事件。[7]267由此可见,道教传入高句丽后,很快便压制了佛教的社会地位,这种宗教风气的变化同唐朝皇室崇道抑佛息息相关,可见中原宗教文化对高句丽影响之深远。其实,从高句丽壁画墓中为数众多的仙人形象可以看出,道教文化应该在唐之前就在高句丽社会有所流传,尤其是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推崇,因为道教修仙长生的思想恰恰符合高句丽统治阶层的祈愿,所以才能大量出现在贵族墓葬的壁画中。如前文所述的佛教流入途径一样,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途径[22],而从文献来看,民间途径要早于官方,也正是非官方途径早已在高句丽社会大量流传,促进了统治阶层的政治需要,才有了官方主动遣使唐朝求道家经典的行径。
道教在南北朝地位并不高,由于唐帝室以老子为远祖,所以唐初道教获得了尊崇的地位。泉盖苏文尽管在政治上与唐对抗,但在对汉文化的追慕上却丝毫不落人后,汉文化的强大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
三、高句丽与中原艺术文化的交流
高句丽艺术文化与中原艺术文化的关系,可从高句丽遗存的墓室壁画中得以窥见。高句丽壁画墓主要集中分布在集安、平壤、安岳三地。壁画题材大体可分为三类:社会生活风俗画、图案画和神灵画。前两类多为3世纪中期至5世纪中期的作品,后者多为5世纪末至6世纪中期的作品。高句丽的政治中心于公元427年转移到朝鲜半岛之后,墓室壁画从题材到技法仍继续保持着与汉文化的紧密关联。
高句丽壁画墓中的神灵题材大多取材于中原的神话故事,如代表四方和整个宇宙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中原,汉代墓葬里早就出现了四神图像,到南北朝时,四神已成为墓室壁画、墓志、石棺上不可缺少的形象。[24]高句丽晚期墓室壁画题材也以四神为主,充分体现了与汉文化深厚的渊源关系。
高句丽晚期壁画墓五盔坟四号及五号墓里,还画有驾鹤仙人王子乔,也来自中原神仙故事。伏羲、女娲是中原传说中的人类始祖神。高句丽晚期墓室壁画中的伏羲氏,双手举一日轮,中画一三足乌;女娲双手举一月轮,中画一蟾蜍,二者均为人首蛇身。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在西汉初期早已成为常见的装饰图样。日中画三足乌,月中画蟾蜍,既取材于中原的神话传说,也采用了中原的表现手法。
高句丽墓室壁画在吸收中原绘画技巧和表现方法的基础上,还创造了本民族的绘画特色。无论设色和用线,都达到了气韵生动的效果,因此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东方绘画艺术的瑰宝。[25]
高句丽4世纪末至5世纪的土封墓,是在汉、三国时期以平壤为中心的汉乐浪郡故地内,完全受中原文化系统的壁画墓的影响下,模仿中原墓制而营造的。表现为:前室左右有室或侧室,其面积比主室大,平面呈“T”字形。壁画亦仿中原样式:前室以墓主夫妇的画像为中心,两旁配绘侍者、臣僚等。此外,在南北朝美术的影响下,出现了莲花纹饰。朝鲜半岛上江西郡肝城里莲花墓的天井上绘有北魏式的满开莲花纹,这类高句丽古墓与著名的彩箧墓等汉乐浪郡古墓一致,与中原本土的汉代墓以及辽东的汉、三国时期的墓葬表现手法完全一致。平壤附近龙冈郡池云面真池洞的双楹墓,前室与后室之间以及通道左右两侧均有八角柱,因此命名为双楹墓。这种双楹墓显然是仿效云冈等石窟而建造的。集安市通沟舞踊墓东壁的狩猎图,其范本为汉代的狩猎图,图案化的山脉、奔跑的动物等构图都是一致的。[26]56
平安南道中和郡真坡里一号墓,玄室北侧的树木图:山坡的两侧有大树,树间为线描的玄武,树干与树叶显得颇为悠然,并给人以真实感。天空中,似和着节奏,在飘舞的忍冬、飞云、莲花描绘生动。大树被劲风撼动的情景,以及树间的景物,其构图源于南北朝的美术。但真坡里一号墓的这幅画,与南北朝美术相较,则更具律动感[27],显然是在前者基础上技艺的进一步提升。
高句丽土封墓的玄室多采用抹角藻井的架构,这种架构在河南省沂南3世纪的石室墓以及在云冈石窟中早已出现过。[26]56
高句丽雕像艺术以佛雕艺术最具代表。1959年于汉城郊外纛岛发现5cm的小铜坐佛,乃400年前中原内地的作品,可以认定这是中国佛雕在朝鲜半岛最早的范本。1963年3月,在庆尚南道宜宁郡发现延嘉七年巳未铭金铜立佛,这是朝鲜半岛现存年铭最早的高句丽佛雕,此佛雕亦属中国北魏系统。以身躯中心线为基准,衣褶略向左倾,衣襟搭在左手,这些都是6世纪前半期中国典型的佛雕手法。可以认定,高句丽佛雕在此时已确立了它的基本形态。延嘉七年巳未,据推断为公元539年,韩国学界认为这是高句丽的年号。[26]69
此外,高句丽舞乐艺术也深受中原艺术文化影响。从冬寿墓⑨位于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的安岳三号墓,公元375年营造,1949年发掘。墓主冬〈佟〉寿,原为辽东慕容氏的官员,于公元336年亡命到高句丽。前室壁画奏乐图上可以看到:乐队坐,仪仗队立,有箫、鼓、歌舞。据此判断,在殿庭演奏的这种仪礼乐,应是鼓吹乐,并可推断高句丽的这种殿庭鼓吹,应即汉代的黄门鼓吹。[28]从该墓的回廊大行列图可以见到:由擔鼓、擔钟组成的前部鼓吹,以及由二重鼓、箫、角、铎形打击乐器组成的后部鼓吹。据此可以判断,应即汉代的短箫铙歌。从该墓后室壁画舞乐图可以看到高句丽乐器玄琴。据《三国史记·乐志》记载:“初,晋人以七弦琴送高句丽,丽人虽知其为乐器,而不知其声音及鼓(弹奏)之法。购(征求)国人能识其音而鼓之者,厚赏。时,第二相王山岳,存其本样,颇改易其法制而造之,兼制一百余曲以奏之。’于时,玄鹤来舞,遂名玄鹤琴,后但云玄琴。”[7]408从后室的舞乐图还可以看出,与前室壁画的殿庭鼓吹不同,这里没有仪仗队。因此,可以断定这里不是礼宴,而是曲宴(私宴),使用的乐器为玄琴、洞箫,以及晋人创制的阮咸。[29]
6世纪后半期至7世纪后半期为高句丽音乐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高句丽音乐——“高(句)丽伎”曾列入隋开皇初制定的“七部伎”[10]376、大业中的“九部伎”[10]377以及唐太宗时的“十部伎”[30]。可见,在高句丽艺术文化与中原艺术文化的交流中,不是单方面的受容,而是相互影响。高句丽乐文化的回流更加证明了高句丽文化系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高句丽与中原服饰、科技文化的交流
高句丽在服饰文化方面也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旧唐书·高丽传》云:“衣裳服饰,唯王五彩,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其冠及带,咸以金饰。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袴大口,白韦带,黄韦履,国人衣褐戴弁,妇人首加巾帼。”[8]5319-5320这种等级森严的服饰规定,显然是模仿中原王朝的制度文化并略加变化而成。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所绘高句丽人所戴巾帻和衣冠,许多均系中原地区汉服文化和辽西鲜卑服饰文化的传统服饰。[31]
在历法、医学等方面,高句丽与中原也有大量交流。公元624年,高句丽王高建武“遣使如唐请班历”[7]251。高句丽的医书《老师方》传入唐,对中国医学有一定的影响。[32]高句丽的冶炼术和人参也传入唐。陶弘景《名医别录》谈到冶炼时说“高(句)丽、扶南及西域等地成器,皆炼熟可服”[33]459;对人参则称“百济(参)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者,次用高(句)丽(参)……不及百济”[33]700。
可见,高句丽在科技文化上与中原内地有着极为频繁的交流和互动,相互影响。
五、高句丽人移民唐朝及影响
隋唐,高句丽与中原王朝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尤其是唐屡次攻打并最后翦灭了高句丽,先后迁移了大量高句丽人至内地。[34]如贞观十九年(645)战后,“诸军所虏高(句)丽民万四千口,先集幽州,将以赏军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35]6231。这些高句丽人从此便留在了幽州。总章二年(669),因为“高(句)丽之民多离叛者,敕徙高(句)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35]6359。仪凤二年(677),唐朝遣高句丽降王高藏还居安东,“高(句)丽先在诸州者,皆遣与藏俱归。……藏至辽东,谋叛,潜与靺鞨通;召还,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于河南、陇右诸州,贫者留安东城傍”[35]6382-6383。大量高句丽移民迁入中原内地促进了高句丽文化与汉文化最终的融合。
高句丽灭亡后,大量高句丽权贵投唐为官,史书上有记载的高句丽人如泉盖苏文的孙子泉献诚,武艺高强,“授右卫大将军,兼令羽林卫上下。天授(690—692)中,则天尝内出金银宝物,令宰相及南北衙文武官内择善射者五人共赌之。内史张光辅先让献诚为第一,献诚复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吐摩支,摩支又让献诚,既而献诚奏曰:‘陛下令简能射者五人,所得者多非汉官。臣恐自此已后,无汉官工射之名,伏望停寝此射。’则天嘉而从之”[8]5382。唐玄宗时名将高仙芝、王思礼、王毛仲等均是高句丽人,他们为唐朝建功立业,在《新唐书》与《旧唐书》中都有其列传。从代宗至宪宗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李师道家族亦是高句丽移民中的显赫者,他们兼海陆运使,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等职,在中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例证反映了高句丽人不仅在唐朝得到了很好地安置,而且能力出众者还能够在政治舞台上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说明了唐朝社会的开放态度⑩参见冯辉:《唐代社会的开放风气》,《求是学刊》,1992年第1期,第101-106页;冯辉:《唐代政治开放述论》,《求是学刊》,1997年第4期,第99-103页。,更进一步证明了高句丽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单元。并且,高句丽并非是单方面吸纳和学习中原文化,其在交流过程中还有反哺的情况发生,如享誉唐代的重要军备“陌刀”,便是由高句丽传入,尤其是伴随着高句丽移民的到来,而逐步流传到中国西北地区,直至确立为唐军重要的军事装备。[36]
六、结语
可以说,高句丽文化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关联性。独特性是任何一个区域和民族自身区别于周围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显著特征,高句丽民族亦不例外;而关联性是说高句丽文化究其本源仍旧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其与已经消失的鲜卑文化、契丹文化一样,对中国北方尤其是中国东北的文化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表面上看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其实质却是流散在了中华文明之中,其产生之初便受中原文化影响,二者关系紧密。正是高句丽与中原之间频繁而密切的文化交流,成就了高句丽文化的辉煌灿烂,使其屹立于东北亚民族之林。中原文化不仅深刻影响和造就了高句丽自身的文化形成与发展,更促进了其迅速从原始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走向封建化发展的道路。尽管与中原汉地文化相比,高句丽文化仍保留着一些自身特点,还稍显落后,但相比较高句丽周边的其他国家和民族来说,其文化更加昌明,社会更为进步,是东北亚地区独树一帜的文化表率。而这一切皆是因为高句丽对于汉地中原文化的交流和学习,使其成为连接中原汉地和东北亚其他国家与民族的重要中转站和枢纽,承担着中原文化向外传播的巨大使命,同时,也担当了反哺中原文化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