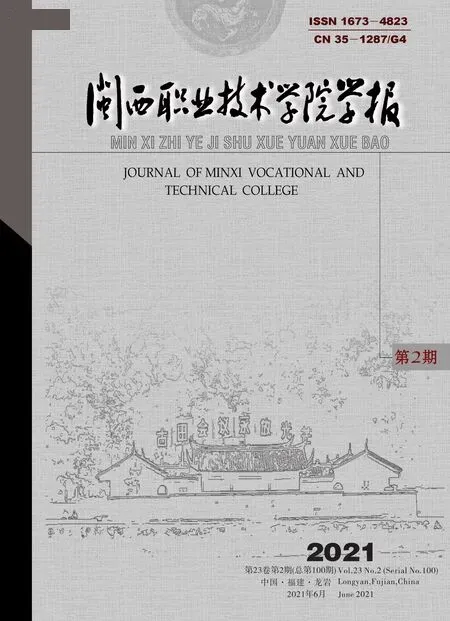七等生小说现代与浪漫融合的精神向度
——以《我爱黑眼珠》为中心的考察
2021-12-06何海峰
何海峰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州 350300)
现代主义思潮盛行于台湾20 世纪50—60 年代。 虽然现代派作家在创作理论上极力抵制浪漫主义倾向, 但在一部分作品中又或隐或显地夹杂着浪漫精神的美学意蕴, 显示出这一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 现代意识中的存在价值探寻与浪漫精神里的孤绝感伤颉颃互渗。
七等生,原名刘武雄,台湾苗栗人。 七等生是其笔名,取意于“七竹寺生”。 其作品文风奇特,多次获得“台湾文学奖”,是台湾20 世纪60 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 也是一位在现代意识下潜藏着浪漫因子的作家。创作于1967 年的《我爱黑眼珠》就是他融合现代与浪漫两种精神向度的创作实践, 现代与浪漫的融合形成七等生小说精神世界的奇特风景。 通过考察《我爱黑眼珠》,我们也得以窥见20 世纪50—60 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挣扎矛盾的心灵困境以及强烈的精神突围取向。
一、现代主义的探索
现代主义其实是现代工业兴起后, 西方文学哲学思潮的总称,因此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思潮,不如说是作家创作的一种精神向度与风格探索。 通常认为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他的《变形记》挖掘人物心理深度, 讲述人物在资产阶级现代体制下的异化过程, 文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就是社会失衡与人性失衡的产物。 现代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家如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伍尔夫、川端康成等都将这种风格奉为圭臬,分别创作出《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喧哗与骚动》《墙上的斑点》《雪国》 等代表作。正是世界与心灵被双重解构的背景下,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西方广泛流行。某种程度上,七等生就是在追随他们的步伐。
台湾现代主义的兴起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 由于20 世纪50 年代台湾依赖美国经济、军事,台湾文化呈现西化状态;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对文艺严厉控制,高压政治钳制人民思想,使个人的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逐渐虚化。因此,台湾现代主义作家不再一味地摹写外在的现实世界, 而是转向自身生存的反思,利用象征手法隐晦投射自身的“心像”。
(一)存在困境中的抉择
20 世纪50—60 年代, 台湾地区的知识分子普遍感到焦虑、孤独、虚无,存在主义引起他们的精神共鸣,契合了他们的心理需求。 为了摆脱这些枷锁,知识分子们利用存在主义来反思个人的存在本质——存在主义总是将人物抛在一个极端的处境中,让人物在荒诞不经的环境中挣扎与选择。
在《我爱黑眼珠》中,七等生为小说主人公李龙第设置了选择的困境——当面临灾难时, 是救助妻子还是救助一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这成为主人公的艰难抉择。故事一开始,李龙第与晴子约好一起去看电影,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打乱了计划。随着雨势加强,城市被洪水淹没,人人自危,这时李龙第依然没有放弃对晴子的寻找, 他叹息道:“即使面对不能避免的死亡,也得和所爱的人抱在一起啊。”[1]可以看出李龙第深爱着晴子。 但当他救起一位奄奄一息的妓女时, 故事的走向开始挑战人们惯有的思维和世俗道德。按照伦常,晴子本应是李龙第所应担负的伦理对象,但他选择照顾素不相识的妓女,而无视对面歇斯底里的晴子, 甚至眼睁睁看着晴子被洪水冲走。以日常的道德伦常来审视,很明显李龙第的行为没有承担基本的责任。 但如果换成存在主义的视角,则是另一番理解。 萨特认为,人的本质是由自身决定的,而非上帝和环境决定的,人通过自由选择创造自己的价值,担负起自身存在的责任。李龙第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实在的人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我承认与缄默我们所持的环境依然不变, 反而我呼应你,我势必抛开我现在的责任,在我的信念之下,只伫立着等待环境的变迁, 要是像那些悲观而静静像石头坐立的人们一样,或嘲笑时事,喜悦整个世界都处在危难之中,像那些无情的乐观主义者一样,我就丧失了我的存在”[1]。李龙第确信只有主动选择,承担眼下的责任才能保有自我的存在价值。
李龙第为什么选择对妓女承担责任? 李龙第没有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来源, 只能依靠自己的妻子养家。 这种依赖让他丧失自我的价值感与尊严感。 因此,在他的潜意识中希望能摆脱对晴子的依附,成为一个负有具体责任的自由人。 这场洪灾给李龙第提供了一个契机, 而妓女的出现则为其确证存在创造了条件, 所以李龙第选择重塑自我的角色——亚兹别来承担新的责任。七等生让李龙第在方寸的屋脊之上,圆了一场“英雄梦”,李龙第残缺的人格与意义的模糊通过这场荒诞境遇里的选择得到补偿和满足。
(二)象征隐喻的建构
现代主义的另一特点是大量运用象征隐喻。 作家通过设置一些具体的象征物来引发读者的感受与想象,进而填补作品中的空白。 七等生在《我爱黑眼珠》中大量运用象征隐喻的手法,使主人公内心的矛盾世界得到投射与映照, 呈现七等生创作时的深层心理机制与独特的情感体验。
黑眼珠这个意象在文中一共出现三次。 第一次是“李龙第想着晴子黑色的眼睛,便由内心里的感激勾起一阵绞心的哀愁”[1], 这是因为李龙第想到了他所深爱的、拥有一双黑色眼睛的晴子。 第二次是“李龙第疑惑地接触到隔着像一条河对岸那屋脊上的十分熟识的眼睛,突然升上来的太阳清楚地照明着她”[1],这是李龙第在洪灾中意外看见晴子时的感触,那双熟识的双眸就是晴子的象征。第三次是“李龙第低下他的头,正迎着一对他相似熟识的黑色眼睛”[1],此时, 李龙第所看见黑眼珠的主体人物已发生转变——由李龙第的妻子晴子转变为他怀里的妓女,预示李龙第最后“抛弃”晴子而救助妓女的结局。 为何黑眼珠会发生转变?在洪灾之前,李龙第作为晴子的丈夫,理应爱护晴子;洪灾发生之后,晴子与李龙第遥遥相隔,怀里的妓女才是李龙第此刻的责任,才是实现个人存在价值的正确抉择。 黑眼珠不仅指涉特定对象, 而且寄托作者在灾难中生存的情感——对个人理想的追寻,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追寻。在七等生另一部作品《我爱黑眼珠续纪》中,黑眼珠依然象征着李龙第的理想追寻——他希望找回被洪水冲走的晴子。但晴子已经迷失在社会运动中,再也找不回往日的那个纯真。 这两部作品串联起李龙第理想追寻的悖论——不断追寻黑眼珠,却又不断失落,从而映照出七等生颓靡的心境: 理想的追寻与失落永无止境地循环。
洪水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象征。 《我爱黑眼珠》是一部象征性寓言,洪水来临时旧的伦常关系、旧的价值规范都土崩瓦解,在旧秩序瓦解的处境中,人挣脱旧有的道德枷锁,企图重建新的个人价值。 因此,洪水是毁灭与重建的双重隐喻。 李龙第在这场洪水中摆脱了过去依靠妻子的边缘人身份, 成为具有自我价值的存在。 同时, 洪水也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李龙第所在的此岸是李龙第自己所建构的理想世界,而晴子所在的彼岸则是被隔绝的现实世界。这道鸿沟让李龙第得以躲在自我的理想世界里, 沉溺于自我认同与抉择的光荣, 但幻想式的乌托邦建构毕竟是虚幻苍白的,洪水过后,李龙第送走妓女,继续回到现实寻找晴子。
小说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色彩意象,比如:红色茉莉花、尼龙伞、绿色雨衣、香花等。七等生在小说中营造的总体底色是灰色阴郁的, 而加入这些点缀性的色彩意象则让读者感受到, 即使在灰暗的世界里依然存在一些明亮的温暖——雨伞是寻找心爱之人所借助的标识,雨衣是为心爱之人准备的,香花是给救助之人的温暖。七等生笔下的这些色彩意象,其实也是人性色彩的折射——作者个人的灰暗心境中依然保有人性的光亮与温暖。
二、浪漫主义的执著
如果说现代主义着重表现人生的荒谬, 那么浪漫主义则是追求人生的崇高; 如果说现代主义意味着人性的压抑和异化, 那么浪漫主义则意味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如果说现代主义注重历史批判,那么浪漫主义则崇尚人文情感。所以,浪漫主义是与现代主义相对的一种文学思潮。但20 世纪的台湾文学并没有适合浪漫主义的生存土壤, 一方面台湾文学倍受日据统治者的压抑, 另一方面官方文艺政策排斥浪漫主义。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些作家在现代意识下还潜藏着浪漫精神。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就体现了他的浪漫主义精神向度。
(一)隐遁者的“心像”抒写
浪漫主义推崇自我情感的抒发与内心世界的刻画。七等生在小说中主动关照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趋向故事人物的内心,探索个体内在的世界,揭露自己的“心像”。
七等生的小说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 他生命中的各阶段主要经历几乎都被他写进自己的小说中。深入剖析《我爱黑眼珠》这部作品,我们可以从李龙第身上窥见作者的思想理念与生活经验。 李龙第在小说中被作者有意识地塑造成边缘人的形象——没有正式的社会工作,也没有基本的社交活动。李龙第的边缘人形象与七等生局外人的生存经历颇为相似。
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创作于1967 年。他为了写作辞去教职工作来到台北,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由于已经成家,且孩子也已出世,经济上的压力逼迫他不得不再次进入职场,却四处碰壁,重拾教鞭的愿望也落空。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妻子的微薄收入。这种“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模式,与李龙第和晴子的状况相同。 七等生对社会的疏离与厌恶感深受其人生经历影响:自小就因家庭贫困遭受诸多冷眼,父亲失业更加剧家庭的困顿; 求学时期因贫穷而遭受许多不公正待遇,甚至差一点就被学校开除;步入社会后,又因不愿像其他人一样扭曲自我、阿谀奉承而被领导同事排挤, 工作上四处碰壁, 最后不得不辞职。七等生自觉是一个无法自洽的现代人,想要远离这个所谓的“现代文明城市”。
七等生在表现自我的同时,也在重建自我。从孩童时期到长大进入社会, 七等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几乎都在因贫穷而带来的苦难中度过。 但是七等生并没有因此而沉沦, 而是积极寻找突围的途径——不断地通过写作来表现自我、宣泄自我,企图从探寻内在的自我达到破茧而出。七等生以疏离社会的姿态,走向自我的内心世界, 希冀在荒诞异化的社会之中寻求一处心灵栖息地,重建自我认同的根源,寻得自我确证的生命意义。
“浪漫主义看似专注于个人内心的狭小世界,实则通过自我意识的反复追问和想象转移, 由此通向一个广大的世界。”[2]七等生的内倾性书写,不仅是自我的表现与自我“心像”的揭露,而且是当时台湾地区知识分子共同情感与需求的记录。20 世纪50—60年代台湾文坛以服务社会的实用性为主流, 文学内容经常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 相较之下,七等生为个人而写作成为这个时代文学体制的一场浪漫叛逃。
(二)超验理想的忧郁情怀
超验想象通常运用夸张荒诞的想象力创造一个奇异的世界,以此来解构现实的经验与事实。七等生的超验叙事体现在对故事环境的夸张刻画和故事情节的离奇构思。
一场奇异的暴雨让城市陷入了混乱, 也打破了李龙第的日常生活轨迹, 他的处境从社会边缘一跃跨上舞台的中心。 七等生首先为李龙第构造一个虚拟的超现实场景:“他用雨伞抵着那万斤的雨水冲奔回到戏院的廊下, 仍然站在人丛前面”“李龙第重回到倾斜着豪雨的街道来, 天空仿佛决裂的堤奔腾出万钧的水量落在这个城市”[1]。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出现“万斤的雨水”“万钧的水量”,这些场景只能出现在作者的超验想象之中。这个超验的想象寓言世界,从更深层次说就是李龙第的理想世界。 洪水具有毁灭与创建的双重意蕴——旧的被毁灭, 新的得以创生。 因为时空与环境改变, 人的行为也必须重新界定,“无论如何, 这一条鸿沟使我感觉我不再是你具体的丈夫,除非有一刻,这个鸿沟消除了,我才可能返回给你”[1]。洪灾到来之后,李龙第认为不该再纠结于过去的关系,而应该在现况中重新抉择,担负起此刻的责任。
弗洛伊德认为人之所以会幻想, 是因为现实中有无法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都是对现实的补偿。作家与梦幻者都在自我捏造的世界中实现愿望,获得满足。 王幼华在《失神》的序言中写道:“许多作家都曾有受到创伤或与人群隔绝的经历, 在那段时间里,他必须依靠迷离的想象与编造故事,来度过难捱的日子。”[3]纵观七等生的人生遭遇,有着与李龙第相似的边缘、孤绝处境,对“正常”社会的不适应,对社会生活的恐惧与逃避, 从而形成他补偿性的超验想象创作动力。 但是七等生小说中的超验想象只是一种手段,社会现实才是他关注的中心,只不过他不直接触及现实问题, 而是将现实加以改装、 变形再呈现。 七等生将人生场景以一场灾难的形式缩影在城市屋脊之上,在这场灾难中,有“以无比自私和粗野的动作排挤和践踏着别人”的逃生者,也有不愿丧失自己存在的李龙第,“宁愿抱着巨柱与巨柱同亡”。这一场城市洪灾就是现实众生的投射, 异化的世界扭曲人性, 直接导致人产生生存的无意义感与内心的焦灼感。七等生用超验的想象反观现实,舍弃一般表面性的描写,着重挖掘骨子里的精神实质。小说表现台湾社会虚伪和堕落的常态, 浸染20 世纪60 年代暗淡忧郁的色彩。
“洪水过后,李龙第感觉极度疲劳,回到现实世界,他那光荣的幻影立即显示出虚弱不堪的本质。”[4]七等生也意识到浪漫的超验想象自有它的虚妄性与短暂性,理想与现实总是充满剧烈冲突。但即使超验的理想世界像辛德瑞拉的魔法一样具有时效性,七等生也愿意以浪漫的激情进行一次虚幻的理想追寻——借浪漫的激情从孤寂边缘的生活中进行自我救赎的突围。
三、结语
七等生或许可以称为20 世纪台湾文学史上最孤独的行者,他像个长期处于青春期的叛逆青年,在文学创作中始终坚持他的“殊异之性”。 他的小说不但形式怪异、文体奇特,而且相当晦涩难懂。《我爱黑眼珠》一发表,文坛上就出现“毁誉对峙的争执”现象。与其说这是一场论辩,不如说是各自价值观点的呈现,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世界充满着幽默,它是对既成思想的不思索、媚俗的反动,且是作为上帝发笑回声诞生的艺术,它创造了迷人的想象空间,在那里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 每个人都有权被理解”[5]。 七等生以其独特的思维、独特的小说世界,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使我们得以窥见窗外的风景,只不过每个人所看见的风景不尽相同。
现代主义描绘个体在异化的社会之中存在的困境以及困境之中人类的精神苦闷, 而浪漫主义又企图通过理想世界的建构来消解这种生存的无意义感与危机感,以此来释放苦闷。现代与浪漫的交融也是一种冲突, 七等生所代表的20 世纪60 年代台湾知识分子内心挣扎的精神矛盾如实地投影在他的文学世界中。 文学世界里的浪漫主义乌托邦追寻注定是虚幻苍白的, 李龙第注定要从洪水的超验世界中回到现实。 由此,在《我爱黑眼珠》中,既有现代主义对个体或社会沉沦的刻画, 又有浪漫主义对沉沦的反叛与超越。现代主义意识与浪漫主义情怀颉颃互渗,使《我爱黑眼珠》更富有审美情趣与精神张力,给人留下的不再是晦涩抽象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