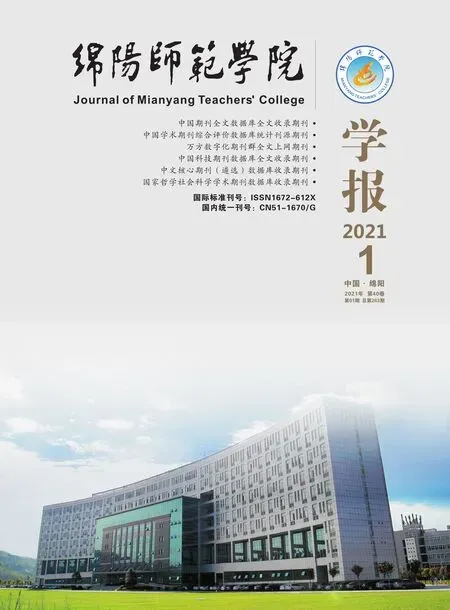流别批评: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方法
2021-12-06方志红
方志红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 464000)
流别批评是中国古代一种非常独特的诗文评方法,它指的是通过对文学现象(包括文体、作家作品、流派等)进行史的回溯,一方面认识文学现象的发展与传承,另一方面在比较中充分认识某一文学现象的根本特征。
一
中国古代的流别批评主要有两类:一是文体流别,二是风格流别。
“流别”一词,最早见于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据《晋书·挚虞传》记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为《流别集》。”又据《隋书·经籍志》著录:“虞有《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文章流别集》与《文章流别志》二书都已散佚,现存《文章流别论》的残篇,主要是关于各种文体性质、源流的论述,挚虞对赋、诗、七发、箴、铭、诔、哀辞、碑等文体的性质、渊源进行了探讨。挚虞所谓的“流别”,为“分门别类”[1]1787和“文章或学术的源流”[2]2178之意,即是对文章体裁的“类聚区分”和对不同文体的性质、源流、特征、风格等的探讨,这就是文体流别。对文体进行溯源式的探讨是六朝的风尚[3]50。拿“赋”这一文体来说,早在挚虞之前,汉代的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就已探究了其渊源、性质: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俗之亚也。
晋代皇甫谧也指出:
自夏殷以前,其文隐没,靡得而详焉。……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
这里都指出了赋这一文体的渊源是《诗》,并在与诗的比较中看出赋的特点。《文章流别论》中挚虞对“赋”的源流与性质的说明正来自他之前的这些论家,不过挚虞之前的论家虽在批评实践中已经使用了文体流别的方法,但在理论上尚未自觉。到挚虞提出“流别”一词并自觉采用这一方法对诗、赋、碑、铭等文体的源流、性质、特征进行探讨时,文体流别的方法才正式形成。之后,李充《翰林论》、谢混《文章流别体》、孔宁《续文章流别》、刘勰《文心雕龙》等,都是就文章体裁而分门别类,比较说明其性质、特征,并溯其源流。文体的流别有利于文学史的细化。如刘勰《文心雕龙》中谈到了34种文体,不但分别叙述了每一种文体的性质、源流,而且还在总体上指出一切文章都源于五经,把五经作为千古文章之祖,奉为写作的楷模。不仅是相当详尽的分体文学史,还可以说是文学史的雏形。
六朝以后,这种批评方法仍然广泛使用,如明胡应麟论小说之渊源云:
小说,子书之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之《本事》、卢瑰之《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
胡应麟采用文体流别的批评方法探究了“小说”这一文体渊源。他认为小说的源头是子书,甚至“近于经”“通于史”。这种说法并不恰当,但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体流别的一个根本特点,即把一切文体的源头都归宗为“经”。这种溯源“往往带有明显的托体自尊的意味”,因为凡一种新文体的产生总是来自民间,要想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就总要“探寻其源,找一个古已有之的说法”,“借古已有之来争得今日的一席之地”[3]53。
至梁代钟嵘,“流别”含义发生了变化,主要不再仅仅寻绎某一文体的源流,而是同时划分同一文体作家作品因风格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派别,追溯其师承源流,这就是风格流别。
钟嵘《诗品》分上、中、下三品品第了自汉到梁的123位五言诗人诗作,同时对其中的36位诗人“一一溯其体之渊源”[4]82,如:
(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李陵)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怨者之流。
(王粲)其源出于李陵。发惆怅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
这里的“其体源出于”“其源出于”等说法就是钟嵘所说的“致流别”(《诗品序》),即指出诗人的师承渊源。从钟嵘所论古诗、李陵、王粲等诗人源出的具体内容上,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从诗人诗体的体貌特征,即我们说的风格来谈的,这是钟嵘的流别法的独特之处。章学诚认为《诗品》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这种“溯流别”的批评方法,他在《文史通义》中说: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所能喻也。
章学诚说的“溯流别”“深从六艺溯流别”就是《诗品》的流别批评方法。曹顺庆先生曾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诗品》的‘深从六艺溯流别’,其实,钟嵘所谓某人诗体源出于某人,着眼点并不在诗的思想内容与文词,而是专门论述风格——‘体’的。”[5]212也就是说钟嵘的流别是风格流别。如上引称李陵诗“凄怨”,王粲诗风“文秀”“惆怅”,在风格上与《楚辞》的惆怅多怨一脉相承,所以说“其源出于《楚辞》”。当然,这里的风格——“体”,和西方侧重于修辞学、语言方式与笔法、技巧的风格不同。它“是诗人透过其作品的多种复杂因素表现出来的”,所以钟嵘的风格流别法,“其具体着眼处或为主题,或为题材,或为技巧,或为语言,不可一概而论”[4]83。
另外,钟嵘《诗品》探讨的是许多诗人诗作的体貌特征及其渊源继承关系,“有渊源继承关系的作家作品,就在诗歌史上形成了流派”[6]179。“文学流派是建安以降才出现的一个文学史实”[7]18,而在理论上最早有文学流派意识的当推钟嵘。钟嵘《诗品》不仅品第了建安以来的123位五言诗人诗作的优劣,还通过古今诗人诗作风格的相互比较,追溯了其中36位五言诗人诗作的风格渊源和诗派流承,形成了《国风》《小雅》《楚辞》三大派别,《国风》《楚辞》两派中又分出不同的支流。如:
《国风》——《古诗》——刘桢——左思
《国风》——曹植——陆机——颜延之——谢超宗、丘灵鞠等七人
《国风》——曹植——谢灵运
《小雅》——阮籍
《楚辞》——李陵——班姬
《楚辞》——李陵——王粲——潘岳——郭璞……[6]550
上述每一支都有不同的风格特点。《诗品》中的流别,除了指对个别作家作品风格渊源的追溯,还指对一定时期作家作品在评析、比较基础上的区分流派。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四云:
诗家相沿,各有流派。盖潘、陆规模于子建,左思步骤于刘桢。而靖节质直,出于应璩之《百一》,盖显然明著者也。则钟参军《诗品》,亦自具眼。
清纪昀《田侯松岩诗序》云:
钟嵘《诗品》阴分三等,各溯根源,是为诗派之滥觞。
这些都指出《诗品》流别批评的流派意识。这样,钟嵘风格流别就不仅着眼于个别作家作品风格的渊源,还着眼于流派风格的渊源,刘明今对这一点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
品藻流别之流别系指作家作品艺术表现风格的流别。“流别”必须建筑在“别”的基础上,先有区别然后能溯其源流,理清其渊源变化。此所谓“别”,不仅是个别作家之别,而主要是有代表意义的类型之别。若无类型概念,一盘散沙,便无从梳理其流别。如颜、谢诗风的不同,便不仅是个人的差异,而代表了不同的流派[3]501。
综上,流别这一诗文评方法即是对文章源流的探寻或派别划分,它的着眼点是文章的特征和风格。它注重的是在历史中考察文学现象(包括文体、作家作品、流派等),在历史发展的前后联系与比较中对文学现象进行衡量与评价,并揭示文学递嬗传承的复杂性。
二
溯流别的诗文评方法是在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这一文化传统包括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和文学传统。
(一)中国古代学术传统
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最重学术源流。流别法最早就是一种学术方法。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等用的都是流别法。《别录》《七略》均佚,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把《七略》“删其要”而来,它就是关于学术源流的叙述,采用的就是流别法。如《诸子略》云: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可以说,中国古代学术最喜好探究源流。这种思想影响到诗文评,就形成了诗文评中的流别法。钟嵘自己也说,他的“致流别”的方法是受刘歆《七略》影响而来。《诗品序》中说: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而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紘既掩,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谅非农歌辕议,敢致流别。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笑谈耳。
这一段中,钟嵘指出了《诗品》中两种重要的批评方法——品第与流别,主要是流别法的使用原因。在钟嵘看来,从汉以来政治上以九品来品选士人,修史者以七略来裁选诸子,都不够准确。而诗歌创作和下棋一样,是可以通过比较来判断高下优劣、分出师承源流的。当时的梁武帝萧衍爱好文学,造诣又深,有才华的文士都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以新体诗为尚,而不顾汉、魏、晋、宋的传统,所以钟嵘大胆采用流别的方法,裁决汉魏以来的诗人,并溯其师承源流,目的在于“辩彰清浊”(《诗品序》),“恢复诗歌的《风》、《骚》‘正体’”[4]356。显然,从钟嵘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诗品》品第的批评方法直接来自班固“九品论人”,流别法则来自刘歆“七略裁士”的学术传统。章学诚也说《诗品》“云某人之诗,其源出于某家之类,最为有本之学,其法出于刘向父子”(《文史通义》卷五《诗话》)。
(二)繁多的文体
流别批评法的产生还和中国古代文体繁多有关。中国古代文章文体很多,如诗、赋、颂、赞、箴、铭、诔、碑、策、论说、书序、奏议等,刘勰《文心雕龙》中就记有34种文体,这和西方文体只分抒情类、叙事类或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很少的几类不同。新的文体不断产生,而每一种新文体产生后,要想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就会去寻一个“古已有之”的正统的源头。前引胡应麟对小说文体的溯源可见一斑。
(三)文学创作上的模拟之风
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中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喜好模拟,有大量的模拟作品。如《诗品上》“古诗”条云“陆机所拟十四首”,指出陆机有模拟古诗所作的《拟行行重行行》《拟今日良宴会》《拟明月何皎皎》《拟青青陵上柏》等十四首诗歌(现存有十二首)。江淹《杂体诗序》云:“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指出江淹有拟作《杂体诗三十首》。江淹的诗作,拟作占现存诗篇的一半,除《杂体诗三十首》外,还有《学魏文帝》《效阮公诗十五首》等。据张伯伟研究,这只是文体上的摹拟,还有从结构、句式、意象、炼字等技巧方面的摹拟,如在句式上,他举:
曹植:“步登北芒坂,遥望洛阳山。”(《送应氏诗》)
刘桢:“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 (《赠徐干》)
阮籍:“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咏怀》)
谢灵运:“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晚出西射唐》)[4]349-351
显然谢、阮、刘的诗句都是对曹的摹拟。
为什么古代的诗文创作中有这样普遍的摹拟现象呢?关于这一点,张伯伟的认识较有说服力。他认为:“文学史上一种新体裁的出现,往往最先来自民间。其后经过文人的雅化而逐步步入正统文学的领地,又有大作家大诗人的出现而形成典范。后人想要对前人有所超越,既然体裁已经确定,就必然要遵循其典范,通过模拟的手段以掌握其技能技巧。”[4]132文学创作上后人对前人从文体到技巧等各方面都加以摹拟,虽然并不一定就能形成相似的风格或成为一派,但文学上相似风格的形成无疑与这种摹拟有关。如上举鲍照,虽有摹拟刘桢的诗作,但与刘桢诗风并不相同,所以钟嵘在《诗品》中致流别时并不将其归入刘桢所属的《国风》一派。阮籍与刘桢、谢灵运都摹拟曹植的句式,故刘、谢可归入曹的《国风》一派,而阮又自为《小雅》一派。
文学创作上的摹拟师古形成文学风格上的相似,这种文学现象引起批评家的关注,就会使用流别法溯其渊源所自,钟嵘《诗品》推“其体源出于”即是此意。叶梦得《石林诗话》也指出了这一现象:
魏晋间人诗,大抵专工一体,如侍宴、从军之类,故后来相与祖习者,亦但因其所长取之耳。谢灵运《拟邺中七子》与江淹《杂拟》是也。梁钟嵘作《诗品》,皆云某人诗出于某人,亦以此。
学术上重视师承源流,文学创作上体裁杂多,喜好摹拟师古,是中国古代学术和文学的传统。这与西方的文学观念大为不同,“西方表现主义注重独创性,刻意求新。亚洲的文学观则是提倡师承前人,墨守传统,以古为法”[8]。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学、学术传统促成了中国特有的流别这一诗文评方法的形成。
中国古代诗文评采用流别批评,其意义有两点:
一是通过梳理某一文学现象的历史渊源,认识文学现象的历史嬗变。如用流别法对“赋”这种文体的探源,除了为其正名,明了其性质特征外,就是认识“赋”这一文体的历史嬗变。这种方法在当代学术上仍有采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采用的其实就是流别法,详细阐明了小说这一文体的来龙去脉、流别师承,使我们能够清楚辨析这一文体的历史嬗变。
二是正本清源,以复古为创新。中国古代的流别批评,无论是文体流别,还是风格流别,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以“经”为本源。刘勰认为“经”是“恒久之至道,不堪之鸿教”,“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文心雕龙·宗经》),所以他把一切文章的源头都归为五经。钟嵘《诗品》中把汉魏五言诗家36人,分别归为诗、骚两派,其目的也在正本清源,以复古为创新。厄尔·迈纳说:“亚洲的文学观是提倡师承前人,墨守传统,以古为法。”其实我们的回归传统,并非“墨守”,而是以复古为创新。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大凡一个时期里,受异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新的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把社会审美风尚引入歧途时,总会有人提出回归传统,在传统中寻找新的文化生长点。齐梁时刘勰、钟嵘提倡发愤抒情,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以至于当代的“国学热”“建设中国话语”等,都是为正民族文化之根本、为文化创新而来的。
三
中国古代诗文评中的流别批评由哪些内容构成呢?关于这一问题,张伯伟的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张伯伟在研究《诗品》中的推源溯流法时指出,钟嵘运用推源溯流法评论诗人时,其完整的评语由三部分构成,即:渊源论——推溯诗人风格的渊源所自;本文论——考察诗人及作品的特色;比较论——在纵横关系中确定某一诗人的地位[4]155。以此为参照,考察中国古代诗文评中的流别批评,可以看出,流别批评基本包括源流论、本体论、比较论三方面内容。
源流论,就是叙述某一文学现象的渊源、流变,即刘勰所谓“原始以表末”(《文心雕龙·序志》)。班固、挚虞谓“赋者,古诗之流也”;胡应麟说“小说,子书之流也”;钟嵘说“其体源出于”。或是追溯某一文体的起源,或是指出某一诗风的渊源,就是源流论。
本体论,就是指出某一文学现象的性质、特征,即刘勰所谓“释名以章义”(《文心雕龙·序志》)。挚虞说:“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指出“赋”这一文体的根本特征是借助于物象的描摹和华丽的言辞来表达情志。钟嵘《诗品》评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所论是刘桢诗歌气度劲逸、超拔脱俗,但文辞少雕琢的风格特点。这些流别批评的内容属于本体论。
比较论,即对某一文学现象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和时代的横向比较,以达到对对象全面准确的把握。如钟嵘《诗品》评陆机“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把陆机的诗歌与刘桢相比,少了刘桢的劲逸之气,与王粲相比,则没有王粲秀丽的文辞。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能够更全面地把握、体味陆机诗歌的风格特点。
仍以挚虞《文章流别论》中对“赋”的论述为例,可以看出挚虞在勘察“赋”这一文体时完整地使用了流别法: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源流论(溯源)
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本体论
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源流论(流变)
《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源流论(析流)、比较论
当然,每一位批评家在使用流别法时,并不一定三者兼备。尤其是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大都是批评家印象的简单表达,象钟嵘、刘勰这样对诗、文进行系统批评论述的著作很少。六朝以后又多以书信、序跋、诗话的形式进行诗文批评,限于篇幅和体例,在使用流别法时也都不可能三方面内容兼备,多数都只是简单叙述源流及风格。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云:“诗有出于《风》者,出于《雅》者,出于《颂》者。屈宋之文,《风》出也;韩柳之诗,《雅》出也;杜子美独能兼之”,就只简单追溯了屈原、宋玉文章源出于《国风》,韩愈、柳宗元的诗歌源出于《小雅》,而杜甫的诗歌则兼源《风》《雅》,至于他们的诗文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风格,并没有进一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