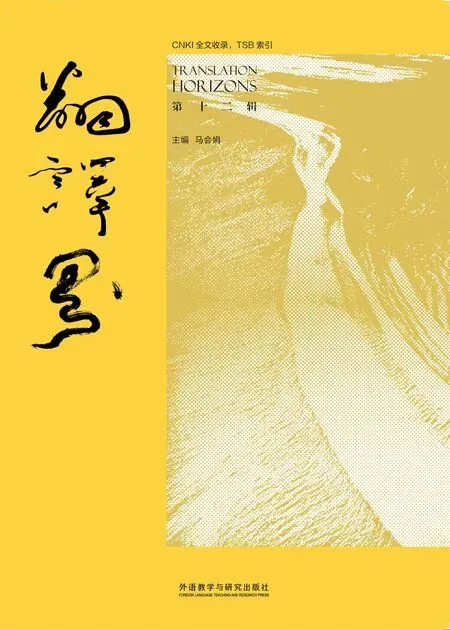从文化翻译的视角看《射雕英雄传》郝玉青英译本的语境化策略*
2021-12-06宋歌
宋 歌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1 引言
2018年2月,英国麦克洛霍斯出版社(MacLehose Press)发行了《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第一卷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A Hero Born,该卷涵盖了原作第一章到第九章的内容。译者为瑞典人郝玉青(Anna Holmwood)。该书上架不到一个月,就在英国亚马逊上荣登畅销书榜单,上架一年就被重印七次,足以见得它在英语世界里非常受欢迎。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武侠小说开始出现英译本(Mok,2001b:93)。在《射雕英雄传》(简称《射雕》)英译本问世之前,只有三部金庸小说被译成英文,它们分别为《鹿鼎记》(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和《书剑恩仇录》(The Book and The Sword)。但这三本书的英译本销量不佳,海外馆藏量少,参与书评的人数也不多,因此并未真正走进英语世界的大众视野(洪捷、李德凤,2015)。
截至2019年7月,中国的期刊文献对金庸小说英译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微观操作层面(谭华,2018)。至于用英语发表的研究,莫锦屏(Olivia Mok)探索了金庸作品的不可译性以及功夫名称和武侠术语的翻译(1993,2001a,2001b),罗永洲(Luo,2007)用实证法探究了译者的翻译策略。然而,这些研究或是绕不开微小的字词翻译,或是一再印证金庸武侠世界对于西方读者的异质性,缺少对多种翻译现象的整合思考和理论探讨。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探讨《射雕》郝玉青译本Legends of the Condor Heroes:A Hero Born在英语世界受欢迎的原因。笔者用两个步骤来回答这一问题:第一,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用描述法系统挖掘《射雕》译本的种种特殊现象和策略,并从“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理论视角做出阐释,指出这些现象的合理性;第二,把“文化翻译”理论置于中国文学英译这一宏大的背景下,将其外化为具体的跨文化翻译机制,以进一步阐释《射雕》英译本成功进入英语世界的多方面动因。
2 本研究的理论视角:文化翻译
金庸的武侠世界展现了中国思想、宗教、历史掌故以及传统习俗和价值观念(Mok,1993),能传达出中国文化的精神(严家炎),建构起武侠世界背后的“文学―文化”生成机制(李泉,2015;Hamm,2004)。因此,武侠文化并非是简单的一招一式,而是一个宏大的意义世界。从这一层面对《射雕》的英译本开展研究,就不能拘泥于对某个词或某个武功招式的翻译,而是将视线拉远,把细节整合。
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 是个关键性的概念工具(Bhabha,1994; Buden & Nowotny, 2009; Mary et al., 2010; Hassan, 2011;Wagner,2014),可用来理解在一系列宽泛语境下的混合效果。它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文化差异。文化差异不容回避或试图减少,需正视处理,还需欣然接受并对其前景化。凡是具有文化接触和协商性质的翻译行为,都可在宽泛意义上称为文化翻译(孙艺风,2016)。文化翻译在文化人类学和后殖民领域里虽有不同的含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不拘泥于“原文—译文”的刻板对应关系,力图在跨文化的协商中充分暴露文化差异,并将这种差异有效地传达给读者。安东尼·皮姆(Pym,2010)认为,文化翻译理论所关注的是一般的文化过程,而非有限的语言产品。从霍米巴巴(Bhabha,1994)的观点来看,文本的跨语言旅行如同人的跨文化流动(migration),是个不断杂合(hybridity)和不断离散(diaspora)的过程。阿萨德(Asad,1986)认为,文化翻译应呈现出他者文化的结构和本质,翻译的过程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改造,以便传达出原作或原文化的意义世界。因此,将文化翻译这一视角运用到本研究中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射雕》英译本种种现象背后的跨文化过程,揭示译者对原作进行重新语境化的努力,解释译作在英语世界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而提炼这一文化翻译的机制,把看似不相关的一系列翻译现象纳入这一共同机制之中,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这些现象,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些理论思考。
文化翻译理论如何在研究分析中具体化并提升可操作性,是本文在理论层面试图开拓的两个方面。其宏观架构实际上是两种相异的文化能够真正互相理解的机制;具体到操作层面,则把不断出现的原文与译文不对应的现象视为文化适应的过程,因语言和接受差异而导致的文化流失反而通过这种不断出现的“不对应”来获得更大、更自由的阐释空间,使得译本以整体的形式来传达原作整体的文化意涵。若干类型的“不对应”现象将基于语境(尤其是文字之外的文化语境)得到阐释和正名,并将全部纳入文化翻译观的视阈之中。在此基础上,本文再对这类跨文化实践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这是本研究的理论思路。
在具体分析翻译现象之前,首先有必要站在西方读者的角度审视《射雕》的文化意涵。小说里体现的中国传统思维、道德架构、江湖规矩、武侠世界等很难在短时间内让普通的西方读者理解。缺少共同的文化经历,外国人很难在不理解中国哲学、佛教、道教的情况下,通过翻译理解其含义。然而译者郝玉青认为,一部作品的文化特质不会在翻译过程中真正成为跨文化理解的障碍,反而有可能让翻译后的作品更加突出,体现出一种可控的独特(王杨,2018)。这就类似于一个人不出国门也能通过阅读来体会和理解异域文化,全靠译者所做的充分语境化或重新语境化的努力,这是两种相异文化进行有效、真实交流的前提。
其次,不同文化间的相通之处往往是跨文化理解的重要突破口,而《射雕》蕴含的普遍性元素无疑提升了其可译性的限度。郝玉青在译本的前言中写道:“虽然很多人认为《射雕》太中国化,但这个故事里的爱、忠诚、荣耀,以及个人对腐败官僚的抗争、对入侵者的抵御,是全世界共通、每一个故事都渴望拥有的”(Holmwood,2018a:I)。她还认为,金庸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人物情感的表现很能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郭靖从小背负金人的杀父之仇,在蒙古成长,在后来的《神雕侠侣》中又要与养育自己的蒙古人对抗。这些元素具有世界性,郭靖所经历的情感也是世界共通的(王杨,2018)。此外,与金庸武侠作品有类似之处的欧洲骑士文学以及现代幻想类作品在西方本来就很受欢迎。美国的瓜尔特兹(Guartzy)网站早在2017年11月17日推广即将发行的译本时,就发文称金庸武侠世界的深度、宽度及创造力和英国作家托尔金(J.R.R.Tolkien)的作品不分伯仲。由此可见,金庸的武侠世界在西方虽然没有对应物,但还是有很多方面可以和西方文学做比较,并可作为跨文化理解的切入点。
显然,《射雕》的文化特质决定了绝对意义上的忠实翻译是不现实的,对大众读者而言更是如此。然而其英译本却受到西方普通读者的欢迎。因此可以推断,译本应当存在一些挣脱原文束缚、具有文化翻译性质的现象。下文就紧随这一思路,寻找“非忠实”的翻译现象,并以文化翻译的分析思路加以阐释。
3 《射雕》英译本五种较为独特的翻译现象
对比译作和原作,本文观察到以下五种现象。现依据“从宏观到微观,从文本外到文本内”的原则分别加以探讨,以期能系统地、由远及近地对研究问题展开分析。
现象1:整合出版三部曲。
此次译本出版计划涵盖《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简称《神雕》)和《倚天屠龙记》三部曲,共12卷。本文所探讨的译本只是第一卷,是总计划的十二分之一。在中文世界里,这三部小说虽说有关联,但后两本完全具有独立和完整的情节,读者大可不读《射雕》而先看《神雕》。然而出版商用12 卷的篇幅囊括这三部书的内容,建构宏大的中国武侠世界的语境,加强这三部书的关联性,从而在用英语建构出来的意义世界中,武侠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能互相注解,互相阐发,不至于最终让《射雕》译本孤零零地躺在与它格格不入的西方世界中。这一现象是翻译中国文学时不常见到的,说明充分语境化中的“语境”可以囊括一本小说的前世今生,提供更丰富的文化背景,创造条件来增强可译性,提升文化翻译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现象2:貌合神离的类比。
无论是在扉页上,还是在宣传推广方面,译本都被称为中国的《指环王》。我们知道,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常常被类比为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本是不足为奇的跨文化策略。但中国的武侠小说在西方根本找不到严格意义的对应物,正如书法一样,其传达的精神世界是传统的、地域感很强的。因此把《射雕》说成是《指环王》实际上是传播考虑胜于文化考虑,是英译中国文学较为独特的现象,值得批判性借鉴。
事实上,《指环王》这句推介语也确实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争议,因为有看过英译本的西方读者认为它和《指环王》完全不同。然而,写这样的推介语也并非译者的本意。郝玉青曾说,出版方了解这是什么类型的书,并且产生兴趣以后,才会进一步去看她准备的材料:金庸的地位、故事的梗概、有哪些共通的价值观可以打动西方读者等(窦元娜,2018)。显然,译者只是把《射雕》和《指环王》做题材上的类比,目的是更好地和出版人沟通,客观上也成为后来出版商的宣传噱头。然而,两者的精神内核迥然相异。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轻言这种类比是一种误解,因为如果拉远视线,我们发现,这种貌合神离的类比能够在一开始就成功地在英语里寻求引人入胜的(虽然是不妥的)文化相关性(cultural relevance),以本地化策略来改变和替换读者本不熟悉的文化特征(Sun,2009),以便抢先抓住西方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而现象1(整合出版三部曲)为读者的沉浸式阅读(immersive reading)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读者完全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消除将《射雕》进行《指环王》化的误解,进而全面进入中国武侠世界。这一现象实则也是《射雕》英译的一大特色,是文化翻译与跨文化接受机制的“诱因”。
现象3:副文本提供大量的文化语境和视觉叙述。
副文本的存在对文学外译而言本也是常见的现象,但笔者发现《射雕》译本里副文本的种类特别丰富,不局限于扼要介绍和译者的前言、后序等,展现出独特的一面。《射雕》译本的正文之前有三篇副文本,之后又有三篇附录。前者除了有一篇惯常的故事简介之外,还有一篇介绍人物关系的短文。这篇短文不似大多文学作品那样画张人物谱系图,而是详述了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武侠家族,如江南七怪和全真七子,采用故事化的方式来介绍人物,这一点在英译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小说里的人物本身是难以让西方读者理解的。从文化翻译角度来看,这种故事性的介绍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译本正文已经在此开篇,因为它小范围地重组了原文故事,从整体上满足了英语读者对进入小说初期的跨文化适应性体验。为了解释清楚“江湖”和“武林”这些概念,在这两篇副文本之外,译者又用叙事口吻加了一篇《写在前面的话》(Prologue)。这篇副文本依然承接前两篇副文本,进一步推进叙事。到了正文第一章的“靖康之耻”时,读者就会感到水到渠成。
译本之后有三个附录,分别为译者对“功夫”“雕”和专有名词的翻译做的注解,并且包含对中国文化的大量解释性文字。可以说,译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语境提供给了读者。这一策略也特别值得“中国文化走出去”借鉴。此外,在注解“狼牙棒”时,译者还用16世纪英国的武器作为类比(Holmwood,2018b),引导读者用自己的已有知识去理解异质他者。附录后面还对即将出版的第二、三、四卷的情节做了简要介绍,延伸了第一卷译本的语境。正文之后的副文本为读者提供了查漏补缺以及语境延伸的机会。综合来看,《射雕》译本里副文本繁多而又层层递进,和正文一起构成一个叙事整体,这一特点是区别于其他文学外译的。
插图作为副文本的一类,也是《射雕》英译本较为特殊的现象。该译本里的插图并非单纯地为了活跃阅读气氛,而是一种视觉上的翻译。证据是几乎所有的图片都是打斗场景,而图片附近的文字亦为武打描写(如Jin,2018:10,91)。我们知道,原文对武打的描写可谓天马行空,用词奇异,中文读者读罢往往深感精彩。但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打话语在跨文化翻译时就会成为挑战。若是完全忠实,亦步亦趋,轻则不知所云,重则闹出笑话。笔者发现,译者对武打的翻译较为节制,选词到位而不浮夸。然而这么做的后果就是,读者本应得到的精彩感受就失去了。绘有武打场面的插图无形中弥补了由跨文化语言转换而丢失的意蕴,和文字描述互为补充,引导读者想象中国武侠的应有场面。因此,多层次的表现对文学翻译而言至关重要(Sun,2012)。插图作为非文字媒介,弥补了文字(译文)作为单一层次表现的局限,时不时地给读者提供视觉参考,成为在翻译中构建完整武侠意义世界的策略之一。施尔顿(Shilton,2013)认为,仅仅靠话语使人深入理解某一文学艺术是不够的,一手经验必不可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插图恰恰为读者提供了关于武侠的一手经验,读者在阅读文字的过程中头脑所产生的画面便可和插图互动,于是译文和插图密不可分(Chan,2012)。显然,这种视觉层面的翻译不是基于特定的文本,其效果是达到跨文化的深入、真实的理解,故可被囊括进文化翻译的范畴。
现象4:结构重整留痕迹。
对原作的部分内容进行不露痕迹地重新分段,本来也是文学外译常见的现象,但《射雕》译本进行结构重整时大多留有痕迹,似乎是在告诉读者读到何时可短暂休息,何时可合书回味。这是该译本的独到之处。
具体来说,译者在每一章都加入了自己的分节,并且分节有两种:带阿拉伯数字的分节和带波浪线的分节。笔者发现,阿拉伯数字部分代表一段完整的情节,而波浪线部分则类似于电影里的一个镜头。这种重整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试图控制读者的阅读节奏,操纵读者脑海中形成的一个个意义群。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看,这种策略有利于读者按照译者的意愿去逐渐建构起小说的意义世界,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对情节、思想或文化的误解,从而按照译者精心设计的跨文化理解的路径来阅读。
结构重整还见于段落的重新划分,尤其是对话部分,更是一句话就列为一段(如Jin,2018:16,61)。严家炎(2004)认为,金庸小说未脱离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结构,并且较多地承继了宋元以来的传统白话文乃至浅近文言的特点。郝玉青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承,有点像《西游记》和《水浒传》(窦元娜,2018)。由此可见,重新分节必然是译者有意为之,其目的是打破阅读习惯的隔阂。
现象5:因剧情而创译的人名。
在人物名称上,《射雕》英译本有很多创造性的译法。比如,杨铁心被译为“Ironheart Yang”,郭啸天被译为“Skyfury Guo”,梅超风为“Cyclone Mei”,等等。但真正属于《射雕》英译特色的是对“黄蓉”一名的英译——“Lotus Huang”(黄莲花)。原文里,郭靖和黄蓉初次见面时,黄蓉是女扮男装,郭靖并不知情。郭靖请教“黄兄弟”的高姓大名时,黄蓉是这样回答的:“我姓黄,单名一个蓉字”(Jin,2018:229)。在英译本中,“黄兄弟”这样回答:“My family name is Huang,my given name Lotus”(Jin,2018:229)(我姓黄,名字是莲花)。随后英文版附加一段描写:
His companion looked at him meaningfully, but Guo Jing did not know what a lotus was and thus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velation (Jin,2018:229)(同伴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但郭靖不知道莲花是什么,因此没有领会到其中深意)。实际上,译者在附录里特别做了一个长注释来解释她的用意。译者写道:“这个角色在许多金庸迷那里是以她的拼音名字Huang Rong 而被熟知的。但我把她的名字译作Lotus,因为在故事的这个阶段,读者正置身于一个郭靖所不知道的秘密之中”(Holmwood,2018b:304)。在英语世界的读者看来,lotus 一望便知是女性的名字,就像“蓉”之于汉语世界的读者一样。所以,在金庸的精心设计下,读者通过姓名提前洞悉了黄蓉乔装的秘密,真正被蒙在鼓里的只有郭靖,而译文恰好还原了这种阅读体验。笔者认为这种翻译策略是可以推广的,尤其是把具有性格特征的中文名翻译为英语时。该策略弃“形”而取“意”,起到偷换文化躯壳以植入文化内核的作用,和文化翻译的终极目的之一——理解真实的异质他者——是一以贯之的,是一种还原文化心理构成的文化翻译。
4 文化翻译视阈下《射雕》郝玉青译本的跨文化机制
上文分析的五种现象,虽然看似各自独立,但都是传递文化差异、充分语境化的举措。这些现象共同在英语世界中重建了“中国传统侠义精神”(洪捷、李德凤,2015:226)。于是,译本不再绝对受制于原作的语言,而呈现出文化翻译的性质。
如果目的语子系统不允许创新的话,那么属于源语文化特质的东西就没法传递(Even-Zohar,1990),而文化特质可能又是《射雕》的最大卖点(王杨,2018)。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原著中的中国特质(Chineseness)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地予以保留(Mok,2001a)。至于如何不惜代价、如何保留、如何传递,笔者认为郝玉青译本的上述五种现象给出了答案:从宏观设计和语境建构方面冲破原文的桎梏,把着眼点放在文化传递层面,从多个维度把原作进行重新语境化,而非因循守旧、亦步亦趋地翻译。在这一过程中,原作虽然被改头换面,但其文化内涵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留。如此,译文才能真正植入目的语文化,而非成为披着目的语外衣的无源之水。
文化翻译为普通读者提供了浸入式的阅读体验。读者一开始感到困难是正常的,毕竟所获得的语境尚不足以支撑书中人物的行为和价值展现,上文分析的五种现象恰到好处地缓解了文化上的直面冲突。随着故事的展开,译者的多种语境化策略渐次登场,读者获得的语境自然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具体,随时会对前面读到的内容进行纠偏或有更加准确的理解。文化翻译的宗旨是使译文以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充分展现文化差异,并带领读者去理解差异,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删减文化专有项的方式来消解和回避差异。译者直言,她在翻译时会在屋里比划武功招数,有了亲身体验,再确定用什么词,以便引导读者沉浸其中,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就抓住、理解或欣赏了差异。莫锦屏也认为,译者应当广泛地改写原作,使译作的语言和篇章精妙到能够捕获原作的意涵、品味和叙述节奏。这样一来,读者才能逐渐“滑入”(steep in)中国传统价值中去(Mok,2001a:7)。此外,译者力求用视觉化的语言来取代注释,这也是文化翻译的应有之义。
文化翻译在《射雕》郝玉青译本里主要由以下五个要素来体现:(1)整合出版三部曲以建构宏大的文化语境,为其他诸要素的效能打下基础;(2)用貌合神离的类比来强化文化关联度,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提供阅读前的吸引力;(3)用副文本(含图像)的叠加与交融来沟通读者和源语文化,并贯穿译作始终,使符际翻译时刻强化着文本层面的翻译效果;(4)重组结构以贴近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也是贯穿译文的策略,避免中西方行文差异造成阅读障碍;(5)用创造性的人名来体现原作人物的性格,让读者易于记忆又能领会作品中人物的文化特征。这五个要素涵盖了宏观和微观、静态和动态、文本和图像、迎合和保真等跨文化沟通的方方面面,以特定的顺序应用于《射雕》译本的不同章节,互相交织,构筑成动态而稳固的内生结构,形成一种跨文化机制,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中水到渠成地了解、理解并欣赏了中国武侠文化。文化翻译不仅能将异质因素带入目标语,而且在译者充分意识到目标语文化差异的情况下,使其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更好地就文化条件开展协商,探索变通的方式来思考和想象隶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群体是什么样的(孙艺风,2016)。这一跨文化机制可在“文化的碰撞”(the encounter of cultures)(Iser,1994:5)之中有效克服“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并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
5 结语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华人世界的共同语,但面对英语读者,它凸显异质性。文化翻译作为一个概念和理论工具,在增强跨文化兼容性的同时,也充分展现异质性。文化翻译试图打破翻译实践中原文—译文的二元对立关系,将译文表达的重心从“忠实于原作”向“语境化原作”的思路转变。
《射雕》郝玉青译本第一卷中五种独特的翻译现象共同指向文化翻译的内核,皆可在文化翻译这一理论视角下得到解释和正名。它们都是原文和译文在意义层面不能对应的例子,只是方式上和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译者通过这些策略将异质性很强的原作成功地送到了英语世界中去,让译本和普通读者发生了有效互动,保障了译本能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的接受。据郝玉青观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正呈现出向好的趋势。她希望《射雕》英译本的成功不是指某一本书卖得好,而是能不断积累影响力,甚至扩展到其他类型,带动其他的中文作品“走出去”(窦元娜,2018)。当然,随着中外交往日益加深,原先被视为异质的东西会逐渐不再异质,但这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翻译观所提供的跨文化策略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