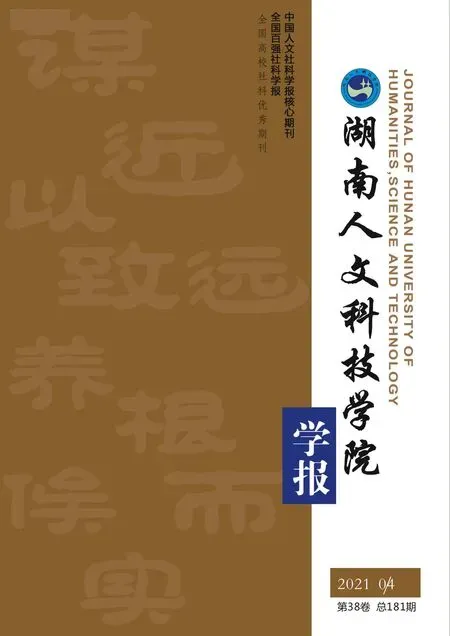唐诗女性题材中的镜子意象解读新探
2021-12-06刘万磊唐志远
刘万磊,唐志远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镜子是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物品。考古学、民俗学、艺术史等学科都从各自领域研究古代铜镜,古典文学对镜子的探讨多在唐传奇、《红楼梦》、意象文化等方面。目前,涉及唐诗中的镜子的研究有专著《唐代铜镜与唐诗》,在铜镜与唐诗的互动参照中欣赏各自美感;部分论文总述镜子意象的文学作用与抒情功能,也涉及到镜子本身制造使用的历史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文化的历史①。有鉴于此,拟以镜子为线索分析唐诗从意象选择到意境建构的中间地带,试图提供一种新的意象探讨思路,从更具体、更细微的层次思考唐诗女性题材中镜子与场景、人物、情节之间的内在关系。
镜子是建构唐诗女性空间与审美意境的重要“编码”:首先,镜子是古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目前出土的汉唐铜镜数量众多、精美绝伦,足见唐镜的世用意义与审美价值,在文本世界中镜子依然发挥着生活物品的实用功能。此外,诗歌中的镜子意象还有一种聚焦作用,照镜动作将文本世界的核心张力集中展现,女性在凝视时的心理意识与身份认同等问题需重点思考。最后,唐诗中的镜子发挥着情节道具的作用,不同诗人都利用镜子表现爱情、政治、社会等内容,突破观念物品(意象)、物与人关系(照镜)等视阈,在人与人的场域(事件)上讨论镜子内涵,应该会有别样意趣。唐诗中镜子的功能不是按照时间先后递进演变的,同一诗人在创作中可能无意识地采用不同方式书写镜子。此处将打乱时代顺序、诗人身份,整合相似的镜子使用策略,希望由此思考唐诗女性题材中更为微观的解读可能。固因鄙陋,未免有过度阐释、以蠡测海之弊,敬请方家指正。
一、实用生活物品与构建女性空间
回到历史原境,镜子是作为一件物品存在于唐代生活,在诗歌创作中镜子的最初作用就在于还原实际生活中使用镜子的真实场景。对唐诗镜子意象的研究,必须要考虑它本身的物质性。唐代铜镜纹饰繁复,种类多样,从铭文出发或可推测当时的使用场合和使用者,涉及爱情主题的镜铭足以暗示它们是家居闺房的实用之镜。隋唐铜镜“乍别情难忍铭莲花镜”形制较小,圆形圆纽莲花瓣纽座,外围有一周环形楷书铭文可释读为“乍别情难忍,久离悲恨深,故留明竟子,持照守贞心”[1]。前两句写相思,后两句表忠贞,当为实际生活中妇女使用之物。唐诗闺怨闺情题材中的镜子内容,或许与此类镜铭有关。作为一种商品,镜子以缠绵的铭文与精美的式样吸引买者;使用者在照镜时必然会注意到镜铭文本并受此影响。
当镜子进入闺房中,它就天然与女性产生联系,同时也成为女性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意义而言,当唐诗中出现镜子意象之时,它是作为一件生活物品,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激起我们对现实中的镜子的特殊记忆。“艺术作品不是镜子,然而它们跟镜子一样,都有那种令人捉摸不定难以言传的变形魔术……再现不一定都是艺术,然而其神秘性却不会因为它不是艺术而减弱。”[2]物象之镜具有一种奇妙的反射能力,再现了镜子物品的物质性,预设了镜子意象的观念性。物象与意象的细微差别在于,物象在文本世界中依旧是一件物品,观念上的物品,而意象则是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其建构诗歌意境的作用而非仅仅表现其物质功用。
在唐代爱情婚姻中,镜子不仅是一件实用物,更是一类富于礼仪作用的象征物。《酉阳杂俎·礼异》载:“夫妇并拜,或共结镜纽。”[3]唐代婚礼有结镜纽之说,虽无法还原具体仪式,但在唐代婚恋中镜子的礼仪功能确不容忽略。唐诗中还有类似的材料,王建《老妇叹镜》首联:“嫁时明镜老犹在,黄金镂画双凤背。”[4]24此诗中的镜子就具有双重内涵,其一是婚礼之镜,镜子作为礼仪物品而被使用;其二是女性之镜,老妇衰老重新照镜,以一件物品反衬自己青春之逝。当初可能是丈夫买来当作聘礼或娘家买来当作嫁妆,女主角因其特殊价值而珍爱有加,“自绣芙蓉带”,将之好好保管。现在,镜子是闺房中的特殊见证,暗示了老妇一生的婚姻轨迹。男女赠物传统由来已久,而唐诗中亦有赠送镜子作为爱情信物的描述。李白《代美人愁镜二首》:“美人赠此盘龙之宝镜,烛我金缕之罗衣……狂风吹却妾心断,玉箸并堕菱花前。”[5]1487在此文本中,镜子依旧作为一件物品出现,以镜子的礼俗功用构建爱情联结,后来在男女情变结局中镜子又丧失了爱情象征意义,重新恢复为一件纯粹的物品,在照镜时默默见证女子在镜前垂泪伤情。宇文所安解读《羽林郎》“贻我青铜镜”句:“一面镜子,在镜子里她能看到自己,就像她被别人看到一样,在镜子里她能看清自己在轻佻挑逗的言词往来和礼物交换之外的身价。”[6]由此可知,镜子就是一件礼物,是一件在男女交往中表达双方爱意又隐含人际规则的物品。不论爱情故事是不是发生在唐代,镜子多有特殊奇异之处,超越了一般的爱情信物②。镜子表现对女性容貌的赞赏与珍重,也寓意婚恋礼俗性质,它似乎将单纯相恋的情欲冲动转化为一种婚姻与责任的礼节邀请。就诗歌故事的开始而言,镜子是一件合乎道德与人情的客观物品与观念象征。
在诗歌文本中,镜子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再现一个包含女性物品的女性空间,同时确认和肯定该诗歌空间中的女性角色。镜子是一件闺房之物,暗示了拥有者的性别。韩偓《北齐》:“几千奁镜成楼柱,六十间云号殿廊。”[7]这是一首咏史诗,与女性题材相去甚远,但是诗中所写的建筑结构却十分巧妙,可以帮助理解镜子这一内涵。君主多情好色,贪图玩乐,几千块镜子仿佛搭建了一个充满欲望美色的建筑物,这是一个女性空间(虽然建筑的主人是一位君王),在镜子制造的建筑空间中美女如云。《北齐书·幼主纪》记载皇帝大兴土木,营造镜殿等众多宫室,镜子寓意其琳琅满目的奢靡景象。诗人正是用镜子表现君主对女性的欲望与迷恋。就文本结构而言,镜子意象虽未真的搭建出一座镜楼,却异曲同工地暗示了一个镜像般的女性空间。与之类似,王建《宫词》:“小随阿姊学吹笙,见好君王赐与名。夜拂玉床朝把镜,黄金殿外不教行。”[4]616学吹笙、被赐名两件事已经暗示了主人公的性别,即宫中侍女。朝把镜这一动作更是直接点明其女性身份,如果将镜子换成其他东西如剑、书等,诗中角色的性别就会显得含糊不定。在此处,镜子不发挥其他作用,只是担任一个典型的性别指示符号。第四句“黄金殿外不教行”仿佛又是在说一个文本世界中的建筑空间,用一间宫殿将女性锁住,形成一个权力专制的特殊场所,而镜子正是这个空间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空间建构与身份确立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到一类特殊的诗歌——挽诗。它们针对女性而作,其中有不少都使用了镜子意象。在这样的文本世界中,女性角色固然是中心投射的焦点,但不论是在文本中还是在现实中她们都已消亡逝去,镜子暗示的人物对象实际上是一段关于女性的象征与追忆。沈佺期《章怀太子靖妃挽词》《天官崔侍郎夫人卢氏挽歌》、顾况《义川公主挽词》都是社会应酬之作,所谓“埋镜”“鸾镜阴”等字样只是简单地将镜子比拟为女性,暗示伤逝,表达含蓄,这些用法是基于人际交往与社会规范中最基本的礼仪要求,因为文本人物与作者无关,故此类诗歌亦鲜有感染力。相比而言,宋之问《伤曹娘》的艺术效果更为精巧,前两联为:“凤飞楼伎绝,鸾死镜台空。独怜脂粉气,犹著舞衣中。”[8]鸾死,与凤飞对应,又合于鸾镜之谓,更进一步而言,铜镜多鸾鸟式样,鸾鸟已死则铜镜空白无纹,进而呼应“镜台空”一语。此处之镜是以自身物质性存在暗示使用者肉体性的不存在,它维持了这个空荡无人、摇摇欲坠的女性空间的继续运行。在文本创造的观念世界中,镜子是逝去女性的替代物,在某种情况下它可以再现和维持原本女人在这个闺房空间中的存在。睹物思人,正是此意。需要明确的是,镜子在失去它的使用者亦即那位女主人的时候,已经丧失了它的本质意义,无人照镜则镜子亦无用,镜子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已经消亡。鱼玄机《代人悼亡》言:“珠归龙窟知谁见?镜在鸾飞(台)话向谁?”[9]睹影而哀鸣,丧偶再难见,这是对于生命的终极追问与无限悲伤。使用者已然不在,镜子虽在原处也不再发挥实用功能。
此外,诗歌中还存在反向建构女性空间的特殊情况。许浑《题舒女庙》:“妆镜尚疑山月满,寝屏犹认野花繁。”另一首《题义女亭》云:“四望月沉疑掩镜,两檐花动认收屏。”[10]舒女庙和义女亭,都是属于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建筑,不同于典型的闺房空间,它们本身都消解了性别属性而强化了社会属性。《庵上坊》云:“一座贞节牌坊就不再是一位妇女的传记,也不是她个人的纪念碑,而是炫耀家族势力的舞台。”[11]不论是神女庙、烈女亭、贞女坊,这些建筑本质上都不是在宣扬纯粹的女性之美。它们表现的是社会道德对古代女性的“期待”。然而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个实际存在的建筑空间中用虚拟的镜子与屏风意象试图建构一个文本中想象的女性空间。面对模式化道德表彰建筑,作者刻意幻想当时她们照镜子、用屏风等生活场景,突出她们身上的女性特质。两首诗技巧相似,都将自然中的月色与野花比喻为闺房中的镜子和屏风,这样一来空间与场景得到了置换,从公共领域转到私密领域。镜子意象再一次发挥作用,打造出一个可以指示性别身份的文本世界。在那个虚拟的女性空间中,女性之美大于女性之德,成为诗意之所在。
二、美人照镜动作与人物缺席影响
孤立物品需要与人物发生互动才会产生意义,此时照镜动作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当不再仅仅满足于再现与暗示时,照镜行为使得这个女性空间充满生机,在女主人注视镜子的一瞬间,人物特质与情感心理得以彰显。巫鸿《中国绘画的女性空间》分析:“‘正背式’构图使《女史箴图》的画家得以创造出独立的女性空间,其中的女性人物通过镜像与其自身发生互动。”[12]传为顾恺之创作的《女史箴图》有一个片段“饰容”,画面女性背对观众,只有镜子中反射出人物的容貌,随后该人物被描绘为正面形象,然而镜子却又只能显露其背后纹饰。此图不属唐代,其照镜构图的核心理念却值得思考——镜子正反两面关系、照镜修饰容貌作用、照镜与观看照镜问题。镜子是一体两面的,镜背本身的铭文与图样看似与照镜的功能无关,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吸引和塑造了照镜者。在大多数诗歌中,镜子背面基本处于隐藏潜在的状态,我们更多地是在关注镜子的照射功能,镜子正面在照镜的瞬间真正“开启”。对于普通人而言,正衣冠、饰容貌就是镜子的价值所在。
李商隐《无题》诗亦涉及镜子与照镜。“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13]作者讲述了一位女子的成长历程。首句便是八岁照镜这一阶段,他略去之前童稚时期的种种表现而仅仅抓取这一动作,意在说明女孩偷偷照镜子之时她自身的审美意识开始觉醒,她对自身生命的关照有其特殊意义。就常理而言,因其性别意识还不突出,稚幼儿童男女混养。然而等到一定阶段,譬如李商隐所言照镜之八岁,女子需要与男性隔离开,仿佛进入了一个特定且特殊的成长轨迹,从一个孩童变为一个女孩再长成女人。叶嘉莹分析:“从古代的《诗经》到《礼记》,照镜是对自身的反省。到唐代的诗人演化成女子之爱美,女子之爱美是对美的追求……‘簪花照镜’是你自己对于你自己美的认识和肯定。”[14]镜子,就是审美爱美的外在肯定,相当于一个无言的赞赏者。他人可以用语言等互动因素主观地肯定女子的美丽,镜子也可以通过映照功能客观地反映女子的容貌,进而给予照镜者以肯定。在照镜子的过程中,女子发现自己的美丽,整饰自己的妆容。白居易《简简吟》是一首挽诗,同样截取了那个女孩短暂一生中最典型的画面:“十一把镜学点妆,十二抽针能绣裳。十三行坐事调品,不肯迷头白地藏。……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15]698在女子生命中最美好的瞬间,一切戛然而止,反衬出简简十三岁夭折的不幸事实。即使作者再怎么劝慰开导,说她为天上的谪仙人而归期已到便回天界,人们总不能轻易释怀,早夭是令人扼腕叹息的。镜子意象再一次成为了女性之美的“物证”,不是简单地说明文本世界中的女性身份,更是要照耀出人物身上的生命亮点。
青春时候,镜子映照和肯定使用者的容貌;韶华不在,镜子又激起照镜者白发衰鬓的哀叹。沈佺期《和杜麟台元志春情》有句:“青春坐南移,白日忽西匿。蛾眉返清镜,闺中不相识。”[16]悲莫悲兮伤美人之迟暮。美人窥镜自叹,以至于仿佛对面不相识。人的相貌具有稳定性,即使表情改变年岁渐长,还是可以依稀辨认,之所以故作不相识,正是因为照镜者认出了自己及青春容貌的衰老变易,后者才是悲伤喟叹、故作不识的原因。
不论男女,都有镜中衰鬓之累。对于女子而言,她们选择罢镜不看。“十年不开一片铁,长向暗中梳白发。”(《老妇叹镜》王建)或许在现实中,基于各种因素不得不“对镜贴花黄”,但是在观念中幻想罢镜,确实可以给人以“自欺欺人”的慰藉,人们可以借此逃避衰老这一事实。对于男子,他们一方面宣扬女子在德不在容,一方面又在介意自身的容颜青春,甚至是感慨自己的“可怜白发生”。白居易《叹老三首》表现的是一种超越了男女性别的人类共同关心的衰老问题。不是长生不死,不是死后成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关注的是容颜易变,所以白居易说:“万病皆可治,唯无治老药。”[15]517古人言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就是一种不老药,然而人们在转向追求精神品德、超越生命大限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回视与伤感肉体容颜的衰老。袁枚《随园诗话》议论说:“是镜有恩于女子,有怨于老翁也。”[17]此言差矣,他并未看到美人迟暮之悲哀。在古代,男子犹可建功业得美名,女子惟有罢镜悲白发。诗歌中的镜子,对于女性角色而言,具有肯定与否定的双向作用。当她青春年少之时,镜子照耀着她自身的美丽;当她年老渐衰,镜中之我容颜不再却又给予悲哀伤感。
女为悦己者容,没有爱人在场,镜子对于女子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当然,女子可以为自己而妆扮,自美其美,但在唐诗的语境中,她们更多是为了身处异地的丈夫而相思悲怨,这或许也跟创作者大多为男性有关。曹邺有一首组诗《四怨三愁五情诗》,其一怨为:“美人如新花,许嫁还独守。岂无青铜镜,终日自疑丑。”[18]美人因为不受丈夫宠爱,而对自身容貌产生质疑,其实她质疑的不是自己的美丑,而是丈夫的有情与否。从这个角度而言,即使诗中女子在镜子中获得了自我审美的肯定与生命价值的觉醒,她们也会因为爱情幸福与否而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
镜子只是作为这种情感转变的见证与暗示。在物与人的关系中,人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金圣叹点评《西厢记·寺警》引斫山之言:“美人于镜中照影, 虽云看自, 实是看他……”[19]他者不出现在镜子影像中,却对镜子与女子的互动产生关键影响。王昌龄《朝来曲》云:“月昃鸣珂动,花怜绣户春。盘龙玉台镜,唯待画眉人。”[20]在一个典型的女性闺房空间中,镜子成为了一个视觉焦点,却因为缺乏与之对应的使用者而失去实用价值。作者只是指出缺少画眉人这一客观事实,不言缺席原因而留给读者猜测想象。此处用张敞画眉的典故,男子为女子画眉以示恩爱,画眉之乐即在于此,女子因丈夫不在身边而无人画眉,自然对妆扮一事毫不上心。古之贵人出行,马配玉饰而鸣珂作响,女子月夜独闻路过显贵的车马声,遂念自家男子未能鸣珂而归,颇有“悔教夫婿觅封侯”之意,又有“过尽千帆皆不是”之感。惟有铜镜相伴,空照镜,自相思。李频《春闺怨》云:“红妆女儿灯下羞,画眉夫婿陇西头。自怨愁容长照镜,悔教征戍觅封侯。”[21]这首诗直接说明了画眉人为男子,是典型的闺怨题材。女子闺怨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男性的缺席,闺怨诗可以和边塞诗结合,因为男子不在闺房而在边塞,视角的相互转化以及代言体的运用都可以从另一面暗示闺房或边塞的情况。
镜子是一个见证者,见证了闺房中一个缺席之人对于一个在场的人的深刻影响③。梁锽《名姝咏》云:“怕重愁拈镜,怜轻喜曳罗。”《艳女词》云:“自爱频开镜,时羞欲掩扉。”《代征人妻喜夫还》云:“千日废台还挂镜,数年尘面再新妆。”[22]通过这些诗句,可以勾勒出一个女性的爱情轨迹,镜子还是那个客观的物品,却因为男子的登场与缺席而遭受到了不同的待遇:一开始,女子年纪尚小待字闺中,懒得化妆打扮,镜子重量虽轻却不愿亦不必使用;当男子登场、两人热恋,女子频频照镜,只为照己及照他;在男子缺席的时空片段中,女子愁苦无聊,懒得照镜;当丈夫征戍归来,女子一扫愁容振作起来,重新挂起铜镜照镜梳妆。同样都是罢镜,男子都处于缺席状态,但是其中情感是有差别的。缺席亦有差别:一种是男子未登场,一种是男子不在场(边塞征戍或入京科举),一种是男子不愿在场(抛弃或绝情)。境随人转,女子心境不同,镜子之作用亦不同,诗中营造的情感意境也不尽相同。镜子的使用或弃置乃与人物状态有关。
三、见证情节事件与反映社会生活
镜子可以作为一件实用的物品出现在唐诗中,也可以通过照镜这一动作反映文本故事中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感情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文本事件的一部分,见证或者推动故事的转向与人物的改变。单纯的照镜动作与孤立的人物状态无法构成事件,有的文本本身就缺乏情节的突变。虽然许多诗歌的叙事与抒情功能的分隔并不明显,然而确实有一些作品将故事交代得更为清楚,在这些文本中,镜子可以成为情节的见证。
王建《失钗怨》与《开池得古钗》共同讲述了一个钗子遗失与得到的故事[5]43,19。两个文本空间中镜子起到了一个节点式的作用:“失钗记”中“镜中乍无失髻样,初起犹疑在床上”,在镜子中,观念时间好像回溯到失钗之前,这是婚恋生活的回顾,某种比钗子更珍贵的东西失而不可得;“得钗记”中“可知将来对夫婿,镜前学梳古时髻”,女子又想象出对镜梳妆的婚后生活,将观念时间向后拓展,结尾亦点出再度失钗的可能性。两则处于不同时空的故事完美串联,镜子见证了得钗与失钗的故事发生。得钗与失钗的循环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也再现了女性婚前婚后人生阶段某些片段。
与之类似,杜牧的两首诗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唐诗中的爱情书写。《破镜》云:“佳人失手镜初分,何日团圆再会君。今朝万里秋风起,山北山南一片云。”[23]715《本事诗·情感》有破镜典故,意指男女离散终因爱情得以再会,也有一些诗人反用其意,如孟郊《去妇》以破镜直言情感破裂。杜牧此诗沿用本意,以镜子破碎比拟男女分离,女子不禁发问何日才能重逢,可是诗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以景结尾,留下遐想,让读者自己去想象故事的最终情节。从文本而言,万里秋风,似乎可以说明两人距离之远,让人顿生绝望,可话锋一转以“一片云”作结,似乎又在暗示两人情真意切至死不渝,最终可以克服困难再度相会,然而彩云易散总不坚固,结局究竟如何是难以论定的,故有余味无穷、联想不尽之意。这首诗是以第三者视角叙述,仿佛有一个“他者”知道这一对恋人的经历,“他者”又将故事转述给读者。这首诗存在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留待众人解读,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自己渴望和预想的结局。《留赠》云:“舞靴应任闲人看,笑脸还须待我开。不用镜前空有泪,蔷薇花谢即归来。”[23]676杜牧此诗则是运用了男性第一视角,根据描述可知文本人物为男子,应为杜牧,这是他自己给一位女子的赠诗。舞靴可以任由他人观看,这一描写恐不符合唐代对于有夫之妇或恋爱女子的社会期待,因此前两句似乎暗示了留赠对象可能是一位舞伎。男主人公对那位女子说,她的笑脸应专属于自己,且安慰她待到落花时节便会归来。此处男子为叙述者,但是话语对象和视觉焦点依旧集中于那位没有出场的女子身上,当读者阅读的时候,角色出现了错觉般的置换,似乎自己成为了“收信人”,读者的感受正好与故事中隐处的看诗女子的心理相通。
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文本人物与实际作者的性别错置。具体来说,当作者为男性的时候,故事主角可能为女性(代言),或是代替女子作闺音表现女子的态度情感,如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或是模拟女子口吻叙说自己的隐晦态度,如张籍《节妇吟》;还有的情况是故事人物与创作者的性别保持一致,不存在性别错置问题,如杜牧《留赠》、鱼玄机《重阳阻雨》。造成此复杂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深究,或与自《离骚》以来的君臣美人传统有关,又可能与古代女性缺乏文学教育、丧失文化话语权有关。李白《自代内赠》有句:“妾如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窥镜不自识,别多憔悴深。安得秦吉了,为人道寸心。”[5]1491如果忽略作者身份,这一首典型的代言诗,将夫妇分离之后女子的相思与纠结刻画得入门三分。井底之桃,纵有千般美丽更与何人说;天上之月,总不肯回首垂怜闺房;又以禽言代替人言,道出不尽哀愁。然而,“自代内赠”意味着这是一首李白模拟内人口吻写给自己的诗歌,文本中更是以女子身份寄给那个如明月般的男子,亦即自己,如此一来,这首诗的人物逻辑关系就显得十分特殊。作者、故事主角、预设读者,都是一个人,圆圈式的逻辑链条最终回归到原点。荡开一笔而言,既然作者对于自己内人的相思憔悴状态了解得如此之深,为什么他还不肯“回首相照”?这究竟是因为李白自我表白功名重于家庭的大丈夫心志还是缘于其它创作动机,当可追问之。此诗与《秋浦寄内》一篇写法各异,别有趣味,参读或有新收获。钱锺书言:“己思人思己,己见人见己,亦犹甲镜摄乙镜,而乙镜复摄甲镜之摄乙镜交互以为层累也。”[24]这种反复折射的模式,正是镜子隐含的一种表现可能。《代自内赠》可以算作这种层累的、反复的多重镜像,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心理态势在想象与虚拟中分作两边相互应和。
超越文本故事本身,唐诗女性题材还可以表现闺怨离情、君臣关系等内容,也有不少涉及镜子意象的诗歌亦可以折射当时社会民俗等方面的若干史实。唐代婚礼有催妆诗:贾岛《友人婚杨氏催妆》云:“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阳台近镜台。”[25]诗中表现了镜子在婚礼仪式中的运用,在亲迎礼中男方唱催妆诗,意在催促新娘换妆,尽快接到新娘回家成亲。这首诗以镜台与阳台巧妙对举,充满调笑与趣味,此处的镜台只是一个文本意象而已,新娘未必还在镜子前梳妆打扮,但在催妆的实际环节中,镜子等闺房物品是必然存在的。在这种婚礼习俗中,镜子起到礼仪作用和实用效果,同时它又被写入诗歌成为一种意象,镜子意象继续在文本世界中发挥作用,同时又再次“折射”回唐代婚恋风俗现实。
镜听习俗说明了唐代生活中镜子之于女性的又一作用:求疑占卜。王建《镜听词》云:“重重摩挲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可中三日得相见,重绣锦囊磨镜面。”[4]77诗中相对完整描绘了一位妻子利用镜子占卜丈夫归期的故事场景,她小心翼翼,虔诚笃信,最后占得一个归来好结果而欢喜,开始收拾房间准备迎接丈夫。至于最终占卜应验与否,诗中并未交待。李廓《镜听词》曰:“铜片铜片如有灵,愿照得见行人千里形。”[26]语言似乎更加质朴通俗,期待铜镜带有灵性神力,可以保佑丈夫早日安全归来。简单来说,唐代普通妇女的民间信仰是简单的、生活化的,她们相信万物有灵论,在除夕的晚上,在灶台前举行仪式,企图赋予镜子以神奇的力量,并以此占卜,这种信仰活动足以慰藉人们空虚的心灵,镜子成为了一种精神寄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镜听词可以视为唐诗女性题材的一种类型,那么与其它诗歌不同的是,此处所描绘的女性人物具有主动性:对于当下生活,她们渴望改变、渴望预知,最终的结果可能并没有因为自身的行为活动而受到影响,但是她们不再是传统闺怨诗中徒劳哀怨消极等待的思妇怨妇了。她们赋予镜子以魔力,反过来镜子也给她们以勇气。此外,唐传奇中曾言镜子之奇异,哲学宗教中亦用镜子取譬说法,内容驳杂,留待他论。总之,在唐代镜子成为了一件特殊的物品,在诸多领域都可见其影响力。
四、余论
此处对唐诗女性题材镜子意象有所讨论。从微观角度细分、细化、细读文本中的结构层次与逻辑关系有助于理解诗歌中的人物情感与文本脉络,涵咏体会自然会对诗歌意境有更深的认识。从文本内部的单独物品、物品与人、人与人三个角度以及文本之外的作者、读者及社会生活等更大维度来看,镜子可谓是解读唐诗女性题材的一把“钥匙”。首先,它是一件生活用具与礼俗物品,进入到诗歌文本世界后依旧保持其实用与礼仪功能,并参与构建女性空间、确认角色性别。其次,文学加工赋予了镜子更多的文本功能,照镜瞬间物与人的关系得到了最强力的聚焦,现实之我得到镜像之我的肯定,镜子在使用过程中也凸显了人物存在的本质意义。与此同时,在唐诗女性题材中,男性大多处于缺席状态却依旧能够影响镜子、女子以及故事。此外,除了故事内部的情节事件分析,诗歌还具备超越文本的解读可能,镜子可以反映当时习俗、文化等社会内容。
这是一次新的文学解读尝试,从现实中的物品到文本中的物品,从肯定自信的照镜动作到婚恋故事的见证道具,从故事主角与实际作者的性别错位到镜子诗歌背后反映的社会文化,文本内外贯通分析,而不是简单化平面化地讨论意象的分类特点。总之,镜子意象的再解读可以提供感知诗歌意境与情感内涵的新路径。至于剑、酒,花、月等其它意象是否也可以沿着这一条路径出入文本内外,则又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王纲怀,孙克让:《唐代铜镜与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李海燕:《唐诗中的镜子意象研究》,暨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王彬:《唐人“咏镜”之风研究》,北方民族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此外还有不少期刊论文讨论唐诗镜子意象。览镜诗亦是一重点,偏向男子化、文人化的览镜行为,可参看衣若芬:《自我的凝视:白居易的写真诗与对镜诗》,《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侯体健:《幻象与真我:宋代览镜诗与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文艺研究》2020年第8期等。
② 镜子有辟邪魔力,已成民俗共识,详见相关著述。女子出嫁时身带镜子,或有辟邪保护之考量。此点承鄢嫣老师赐正。
③ 李溪分析绘画中的屏风对镜:“屏风背后的对镜/影自怜,表面上看只是女子个人心境的一个展露——她此刻凝视着自我。可是,在这个不为外人所见的空间中,她注视到的恰恰是外人眼中的自我。在这个最为封闭的环境内部,她依然无法只关注自己的内心。她们的身体,作为一个对象,借助于她们自己的眼睛,最终成为画面外部的男性视觉世界中的一件物品。”(李溪《内外之间: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此论或可参考,女性照镜,名为照己,实为照他,这是古代性别权力话语的特殊反映。在古代,男性创作的诗词绘画中表现的女子照镜内容正好说明了男性凝视是一种占有的欲望表达与权力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