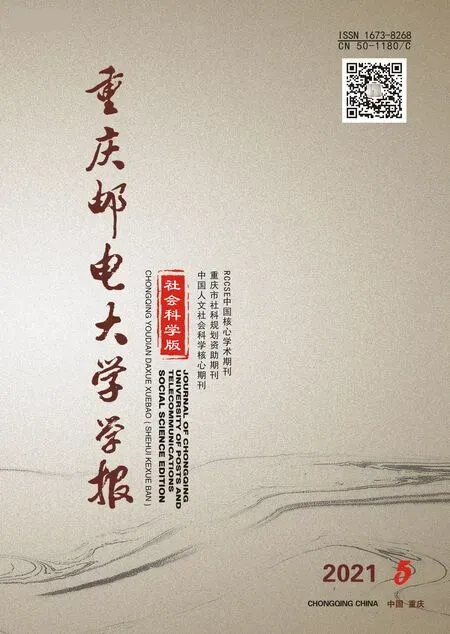视角·结构·策略*
——从《鬼作家》到《退场的鬼魂》叙事的承袭与嬗变
2021-12-05张媛,刘芬
张 媛,刘 芬
(1.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2.武汉工商学院 经济与商务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一直是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的热点,中国学界关于其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研究论文汗牛充栋,杨金才、朱云在《中国菲利普·罗斯研究现状论析》中对此进行过全景式扫描并高屋建瓴地展开分析、指出方向[1]。仅从叙事学研究角度粗略统计,对菲利普·罗斯作品展开研究的论文就达30余篇(1)截至2021年7月9日,关于菲利普·罗斯作品的叙事学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以“菲利普·罗斯”含“叙事”搜索共计37篇。。纵观菲利普·罗斯的作品,其叙事技巧既有承袭也有嬗变,这在他最负盛名的九部“祖克曼系列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2)“祖克曼系列小说”共九部,分别是:《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1979)、《解放了的祖克曼》(Zuckerman Unbound,1981)、《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1983)、《布拉格狂欢》(Prague Orgy,1985)、《反生活》(The Counter life,1986)、《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1997)、《我嫁给了一位共产党人》(I Married a Communist,1998)、《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2000))以及《退场的鬼魂》(Exit Ghost,2007)。。自1979年发表《鬼作家》(TheGhostWriter,或译作《幽灵作家》)到2007年出版《退场的鬼魂》(ExitGhost,又译为《鬼退场》),“祖克曼系列小说”完整再现了菲利普·罗斯叙事技巧的流变过程。
《鬼作家》作为“祖克曼系列小说”(Zuckerman series)的开篇之作,而《退场的鬼魂》作为其收官之作,两者一以贯之,情节设置围绕叙事主体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人生际遇,融合现实书写与文学想象,文本中现实与回忆相互交织折叠,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诸多相似之处,承续关系显著。单就叙事技巧而论,其中的承袭与嬗变轨迹尤为突出。事实上,对《鬼作家》叙事技巧展开研究的论文并不少(3)对《鬼作家》叙述技巧展开研究的论文有刘文松《〈鬼作家〉对〈安妮日记〉的后现代改写与困惑》(《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雷术海《菲利普·罗斯〈幽灵作家〉的元小说特征解读》(《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陈莺《菲利普·罗斯〈鬼作家〉的后现代文本特征研究》(福州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李葆华《〈鬼作家〉中的元小说叙事策略》(《考试周刊》2014年第80期)、崔玲与胡文辉《〈鬼作家〉中的后现代叙事策略及其意义》(《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刘华珺《〈鬼作家〉中的张力分析》(《名作欣赏)》2020年第21期),等等。,而对《退场的鬼魂》叙事技巧展开研究的论文同样不少(4)对《退场的鬼魂》的叙述技巧展开研究的论文有,林莉《论菲利普·罗斯小说〈鬼退场〉的叙事策略》(《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4期)、李俊宇《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析〈退场的鬼魂〉中的元小说艺术手法》(《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陈军《菲利普·罗斯〈鬼退场〉中复杂多变的叙事手法》(《短篇小说(原创版)》2013年第36期)、李丹《菲利普·罗斯〈退场的鬼魂〉写作特色》(《芒种》2015年第6期)、罗建芳《菲利普·罗斯〈鬼退场〉中复杂多变的叙事手法》(《作家》2015年第8期)、韦娅《〈退场的鬼魂〉创作主题和写作特色解析》(《短篇小说(原创版)》2015年第23期),等等。。但对菲利普·罗斯在《鬼作家》问世到《退场的鬼魂》出版30年间叙事技巧的承袭与嬗变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还未见诸期刊或博硕士论文。因此,研究菲利普·罗斯从《鬼作家》到《退场的鬼魂》叙事技巧的流变对作家作品整体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笔者将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策略三个维度对菲利普·罗斯“祖克曼系列”首尾两部作品叙事技巧的承袭与嬗变展开研究,以说明其创作的承启关系及其成熟过程。
一、叙事视角: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
叙事行为的关键在于叙事视角的选取和叙事时空的呈现,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将有助于叙事者叙事意图的传达。叙事视角的选取主要表现在叙事人称上,无论是《鬼作家》还是《退场的鬼魂》,菲利普·罗斯习惯采用回溯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两者间的承袭痕迹明晰可辨。
《鬼作家》开篇点明叙事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
那是二十多年以前……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天快要黑的时候,我到了这个伟人的隐居处去见他。[2]3
《退场的鬼魂》开篇同样如此:
我离开纽约已经有十一个年头……过去的十一年里,我一个人住在内地的一条土路边的一所小房子里。[3]3-4
“祖克曼系列”的开篇之作与收官之作都立足于主人公祖克曼出现在读者视野的当下时间“现在”,菲利普·罗斯擅长以回溯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展现现实生活与回首往昔岁月,在“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叙事中展开故事,以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很明显,《鬼作家》《退场的鬼魂》的回溯性叙事在叙事视角上存在明晰的继承关系。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菲利普·罗斯在叙事视角的承袭中显示出了同中有异的叙事变化。
通常意义上,人们把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称为“个性化视角”,把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称为“全知叙事”。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在《理解文学要素——它的形式、技巧、文化习规》中指出:“与第三人称叙事相对照,第一人称叙事通常标志着个性化的视角。全知叙事者一般采用第三人称代词来指涉人物,以强调人物的不同存在;而第一人称指涉则将故事中的人物与叙事者合为一体。”[4]对“故事中的人物与叙事者合为一体”的情况,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提出了更为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叙事者在叙事中只能以第一人称存在”,并将第一人称叙事者的情况做了精细划分:“一是叙事者为叙事的主人公,一是叙事者只起次要作用,可以说始终扮演观察者和见证人的角色。”[5]171-172申丹对于回溯的第一人称视角也有明确的论述:“在第一人称回顾往事的叙事中,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为叙事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6]187赵毅衡使用“二我差”这一概念对第一人称回顾往事做划分:当一个叙事者“此我”在讲述自己的往昔时,既可以用“昔我”也可以用“此我”的语言,既可以表现“昔我”也可以表现“此我”的意识、经验、判断[7]。对此,胡亚敏在《叙事学》中将其划分为“视角”与“声音”:“视角研究谁看的问题,即谁在观察故事,声音研究谁说的问题,指叙述者传达给读者的语言,视角不是传达,只是传达的依据。”[8]
在《鬼作家》中,以第一人称叙事者身份出现的祖克曼始终扮演了观察者和见证人的角色,其中的叙事者“我”实际上是一个线索人物,采用“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展开故事,是“此我”用“昔我”的语言讲述“昔我”的故事,其视角是“现在进行时”,声音却是“过去进行时”,“视角”与“声音”是不一致的。在《鬼作家》的四个章节中,其中的“大师”“冤家命定”“嫁给了托尔斯泰”三个章节都围绕E.I.洛诺夫与艾米·贝莱特而展开,我只是担任“观察者和见证人的角色”,而且是用20多年前年仅23岁的青年人的眼光进行观察和见证;即使在“内森·代达罗斯”一章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也是用23岁的我的“视角”展开。在“祖克曼系列”的另外两部小说《美国牧歌》和《人性的污秽》中,菲利普·罗斯沿袭了这种写法,“我”(祖克曼)只是小说的叙述者和小说中主要人物的观察者,而非主要人物,“我”作为公开的叙述者主导叙事进程,“祖克曼系列”叙事的承袭可见一斑。
而在《退场的鬼魂》中,以第一人称叙事者身份出现的祖克曼则是叙事的主人公,其中的叙事者“我”采用的是“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是“此我”用“此我”的语言讲述“此我”与“昔我”的故事,视角是“现在进行时”,声音也是“现在进行时”,“视角”与“声音”是一致的。这是《退场的鬼魂》对《鬼作家》叙事视角继承中发生的嬗变。依据赵毅衡先生的观点,该种现象在所有成熟的“自我叙述”(homodiegesis)中普遍存在[7],但其反思意义更加凸显。在《退场的鬼魂》五个章节中,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既是故事展开的线索,也始终是故事的主人公,祖克曼无论是描写现实还是回顾往事,都是采用“现在进行时”(包括“历史现在时”)展开故事,“此时此刻”如此,“心猿意马”“艾米的大脑”“我的大脑”“莽撞的时刻”同样如此。现在与过去、实际与幻觉、真实与想象、主人公与叙事者、作者,“视角”与“声音”都是采用“现在进行时”。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鬼作家》《退场的鬼魂》表面上均采用回溯的第一人称视角,但实质上《退场的鬼魂》比《鬼作家》艺术技巧更为成熟。我们都知道,第一人称是所谓“内聚焦叙事”(也有的将其称为“间接化叙事”)。采用这种叙事方式,一方面拉近了叙事者和读者的心理距离,正如论者所言,“由于第一人称叙述者内森·祖克曼是小说人物,他在观察的范围、感情态度、可靠性等诸方面都表现出真实性、可靠性和逼真性的优势”[9]91;另一方面也有其局限,即个人视野限囿带来文本叙事的片面性。《鬼作家》“现在进行时”视角与“过去进行时”声音的分离,无法克服“个人视野限囿带来文本叙事”的局限;而《退场的鬼魂》的叙事视角与叙述声音既是“现在进行时”,也是“历史现在时”,叙事视角与叙述声音的一致,使作者在叙事时游刃有余,类似于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将三个叙事主体(主人公、叙事者、作者)集于一身,既是“第一人称的叙事”,又往往是“无所不知的叙事者或作者的叙事”,能够自然摆脱个人“视野限囿带来文本叙事”的局限,在带来叙事张力的同时,增加了文本的厚度与深度。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鬼作家》与《退场的鬼魂》的叙事视角虽然表面有承袭,但实质上是包含变异的。同中有异的叙事视角构成不同的表意层面,不同的表意层面搭建起相互补充、相互制衡的叙事空间。从《鬼作家》《退场的鬼魂》采用回溯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可以清晰看出菲利普·罗斯叙事技巧承袭与嬗变的轨迹。
二、叙事结构:框架式结构
叙事行为的关键除了叙事视角的选取外,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叙事时空的呈现。叙事时空呈现的核心是处理叙事的两组时间:“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5]12叙事“时间处理绝不仅仅是严格地按照故事发展的前后顺序安排而不带丝毫的艺术处理和把握”[10],其关键在于本质时间与文学时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叙事结构问题。结构对于文章具有“弥纶一篇”的功能[11]。莫言认为,“结构就是政治”,“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2]。
在西方经典、传统的叙事结构中,处理“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往往采用框架式结构。叙事者(作者)将一部小说的叙事时空限制在较短的时间、较少的空间框架内,通过倒叙、插叙、补叙等手法展现被叙事者(作品主人公)在较长时段、较多空间的活动。简言之,框架式结构就是尽量将被叙事者的故事压缩进极为有限的叙事者的叙事时空内。对此,苏联文艺理论家列·谢·维戈茨基用“本事”(或者“故事”)和“情节”两个概念来表示[13],德国理论家用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对立来表示[5]12,法国叙事学权威热拉尔·热奈特用故事、叙事、叙述三个概念来表示:把“所指”或者叙事内容称作故事(真实或虚构的事件);把“他指”、陈述、话语或文本称作本义的叙事;把生产性叙事行为……把该行为所处的真或假的总情境称作叙述[5]7。中国学者申丹认为,没有可能将叙事和叙述区分开来,“因为读者能接触到的只是叙述话语(即文本)”[6]15,在此基础上,申丹进一步指出,“研究叙事的时间顺序,就是对照事件或时间段在叙述话语中的排列顺序和这些事件或时间段在故事中的接续顺序”[6]14。因此,结构的核心是处理故事时间、叙事时间之间的复杂关系。既涉及故事时间、叙事时间,也涉及叙事者、被叙事者(作品人物)的相互关系。简言之,结构主要处理叙事者的叙事时空与被叙事者故事时空的相互关系。在《鬼作家》《退场的鬼魂》中,菲利普·罗斯都采用了这种框架式结构,具有明显的承袭因素,其脉络清晰可见。
在《鬼作家》中,叙事者将整个故事的时空安排在一个相当紧凑的框架内:时间以青年祖克曼两天的做客经历为线索展开,空间以E.I.洛诺夫的隐居地伯克希尔山为人物活动场所。而在这种有限的叙事时空里,展现了被叙事者“我”(青年祖克曼)在该时段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交代了崭露头角的犹太青年作家祖克曼“我”的成长历程(第二章“内森·代达罗斯”),描写了文学前辈E.I.洛诺夫的日常生活及与妻子霍普、艾米·贝莱特的纠葛(第一章“大师”),叙述了E.I.洛诺夫收留艾米·贝莱特的现在和过去的方方面面(第三章“冤家命定”,第四章“嫁给了托尔斯泰”)。
在《退场的鬼魂》中,叙事者同样将整个故事的时空安排在一个相当紧凑的框架内:时间以“我”(老年祖克曼)重返纽约治病一周之内的际遇作为小说线索展开,空间以泌尿科诊所、杰米·洛根的家、希尔顿酒店的一间房为人物活动场所。在这种有限的叙事时空里展现了被叙事者在该时段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有老年祖克曼现在的生活状态、过往生活和复杂的人生经历,还有其朋友拉里·霍利斯“退场的鬼魂”,艾米·贝莱特1956年后经历的沧桑巨变,杰米·洛根与比利·大卫多夫的恋爱、家庭、过去和现在,理查德·克里曼与杰米·洛根的暧昧关系,理查德·克里曼与艾米·贝莱特及文学前辈E.I.洛诺夫的纠葛,等等。
虽然《鬼作家》《退场的鬼魂》都采用这种框架式结构处理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但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却有简单和复杂之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叙事时间有简单和复杂之别。《鬼作家》的线性叙事框架非常简单,叙事时间非常清楚。第一章“大师”开头为:“那是二十多年以前……十二月的一个下午,天快要黑的时候,我到了这个伟人的隐居处去见他。”[2]3结尾一章“嫁给了托尔斯泰”开头为:“第二天一早我们都在一起吃早饭。”[2]165整个故事限制在“第一天下午”“天快要黑的时候”到“第二天一早”这个框架内。而《退场的鬼魂》线性叙事框架相对复杂,叙事时间也呈现混沌。还是以其开头和结尾一章为例。第一章“此时此刻”开头为:
我离开纽约已经有十一个年头……不过现在我已经往南开了一百三十英里,前往曼哈顿的西奈山医院去看一个泌尿科医生。[3]3
我是在前一天下午到达的。我在希尔顿预订了一间房。[3]13
最后一章“莽撞的时刻”的结尾为:
我逃跑了……我在纽约的历险维持了不足一个礼拜……如今我回到了适合我的住所。[3]231-235
《退场的鬼魂》叙述时间明显不如《鬼作家》简单、清晰,“我”在什么时间到达故事核心事件发生地纽约,又在什么时间宛如南柯梦醒般意兴阑珊离开纽约回到适合“我”的隐居住所,都没有明确的交代和界定,时间线索显得复杂、混沌,这与老年祖克曼的身份是极为吻合的。
其次,故事时间同样有简单和复杂之别。《鬼作家》《退场的鬼魂》都是故事中嵌套故事的作品,由此形成了叙述层次。《鬼作家》的故事时间,通过插叙、倒叙等方式,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泾渭分明。以第二章“内森·代达罗斯”为例:“在这以后,谁能入睡呢……坐在洛诺夫的书桌前,在拍纸簿上吃力地向我父亲……解释……这封信早已该写了。到如今他已等了三个星期了,盼望我在做了对不起伟大的提携者的事以后有一些幡然悔悟的表示。”[2]79明确交代叙事时间,之后直接进入回忆展开“我”的故事:“我们之间的问题处在我把一篇根据家庭纠纷所写的小说原稿交给我的父亲以后”[2]79,插入大段回忆,按时间顺序交代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后“在十一点钟,我听到镇上的雪犁在清扫苹果园土路上的积雪”[2]115时,将回忆拉回到叙事框架的时间线索上。现在——过去——现在,叙事线索清晰可见,是传统而经典的框架结构,但多少显得生涩而幼稚。
《退场的鬼魂》的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水乳交融,现在与过去缠绕交织,显得老道而成熟。我们选取第一章“此时此刻”祖克曼与艾米·贝莱特意外相遇的一段为例,看看晚年菲利普·罗斯在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中的转换,以窥见其叙事技巧的嬗变。
叙事时间用A、B、C、D、E、F表示,故事时间用1、2、3、4、5、6、7、8表示,其具体情况为:
A.第二天,在我离开医生诊所的时候,我已经预约好了翌日一早去做胶原注射。[3]15
B.在泌尿科的下面一层,我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老妇人,我跟着她到麦迪逊广场餐馆。[3]16
C.现在是十点半,艾米·贝莱特和我在餐馆就餐。[3]16
1.1956年我们遇见时,她(艾米·贝莱特)才27岁。[3]17
D.第二天早晨的治疗花了一刻钟时间。[3]17
2.我又一次看见我自己在大学游泳池里来回畅游。[3]17
E.还没有到中午我就已经回到了宾馆。[3]18
3.前一天下午离开餐馆后,我买了初版的六卷本的E.I.洛诺夫短篇小说集带回宾馆。[3]18
4.隔了二三十年没有读洛诺夫的作品,重读E.I.洛诺夫作品发现对他的景仰程度一点也不比上世纪五十年代有所降低。[3]18
5.在E.I.洛诺夫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开始了有艾米·贝莱特伴随,洛诺夫离开伴随了他35年的妻子霍普。[3]19
6.E.I.洛诺夫那5年(1956-1961)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3]19-20
F.到我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这些问题根本没有触及关键所在,洛诺夫51岁到61岁为什么没有能写出一部小说。[3]20-21
7.1956年我与E.I.洛诺夫、霍普、艾米·贝莱特会面。[3]21-22
8.我过了一个小时也离开了,从此再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1961年洛诺夫因白血病亡故。[3]22
叙事时间是到纽约的第二天早晨到次日晚上准备上床睡觉,而故事时间则要追溯到1956年我与E.I.洛诺夫、艾米·贝莱特、霍普的见面。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混杂,现在与过去浑然一体。由于叙事框架的存在,叙事者在横截面中展现被叙事者纵向的过往历史经历时显得非常自然而井然有序,现实的节律与回溯时的时空自然转换为读者接受创造出混沌而需要思索的节奏。在叙事时间的每一个节点上,自然插入祖克曼的回忆与想象,采用符合叙事常规的“顺叙”叙事方式,以“自传性”写作的线性叙事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模式。这既增加了文本的容量和厚重,又不露斧凿痕迹。这有别于《鬼作家》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界限分明,也有别于其倒叙、插叙故事时显露的明晰痕迹。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鬼作家》《退场的鬼魂》在叙事结构上均采用了西方经典的框架结构,存在明晰的继承关系,但《退场的鬼魂》在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中转换自如,作者运用倒叙、插叙、意识流手法如行云流水,与《鬼作家》明显的斧凿痕迹相较,高下立现。
三、叙事策略:虚实相间的后现代小说艺术
除了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上存在明显的承袭与嬗变外,《鬼作家》《退场的鬼魂》在叙事策略上同样存在承袭与嬗变。
从本质上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小说又要追求真实的艺术效果。叙事策略的核心,就是在营造虚构与真实的迷宫时让接受者“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是让读者相信作者叙述的真实性,“出乎其外”是让读者从作者虚构的故事中得到审美享受与艺术熏陶。这牵涉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接受者四方面的因素。菲利普·罗斯采用虚实相间的后现代小说艺术手法,运用显性叙事与隐性叙事两种策略,在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之间混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为接受者营造真假莫辨、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有论者认为“罗斯的小说一直让读者无法分清真实与虚构的界线”[9]93。这种真假莫辨、虚实相间的叙事策略贯穿在“祖克曼系列小说”中,特别是在《鬼作家》《退场的鬼魂》中,其承袭与嬗变的脉络非常清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让接受者无法厘清叙述者与作者真实与虚构的界线。《鬼作家》《退场的鬼魂》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鬼作家》写于1967年,回顾的是23岁的“我”(青年祖克曼)1956年12月一个下午到第二天早晨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退场的鬼魂》写于2004年,展现的是71岁时的“我”(老年祖克曼)2004年在纽约不足一周的生活、生存状态。作者菲利普·罗斯与叙述者“我”(主人公“祖克曼”)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如论者所言:“在祖克曼系列小说中,菲利普·罗斯以个人经历为基础,借祖克曼这个他我表达自我,在有意无意中使现实与创作混为一体。”[14]作者的主体身份为小说主人公的经历提供了可信的背景与素材。此外,两部小说不仅叙述者相同,主要人物如E.I.洛诺夫、霍普、艾米·贝莱特还在两部作品中出现并充当重要的线索人物,《鬼作家》与《退场的鬼魂》之间的承袭有迹可循。
但也应该看到,在营造真实与虚构的迷宫时,《鬼作家》与《退场的鬼魂》的叙事策略在承袭时是有嬗变的。
在《鬼作家》中,“我”(“祖克曼”)只是故事的叙述者和观察者,与作者菲利普·罗斯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在《退场的鬼魂》中,“我”(“祖克曼”)既是叙述者也是主人公,与作者菲利普·罗斯三者几乎融为一体,造成了更加难以厘清的境况。“祖克曼作为罗斯的另一个自我,以第一人称践行着与作家极为相似的人生与职业生涯的方方面面。”[15]1984年,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菲利普·罗斯自认:“我的生活就是从我生活的真实剧情里伪造自传,虚构历史,调制出半想象的生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认为:“一切小说精密地说起来,都是一种自叙传,凡是真批评家都只是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16]这在中外文学历史上大致可以找到佐证,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日本自然主义私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郁达夫、郭沫若的自叙传,都与菲利普·罗斯的多部作品一样,叙述者与作者同一化呈现某种真假难辨、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这一方面拉近了作品与接受者(读者)的距离,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给接受者造成了困惑:叙述者“祖克曼”叙述的事件与作者菲利普·罗斯的生活究竟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某种程度上说,叙述者与作者同一化造成接受者真假难辨的困惑并引起接受者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叙事策略意欲取得的效果之一。
二是让接受者无法厘清叙述本身的真实性与虚构性。在叙述策略上,不仅叙述者与作者同一化造成接受者真假难辨,而且叙述本身的真实性与虚构性,同样使得接受者真假难辨。
艾米·贝莱特是贯穿《鬼作家》《退场的鬼魂》的主人公。在《鬼作家》中,对《安妮·佛兰克的日记》及其作者艾米·贝莱特的后现代改写就是典型。刘文松用“非神圣化”“后现代戏拟”“互文性”“幽默、诙谐的笔调”做过颇有见地的分析[17]。菲利普·罗斯通过祖克曼的偷听,通过艾米·贝莱特的自叙来交代艾米·贝莱特作为《安妮·佛兰克的日记》原作者的离奇经历。但问题在于,一是祖克曼偷听后记下的艾米的话是否绝对真实?换句话说,祖克曼是可靠的叙事者吗?艾米的真实身份是否如小说呈现的意外为祖克曼获悉?二是艾米本人叙述自己为安妮(缺少任何可资佐证的证据)是否绝对真实?艾米的叙述是否真实,祖克曼的记叙又是否真实,作品并未给出确定的答案。而在续貂之作《退场的鬼魂》中,菲利普·罗斯又借艾米之口否定了其先前自认的安妮身份,这使艾米·贝莱特身份之谜愈加扑朔迷离。
在《退场的鬼魂》中,叙述本身的真实性与虚构性又有了新的发展。这在五段真假难辨的戏剧场景中格外明显。国外有学者对此做过分析,认为构成菲利普·罗斯大部分写作的文本与逆文本对自传与虚构故事之间的相互作用做了补充[18]。中国研究者林莉对此也作过分析,她认为五段戏剧场景在叙述人称上发生了变化,从第一人称叙述转变为“他”和“她”之间的对话,在同部作品中出现两种类型的文本,前文本先入为主给读者“真实”的感受,引导并暗示着后文本的虚构,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着元文本的关系。她还认为“实际上在读者看来,两个文本都是虚构的”[9]90。的确,五段剧本式书写具有元小说特征,对“我”的叙述进行补充,是与“我”的叙述形成异质同构的有机成分,在解构虚拟真实中建构独特的文类品质。维多利亚·亚伦(Victoria Aarons)认为,挫败于恢复性魅力的荒谬希冀,祖克曼在想象中构建出浪漫情节,一出戏中戏,因为如果事实上他不能拥有,至少还可以写出“他和她”之间令人浮想联翩的恋情萌芽的前奏[19]。但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或多或少偏离了菲利普·罗斯采取这种叙述策略的初衷。五段剧本式书写究竟是实际发生的事件,还是“我”(祖克曼)的虚构抑或幻想,处于真假难辨的状态中。在《退场的鬼魂》的视角转换与多重叙事中,菲利普·罗斯有意模糊现实与想象在戏剧场景中的界限,目的就是要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弄得扑朔迷离。在小说文本的五段剧本中,真实与想象、戏剧与人生、庄周与蝴蝶亦或蝴蝶与庄周,每章戏剧真实与虚幻的角度,使得事实与想象紧密契合、浑然天成。在真假莫辨的叙述中引发读者的兴趣,给读者的理解制造障碍,以扩大作品的张力。
三是让接受者无法厘清叙述文本中主人公真实与虚构的界线。贯穿《鬼作家》《退场的鬼魂》文本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艾米·贝莱特、E.I.洛诺夫,其离奇身份与际遇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
在《鬼作家》中,艾米·贝莱特自称是《安妮·佛兰克的日记》原作者;在《退场的鬼魂》中,艾米·贝莱特又否认自己是《安妮·佛兰克的日记》原作者。究竟艾米·贝莱特自称是《安妮·佛兰克的日记》原作者是真,还是艾米·贝莱特否认自己是《安妮·佛兰克的日记》原作者是真?真真假假、真假难辨。
在《鬼作家》中,E.I.洛诺夫是令人仰望的文学大师;在《退场的鬼魂》中,查德·克里曼发现了E.I.洛诺夫乱伦的手稿。究竟E.I.洛诺夫是文学大师,还是一个有乱伦丑闻的人物?理查德·克里曼发现的E.I.洛诺夫乱伦的手稿,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艾米·贝莱特告诉理查德·克里曼的情况,有多高可信度?真实与虚构的界线同样无法厘清。
后文本(《退场的鬼魂》)照应前文本(《鬼作家》),后文本又对前文本予以否定,两个文本存在明显的交叉和对立关系,按照逻辑推理前、后文本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前文本为真,那么后文本必为假;二是后文本为真,那么前文本必为假;三是前后文本都为假。接受者无法厘清前、后文本的真假,也就无法厘清叙述本身的真实性与虚构性。笔者认为,主人公扑朔迷离的身份,真实与虚构的难以厘清,同样是菲利普·罗斯有意为之,因为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就是消除并沟通虚构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绝对对立。从叙事策略看,真实与虚构穿插杂糅,小说与非小说失去界限,让接受者真假难辨,是能够让阅读者产生浓厚兴趣的策略之一。
综上,菲利普·罗斯“祖克曼系列小说”首尾两部作品在叙事上达成了内容与形式上的辩证统一,同时在创作主题与语言艺术上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其叙述策略就是有意无意造成叙述者与作者、叙述本身、叙述文本中主人公的真实性与虚构性界线模糊,“考察日常叙事话语突围的维度,对把握作家的自我认同变化以及当下小说的精神重建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20]。这实质上在现实书写的实践层面履行了小说家与诗人的职责:“用虚构成分模仿真实,并有夸张。”[21]当一种形式可以按照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理解时,它在美学上才是有价值的[22]。“小说是最伟大的艺术,因为它将私密的、个人的世界与更大的社会视野联系起来。”[23]虚实相间、真假莫辨的叙述策略,无疑是菲利普·罗斯叙事艺术的又一亮点。
有论者认为,“《鬼作家》是罗斯的第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祖克曼小说……而《退场的鬼魂》则并非罗斯最强有力的作品”[24],但如果从叙事视角、结构、策略三个维度来分析这两部作品,《退场的鬼魂》对《鬼作家》不仅有因循与承袭,更有发展与完善。从这一点来看,《退场的鬼魂》堪称菲利普·罗斯“祖克曼系列”叙事艺术技巧上的扛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