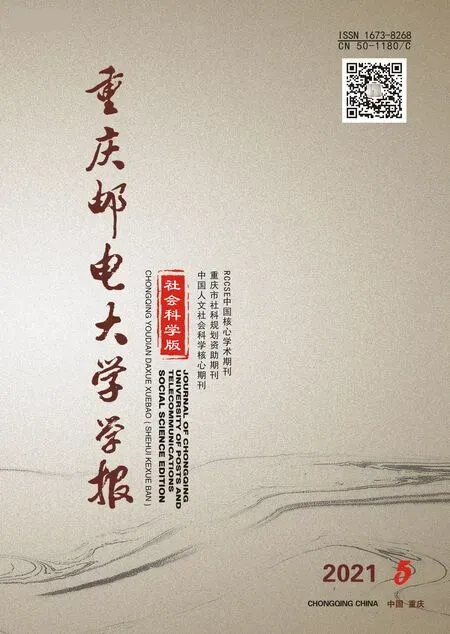“再虚构”与逻辑的悖逆及思想的断裂*
——《药》与《阿Q正传》的电影改编合论
2021-12-05陈伟华
陈伟华,胡 洁
(湖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1918年5月,《狂人日记》于第4卷第5期的《新青年》刊出。此后,鲁迅先后创作《孔乙己》《药》《阿Q正传》《祝福》等多篇小说,收于《呐喊》与《彷徨》两部小说集。得益于极深的古文修养,语言的精简与意义的浓缩形成鲁迅小说内部的张力,使其从一开始就展示出高度“雅化”的特征。
电影从诞生初期,就自觉地向文学寻求资源。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主要载体,成为电影的主要改编对象。以鲁迅的小说为例,改编成电影的便有五部之多,分别是《药》《阿Q正传》《祝福》《伤逝》与《铸剑》。但电影与小说从属于不同的艺术样式,相较于着重表现自我的小说,电影更强调面向大众。正如乔治·布鲁斯东在《从小说到电影》中指出:“一般说,一部有份量的小说总是拥有一批为数不多然而有文化的读者,总是由一位作者独立创作,而且比较地不受生硬的检查机关的干涉。电影却不是这样,它依靠人数众多的观众的支持,在工业化的条件下进行集体生产,而且受着一部强加的‘海斯法典’的限制。”[1]前言2乔治·布鲁斯东所指“海斯法典”即“官方与非官方的检查”。换言之,以集体化创作与大众化受体为表征的电影,生产程序较小说更为复杂,时代特征与官方话语的烙印较小说更为明显,“作为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代表,电影的流行性与通俗性都无与伦比”[2]。
观察历史与现实的典型化造就了鲁迅思想的典型化,以极简的语言承载极深刻的思想,高度“雅化”形成了鲁迅小说最根本的质地。“雅化”的鲁迅小说以其独特的质地,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电影工作者。有关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此类研究或以是否“忠实原著”为评判标准,围绕单篇改编作品展开评论,或分析单篇电影的改编模式,或对比小说文本与电影剧本。当然,也出现了鲁迅小说电影改编的综合性研究。宋亭荣的硕士论文《论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3]从改编模式、影像呈现与语图关系三个角度对由鲁迅小说改编而成的八部电影展开分析。吕萍的硕士论文《叙事与阐释:鲁迅小说及其电影改编》[4]借用叙事学与阐释学理论对比分析小说文本与电影剧本,探究两类文本的优劣得失。李英凡的硕士论文《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5]以时间为轴梳理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史,并试图勾勒鲁迅小说电影改编的基本特征。在众多的鲁迅小说中,《药》与《阿Q正传》皆关涉“辛亥革命”这一重大政治命题,且均被改编成电影。本文拟以吕绍连导演、肖尹宪编剧的《药》与岑范导演、陈白尘编剧的《阿Q正传》为研究对象,从鲁迅的文化史观入手,探究影片在再虚构“病例”与“灵魂”使小说实现光影转世与跨界传播的同时,能否再现“雅化”的鲁迅小说。
一、空间文化史观:虚构的病例与灵魂
“文化史观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历史观。文化史观认为,人类的历史不过就是文化的历史。”[6]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正处于转型期。五四运动中致力于启蒙的知识分子,将目光对准传统文化,他们希望“重估一切价值”,并欲借此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很显然,他们的历史观表现为一种文化史观,文化价值的毁灭与重建是他们心目中的“救国良药”。历史乃是时间的线性发展,但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肯定西方现实的前提下回看中国,产生一种批判视野。非理性的时代情绪,演变为自我化的历史焦虑,并指向自我否定。以空间为轴,横向对比,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唯文化思想论”[7]的痕迹,盛行于知识分子之中的乃是一种空间文化史观。
与同时代其他人一样,鲁迅自始至终浸润在时代情绪里。但相较于其他人,鲁迅不仅看到了“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也意识到了“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实乃中国之现状。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閟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8]74因此,欲以己力改变“二患交伐”的现状,最终弃医从文。1902年,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认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神力”,“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908年,鲁迅于《河南》杂志第2期、第8期先后发表《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两篇重要文言论文,文化和道德被鲁迅置于科学之上,并认为“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8]65,“心声”即语言,此处代指文学创作。由此可见,鲁迅已将文学视作民族精神与本质的主要承担者,文学乃“张灵明、扬个性”的重要方式。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用白话文写成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狂人日记》,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脉相承,沉默十余年之久的鲁迅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呐喊,他开始将小说作为考察“国民性”的窗口,借以实现他“启蒙”与“立人”的理想。
“国民性批判”是一种负性的文化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时代情绪(落后的焦虑)的释放。鲁迅是一位有着很深时代情绪的作家,“鲁迅彻头彻尾是在情绪里”[9]。但作为小说家的鲁迅,表达焦虑的方式并非情绪的宣泄,而是情绪的压抑。情绪的压抑造就了鲁迅式的理性,表现为一种非乐观主义。鲁迅在小说中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根本目的是“启蒙”,“启蒙”即使人脱离纯粹“感性”状态,进入到理想的“理性”状态。但“理性”是否真能如鲁迅所希望的那般,通过精神性拯救,赋予一般群众,使他们不再是历史的庸众,完成“立人”的理想?鲁迅深知,希望本身就是虚妄。“我能救人吗?”——矛盾的自我挣扎,鲁迅在小说中尝试虚构病例与灵魂,“他想在文学中寻找一种对自己民族‘精神上的病’的诊断”[10]26。用文学表达理想的虚妄所生成的绝望,形成小说中特有的暗色。
“病”常被鲁迅用来表达历史和现实感,《狂人日记》中鲁迅第一次虚构病例。由文言做成的小序,故事结构完整,整个文本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结构,类似于古代文人笔记体小说,狂人“生病”期间所写的十三则日记更像是附录。“礼教吃人”是狂人对历史所作的言简意赅的总结,也是鲁迅对历史的直接感悟。病愈后的狂人最终“赴某地候补”,表明孤独的精神战士终究为庸众所吞噬,呐喊于铁屋子的鲁迅终究还是绝望了。鲁迅在小说《药》中尝试第三次虚构病例,《药》属于相对写实的作品,它截取生活的横断面,由具体的人和事表达鲁迅深重的记忆。《药》共四节,前三节为一个整体,即“药”从何而来,到何而去?前三节像戏剧的排演一样,由远而近,每个小节都有一个中心人物,即华老栓、华小栓、康大叔,革命者夏瑜的“人血馒头”是联结这三节的纽带。华小栓的“病”与夏瑜的“药”,蕴含两个隐喻。“华”“夏”两字合在一起即“华夏”,“病”与“药”相对,既是具体的“病”(痨病)与具体的“药”(人血馒头),又是抽象的“病”与“药”。华小栓最后因病去世,宣告具体之“药”(人血馒头)的失效,也宣告鲁迅“灵魂”拯救的失败。《阿Q正传》中鲁迅再次虚构了更具典型性的病例。阿Q是一个生活在未庄的无名、无姓、无家的游民,“精神胜利法”是阿Q最大的病根。作为“必朽”之人,阿Q从未进入历史,鲁迅执意用文学的方式为“必朽”之人阿Q作传,并借此戏拟历史。《阿Q正传》共九章,鲁迅用细节的方式描写阿Q一生的行状,以阿Q革命为分界点,对阿Q的命运进行前后追溯,展现未庄之风云变幻,呈现出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药》与《阿Q正传》中的病例,绝非仅限于华小栓与阿Q,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下的民众全都是“灵魂”拯救的对象。且这两部小说不仅关涉深重的华夏文化历史,也关涉重大的现实命题“革命”,虚构的“病例”与“灵魂”是鲁迅表达历史与现实观感的典型方式,也即鲁迅思想表达的典型化。精简的语言与深刻的思想,高度“雅化”的特征,为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增添了难度。
二、再虚构与真实历史逻辑的悖逆
1981年,适逢鲁迅诞辰100周年,电影《药》与《阿Q正传》作为献礼之作登上荧幕。《药》的导演吕绍连表明拍摄意图,即“通过电影艺术的各种手段,准确地再现原著”[11]13。但电影作为一种以集体化创作与大众化受体为表征的艺术样式,通俗化的诉求与生产形式的相对不自由,彻底还原小说不太可能。改编自小说的电影,实则已是一种再生产、再创作,电影本身必然留下时代特色与官方话语的烙印。正如乔治·布鲁斯东在《从小说到电影》一书中所指:“在电影中,社会力量在最终的成品中留下的痕迹,比在其他任何艺术中更为明显。”[1]38
历史将目光投射于帝王将相式的英雄人物,却忽略了现实生活层面的细节,文学中间的人物往往不为历史所取材。《药》之华老栓一家与《阿Q正传》之阿Q,都是被历史遗忘的角色。但鲁迅何以如此执着书写底层的普通民众,实则源于鲁迅之启蒙“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12]的观念。关注普通人现实的生存状态,虚构精神“病例”,以“灵魂”为基点,作历史的追溯,寻求病因以期望作“灵魂”上的疗救,是鲁迅表达历史与现实观感的主要方式。《药》与《阿Q正传》皆涉及辛亥革命前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虚构了一系列符合真实历史逻辑的“病例”。虽然电影改编基本遵循文本的构架,但叙事重心的偏向或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再虚构的“病例”一定程度上悖逆了真实的历史逻辑。
《药》这一小说采取的是倒叙方式,前三节联系紧密,皆围绕“药”展开,分别塑造了三个场景。第一小节的场景是华老栓买药,第二小节的场景是华小栓吃药。相对来讲,第三小节的场景是较大的,在茶馆最热闹的时候,康大叔等人谈论“药”的来源。革命者夏瑜从来没有正面出现在小说中,读者获得的关于夏瑜的印象来自于大众的叙述。很显然,小说是将夏瑜当成暗线来处理。在《药》中鲁迅有意采取主体缺位的方式,作一种现象式描述,以底层视角去观察现实政治问题“革命”。“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13]《药》作为文学作品,表现的正是普通老百姓在社会政治大变动下无意义的生活。对华老栓一家而言,华小栓的病才是给家庭带来灭顶之灾的原因。华老栓根本无暇关心“人血馒头”沾的到底是谁的血,他只有一个目的——治好华小栓的病。像华老栓这样的普通民众,执着于最现实的生活层面,历史此类宏大命题从未进入他们的视野。实际上,我们总是很难将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与历史挂钩。他们通常安分守己,固执于历史的无意义生活,仅仅在现实层面,消耗自己、完结自己,他们的生存是最基本的社会生存。有史以来,任何社会最底层的民众,过的都是与历史毫不相干的生活,大多处于一种对历史的无意义感的精神状态。此即鲁迅所言:“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8]224于普通民众而言,无论再大的政治风云变幻,除非危及自身最基本的生存,否则皆与己无关。他们认为“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14]557。因此,康大叔等人认为因造反获罪的政治犯夏瑜该杀,只是根源于他们的日常认知。正如夏瑜劝牢头造反,本质上是虚幻的。但鲁迅为何这样写?前文已表明,鲁迅是采用最底层的视角去观察“革命”这一现实政治问题的,为让作品落实到常识的真实,鲁迅必须去除“自我”思维,而采用普通民众的思维。在普通老百姓的思维中,任何带有不低头、不屈服、不认罪的行为,都会被模式化。普通民众对革命的认知,全是有感而发,完全没有理性参与。无论是执着求药的华老栓,还是康大叔等人对于革命者夏瑜的认识,在鲁迅笔下皆是真实历史逻辑的再现——普通老百姓永远处于无知无识、与历史相隔膜的状态。但“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14]54-55,鲁迅显然是否定普通民众这类生活常态,认为他们处于一种病态的真实,而革命(辛亥革命)之“药”终究是无法发生效力的。
吕绍连在改编《药》时,弃用倒叙而转用顺序的方式,同时叙事重心也发生了偏移,将原小说中做暗线处理的夏瑜变为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之一。导演吕绍连曾自述:“小说《药》是以辛亥革命为背景,以女英雄秋瑾为模特儿,以麻木、愚昧、落后的人们为典型而写成的。”[11]11很显然,这一观点在他导演的影片《药》中得以具体再现。影片《药》有两条叙事线索,所用篇幅大致相等。一是为“药”奔走的华老栓一家以及充当中间人与看客的康大叔、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人;一是策划、刺杀巡抚及至最后英勇就义的夏瑜。影片中夏瑜拥有了开口说话的机会,他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使命,舍小家为大国,且在与普通民众的对比中,夏瑜的英勇形象得以进一步巩固。普通民众不再仅仅忙于生老病死,而表现出对“革命”的极端关注,且自觉站在“皇帝”那一面,与鲁迅之所言“无论站在那一面”截然不同。影片增添康大叔、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再劝华老栓买人血馒头一幕。他们讨论皇上正在杀革命党,且将革命党称作“逆党”,在他们口中,皇上乃真龙天子,兵多将广,大开杀戒理所应当,沾上逆党夏瑜之血的馒头更显皇恩浩荡。革命者夏瑜口中的千古罪人,是阿义、康大叔等人口中的真龙天子,明智与愚昧对比强烈,政治立场产生明显分歧。《药》全文共五千余字,匠心独具,以倒叙的方式构建了四个小节,形成四个场景,留下大量的叙事空白。同名影片则采用顺序方式和双明线结构,增添夏瑜策划刺杀巡抚、门口与夏四奶奶告别、康大叔众人劝华老栓再买馒头并表明政治立场等,具体化夏瑜狱中劝牢头造反与英勇就义的片段,填补了小说的叙事空白,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不难看出导演在通俗化上所作的努力。编剧肖尹宪提出:“我以为,鲁迅之作《药》的原意在于通过对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的麻木和愚昧的描写,抨击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指出必须唤起民众才能使革命成功。”[15]将小说中原有的普通民众固结于无意义与无历史感的日常生活的生存常态转换成鲜明的政治立场,让他们主动发表对于“革命”的看法,以表现普通大众的愚昧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在某种程度上悖逆了历史的真实逻辑。辛亥革命作为政治意义上的上层革命,旨在结束封建帝制。小说《药》所否定的乃是辛亥革命未能改变底层民众的精神状态(无历史感与无意义感),以达到“灵魂”救治的目的。而影片《药》却竭力突出普通民众的政治立场,对民众的“愚昧”进行漫画式的图解与再虚构,这并非真实历史逻辑的再现,而是主观化的解读。
《阿Q正传》中,阿Q一生的行状无从追溯,他是存在于未庄整体结构之外的游魂。鲁迅以文学的方式为游荡于历史之外的阿Q立传,并辅之以具体可感的细节描写,用零碎的片段为读者展示其劣根性。阿Q的形象往“革命”前追溯,只能是细节性的片段式的展示,读者无法知晓阿Q成长的全部过程。但“精神胜利法”的病根却在阿Q身上展露无遗。阿Q式的人性之劣,表现为阿Q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满足其动物式的生存,以及在获取基本生存物资之后所要求的归属感。他忍受地保的欺压,忍受赵太爷的辱骂,其本质是利己。没有受过教育的阿Q,没有被文化构型容纳的阿Q,欺软怕硬,麻木可笑。纵观阿Q的一生,他都在不计任何后果地冲入群体。阿Q冲入群体所采取的举动,诸如认本家、恋爱以及他最终因被群体所抛弃而选择的革命,是推动他一生悲喜剧交替的主要动力。鲁迅正是通过阿Q悲喜交替的一生以及未庄人的生存状态,打开了一个反思历史的窗口,窥见其形成的原因,从而揭露历史的惰性。与阿Q一样,王胡、小D等都属于游离于未庄之外的个体,但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温情,只有因缺乏理性而进行的纯粹动物性比较,如阿Q与王胡比赛捉虱子。除去阿Q、小D等边缘人物,同时生存在未庄的,还有受过教育的赵太爷、秀才等。鲁迅以阿Q为基点去审视这些有文化与有理性的人,所得到的结论是文化造就了与阿Q对等的人性之劣。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家里照例不许点灯,只有在阿Q舂米时才许点灯,赵太爷有的只是吝啬与对阿Q的残酷压榨,毫无半点仁义之心。阿Q调戏吴妈之后,赵太爷给他一顿毒打,并要求阿Q赔偿香烛,抵押棉被。阿Q上城归来后,赵太爷又不顾之前定下的规矩,让阿Q进门,还想买他从城里捎来的便宜好货。革命风声紧时,举人老爷和他排了转折亲,他一看对自己是利多于害,便欣然接受了举人老爷要寄放在他家的行李。利己也是赵太爷生存的唯一法则,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毫无知识分子的原则与良知。与阿Q相比,他多了一层虚伪,显得更加可笑。而这种比较,在第七章《革命》与第八章《不准革命》中达到高潮。假洋鬼子与秀才“他们的喜剧化革命体现这类知识分子阶层道德行为的价值标准的阙如和历史责任良知的淡薄”[16]。由此可见,鲁迅通过虚构阿Q以及与他同类的王胡、小D或处于其对立面的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病例”,表明无论处于传统文化构型之外的纯粹自然形态的人性还是受传统文化驯养的文化构型之内的人性,皆表现为人类的一种劣根性,借此鞭挞历史的主流文化。通过比较两种“革命”,也表明鲁迅对于“辛亥革命”这一药方的不信任态度。
岑范导演的《阿Q正传》在很大程度上忠实于原著,如基本按照原小说的叙事顺序结构电影,采用画外音再现文本中“我”的声音。但改编并不是对小说的照搬,导演的主观意图、时代特色与官方话语的烙印也必然以某种形式体现在影片之中。主要表现为增添、删减或改变了一些故事情节,在人物塑造方面,电影则加强了善恶对比。看似改动幅度不大,但鲁迅笔下虚构的所有“病例”,经电影再虚构后,只有部分得以保存,如“土谷祠老头”变成正义善良的化身,阿Q也似乎较原著更为可爱。吴妈与阿Q闲谈时,吴妈认为赵太爷吝啬、虚伪,有钱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且略带温情地劝阿Q这“贱骨头”不要那么卖力气,表现出吴妈的善良。阿Q在社戏赌博时,土谷祠老头关心阿Q,并嘱咐阿Q早点回来。在地保勒索阿Q时,土谷祠老头替阿Q出钱。在阿Q被抓进大牢时,土谷祠老头给阿Q戴上“棉环”。在小说中着墨不多,只是“说些废话让阿Q走”的土谷祠老头,竟然变得温暖与善良。而小说中第一个警觉阿Q在城里做小偷的赵太爷,则不如邹七嫂聪慧,在电影中竟发现不了阿Q是小偷的事实。在影片的最后,增添了赵太爷举报阿Q是抢匪,让阿Q成替罪羊的情节。影片中赵太爷的虚伪吝啬、道貌岸然较小说刻画得更为淋漓尽致。原小说中阿Q不准小D革命,甚至要将小D与赵太爷等一同除去的场景,在电影中变成了阿Q与小D同为白盔白甲的革命者,阿Q也没有杀赵太爷等人的头,只是将其脱掉裤子打四十大板。总而言之,吴妈、土谷祠老头等无产阶级大众是善良的,就算是阿Q,也有着一份善良与可爱,赵太爷、秀才、白举人等则是虚伪的“土绅士”,人物形象的塑造透露着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电影“侧重在二元对立的阶级路线斗争中寻求中国革命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并在对文学文本与历史的追溯中重新书写历史、确立价值”[17]。再者,电影的结尾,王胡竟然感叹“反正啊,倒霉的还是老百姓”。不懂革命为何、对现实从未有过理性认知的王胡、小D之流,何以会有如此高的历史觉悟,这未免悖逆于真实的历史逻辑。陈白尘曾明确指出:“八十年代的‘主将’大概也是‘不主张消极的’”[18],电影《阿Q正传》通过善恶对比,改变了鲁迅作品中的“黑暗”色调,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通俗化特征。
三、再虚构与情节的弥合及思想的断裂
《药》《阿Q正传》皆收录在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之中。《药》中,鲁迅第一次关注到宏大的现实政治命题——“革命”。1921年,辛亥革命十周年之际,鲁迅又一次思考“革命”的意义,在《阿Q正传》中设置了《革命》《不准革命》《大团圆》三章。比较鲁迅两次对于“革命”的叙写与思考,不难发现,鲁迅始终坚持从“底层视角”出发,把历史所认可的辛亥革命的功绩——排满,作了最大的消解,将它还原到生活现实层面,否定未能改变普通民众精神病态与拯救其灵魂的辛亥革命,表现出鲁迅思想前后的一致性。
《药》的第四节是一个尾声,具有很高的象征意义,两个生命——夏瑜与华小栓,最终的结果都是死。作者用了相对抒情的、浪漫主义的手法,荒郊野外,两座新坟相对而立。这两种死极其偶然地关联在一起,似乎一个有价值、一个无价值。但从人性的意义上看,死和生的价值都是相对的。把夏瑜当作革命烈士来看,他的死是一种宏大叙事,于家于国都有意义。华小栓,他的死是生活的琐碎,无意义。小说的核心是病和药,那么华小栓的死对华老栓一家就没有意义吗?在死的意义层面,这两者是同等的。不同的命,相同的死(人性意义上来理解)。这恰恰是鲁迅创作的深意。面对苍天和大地,在死的意义上,人都回到了本位。两位母亲的痛苦一模一样,在悲戚中,夏瑜母亲鸣冤叫屈,不是政治觉悟,而是一种凡俗痛苦的无意识的发泄;华小栓的妈,眼泪往肚里咽。一个动静大,一个动静小,而悲痛是一样的。夏瑜的死只对家庭有意义,是平凡的而非英雄的死,对社会而言毫无意义,民众的灵魂依然没有被夏瑜这一类革命者的“药”治愈。但在最后,作者还是不得已凸显自己的政治立场,一种脱离自己的关于人性的诗意的领悟,虽然有意义,但属于历史的一种矫饰。“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必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山平空添上一个花环。”[8]441这种曲笔让人感觉到不真实,所以乌鸦最终是没有飞上坟的,没有给任何想要得到政治宽慰的人一点机会,“它显然排除了加在结尾的那个花环所带来的世俗的乐观”[10]78。
《阿Q正传》中鲁迅在阿Q革命的同时穿插了辛亥革命。阿Q革命,是游离于教养与文化之外的人的本能。在此之前,阿Q为融入未庄而作的种种努力,皆以失败告终。从恋爱的悲剧开始,阿Q就已经被彻底抛弃,在最高意义的孤独状态下,阿Q想到了革命。“阿Q作为失意者对周围世界的怨恨与刻毒,正是他走向‘革命’的心理动力源泉。”[19]但这是原始意义上的革命,是阿Q因没受到文化感化,在生存层面产生的人生躁动,根源于非理性。阿Q的革命幻想,完全来自于他对立面的夸张。阿Q对于文化完全是隔膜的,之所以革命也是因为革命或可以满足他的皇帝梦,他没有什么革命理想,甚至不知道革命为何物。在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之后,他甚至默念着“革命是要杀头的”。阿Q的革命诉求,是阿Q式的人性之劣的最高表现,是利己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因为不被接纳,所以不加思考地走上反抗的道路,为奴隶而不得,转而想成为主人,最后却沦为反抗的牺牲品。假洋鬼子与秀才的革命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假洋鬼子在革命到来之时,开始审时度势,联系自由党,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他接纳了秀才的革命诉求,并在秀才给他四块洋钱之后,给了秀才一块能抵得上一个翰林的银桃子。仔细探究假洋鬼子与秀才的革命,并非是为了什么崇高的理想,虽然有理性的成分在(利己),却并不比阿Q的革命高尚。
从《药》到《阿Q正传》,鲁迅总是高度客观化地审视辛亥革命,不将自我的主观情感投射其中,坚持让自己的视角与底层保持一致。而现实是,辛亥革命确确实实与底层异常隔膜,无论从历史视域中赋予它多高的认同,站在底层的视野中看,它是无意义的,它与生活不发生关联,于大众的灵魂救助无益处。鲁迅消解了辛亥革命的宏大意义,即“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20]32。
电影《药》与《阿Q正传》均为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的献礼之作。鲁迅曾自言:“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20]21为让面向大众的电影增添一抹亮色,使观众获得轻松的观感,影片《药》与《阿Q正传》都在原小说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程度的改编。电影《药》的导演吕绍连延续世俗的乐观,依据夏瑜坟上的花环,对原小说进行政治解读。影片《药》除了正面表现革命者夏瑜的英雄形象外,还增添了原小说中未出现的带瓜皮帽的另一革命者。影片没有透露这一革命者的姓名,对他着墨也不多。根据他在影片中的出场,如夏瑜被杀时这一革命者站在人群中显得极其悲痛与愤怒,如夏四奶奶因夏瑜造反备受世人冷落之时,他放在夏四奶奶篮中的两块银元,可以推测夏瑜坟上的花环很有可能与他有关系。通过考察夏瑜的英雄形象与另一革命者形象的设置,可以得出结论,即在导演看来,虽然辛亥革命因未能发动群众而略显不彻底,但夏瑜这类革命者的死相较于华小栓凡俗的死更有意义,且革命前途一片光明。影片给予观众政治慰藉,在改变鲁迅原小说最为根本的“黑暗”特质的同时,也明显改变了原著所表达的思想。
阿Q革命中穿插了辛亥革命,小说《阿Q正传》借此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作最大的消解。影片《阿Q正传》延续这一基本思路,将《药》中的夏三爷与革命者夏瑜融入影片中,实现情节的弥合。原小说《药》中,夏三爷是夏瑜的叔父,也是告发夏瑜革命的罪魁祸首。岑范导演将《药》中的夏三爷与《阿Q正传》中的白举人合二为一,白举人变成夏瑜的舅父与革命的告密者。这一改编,将《药》与《阿Q正传》的革命紧密关联起来,使得两部作品的情节弥合无间,丰富了影片内容。《阿Q正传》原著中鲁迅描述阿Q所作的革命之梦仅用三百余字,而影片集中表达阿Q革命之梦片段时长达十余分钟。影片中阿Q身穿象征皇权的枯黄色毛皮上衣,表明阿Q的革命幻梦实乃皇帝梦。影片中阿Q对曾经欺压过他的人一一进行报复,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都跪在他的面前,为讨好阿Q,赵太爷爽快承认阿Q姓赵,秀才叫阿Q太公,假洋鬼子自愿挨打。吴妈、小尼姑在阿Q面前表现娇媚,满足阿Q对于女人的渴望。总而言之,影片中阿Q的革命幻梦是对小说中阿Q革命之梦的再补充与再拓展,增强戏剧性的同时无碍于思想的表达。影片中阿Q最终在曾经看夏瑜被杀的古轩亭口枪杀示众,原来革命者的死与阿Q的死是同等效果,影片最终完成对辛亥革命的讽刺。
从电影《药》到电影《阿Q正传》,情节的弥合使两部影片关联更为紧密。但两部影片所表达的思想发生了断裂。影片《药》在通俗化的同时,保留了世俗的乐观,肯定辛亥革命,用花环映射革命的光明前途,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原著。电影《阿Q正传》延续鲁迅的一贯思考,展现阿Q革命幻梦,消解辛亥革命的宏大意义,与原著保持一致。同为1981年上映的影片,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情节的弥合必然使观众将两部影片联系在一起,而两部影片所传达的思想间的断裂又会让观众产生矛盾心理。因此,电影改编虽然是一种再创作,但在改编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之时,应对其前后思想作统一考察,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四、结 语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西对比,鲁迅产生了焦虑的时代情绪。他希望通过文化价值的毁灭与重建,拯救国家与国民,所秉持的是一种空间文化史观。他以虚构“病例”与“灵魂”的方式,思考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弊病,而能否拯救国民“灵魂”成为他评判一切现实政治运动的标准。
影片《药》与《阿Q正传》总体而言忠实于原著,且以再虚构“病例”与“灵魂”的方式,使得原小说《药》与《阿Q正传》再一次进入大众视野,实现了光影转世与跨界传播。小说《药》与《阿Q正传》中的所有人皆处于一种与历史相隔膜的状态,所有人都是鲁迅虚构的“病例”。而影片《药》与《阿Q正传》明显增强了善恶对比,《阿Q正传》中吴妈与土谷祠老头的善良,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药》中普通民众坚定的政治立场与《阿Q正传》中王胡高于历史中间普通民众的政治觉悟均与真实的历史逻辑相悖逆。此外,影片《阿Q正传》通过夏三爷与白举人的合二为一,将《药》中夏瑜的革命引入影片,实现了情节的弥合。电影《药》与《阿Q正传》虽然在情节方面有所交叉,但两部影片所传达的思想并非一致,而是处于断裂状态。电影《药》与《阿Q正传》皆是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作,很显然,《阿Q正传》的电影改编较《药》更为成功,体现在以通俗化的方式准确传达了鲁迅原著的思想。但受时代与艺术特质所限,改编后的《阿Q正传》与《药》只能是某一时代与某一导演的作品,这也正是文学名著屡被改编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