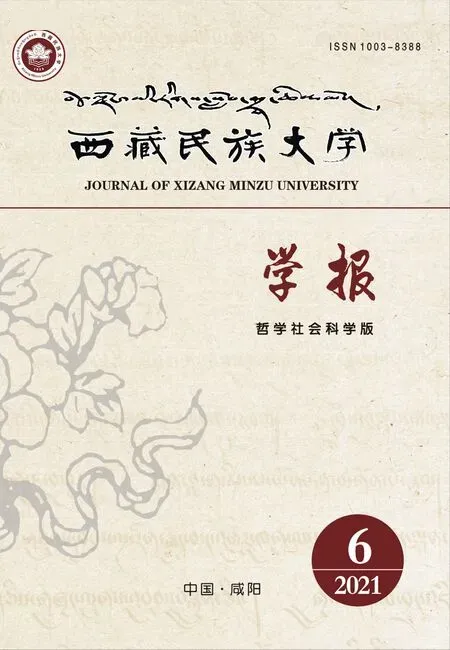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选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情感进路及其实践
2021-12-04狄鸿旭
狄鸿旭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1)
西藏和平解放是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①,党通过爱国统一战线等形式,选任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以下简称民族干部),为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提供了干部保障,为新中国治藏建藏奠定了基础。干部问题是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如在“三八干部”“南下干部”、基层组织建设干部角色等方面都有丰硕成果,但民族干部研究方面仍相对薄弱②。本文即以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对民族干部的选任培养为中心,结合文献和回忆录等史料,为党在斗争形势复杂和干部基础薄弱条件下,如何有效运用情感、政策和策略选任培养干部,进而联系群众以推进工作,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一、和平解放西藏时期的斗争形势
1949年11月,毛泽东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并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任务,西北局协助,采取由川、青、新、滇四个方向“多点向心”进藏模式。当时解放西藏面临着复杂斗争形势和多重困难。国际上,美、英等国直接插手和干涉西藏事务。印度也希望保有英印殖民当局在西藏攫取的特殊权益,并试图向西藏地方当局施加影响。在国内,党在西南、西北解放区的干部和群众基础尚薄弱,各省的藏族聚居区还处在民主建政过程中。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分裂保守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加紧扩编藏军,妄图维持西藏现状。而当时西藏社会尚处于封建农奴制度下,广大藏族群众尚未觉悟,在帝国主义和地方分裂势力的长期有意误导下,民间充斥着排汉观念和对共产党、解放军的恐惧心理。同时,西藏极为艰苦复杂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等条件,也给进军西藏带来一系列直接困难,成为解放西藏的现实阻碍因素。
二、选任培养民族干部的具体形式
尽管工作局面和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中国共产党仍果断部署进军西藏,并制定和实施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各项方针策略,在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后,围绕贯彻协议展开一系列工作安排部署,围绕党的西藏工作对民族干部的选任培养也随之开始。
(一)从革命队伍中选任培养民族干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全面系统研究民族问题,并通过举办民族学院等形式培养民族干部。在进军西南、西北,解放西藏提上日程之际,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并要求地方组织政权,“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1](P20)。长征时期投身革命,并在延安参加过中央党校少数民族班的藏族干部主要有天宝、郭锐、杨东生、孟泰、罗德干、贺土司、王寿才、扎喜旺徐等人[2]。为此,扎喜旺徐从察哈尔调至第一野战军参加解放西北工作,天宝赴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调西南局参加进军西藏工作,皖南军区杨东生也调入西南局参加进军西藏工作。中央还召曾在藏工作、彼时在西康组建康藏边地方工作委员会的中共地下党员平措汪杰至西南局汇报工作,并任命平措汪杰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参加进军西藏。自然,民族身份并非党内选任培养民族干部的绝对条件,对党忠诚和能够联系群众才是干部选拔的决定因素。因此,党在选拔民族干部的同时,也安排熟悉民族工作的干部参与其中。如在延安时期曾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牙含章、韩戈鲁、周仁山、白云峰等同志,也陆续参与到解放西藏工作中。同时,党还对进藏干部提出“生活高原化”要求,并开展藏语文学习培训,以加强干部联系群众和适应地方工作需要。
(二)广泛吸收发展爱国进步少数民族上层人士
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践“和平民主建国”政治主张,在运用统一战线吸收发展干部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1949年9月解放军攻克西宁后,即邀与西藏宗教界有密切联系的爱国僧侣喜饶嘉错参加青海省建政工作。中共西南局先后派出志清法师、格达活佛拟入藏开展工作,西北局也组织青海寺院代表团入藏谈判。党中央对派出代表团人选事宜多次给予指示,如在志清法师进藏时指示西北局,“如有适当之人能派到拉萨去进行说服达赖集团者,亦应即设法派去”[3](P22)。在安排格达活佛入藏时指示西南局应争取大金寺堪布去西藏,如青海劝和团夏日仓、当才等经过甘孜,也可就谈判问题给予指示[4](P77-78)。
通过统一战线发展选任民族干部的重点是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西康是西南局进军西藏的后方基地,十八军进抵甘孜后,天宝、吴忠等立即对降央白姆、夏克刀登和邦达多吉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同时吸收拟与志清法师赴拉萨的色拉寺高僧阿旺嘉措等人参与西康建政,这些上层人士为党和政府所开展的工作,为进军西藏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持。昌都战役开始前,吴忠、天宝等通过川康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将中央争取西藏和平解放方针传递给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和驻在金沙江畔的藏军各代本等。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发起,9日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即率350名官兵起义。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于21日命令藏军放下武器,昌都各宗相继获得解放。中共西藏工委颁布详细工作指示,强调严格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实施对喇嘛寺、民兵组织与正规藏军区别对待策略,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对民兵武装和战俘进行政治教育,对排以上官兵转团师集中训练,以奠定开展上层政治工作的基础。在1950年底成立的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35名委员中,汉族干部12人,少数民族干部23人。该地区12个宗的解放委员会中有汉族干部14人,少数民族干部154人,均为上层人士[5](P10)。由此,运用统一战线,依托解委会各级组织,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吸收到党周围开展工作,并逐渐培养成干部的模式在西藏得到成功实践。
(三)五湖四海选任民族干部
1950年1月,朱徳在北京主持召开西藏工作问题座谈会,征求在京藏族人士对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和建议,并作物色选拔干部准备。周恩来指示统战部和民委,拟定计划,举办藏族干部训练班,由刘格平具体负责。当时内地可资培养的藏族有限,训练班重点从在北京、南京等地学习的藏族学生和曾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等机构从事文化工作的职员中选拔,并多方物色教师。很快,由内蒙古等地来京的天宝等党内干部和多方选拔的藏族干部30余人,共同组成干部训练班。同时,在彭德怀、习仲勋亲自指导下,西北局也在兰州举办藏族干部训练班。在藏族干训班基础上,中央成立西藏工作团,天宝任团长,杨东生、韩戈鲁、昂旺格桑为副团长,向西康进发。1950年2月,西南局指示承担进藏任务的十八军建立政策研究室,军长张国华在成都、重庆等地广泛寻访熟悉西藏情况人士,并先后延请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等深谙藏情的学者参加研究室。西藏工作团抵达西康后,巴塘地下党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56名藏族青年在平措汪杰带领下到达康定,西南局全部接纳,并指示除8人留康定工作外,其余48人全部进入西藏工作团[6](P52)。十八军进驻西康后,为开展工作和储备干部,在康定、甘孜、德格、巴塘等地,招收藏族青年近80名。以上青年到甘孜后,通过集中培训,编入工作团,承担进藏工作,在西康南部,也有20余名藏族青年参军,直接编入南路入藏的十八军53师,到波密、林芝等地区开展工作,这些藏族青年不断成长为西藏工作急需的干部骨干[6](P72)。
(四)建设发展干部培养渠道体系
在实现解放西藏工作中,党制定了“和平解放,暂维原状”的基础工作方针③,这表明当时在普通群众中选任培养干部条件尚不具备,因此主要是通过开展影响群众工作、建设发展群团组织等形式来拓宽培养民族干部渠道。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前后,中共西藏工委首先在工作条件较好的昌都开展多方面的宣传、服务群众工作。昌都解委会在建立两年内,开办小学14所,招生500余人,开办民族干部训练班1所,招收学员150名(其中送内地学习者100名)。组织2次赴内地参观,参观代表54人,被宣传群众5万余人。并开展下乡宣传,组织在团结爱国公约上签名群众达25000人。另外,还通过节日群众大会、座谈会、组织头人学习、放映电影、表演戏剧、舞蹈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和联系群众工作,因此昌都地区两年内即培养吸收民族干部参加工作者223人[7](P90)。
中共西藏工委进抵拉萨后,中央指示“对支持靠近中央的分子(如阿沛等),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如两代理司伦)尤须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工作”[3](P65)。依据指示,工委除举办藏干校外,主要通过宣传服务群众和群众团体建设等形式,做培养民族干部的基础工作,以拓展干部选任渠道。1952年至1957年,工委先后组织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寺庙上层喇嘛、青年和妇女等13批1000多人次到北京和内地参观访问。1952年5月组建青年团西藏地方工作委员会,并组织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此后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并组建拉萨爱国妇女联合会。青年文化联谊会组织青年学习和文体活动,组建赴内地参观团、赴康藏公路慰问演出等活动,将贵族青年不断吸纳和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并逐渐成为西藏革命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8](P163-172)。1952年工委开始在拉萨、日喀则等地建立小学[9](P100)。以上活动都为吸收培养民族干部提供了基础保障,并发展了一定数量干部。
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试行方案》,延续延安时期举办民族学院,在北京成立中央民族学院,西北、西南军政委分别成立西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开启了民族干部的规模化组织选拔培养,这些民族学院在办学初期招收的西藏学员主要面向藏族上层。此后,随着民主改革推进,西南、西北民族学院面向川、青等地藏族农牧民群众招收学员的比例和规模在不断扩大。1956年以后,中央民族学院也扩大了直接面向西藏招收学员的规模,1957年西藏公学在陕西咸阳创建④。这时党已经具备面向群众大规模选拔培养干部的条件,为长期开展西藏工作提供了重要干部储备。
三、选任培养民族干部的情感进路
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选任培养民族干部方面具有深厚的情感意蕴。这一情感逻辑在于,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的藏族群众,历史上所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更为深重,而藏族的尽快解放意味着整个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解放;另一方面,民族干部是解放和建设的基础力量,党对于藏族人民的情感及对西藏工作的开展,需要通过党对民族干部的领导,由干部联系群众得到实现。党中央对民族干部的选任培养贯穿这一情感线索,并结合工作政策和策略运用开展实践。
(一)党的民族情感是选任培养民族干部的基础
党中央对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情感,统一于希望尽快达成西藏和平解放,使西藏和藏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组成团结友爱的多民族大家庭,这一情感因素具有对中华民族、藏民族和藏族人民三个层次。首先,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情感是贯穿和平解放西藏全部工作的基础动因。一方面,和平解放西藏是完成领导包括藏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斗争,并最终实现全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如1950年10月,毛泽东在一涉藏事务的对外表态中批示“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⑤。可见,在西藏工作展现涉外因素时,党在承续书写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中,首先是代表包括藏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尊严和情感表达。
更为直接的情感因素来自党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民族的情感,特别对长期受多重反动力量压迫的少数民族,这一情感意蕴尤为强烈。从历史来看,代表中央王朝的皇帝在藏族民众的信仰和情感谱系中的位置不断稳固清晰,传统中央王权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情感上的认同⑥。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代表中央的共产党领袖,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一历史情感⑦。自然,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情感与人民情怀,决定了党对藏民族的情感基础是藏族人民。这些情感因素的叠加,使党在干部选任培养中认识到,在当时条件下,为真正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形成建设发展良好环境,党就要成为包括藏族上层分子在内的整个藏民族的先锋队,并通过在藏民族上层中选任培养作为民族先锋的干部,将西藏地方政府为代表的西藏统治阶层纳入到全民族解放斗争体系中,最终推动人民群众的逐步觉悟,是最为有效的方式。在解放西南、西北时,党中央就发出指示,要求“向各少数民族极力表示好感,多和他们发生关系”[3](P6)。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毛泽东强调,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各民族人民以及和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们自觉自愿地去进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强迫地去进行,而由汉族或他族人民中出身的工作人员生硬地强制地去进行,那就只会引起民族反感,达不到革命的目的”[3](P54)。
党中央指出,“西藏地方政府虽为西藏人民所不满,毕竟是西藏民族现时的地方政府,又由于它是达赖的行政机关,仍能维系西藏民族的感情”[3](P65)。因此在干部选任政策中突出强调本民族干部重要性,并明确指示,民族干部选任培养“可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达赖、班禅的宗教事务官员,各大寺庙的喇嘛,藏军官员及僧俗知识分子”中进行统战,并要注意“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感情,加强和他们的联系”[3](P92)。1956年以后,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但此时毛泽东在接见西藏代表团时仍多次表示,对于贵族,可参考民族资产阶级赎买的方式进行改造,并做出六年不改、机构收缩的决定。可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之下,党中央从对藏民族的情感和立场出发对西藏上层持续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并希望通过系统工作,使之部分转化为民族先锋队。
1959年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开始后,由于上层分子已经明显分化,自绝于国家和人民的反叛者和落后分子其时已成为革命对象,党的情感表达则不再透过上层,而是直接面向西藏人民。4月,毛泽东专门致信汪峰表示要研究藏族情况,并特别关注农奴制度、贵族对农奴关系等问题[3](P207)。叛乱平息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讲“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3](P211)。正是党中央立足对西藏社会现状和对西藏人民的情感,确定了民族干部选任培养的基本原则和实践方略。
(二)统战工作中的情感互动是选任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方式
运用统一战线主要从少数民族上层中选任培养干部,成为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进行干部选任的最主要方式,这不仅是开展西藏工作的一种审慎策略,还贯穿着党与少数民族群体的情感互动。首先,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情感为党和少数民族上层所共有,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又为少数民族上层对党建立信任与认同奠定了基础。进而,结合统战工作,通过一系列对少数民族上层群体和个体的尊重与关心,在落实协议、未来实行民主改革和保障上层权益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构成了二者的情感互动。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一批民族上层人士成长为民族干部,完成了从工作岗位到情感认同的转变。
这体现在党中央的若干工作细节中。如1950年5月中央在批准西南局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条件时专门回电强调“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应改为“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3](P18)。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党中央多次指示“任何上层分子,只要他不是顽固的帝国主义走狗或蒋匪帮特务,我们都应争取”[3](P80)。在党的具体工作中,也体现着情感互动⑧。昌都战役结束后,王其梅、吴忠等同志并未按俘虏对待新任昌都总管阿沛,而是请他仍住原总管府,自己搭帐篷住,部队虽严重缺粮,仍让其享受首长小灶待遇,并帮助阿沛找到在战役中丢失的心爱物品。在十八军干部感召下,阿沛的立场和工作重心不断向党转变⑨。昌都战役中被俘的代本及四品官员则通过照顾日常饮食、发还私人财物、开座谈会、交流学习藏语、释放后仍发给生活费等方式开展工作,并吸收为昌都解委会成员,他们深受感动,对党和解放军信任大为增强[10](P84-86)。
党对西藏工作的具体安排,也影响着西藏上层,并使之产生情感认同。如协议签订后,张经武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桑颇·登增顿珠等离京赴藏。李济深、董必武、陈云、黄炎培、李维汉、吴晗等十余位首长并组织中央民族学院学生四百多人前往车站送行。三位代表深受感动,为抗美援朝总会捐款一百万元,并表示回去以后,还将发动西藏人民开展捐献运动[11]。1952年6月,张经武特意邀请阿沛全家到住所玩,并特为他组织了一个小型晚会。一个月后,阿沛在拉萨借用一场地,专门回请工委同志们前去游玩。在这一过程中,“大家已经谈笑风生,亲密无间”[12](P90、93)。西藏工委在总结一年来进藏工作经验中谈到,“在初期,通过走访、送《协议》上门和请客(主要对上层头面人物和有影响人士)从感情上接近到交朋友……,这一工作在西藏地区是极为重要的”[12](P99)。
这一时期,组织参观团赴内地参观,在选拔培养干部方面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方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并宴请参观团,传递和表达对西藏上层贵族和人民的情感。1953年毛泽东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时讲“西藏地方对于中央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天靠拢的”,并表示“中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一定会帮助你们”[3](P102-103)。1953年赴京的西藏青年参观团不仅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还应邀列席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安排全团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三个月,从而“加深了对伟大祖国的了解和热爱”[13](P42)。拉鲁·次旺多吉回忆1955年赴内地参观受到中央领导接见的情形时谈到,“在聆听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教诲之后,心里也考虑着回去后,要着手逐步实行改革事宜”[14](P12)。正是通过统一战线的情感互动,少数民族上层逐步实现由地方政府官员向民族干部的转变。
(三)对少数民族干部坚定信任、依靠和使用
建诸情感之上的干部选任培养,直接体现在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对民族干部的坚定依靠和信任上,并通过民族干部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这一点与“南下干部”主导基层政权建设的特点不尽一致。这一时期,党中央多次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毛泽东在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立即强调恪守协议并指示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3](P55)。此后,党中央在关于西藏事务的多次指示中,都表达了依靠西藏地方的态度。如1953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时讲:“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3](P103)。1955年3月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中再次强调“实行区域自治是真正的自治,主要是依靠西藏自己的干部”[3](P118)。
在实际工作中,信任依靠民族干部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进藏部队先遣支队300余人进藏时面临自然环境和粮食供应等诸多困难。在进藏无详细地图且不明道路情况下,平措汪杰等藏族干部担负向导、翻译、调查情况和组织牦牛运输、选择营地、识别有毒水、草和介绍高原气候常识等一系列工作,而阿沛和夫人与先遣支队同行入藏,更是协助先遣支队完成筹措粮食等重要工作[15](P115-116)。
对于依靠民族干部的道理,1956年毛泽东在听取甘孜和凉山改革和平乱问题汇报时,曾讲道:“我们是共产党,就要做到民族之间的完全信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本地人总是了解本地的事,即使有些话说的不对,也只能用同志的态度去说服”[3](P169)。
(四)通过开展民族干部工作以联系群众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党选任培养民族干部的基本出发点在于联系群众,即建立与群众的情感。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后,党中央西藏工作的方针即强调,“争取群众”,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并指示西藏工委,“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党中央对比分析到,“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3](P68-71)张经武在进藏三年的工作总结中也认为,上层群体爱国观念和政治觉悟的增强,是西藏未来发展的骨干,而贸易、修路和教育、医疗等事业则对培养干部和西藏事业更进一步有重大积极作用[16]。
十八军等部队进藏之初,就要求时刻注意党的形象和与人民关系,以获得少数民族上层和人民群众认可。陪同张经武一行进藏的帕里宗宗本索朗塔杰就曾着重记录了张经武沿途婉拒当地头人和群众馈赠礼物的过程[17](P56-67)。军区和西藏工委也通过对少数民族上层的工作来团结教育群众并收到良好效果。据张国华回忆,“我们朝拜各寺庙的行动,轰动了拉萨,传遍各地。反动派制造的‘布达拉宫铜佛流泪了’等谎言,一下子就破灭了”[18](P102)。1951年11月至次年元旦,阴法唐、陈子植率访问团访问江达、雪卡等九个宗时,首先是走访当地上层人士,拜访寺庙活佛,发放布施等,在上层头人支持下,开展影响群众工作。如在朗宗开了一周的宗本头人会议,进而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协议,同时放映电影。“广大群众都是第一次看电影,有种说不出来的高兴”“一次在一个头人家里发现有几十个被关押的珞巴族奴隶,经过与头人协商,征得头人同意,把他们放出来看电影,这些奴隶们欣喜若狂,激动万分,觉得这是第一次过上了人的生活”。在此过程中,“藏胞的态度也由怀疑变为信任,由疏远变为亲近”[19](P104-114)。正是在党立足统战上层选拔干部开展工作,成功实现了通过上层影响群众,从而使党实现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不断充实在西藏的工作基础。
四、民族干部选任培养工作的实践成效
选任培养民族干部首先打开了实现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局面。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工作受到帝国主义的强烈干扰,天宝、喜饶嘉错等代表新中国和藏族群体,向帝国主义企图分裂西藏的图谋表达了鲜明立场,并投入和平解放西藏工作中。党中央依靠东藏青年团等干部力量和在西康、青海等地的统战工作,发展壮大了民族干部队伍,为进军西藏稳固后方发挥了重要作用。昌都战役后,党继续秉持统一战线方针,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祖国大家庭对藏族的深厚情感传递给西藏上层和群众,将解放军的良好形象展示给藏族人民,进而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并发展了阿沛·阿旺晋美等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十八军和西藏工委到拉萨后,延续和发展这一干部选任培养模式,不断巩固工作基础,推进联系群众。军地工作干部分驻西藏各地后,普遍建立起以由党组织牵引,以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并围绕宣传、贯彻和执行协议,“给群众做好事”,共同建设西藏。不仅西藏工委和进藏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青藏、康藏公路也在藏族干部群众的支持下竣工,为建藏治藏提供了保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中央已经逐渐培养起一支以西藏上层为主的民族干部队伍,并结合宣传、文化、教育等工作推进,实现对群众的影响,不断改变群众对党和解放军的认识。至1959年西藏部分反动分裂分子发动叛乱之时,少数民族上层群体形成分化,为平叛和民主改革提供了支持。此后,党扩大了民族干部的选任培养渠道,更多面向劳动群众选拔并依托民族院校培养干部,至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后,党在民族干部选任培养方面的渠道和形式不断丰富。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的民族干部选任培养贯穿着深刻的民族情感,并伴随政治教育、宣传动员和政策实施的一系列情感互动。在党组织与干部的情感交流中,干部思想观念和认识得到转变和塑造,实现“对党忠诚”。在团结领导西藏上层共同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任务后,在推进民主改革,解放西藏人民的新任务中,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因固守自身利益,不能联系群众,党则通过和平赎买和直接面向群众选任培养干部等方式开展民主改革。这一变化,体现了党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对党忠诚实际是对人民忠诚的本质。
[注 释]
①一般将1950-1959年确定为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并分为实现和平解放和排除干扰执行协议两个阶段。参见《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理论与实践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组:《中国共产党西藏政策的内涵及决策模式研究》,《中国藏学》2011年2期。
②目前有关党在西藏工作的民族干部选任培养研究仍以文献梳理和历史回忆为主。如赵重山:《西藏军区藏族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回顾》,《中国藏学》,2001年第2期;徐万发、柳欢:《论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党的爱国统战组织建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2期;屈鸿罡:《中国共产党西藏基层组织建设的历程、成就及经验分析》,《西藏研究》,2019年3期;高中伟、田向勇:《新中国成立70年来西藏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回顾与展望》,《兰州学刊》,2019年8期;李荟芹:《和平解放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上层统战工作探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1期;[美]梅·戈尔斯坦等著、黄潇潇译:《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③参见王小彬《中国共产党解决西藏问题的“和平解放,暂维原状”方针的历史由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2期。
④西藏公学即为今西藏民族大学,首批学员共3415名,其中藏族3129名,80%出身翻身农奴家庭。参见西藏民族大学官网“历史沿革”。
⑤1950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我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在上报的印度外交部约请使馆政务参赞申建谈话的报告上专门批示:“周并外交部:申健答的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⑥自元代藏传佛教向中央王朝寻求支持过程中,就将以转轮王和菩萨化身称呼世俗统治者的做法扩展到了蒙古和汉地统治者。明清时期,皇帝多被认为是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
⑦如刘曼卿入藏时即携带蒋介石照片等作为礼物馈送西藏上层。党中央代表张经武入藏时,也携带毛泽东等领袖像作为礼物馈送西藏上层和群众。
⑧这一情感互动首先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达赖、班禅的交流联系。在这一过程中,班禅成长为爱国宗教领袖和党的干部,达赖在1959年前产生的很多积极认识与情感变化也与进京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流有密切关系。可参见周良书:《毛泽东与班禅及达赖的交往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关注西藏发展的一个侧面》,《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6期。
⑨曾担任十八军先遣侦查科科长的王贵,对十八军开展对阿沛的统战工作有具体描述。可参见王贵、黄道群:《十八军先遣侦察科进藏纪实》,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6-88页。此外,曾任阿沛随从官的金中·坚赞平措对这一情况也有回忆。参见《昌都解放前后》,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九),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