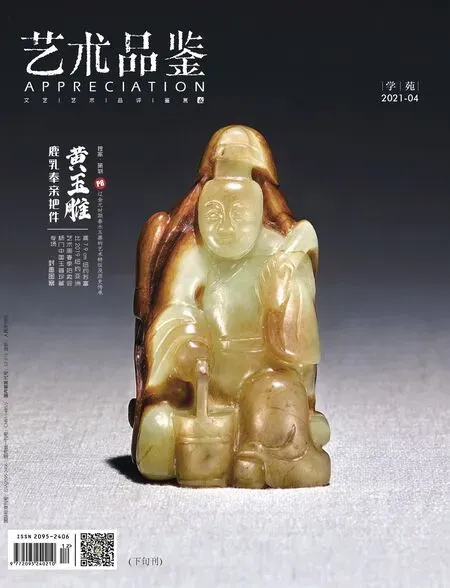钟表的“物体系”与近代中国的时间观念
2021-12-03曹珑颖
曹珑颖
现代化进程以时间观念的变革为先导,而近代中国是时间观念转变的重要时期。时间观念在晚清至20世纪40年代的变迁与社会现代化同步行进,它既与当时的政治变动相关,也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正如《时间观念与社会背景》一文中指出的,共同的历法和时制、城市的标准钟,民众的手表是现代国家的必要要素,它提供的准时性、对速度和高效的追求以及期限感都成为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和心理机制。[1]这意味着机械钟表作为时间观念的实质化表征,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物的认知修辞学”:一种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有关时间的思想历史来看,相对于时间本身而言,计时的器物并未获得与时间本身同样程度的重视。为了探讨机械钟表的传入如何影响近现代中国的时间观念的转变,本文借鉴鲍德里亚有关物体的语意结构系统分析,将物作为一种放在文化环境里的语言,探讨与物相关的语意修辞如何影响有关物的认知。
在鲍德里亚的物质文化理论体系里,物并非是对文化现象的简单反映,而是在物的功能性基础上形成符号性要素来反哺于社会活动。“物体系”就是在使用层面上的功能系统和在价值层面上的符号意义共同组成的语用结构系统,它关注生活中的人与物产生关联的过程,以及人由此生成的行为系统和认知方式。可以说,物作为一种隐喻塑造着人们有关物的概念,作为文化研究,需要侧重关注的是作为非本质性的造型、气氛性的感知部分如何塑造了我们对于物的认知并接受了物。
相对于其他机械产品和科技,机械钟表在中国的传播和认知接受的速度是无可比拟的,钟表已经不单单是实用的计时工具,更是文化交流的途径。在晚清民初的近代中国与机械钟表产生关联的过程中,着重关注机械钟表的造型变化如何嵌入大文化语境,机械钟表作为时间的一种隐喻如何塑造了人们新的时间知觉和时间概念。
二、钟表的“物体系”:塑造现代时间感知
就物的结构意义系统而言,必须承认科技的层次能够对物的变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相对来讲,审美上的秩序感和装饰上的艺术变化对于物的本质形态是非根本的,但后者对于人们感知、理解和接受物以及由物承载的概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形成时间意识的最初阶段,机械钟的形态同样构成了整体的功能系统,起到了触动新时间意识生发的效果。
(一)时间祛魅:从情景模拟到现代中性化的造型风格
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有关计时装置的发明。传统中国的时间体验是基于具体情境的,时间意识在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生产经验中产生,它确立的是“做某件事情与某种环境条件、情境状态的内在关联”[2],因此传统农耕社会对时间的解读具有高情感的心理密度。早期的计时器物例如圭表、日冕多结合自然光影推测时间,而漏壶则是利用水位变化的直观原理,在蓄水壶的水由滴水孔流入受水壶后,通过观测壶中刻箭上显示的数据来计算时间。这些计时装置都与具体的自然原理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模仿具体的自然运作方式以实现计时效果。
当欧洲的钟表工厂和经销商在针对近代中国的市场需求,尤其是皇帝的个人兴趣取向进行机械钟设计时,同样保留了模仿具体情境的逻辑,但自动化的机械运作已经有效地满足了计时的精确性和时刻单位的规整性,原有的模仿成分便向着非功能性的成分演变,作为机械钟表的艺术装饰存在。以铜镀金象驮琵琶摆钟为例,这顶机械钟与琵琶的造型融为一体,到了报时的时辰,驮钟表的大象的眼睛、耳朵、鼻子、尾巴均活动起来,布置于周围的料石花随之转动,底层乐箱的门自动开启并放出音乐,有小人在溪中泛舟,设计精巧且悦人耳目,能充分让人注意到时间的报时效果。晚清华丽繁复、金碧辉煌的钟表通过争取装饰性的审美认同,将有关标准时间的意识深入到了私人意识层面,孕育了有关时间感知的新型经验。
随着工业技术的演进,制造材料的选取和机械钟表的形象色彩走向了中性化。到20世纪初,晚清宫廷里常用的金属材质逐渐减少,而且表罩的材料也从黄仿丝棉套演变成玻璃。[3]金属材质在时间中的持久性和固定性似乎在证明时间的恒定在场,这与皇权的至高无上和金属的奢华以及触不可及感相联系在一起,而玻璃相对于黄金和珐琅彩而言在审美强度上更倾向于一种中性的现代审美效果。玻璃不会产生偏好,不会随时间演变而改变形式,而且不会遮隐内容,非热导体的性质可以阻止任何混淆。它建立了内容和形式的透明性,由形式的透明可以将人们对钟表的关注从外部设计引导到钟体的内部空间,同时也是将规范计时引入到内在时间意识和行为规范中的象征。玻璃营造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客观感,人们看着时间的演变在玻璃搭建的剧场内上演,指针的机械行走似乎表明了时间会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循环往复的传统时间观念在潜移默化中被机械钟表的中性化造型所祛魅,时间不再是神秘的东西。
(二)自动神话:从造钟处到工业化的绝对地位
从顺治朝开始宫内便有了钟表制作,造办处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专门承接皇帝下达的制钟任务,所以晚清时期的钟表设计中皇帝参与很大一部分,其产品具有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体现了皇帝的个性色彩。20世纪初期出现了工业化造钟场,产销的对象也走向了沿海地区的百姓大众。[4]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系统化的生产处理方式促进了机械钟表造型中性化的现代工业进程。这种现代化生产方式大大减少了钟表匠参与机械钟表形象设计的主动性。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与机械钟的自动化紧密关联。机械的自动属性是让渡出人的一部分主体意志来获得物自主运转的标志,所以自动化并不仅仅是技术理性和人类解放的实现,更是一种耗费最少的力气而达到最多功效的希冀,它确立了时间的绝对地位。
与绝对时间相对应,自动化让机械钟进入了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上海江海关大楼装点着东亚最大的机械钟表,这口大钟完全按照英国的大本钟复制而成,与伦敦大本钟一样每十五分钟和一小时鸣响一次,它位于十层楼高的海关大楼顶上,使得钟的四面都能被外滩的人看见。如此巨大的钟体的相对大小可以提供一种尺寸感,即以市民自己的身体感觉为判断其他事物的大小,从而能基于人体产生相应的掌控测量单位的心理概念。巨大的物件可以在公共场合起到宣告作用,于是公共场合的机械大钟确定了生活的步调,为了融入现代经济领域,机械钟被当作一种标准化且大于人力可控程度的度量,用以统一和安排人们的公共生活节奏,规定日程安排的社会机制也基于此形成,嵌入到人的内在意识之中,与人的主体意识发生关联,由此可以看到最初那些外部强加的标准时间制度逐渐被内在化,形成了一种自觉强加的绝对定律。
(三)具身联结:由“钟”到“表”的迷你化嵌入
机械钟作为器具只给出了隐喻世界的参数,还必须把这些参数运用到每个生活空间当中去,“钟”到“表”的具身化和迷你化的过程为生活化的使用提供了更多的场合。微型迷你的物体的美学内涵就是它“占据着被控制的空间,而微型物体本身又可以被控制、被拥有”[5]。
伴随着迷你化过程,机械钟表的使用逐渐私人化,进入到收藏的语境,与人的主体性发生具身性的联系。怀表是收藏时间的象征,它从公共场合里的社会时间中脱序出来而进入私人化的收藏语境。私人语境也是主体实施操控的领域,在每个人不同的操控结果下就会形成各异的修辞效果。
钟表作为隐喻其真正的符号所指不仅仅是机械之物,还包罗了有关时间的感知。当收藏的对象是机械表时,收藏的行为本身也在指向着私人时间。收藏品通过日常使用的行为修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收藏品承载的概念的碎片化和个人化,私密的结果与个人主观的态度有关。但进入收藏语境的机械表不同于其他收藏品的地方就在于它用永动的机械说着无终无止且绝对客观的时间,它区隔出了一个不为个人所能控制的部分。其他收藏品逃脱了市场生产流通的序列,进入到受主体把玩的主观收藏空间,释放出的超越社会群体力量,而机械表则一方面在解耦着与公共时间的关联,这个是由收藏行为赋予的。另一方面又在重新联系起客观时间,这则是机械表作为客观时间的隐喻所赋予的。因此,机械钟表代表的就是客观时间,尽管被收藏的语境进行私人化的使用方式,但个人对机械钟表的具身化使用却形成了客观时间向着私人时间的渗入通道,个人有关时间的计算认知借助机械表嵌入了私人时间的体验当中,私人化收藏语境下人与机械钟表建立起亲密的具身性联结,绝对时间观念在内在时间意识中生根。
三、结语
总而言之,机械钟表在与人发生的实践关系中被赋予了重要意义。钟表的发展集中体现了机械技术在时间计量、时间管理方面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它们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精确化计时和控时;工厂和学校作为受严格时间制度控制的现代社会组织,前者体现了工业化生产形式之下时间与工作纪律、劳动精神和报酬获得之间的严密关系,后者则反映出现代学校时间管理的严格和科学化特征,它们最能代表工业化时代时间被精确计算和管控的特点。
除此之外,由阳历、各种纪念日、各类控时精确的时刻表所编织的时间网络,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笼罩着公共领域,一个新的时间计量工具的使用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扩展和面向公众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