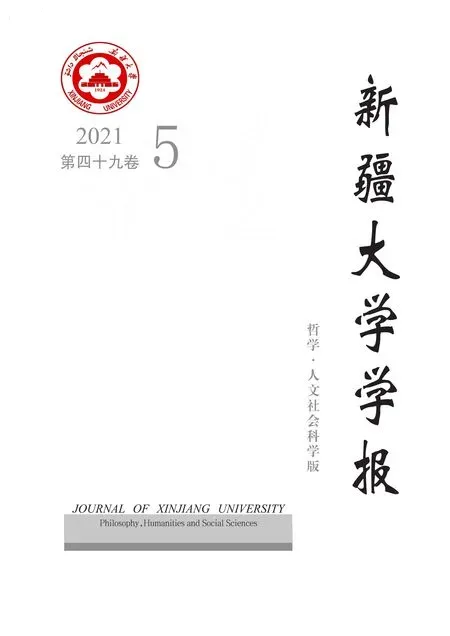空间转换中的悲剧隐喻①
——重读《德伯家的苔丝》
2021-12-03张春梅郭丹薇
张春梅,郭丹薇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214122)
托马斯·哈代(以下简称“哈代”)最负盛名的“威塞克斯小说”主要描写英国19世纪末在工业革命影响下渐变的宗法制农村生活,传统农业被工业机器取代,倚靠土地生存的农民被迫遭受生活方式的转变,其命运在劳动力迁移中几经流转。挽歌色彩在哈代笔下主人公的“城市”与“乡村”的迁移间,成了19世纪中后期英国气质的表述之一。“城乡空间”书写作为哈代小说的重要特征,是哈代研究中的关键部分。然而,在空间理论视域下将空间转换与悲剧性结合起来进行文学社会学、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研究却是少数。空间转换中的悲剧如何发生、具有何种隐喻性质,城乡转型期中不同阶层、不同空间人物关系所面临的精神矛盾如何在文化地理上互为表达、彼此关联,这些问题并未在现有的哈代文本空间研究中得到解答。
在哈代小说特别是《德伯家的苔丝》[1],因对威塞克斯地区贴近现实生活的描述以及随着主人公在不同城市、乡村位置中的流动,其中的“地理空间”就成为典型的“空间”对象。这些地理景观并不只是单纯的物质地貌,更是一种可解读的“文本”,有其深厚的隐喻体系与精神内涵,因此可称为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文化表征。借用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划分,哈代文本中的空间不仅是表征的空间,亦是空间的表征。那么,这些充满表征性的空间符号如何结构起整体的悲剧意蕴,人物、空间与社会又是如何建构起哈代眼中的英国世界,就成为本文“重读”、立论和思考的基点。
一、空间理论与哈代小说中的空间书写
传统的“空间”研究并不少见,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牛顿、胡塞尔、海德格尔,都对“什么是空间”有所论述。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专辟“空间”章节,指出“恰如容器是能移动的空间那样,空间是不能移动的容器”[2]。笛卡尔则认为“物质的本性仅仅在于它是一个广延的东西”[3],“长、宽、高中的同一广延既构成了空间也构成了物体”[4]。到了海德格尔,他将人对空间的认知纳入“空间”的范畴之内:人在空间中的生存实质是“在物和位置那里的逗留而经受着诸空间”[5]。显然,这些论述都离不开固定之“物质”与流动之“精神”。直到20世纪中叶,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注意到“空间”的社会性,进而打破了一直以来物质、精神的二元对立格局,提出“空间是社会空间的客观化,也是精神空间的客观化”[6]22。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具有生产性,由各种社会关系生产出来。他阐发了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观点,结合当时工业城市的发展,拓展了社会空间理论。在他的理论中,空间不再是原有的几何物理概念,也不单单是一种精神的“主观存在物”,而是一种“历史产物”,与社会的变化发展相关联,体现出社会的实践活动。如他所说:“空间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它是中性的。它首先会表示出来自己没有意义,会表现出它空洞的特征,通过这种中性的、明显的空洞性,还会表现出某种在整个社会(即新资本社会)层面上的东西。”[6]18也就是说,在这种“中性的”“空洞的”地方,社会要素得以再生产,从而表征出其背后独特的文化内涵。空间成为这一“再生产”的场所,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正是我们理解空间的重要手段。
在列斐伏尔这里,空间被划分成为三种类型,即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以及表征的空间。文学——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媒介,从属于“表征的空间”。“表征的空间包含复杂的、有时被编码有时没被编码的符号,它关联着社会生活中的私密方面,也关联着艺术,该艺术最终更多地是被定义为表征的空间的一个符码,而不是仅仅作为空间的一个符码。”[7]33小说家通过文字将世界重新进行“再加工”“再展示”,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空间就成了一种“被编码过的符号”,对文学中的“空间”要素及空间中社会关系的探讨成为解读文学文本的一种方式。
作为一名从多切斯特出来的学徒,哈代熟悉乡村和城市两种空间的文化生活,这从他小说中主人公活动的主要场所大略可见。《还乡》①参见托马斯·哈代《还乡》,孙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中的克林和游苔莎两夫妻,一个厌倦了城市生活,渴望大自然的宁静平和,梦想返回乡村;另一个则一心想离开穷乡僻壤,去到人群熙攘的富庶繁华之地,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追求者,两人对城市和乡村无法调和的矛盾态度成为悲剧的导火索。而像《无名的裘德》②参见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刘荣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男主人公裘德虽出生于农村,但对城市(基督寺)心怀向往,然而走出了“乡村”的他,却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这就在城与乡之间架起一面互为镜像的界面。哈代借裘德的悲剧和痛苦表现了乡民阶级企图通过教育手段摆脱自身阶层的失败,而乡村和城市暗喻着以阶级区隔的社会空间,城与乡的矛盾前所未有地被放大和彰显。《远离尘嚣》③参见托马斯·哈代《远离尘嚣》,傅绚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和《卡斯特桥市长》④参见托马斯·哈代《卡斯特桥市长》,张玲,张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则更集中地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乡村和城市界限的渐趋模糊和人的生存困境。显然,在哈代的小说中,城、乡空间一直都是文本中的关键。
早在1984年,达比就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空间已有过评论: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小说的世界由位置和背景、场所与边界、视野与地平线组成。小说里的角色、叙述者、以及朗读时的听众占据着不同的地理和空间。任何一部小说均可能提供形式不同、甚至相左的地理知识,从对一个地区的感性认识到某一地区和某一国家的地理知识的系统了解⑤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提到,文学形式是地理学者研究地理景观的一个途径,通过与地理有关的重要作家作品就能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就是典型,并且文章中还引用了达比对哈代小说的评论用以验证这一观点。参见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页。。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这种“小说角色占据着不同的地理和空间”的说法体现得非常明显,小说中的人物裹挟着所生活的物理空间,因为人物的活动和关系转换使物理空间承载着不同的社会空间功能。换句话说,物理空间就是社会空间。伴随主人公在各个空间的流动,不同社会空间能够交往流通,小说悲剧性主题得以表现。
正如迈克·克朗所言:“托马斯·哈代对威塞克斯人以及他们的风俗和预言的描述与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谐一致,他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也被看作是为纪念田园生活的结束所作的挽歌。”[8]纯洁善良的苔丝从小在布蕾谷长大,因一场“撞马事故”被迫离开家园,从此流连辗转于纯瑞脊、芙仑谷、棱窟槐、沙埠等地,跟随苔丝在各个空间中的流动,就会发现,哈代对这些地理空间的描写并不是凭空设置。他将苔丝的命运与现代工业革命对乡村自然的入侵联系在一起,每个地域的空间属性和空间中生活的人,都暗藏着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隐喻。纯洁质朴、“毫无人生经验”的苔丝似乎象征着那个自然封闭的乡村空间;亚雷背后矗立着伪善、狡诈的新贵资产阶级场域;安玑·克莱则代表着一个已初具成型但还仍显脆弱的现代文明空间。三个人毋宁说三个空间之间的纠缠,最终在沙埠——这个新兴的城市中走向末路,从而表现了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自然”“乡村”受到现代文明、新贵资本主义影响,注定没落的一场社会悲剧。
二、布蕾谷:传统纯朴的乡村空间
小说一开始就对布蕾谷那种自然、闭塞、未被俗世侵染的乡村空间做了描写。群山环抱、幽深僻静的布蕾谷甚至“不曾有过游历家和风景画家的足迹”[1]17,在这个自然封闭的空间中,丝毫没有19世纪工业城市的侵染。其中的马勒村——苔丝从小长大的地方,“一片土壤肥沃、山峦屏障的村野地方,田地永远不黄,泉水永远不干”[1]17。这里除了有“篱路漫漫灰白,树篱低矮盘结,大气无颜无色”[1]18的自然风光,一些旧日的古风在改头换面之后也得以留存延续。如列斐伏尔所说,“举行仪式和庆典的绝对空间仍保留着一些自然的方面”[7]48,而安排苔丝出场时参加的五朔节舞会就是其一。这个节日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期,但“只有马勒村的游行会,还照旧延续,来维持本地的司瑞神节”[1]19。伴随着对闭塞自然的布蕾谷、传统旧日的舞会仪式的描述,还“丝毫没沾染上人生经验”的苔丝在此时登场。这些都好像预示着,苔丝这个自然的女儿不仅如布蕾谷一般的美丽:“身材高壮”“面容齐整”“闪烁的眼睛”“娇艳生动的红嘴唇儿”[1]19,同样,这个空间中的旧日宗法传统也是她无法隔开的文化质素。“任何一种人化的空间形式具有它所规定的价值取向,从伦理价值、美学价值直到政治价值,都有特定的指标、内涵、口吻、姿势和成色;空间也注定会将它随身携带的价值强行赋予每一个被该空间框架、被该空间挟持的人。”[9]在苔丝身上,封闭乡村空间赋予她的传统宗法道德价值与她不断面对的新生工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她一生悲剧的重要诱因。
哈代将传统、封建的乡村想象都放在了苔丝这个人物身上,小说中写到与苔丝经历类似的女孩并非没有,但她们并不羞愧,甚而嫁人生子,毫无影响。如芙仑谷的那个女工所言:“在情场里和战场上,用什么手段都应当。俺一定学那个女人那样,跟他结婚,俺头一个丈夫的事儿,管他是什么,管他怎么样。”[1]217但是对于苔丝——这个从小在布蕾谷长大的乡村姑娘,她自始至终不能放下自己“失贞”的事实,她完全接纳旧时的宗法道德,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不贞的女人、“是罪恶的化身”[1]104。苔丝不断地徘徊挣扎:“宗教的意识使她认为,前次的结合含有道德的效力,良心的驱使让她觉得,应该把一切情况坦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两种力量,没有一种能够使她长久坚持的。”[1]219最终,传统思想的枷锁、道德的谴责让她无法对安玑撒谎,选择吐露真相,坦白一切,也正是这一举动让她惨遭安玑的抛弃,促使自己的命运走向了悲剧高潮。在苔丝短短的一生中,不管身处何种困境、如何被诱骗,都始终坚持维护着自己的尊严和道德,即便后来为了家人不得不答应做了亚雷花钱买的情妇,然而苔丝见到克莱后的痛苦和最终杀死亚雷的举动,似乎让我们看到这个弱小无助的乡村女孩的坚守。但为什么呢?作者哈代的伦理立场或许给出了答案。
19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大城市开始兴起,新的资本主义道德渐渐占据城市,传统的宗法道德渐被抛弃,乡村的封闭为传统道德的幸存留有最后一点希望,哈代从苔丝的出场描写开始都一直和传统、自然、封闭的乡村空间联系在一起。这个美丽坚贞的女孩是他眼中那个美好、纯朴的乡村空间的化身,但同时传统空间中道德对人性的制约和束缚也在苔丝身上淋漓展现,正如哈代所说,“和实际世界格格不入的正是这些道德魔怪,不是苔丝自己”[1]106。随后,苔丝分别进入了不同的社会空间,并与其中的人物产生了各种关系,在他们彼此的相互交融中,一幅关于不同阶层空间的文化景观铺展开来。
三、从纯瑞脊到棱窟槐:工业资产的入侵
亚雷·德伯维尔的顽劣和伪善,让善良的苔丝一次次陷入命运的漩涡,最终走向灭亡。亚雷的活动场所主要在纯瑞脊和棱窟槐两个地方,与小说中出现的其他地域空间相比,哈代对这两地的描述明显展现出资产阶级对乡村的入侵现状。而且,从纯瑞脊到棱窟槐,伴随资产阶级对乡村空间的逐步侵吞,苔丝受到亚雷的迫害也在这两个空间的流动中越发加深。如前文所指出的,假如苔丝是传统纯朴的乡村空间代表,亚雷则象征着新贵资产阶级空间①这种发生在新兴资本主义空间和代表传统的乡村之间的矛盾,是19世纪文学社会关系的主要延展地点。。
纯瑞脊是小说文本中出现的第一个表现工业资本入侵乡村的空间,也是德伯维尔·亚雷首次出场的地方,对德伯的发家历程和他们院落的描写,我们能看到亚雷这个依靠商业致富的资产者和暴发户后代正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新贵阶级的典型代表。亚雷的父亲是英国北方的一个精明商人,为了回乡之后能让自己看上去更加“体面”盗用了“德伯”的世家姓氏,到了纯瑞脊,便用已经积累的资本财富侵占房产和土地。他们的宅邸在纯瑞脊的一处小山上,“这里没有田地,也没有草场,也没有发怨声、有怨气的佃户,叫地主用种种欺诈压迫的手段压榨剥削,来供给自己和一家的开销”[1]47,这是一所“完全、纯粹为了享乐而盖起来的乡绅宅第……由管家经营、试验着玩儿的田地”[1]47。然而,这样一处资产者“享乐”的建筑却是由侵占乡民的生存空间得来。苔丝喂养的鸡场本是一个乡民居住的庭院,但是等“这份产业法定的典期刚满,司托·德伯太太就满不在乎把这所草房变成了养鸡的地方”[1]48,旧房子的主人和子孙被立刻驱逐出去。福柯在对建筑空间进行分析时提出,“建筑作为一种能呈现权力运作的形式,以各种方式涉及权力的维护”[10]。文本中对亚雷宅院建筑的描写正体现了资产阶级权力对乡村的侵占和压榨。
撒旦般的亚雷就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出场,他顽劣好色,胡作非为,女人在他眼里不过是消遣时候的玩物,一副典型资产阶级的嘴脸暴露无遗。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亚雷夺去了苔丝的贞洁,让她陷入了命运的泥淖。可以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因社会的发展和工业进程的大潮,苔丝之于亚雷,就好比乡村之于资产阶级,已无力抵御这种不公正的压迫和侵入。
“工业革命侵入乡村之后,机器取代了人工,资源共享左右市场,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于是起了变化,原来的民俗风情、生活方式、语言习惯等都受到冲击而改变。”[11]在纯瑞脊,如果哈代对这种入侵的描写还只是初露端倪,那么到了棱窟槐,这种侵占的现状则更被鲜明地体现出来:资产阶级对乡村的侵占不仅仅体现在建筑等物质空间中,其中生活的人也因两者空间意识形态的冲突而异化。
小说写到棱窟槐到处是“颜色漆黑,老嘶嘶作响”的烟囱,好像“积蓄着雄厚的力量”,是“要当这个小世界里面主要动力的机器”[1]379。这个地方的人是“一个一动不动的黑东西,身上满是黑灰、乌煤,神气好像灵魂出窍的样子……态度和颜色都是孤立的”[1]379,这些“司机”虽然“身在农田,但却不属于农田。他所伺候的只是烟灰、煤火”[1]379,心里想的、眼里瞧的就是那个铁机器。小说对“棱窟槐”描述的桩桩件件就将这样一个被工业文明侵占的体无完肤的乡村空间彻底展现在我们眼前——原来自然的景观被工业革命的机器产物所替代,本来纯朴热情的乡民也成了现在“眼里、心里只剩铁机器”[1]379的“工作司机”。
亚雷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又在这样一个残破扭曲、深受资产主义影响的乡村空间中再次登场。他虽表面上“衣服更换,面貌改变”[1]381,化身成了一个福音教徒,但只“用眼一瞥,就可以明显看出,他原来的色欲之气,又满脸都是了”[1]382。此时的亚雷不只是一个依靠商业致富的资产者、奸邪淫乱的花花公子,更是一个披着“普渡众生”外衣背地里自私伪善的“宗教牧师”。到了这里,哈代借用塑造亚雷的形象,将资产阶级的面貌完全揭露了出来: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除了在经济地位上处于无可撼动的优势地位,同样,捆绑普通民众的话语权也掌握在这群人手中。至于苔丝,不仅身体上被“永不休止”的机器作业“累得筋疲力尽,后悔不该到棱窟槐这儿来”[1]381,而且她又一次遇到了“牧师”亚雷,是他引诱自己一步步跌入命运的漩涡,但这个始作俑者却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普渡众生”的“善人”,不用得到任何惩戒,这无疑给她疲弱的精神加上了又一把枷锁。苔丝被其用各种手段虐待、利诱和胁迫,直至为了家人的生计,被迫答应做了亚雷的情妇,抹灭了和安玑重归于好的最后一点希望。由此,棱窟槐中的负荷劳作加上亚雷的精神控制,将苔丝又一次牢牢地困在命运的苦海中再难逃离。
从纯瑞脊到棱窟槐的空间变迁中,一则我们看到乡村从地理空间到精神空间被资本主义逐步侵占的过程;二则在这两个空间的流动中,主人公苔丝的命运悲剧也伴随这种侵占进程逐步达到了高潮。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新模式对传统旧有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以苔丝为代表的底层农民迫于生计,只能沦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在精神层面上,“一切都不可捉摸和令人举旗不定,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展望未来”[12]。亚雷作为一个暴发户的后代,这种来自精神世界的无所适从就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起初殷实的资本让他丝毫不用为生存忧心,但是两种空间的文化冲突却造成了他空虚的精神状态,只能用世俗享乐来排解生活的无趣。之后他又转向宗教,成为一名教徒,但正如哈代在文中所说,“看他的眼光,世界的信仰和宗教的信仰,他同样地缺乏”[1]377。归根到底,亚雷身上的顽劣和轻佻是乡村人失去旧有传统却并未形成新的文化支撑时,陷入迷茫和失去道德准则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亚雷也是那个青黄不接的社会时期,深受两种空间文化入侵冲突的一个悲剧产物。
四、芙仑谷:新生的现代文明?
在苔丝遭遇纯瑞脊的厄运回乡生下孩子以后,她又重振旗鼓来到芙仑谷,并在这里邂逅了安玑·克莱。芙仑谷同样受到19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它不像布蕾谷那般的闭塞、传统,但也区别于纯瑞脊和棱窟槐那种完全被工业资本异化的空间。可以说,芙仑谷是一个同时包容着新时代文明和传统思想的空间。“这儿的世界,是按照一种更广阔显敞的图样描绘的……这儿的农舍,也都摊铺得更宽展,这儿的牛群,都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的。”[1]129苔丝觉得这里的空气也格外的“清新、爽利、飘渺、空灵”,河流也像“生命之河一样地清澈,和天上浮云的阴影一样地飘忽”[1]129,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让苔丝“觉得从未有过的快乐”[1]129。塔布篱农场主相信科学,在牛奶出现异味时,会主动查找原因,最后发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大蒜”,便发动工人一起清除。然而这儿终归还是乡村的世界,这里的人们也有着迷信迂腐的一面,如牛奶厂里的奶牛挤不出来奶,工厂的人就会认为是来了新人的缘故,只要大家一齐唱完民歌,牛又会重新挤出奶来。当机器搅拌不出黄油时,又会认为是农场里有人怀孕了。在这样一个新旧思想兼容的空间中,安玑出现了。
如前所述,苔丝身上寄托着哈代对旧时乡村空间的一种怀念、哀悼和对传统宗法制度的质疑,亚雷这一形象则指向对资产阶级伪善丑陋面目的揭露和批判,到了安玑,这个人物身上被赋予了现代文明的影子。一方面他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对传统持有怀疑的态度,是一个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不愿被父辈所累的新型青年;但另一方面,他又有着幼稚怯弱的一面,在面对严苛的宗法传统现实时,他懦弱胆怯,没有足够的勇气打破旧时的道德枷锁,最终选择逃避他与苔丝的爱之场所,以远走他乡来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
安玑“厌恶那种‘血统高于一切’的贵族偏见,认为人应该以自己的知识道德而受到尊重……他不仅在思想上‘极力想要以独立的见解判断事物’,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极力摆脱中产阶级家庭的规范,自己探索新的生活道路”[1]7。他身上具有强烈的叛逆性,坚持将现代技术带入农场,学习农业技术,不像父亲和哥哥一样成为一个体面的牧师,又放弃与一个和他门当户对且家境殷实的女子成婚,娶了贫困善良的苔丝。可见,安玑具有当时进步资产阶级的特质,他追求自由和平等,鄙视旧日的世家偏见,认为那些“古老名气根本就没有什么古色古香而言”[1]143,也完全“不赞成老门老户那一套的”[1]156。然而,他虽然清高自傲,追求自由理想,但实际上却和芙仑谷一样,并没有真正地与旧传统完全割裂。比如,他一边“在这儿住得越久,就越愿意和他们在一起,真正喜欢和他们一同相处”[1]143,一边又会觉得“和一个牛奶厂里的工人平起平坐,是一种有失尊严的举动”[1]143。显然,安玑虽然觉得好像“脱离了自己的阶级”[1]153,但“阶级偏见”还是隐密地盘踞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苔丝,安玑起初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女子,她漂亮美丽又懂得干农活,无疑是他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贤内助。然而当他得知苔丝并非如其所想的“纯洁”时,即便自己做出了更加伤风败俗的事情,也无法原谅苔丝的“不贞”,最终选择了抛弃和逃离,丢下苔丝一人面对现实的严苛和残酷。
与克莱·安玑一起在农场度过的时光是苔丝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日子,起初安玑进步、独立的“现代精神”给身处黑暗的苔丝投来了一束亮光,但他终归也只是“一个使人温暖的玫瑰色幻影”[1]159。安玑的胆小懦弱,让他无法完全摆脱旧日的传统烙印,就像那个新旧思想交织的芙仑谷一样,在两者之中不停地摇摆。19世纪的英国虽然刚经过工业革命,但却是一场极不彻底的革命,在新旧传统的冲突中,人们的思想还未完全成型,他们一方面受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等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影响,推崇自由、平等和博爱,另一方面传统的宗法制度和道德习俗依旧根深蒂固。在两者力量的激烈交锋中,不乏安玑这样一类虽追求进步思想、行为具有现代倾向却又难逃传统道德窠臼的“新青年”。在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中,哈代就让我们看到了当时那个追求进步却还稍显幼稚的现代理性文明在旧有宗法制道德面前的软弱无力。
五、沙埠:现代城市的诞生
“资本主义的发展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①参见韩子满《文学中的乡村与城市综论》(乡村与城市·译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页。,这种优先权就让城市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和象征空间。小说中出现的其他几个地域空间都是受资本主义影响的乡村空间,城市只是以一种“空间魅影”的形态出现其中,或隐或现地影响着空间中的人物,但是到了沙埠,哈代将这个现代化城市明晃晃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从建筑空间上看,这里是一个“时髦的海滨胜地”“一个辉煌新异、供人游乐的游乐胜地”,有“新奇宅第的屋顶、烟囱、望阁、塔楼,这个地方全是由这种新奇的建筑物组成,是一个各占一方的巨宅所构成的城市”[1]435。在这样一个富丽繁华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皆为这里的外乡人,但哈代却偏偏安排他们在这里走向结尾,就显得别有意味。
苔丝父亲去世,全家人又被赶出马勒村,迫于生存的苔丝走投无路,不得已沦为亚雷用钱买来的情妇,跟随他一起来到了沙埠。如安玑所说,苔丝这样的乡村姑娘与这个地方是完全格格不入的,这个“在旧世界上出现的新世界,无地可耕,也没有奶可挤,没有一个是可以让苔丝得以安身的地方”[1]436,当见到苔丝本人时,只觉得“她的肉体看作是水上的浮尸一般,让它任意飘荡,和她那有生命的意志各走西东”[1]439。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现代城市,连接“纯洁的”苔丝的乡村空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旧世界似已完全没有容身之所。苔丝被社会、被生活驱使而至布蕾谷,到沙埠,沉默了许久的对个体生命的无视终在与安玑的重逢中爆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个体意识的重新觉醒让她再也忍受不了亚雷的冷嘲热讽,举起尖刀刺向这个带自己坠入深渊的男人,最终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
在几番空间流转中,苔丝成了哈代倾注浓烈情感的自然乡村空间的象征,她善良纯朴又用严苛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无论如何反抗,终究难以摆脱亚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压迫。安玑身上关于“现代文明的影子”给苔丝灰暗的人生带来了一抹光束,但带着太多旧时代阴影的还未成熟的理性之光抵抗不了残酷的社会现实,甚而成了迫害苔丝的催化剂。苔丝对于新的工业社会,毫无疑问是排斥的,正像文中所说,她只愿意找一些挤奶、养鸡的户外农活,然而社会大潮的涌动却让她这个乡村驻留者不得不走向城市。在哈代笔下,苔丝被迫走向城市的这一路,也是她走向悲剧灭亡的一路,最终在沙埠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中受刑绞死,暗示着乡村注定被现代工业革命侵吞的社会现实。从空间的变迁看,苔丝的悲剧不仅是一个“女人的悲剧”,更是一出在社会转型期下的“乡村的悲剧”。而对个体的命运和前途的不可知,使苔丝成了社会转型期里无知无觉的大众代表。
我们看到,在空间与人物的关系流转中,作为在空间中“活动着的人”带动着空间发生着社会变化,于此,“空间”就不再仅仅是前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固定的物理场域,而成为打破物质—精神对立的具有现象学意义的社会表征。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这位被作者打上“一个纯洁的女人”标签的农村女孩,在不知不觉中被看似不可知的命运推向了漂泊的人生之路,空间的变化,映射出苔丝对生存境况的恐惧和渐趋麻木的心理。作者为了写出“纯洁”如何在破败的乡村和功利的城市之间留存,毫不怜惜这个农村女孩面对残酷现实的茫然和无措,以“相当现实主义”的态度引导读者走过乡村,经过小镇,终被机器和生存危机裹挟。从这个意义看,被打造出的“空间”浇筑上了浓厚的哈代“眼中的世界”色彩,成为19世纪后期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席卷英伦的“盛景”。而弥足珍贵的,还在于这一个“纯洁的女人”。苔丝一路走来,最大的打击并不在于身体“贞洁”的丧失,来自克莱的拒绝和抛弃也并没有将她完全击倒,在不断遭遇困境中的“女孩”一直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地走着,使她坚持下来的是早已内在化的、不失原始意味的“道德力量”,并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伦理。这种道德之力,或伦理之力,既支撑着苔丝的心理建设,同时也化为一道道绳索,逼使她只在简单的判断中决定自己的行为。她的“死亡”之途以及直白的“恨与爱”见证了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对“自给自足”的“原始”生活猝不及防的沉重打击。在这一过程中,内心中浅淡却执着的“苔丝感到”“苔丝想”化为一把直面艰难时世的自我之剑,描绘出面色愈趋苍白的姑娘,在苦难的人生历程里,不曾丧失的“单纯”世界。这一世界,被哈代铭刻在“威塞克斯”,那遥远却终将会被机械化生产侵蚀的“乡村”,显然,这是精神性的、原乡性的,是人们对即将逝去或已然逝去的理想社会的留恋和怅惘。
哈代笔下的空间就像建筑师手中的模块,不同位置牵连着不同人物的命运。建筑空间划分着人群,自然空间形塑着不同的文化需求,这些空间组成彼此交叉穿梭的社会空间,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情感结构在“人与空间”的互为作用下残忍而真实地呈现出来。以“一个纯洁的女人”命名文本的哈代,带着悲悯而无奈的目光看着在伦理、生存与爱情之间辗转的苔丝,走出乡间,走向繁华之地,却仍如裘德般没落于爱敦荒原。显然,城与乡已经不单单是地理、界限,或者特定的生活方式,“空间”已经开始重新规划人群,一个“崭新”的世界已然袭来。只不过,作为彼时情境中的体验者,哈代深感资本主义对乡村田园的侵袭,又对初展头角的现代文明缺乏信心,这让他的作品充满着世纪末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