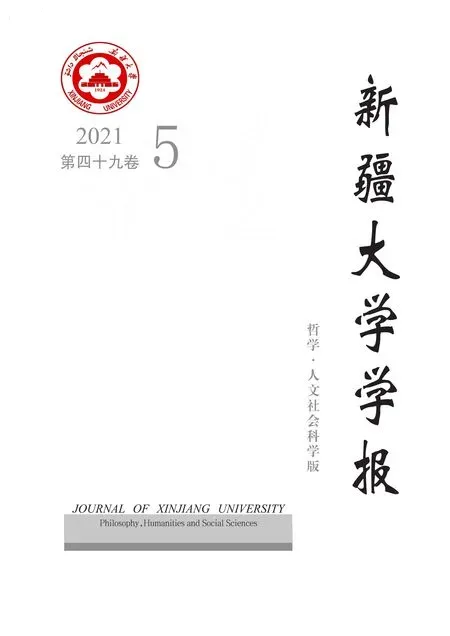民国国人新疆游记中的比拟与江南文化意象*
2021-12-03成湘丽
成湘丽
(新疆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46)
就通常以为,在新疆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比较中,新疆势必居于劣势,民国时期国内其他地区行者关于新疆之想象也必然与荒凉、闭塞、穷困相关,尤其是那些未来过新疆而论新疆者,“多以其辽远,臆料地必艰穷,人必陋野,气候必酷烈,而不足一顾”,但吴绍璘同时还指出,“除少数奉公其地,或经商此间者,鲜有灼知实情。须知其地未必尽穷,人未必尽野,气候未必便尽酷”[]113。的确,民国时期大多数行旅考察过新疆的文化人,除险遇兵荒马乱或辗转乱世的个别者外,其笔下的新疆形象大都会呈现出正面、远大的发展前途。其中缘由,笔者以为主要不是为补偿自己的思乡情浓或有意美化的儿女情怀,而是源于这些知识分子塑造家国集体记忆和中华文化一体的必然话语选择。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作者频繁将新疆风景与国内其他地区生活、桃源理想、江南意象相类比,表面看这源自行旅者在广袤艰辛的新疆行旅中偶遇绿洲安稳生活的一份惊喜,就如余应霖形容初到哈密的感受,“朋友!你试闭着眼睛想想,在一个广大辽阔的沙漠中,能找出一片苍苍的绿荫……能不使你欢喜若狂,这风味该不会差过春之江南吧!”[2]从深层看,大量国内其他地区行旅新疆作者以国内其他地区地名指代新疆富庶之地、以桃源胜地取代偏僻荒凉之景、以联想江南类比新疆大小绿洲,并非是一般以为的以自我文化覆盖淹没“被注视者”,也非以文化吹散消弭固有文化,而是潜藏着行游者试图建构国内其他地区—新疆文化一体化和心理共通性的深层动机。在此投射下所形成的感觉文化区和类型化意象,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理念在边疆的精神濡化和文化传播、回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疆的凝聚历程和文学再现、感受中华文化集体记忆在边地的千年承衍和文本储存,尤其是对于我们进一步打通新疆与国内其他地区之间根脉相通、共融共生的文明进程,提供了一条看似曲折、实则敞亮的历史通道和记忆门径。
一、将新疆繁庶之地比诸国内其他地区
古代西域游记更多是基于中原中心观念的统一天下观,新疆因此便是传统的蛮夷之地、流放之地,即使是《穆天子传》也莫能其外,虽然看来是主客平等,但实际上还是潜藏着天朝心态。随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深入和新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民国虽然也有不少游记涉及到对新疆当时黑暗军政和频繁战乱的批判,但从游记作者们对新疆的整体印象看,当以赞美新疆的自然风光和淳朴民风为主流,并常将新疆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提并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积极正面新疆形象的传播效应。
早在民国初年,贾树模就指出新疆“应具乐观主义者有七”[3],即土地广袤、气候中和,地味肥腴、水利充足、农产丰饶、矿产富饶、无虑外患,其新疆形象还大体呈现出与国内其他地区(故乡)印象两相呼应或者彼此暗合的相似性来。其实早在清末,行旅者在身处少数相对富庶繁荣的新疆城镇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国内其他地区比较成熟发达的商业城市,如方希孟见迪化“至十字口为大街,廛市喧嚣,铺屋整丽……大似京都前门景象”[4]141。这类印象也频频出现在民国新疆游记始终,如谢彬说迪化“政界在前清时,湘楚人居十之九,散军留此种地者亦多,当时有小湖南之称”[5]108,称惠远“益以伊犁将军缺优全国(次为四川将军),不赚不贪,一年百万,幕游上客,恒数十百人。文酒风流,盛极一时,有‘小北京’之目”[5]147。吴绍璘也称清末伊犁惠远“市肆极称繁华,有小北京之誉”[1]137,称清末迪化“商肆多为平津人所经营,故无异北平之大栅栏一带风味……当全盛时代,目为小南京”[1]129。李德怡《北草地旅行记》也称迪化有“小南京”[6]23之称,绥来、连木沁有“小四川”[6]30之名;吴蔼宸也说左宗棠西征后,新疆“一时传有小湖南之称”[7]188-189。
除了城市地名的相似联想外,行者还多将新疆自然风光与国内其他地区名胜佳地自然联想起来。如1911年5月初袁大化出哈密界,北路天山“望之如海外蓬莱,时没时露,奇景毕肖”[4]213。谢彬称伊犁果子沟“山水之奇,胜于桂林。岩石之怪,比于雁荡”[5]145,穿行在库车铜厂附近的山间,感叹“人行其中,疑在港沪洋场”,“昔人云:五岳归来不看山,此又非五岳所能比也”[5]169,在水磨沟见“有巨泉涌出,泡高数寸,若济南之趵突泉然”[5]120;徐戈吾也称水磨沟“温泉柔润,不沾肌肤。浴后,心怡神爽。非寻常温泉所能相较。南京汤山,西京华清池之外,水磨沟可鼎足而三也”[8]141。1949年初冬,林鹏侠登博格达山见“四山白雪皑皑,晶莹似玉,一白无碍之冰天,与黛色濛濛之翠松,相映成一幅天然画图”,感叹“南人目西子湖为无上胜景,不知塞外山川,雄奇美秀,不事雕琢,一秉天成,非西子之滥施脂粉者所能及其万一”[9]148。罗家伦名作《山上天池》开篇即是“淡妆浓抹更相宜,西子湖光未足奇”[10]。甚至还有在天池划舟者,感觉“仿彩置身西湖,胸襟为之一畅”[11],“西湖有水而山不高,秀媚而鲜雄伟;匡庐山高而水不近,雄伟而少透逸。此则高山潭水,两臻妙境,轻桨慢荡,渊然有天上感”[12]。
不仅是在天山天池联想到西湖胜景,新疆当时已有数个景点被称为“西湖”,比如哈密苏巴什龙王庙附近的天山融雪汇流之湖,“或称为小西湖,固未必与西湖相类,然行人至此,其心胸之愉快,固远胜于置身六桥三竺间也”[13]。谢彬也称哈密“风景之佳,不啻塞外一西湖也”[5]87。邓缵先在辞别乌苏所作《六别诗》之一《别县田》中写道:“县田在东郊,又在西湖边……欲将筑田宅,终老西湖间。”[14]16更有意思的是迪化西大桥附近的鉴湖,既与浙江绍兴的鉴湖同名,如邓缵先说:“会稽有鉴湖,名区震人耳。巩宁有鉴湖,胜地阙于史”①参见《鉴湖》,邓缵先《毳庐诗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页。又如当代新疆诗人王子钝在《游鉴湖》中写道:“鉴湖我亦比西子,佳句西湖却姓苏。”当代学者朱玉麒则援引“《辞海》上说中国有两个鉴湖,一个在绍兴,一个在乌鲁木齐(西公园)”。见朱玉麒《“一炮成功”》,《文汇报》,2020年8月21日,第7版。,有时也被称作西湖,如邓缵先还在诗中写道“秋月印平潭,琼源养活水”。谢彬也曾记道:“渡巩宁桥(俗呼西大桥),至鉴湖——一名西湖。”[5]126
这也可见重要的不是景观之自然呈现或相像指数,西湖、鉴湖等作为江南地区积淀丰厚的文人记忆、巧夺天工的人文景观与旖旎多情的自然风光结合的最佳典范,成为大量行旅新疆者和新疆本地人日常“交往记忆”中频繁所指的理想地名,一方面,可视为论者先入为主的国内其他地区文化优越心理和中心强势话语先导;另一方面,更体现出行者通过消弭新疆与国内其他地区、边疆发展差距和自然差异来强化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段义孚说:“符号是意义的仓库。意义来自在时光里不断积累起来的深厚经验。这些经验尽管植根在人类的生物性里,但往往有着神圣和超越世俗的特性。”[15]无论是取国内其他地区富庶省份之商业类比,还是观古来名胜佳地之风景联想,这些地名符号所凝聚的文化积淀和情感力量,都超越了一时一地一景一物的当下经验和视觉印象,而传递着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数千年的交融交往与相连相通,正如邓缵先在迪化鉴湖多次联想到昆仑天山,如“源通昆仑墟,澜洄天山趾”(《鉴湖》)[14]26、“槎浮博望融仙液,波映昆仑净俗埃”(《同友人游鉴湖二首》)[14]94。
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还是偶尔有将新疆重镇比照中国国内其他地区的,如于右任在回到国内其他地区的演讲中说,“在新疆有个比拟,说迪化很像南京,是一个政治中心,喀什(疏附、疏勒)很像北平,有着悠久的历史,把和阗拟作杭州,因为手工业很发达……伊犁一切比较现代化,他们比作上海”[16];方宗岱也说,“喀什噶尔是疏附疏勒两县的回名,是南疆的上海或天津,对外贸易的枢纽”[17]4。这样说自然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我们或许可以从中一窥作者通过对观看对象的认同而强化文化认同的心理需求,比如1930年代末到新疆的记者陈纪滢多次提到“九一八”后流亡到新疆的大量东北军民,并感慨“站在乌鲁木齐河畔,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白河,同时联想起黑水白山,以及一切与那些人有关系的地方,乡村,院场,或者风俗习惯之类”[18]。将思乡情结和故土情深融化于这片陌生又熟悉的土地,勾连起的“故乡”和“异地”使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形象更加开阔和坚韧,这既是多数游子身处遥远异乡时情不自禁的文化联想,也潜藏着知识分子对国家边疆领土的自然亲近和自觉维护意识。
二、视偏远落后之地为“桃源”
自清王朝于18世纪中叶平定叛乱收复新疆后,西域诗风一面继承了汉唐边塞慷慨悲壮的阳刚之美,一面发掘出既往边塞诗风中难得一见的冲淡平和的田园之美,其动因与彼时清代赴新官员更为积极自觉的主体定位和文化认同有关。因为勃兴发起于边疆的清政权一直推进将重纳疆土与中原江南一视同仁的边靖之策和治国理念,加之清朝鼎盛繁荣时期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和拓疆行动力,使得无论是遣派戍边的武将还是贬谪流放的文人,多自觉地在文中以尽显忠君报国思想为动机、以呈现新疆博大风物为乐事、以书写百姓安居乐业为己任,是以田园之乐和风俗之新成为了此时文人在感叹行路难和思乡苦之外的现实补偿和积极作为。如施朴华写道“胡麻叶大麦穗黄,百株垂柳千株杨。东村西村通桥梁,鸡鸣犬吠流水长”(《轮台歌》),又吟“龟兹城东七十里,蝶飞燕语春风温。杨柳青随一湾水,桃花红入三家村”(《泽雅堂诗二集》卷七),即使被清廷关押流放新疆的裴景福也有“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好春风”(《颂哈密》)之句。
民国初年,将新疆比作桃源之相似联想频繁地出现。民国初年,邓缵先眼中之迪化“寸心辟灵境,随处皆桃源”,并称是“熙熙太平民,不识兵甲烦。初因避秦来,息躯边塞垣”(《乌鲁木齐》)[19]1,过哈密称“尘外有达人,桃源良可拟”(《哈密道中》)[19]5,给家人书信中说“境拟桃源并,居非木垒同”(《答家人函询迪省风景》)[19]20。杨增新还曾在督署大堂前悬挂有一幅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20]的确,不少作者都肯定了新疆生活中的“太平民”状态,吴绍璘就说杨增新治理下的新疆“盗贼不兴,故熙熙攘攘,恒目为世外桃源”[1]97。
尤其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的民国赴新游记中,桃红柳绿、鸡鸣犬吠的田园风光中的理想因素和美誉功能被进一步强化。中国士人远离江湖、归隐山林的出世之心在国运不济、忧患重重的现实中因无处存身而隐匿难见,民国新疆虽也曾经历战乱动荡,但时局总体而言较国内其他地区更趋平稳,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新疆作为战略物资运输的国际交通线,相较于当时东北、华北、华南、西南等大部分地区而言,离战火硝烟最远,这使得不少在战时执着学术理想和决心献身科学的赴新考察学者,在新疆有过一段可以一心向学的难忘时光。如黄汲清、杨钟健、程裕淇等在1942年冬—1943年春组成新疆地质调查队,在新疆独山子、库车等地展开野外地质考察时,黄汲清在塔里木盆地之锁钥铁门关,见“茅舍二三,农田数顷,杨柳夹道,鸡犬相闻”[21]51;在库尔勒见“沃野农田肥美,渠沟纵横,杨树参天,杏花夹道;清澈可鉴的河渠旁边,往往遇见嫣然带笑的浣衣少女”,“这确是一个世外桃源,而我们置身其间亦不自觉其为捕鱼的武陵人了”[21]52;在从库车到温宿路上,感受着南疆的融融春色,“水田无尽,阡陌纵横,芳草映着垂柳,莺燕飞舞上下,杏花虽还没白头,海棠已处处胭脂透。茅屋之下,马路之旁,车水马龙,孩童嬉戏于其间,村姑少妇正头顶喀巴克到西边取水。一副羲黄图画,让人无从描写其神情。这是阿克苏和温宿沃野,是天山南路的极乐园”[21]95;在库车时作者听说南疆一些地方初夏以桑葚为食,感叹“这是诗人的作风,而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也特富诗意。我想儒家所讴歌的唐虞郅治之世,其理想的人民生活也不过如此!”[21]118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在交通还很不便利、通行条件非常苛刻、赴疆机会难得一求的行游中,国内其他地区文化人也会更为珍惜和留意青壮年时代难得一遇的新疆之行,其见闻遭遇和体验感受往往成为他们日后多年回忆中游走在日常生活轨迹之外的别样风景。如黄汲清的子女们就曾回忆过父亲对于新疆一往情深,比如他时不时会拿出花帽给孩子们表演新疆舞蹈①参见黄浩生关于其父黄汲清的回忆文章《情系天山》,中国地质科学院《黄汲清纪念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8年。。
甚至一些新疆民俗民风也被国内其他地区旅疆者视为可羡之事,褚民谊感叹哈萨克族“出外旅行,不用带干粮,可以随处到同教的人家去借宿饮食,真是□民安居乐业,犹有古风”[22]3。一行人返回博乐时,竟收到了三日前不慎遗失在路边的皮包,原是“蒙人巴拉拾得之,绕道六十里,送至村长,转呈警局待领云”,作者不仅感叹:“蒙人诚朴,可敬可爱,道不拾遗之风,乃见之于边地,岂诚‘礼失而求诸野’乎!”[22]61
一直到民国末年,依然有很多游记作者怀抱澄清改造国人对新疆刻板印象的自觉意识,加之日益成熟的现代国家领土、中华民族和国家安全等观念的渗透,也使得他们会有意美化新疆形象,甚至不乏夸大。比如视耽在孔雀河畔,感叹“悠哉游哉,虽羲皇上人无我乐也”[23]。作为“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24]的新疆,在1948—1949年赴南北疆考察的南洋华侨林鹏侠笔下更是一片歌舞升平、富饶祥和的沃土,她写到,“花团锦簇之焉耆”,“每当瓜果熟遍时,男女行乐于瓜田绿野间,歌声荡漾,响遏行云,熙熙和和,不复知人世间更有何事。江山锦簇,人物秀美,亦南疆一大乐园”[9]72。写库尔勒“城内街衢整洁,古木夹道,绿荫荡漾,树下皆渠,有户户垂阳,家家泉水之致,人民熙熙和和,宛然避秦处也”[9]75。称赞库车“歌管喧奏,连宵尽日,维族人视之不啻沙漠中之仙乡”[9]82。写乌什“夏时,万花争妍,百鸟齐鸣,徘徊其间,恍若身在‘两岸桃花夹古津’之桃源胜地”[9]91。当然,这也可以说是,生活体验和思想观念不断趋向现代的行旅者面对南疆亘古不变之生活方式所产生的错置感和滞后感。
行游者一面渴望新疆保持这样淳朴原始的民风,一面又寄希望于新疆社会能慢慢与现代生活接轨,所以,这些游记一面将新疆“风景化”和“神秘化”,对其传统古老的民风大加赞誉;一面又在外强觊觎、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对新疆落后沉滞的社会面貌忧心忡忡。如吴蔼宸就曾尖锐指出,由于新疆长期的闭塞孤陋,此地“故步自封,仍过其太古生活”[7]253,“物质文明一无所有,较诸国内其他地区至少退后在半世纪以上”[7]256,夸张之外更多面向新疆现实未来的忧虑。
三、新疆处处赛江南,反认他乡是故乡
大体说,如果说将新疆繁华之地比作国内其他富庶之地已是民国时期流传于百姓日常经验中的民间套话,很大程度上与千年以往中原与西域的交融交往、尤其是新疆建省以来大量国内其他地区人口涌入新疆有直接联系,那么一些有机会深入南北疆的作者将封闭自足的边地比作桃源,很大程度上则与现代中国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百姓生活困苦动荡、变故频发有内在关联。同时,还不断有作者会提及类比江南的新疆印象,但不同于清代西域诗人对江南故里的眷恋情深,如史善长的“醉里不知身万里,落花时节在江南”(《对雨》),亦或洪亮吉的“鹁鸪啼处却春风,宛与江南气候同”(《伊犁记事诗》)。民国时期大量行游新疆者的“‘江南认同’提供了源自文化观念的有力支撑和制度化的重要保障”[25],其笔下的江南文化象征符号包孕了更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乡愁,无疑与国家立场、民族精神、文人想象之间的关系就更为曲折迂回而意蕴深远了。
如民国初年高得善称迪化“从前此地彻夜笙歌,有赛江南之名”[26];谢彬特克斯川流域见“哈萨少女,欢笑偎郎,姿首佳丽,比于江浙”[5]159,崆谷斯流域见“一望新苇,仿佛仲夏江南之稻畦”[5]160,在阿克苏见“官柳连绵,稻田弥望,景致佳幽,埒于江浙”[5]182,出阿克苏在萨伊里克见“良田万顷,村庄稠密,饶有江南风景”[5]185;徐戈吾称三堡至哈密“草木向荣,黄雁三五,高翔空际,水蛙成群,共鸣田园,沙漠夏景,大有江南春色之慨”[8]234。还有一些作者,言入疆有还乡之感,如吴绍璘说,“所谓既抵天山,欢然如还故乡者”[1]2,迪化“举凡饮食起居,语言习俗,俱与国内其他地区无别,亦不自知身处万里外之西北”[1]129,其近郊“景物幽丽,状若江南”[1]130,绥来“风景之佳,犹如江南”[6]140,叶城“具江南之风”[1]154。
待到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新疆行游者,江南意象已成为普遍共识的新疆观感了。这一时期的江南意象有时是以北疆伊犁、迪化、乾德、鄯善等地作比,如李烛尘1943年初从伊犁赴霍尔果斯巡视国界时,因连天风雪,见“雪上树梢,晶莹如玉,不啻花开银树,路旁裹草,尽着琼葩,当时有‘塞外三冬雪,江南二月花’之句”[27]145,在从哈密至迪化途经鄯善时,李烛尘说“树木更盛,麻棉长得甚高,俨然江南气象”[27]108;罗家伦在《登博格达山道中》写“榆阴深处草芊芊,宛似江南四月天”[19]119;张焕仪感叹稻田密布、渠沟纵横的乾德是“塞外的‘鱼米之乡’。有人喻为塞外的三湘,真是名副其实的妙喻”[28];萨空了在翻过达坂城见到溪水杨柳田亩农家时,感叹“恍然若在江南”[29]。
更多的则是将南疆比作江南,黄汲清到阿克苏河畔正是“春色顶恼人的时候:莺飞燕舞,流水落花,走不完的长堤芳草,看不透的柳绿桃红,人家都说阿克苏是塞外江南,我总觉得江南春景比不上此时此地的塞外!”[21]112徐苏灵听说“喀什和阗等且有‘江南’之称”[30];袁见齐说莎车“阡陌之间,遍植白杨,公路两侧,新植小树,亦欣欣向荣,驰车其间,恍若置身江南”[31],库车“气候和煦,略如江南”[32];卢前在开都河上的平桥上,见“好几百个阑干,颇有江南风景”[33],“庆平里许长桥,天山雪水滔滔,一幅江南画稿”[34];方宗岱在焉耆见“开都河水量充足,鱼鸭成群,全是江南景色”[17]3;陈少甫在开都河上也见“山光倒影,一如江南景色”,“有如江南暮春时节,人道南疆好,自和硕以西即可见之”[35],“昔闻库尔勒有‘小江南’之称,诚然”[36]。
更有南洋华侨林鹏侠,她称天山南麓“全年青翠,花果缤纷,虽江南莫可与京”[9]27,在焉耆见“桥下万顷波光,滟潋连天,夹岸青翠,花柳缤纷,山光水色,酷似江南,有‘小江南’之称”[9]71,见库尔勒“附郭桑树如云,稻田错落,花态柳情,山容水意,恍若江南风光”[9]75,见阿克苏“环城绿云连亩,阡陌如云,恍若江南风光”[9]88,见喀什噶尔河“下游沿岸水田纵横,饶有江南风景”[9]96,真是新疆处处皆江南!1943年,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后,梁寒操奉派宣慰新疆时,更从国家战略高度盛誉新疆胜于江南:“从天、地两者分析,新疆是未来建国基础的所在,尤其是南疆,有江南之长,而无江南之短。江南所富者为生产资源,而南疆则兼生活战斗两种资源而有之。”[37]
“江南”这一意象的选择,绝不仅仅是基于时节气候和自然风物方面的相似性,更有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心理和审美经验的千年沉淀,因为江南从来都是一个地域上不断流动变化、文化上不断淘洗净化的历史空间,其高度的弹性和开合的张力使其早已成为中国最富有古典美和意境美的文化范畴。如梅新林所说:“‘江南’是一个同时兼容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历史意涵与现实意涵的充满活力与魅力的空间概念,主要包含了地理方位、行政区域以及意象空间三重意涵,彼此有分有合,相互交融,由此形成‘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不同空间指向。”①梅新林在为“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所作总序中引周振鹤等学者观点后指出,“大江南”涉及今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小江南”对应于环太湖流域,“中江南”或接近于通行的“江东”“江左”的区域范围。参见赵红娟《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页。有意思的是,20世纪40年代初,也有新疆本地作者称南疆为“小江南”②参见寒默《中国的小江南》,《新疆青年》,1941年第4卷第1-2期。,更多是如上述将南疆库尔勒、焉耆、阿克苏、温宿、库车、莎车、和硕、喀什、和阗等地与江南类比者。其中缘由,与当时逐渐深入人心的中华民族观念有关,也与南疆长期与我国国内其他地区消息难通、交通阻隔有关,甚至也与南疆30年代前期曾陷“泛突”导致暴乱的历史教训有关。所以这些偶有机会前往南疆考察的国内其他地区作者,都会有意识地赋予这片土地“似曾相识燕归来”“风景旧曾谙”的被再发现的传统美感,使其成为富有某些象征性和隐喻式的文化意象。不断地重申和强调南疆类比江南的文化亲近和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了新疆与国内其他地区之间的文化相似性和共鸣感,有着民国知识分子未曾点破的家国情怀和集体记忆,更是基于现代国家立场的空间类比和文化建构。
当然,类比江南并不全是自觉地构筑新疆与国内其他地区同源同根的文化想象,有时也是为了安置行游者无可名状的乡愁吧。事实上,新疆气候地理也并非都是宜人之处,1927年存吾为杭州人钱之万的新疆游记作序时就喟叹:“杭为东南胜地,气候温煦,交通便利,文化发达;新疆位西北边陲,寒暑剧烈,荒凉阻塞,人迹鲜少,文野之殊,盖有难言者。”[38]霍布斯鲍姆曾提出传统是人们依现实情境的需要所建构的与过去的连续性关系,它既可指一系列活动,“也意指一系列仪式性或象征性的自然,它以重复的方式努力重申某些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并自动地表明与过去的连续性”[39]。行旅作者们有时是为了表现新疆与国内其他地区的一致性与同步性,唤起受众的文化认同感,所以多以具有现代观感的城市作比;有时则是为了回避新疆远滞后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现实性和差异性,唤醒受众的审美认同感,所以转而诉诸于更具文化乡愁和怀旧意味的江南想象。正如朱氏威说:“(迪化公园)这几个江南人似乎占有了这片丰腴的花园,当然我们不会在这里一辈子住下去的,我们嘴里谈着眼前与身边事,心中却想着成都、重庆以及家乡芜湖、上海、南京。”[40]越是以国内其他地区省份地名类比新疆诸地,越是在表达自己未能忘怀的故园乡愁和文化记忆,越有可能表达着与新疆现实的疏离感和隔膜感。所以“类比江南”是文化印证和文化吸收双重作用后的地景记忆,它既呼唤着行旅作者的家园之思和文化乡愁,又形塑着行旅主体的家国体验和文化经验,牵动着文化乡愁、地景记忆、家国记忆等,是一种复合体验。
另外值得深思的是,那些将新疆比作江南的作者,几乎全都是行游或旅居新疆者,选择一辈子留在新疆、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者的苏北海先生,青年时代就曾对比过江南故乡的“曲线美”和新疆文化的“直线美”,感叹“这七八年来,使我陶醉在西北的山水之间,那雄浑的气派,使我含在心意之间,觉得唯有直线才是力量,才是伟大,曲线的小巧,我已开始厌恶,她大的表现,只是昙花一现,永远的永远,必须要有直线的力,才能有天上人间的真美”[41]。实际上,只有超越了江南地景与文化乡愁,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新疆的地理之美和文化之核。
“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边疆处处赛江南》),这首传唱了近半个多世纪、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建设边疆的经典歌曲背后所沉淀蕴积的集体无意识,数千年来,一直埋藏在自汉唐至清代以往不畏艰险、建业报国的漫漫古道之下,呼啸在数千年边塞诗风雄奇遒劲、慷慨悲壮的猎猎风尘之后,流淌在无数西行故人离乡背井、再建家园的涔涔热泪之中。所以也可以说,“国内其他地区—新疆”的对应联想,更多是基于现实层面,行旅者以及新疆本地人之于近现代新疆社会发展进程能与国内其他地区同步的热望;“桃源—新疆”的相似联想,更多是基于理想层面,在中华民族深陷内忧外患、孜求民族独立解放之路的现代中国,民国知识分子对新疆和平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祈愿;那么“江南—新疆”的比拟联想,则更多是基于文化层面,肩负文化使者责任和国家本位立场的民国文化人对新疆文化与中华文化同一性、同根性、同构性的自觉守护和大道传承。更重要的是,“国内其他地区—新疆”“桃源—新疆”“江南—新疆”的稳定结构和知识谱系,经中华民族数千年心理积淀、文本吟唱和历史累积,在清中叶西域“故土新归”后得以一唱三叹的反复歌咏,继而在民国行旅新疆者的笔下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当代中国,已成为尽人皆知的风景类比和文化联想。比如在当代新疆美文中,“桃源”或是“江南”也成为几乎可以信笔拈来的符号式象征,如颂彦在《天山深处的人家》中称在伊宁市看到“满街瓜果,我们还以为是到了江南果乡”[42],汪曾祺在《天山行色》中说在乌鲁木齐市郊见路旁“行人的起色也很好,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全都显出欣慰而满足”[43]。这其中所蕴藏的文化密码和集体记忆,恐怕作家自己也习焉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