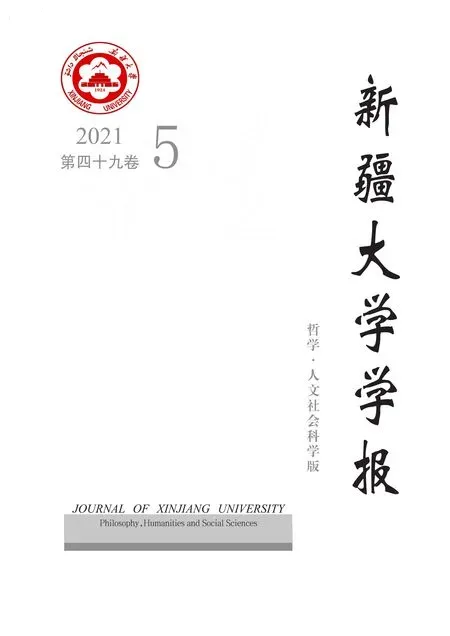庙见礼与《周南·葛覃》题旨的形成①
2021-12-03李申曦
李申曦
(石家庄铁道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43)
《葛覃》之旨,《毛诗序》言:“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1]30言后妃未嫁之事。然《毛传》又言“妇人谓嫁曰归”[1]30,言女子归宁父母家,由此形成了待嫁与已嫁的阐释困境。后世学者认为诗述后妃在父母家之事,却又称其出嫁。同一诗篇,兼及嫁与未嫁之意,于诗旨似难疏通②袁行霈言:“前人就未嫁与已嫁,聚讼纷纭,皆因《小序》之含糊引起。”参见袁行霈、徐建委、程苏东《诗经国风新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1页。。诗中女子是否出嫁?诗篇所言之身份为何?是解开此诗诗义的关键。这就需要我们结合诗中的内证,对其中蕴含的礼制背景进行考察,从更为深广的维度探寻此诗的诗义,并在此基础上观察后世对其题旨的理解是如何远离诗义而进行推衍,由此观察诗义脱离礼制背景而形成诸多阐释的生成方式。
一、女子初嫁及“得氏初”之义
最早对《葛覃》主旨进行讨论的是孔子:
孔子以“氏初”总括《葛覃》诗义,是目前我们能看到较早对《葛覃》诗义进行的解释,我们可以由此观察春秋时期对《葛覃》一诗的理解。氏,是基于姓以下的具体分支。而姓,本义指女子所生,同一血统的子孙同姓③能够对此说明的如《说文·女部》言:“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通志》曰:“女生为姓,故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妫、姞、妘、婤、姶、㚰、嫪之类是也。”孔颖达言:“姓者,生也。”《广雅·释亲》言:“姓,子也。”王念孙疏:“姓者,生也,子孙之通称也。”参见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12页。郑樵《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王念孙《广雅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787-788页。。《世本》记载:“言姓即在上,言氏即在下。”[3]段玉裁云:“姓者,统于上者也;氏者,别于下者也。”[4]628氏为姓的分支。《左传·隐公八年》就记载了周天子以功德赐姓命氏的情况:“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5]112如鲁、蔡、郑等国诸侯与周天子同为姬姓,赐以国号为氏。《白虎通·姓名》曰:“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闻其氏即可知其德。”[6]402根据功德以命氏,通过氏而知其功德。郑樵言氏的用意:“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7]氏用来别贵贱、论功德,贵族有氏,平民有名无氏。男子有氏,女子的“氏”则依其夫而定。《颜氏家训·风操》云:“已嫁,则以夫氏称之。”[8]女子在嫁前跟随父氏,出嫁后归属夫家,获得夫氏。《左传》所载雍姬、息妫、芮姜,以及出土的媵器铭文中毕媿、京氏妇叔姬、亲姬娈人、丰孟妘、成姜桓母等人的称谓均冠以夫氏①参见高兵《周代婚姻形态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43-44页。。
值得注意的是,女子嫁入夫家之后,得以夫氏命之;若不为夫家接纳,则无法称氏。《春秋·僖公九年》记载伯姬因婚姻尚未完成便去世,故无法以夫氏相称②《春秋·僖公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云:“称伯姬,则许嫁可知……但未往彼国,不成彼国之妇,故不称国也。”参见竹添光鸿著,于景祥、柳海松整理《左氏会笺》,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左传·文公十二年》言:“叔姬卒。不言杞,绝也。”[5]539叔姬本为杞桓公的妻子,被其休弃,便不能再称夫氏。由此来看,孔子所言“得氏初之诗”,是说《葛覃》这首诗,叙述女性嫁入夫家,初得夫氏之事。从周之贵族婚仪来看,女子嫁入夫家,获得夫家的认同,是为“得氏初”。
孔子认为《葛覃》与庙见礼有关,我们可以回归到诗篇本身,来观察女子初嫁的情形: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汙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1]30-33。
诗中对黄鸟的描写,交代了诗篇发生的时令。陆机释黄鸟云:“一名仓庚……应节趋时之鸟也。”[1]31黄鸟,又名仓庚,是感应时节而迁徙的鸟类。《毛诗名物解》云“黄鸟,其鸣以春为期,其去以秋为度”[9]2,进一步指出黄鸟为春来秋去之鸟,以其鸣作为春天来时之征。据《礼记·月令》《大戴礼记·夏小正》《逸周书·时训》的记载,黄鸟鸣叫为仲春二月的物候③《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鷹化为鸠。”《大戴礼记·夏小正》:“二月,有鸣仓庚。”《逸周书·时训》:“雨水之日,桃始华,又五日仓庚鸣。”参见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70-471页。戴德撰,卢辩注《大戴礼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皇甫谧撰,宋翔凤、钱宝塘辑,刘晓东校点《逸周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5页。。黄鸟鸣飞,汇集于木,即发生在仲春二月。《周礼·地官·媒氏》言:“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郑玄注:“中春,阴阳交,以成昏礼,顺天时也。”[10]362按照周制,仲春为婚配之时,男女于此时约会、成婚。《大戴礼记·夏小正》“二月,冠子取妇之时也”[11],亦言仲春二月适宜婚嫁。《白虎通·嫁娶》解释仲春成婚之理:“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6]466因此从物候来看,《葛覃》所言女子出嫁,发生在仲春二月,合乎周俗。
诗以葛起兴,以采葛、治葛、服葛、浣葛之事为时间流程,我们可以由此观察诗时与诗事。《说文·艸部》云:“葛,絺绤草也。”[4]35《系部》言:“絺,细葛也。绤,粗葛也。”[4]660絺为精致的葛布,绤为较粗的葛布。周代专门设置了“掌葛”一职,征收葛草用作絺绤之材④《周礼·地官·掌葛》记载:“掌葛,掌以时征絺绤之材于山农。”参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21页。。《逸周书·文传》言“树之葛、木,以为絺绤,以为材用”[12],记载文王九年树葛以为民生利。葛经过煮制后脱胶,分离出的植物纤维可用于纺织。因此,周人种葛、采葛、征葛是为制作葛布。此外,《周礼·天官·屦人》记载王、后服“葛屦”[10]215。《仪礼·士丧礼》云:“夏葛屦。”[13]673有王、后、士人穿着葛屦的记载,这表明葛亦为士阶层以上所服原料。孔子曾说:“夫葛之见歌也,则以絺绤之故也。”[14]葛作为纺织的原料出现在诗歌里,是言采葛以制絺绤之事。《王风·采葛》言采集葛草,《齐风·南山》《魏风·葛屦》《小雅·大东》之“葛屦”,便是以葛为材录于诗中,以为兴辞。《葛覃》中不仅以采葛起兴,而且明确言“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正是叙述采集葛草到煮制的葛布加工过程。
从传世文献来看,治葛为女子嫁入夫家所必备的技能,是为女功之事。《礼记·内则》言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学女事以供衣服。”[15]870女事即女功之事,尚为女子之时便要学习如何使用葛麻一类原料制衣。《白虎通·姓名》云“妇人十五通乎织纴纺绩之事,思虑定,故许嫁”[6]416,知女性掌握纺织才能够许嫁成妇。女子既已出嫁为妇,理应操持女功之事。《礼记·昏义》指出“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15]1622,要求女子为妇后完成治葛在内的纺织之事以孝顺公婆,使室家和睦。《墨子·非乐》言“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此其分事也”[16],强调纺织麻葛等物为妇人本分。女子熟练掌握纺织以完成对女功的学习,出嫁成妇后便要承担此务。因此,包含治葛在内的女功之事是为女子与妇人所须通习、操持之事,始终伴随着女子成妇的过程。
二、三月庙见与师氏教习
初嫁入夫家的女子,需要在夫家三月之后,才能举行庙见礼。《礼记·曾子问》详细描述了三月庙见之礼,“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15]584。又言:“女未庙见而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不迁于祖,不袝于皇姑……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15]584也就是说,庙见之礼是关乎女性是否被夫家正式接纳,即女子成妇的重大婚仪。而庙见之礼的完成,标志着两家婚姻的正式缔结。
《白虎通·嫁娶》同样记叙了这一古礼:“妇入三月然后祭行,舅姑既殁,亦妇入三月奠采于庙。”[6]464记叙揭示了舅姑存没与否,庙见仪程的细微差异。在这一婚制中,庙见“三月”是为判别新妇是否怀孕的考察期。首先,胎儿三月初成人形,女性身形彰显,医书中有“三月始脂”“三月始胎”等说,故为期三月足以验证[17]。其次,在庙见期间,夫妻不得行房事。
《左传·隐公八年》记载了郑公子忽与迎娶之女妫氏“先配而后祖”,陈鍼子评价其“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贾逵注云“三月庙见,然后配”[5]111。显然,忽、妫二人成婚,未行三月庙见便同居,是有违礼制的。《列女传》记录了宋恭伯姬、齐孟孝姬“三月庙见,而后行夫妇之道”[18],清楚地表明夫妇理应于庙见之后同房。最后,庙见之制的形成,是在周代宗法制的背景下,出于对继承人血统之考量,其或根源于原始社会风俗的某些遗留①胡新生对三月庙见礼的创制意图和起源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认为:“三月庙见礼是在父权制已经确立而原始的两性风俗仍然残存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的性质与某些民族曾经流行的‘杀首子’风俗和‘审新娘’风俗极为相似。”参见胡新生《周代的礼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7页。。庙见礼设有三月之期,即“来妇”需要有三个月的时间无法与丈夫同房而被安置在别处,以检验其是否怀孕。三月之后,若无身孕,则拜见男方宗庙,完成婚礼。
庙见礼设有三月之期,这一时间长度恰恰暗合诗中的描述。诗状葛之形状“萋萋”“莫莫”,暗喻时间的流逝。《毛传》言:“萋萋,茂盛貌”[1]30,“莫莫,成就之貌”[1]32,以葛之兴旺与成熟为时间流程,这与《豳风·七月》描写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的表述相类,透露出时间的推移。葛为苎麻,每年收割数次,在黄河流域每次90天左右。根据葛的习性,其从仲春繁茂到夏日长成,需历经三个月。《本草纲目》记载,“春生苗,引藤蔓,长一、二丈”[19],知葛在春日生长。又因黄鸟鸣为仲春之月的物候,此时草木生长繁茂,正与葛“萋萋”之貌的描述相符。葛春生而夏成,夏季方可采练。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引《葛覃》并详细介绍了采葛、练葛之法:“采葛法,夏月葛成,嫩而短者留之……练葛法,采后,即挽成网,紧火煮烂熟……纺之以织。”[20]夏日葛成,采治以织布。由此便能理解诗二章采、煮以练治葛布的描述。这样看来,葛从“萋萋”到“莫莫”需三个月长成,这三个月与女子在夫家等待庙见的时期相合。
诗中所言“师氏”,则为女功之事的传授者。《礼记·昏义》记载了妇人在成妇前,需要学习女功在内的事人之道:“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祢未毁,教于公宫。祖祢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15]1622依周制,妇人在正式成妇前,需在指定地点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学习,以培养其德、言、容、功,而“师氏”即为她们的培训者。《毛传》曰:“师,女师也。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1]33可见,专门有女师传习女功等事。《白虎通·嫁娶》亦云:“妇人所以有师何?学事人之道也。诗云:‘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昏礼经》曰:‘教于公宫三月。’妇人学一时,足以成矣。”[6]485妇人有师,师氏是为教授其事人之道的老师,即女师。值得注意的是,师氏并非当时陪伴在女性身边的“姆”。孔颖达根据郑玄注《仪礼·士昏礼》“姆纚筓绡衣”之“姆”为“姆,妇人五十无子,出而不复嫁,能以妇道教人者,若今时之乳母矣”[1]34,遂认为姆即为诗句中的“师氏”。事实上,姆与师氏虽同样承担教育女性职责,但却不能等同。《礼记·内则》言:“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学女事以供衣服……二十而嫁。”[15]870-871可见,姆在女子十岁之时就已教导女功等事。然《礼记·昏义》中师氏教育未成妇少女只有三个月。倘若姆即为师氏,同出于一书之记载何以采用两种称谓?且姆与师氏的教授时间本就存在差异,《礼记》对古礼的记载更不至相互违背。又据《公羊传·襄公三十年》记载伯姬因不见傅母不得下堂的礼制而困死于火中①《公羊传·襄公三十年》载:“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逮乎火而死。”参见何休注,徐彦疏《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9页。,《齐风·南山》中《笺》云“文姜与侄娣及傅姆同处”[1]343,知姆在女性尚为女子之时及嫁为人妇后始终伴随。《礼记·昏义》之“先嫁三月”与《白虎通》“妇人学一时”,均揭示出姆与师氏的这种差异。此外,按照《礼记·内则》的记载,大夫以上有子师、慈母、保母三母②《礼记·内则》:“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正义》:“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则具三母。”参见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62页。。而根据《仪礼·士昏礼》的记录知士阶层仍有姆,而师氏必不会是当时之“姆”,因此《葛覃》中有“师氏”教习的女子,当出于大夫以上阶层。
师氏既为婚前短暂教导女子的老师,那么诗中操持女功、告归、浣衣之人则可以确定为将成人妇的贵族女子。诗中女子告师氏“归”,点明了女子出嫁之意。“归”有“嫁”义,《公羊传·隐公二年》言“妇人谓嫁曰归”[21]33,《春秋·成公九年》记载伯姬嫁入宋国为“伯姬归于宋”[5]735,《说文·止部》云:“归,女嫁也。”[4]68孔颖达疏“归”义言:“以夫为家,故谓嫁曰‘归’也。”[22]女子出嫁往归于夫,故以嫁为“归”,《桃夭》《鹊巢》《东山》等“之子于归”的“归”均指女子出嫁。再联系师氏的身份与出现的场合,此处“归”解作“嫁”较为合适。
诗中女子受师氏教导学习女功,也是在其成妇前的三个月进行的,即《昏义》“妇人先嫁三月”时学习。既言先嫁,显然已确定嫁期,经历了女方许嫁、夫家请期等仪程后,被送往某处跟随师氏学习三个月。由诗中女子随师氏采葛、治葛、作衣,可知娶入男方之家的新妇在这三个月中从事女功,以待庙见。《礼记·昏义》言:“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祢未毁,教于公宫;祖祢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15]1622规定女子正式成妇前,根据血缘之亲疏,被送至公室或者宗室进行妇德学习。查诸史料,女子初入夫家至庙见之礼成妇有三月之期,因此,女子随师氏学女德、成女功之事,正是女子三月庙见期间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葛覃》所写的正是女子被娶入夫家之后、三月庙见之前的女功之事。
需要补充的是,三月庙见之礼是大夫以上阶层的婚制,士阶层也有拜祭夫家祖庙之仪,但常在成婚当夜便已圆房,夫妻不必相隔以待三月之久③《仪礼·士昏礼》记载亲迎当天夫妇同居,属于士礼。孔颖达引贾逵、服虔语:“大夫以上……皆三月见祖庙之后,乃始成昏。”参见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5页。。因此,《葛覃》所言的有师氏教习并需要三月庙见者,当是大夫以上阶层,依照《毛诗》的“后妃”之德的解释,其或为诸侯以上阶层的婚礼描写。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作出一个判断:《葛覃》因絺绤之事而咏葛,因葛言及女功,黄鸟、师氏、归等词又揭示出诗与女子成婚有关。女子学习女功,妇人操持女功本为寻常之事,而受教于师氏,宣告出嫁,则又透露出与婚姻相关之仪程。据孔子的表述可知,《葛覃》体现的当为周代昏礼中的庙见礼。若以三月庙见为礼制背景,则能够合理地印证、解读诗句描述的主要内容。
三、庙见换服时的归宁之思
孔子对《葛覃》“氏初”的评论,反映出女子庙见前后身份的转变,点明了诗的形成背景,“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则是对诗中情感的解读,认为《葛覃》体现了嫁入夫家而不忘父母的人之常情,是为“见其美必欲反其本”。
初嫁女子通过三月庙见礼后得到夫家认可,于宗庙祭祀加以确认,从此成为夫家的一员,方可以夫氏相称,是为“得氏”,也就是说,女子从此有了夫家的身份。姓氏相合的称呼,成为女子的新身份,出土文献中苏治妊、郑同媿、吕雔姬的称谓即是父氏加夫氏④参见张淑一《周代婚姻形态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女子的“夫氏”为婚后获得,“父氏”却与生俱来,无法剥夺,因此已嫁女子仍不绝于宗族。《仪礼·丧服》言:“妇人虽在外,必有归宗。”[13]581已嫁妇人为父家服丧,表明其与宗族之间的联系。《左传·桓公十五年》载雍纠欲杀雍姬之父,雍姬问其母:“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5]206父母宗族始终为子女的至亲。《公羊传·隐公元年》载:“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休注曰“仲,字,子,姓。妇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适同姓”[21]19,认为女子称姓为不忘本。在这种语境下,本,正是包括女子父母在内的家族,故孔子所谓“返本”,便是强调女子嫁入夫家并被认同的时候,心中更加思念父母。
《葛覃》末章言“薄汙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正是叙述女子在三月庙见期满时念亲而不忘本的情感。汙,《毛传》云:“烦也。”郑玄笺曰:“烦撋之”,即搓洗以去除污垢。浣,《笺》言“谓濯之耳”[1]33,浣有濯洗之义。汙、浣即是清洗私、衣的污渍。私,为贴身衣物。《释名》云:“私,近身衣。”王先谦根据“私”字“亲亵”之意,指出《释名》所言近身衣当为亵服,且衣与私“对文以见义”,故“衣”为外衣,“私”为内衣[23]22。“薄汙我私,薄浣我衣”,是言女子亲自清洗自己的全部衣物。《毛传》云“害,何也”[1]33,与“何”相通;“害浣害否”,是女子反问“哪些衣服还没有清洗干净?”如此反复地陈述对自己衣物的濯洗与整理,常为此前释者所不解,然将之放置于庙见之礼中观察,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重大的礼制。
来嫁女子通过三月庙见期考察后,便正式成为夫家成员。孔子“氏初之诗”,也指出了女子身份的转变。在庙见之前,虽然名义上嫁入夫家,但仍在三月考察期间,其有可能被送还父母家,因而并没有获得与丈夫相配的“命妇”身份,只有在庙见之时,才能获得与丈夫爵位相应的“命妇”身份,因此换服,成为女子得到夫家承认的标志。
周人认为服饰是礼的体现,有明确的服制规定。《礼记·坊记》言:“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15]1403礼别亲疏同异,服饰亦需体现这种差异。《礼记》中《王制》《檀弓》《祭义》《昏义》《月令》等篇,对服之数、料、色、度等方面有严格要求。在重要的礼仪场合,妇女需身着与之地位相符的服饰以合于礼制。“妻以夫贵”,初嫁的女子在庙见礼上着相应的服饰,祭拜夫家宗庙,标志着成为夫家的重要成员。周制,公侯伯子男之妻受封为“命妇”,着相应的服饰。王后亦有特定的服制。《周礼·天官·内司服》载王后、内外命妇的服饰:“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翟,鞠衣,展衣,缘衣,素沙。辨外内命妇之服,鞠衣,展衣,缘衣,素沙。”[10]202-205王后六服用于不同场合,褘衣、揄翟、闕翟为祭祀之衣,鞠衣桑服,展衣待王及宾客,褖衣作御王或燕服。内外命妇也有相应的服制:
内命妇之服:鞠衣,九嫔也;展衣,世妇也;缘衣,女御也。外命妇者:其夫孤也,则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则服展衣;其夫士也,则服缘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后褘衣[10]205-206。
不同身份的命妇着不同的服装,也就是说《葛覃》中的女子要根据丈夫的身份着相应的服饰。而且,诸侯邦国的服饰也有不同,齐鲁地区“多文䌽布帛”;秦国服饰则“其服不挑”;楚国与中原的服制不同,《战国策·秦策五》载秦王孙异人着“楚服而见”华阳夫人,显然“楚服”有别秦服①参见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13页。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3页。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9页。。因此,女子若嫁入他国,三月庙见之前尚未得到夫家承认,因而可以着父母之邦的服饰;三月庙见时,得到了夫家的承认,则要着命妇之装而成婚。《葛覃》最后四句,写的正是女子在换服时事夫念亲的感受。
在等待三月庙见的时间内,女子在师氏的教习下,采葛、治葛、制衣,依照未来的身份准备了庙见之服。其中的“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描述了女子采葛而制成衣裳。《礼记·月令》言:“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惰。”[15]485-486周制,即便后妃也有亲自治桑,以为丈夫制作郊庙祭祀之服。其中的“无有敢惰”,意同“服之无斁”,是言三月期间,女子已经制成了庙见的礼服。这样便能理解诗中所言女子亲自治葛、心无厌惰的描述,正是虔诚地制作庙见拜祭夫家祖庙的礼服。
三月之期结束后,女子告别师氏,“言告师氏,言告言归”便是感谢师氏三月教诲陪伴,然后换上与夫家身份相符的服饰,行庙见之礼。《礼记·祭义》云“夫妇齐戒,沐浴,盛服奉承而进之”[15]1317,便是言新婚夫妇斋戒之后,依照身份着相应服制,参加祭祀。在换夫家盛服之前,其所言的“薄汙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是对娘家衣物的仔细清洗、认真整理,将来自父母之邦的衣物收归放好,此刻内心思念父母愈甚,希望将来有一天回去“归宁父母”时,仍能着当初在娘家的服饰。
已嫁女子回娘家归省,向父母问安,为“归宁父母”。女子出嫁后回家探望父母本是人之常情,但对诸侯以上阶层的女子来说,是一件可以想象而很难实现的愿望。《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记载:“冬,杞伯姬来,归宁也。”[5]286遵照常事不书的笔录原则,杞伯姬既嫁归宁显然有悖常理而被书之于史。何休注此事云:“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21]176女子既嫁诸侯,便不能像寻常女子一样返家探亲。妇人“踰竟”也被视作非礼,《谷梁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了因宋荡伯姬越竟迎妇,宋杀其大夫,《鄘风·载驰》中许穆夫人因国破君亡欲赶至漕邑吊唁,而被许国大夫拦下①参见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榖梁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4页。郑玄注,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1页。。朱熹言:“夫人知其必将以不可归之义来告……既而终不果归,乃作此诗,以自言其意尔。”[24]44所谓“不可归之义”,正是指当时诸侯夫人不得出境吊唁的礼法限定。毛序《邶风·泉水》云:“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1]165已嫁女子即便在宗国覆灭、父兄去世之时也不得归。而女子要真正返归娘家,常常是在被休弃后,称为“来归”或“归于某”②《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春秋·宣公十六年》:“秋,郯伯姬来归。”《战国策》记载赵威后送燕后出嫁“持其踵为之泣”,“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赵太后纵使不舍,也不希望女儿遭受变故返国。参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6、674页。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70页。。因此,《葛覃》写女子换服之时的归宁之思,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赞扬,言之为“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这正是人之常性、常情,孔子所言即是对诗中女子事其夫而念其亲的情感肯定。
可以印证的是,《礼记·缁衣》对“服之无射”句的解释,也是从成礼的角度来言:
子曰:“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人苟或言之,必闻其声。苟或行之,必见其成。《葛覃》曰:‘服之无射。’”③郑玄注《礼记》时言:“射,厌也。”而《毛诗》作“斁”,《毛传》云:“斁,厌也。”知射、斁字异而意同。参见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17-1518页。郑玄注,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葛覃》中的“服之无射”,是为庙见期女子治葛以供祭祀,无敢厌怠的恭谨之状,孔子借以告诫人应谨言慎行,坚持礼制,必有所成。郑注“凡人举事,必有后验也”,孔颖达认为乃言“言行必慎其所终”的道理[15]1517-1518。其中的见车之轼、睹衣之敝、闻言之声、观行之成,皆言事情的发生必能得到相应的验证,由此阐释人要谨慎自身言行、不敢懈怠的道理。结合三月庙见的理解,我们更能看出孔子引用“服之无射”的原义。
四、《毛诗》对《齐诗》《鲁诗》说解的调和
由于对庙见之礼的疏忽,齐、鲁、毛三家对《葛覃》的阐释,便存在了较大的分歧。
齐诗对《葛覃》的阐释主要有两处。《礼记·缁衣》引“服之无射”句,郑玄注云:“言己愿采葛以为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无厌,言不虚也。”[15]1518王先谦指出:“云‘为衣令君子服之’者,是以为女适人后事……此齐说也。”[23]21郑玄注解《礼记》采用《齐诗》的说法,《齐诗》认为诗句是说女子为君子整治葛衣而无所厌倦,可以看到诗义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偏移。且根据“为令君子服之”的解说,知齐诗认为《葛覃》记述的是女子嫁人之后的事。《易林·兑之谦》曰:“葛生衍蔓,絺綌为愿。”[25]言“为愿”与郑玄“已愿”同,都是《齐诗》的观点。而郑玄在注《毛诗》该句时则云“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将所适,故习之以絺绤烦辱之事,乃能整治之无厌倦”[1]32,认为诗句叙述女子在父母家之事,即其尚未出嫁。这至少表明,《毛诗》《齐诗》在诗句的解释上不仅存在已嫁、未嫁之差别,同时皆已偏离诗句原初之义。
鲁诗对《葛覃》的解释,保存在蔡邕《协和婚赋》:
惟情性之至好,欢莫备乎夫妇……考遂初之原本,览阴阳之纲纪,乾坤和其刚柔,艮兑感其脢腓。《葛覃》恐其失时,《摽梅》求其庶士。唯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齿。婚姻协而莫违,播欣欣之繁祉。[26]
在蔡邕看来,婚姻本乎人之情性,顺应阴阳纲纪,故应莫违婚时,《葛覃》中的女子正是“协而莫违”,不失时而嫁。徐璈具体阐释道“赋意盖以葛之长大而可为絺綌,如女之及时而当归于夫家”[23]17,将诗对葛的描述理解为葛长成可做絺绤之材,是对女子到达一定年岁,及时嫁入夫家的比喻。汉人对出嫁年龄十分重视,《白虎通·嫁娶》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女二十肌肤充盈,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6]453,女子十五及笄许嫁,至二十岁是其出嫁的最佳时间。蔡邕言“男女得乎年齿”,重视婚时。蔡邕举证《葛覃》,以说明女子当按时出嫁,使婚姻协和,认为《葛覃》叙述了女子顺时而嫁。
从《诗序》《毛传》《郑笺》可以较为完整地看到毛诗学派对《葛覃》的阐释。《诗序》云“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1]30,总括诗义,将诗中女子身份确解为后妃,认为诗叙述后妃在父母家研习女功,又描述了出嫁后事。具体而言,从首句至“服之无斁”句,毛、郑皆以为述女子尚未出嫁时事。而末章“言告师氏”等句,则认为是描述女子嫁入夫家后的情况。“言告言归”句才宣告女子出嫁,师氏亦是在嫁前三月教授女功。倘若全诗是言女子嫁入夫家之后的事,不仅前两章显得铺垫过长,且难以阐明治葛、师氏等事的缘由。《毛诗》称前两章言女子未嫁,末章已嫁,调和了齐、鲁之说而显得更为融通,但其忽略了诗句背后的礼制背景,使得注解显得勉难成说。
《葛覃》为女子庙见之诗,孔子所言“本”原是就事夫念亲的情感而言。《毛诗》将其对人之本性的讨论曲解附会为“后妃之本”来理解、阐释诗义,诗旨解析虽然详尽,却悉非原意。《葛覃》原可入乐而歌,到了汉代周乐失传,乐义亡而诗义兴,前人对诗的记载及诗篇文本成为汉人解诗的依据。《仪礼》《礼记》记载了举行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时,合乐演奏《葛覃》等诗的情形。郑玄言之为“房中之乐歌也”①《仪礼·乡饮酒礼》《仪礼·乡射礼》载:“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仪礼·燕礼》言:“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大师告于乐正曰:‘正歌备。’”《礼记·乡饮酒义》曰:“合乐三终。”参见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1、186、275-276页。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34页。。周代房中乐由后妃所演唱,汉儒以后妃说诗,则是将《葛覃》的音声义附会到文本义当中②王先谦言“此推言房中乐歌义例,若用以说诗,则不可通”,意识到了乐义与诗义的差别,惜未能做出解释。参见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页。。
后世众多学者受《毛诗》“后妃”说的影响进一步推衍诗旨。一是着眼于对“后妃之本”的疏解。孔颖达认为后妃之本是说后妃的本性,其在《正义》中言“谓贞专节俭,自有性也”[1]30,将这种本性定义为后妃“贞专节俭”的品格。张文伯、黄式三则认为“本”与勤俭有关③张文伯《九经疑难》:“曷谓本?……贵而勤俭。”黄式三《儆居经说》:“在家为女,勤俭淑慎,是其本也。”参见刘毓庆等撰《诗义稽考》,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80-81页。。而胡承珙《毛诗后笺》分析指出,“盖勤俭自是后妃之本性,女功亦是后妃之本务”[27],将“本”理解为本性及本务。此外,尹继美《诗管见》云“《葛覃》见妇孝敬之道,故首《序》云后妃之本,孝敬者,立身之本也”[28]45,以孝敬释“本”。这些学者致力于分析“后妃之本”来讨论诗旨,无疑是对《诗序》的承袭。二是将后妃的品德具体落实于诗句之中。如刘玉汝《诗缵绪》“此篇《传》以勤俭敬孝论之精切矣,窃又因此而推之,以为古者女子,姆教四徳,今诗所言为絺为绤者,妇功也。服绤澣濯者,妇容也。言告,妇言也。勤俭孝敬,妇徳也”,明言推衍《传》义,把妇功、妇容、妇言、妇德对应具体诗事。又如朱善《诗经解颐》言“‘为絺为绤’之辞而知其能勤,即‘瀚濯’‘无斁’之辞而知其能俭,因其‘告师氏’而知其能敬,因其‘归宁父母’而知其能孝”,分析诗句所体现的后妃勤、俭、敬、孝的品格。与之同理的还有范家相《诗沈》“治絺绤,勤也;服无斁,俭也;念归宁,孝也;澣私衣,敬也;告师氏,礼也”,以后妃的五种美德解释诗句。此外,朱谋㙔、范处义等人则将后妃的身份明确为“太姒”[28]43-44。三是同样认为《葛覃》为后妃之诗,但对诗旨的理解有所差别。朱熹在《诗集传》中言“此诗后妃所自作,故无赞美之辞”[24]4,将诗解读为后妃自述自作之诗。李光地认同这一观点,“后妃所自作以训嫔御者”指出后妃作诗是为训导嫔御。而刘克《诗说》则认为“被覃及之义,此盖名诗之旨……明后妃自公室风化天下也”[28]45-47,根据诗题“覃”有“延施”之义,进而将诗解读为后妃自内及外风化天下。这些解说较汉儒之说更为细致、新颖,但仍未摆脱旧说的干扰,踵蹈“后妃”言诗的窠臼,其关键在于不以庙见之礼视之,使诗义不明,又辗转于乐义的阐释之中,遂使得说解愈繁而愈难通。
综上所述,《葛覃》原为女子三月庙见之礼的记述,表达其出嫁后对父母思念、眷恋的宗族情感。孔子基于对庙见传统的洞悉,看到了这一礼制背景下女子身份的转变,以“反本”点明蕴含其中的人性、人情。齐、鲁、毛对于诗旨的解说纠结于已嫁、未嫁,已偏离原义。特别是毛诗的“后妃之本”说,将事夫念亲之思曲解为后妃勤俭的本性,而“治葛”“师氏”“归宁”等文本所蕴含的礼制意义又被消解,此诗的题旨便成为没有礼制附着的开放文本,可以任意推衍诗义,使得其解释愈行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