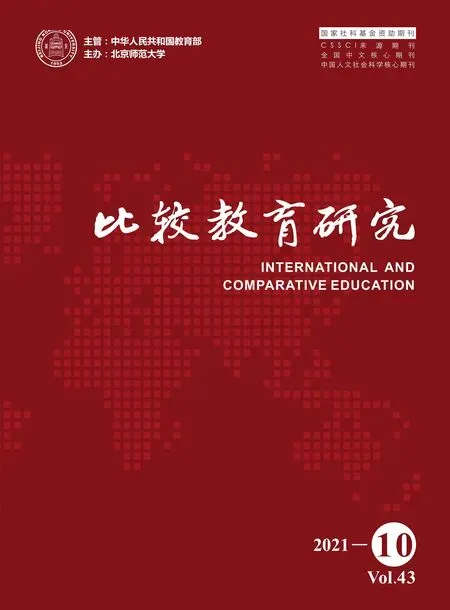德国社团主义传统及其对职业教育立法影响
2021-12-03荣艳红傅修远
荣艳红,傅修远
(1.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2.南京工程学院工业中心,江苏南京 211167)
社团主义是一种介于多元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中间形式。对于社团主义概念的理解,有学者从体系特征的角度认为社团主义是一套具有独特内在结构的不同利益团体代表系统;[1]有学者从公共政策形成角度认为社团主义是制度化的政策形成机制;[2]有学者简单认为社团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促进团体之间矛盾解决的协调机制;[3]还有学者指出社团主义政治无涉,它是持有不同政治主张的政府实施管理的手段……[4]不论从哪个角度理解社团主义,主张共同体由不同利益团体构成,与共同体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都应依靠团体之间的谈判或协商方式来解决,是不同派别学者公认的社团主义概念核心的特征。德国具有浓厚的社团主义传统,社团主义在德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在职业教育立法领域均有着鲜明的体现。
一、德国社团主义的传统
德国社团主义的传统源自中世纪其内部各邦国、城市以及行会之间彼此相处的方式。由于中世纪德意志皇帝抱有建立真正的全球帝国的梦想,为了获得属地领主们更多的帮助以达成对罗马教廷的征服,德意志皇帝经常与追求独立的领主们商议并结成联盟。至14世纪中叶,在德意志统一的外表下出现了一大批独立的邦国和邦君,除七大选帝侯外,还有10多个大诸侯,200多个小诸侯,1000多个帝国骑士。他们的领地就是大大小小的邦国。[5]由于邦国数量较多且力量相对均衡,在重大的冲突过后,谈判协商是解决问题的普遍做法。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合约》的签订就是这一做法的典型代表。除了以上具有德国特色的政教管理方式,中世纪欧洲城市经济恢复之后,包括德意志在内的欧洲国家再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手工艺行会。作为一种自治机构,行会内部的事务依据共同制定的行规来管理,而行会之间的事务依靠彼此的协商来解决;[6]自治城市是与行会一同出现的中世纪政治、经济管理的新单元(在欧洲某些地方,行会和自治城市就是同一组织),这些具有自治功能的城市拥有独立的行政机构。[7]为了促进城市之间人员流动和贸易开展,城市之间还缔结了同盟,较为有名的莱茵同盟、士瓦本同盟、汉萨同盟等就具有明显的社团主义特征。
近代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促进了与德国毗邻的英、法等国自由经济的发展,也为这些国家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以及其国内政治、经济等的巨大变迁奠定了时代的基础。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其革命主张几乎令所有欧洲贵族及宗教特权者不寒而栗,之后法、英等国先后推出了自由贸易法案,传统的行会制度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面对邻国的巨大变化,依旧是封建农业国家的德意志该何去何从?此时期,无论是参与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的思想家还是持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的上层人物都对邻国的变化充满警惕,他们大多主张反其道而行之。比如,一些思想家竭力为传统国家管理模式辩护,他们明确提出权利和义务不是源自民众的意愿、自然法或者叫作宪法的那一张纸,而是来自古老的、源远流长的习俗和传统;[8]一些思想家反对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贸易自由,他们甚至倡议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借助国家垄断来实施对外贸易……[9]当然,更多的思想家反对君主专制统治,他们理想中的国家是以中世纪的城市或行会为模板的,即这样的国家既不会压制个人自由,又对君主专制有所限制。黑格尔(Georg Friedrich Hegel)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认为国家并不是一种外在于个人且把自己强加于个人之上的异己的权威,相反,国家就是个人本身,个人只有在国家中个性才能得到真正地实现。[10]基于国家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特殊利益的统一性,他提出国家要承认市民社会不同构成单元的地位、合法权益并给予其特定的保护。黑格尔将其所认为的市民社会的不同构成单元称为“等级”,而这样的“等级”主要包括:由贵族庄园主所构成的实体性等级、行政官吏所组成的普遍等级、工商业代表所形成的私人等级以及同业公会等行业组织。黑格尔认为以上“等级”是个人参与公共事务最好的中介,“国家通过它们进入人民的主观意识,而人民也就开始参与国事”[11],当人们在实现个人目的的同时也为他人服务,他们将更具公共精神,而更为广阔和普遍的社会目的就更容易达成。[12]黑格尔的以上看法为社团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完美的阐释。
1848年之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卡尔·马里奥·温克尔布莱奇(Karl Mario Winkelblech)等人进一步推动了社团主义理论的发展。温克尔布莱奇提出理想的社会应该通过创建全面的行业协会章程,以确保在绝对不需要考虑其特权的基础上,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获得与其工作能力相当的谋生手段。此外,他还建议各行业按照有产者、无产者和其他类型的职业活动者一定的数量比例关系组成“社会议会”(social parliament),所有代表均可以在议会中就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进行充分协商,同时,该议会还可以向传统的政治议会(political parliament)递交决议。在他所设想的这一和谐的社会秩序中,行会式的业主协会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工业自治”将取代官僚集权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而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确定总体经济政策、管理不多的公共行业和改进社会立法。[13]
德国保守主义运动吸纳了温克尔布莱奇等人的主张,遂在此后的社会管理中加以运用。比如俾斯麦(Otto Von Bismark)所希望创建的强大的君主政体就是受到不同团体限制的一种联合政体,[14]魏玛共和国临时由工业、劳工、消费者和自由职业者以及专家组成的经济委员会也是温克尔布莱奇思想的体现。1920年,魏玛政府颁布的《工作委员会法》更是将这一思想拓展到了整个经济领域。该法授权在各企业工会之外创建由雇员组成的工作委员会,以最终促成劳资双方就企业内部所有重大事务相互协商、共同决策模式的出现……[15]尽管纳粹统治期间该制度遭到破坏,但是在德国工会的努力下,1946年,工作委员会的部分功能得以恢复;1947年德国煤、钢产业率先建立了由工人和雇主一起决策的机制;1952年德国《工作章程法案》再次将雇员参与企业决策变成了国家意志。19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主政后,由于该党明确主张所有政策都应该建立在雇主协会、工会和国家机构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因此,社团主义更是逐步渗透进了德国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16]如,德国联邦就业办公室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仰赖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合作,作为利益相关者,联邦层面的雇主和工会代表与联邦政府机构代表共同构成了该办公室管理、决策部门的主体;德国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同样拥有一个由工会、雇主协会代表以及金融和电信领域专家所构成的管理机构……社团主义除了体现在联邦层面的管理和决策过程中,在区域或部门层面以及在个体企业层面的各项管理和决策中,也都有明显的表现。
二、德国职业教育立法筹备、倡议和创制活动中的社团主义
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是一个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是由联邦和各州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构成的。在联邦层面,1953年颁布的《手工业法典》和1969年颁布的《职业培训法案》是两部最为重要的法律,《职业培训法案》更是奠定了德国独具特色的双元职业教育制度的基础。与以上法律相配合,德国联邦还拥有一批相关的、辅助性的职业教育立法。从各州的角度来看,在各州常设教育和文化事务部长会议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框架指引下,各州独立制定本州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整体来看,无论是德国联邦还是各州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在立法筹备、倡议以及创制的过程中,社团主义均有着明显的表现。
(一)立法筹备、倡议活动中的社团主义
如果将国会正式开始对某一立法提案审议之前的与该立法主题相关的所有讨论和协商都算作立法筹备或倡议活动的话,那么,该阶段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时间跨度都将远远超过国会立法创制过程。整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社团主义主要有两种表现方式。
第一种是社会范围内的讨论和协商。自近代德国政府肯定了行会(后为商会)对于职业培训的直接管理权之后,工会方就强调学徒培训的公共属性,质疑将大量的年轻人置于私人企业手中的合理性,批判学徒培训过于依赖经济而非教育逻辑,认为将企业作为主要培训基地不合时宜。而雇主方则坚持企业承担培训成本、负责学徒培训无可厚非,且行业自主管理有助于避免国家集权,增加企业应对市场或技术变迁的灵活性。此外,关于学徒培训是教育关系还是工作关系的争论也很多,工会方面认为培训合同是一种工作协议,而雇主方由于担心培训津贴被视为工资而陷入工资纠纷更愿意其为教育关系……诸多关于职业教育本质、其该如何发展的争论不仅见诸各类媒体,而且在不同层面的专业会议上也有所体现。[17]偶尔出现在司法领域的一些诉讼也会进一步加剧此类纷争的激烈程度。
第二种是立法提案起草过程中的讨论和协商。由于除了政府、政党、议会党团或议员个人之外,德国公民个体、公民小组、工会、经济协会、教科文卫各种联合会等均有权对各自领域的重大事宜提出立法或修法要求,并同时起草参考法案,参考法案经一定审批程序后可以转变为正式递交国会的议案。[18]加之德国《工作委员会法》《工作章程法案》以及之后的《共同决策法案》很早就构建了不同利益团体在机构内部就重要事务协商的机制,因此,与美国等国家在立法倡议或辩论环节临时组建大型游说集团或者依靠个人活动来强化影响不同,[19]各类团体参与机构内部共同决策早已经成为正式制度渗透进了德国社会的机体中,特别是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民主进程的加快,这种现象更为明显。[20]
从职业教育立法提案起草的角度来看,自1919年德国工会向国会递交职业教育立法提案后的半个世纪时间内,先后有多个职业教育立法提案被递交到国会,它们绝大多数是经过内部多种不同利益团体协商之后的结果。比如1969年3月由联邦议院职业培训法小组委员会递交的提案就历经了13次的内部会议协商。[21]
(二)国会立法创制活动中的社团主义
国会是社团主义表现得最为集中的地方。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德国国会的机构设置方式为不同利益团体参与讨论与协商奠定了组织的基础。德国国会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其中参议院由各州代表组成,其主要代表各州人民参与联邦立法过程。联邦议院代表来自公民直选,德国选民在大选中可以投两张票,其中的一票投给自己认可的候选人,另一票投给自己认可的某一政党。因此,联邦议院中就拥有两种利益代表,他们对议院组织机构创建、议事规程制定、大会发言及其时间分配、表决安排等,甚至对联邦政府的组成,政府政策或法案能否在议院顺利通过等均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建立影响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协商、讨论与投票。其次是德国国会的立法程序确保了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对于重要事务的全程参与。德国基本法规定无论哪一种渠道的立法提案,其一般都要经过前置和三读程序,而在每一道关口,倾听不同机构或利益群体的意见并做出积极回应是其顺利进入下一步的前提。比如在前置程序,来自联邦政府的立法提案一般要先经过参议院的审读,参议院的立法提案也会先经联邦政府的审读后,才会递交议院议长。而联邦议院本身的法律提案,也必须首先在议会党团内部取得一致意见,由议会党团提出,或由5%的议员联合提出后才能直接交给议长。此外,在议院的正式审议程序,除了联邦议员、参议员、联邦各部委代表会全程参与讨论协商外,借助媒体,公众也会对正在进行的立法过程有所了解并开展讨论,而有关方面正好借此机会向议员、政党和政府开展院外活动,以期法案能顺利通过。[22]
以上特征在1969年《职业培训法案》的国会创制过程中就可见一斑。此期间,各相关利益团体就职业培训是否具有公共属性、企业培训与学校职业教育的关系如何协调,联邦和州政府应该如何划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责任以及即将制定的法律究竟应该规范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哪些领域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期间,德国社民党着重强调职业培训的公共属性,德国教育委员会则提醒人们不要忽略企业培训也是一种“教育”,议会劳工事务委员会则提出公司和校内职业培训必须尽可能相互协调,议会职业培训法小组委员会主张新创制的法案应该冠以“职业教育和培训法”而非单纯的“职业培训法”……可以这样认为,几乎所有的德国联邦或州职业教育立法的议会创制过程都有社团主义的重要影响。
三、社团主义对德国职业教育立法全面深刻的影响
(一)社团主义决定了德国职业教育立法出台的可能性
由于社团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没有哪个部门拥有绝对的权力,重大事务的处理结果往往是多个利益集团协商讨论、博弈之后的均衡解,这就导致德国包括职业教育法在内的几乎所有法案的出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受社团主义的影响,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原本已经搁置的议题也可能由于一些利益集团的支持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因此,社团主义既是大多数法案经历漫长的立法准备的原因,也是一些法案最后得以颁布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职业培训法案》的出台过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工会希望创建由国家牵头的、独立于手工业和工业部门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23]但是由于工会的提案直接动摇了原有学徒制的基础,遂遭到了工业和手工行业代表的强烈反对,加之其他立法条件并不具备,该提案遂被搁置。之后,尽管社民党利用联邦议院的平台,在1962年4月曾呼吁联邦政府向国会递交职业培训立法提案,社民党希望该提案能够将职业培训领域的多个条款捆绑在一起,同时新提案能够调控青年人就业领域的所有培训关系和雇佣关系,[24]但是联邦政府以此领域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为理由拒绝了此要求。1966年,在看到社民党代表和议院的其他5位成员联合向国会递交了关于劳动力市场调整的相关提案,借此良机,多党联合政府随即在两个月后递交了职业培训提案,尽管该提案很快进入了一读程序,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也不了了之。1968年10月至次年3月,联邦议院职业培训法案小组委员会在社民党主席哈里·利尔(Harry Liehr)的领导下,重新起草了一个职业培训提案,从那时起,讨论协商了40余年的职业教育立法事宜才迈入了实质性的立法阶段并很快成为法案。
(二)社团主义决定了德国职业教育立法的最终形式
一般来说,在社团主义影响较大的国家,提交国会的立法提案与国会最终通过的法案之间会有着巨大的差异,其原因就在于任何通过的法案都是在多方面吸取各团体意见后集思广益的产物。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立法中“双元”“行业自治”等典型特征的形成就是社团主义的产物。
德国教育委员会早在1964年就已经提出了“双元”概念,但是由于德国基本法对于联邦教育权力的限制,1966年由多党联合政府递交的提案仅仅提及了工业部门的职业培训,1969年由社民党牵头递交的提案,仅仅关注手工业和工业部门的培训,传统由各州负责的职业学校的教育并没有涵盖在立法提案之内。为此,学校方面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们坚决要求国会采取措施确保职业学校成为工业和手工业部门培训重要的合作者。由于1969年法律对于联邦政府在教育资助、管理方面的限制已经解除,党派格局也朝向有利于职业培训法案出台的方向发展,因此,在社民党最终递交的提案即将被国会通过之前,学校方的意见终被采纳,双元职业教育制度遂正式形成。
当然,除了“双元”这一特征之外,德国工会1959年提案提出的希望创建由国家管理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完整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建议之所以不可能通过,也是社团主义影响的结果。一方面由于德国商会的力量非常强大,且1953年颁布的《手工业法典》已经对行业自治做出了必要的规定;另一方面,国内主要政党也对国家过多干预教育持反对的态度。因此,多方博弈和协商的结果就是行业自治得以保留。
(三)社团主义决定了德国职业教育立法实施的方式
德国职业教育立法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受到社团主义的影响,主要依靠各类理事会或委员会来实现该影响。如,联邦职业教育培训部是《职业培训法案》规定的联邦层面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宏观管理机构,其内部的主要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8名成员中来自雇主、雇员和州的代表各1名,其余的5名来自联邦政府,教育培训部所有重大决策均出自理事会各派代表的共同协商。商会是直接规约企业培训活动的主要领导机构,《职业培训法案》要求每一种类型的商会均要建立自己的职业培训委员会,凡与职业训练有关的重要事项,均应通知该委员会并向其提出咨询要求。法案要求各商会职业培训委员会由6名雇主代表、6名雇员代表和6名职业学校教师代表组成,职业学校教师有发言权但是没有投票权。只有拥有投票权的半数以上成员到场才符合法定的人数,所有的决定都必须获得委员会多数赞成票后才能产生。[25]法案要求联邦各州也要建立职业培训委员会,尽管各州职业培训委员会接受的是州政府的管理,但是各州委员会也同样是由同等数量的雇主、雇员、州最高当局代表组成……[26]重要事务由不同利益群体共同参与、共同协商,是德国职业教育立法实施的重要特征。
(四)社团主义决定了德国职业教育立法的监督方式
社团主义决定了德国职业教育立法的监督绝不可能来自单一部门。首先不应该忽略上文提到的各类理事会、委员会,它们同时具备监督的功能。因为不同来源的代表在各类理事会、委员会共同决策时,他们之间的相互协商、争论,对于确保法律运行在正确的轨道有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发生在理事会或委员会中的相互监督,德国职业教育立法的设计方式,也确保了各层面的重要事务随时能够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比如,企业参与学徒培训是双元职业教育立法的基点,为了使单个企业的培训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职业培训法案》第4条明确要求企业必须在国家认可的培训行业名单内进行培训。而法案同时规定:联邦经济技术部和其他主管部门应与联邦教育研究部在达成一致意见后(可无须经联邦议院批准)正式发布这一名单……如果培训名单或其他事情发生变化,主管部门应及时通知州政府相关部门,并让他们参与协商。[27]此外,对于培训企业自身的资质问题,法案也要求多个管理部门协商后首先要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向联邦职业教育培训部征询意见之后再行发布。由于企业与学徒之间签订的合同是确保初始培训(Initial training)沿着预定轨道进行的重要保障,因此,签订好的合同不仅需要在各类商会注册登记,且商会还会雇佣专门的培训指导员对所辖企业的培训活动和学徒考试质量实施全程的监管。当然,除商会监管之外,工会、雇主协会也会对公司的培训过程及培训质量实施多次的检查。除了以上来自企业外部的监督力量,所有的学徒都持有培训日志本,该日志详细记录了学徒如何向企业方进行咨询、学徒的日常行为、学徒与同事的关系等内容,负责任的企业培训人员会定期检查该记录并签字,各商会考试局也非常看重这一记录。[28]
(五)社团主义对德国职业教育立法实施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团主义也影响着德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实施效果。由于立法确保了企业培训领域的几乎所有重要事情都是由政府、商会、工会等多部门集体协商、一致同意后决定的,这一机制不仅是培训企业高度认可培训活动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为各相关利益团体积极参与与培训相关的各类活动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和心理基础。因此,与英、美等国企业更为经常地从市场直接招募合格劳动力的做法相比,德国企业更愿意参加双元制培训。据统计,2015年,德国有占总量近20%的企业提供了各种类型的学徒培训,其中,超过81%的大型企业参与了各种类型的培训。[29]这些企业不仅是培训场所、培训活动、培训费用、学徒津贴的提供者,而且培训结束后,培训企业还将为至少60%的学徒提供在本企业任职的机会。
德国企业的以上做法不仅强化了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国青年的失业率。2018年3月,德国15~24岁青年失业率为4.8%,为欧盟最低,而欧盟所有成员国青年的平均失业率为15.9%。[30]此外,由于相对较高质量的双元制培训,德国企业还收获了源源不断高水平的员工,从而使德国产品的质量得到了较好保障。当然,由于社团主义是一种将不同利益团体捆绑进职业培训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方式,在经济发展良好、变化相对缓慢的时代,社团主义可能对职业教育立法实施效果带来更多正面的影响。但是,在技术更新速度加快、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中,由于各个团体的利益都要平衡,社团主义不仅可能降低企业决策的速度,还可能降低企业参与培训的意愿,进而对立法实施的效果带来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