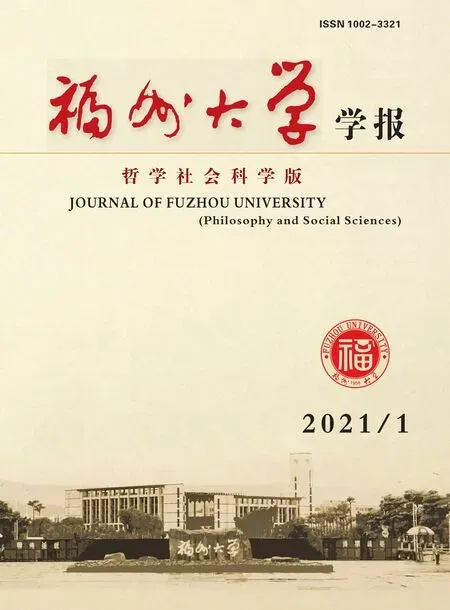论《春秋》经传二案如何“别嫌疑”
2021-12-03陈罕含
陈罕含
(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 台湾新竹 300044)
一、“嫌疑”义小解
《说文》:“嫌,一曰‘疑’也”;“疑,惑也。”[1]“嫌疑”乃同义复词,“疑”字常读为“拟(擬)”,如《礼记》卷六二《燕义》:
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亢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
郑《注》:
疑,自下上至之辞也。公卿尊矣,复以为宾,则尊与君大相近。
孔《疏》点明:
疑,拟也,是在下比拟于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辞也”。[2]
简言之,因为“拟”(相近),所以难辨而容易产生“疑”惑。“嫌疑”一定存在参照物,它描述的是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事物差别幽微。进一步来说,古人认为哪些事物很有必要“别嫌疑”?这范围由小及大,涵盖甚广,然而下面三种是比较常见的:
(一)上下尊卑
按照法礼,甲尊不可比,而乙将要或可能近之,这时就必须在二者间设防,以免乙企及甲。此类案例不待烦举。
(二)文辞歧义
特别是官方文书,注重指谓、语义的明确表达,避免模棱两可,造成误会。《公》《谷》二传认为《春秋》乃微言大义,为了阐发“大义”,就不能不辨析“微言”,是以孜孜堵塞各种文辞歧义,从而导向各自师传的解经正道。例如,《公羊·桓公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战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恶乎嫌?嫌与郑人战也”[3];《谷梁·昭公二三年》“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别嫌乎尹氏之朝也”[4]。
(三)罪恶
对于法礼、伦常、道德中负面的人事物,儒家尤其注重要主动防避。例如,《荀子·礼论》:“丧其严亲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则嫌于禽兽矣。”[5]儒家洞察到人与禽兽绝非相隔悬远,人与动物的防线不在栅栏,而在道德自觉,然而“人心之危,道心之微”[6],道德的脆弱性终究使得“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7]。有鉴于此,“几”“微”的罪恶乃至起心动念都必须防杜。
古人在决“是非”“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别嫌疑”的大原则,所谓“是非难别者在……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8]。他们观察到世界除了是非分明的有色区块,某些角落似乎还覆盖着难辨的迷雾、未知的阴影。对认识事物的性质来说,已然是一大进步。难辨的困窘、未知的不安,都更加促迫人们想要探索未知、拨云见日的欲望,然而,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豁然解决之道。为什么说“嫌疑”“难别”呢?产生困难的原因乃至根源究竟为何?礼文本身没有多加阐释,却引人深思。《春秋》经、传记载了两起非常特别又密切相关的“弒君”案:“赵盾弒其君夷皋”“许世子止弒其君买”,似乎对“别嫌疑”的礼义,投射出些许鉴镜的微光。
二、史官书“弒”臆诠
《春秋》经,鲁宣公二年(晋灵公十四年):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弒其君夷皋。
三传微别者,《公羊》“皋”作“獆”,乃通假字。三传皆云,《春秋》之所以如此记载,据三传是本自当时晋史所书:
(晋)大史书曰:“赵盾弒其君”。(《左传》宣公二年)[9]
晋史书贼曰:“晋赵盾弒其君夷獆”。(《公羊》宣公六年)[10]
史狐书贼曰:“赵盾弒公”。(《谷梁》宣公二年)[11]
或许缘于此桩大案在当时过于轰动,晋国本土乃至列国间流传甚广,是以难得地留下了秉笔的史官名氏:董狐。另一桩案件则发生在鲁昭公十九年(许悼公二十四年),《春秋》经:
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弒其君买。
鲁、许虽非邻国,然许公卒、葬常常见载《春秋》,卒书日而葬书时,显然二国有使者互通消息。鲁史书“弑”,当源于许国赴告、传闻之辞。这两桩案件的共同点在于:史官斩钉截铁地书此二人为“弒君”,然而三传推寻事情原委,皆认为赵盾、许止并非忍弒君者,同时又承认他们都有难以撇清的咎责。《谷梁·宣公二年》早已观察到这两桩案件间丝缕暗穿,相形益彰:
于盾也,见忠臣之至;于许世子止,见孝子之至。
“忠臣之至”“孝子之至”,意谓臣尽忠、子尽孝的最高标准。《谷梁》没有否认赵盾是忠臣,许止乃孝子,但认为二人达不到“至”的高度,遂不慎背负“弒君”的极恶名。司马迁大概对其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冷峻气氛深有所感,严厉而沉重地警示: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弒之诛、死罪之名。[12]
此二桩案件于今遥渺,当日历史真相如何,恐难悬断。现且循着三传所回放的“录像”,试探当日国史书“弒”之情由:
(一)赵盾
赵穿率人亲弒晋君,当时赵盾在外,并未参与弒君事,此三传共识: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左传》)
亲弒君者赵穿也……赵穿缘民众不说,起弒灵公,然后迎赵盾而入。(《公羊》)
穿弒也,盾不弒……赵穿弒公而后反赵盾。(《谷梁》)
那么,晋大史董狐为什么不径书赵穿弒君,而书赵盾弒君呢?三传共录史狐作为“控方”的辩辞:
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左传》)
尔为仁为义,人弒尔君,而复国不讨贼,此非弒君如何?(《公羊》)
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弒,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谷梁》)
对比来看,《左传》最为简单,三传重合浓墨处,即史狐列举赵盾身为正卿的最大罪状——反不讨贼。执政大臣乃君主股肱,元首被弒,理应担起讨贼之任,结果竟不讨贼,这是不是严重的罪过呢?于情于理,当然是,然而,即使执政大臣不讨弒君贼是严重的罪过,也不意味着他就等同弒君之贼了。否则,《春秋》君弒而执政大臣不讨贼之事俯拾皆是,被扣弒君帽的怎会仅见赵盾一人?那么,史狐究竟是如何把赵盾不讨贼的行为与弒君罪名紧扣起来的?《公羊》点了一句“尔为仁为义”,看似突兀,实则可能包裹深意。试道这句话的潜台词:德行、能力中等乃至低下的当政者,不讨贼,可能因为心志之昏鄙、力势之衰弱,“斗筲之人,何足算也?”[13]然而你赵盾素来仁义面貌,文武兼备,你不讨贼,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此非弒君如何?”《公羊》比《左传》逼进一大层,但中间跳了一步,这一步,由《谷梁》补足了:“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志同”后省略的是“于贼(赵穿)”。史狐指出,赵盾不讨弒君贼臣赵穿,乃因他与穿同有弒君之志,穿之举,正惬盾意。至此,图穷匕见,史狐的锋刃直指赵盾之心——是否有弒君之志。抓住这个“线头”,或许就可以解开史狐何以牵拉起“入谏不听,出亡不远”那些看起来与“弒君”遥隔的蛛丝“罪状”。
如何推测赵盾有无弒君之志呢?一种如史狐所明说的,举赵盾的行迹来表现;还有一种就是察看他是否有弒君的动机。有犯罪动机,未必一定导致犯罪;但有动机,实施犯罪可能性的闸门就会开启。尤其按照公羊学,“君、亲无将”[14],有动机等同付诸实际行动。不知史狐是否暗揣过赵盾可能的弒君动机,即使有,亦不足为怪。今天不论犯罪学说还是实际的司法审理,都会将犯罪动机纳入考虑。赵盾与灵公是何种关系,朝人尽知,史狐更不待言。鲁文公六年八月,晋襄公卒,“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盾首推襄公庶弟公子雍,故“使先蔑、士会如秦立公子雍”。文公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多与之徒卫。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盾摇摆之下,改立灵公,而灵公继位之时,尚不离其母怀“抱”[15],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16]而论,当不满三周岁。至鲁宣公二年被弒,还仅仅是十六、七岁的青少年,然而,这位少年国君小小年纪就已经实施诸多“不君”(《左传》)、“无道”(《公羊》)的桀纣行了。作为“良大夫”(《左传》引“孔子”评论)的赵盾,自然不能“危而不持,颠而不扶”[17],眼睁睁看着君、国一体沉沦,只是他“骤谏”(《左传》)进忠,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使得灵公更加忌恨,数度欲除之而后快。既不容于国君,赵盾只好逃难他邦。于公,赵盾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无望悔改的昏暴少主;于私,赵盾面对的是一个仇己以至屡次痛下杀手的恶人。如果赵盾真的参与了弒君事,以上都有可能成为他弒君的动机。恰巧最后弒君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赵穿——赵盾的族亲。[18]且盾闻穿弒君,“未出山而复”(《左传》),不但不讨贼,反倒与弒君贼一起拥立襄公弟公子黑臀——似又回到了襄公卒时、赵盾欲立长君的起点上。这一切与本案有关的“蛛丝马迹”,或疑于董狐之腹而坐实于宋儒之笔。[19]
综上,史狐虽然用反诘的口吻、独断的语气,下了一个赵盾“弒君”的判决,但他的辩证过程却不是从弒君之行本身举证,而是从赵盾有弒君之志的表现举证。不禁让人联想起“鸭子测试”的归纳推理:
如果它看起来像鸭子,游泳像鸭子,叫声像鸭子,那么它就是一只鸭子。
类似地,史狐的辩证逻辑是:身为正卿的赵盾,你在君弒事前、事后的种种行径都像有弒君之志的人会采取的行径,那么你就是弒君者。接下来,问题症结出现了,史狐为什么不径举赵盾的实际弒君行为?而要绕到外围去抓罪证呢?显然,史狐没有找到任何赵盾与赵穿暗通曲款或盾早谋弒君的罪证[20],否则,不怕被当政者打击报复也要坚持“不隐”“恶”(《左传》引“孔子”评论)的史狐岂会舍此铁证而责彼曲志?赵盾的不讨贼等举止让他无法与弒君之人划清界限,乃至暗示他很可能也有弒君之志,这在史狐看来已是不可原谅,弒君嫌疑不比其他,“宁可错杀,不能放过”,所以即使他举不出铁证证明赵盾是弒君贼,但也不能就此放过这位嫌疑犯。《谷梁》“志同,则书重”[21],身为正卿的赵盾乃君之副贰,自然比赵穿来得贵重,更不必说赵穿弒君时所率领的那些部众,是以史狐集诸责于盾一身,书曰:“赵盾弒其君”。
(二)许止
许止被认定为弒君贼之时,当为国君被弒后不久。悼公之死,《春秋》经文外,三传所记[22]甚简。《谷梁》几乎无文,《左传》对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各以一言概之:
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
点出一个关键信息:许君服世子止所进之药,当天即离世。因为时间相隔甚近,是以当时人归咎在了世子所进之药上。《公羊》对整个过程一言以蔽之:
止进药而药杀。
试拟当时所见之景象:一是国君服了世子药而暴卒。在春秋,嗣子谋害君父,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以至于构陷嗣子预谋作乱的案例亦层出不穷。或许有人会产生与宋平公类似的疑问:作为嗣子,不是可以顺理成章继位的吗?走弒君这一险着,图什么呢?最简捷的回答就是:“欲速。”[23]何太急也?理由当然很多,不得不提的春秋舞台上同时常见的场景:君父废黜、囚禁、放逐乃至戕害嗣子。所谓“君二多难”[24],为政大臣与嗣子在这点上的处境殊为相似;二是疑犯的反应,从三传来看,世子似乎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辩解的说辞。不论是《左传》“大子奔晋”,还是《谷梁》“止曰:‘我与夫弒者’”,世子要么回避,要么承认了扑面而来的弒君罪名(详参下章)。时人面对一个无法开脱弒君罪名的重大疑犯,乃认定曰:“止弒其君。”
三、疑犯的反应
(一)赵盾
为避灵公追杀,赵盾出亡,已是劫后余生,复国回朝,又临一劫。猛然面对大史当朝手执书简指斥自己为弒君元凶,赵盾是何反应?参照《左传》,他的第一反应非常明确:“不然!”且不作解释,为何?若非赵盾咬紧牙关不认账,则很可能在他的认知里,自己没有弒君这件事昭然若揭,无需解释。史狐进而逼问盾“亡不越竟,反不讨贼”是何居心?赵盾或许百感交集,最后吐露了这几句话:
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赵盾赋诗言志,他说自己自取忧咎,皆因不该“怀”而“怀”。需要厘清的是,“亡不越竟”本身并非过错,《左传》引“孔子”评论“惜也,越竟乃免”,杜《注》“越竟则君臣之义绝,可以不讨贼”。君臣义绝,则赵盾不复为晋国之臣,更非正卿。既不在其位,可以免去讨贼之责。当然,不在其位,也意味着赵盾失去了正卿的位禄、荣宠、权力而退出晋国政坛,难再参与国家的一切政事,包括自己对晋国与先君的责任、感情。于公于私,赵盾大概都有难以割舍的“怀”恋,所以他基本上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头。这一回头,赵盾旋即踏进弒君嫌疑的泥沼。
《公》《谷》二传中,赵盾初闻弒君罪名时的反应更加激烈:
天乎!无辜!吾不弒君,谁谓吾弒君者乎!(《公羊》)
天乎天乎!予无罪,孰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谷梁》)
二传辞义无甚差别,寥寥数语,却包含了多重意义:赵盾呼天,先不论其深层涵义,且从表面看,他的情绪非常激动,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弒君乃人臣罪恶之颠,他实在难以接受如此恶名。另一方面,赵盾认为自己本无弒君行,何来弒君罪?更进一步表示“谁谓吾弒君者乎!”“孰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用今天的大白话说就是:“我怎么会是那种人!”这已经涉及史狐责难的聚焦点:赵盾有没有弒君之志?不论是《左传》归咎于“怀”,还是《谷梁传》的不“忍”(狠),赵盾都间接/直接地否认了自己有弒君之志。史狐显然没有接受赵盾的辩解,不改所书。
(二)许止
许止表现出的反应与情绪激动的赵盾完全不同,根据三传的简略记载,他对于弒君罪名,不作任何自辩,这包括解释药品的配方、来历、进药经过,乃至自己毫无弒君意图的表态等等。除了《谷梁》留下一句“我与夫弒者”径直认罪的话。三传倒是积极作为许止的“辩护团”,努力将他的罪责从弒君下降到过失致君死亡。三传何以如此确定?或许不是因为简略的传文外还掌握多少宫闱内幕,而更可能是从许止的后续表现推测,加之《公》《谷》以义例解经的习惯。
以《左传》而论,许悼公暴卒后,许止非但没有以嗣君身份继位,却仓皇“奔晋”,流亡他邦。《左传》梗概的记事下完全不见人物意志,《传》本身也没有添加任何品评笔墨[25],最后由“君子”站出来给整个故事注入骨血:“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君子”显然也认为许止于君父死亡非蓄意谋杀,否则,如同弃兵器岂可止杀,“舍药物”又岂足止弒呢?《公》《谷》解经一向以义例束约,《春秋》经书“冬葬许悼公”,二传皆有“君弒,贼不讨,不书葬”[26]的义例,而许君弒、葬间不见讨贼经文,《谷梁》适又提出“日杀,正卒”的义例,是以《公》《谷》不待参考传记,单凭经文已将许止定格在“不成于弒”/“不弒”的解释框架内。《谷梁》续足许止后闻,叙止主动让位,又因沉溺在弒君罪责中,身体不堪精神重压,“未逾年而死”。后世多疑赵盾而寡嫌许止,恐怕与传闻弒君后二人的荣辱得失关系不浅,然二人后续如何,应无改于国史当日所书及他国史官遥载。
四、二案引发的省思:如何“别嫌疑”?
暂且假定赵盾与许止都无意弒君,他们要如何撇清自己弒君的嫌疑呢?先说许止。按照一般情理,许君之死与许止所进之药间有以下几种关联可能:
A. 药乃欲弒许君之毒药,但下毒之人却并非许止,止不知情而进药。
B. 药本身并非毒药,但其中含有对许君病情有害的成分,许止不知药性而进献,间接促成或直接导致许君猝死。
C. 药本身并非毒药,且许君之死与服用此药毫无关系,只是许止进药时间凑巧赶上其父垂危之际。
三者中,只有在C的情况下,许止才是绝对无辜的。如果放在现代,或许有机会通过尸检或对药物进行化学检测来证明死者死亡原因与服用自己所进献的药物无关,然而,在春秋时代,这样的观念与技术尚为欠缺。因此,许止很难撇清自己所进药致君死亡的重大嫌疑,甚至,连他自己都未必能够确定此药竟与君父死亡之间关联几何。那么,许止唯一可能撇清的嫌疑,就是自己并无弒君之志,他乃过失犯罪而非故意犯罪。但就连这一点,也不简单。按照上文提到的两种后续结局,他主动或被动地弃位、出逃,乃至因为深陷弒君罪责、精神崩溃而早夭。总之,在案发后非但没有得到丝毫利益,反而灾咎加身,都让人更愿意相信他是无心之失。只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27],诸般揣测,究竟不同于证实。许止至多能让他人主观上选择相信自己是无心的,而不能让他人客观上确认乃至证实自己是无心的。简言之,许止案发后的表现的确有助于他辨别“有意弒君”的嫌疑,但终究不能彻底撇清嫌疑。并且,类似事后“别嫌疑”的方式,当事人往往要付出相当代价。那么,三传是否提出良策呢?《谷梁》提出“尝药”方法,以今日医学常识来看,作用未必充足。因为尝药之人与身患疟疾的许君体质不可能完全一样,药品的作用力也会随之变化。除非药真是毒药,否则尝药能起的预防作用有限。《公羊》责止“子道之不尽”,并举出“乐正子春之视疾”的正面榜样,大义坦然,却不免失于笼统。相较之下,《左传》“君子”返回最初起点:“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君子”提出,从世子进药这个源头就应该掐断。试推拟“君子”如此主张的深层考虑:世子进药,即使这药没有问题,一旦国君出了事,世子说得清楚吗? “君子”显然体察到,世子进药后的麻烦,并非可凭目测以提早规避[28],而如草莽掩盖下纵横交错的荆棘一般,隐而不见。这种眼光、思路在后世定型为“蚤防”“远嫌疑”[29]的原则、精神,正式在草莽外围树立起警示牌:禁止踏入。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把焦点转向赵盾,如果他在灵公被弒、赵穿召归之时,不回头地越境而走,远离是非,那么弒君嫌疑也就无从困身了。照这样说来,“防嫌”乃上策,然而,前提是赵盾/许止能够逆料到回朝/进药可能会惹来何种后果。此外,“防嫌药方”有一大“副作用”:积极“防嫌”有时会滑入消极作为。如果赵盾选择远离家国,于公于私都要抛却甚多,所以即使他能逆料到会被大史书为弒君贼这个后果,他也未必会选择“防嫌”之路。以许止来说,如果这药是他潜心觅得的奇方仙草,为了“防嫌”而怀宝坐待,岂能算“尽心力以事君”?有力而不出,不也是“子道之不尽”吗?总之,不论事先“防嫌”,还是事后“别嫌”,都需要权衡利弊得失,难以概论优劣。最后,剩下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赵盾没有弒君之志,那他为什么不“讨贼”?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无意为赵盾回护,的确,不讨伐弒君之人,是他作为正卿不能逃脱的重大罪咎,但是,“讨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赵盾有心且有力诛杀赵穿。赵盾显然不是如此,但即使他“不讨贼”,也不意味着他就成了“贼”。与此相对的是,《春秋》那些真正的弒君贼倒会找“替罪羊”而“讨”之[30]。或应警醒的是,“讨贼”有助于“别嫌”,却无改于真相。
不论从上文粗浅的讨论,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切身经验,我们大概都会感到“别嫌疑”有时并非易事。那么,它的困难、症结产生的根源究竟为何?上文提到,面对史狐的诘责,《公》《谷》二传中赵盾的第一反应皆是对天明志“天乎!无辜!”“天乎天乎!予无罪”。何止赵盾,面对猜疑、问罪,人们经常会通过诉天、赌咒来表示自己诚然无辜,如《毛诗·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
昊天已威,予慎无罪。昊天大幠,予慎无辜。[31]
再者,那段众所周知的孔子窘事: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32]
古今中外皆然,不待烦举,有意无意间昭示了古人认为欲“别嫌疑”者应该诉诸的大法官:天/神/上帝。[33]天知晓,但是天无言。古人就想方设法请老天爷开口示下,“卜筮决疑”与“昭神断疑案”即为两类典型案例。所谓“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34],只不过“疑”难杂症,非“卜筮”不能“决”了,《尚书·周书·洪范》:
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择建立卜、筮人。[35]
相对于“视曰明”[36],“疑”乃凡人看不到的盲点。“明作哲”[37],不止是眼睛看不到,更因不具备“哲”智的心眼。“明”的全视之眼除了高瞻当下万物,也包括远瞩未来几变:“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38]。以为有了全视者的指示、扶助,自然就能毫无疑虑地做决定,且保证决策必然准确无误,是以《礼记·曲礼上》说:
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39]
道理虽备,还需以实例辅明,《左传·襄公三一年》与《昭公二六年》记载了鲁国与周室贵族相传中先王制定的王位继承原则:
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长立,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
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40]
继承顺序依次为:1.嫡(贵贱);2.长(年资);3.贤(才德)。[41]诸般人为条件都相等,意味着对常人来说,候选人拥有完全一样的继位资质。卜筮绝非如抓阄一样随机选择,而是非常严肃地“请神择”“立”。《左传·昭公十三年》记录下一个较为完整的案例:
(楚)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42]
相对于预测未来的卜筮,“疑案”则是已经发生的事。赵盾、许止的两个案例已能略微显示,“已然”却未必能够“了然”,所以“疑案”难以完全避免。针对“疑案”,《论衡》记载了上古传说中的一种“羊触”决疑法:
觟角虎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43]
参考《墨子·明鬼下》,可知在巫术信仰盛行的上古,之所以有人认为此类“羊”能够断案决疑,或许除了偶然间“发现”它们身上暗藏某些辨别是非的“性”能,更可能是经过一番巫术仪式后,将之视作绝对公正的“神”的化身而信赖听从:
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于是泏洫,扌恶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出],而槁之,殪之盟所。[44]
关于这桩疑案,传说除了透露“讼三年而狱不断”以见疑案难解之外,别无其他信息。其实,案件细节并不重要,关键的是,古人察觉到,有一类罪恶是他人乃至当事人都很难看见、觉察的,所谓“隐慝”,然任何罪恶于“神”面前皆无所隐遁。古人相信,透过“神”力、“天戒”就能将这些“隐慝”暴露于日光下。[45]
相对于古人认为天/神/上帝眼中一清二楚,绝无阻碍,本来无“嫌疑”,何需“别嫌疑”?人的智识却是有限,因此难免会产生“嫌疑”。当然古人也提出有所谓的“特例”——圣人,所谓“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46],然而,从孔子矢誓自明的窘急可见,即使圣人可以正嫌别疑,但他们却不能保证对方也是圣人,不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以至于让别人撇清自己的嫌疑。
综上,“嫌疑”是古人发现在是非之外难辨而又不能忽视、错漏的环节,比如上下尊卑、官方文辞与忠孝大义。本文所举案例,赵盾与许止是弒君真凶吗?乃至他们有弑君之志吗?千载之下已无从悬断。《春秋》史官径书“弑”字,展现的是史家担负辨别黑白的天职,以至于必须作出“断案”处理,看似别清了“嫌疑”,然而三传铺展了更多材料来揭示,“嫌疑”者未必是真凶,“别嫌疑”的工作并未完成。单单一个“弑”字,遮蔽了更复杂的历史真相、情景。窃以为礼文“别嫌疑”在这两个《春秋》经传的实例中展现了它大纲领下的多棱面相,或可略窥礼在实践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规范价值与实际解决问题时面对的复杂情形。简言之,“别嫌疑”非常重要,但是如何“别嫌疑”却并不容易。或许更多的案例的探讨,方有助于对礼文与《春秋》经传的切实理解。本文仅是一管之窥而已。
注释:
[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十二篇上《女部·嫌》,第623页;卷十四篇下《子部·疑》,第743页。
[2] 孔颖达:《礼记正义》卷六二《燕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90页。其他“疑”“拟”通假案例可酌参高 亨:《古字通假会典》,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376页。
[3] 徐 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220页。
[4] 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440页。
[5][6] 王先谦:《荀子集解》,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605,656页。
[7] 孙 奭:《孟子注疏·离娄下》,《十三经注疏》,第2727页。
[8] 苏 舆:《春秋繁露义证》卷二《竹林》,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7页。
[9]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一《宣公二年》,《十三经注疏》,第1867页。《左传》记载“赵盾弒君”案前因后果,主要在此年,从“晋灵公不君”至“壬申朝于武宫”,《十三经注疏》,第1866-1867页。本文以下凡引此段传文者,皆不复一一标明卷数、页码。
[10]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五《宣公六年》,《十三经注疏》,第2279页。《公羊》记载“赵盾弒君”案前因后果,主要在此年,从“赵盾弒君”至“而立成公黑臀”,《十三经注疏》,第2279-2280页。本文以下凡引此段传文者,皆不复一一标明卷数、页码。
[11] 《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十二《宣公二年》,《十三经注疏》,第2412页。《谷梁》记载“赵盾弒君”案前因后果,主要在此年,从“穿弒也”至“见孝子之至”,《十三经注疏》,第2412页。本文以下凡引此段传文者,皆不复一一标明卷数、页码。
[12] 司马迁:《史记》卷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58页。
[13] 邢 昺:《论语注疏》卷十三《子路》,《十三经注疏》,第2508页。
[14]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九《庄公三二年》,《十三经注疏》,第2242页;卷二二《昭公元年》,《十三经注疏》,第2316页。
[15]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十三经注疏》,第1844-1845页。
[16] 《论语注疏》卷十七《阳货》,《十三经注疏》,第2526页。
[17] 《论语注疏》卷十六《季氏》,《十三经注疏》,第2520页。
[18] 一说为盾从父兄弟,如《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盾昆弟将军赵穿”,第201页;一说为盾从父昆弟之子,如韦昭,见徐元诰:《国语集解·晋语五·灵公虐·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81页。可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文公十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90页。
[19] 略举二例,[南宋]洪咨夔《春秋说》卷十五《宣公二年》:“盾无君之心久矣。灵公之立,非其本志,君臣之猜隙已深。而盾以拥翼为己恩,尽专晋政,威福已出。新城之盟、棐林之会,偃然以大夫敌列国之君而不忌;桃园肆恶,与穿素有成谋,特至此而动尔。穿攻公而盾出奔,二人相为表里,以嫁其迹,发踪不可掩也。穿为盾弒,盾为穿芘,盾首、穿从,坦然明白。”(王云五《四库全书珍本三集·7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6b页)[南宋]张洽《春秋集注》卷六《宣公二年》:“及至灵公欲杀盾,而盾伪出奔。穿弒公于桃园,则未出山而归复其位。若取穿尸诸市朝,犹可以自明也,乃使穿逆公子黑臀而为君……不讨而用之,董狐‘非子而谁’之言,是乃推见至隐而归弒于盾,真至公之笔也。”(王荣国:《辽宁省图书馆孤本善本丛刊》第一辑,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第114b页)
[20] 从相关传记来看,后世似乎也没有抓到赵盾实际参与弒君的罪证乃至重新清算此案。赵盾卒后,即使在赵氏家族危亡之际,时人依旧推崇盾之“忠”。《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六《成公八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景公)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十三经注疏》,第1904页)据《成公十七年》,韩厥曾“畜于赵氏”,受恩于盾乃事实,但若赵盾在当时恶有所发,厥岂敢在国君面前颠倒黑白,指奸为忠?《国语集解·晋语六·赵文子冠》记载赵武成年举行冠礼之日,拜见诸卿大夫,知武子(罃)同样以乃祖赵盾之“忠”勉励他:“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宣子尽谏于襄、灵,以谏取恶,不惮死进,可不谓忠乎?吾子勉之!”(《国语集解》,第387-389页),可见至少在传闻中,赵盾身后晋国庙堂之上依旧认他为忠臣典范。
[21] 值得一提的是,“书(当事人/国)意/志”与“书/举重”向来是《公》《谷》反复提出的春秋书法。《公羊》惯用书“意”,如卷十《僖公元年》:“夏六月,邢迁于陈仪。迁者何?其意也。迁之者何?非其意也。”(《十三经注疏》,第2246页)《谷梁》惯用书“志”,如卷二《隐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及者,内为志焉尔。遇者,志相得也。”(《十三经注疏》,第2369页)又《公羊》惯用“书”重,如卷三《隐公五年》:“秋,卫师入盛。曷为或言率师,或不言率师?将尊、师众,称某率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卑、师少,称人。君将不言率师,书其重者也。”(《十三经注疏》,第2207页)《谷梁》多用“举”重,如卷九《僖公三三年》:“陨霜不杀草。未可杀而杀,举重也;可杀而不杀,举轻也。”(《十三经注疏》,第2403页)
[22] 三传记载“许止弒君”案,皆为昭公十九年,《左传》从“夏许悼公疟”至“舍药物可也”,《十三经注疏》,第2087页;《公羊》从“贼未讨”至“免止之罪辞也”,《十三经注疏》,第2324页;《谷梁》从“日弒正卒也”至“故君子即止自责而责之也”,《十三经注疏》,第2439页。本文以下凡引出于上述传文者,仅标明引自何传,不复一一注明卷数、年份、页码。
[23] 《左传·襄公二六年》:“(寺人惠墙伊戾)告(宋平)公曰:‘大子(痤)将为乱……’公曰:‘为我子,又何求?’对曰:‘欲速’……公囚大子……(大子)缢而死。”(《十三经注疏》,第1990页)杨伯峻指出:“子谓嗣子”,是也,例证可参《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六年》,《十三经注疏》,第1118页;《哀公二年》,《十三经注疏》,第1612页。
[24] 《左传·哀公六年》:“君异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匮,君二多难。”(《十三经注疏》,第2162页)
[25] 所谓品评笔墨,指的是诸如“晋灵公不君”、“佐恶而婉,大子痤美而很”这样以简单概括文字“不君”“婉”“很”品评人物品质、性格的传文。
[26]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三《隐公十一年》,《十三经注疏》,第2210页;《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二《隐公十一年》,《十三经注疏》,第2371页。
[27] 孔颖达:《毛诗注疏》卷十二之三《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十三经注疏》,第454页。
[28]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八《昭公十九年》,杜《注》以技术层面解读“君子”之见:“药物有毒,当由医,非凡人所知”(《十三经注疏》,第2087页),似不足据。怎知世子进药不由医?难道药方全是世子自己想出且亲自采集、配制的?杜预的解释未免把复杂问题单一化了。
[29] 苏 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八《度制》:“凡百乱之源,皆出嫌疑纤微,以渐浸稍长至于大。圣人章其疑者,别其微者,绝其纤者,不得嫌,以蚤防之。圣人之道,众堤防之类也,谓之度制,谓之礼节。”(《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26页)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二八下《冯衍传下》:“卫尉阴兴,敬慎周密,内自修敕,外远嫌疑,故敢与交通。”(《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2页)
[30] 如《春秋左传正义》卷四《隐公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贼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十三经注疏》,第1737页)《公羊传注疏》卷九《闵公元年》,第2243页:“庄公死,庆父谓(仆人邓扈)乐曰:‘般之辱尔,国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后诛邓扈乐而归狱焉,季子至而不变也。”(《十三经注疏》,第2243页)
[31] 《毛诗注疏》卷十二之三《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十三经注疏》,第453页。
[32] 《论语注疏》卷六《雍也》,《十三经注疏》,第2479页。
[33]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卷十八《赵策一·4晋毕阳之孙豫让》,记载著名的豫让刺赵襄子事,豫让伏剑而死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而可以报知伯矣!’”其中“呼天”,同样是将旁人难以理解的报恩节义的委曲心意对上天乃至死去的知伯表达。见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6页。
[34]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三《昭公五年》,《十三经注疏》,第2043页。
[35] 《尚书注疏》卷十二《洪范》,《十三经注疏》,第188-191页。
[36][37] 《尚书注疏》卷十二《洪范》,《十三经注疏》,第188,188页。
[38] 《后汉书集解》卷八二上《方术列传上》:“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后汉书集解》,第945页)
[39] 《礼记注疏》卷三《曲礼上》,《十三经注疏》,第1252页。
[40]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襄公三一年》,《十三经注疏》,第2014页;卷五二《昭公二六年》,《十三经注疏》,第2115页。
[41] 实际政治运作固然不可能完全遵守此规则,然从《左传》来看,此三点的确是王公大夫择立继承人的重要参考指标。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指标也常常纳入考虑:一为是否得君父之“宠”;一为有无大国之“援”。如上文提到,晋襄公卒后,赵盾本欲立公子雍,是以与欲立公子乐的贾季当朝辩争。《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上《文公六年》:“赵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贾季曰:‘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孟曰:‘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辟也。母淫、子辟,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安焉……先君……爱其子(公子雍),而仕诸秦,为亚卿焉。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十三经注疏》,第1844页)
[42]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六《昭公十三年》,《十三经注疏》,第2070页。
[43] 黄 晖:《论衡校释》卷十七《是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60页。
[44] 孙诒让:《墨子閒诂》卷八《明鬼下》,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32-233页。
[45]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四《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十三经注疏》,第1808页);《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一《僖公十五年》:“雷电击夷伯之庙……天戒之……何以书?记异也。”(《十三经注疏》,第2254页)类似一幕,早见诸《尚书·周书·金縢》:“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成王不辨忠邪,狐疑周公,当面又“未敢诮”,憋在心里。若非“天动威”,“(君主)蒙,恒风”,导致王发金縢之书,成王岂能感悟天意,体察周“公勤劳王家”、自觉“惟予冲人弗及知”而悔改?参《尚书注疏》卷十三《金縢》,第196-197页;卷十二《洪范》,第192页。循此脉络,再看《论语注疏》卷十《乡党》:“迅雷、风烈,必变”(《十三经注疏》,第2496页),乃至《礼记注疏》卷二九《玉藻》:“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十三经注疏》,第548页),或许就可以了解何以“变天”要“变色”了。
[46] 《春秋繁露义证》,卷十《深察名号》,第296页;《实性》,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