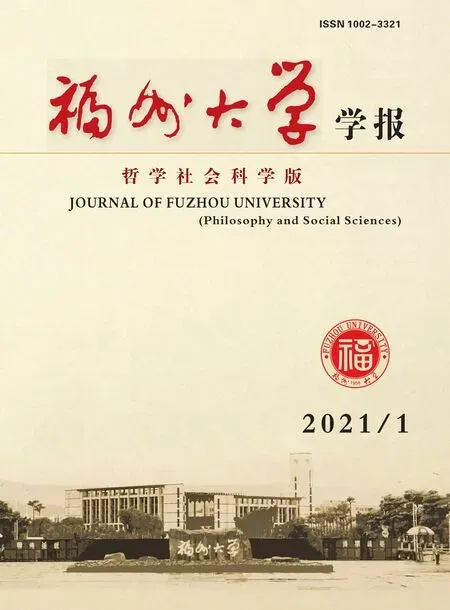“以史注《易》”与“以《易》言史”
——干宝《周易注》的史家本色
2021-12-03程若昕
程若昕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北京 100872)
干宝(280-336)是东晋的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易学家,著有《搜神记》《晋纪》《周易注》等。《周易注》一书多已散佚,清代以来,学者不断辑录,整理出一些文献[1],大致可以反映干宝易学的面貌。从中可知干宝解《易》基本保留了汉代孟京象数解《易》的思路,同时又喜引用历史事件注解卦爻辞,学界谓之“以史注《易》”。本文仅就干宝易学中的“以史注《易》”问题略述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干宝“以史注《易》”的内容及主旨
干宝“以史注《易》”,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引用“文武纣革”及“周公摄政”等材料注解卦爻辞,如其《周易注》中出现殷周史事的注文共有43条,其中涉及殷纣与文、武之事8条,涉及殷纣有3条,涉及文王有7条,涉及武王有4条,涉及禄父有4条,涉及周公与成王有3条,涉及周公有3条,涉及成王有1条。文武与纣之事26条,周公成王之事7条,两件史事共涉及35条(另有几条没有出现具体人物,但隐藏同一含义的注文没有计入其中)。诚如清人张惠言所说:“其言文武纣革、周公摄成王者十有八焉。”[2]此外干宝亦常常结合《序卦》讨论(夏商周)三代损益等问题。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文武纣革”与“应天人”
干宝引“文武纣革”之事注《易》,与其对历史变革、朝代更替的基本认知有关。干宝认为:“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汤武革命,应天人也。”[3]这是说,帝王的兴起,新旧朝代的变革,与天命有关,非人事所能左右。殷周之变,文武纣革,也类于此。其注《坤卦》上六爻言:“文王之忠于殷,仰参二之强以事独夫之纣。盖欲弥缝其阙而匡救其恶。以祈殷命,以济生民也。纣遂长恶不悛,天命殛之。是以至于武王遂有牧野之事,是其义也。”[4]意思是说文王本为殷纣的忠臣,“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5]。他为百姓着想,致力于弥缝殷纣的过失和恶行,祈求天命对殷纣的垂顾。奈何殷纣作恶多端,不思悔改,上天只好诛杀独夫殷纣。武王的牧野之战就是上天对殷纣的诛杀。在干宝看来,文王、武王本无取殷而代之之意,“文武纣革”乃天命使然。
干宝据此进一步讨论了武王伐纣的合理性,其注《师卦》上六“大君有命”曰:“五常为王位,至师之家而变其例者,上为郊也。故易位以见武王亲征,与师人同处于野也……上六为宗庙,武王以文王行,故正开国之辞于宗庙之爻,明己之受命文王之德也。”[6]依《周易》编纂体例,五爻于位为君、为王,但《师卦》却视上六为“大君”,干宝说这是一种“变例”。之所以出现这种变例,干宝认为是因为上六于位为“宗庙”(作者按,此用汉易解经体例),以“宗庙”为“大君”,乃要彰明武王之伐纣乃是“以文王行”,“受命文王之德”。据史载,文王生前虽服侍殷,但因其“阴行善”,已被诸侯视为“受命之君”,是故武王观兵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7]干宝此注正是要表明武王伐纣乃是承续文王所受之命的壮举。
干宝又进一步将武王伐纣的合理性与天命联系在一起,其注《革卦·彖传》“‘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言:“天命已至之日也。‘乃孚’大信著也。武王陈兵孟津之上,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国,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未可也。’还归。二年,纣杀比干,囚箕子。周乃伐之。所谓‘巳日乃孚’,革而信之。”[8]八百国诸侯都说“纣可伐矣”,但武王深知天命未至,“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9]可见在干宝看来,武王的伐纣与否,要根据对天命的认知而为。干宝说,《革卦》“巳日乃孚”的“巳日”就是“天命已至之日”,天命已至,自当革命以获信于天下。这也正是干宝《晋纪》所谓的“应天人”。干宝以“文武纣革”的历史注《易》的主旨就是为了彰显“革命”与“应天人”之间的关系。
(二)“周公摄政”与权变归正
史载武王克商后不久就病逝了,“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10],周公摄政,受到人们的怀疑,如“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11]。干宝引“周公摄政”之事注《易》,是要对“周公摄政”的合理性做出解释。
干宝注《蒙卦》初六《小象传》曰:“此成王始觉周公至诚之象也。……既感金滕之文,追恨昭德之晚。”[12]据《尚书·金滕》,武王病重之时,周公曾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13]即祈求代武王而死。武王病逝后,周公又基于对先王的使命[14],忍辱负重,平定天下。直到有一天,“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15],“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16]干宝所谓的“成王始觉周公至诚之象……既感金滕之文,追恨昭德之晚”,即指此而言。在干宝看来,周公摄政实为不得已,乃是出于忠诚与光大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事业。
干宝注《坤卦》用六言:“周公始于‘负扆南面’,以光王道;卒于‘复子明辟’,以忠臣节。”[17]“负扆南面”,见《礼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18],“斧依”简称“扆”,也写作“依”,《礼记·曲礼下》:“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 孔颖达疏:“‘天子当依而立者’,依,状如屏风,以绛为质,高八尺,东西当户牖之间,绣为斧文也,亦曰斧依……设依于庙堂户牖之间。天子见诸侯,则依而立,负之而南面,以对诸侯也。”陆德明释文:“依,本又作‘扆’。”[19]此喻临朝听政。“复子明辟”见《尚书·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20]《孔传》:“周公尽礼致敬,言我复还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归政而退老。”[21]干宝此注的意思是说,周公在成王年幼时代行天子之职临朝听正,是为了光大王道;等成王长大后还政让位,是恪尽人臣之节。干宝称之为“唯有推变,终归于正”[22]。李道平疏曰:“‘唯’当作‘虽’,‘推’当作‘权’。”[23]也就是说,“虽有权变,终归于正”。
干宝认为“权变”乃不得已之法,所谓“守柔顺,则逆天人之应;通权道,则违经常之教。故圣人不得已而为之。”[24]在《杂卦传》注中,干宝又借用“时”范畴对于周公的权变做了进一步的申论,其曰:“伏羲黄帝皆系世象贤,欲使天下世有常君也。而尧舜禅代,非黄农之化,朱均顽也。汤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纣之不君也。伊尹废立,非徒顺之节,使太甲思愆也。周公摄政,非汤武之典,成王幼也。凡此皆圣贤所遭遇异时者也。”[25]干宝认为,《易》所谓“穷变通久”,古来之圣王“莫不以是法乎易道”[26],所以有尧舜的禅代,汤武的逆取,伊尹的废立。至于周公摄政,并不是要违背汤武政治,乃是因为遭遇异时,不得不变。可见,干宝以“周公摄政”的史实注《易》,其宗旨乃在于申明社会政治中因时权变与归正复常(“汤武之典”)的关系。
(三)“三教一体”与“圣人治世”
干宝以殷周史事注《易》,与其对于理想社会的憧憬有关。其注《序卦传》言:“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教文。文弊薄,故《春秋》阅诸三代而损益之。”[27]此段见《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民之敝,惷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28]“远之”,孙希旦谓“不以鬼神之道示人”[29];“忠”,郑玄注“以忠恕养于民”[30]。这是说,夏虽事鬼神,但不以此设教,“而专以人道为教”。“敝,谓其后世政教之失也”[31],夏政重人情质朴,相应的便会忽略文饰知识的教导(此之谓“野”),此中之失,至夏政之末,显现殆尽。夫子又言殷政:“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32]殷在夏之后,观夏政失之于野,而“救野莫如敬”,故殷政尚敬。“尊神则尚敬”[33],尊神则“以为事不在实”[34],故心无所定也(此之谓“鬼”)。夫子又言周政:“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35]“救鬼莫若文”,故周人尚文。“尊礼尚施则文胜”,周政以礼设教,但后世多失于虚礼之繁琐,而至礼之实意衰。《表记》对三代政教之优弊进行评判,但并未表明其相承受之意,而后世注文多有此意。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已表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矣。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矣。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矣。”[36]孔子认为变之有常,故百世可知。马融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37]这里的文质三统,早在《礼记·表记》已见端倪:“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38]这里还仅停留在评判社会性质的层面,至董仲舒《三代改质文》[39]才臻成熟,其文直言社会历史的反复更迭就是“质”与“文”的交替,“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后继起之朝代,都相应的对前朝之弊进行补救”[40]。东汉《白虎通》则在此基础上又上升一个层次,将忠、敬、文统合:“三教一体而分,不可单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后。何以言三教并施,不可单行也?以忠、敬、文无可去者也。”[41]意思是,忠、敬、文三教缺一不可,干宝在《周易注》中引《论语》[42],“颜回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43],正是将三代所尚结合,构建了一个理想政治社会,李道平曰:“孔子合三代之法,而损益酌中。”[44]
干宝继而言:“弟子问政者数矣,而夫子不与言古代损益,以非其任也。回则备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45]意思是说,向孔子问政的人很多,但孔子唯独向颜回教授千古之法,是以颜回有王佐之才。干宝又言:“是以圣人之于天下也。同不是,异不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一以贯之矣。”[46]也就是说,只有圣人可以在纷繁错杂的社会政治中,理出一条适应当下的道路(政教)。如此而来,三教一体的理想政治的决定权便落在了“有能力的人”身上,《白虎通》谓之“王者”,干宝谓之“圣人”。至此,干宝构建了一个以为圣人中心的理想政治社会,圣人掌握治理社会的千古之法(三教一体),又不据于常道,唯变所适。
在此有必要对干宝注文中的“圣人”概念作进一步分析。上文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一以贯之矣”,可以想见,不受纷扰,能一以贯之的便是圣人。干宝《晋纪总论》言:“爰及上代,虽文质异时,功业不同,即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47]“安民立政者”就是掌握那个一以贯之之理的人(文质交替,三教一体),由此推测,有能力安民立政的人便是圣人。基于此,干宝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即圣人必须在位。干宝注《乾卦·文言传》曰:“言‘君子’,通之于贤也。凡勉疆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48]又注《革卦》上六《小象传》曰:“君子、大贤,次圣之人。谓若太公周召之徒也。”君子、大贤次圣人一等,不必须在位。可以想见,圣人必须在位。[49]“圣人治世,威德和济”[50],圣人在位才能对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
由此可见,干宝以殷周史实注《易》,背后承载的是从孔子“三代损益”而来的“三教一体”思想。又借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以圣人之能力,须得大位才能对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
二、干宝“以史注《易》”的原因与目的
“以史注《易》”在先秦早已有之,《易传》中已有端倪,至干宝《周易注》蔚为大观,渐有形成体系的趋势。干宝何以喜用殷末周初等史事著《周易注》?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前辈多有探讨,如有学者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分析了干宝“以史注《易》”的原因,认为干宝受《系辞》“《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世邪?”的影响;受《周易》中涉及或暗含的史事影响;受《毛诗大小序》体例的影响;受史官身份的影响,对史事较为敏感[51],等等。以上几点,前两点是易学常识,第三点则属于推论[52],最后一点由干宝的史官面貌绎出,合情合理。但揆诸两晋动荡的史实和干宝所遭遇的现实政治环境,其“以史注《易》”当有更切实的原因和目的。
(一)用史实对治玄谈之空疏
干宝是一位史学家,但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书写者,也是一个官家史臣,更是一个传统儒学的捍卫者。大凡出现一种“新鲜”且频繁的用例,总是要有其时代背景与个人意识的支撑,所以,考察干宝的“以史注《易》”,需从干宝所处之时代说起。彼时,正当西晋灭亡,东晋建立之初,“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53]西晋的灾难在干宝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空谈而导致的。而其《周易注》多落实于人事层面,少谈天道,亦不拘泥于象数,转而辅之以大量史事。或许可以推论,干宝《周易注》中以务实的态度进行注解,是企图对治因玄谈空疏而误国的态势。
干宝注《序卦传》“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言:“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圣人弗之论也。故其所法象,秘自天地而还……而今后世浮华之学,疆支离道义之门,求入虚诞之域,以伤政害民,岂非‘谗说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乎!”[54]“‘正’,当作‘止’……止取始于天地”[55],干宝认为先天地而生的便是“道”,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56],这段注文分明是在说圣人作《周易》之目的并不是为玄谈提供资本,“惧其沦于玄虚也”[57]。
干宝在注文中多次宣明礼法坏乱对于整个时局的危害性,如其反注《乾卦·文言传》“君子四德”曰:“逾乱则败礼,其教淫;逆则拂时,其功否;错则妨用,其事废;忘则失正,其官败。”[58]干宝在此批判礼教破败的社会,认为这样的社会秩序混乱、阻塞功业、事物荒废,终至政权覆败。又注:“四德者,文王所由兴;四愆者,商纣所由亡。”干宝注文中极力推崇文王,此处又以四德联系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逾乱四德联系商纣之亡国,明显是在提倡儒家礼教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已经到了影响王朝兴亡的程度,礼教昌行则天下治,礼教败坏则天下亡。再结合其认为礼法刑政大坏的根由就是玄谈,干宝多引文王、周公之事,并树立文、武、周公之形象,便是企图用传统儒家礼教整治因玄谈大行其道致使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的时局。其引史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警醒世人,摒弃玄谈,回归儒家礼教。
(二)用史实证晋元帝继位之合理性
作为一个史官,干宝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回答东晋建立之初,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两晋之际,政治动荡,学风混乱,门阀大族掌控政治,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显然是皇权合法性的问题。东晋建立者晋元帝的帝位并不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而来,而是其名义上的侄子晋愍帝被捕后让位而来的(晋元帝为晋武帝之从子)。晋愍帝亡后,元帝言:“孤以不德,当厄运之极,臣节未立,匡救未举,夙夜所以忘寝食也。”[59]说明晋愍帝令晋元帝掌国之时是衰乱之世,晋元帝本为人臣却不能尽人臣之责,又登帝位,昼夜难安,故在登帝之后下诏群臣共谋复兴。由此推断,晋元帝之时的文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为元帝登基寻找合理性,或者说,是从历史事件中为晋元帝以臣代君寻求法理来源。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干宝运用“以史注《易》”之方法阐释卦爻辞,反复渲染周公摄政时期的混乱局面,如其注《未济卦》六三爻云:“以六居三,尤周公以臣而君,故流言作矣。”[60]此注文中周公因代行君主之事而受到流言讥谤。而晋元帝登第之时说自己“臣节未立”,也是担心自己政权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干宝在这时以“忠臣节”“至诚”“摄政”等来塑造周公至诚的形象,又论述周公主观不愿行君王之事,是迫于“权变”才不得已摄政,虽然有违伦常,却是天命所降,其行事具有合法性。而晋元帝与周公的处境恰好一致,周公代君(未称王)正可以作为晋元帝代君的法理来源。晋元帝行天子之事虽然有违经常之教,然其与周公一致,是为了光大祖宗之业,为了天下百姓,不得已而代君。
这样一来,晋元帝以臣代君行天子之事就找到了历史依据。表面上干宝注文是在讲周公摄成王的合理性,实际上却是以树立周公“常君”形象论证晋元帝代君的合理性问题。至诚的周公受天命摄政,因此,拥有美德的晋元帝也是被天命选中而登帝位的。关于晋元帝以臣代君的结果,干宝也在其《周易注》中借周公摄成王事件表达出来,注《未济卦》六五爻云:“以六居五,周公摄政之象也,故曰‘贞吉无悔’。制礼作乐,复子明辟,天下乃明其道,乃信其诚。”[61]将注文带入时政当中,晋元帝当政虽然有不明其理的指责,却依然能倾尽一切助晋完成中兴,天下人都会明白的。所以,干宝引“周公摄成王”之事注《易》是为了彰显晋元帝当政的合理性,其德美而志不在位,虽因时权变,终归于正。
(三)用史实证晋代魏之合理性
不仅如此,魏晋之间令人诟病的“禅让”,干宝都运用相同的手法予以化解,其以周代殷喻晋代魏,以文武纣革喻司马氏革曹魏政权。干宝在《序卦》注文中言:“而尧舜禅代,非黄农之化,朱均顽也;汤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纣之不君也;……周公摄政,非汤武之典,成王年幼也:凡此皆圣贤所遭遇异时者也。”[62]不仅给予晋元帝以臣代君的依据,并给予了以晋代魏的朝代正统性。
《晋武帝革命论》中称:“帝王之兴,必俟天命……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汤武革命,应天人也……各因其运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63]区别禅让制度,建立外禅制度,又以《随卦》“随时而变”释“变革”。目的是以汉魏外禅和汤武革命为理论来源,将西晋的建立与天命联系在一起,表明西晋的建立是既“顺大名”又“应天人”的。
为了解决因为朝代更替而产生的政治上的嫌隙,干宝在《周易注》中多次引用“文武纣革”,借此比拟魏晋两家的变革,如注《革卦·彖传》,仅用武王伐纣之事比拟革事,并没有像其他易家的注文扩大至所有历史变革[64],因为武王伐纣之事在干宝思想中是顺天应人的变革之事,借助《周易》将此事塑造成了一个历史上典型的绝对具有合理性的变革之事。又因为司马氏政权代替曹魏政权与周王朝取代殷王朝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司马氏原为曹魏之臣,而后曹魏“无德”,司马氏“顺天命”取而代之,与殷周变革有着同样的性质,如果周武王取代殷纣是合理的(应天人),则晋武帝取代曹奂也同样可以寻得合理性。由此看,干宝引“文武纣革”注《易》目的是从“应天人”的角度论述曹奂禅让给魏武帝的合理性。
干宝又从三代损益的角度加以论证,其注《井卦》卦辞曰:“改殷纣比屋之乱俗,而不易成汤昭假之法度也……二代之制,各因时宜,损益虽异,括囊则同。”[65]注初六爻言:“此托纣之秽政,不可养民也。”[66]这是说,成汤立国之时“尚敬”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而至殷纣之时,时代变化,仅仅“尚敬”已经不够了,此时周之“尚文”恰好能够解决殷纣之弊政,故周取代商是顺应时代的变化。以此可见,干宝在注文中多次引入周取代殷的史实,是想从“三代损益”的角度论述晋取代魏的合理性,论述魏晋外禅也是顺应时代的变化。
由于干宝亦处于历史之中,如果社会变革是历史运行当中无法避免的法则,则晋终有一天会被其他朝代以符合历史运转的方式取代。为了规避这一问题,干宝在注文中构建了一个“三教一体”的理想社会。不论其目的是企图以晋的制度贴合理想社会,抑或是向统治者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这都不失为是一种解决历史变革的好办法。至少在作为史官的干宝看来,这既为当政者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朝代正统性问题,又解决了朝代会被他人颠覆的问题。
三、余论:“以史注《易》”与“以《易》言史”
干宝在两晋之际受到重用,其《周易注》中所体现出的思想亦是为了解决现实政治存在的问题。干宝以文武纣革类推司马氏革曹魏政权,以周公摄成王政比拟晋元帝代晋愍帝王权,再论述周公合理地位与论述武王代商的合法性,即顺天应人,从而确立晋朝与晋元帝的合法地位。并且,由于干宝“始领国史”的地位,其《周易注》中的一系列推论在晋朝政权中心也具有相当重的分量,尤其是在改朝换频繁、思想动荡的两晋之际,干宝非常自觉地维护当权者的合法性,以儒者心中蔚为神圣的文王、周公作为类推的源头,转变风气,统一思想,为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思想保障。
虽然干宝注《易》是源自为论证晋朝与晋元帝的政权合法性,但不能否认其对于易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大量“以史注《易》”的运用为后世注《易》提供了较为新颖的思路。干宝在注《周易》的同时又把《周易》作为历史根据,部分材料虽然也是在谈史谈《易》,但似乎已超出“以史注《易》”的范畴,而毋宁谓之是“以《易》言史”。“以《易》言史”并不仅仅为了印证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也并没有将《周易》当作一部史书看待,而是为了更好的支撑《周易》最原始的哲学思想“以德配天”。如果说“以史注《易》”发明了《周易》的思想,可以称之为“法理”,那么“以《易》言史”所塑造的历史则可以称之为“来源”,二者相互成全,体现了《易》与史互相对待的特点。最终目的则是为了现实政治社会,解决现实社会最急迫的问题。
《周易》每一卦探讨的都是人在宇宙中如何积极地寻求自己合理位置并因此获得存在的合理性的问题,这正是干宝《周易注》所践行的思想进路,因其留思象数而更能在注文中体现天道的化育流行,因其对于《周易》中所体现的天文历法有一套明确的体系,故而其在思考过程中更能游刃有余地切换于天道人道之间,体现人在宇宙中存在主观能动性,并能因此印证天道的合理性。
要之,干宝注《易》佚文较多,无法做更加进一步的分析,但其对于象数的传承,对于义理的发挥,对于史事的多方运用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注释:
[1] 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述,干宝《周易注》辑佚工作可追溯至元朝,但今天能见到,并且较为可据的多始于清朝。如清人张惠言所录《易义别录》、孙堂辑《汉魏二十一家易注》,今人简博贤所辑《魏晋四家易研究》、黄庆萱所辑《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徐芹庭所辑《魏晋南北朝四十三家易学》等。
[2] 林忠军教授也曾指出:“晋干宝以史学见长,并以丰富和详细的史料来揭证《周易》所蕴含的大义。尤其能以殷周变革之史参注释卦交辞。”(林忠军:《干宝易学研究》,《周易研究》1996年第4期)
[3][63] [晋]干 宝:《晋纪论晋武帝革命》,《昭明文选》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74,2174页。
[4][6][8][12][17][22][23][24][25][26][27][43][44][45][46][48][50][54][55][57][58][60][61][62][65][66]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潘语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84,136,437,109,85,85,86,32,736,737,736,736,737,736,736,38,34,719,719,719,44,538,539,736,429,431页。
[5][36][37] [42]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13,71,71,621页。
[7][9][10]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0,121,131页。
[11][13][15][16][20]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抗、盛冬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0,326,336,337,402页。
[14]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尚书今古文注疏》,第326页)。
[18][19][28][29][31][32][33][35][38]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39,138,1309,1309,1310,1310,1310,1310,1311页。
[21] [清]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何 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21页。
[30][34]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33,1734页。
[39] [汉]董仲舒:《三代改制文》,《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3-213页。
[40] 章伟文:《易学历史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41] [清]陈 立:《右论圣王设三教之意》,《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70页。
[47][53] [晋]干 宝:《晋纪总论》,《昭明文选》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85,2186-2188页。
[49] 这其中还涉及,在干宝思想中,孔子为圣人或为大贤的问题。如果,孔子为圣人,则圣人的判定标准不在位上;反之,则圣人的判定标准包括得位。但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暂按下不表。
[51] “一曰受《系辞传》‘《易》之兴也当文王与封之事’一语之影响。”“二曰受《周易》卦交辞中多殷周故事之一影响。”“三曰《毛诗大小序》以史解《诗》之影响。”(黄庆萱:《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91页)“干氏对史学有着精湛的研究,……受其影响,往往站在史学角度来思考和探讨一些学术问题,其易学研究亦不例外,他在注释《周易》时,或是以历史知识印证之,或是用史学理论或方法阐发之,从而使以史注易成为干氏易学的重要内容。”(林忠军:《干宝易学研究》,《周易研究》1996年第4期,第22页)
[52] “干宝既多引他经以注《易经》,又好以他经比附《易经》,故其注《易》受他经传注之影响,自属可能。尤以受《诗序》影响为最。”(黄庆萱:《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第344-345页)
[56]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3页。
[59] [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9页。
[64] “干宝此卦实记史事,又舍汤而专言武王,殆违彖旨。郑玄注……是不专指汤武。王弼……亦不限以汤武。”(黄庆萱:《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