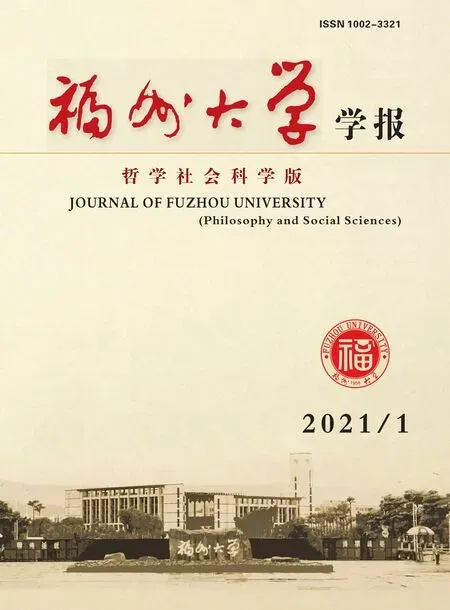敌意收购中的自律监管:英国经验与中国实践
2021-12-03唐林垚
唐林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敌意收购既可能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也可能转变为对公司财富的掠夺。敌意收购规制应该以减少市场不确定性为导向,鼓励良性收购产生,并减少公司内部代理成本。[1]为此,世界上多数国家采取了证监会和法院双重干预的规制模式——证监会对要约收购的程序和信息披露进行实质审查、法院对收购双方的纠纷进行调停,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和日本等国概莫能外。英国却另辟蹊径,建立了以并购委员会为主导、《英国城市收购及合并守则》为核心的自律监管体系,在效率和成本上反而超越其他国家。
英国敌意收购自律监管的形成经历了特殊的历史背景、政治博弈以及制度演化,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英国并购委员会在解决敌意收购纠纷时坚守私法自治的范式抉择。本文从英国敌意收购规制的演进历史和商事立法的传统偏好两个维度出发,深度解构英国自律监管模式的形成原因以及存续基础,藉此反思我国敌意收购中“以证监会为主、以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自律监管为辅”二元监管体制下的有限自律监管体系。
一、英国敌意收购规制的演进历史
英国第一波敌意收购受二战后经济动荡带来资产套利非凡机遇的驱动——汹涌澎湃的通货膨胀使固定资产价格飙升,尤其是土地。[2]1948年之前,英国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很难搜集,投资者将分红看作是董事会对投资者负责的稳定信号,投资者也习惯通过分红来判断股票价值。政府强制的股利限制导致公司囤积现金;所以,当公司资产的价值提升时,股利限制反而导致公司股票价格下跌。这种情况在1948年英国公司法修改后得以改变。随着公共公司的强制信息披露义务得以加强,公司的现金储备比以往更加透明,精明而敏感的投机家们逐渐嗅出公共公司的真正价值。
(一)影响立法选择的三场敌意收购
在上述大背景下,1953年出现了英国史上的第一场敌意收购。从俄罗斯移民到英国的商人查尔斯·克罗尔发现,由于通货膨胀,希尔鞋业零售公司在市中心房屋及土地的投资证券组合在公司账目中被严重低估。由于投资者是根据分红来计算股票价值的,而资产价值并不反映为公司实际的现金流,希尔鞋业的实际价值在市场上被严重低估。克罗尔立刻向希尔鞋业的股东以高于市场价格发出收购要约,这让希尔鞋业的董事会大惊失色。董事会立刻承诺将提高每年股份分红,好让公司股票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公司价值。不过,董事会的承诺来得太迟,公司的中小股东们纷纷接受克罗尔的收购要约,克罗尔很快取得希尔鞋业公司控制权。[3]
同样是在1953年,英国并购金融家哈罗德·塞穆尔发起对萨沃伊酒店公司的敌意收购。由于不动产价格飙升,塞穆尔准备在收购成功后将萨沃伊酒店公司旗下的伯克利酒店变成商务写字楼,以谋求更多收益。塞穆尔对伯克利酒店的虎视眈眈,引起了萨沃伊酒店公司董事会的警惕。董事会主动采取防御手段,他们首先将伯克利酒店出售给一个新的商业实体——伍斯特有限公司;该公司随后通过协议,将伯克利酒店出租给萨沃伊酒店公司,条件是伯克利酒店的资产不能被用作酒店以外的其他用途。伍斯特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萨沃伊酒店公司退休基金的托管人,此人“恰好”也是萨沃伊酒店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简言之,萨沃伊酒店公司董事会自导自演了一出“锁定策略”,目的就是要打消塞穆尔的敌意收购企图。虽然,彼时敌意收购在英国依旧是一种不体面地获得公司控制权的方式,但萨沃伊酒店公司董事会过于露骨的自保行为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他们没有给予股东会在收购中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萨沃伊酒店公司的股东们开始集会抗议,促使英国贸易委员会对董事会的防御行为进行调查。调查报告指出,董事会存在越权行为——对收购的防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商业判断规则,但客观上造成了股票持有者无法改变公司董事会决策的事实效果。[4]
1958年的敌意收购纠纷,拉开了收购规制的序幕。英国管道投资公司、美国雷诺兹钢铁公司和美国铝业公司同时向大不列颠铝业公司的董事会表明了各自的收购意图。在没有充分告知股东会的情况下,大不列颠铝业公司直接同美国铝业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将另外两家公司拒之门外,并以发行新股的方式让美国铝业公司获得自己三分之一的股权。直到英国管道投资公司和美国雷诺兹钢铁公司越过董事会直接向股东们发出要约收购,董事会才不得不补充披露同美国铝业公司之间的交易。董事会试图以合作已经完成的既成事实,来排除英国管道投资公司和美国雷诺兹钢铁公司要约收购的权利,董事会越权行事导致了股东群体的不满。面对股东会的质询,大不列颠铝业公司董事会企图通过大幅增加分红的方式来贿赂股东群体,导致公司股价的大幅上扬。不过,这种事后补救的举措却进一步激怒了股东群体,因为美国铝业公司此前已经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大不列颠铝业公司的部分股权。愤怒的股东们纷纷接受了英国管道投资公司和美国雷诺兹钢铁公司的要约,美国铝业公司最终没能获得大不列颠铝业公司的控制权。[5]
(二)“消极董事”的《大不列颠商业合并规则》
从1953年到1958年的三场敌意收购纠纷引起了股东群体广泛要求提高收购监管的呼吁,他们希望能够完全遏制住董事会在面对敌意收购时肆意妄为的自保行径。1959年7月,代表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的英格兰银行秘密组建了一个编撰收购规则的委员会,由商业银行、机构投资者、大型商业机构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代表组成。这些商业机构代表们或多或少感觉到一种紧迫性障鉴于敌意收购活动的日益频繁,如果他们不立刻采取行动让股东群体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议会、立法委员会等公权力必将强势介入,他们也将在自己的商业活动领域失去立法话语权。果不其然,1959年11月,为应对未来敌意收购纠纷,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公开宣布或专门修订英国公司法。
在时间异常紧迫的情况下,英格兰银行的编纂委员会迅速发布了《大不列颠商业合并规则》(下简称《合并规则》),这是英国史上第一个收购领域的行业自治法规,主张“积极股东,消极董事”的行权理念。《合并规则》由原则和程序两部分构成。原则部分共有四条:第一,任何人不应干涉公司证券和股票市场的自由发展;第二,股东享有股票买卖的绝对自由;第三,股东在做决策时应当被给予充裕的时间;第四,股东在做决策时应当享有充分信息。[6]
《合并规则》的颁布,赶在公司法修订之前,得到英国证券发行协会、票据承兑商行协会、英国发行业协会以及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一致支持。1967年7月,麦克米伦首相表达了对《合并规则》的认可,指出在收购领域进行公权力立法或许不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7]即便如此,由于长期缺乏裁决和执行的机制,当《合并规则》的规制效果差强人意、局限性凸显时,政府内部又逐渐出现了建立英国证监会的呼吁,他们认为具有绝对权威的公共机构比证券行业内部的自律监管更能够实现资本市场的繁荣与稳定。[8]
(三)《英国城市收购及合并守则》和并购委员会
在多方压力下,英格兰银行成立了新的规则编纂委员会,他们首先就《合并规则》的各项缺陷进行探讨和反思。1968年3月,《英国城市收购及合并守则》(下简称《城市守则》)面世。《城市守则》是对《合并规则》的扬弃和突破,其核心原则是董事会中立规则:没有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严令禁止采取任何可能会抑制收购的行为——包括发行新股、分割转移重大资产等等。[9]股东平等对待和平等保护的理念也在守则中多有体现。最重要的是,为了避免重蹈《合并规则》缺乏裁决和执行机制之覆辙,英格兰银行联合各证券行业协会,建立了专门负责执行《城市守则》的并购委员会。委员会最初有9个委员,由代表银行、大型公司、商业组织、基金公司等团体的商界精英组成。委员们宣誓要将自律监管的传统发扬光大;他们一致认为,在收购领域,事前介入比事后的裁决更行之有效。[10]
《城市守则》的颁布备受瞩目,但并购委员会在一开始的表现却差强人意。洪水般涌来的案件压垮了这个完全由非职业执行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光是1968年一年就有575场收购纠纷,这让只有9名委员组成的并购委员会显得势单力薄。敌意收购人屡屡试探《城市守则》的底线,试图以各种出其不意的方式挑战并购委员会的权威。1968年11月,麦克米伦首相宣称,如果并购委员会不能迅速改革、提高效率的话,政府仍将被迫通过立法解决问题。[11]
作为对立法干预主义的回应,并购委员会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自我改良。首先,并购委员会大量增加了全职工作人员,并聘请业界权威执掌委员会,英国贸易委员会前主席肖克罗斯勋爵受邀成为并购委员会的非执行主席,瓦尔堡公司的并购权威伊恩·弗雷泽被聘为执行副主席。随后,并购委员会的工作程序,比照正当诉讼程序进行改良和完善。例如,不服并购委员会的判决,收购人可以选择“上诉”;并购委员会建立了一个新的“上诉委员会”,由英国上议院的高级法官皮尔斯勋爵担任第一任主席。紧接着,在各证券行业协会的拥护下,并购委员会能够采取的制裁和处罚措施得到空前加强。伦敦证券交易所和英国贸易委员会公开表示,将无条件配合并购委员会对违规上市公司做出行政处罚,甚至吊销或者除名不守规矩的上市公司;英国股票交易委员会、英国证券发行协会、英国保险协会、英国信托经理协会以及英国投资公司协会等也纷纷为并购委员会背书。[12]
主动自我改良与行业协会的全方位加持,让并购委员会的地位日益稳固。虽然1970年代英国工党政府左倾趋势严重,立法干预主义随时可能复活,但是并购委员会已经进入不断自我完善的良性循环,其自律监管的理念也逐渐得到英国政界和商界的广泛认可,并一直延续至今。
二、自律监管模式的形成原因
英国收购领域自律监管模式的形成,是一系列政府主导的公共政策和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商业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机构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壮大机构投资者的宏观调控政策
英国机构投资者的野蛮成长,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填补国库亏空,英国政府施行了个人投资所得的惩罚性高边际税率政策,对个人投资所得征收高达90%的边际税率,在1974年至1979年间甚至一度上升到98%,几乎完全摧毁了个人投资的热情。1979年,撒切尔政府同时颁布了税收减免和共同投资计划两项政策。[13]个人投资所得边际税率逐年降低,1979年底降到60%,1988年降到40%。虽然如此,个人投资所获盈余依然远远比不上参与共同投资所获分红。得益于共同投资计划政策,机构投资者缴纳的所得税长期远低于个人投资应缴纳的所得税。例如,保险公司投资分红的税率,是个人税率的一半。[14]更极端的是,为了促进私人养老基金的增长,英国政府对养老基金投资分红给予免税待遇,该政策直到1997年7月才被废除。这些连续的税收政策共同造就了个人投资行为的长期低迷,以及共同投资行为的与日俱增。[15]
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单位信托等机构投资者在英国上市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从1960年末到1980年稳步增长——1969年约35%,1975年约50%,1981年约60%,1987年超过70%。[16]英国的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运营和发展是出了名的被动和冷漠,他们从不干涉公司事务,公司运营状况不佳,他们就“用脚投票”——抛售股票。为了提升英国公司治理水平,英国政府希望能够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鼓励甚至强迫机构投资者在其投资的公司事务上给予更多关注,但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这些本来就只持有公司少数股权的机构投资者相互推诿,谁也不去充当出头鸟。绝大多数机构投资者持有高度分散的股票组合,在一个特定公司中的股票份额非常低,导致他们协同成本巨大。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股东才会联合起来推翻现有董事会,而这种情况在英国实属罕见。[17]
(二)偏向于机构投资者利益的规则
英国机构投资者对英国公司治理的影响,不通过参与公司事务实现,而通过影响立法,直接改变监督公司运作的标准和范式。机构投资者偏向于能够保持他们对公司运营最低参与度和最低参与成本的公司治理制度,说白了,最好是能够让他们一劳永逸被动到底但又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例如,保障优先认股权、遏制非投票权股份、禁止反收购防御、要求公司重大事项必须经股东会批准,对董事会结构、薪酬和任期的诸多规定和限制等等。英国的机构投资者不愿过多干涉公司运营,却在游说立法者加强股东会权力方面显得特别主动。
诚然,游说过程中的搭便车现象也不可避免。但是,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游说法律改革比频频参与公司治理更省事。首先,机构投资者持有高度分散的股票组合,一般同时持有多个公司股票,无力介入每个公司的日常事务。第二,如果不能有效制衡公司董事会,当公司治理状况不佳时,机构投资者只能选择退出。频繁退出、进入(新公司)本身会带来高昂的成本和不稳定性。因此,“用脚投票”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虽然是理性的自保策略,但并非长治久安之举;只有一劳永逸地改变法律和规则,才是长期稳定机构投资者信心、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佳解决方案,即便在这个过程中有搭便车现象的产生。[18]
这就不难理解,当目标公司董事会越权行使职权以求在敌意收购中自保时,为什么代表机构投资者的英格兰银行以及各行业协会会立刻紧密联合在一起,为了贯彻公司收购中“股东会中心主义”的行权偏好而共同使力。《合并规则》也好、《城市守则》也罢,它们归根结底是由机构投资者书写的规则,也是为机构投资者书写的规则。
(三)自律监管偏好的历史传统
由机构投资者主导的收购规则,其自律监管基因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彼时英国早期的资本家、金融家、政治家们都住在“一英里见方”的围城——伦敦市区之中。地缘上的相近性和封闭性使得这些掌握财富和权力的人,在来回重复的交易和商业实践中,能够很方便地形成约束彼此的原则和约定,这些习惯法是此后自律监管规则的重要法源。由于商事交易便捷性的要求,市场参与者都偏好成本低、效率高的治理模式,因此名誉惩罚——例如从市场除名,几乎完全取代了昂贵和程序复杂的诉讼。由此可见,自律监管的偏好和选择在一开始就存在。比起上市公司董事会而言,机构投资者所坚持的“股东会中心主义”的立法偏好,更容易被立法者吸收。这就是为什么,当萨沃伊酒店公司董事会剥夺了股东会表达意愿的权利而擅自采取防御手段以求自保时,机构投资者股东可以很轻易地煽动英国贸易委员会对董事会的越权行为进行调查和惩戒;当大不列颠铝业公司撇开股东会擅自同美国铝业公司达成交易时,机构投资者股东可以乘机占据道德优势将“董事会中立原则”在《合并规则》中具象化。当大不列颠铝业公司董事会的行为引发众怒后,英国投资公司协会发表声明:“在没有股东会授权的情况下,任何董事会可能对公司控制权或者商业实质造成改变的行为,都是不法的。”[19]英国保险协会随即对声明表示声援。
历史上,上市公司董事会也逐渐形成了代表自身利益的团体和组织,例如,英国董事协会、英国商会协会和英国工商业联合会。然而,由于成立时间较晚,缺乏同英国政界、商界高层的紧密联系和关系纽带,它们从来没有强大到可以同代表机构投资者利益团体和组织分庭抗礼的地步;1959年制定《合并规则》时,英格兰银行直接忽略了代表公司董事会利益的协会。1968年制定《城市守则》时,英格兰银行象征性地邀请英国工商业联合会列席编纂委员会,但《合并规则》所确立的“积极股东,消极董事”的精神已在9年的时间内深入人心,成为不可撼动的共识,英国公共舆论对敌意收购的“敌意”也烟消云散。机构投资者及其背后的组织和团体,既是收购自律监管规则的缔造者,也是自律监管规则的最终受益人。
总之,战后的税收政策促进了共同投资对个人投资的倾轧,机构投资者政治影响力巨大且对董事会越权行为零容忍,放大了“股东会中心主义”的立法偏好;私法自治和立法干预的不断赛跑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自律监管和政府监管在唯效果论的往来博弈中适者生存。
三、英国自律监管的实践效果及其启示
自下而上构建的英国路径具有明显“股东会中心主义”的特征: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流的股东群体对公司事务一向理性冷漠,却在防止董事会越权、游说立法、维护自律监管等方面绞尽脑汁,他们所塑造的自律监管规则彻底勒住了董事会在敌意收购中不择手段寻求自保的缰绳。由行业精英自发组建的并购委员会成为英国收购领域中最重要的监管权威,并不是自然而然、按部就班、一帆风顺的,而是在立法干预主义的持续威胁下,被迫一直改善自身、适应市场,片刻不敢怠慢,最终让公法介入毫无必要。同传统敌意收购规制模式相较,英国的自律监管模式在多个方面有着难以超越的制度优越性。
(一)高效率、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模式
英国自律监管模式的优越性首先体现在效率和速度上。《城市守则》对要约收购时间和效率的追求,以及并购委员会的快速介入和实时反应,最大程度减少了收购中围绕目标公司的不确定性。
《城市守则》规定了要约收购必须遵守的清晰时间表,公布收购意向的收购人必须在28天内,正式发出要约收购。如果一个收购人宣布,“正在考虑”对目标公司进行要约收购,那么目标公司可以请求并购委员会要求该收购人立刻明确立场——要么公开宣布其正式收购意向,要么公开否认收购意向。正式要约的预受期间一般不超过60天。在收购人发出正式要约期间,如果出现第二个收购人与之竞标,那么第一个收购人的时间表将被重置以利于其调整要约价格;不过,如果竞标的双方在第二个要约产生46天内依然没有一个确定的最终价格(因为相互竞价),此时将启动拍卖程序,一举确定要约最终价格。要约失败的收购人不能在12个月内对同一个目标公司再次发起要约收购。[20]
《城市守则》的上述规定让英国要约收购能够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当纠纷产生时,并购委员会会及时介入,因此,繁琐的诉讼程序显得完全没有必要。英国上诉法院明确禁止收购中的双方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干扰并购委员会的“实时”决定。1986年,数据金融公共有限公司对并购委员会的裁决不满,向英国上诉法庭提起诉讼。英国上诉法庭面临的难题是,作为一个非政府机构的自律监管主体,英国并购委员会基于私法在商业活动中做出判决;而公法中的判决审查标准用于私法判决的审查是否合适?英国高等法院院长唐纳森爵士最终裁定,英国并购委员会的裁判在收购规制领域至关重要,因此其判决必须要经得起司法审查的考验。不过,为了兼顾商事交易的便捷性需求,英国高等法院赋予并购委员会裁决一审终审的效力,即使其裁决在司法审查中被推翻,也只对今后的裁判产生影响。简言之,该案确立了并购委员会的裁决受司法审查约束、但已经形成的判决不受司法审查结果影响的先例。[21]
在敌意收购领域,并购委员会的“事前介入”完全取代了法院的“事后审判”,这极大地降低了收购双方解决纠纷所需的法律成本。在美国,近半数敌意收购纠纷闹上法庭,纠纷双方都不得不承受漫长的诉讼成本以及高昂的法律服务费用。在英国,纠纷双方不必为并购委员会的调停支付费用。并购委员会的运作资金主要来自对要约收购收取服务费,这也是收购人需要负担的成本。对于超过100万英镑的要约,100万英镑的部分征收0.2%,超过100万英镑的部分征收0.02%;这个费用由伦敦证券交易所代为收取。印刷、销售《城市守则》也给并购委员会带来一定收入。[22]
(二)与时俱进的规则迭代方式
英国自律监管模式的优越性,还体现在并购委员总是能够及时、主动地调整《收购守则》中的各项规则,以应对市场发展和金融创新上。委员们会定期商讨收购案例和行业最新动向,并通过论证和协商决定是否有必要修改《收购守则》。相比之下,由证监会或法院调停收购纠纷,其规则进步往往是被动的、滞后的,只有当问题足够严重时,才会迫使法律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1971年,诺扣斯公司对维尼斯塔国际公司发起要约收购,并得到目标公司董事会的支持。维尼斯塔国际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大卫·罗兰认为要约收购的开价过低,于是开始自己重仓公司股票,以防止公司被出售。罗兰并没有采取要约收购的方式,而是直接在二级市场上大量购入公司股票。最终,罗兰成功成为维尼斯塔国际公司控股股东,而诺扣斯公司的要约收购以失败告终。诺扣斯公司随后向并购委员会投诉,认为罗兰的收购行为违反了1969年《城市守则》第33条要求“收购人及关联方或者受要约方向并购委员会公开任何可能挫败善意要约或影响要约收购结果的交易”的规定。[23]并购委员会在审理后认为,《城市守则》第33条规则并没有被践踏,因为该规则的适用情形是没有向股东群体公布收购意向的善意收购。不过,并购委员会也意识到,罗兰在二级市场囤积股票的行为,没有一视同仁给与所有股东公平价格,鉴于此,并购委员会在1972年新版《城市守则》中立刻增加了一条新规定:“获得上市公司40%以上股份的股东,无论获得股份的速度有多平缓,必须向公司剩余股份发起全面强制要约收购。”[24]这是今天在世界各国证券法中都存在的“全面强制要约收购规则”的前身。
总之,并购委员会以变应变、不断进步的精神与传统,实时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立法体制的产物(例如证监会)望尘莫及的。
(三)自律监管的核心在于相关者利益一致
《城市守则》和并购委员会的自律监管,虽然有着上述显而易见的优点,但自律监管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利益是否相一致。在收购领域,如果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追求效益最大化,那么自律监管可以如鱼得水——尤其是在收购活动频繁的国家和地区,自律监管比立法干预会更好。[25]然而,如果监管者的动机较为分散,那么自律监管可能就起不到相应的作用。
以美国为例。在罗斯福民粹派政府巧借新政之机,将证券行业监管“收归国有”之前,美国证券市场曾经历了上百年的自律监管历史。由《梧桐树协议》发展而来的《纽约证券和交易管理处条例》,奠定了纽约证券交易作为自律监管主体的根基,直到1933年《证券法》颁布,纽约证券交易所创立的多项规则还是美国联邦证券法最重要的法源。然而,由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导的自律监管,并未取得良好的监管效果,这主要是因为监管者同参与者的利益难以协调一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制定者,是数量庞大的经纪人,而经纪人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等同于收购双方的利益最大化,例如,如果一场收购可能会让上市公司不再具有上市身份,经纪人很有可能会倾向于冷藏这笔收购,即使这场收购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26]
诚然,由机构投资者塑造的英国自律监管体系,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实现了监管者同被监管者之间的利益趋同。机构投资者,就像其名称一样,是机构,并非独立的个体。在投资机构的股东和管理人之间,也存在代理成本。当投资机构本身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参与投票时,投资机构的决策由投资机构的代理人做出,而不由投资机构的股东做出。这些代理人在行使投票权时,未必只考虑最大化股东利润。但总的来说,由于面临激烈的同行业竞争,投资机构的代理人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是更关注他们所持股票的公司的整体盈利性。总之,自律监管体系的效率严重依赖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具有高度一致的目标和追求,在收购领域,则是双方都追求收购活动的效益最大化。
四、我国有限自律监管体系的提升与改善
我国证券市场采取以中国证监会集中统一监督管理为主、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自律监管为辅的二元监管体制。然而,在敌意收购纠纷中,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既谈不上“监管”,更谈不上“规制”,所谓的自律监管几乎完全停留在字面上,敌意收购纠纷完全由证监会通过行政干预来平息,导致了证监会一言九鼎、政由己出的路径依赖——“上层意图”比法律实质更能决定博弈双方的胜负输赢。
未来中国敌意收购规制的改革,光靠字面修改法条必然无济于事,当务之急在于从根本上摆脱“证监会一家独大”的规制现状;在敌意收购活动中强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
(一)官民二重性明显的自律监管主体
作为自律监管主体的英国并购委员会,同作为公法主体的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二者彼此独立、各司其职,不存在公法主体对自律监管主体的垂直监管,自律监管主体也不是公法主体的“行政附庸”。
这同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情况正好相反。首先,我国证券交易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独立法人。理论上,我国新、旧《证券法》均赋予了证券交易所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的职能,并明确指出证券交易所是“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同时,《证券法》还认可了证券交易所的财产自主权,其积累的财产和权益在存续期间不得分配,由“全体会员共同享有”。但是,证券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和人事安排却严格遵守证监会颁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以理事会为核心的决策机构,由中国证监会委派的非会员理事人数可以占到理事会的一半。《证券法》还规定,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直接任免。由于证券交易所的实际控制人以及近半数理事均来自证监会,我国证券交易所并未真正实现会员制法人的治理结构,行政化的思维和管控方式依然左右着证券交易所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其次,从历史源头来看,我国的证券交易所从来就不是资本市场参与者自发组建的产物,上海和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均是由政府规划、筹办和设立的。除了掌控证券交易所人事安排和干部任免之命脉,证监会还直接控制证券交易所的经营大权甚至日常管理实务。例如,证券交易所制定和修改章程、制定异常交易行为认定和处理的业务规则、接纳会员、修改业务规则、调整证券交易品种、提供互联网服务等行为,都必须报中国证监会批准。在实践中,证监会更是经常越俎代庖,颁布很多本来应当由证券交易所制定和颁布的业务规则,例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格式和目录、拟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程序和要求等。
我国的证券业协会也不完全独立于证监会。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证券业协会在推进行业自律监管、改善证券环境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证券业协会始终没有能够像英国的并购委员会那样,左右逢源,充当各行业协会之间的“粘合剂”,更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独立的自律监管体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证券行业协会“政府背景”深刻。《证券法》对证券业协会的定性是社会团体法人,因此受《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的约束,作为社会团体,在成立之初必须首先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才能进行注册和登记。中国证券业协会的主管部门为中国证监会,各地证券业协会的主管单位均对应中国证监会的当地派出机构。虽然,中国证券业协会的会长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并不由证监会直接委派,但在实践中,中国证券协会的多数会长都在证监会同时兼有职务。而且,理事会中,有近半数非会员理事,由证监会直接委派。最终,中国证券业协会实际上沦为中国证监会“特定非原则性目标”的达成者。例如,证监会制定主承销商的信誉评分规则,由中国证业券协会进行推进和落实;证监会制定证券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办法,由中国证券业协会代为组织考试并颁发资格证。总之,证券业协会过于重视《证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职权与功能,却忽视了其成员单位的积极利益。英国经验表明,如果证券业协会不能与其会员保持利益高度一致,自律监管很难起到相应的作用。
(二)监督和惩处实权阙如的自律监管实践
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自律监管的上述缺陷,或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内部分工日益细化、证监会简政放权而得以逐渐克服;然而,我国自律监管体系未能在敌意收购规制中发挥任何效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监督和惩处实权的阙如。回顾英国敌意收购的演进历史,并购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在同立法干预主义的赛跑中取得最终胜利,成为英国收购领域中最重要的监管权威,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各行业协会对并购委员会的鼎力支持。即便并购委员会不具备公权力主体的强制执行力,它仍然可以协同行业协会有效威慑和惩戒收购活动中的违规者;那些不遵守《城市守则》的公司和机构将发现他们在英国证券市场中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状态。
反观我国证券交易所,除暂停或终止证券交易、撤销上市资格等过于极端的处罚方式,证券交易所尚不具备其他有效、合理的行政处罚权力。《证券法》赋予证券交易所对违反交易所有关交易规则的人员给予纪律处分的权利,却没有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能采取哪些处罚措施。导致的结果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其《股票上市规则》中,只能对违反交易规则的上市公司进行以下处罚:(1)通报批评;(2)公开谴责;(3)公开认定不应当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4)建议公司更换董事会秘书。除了难以对违规者进行实质有效的处罚,证券交易所甚至连违法行为的调查权都不具备。《证券法》允许证券交易所实时监控证券交易行为,要求证券交易所按照一定的规范对异常交易情况提出报告。然而,身处一线的证券交易所除了向千里之外的证监会提出报告外,无权直接调查并惩处上市公司的异常交易行为,故而根本无法对瞬息万变的证券市场进行有效监管。
证券行业协会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惩处机制。虽然“自律监管”的职能在中国证券协会的章程中被放在首位,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只赋予中国证券业协会“调解会员与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的证券业务纠纷”以及“监督、检查会员行为,纪律处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协会章程的行为”两项非常宽泛但不具体的权力。因此,在实践中,中国证券业协会逐步沦为一个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忙疏导会员关系的协调机构、证券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中心以及直接向证监会报告和提供新闻的信息中介。
(三)自律监管体系的提升与改善
上文指出,英国敌意收购监管采取了堪称完全的自律监管体系,而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制度奠定了政府主导、自律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因此,我国自律监管体系的提升与改善,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实现有限自律监管体系对敌意收购中证监会集中统一监督管理范式的辅助和增益,而非在范式上的超越和颠覆。就此而论,扫清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自律监管所面临的制度障碍、赋予二者在证券活动中监督和惩处实权,最终应当是下一轮收购法律改革的重心。
具体而言,我国证券交易所实行自律监管应从以下几方面落实。(1)应在法律上明确证券交易所会员制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并在实践中改变证券交易所国有事业单位的性质,减少证监会对证券交易所的垂直控制,将治理结构设计和人事安排任免等实质权利回归证券交易所理事会,大幅度减少证监会委派非会员理事,同时取消证监会对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的提名权。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副总经理等任免权也都应交还给证券交易所。另外,应明确划分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的法律分工,对证券交易所的权威地位予以法律保障。(2)证监会应严守政府监管边界,最低限度介入证券交易所的日常监管事务。证券交易所应当具有对会员、上市公司和场内交易充分的监管权、仲裁权和调解权;修改章程、接纳会员、修改业务规则、调整证券交易品种、提供互联网服务、制定异常交易行为认定和处理的业务规则等行为都无需再获得证监会批准,而只需报证监会备案。(3)丰富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手段,赋予证券交易所足够的调查权和处罚权。除了暂停交易和除名上市公司,英国并购委员会还可以要求伦敦证券交易所限制不遵守规矩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以及对他们施以罚款等惩罚方式。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应当在上市协议或入会协议中规定具体的强制性纪律处分措施,作为对现有不完备处罚方式的补充。
证券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也应当在多个方面得到相应完善。首先,应当确定证券行业协会的自治团体属性,增强证券行业协会独立性。应当豁免其按照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行登记,逐步改变中国民间团体登记前必须获得“主管部门同意”的做法。证监会不应过多涉入证券业协会的人事任免,并尽可能减少对证券业协会活动的干预,只保留适当的监督权即可。其次,应当赋予证券业协会更强的自律监管职能。《证券法》已经明确赋予证券业协会调解会员与会员、会员与客户之间证券业务纠纷的权利,证券业协会应当建立内部纠纷调解甚至仲裁机构,并规定具体的纠纷调解程序。《证券法》还应允许证券业协会自行制定自律规则、职业标准和业务规范,同时赋予证券业协会进行充分调查以及实施具体、实质性处罚措施的权力。再次,应当加强证券业协会与其会员之间的契约关系,会员利益至上应当成为证券业协会的执法理念;毕竟,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利益一致,是自律监管得以发挥效用的根基。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利益一致情况下,自律监管才能同政府监管一道,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保驾护航。
四、结语
从英国第一场敌意收购发生至今,以《合并规则》与《城市守则》的颁布为关键节点,英国敌意收购规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规则层面的自律监管到机构层面的自律监管的不断演进,这背后是私法自治同立法干预的并驱争先,也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所倡导的市场化民主传统在当代英国的发扬。我们从中看到现代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在公司决策与利益权衡方面的力量消长,我们也多少可以看出作为市场资深参与者的机构投资者,以自利为动机,对资本市场治理现代化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英两国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法律传统等方面有很大不同,然而所面临的产生于市场经济之上的公司控制权纠纷治理问题却是相似的。自下而上构建的英国敌意收购自律监管体系,很难在以政府机构为主导的强制性变迁路径下,得以自上而下地模仿和移植。但是,即便是有限的自律监管,只要能尽可能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在敌意收购中的利益趋同,也好过对证监会行政干预的过度依赖。应当明确我国法定自律监管主体的独立地位,依照各自的职能和业务样态分别赋予互为补充的监管权力,并辅之以具备有效威慑力的惩处实权。英国并购委员会的发展历史与执法经验对我们有深刻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注释:
[1] 唐林垚:《我国要约收购及触发点的保留与改进——兼析与欧美上市公司收购规则的比较》,《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
[2] Benati Luca, “Evolving post-World War II U.K. economic performance”,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 vol.36, no.4(2004), pp.691-717.
[3] City Notes: The J. Sears Offer, TIMES (London), February 5(1953), p.10.
[4] T. E.Cooke, R. G. Luther, and B. R. Pearson,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defence documents in UK hostile takeover bids”,JournalofBusinessFinance&Accounting, vol.25, no.1-2 (1998), pp.115-143.
[5] Sheppard, David K,TheGrowthandRoleofU.K.FinancialInstitutions, 1880-1966,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13.
[6] Bank of England. Issuing Houses Association. British Insurance Association. London Stock Exchange. Notes on Amalgamation of British Businesses. October (1959), p.4.
[7] Back to the Jungle,Economist, July 22(1967), p.337.
[8] Wardley,Peter. “The anatomy of big business: aspects of corporate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BusinessHistory,vol.33, no.2 (1991), pp. 268-296.
[9] The Panel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The 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12th ed., 2016), Part I18, Rule 21.1.
[10] Johnston, Alexander,Thecitytake-overcode,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1] Armour, John, and David A. Skeel Jr., “Who writes the rules for hostile takeovers, and why-the peculiar divergence of US and UK takeover regulation”, Geo. LJ 95 (2006), p.1767.
[12] Deakin, Simon, et al.,Implicitcontracts,takeoversandcorporategovernance:intheshadowoftheCityCod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 Steinmo, Sven, “The end of re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 pressures and domestic tax policy choices”,Challenge,vol.37, no.6 (1994), pp.9-17.
[14] O'Sullivan, Noel, and Pauline Wong, “Board composition,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hostile takeovers: Some UK evidence”,AccountingandBusinessResearch, vol.29, no.2 (1999), pp.139-155.
[15] Armour, John, and David A. Skeel Jr., “Who writes the rules for hostile takeovers, and why-the peculiar divergence of US and UK takeover regulation”, Geo. LJ 95 (2006), p.1769.
[16]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Share Ownership: A Report on Ownership of Shares as at 31st December 2004,p.9.
[17] 唐林垚:《我国上市公司要约收购制度评析》,《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18] Goergen, Marc, and Luc Renneboog, “Strong managers and passiv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the U.K.”, SSRN 137068 (1998).
[19] Consulting Shareholders: The Institutions' Views,Times(London), February 11(1959), p.15.
[20] The Panel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The 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12th ed., 2016),Part J2,Rule 24.1 (a).
[21] R.v.Panel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Q.B.815,841,842(1987).
[22][25] Armour, John, and David A. Skeel Jr., “Who writes the rules for hostile takeovers, and why-the peculiar divergence of US and UK takeover regulation”, Geo. LJ 95 (2006), p.1727.
[23] The Panel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The 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 (1969), Rule 33.
[24] 唐林垚:《论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之举牌预警及全面要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2期。
[26] Michie, Ranald,TheLondonandNewYorkStockExchanges1850-1914(RoutledgeRevival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