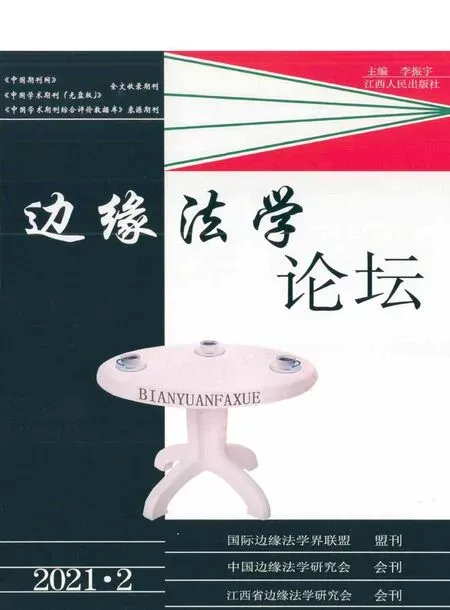女子法庭的纠纷解决之道
2021-12-03重庆400044
李 勇 (重庆 400044)
[内容提要]
女性有别于男性,女性有性别优势。女子法庭的纠纷解决中充分运用了女性的性别优势。一方面,女性具有的爱心、细心、耐心等品质,为妥善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女性看重关系的特质,有助于合理化解邻里纠纷;此外,女法官送法下乡和女子法庭的便民举措也深刻地体现着对弱者的怜悯。
女子法庭 情理关系 司法便民
在中国历史的较长时间里,掌握司法权的是男性。清末民初,国家开始兴办女子法政学校,女法官随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女法官队伍逐渐壮大。许多女法官成为全国法官学习的榜样。
法院涉及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轻微的案件不少,但处理起来十分棘手。由此基层法院纷纷建立女子法庭,试图通过女性的性别优势,采用“以柔克刚”以解决这些贴近民众生活实际的纠纷。
一、女法官解决婚姻家庭纠纷的优势
作为女性,具有天生的爱心、细心和耐心的特殊气质。这对于女法官解决婚姻家庭纠纷具有天然的帮助。因此,在此类纠纷中就需要女法官凭借爱心、细心和耐心才能解开矛盾和冲突。
(一)巧解婚姻纠纷
随着社会的转型,中国人的婚姻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集中表现在离婚率攀升上。从总趋势看,离婚率在未来只会有增无减。在此情况下,各地方建立女子法庭以解决婚姻纠纷不无道理。
婚姻纠纷涉及亲密关系的处理,稍有不慎便可能对社会造成威胁。此类案件的解决“需要女法官细心观察发现问题,以爱心走进当事人内心,再用耐心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在离婚案件中女原告居多,由于同样性别,女法官面对女当事人,更能深入她们的内心、理解她们的担忧、明白她们的诉求,并设身处地的为她们着想。面对婚姻危机和死亡婚姻,女法官能够通过细心观察当事人的面部表情、细微动作、不经意间的言语等,对当事人的婚姻状态进行综合判断。对感情尚未完全破裂、尚具修复弥补可能性的离婚当事人耐心引导,使其全面地认识到离婚对自己、配偶、子女、双方家庭乃至国家、社会产生的影响。对确属婚姻死亡的案件,也需要在安抚双方情绪的基础上果断判决离婚,进而在判决中保障他们的权益。
相较之对死亡婚姻的判离,婚姻危机的调解更复杂。不仅要处理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等问题,更需要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女法官用爱心走进当事人内心,更能抓住婚姻危机的症结、明白当事人的需要、掌握危机解决的突破口,用外在因素助力婚姻危机的解决。
襄城县法院女子法庭在情人节调解的婚姻纠纷中,女法官预先了解到当事人是冲动离婚,专门购买玫瑰花并提前到法庭进行布置。得益于节日氛围的烘托,加上收到鲜花的喜悦,双方冰释前嫌。协兴女子法庭在调解婚姻纠纷时,以《知心爱人》为背景音乐,并放映两人曾经恩爱的照片。双方最终打开心门,和好如初。在这两起案件中,女法官善于利用外在因素唤起当事人的情感。不论是将调解置于情人节、购买鲜花、准备PPT,还是以《知心爱人》为背景音乐都是为唤起当事人的情感体验。
实践证明,女性的爱心、细心、耐心特质在婚姻纠纷解决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不仅能够帮助法官准确辨别出婚姻纠纷的性质,而且可以在案件的审理和调解中运用女性特有的网格化思维帮助当事人情绪冷静,促使她们打开心门,以使面临婚姻危机的当事人重归于好,濒临死亡婚姻的当事人好聚好散。
(二)善解家庭矛盾
“家庭矛盾是亲人之争,纠纷的非理性因素较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当复杂”。在这方面,女子法庭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女子法庭直接以家事法庭的身份出现。女法官具有的细心、爱心和耐心等特点,成了女子法庭化解家庭矛盾的“公开秘诀”。
一方面,女法官细心掌握“实情”,以真正理解当事人的难处并厘清纠纷产生的原委。就可能性而言,吉利根的研究启发我们,女性的思维模式使其在换位思考中占据优势。女法官通过观察和体味当事人的言行举止以还原纠纷从发酵到爆发的全过程,就“必须置身在群众中和人们有同样的感受后才能判断别人的感情和行为”。
另一方面,女法官在掌握实情的基础上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于法”。其中,“动情”是核心。家是重情之地,当事人之间的“情”表现为唤起他们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亲情的重视。女法官能够在唤醒当事人的感情上充分发挥作用。以女法官擅长“讲故事”的优势,基于自身的情感体验,故其故事多能打动人心。
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要求为婚姻家庭纠纷的调解设置更高的目标。若试图达到修复和愈疗的效果,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需要发挥女法官的性别优势。因为,“在女性心理发展的过程中充满对他人的关爱,她们经常以关爱能力定义自己,她们至今仍扮演养育者、关爱者和帮助者的角色”。这使得女法官“更易于洞察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更易于关注当事人的情感状况,更易于实现与当事人沟通”,从而挽救一个个家庭、感动一对对走在婚姻破裂边缘的夫妻。
二、女法官对人际关系的看重
有研究显示,两性在同样的困境中看到的是不同的道德问题:男性看到的是通过逻辑推理解决权利冲突;女性则看到需要通过努力来修复人与人的关系。本文以邻里纠纷的调解来说明。
(一)用真情拉近法官和当事人的距离
在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感情,都需要真情的慰藉。如果人与人之间失去基于真情的连结,人类很可能在兵荒马乱中归于消亡。
首先表现在与当事人的关系上。作为在司法机关面前处于相对弱势的当事人,法官要用真情才能拉近与他们的距离。已有的司法对比试验表明,男性倾向于规则化的思维模式,女性思维更注重关系,对关系的看重使其在纠纷解决中本能的带有情感色彩。真情的融入使女法官能更全面的审视当事人的困境和需要,从而拉近与当事人的距离。
此外,真情还体现在行动上。以陕西一女子法庭审理的邻里纠纷为例。女法官约见一位年过六旬的当事人,时间为上午十点半。因火车晚点,当事人到法院时已过十二点。得知当事人未吃午饭,法官立即带来午餐;在知悉当事人将孙子托于邻居代管时,法官当即开始会见。结束时天下大雨,法官将伞送予当事人。此时当事人说道,“我打了好几年官司,从没遇到过这么亲民爱民的法官,我决定这次是最后一次诉讼了,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会再打官司了,因为我相信贾法官,我相信贾法官会依法公正判决,败诉也心甘情愿”。
总之,与从事调解的男法官比,女法官更能取得成功。早在2001年,山东即墨法院做的一项“对比试验”便证明了这一点。在很多时候,“女子法庭的法官能够放下法官的身份,与当事人像女儿、姐妹一样真心交流。”由于注重关系和连结这种特有的女性气质使得女性法官普遍能够放下身份与当事人沟通交流,以拉近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当然,女法官的真心通常亦能够换来当事人的坦诚对待,从而达到一种真正的沟通状态,这对调解的顺利开展及调解结果的成功都有重要意义。
(二)以真情关怀修复邻里关系
“邻里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中承载着情感沟通和社会支持的功能”。重视关系带来的关怀价值则使纠纷的解决更能达到修复效果。在涉及邻里纠纷时,不断发生的邻里恶性事件已给我们沉重警告,即司法需要看重邻里关系的修复,才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在此类纠纷解决过程中,女法官的目标在修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乡土社会中的民众多以族群聚居,相邻而居的人之间多存在某种亲缘关系,故此类纠纷的处理更看重关系的修复。女法官在面临邻里纠纷时,需要做的不是将已经破裂的关系彻底割断,而是要像界线一样重新“缝合”当事人之间破裂的关系。
杞县五里河女子法庭审理一起邻里土地纠纷。在本案中,村民孙铁成与邻居孙铁柱素有矛盾,两家曾多次发生邻里纠纷,积怨颇深。村委会和派出所多次调解,都未从根源上化解矛盾。随后,孙铁成将孙铁柱起诉到五里河女子法庭,要求被告将自己屋后的土沟填平。经数日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按照正常的调解流程,纠纷到此即已得到圆满解决。为防止当事人反悔,女法官亲自拉起架子车,拿上铁锨取土填沟。当事人为此深受感动,纷纷上前帮忙,很快便将土沟填平。女法官的行为不单从法律上使纠纷得到解决,而从恢复邻里关系的角度进行了更全面和长远的考量。女法官填的不是现实中的土沟,而是隔离邻里关系的心理鸿沟。
女法官的关怀还融入到“理”的阐释中。忠县人民法院第四人民法庭审理过这样一起邻里纠纷,曹大成与曹大宝、曹二宝系未出“五服”的亲属。曹大成与曹大宝、曹二宝南北为邻。曹大成要翻新老房,要求曹大宝、曹二宝挪开放置于其屋后的杂物,二人在口头虽然同意,行动上却拒绝留出空地。双方就此出现纠纷,经多部门调解,纠纷仍未得到解决,延续八年之久。该案最后起诉到了女子法庭。案件受理后,女法官到现场查看情况并分头做当事人的工作。将关怀因素充分融入到了“理”的释明中,帮助当事人跳出相对局限的个人立场,从更全面的角度、更高的层面探讨邻里关系。
除情理外,关怀也融入到了法理的释明中。女法官在释明法理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关怀因素,从而使当事人之间及其与法官之间少了张力,多了聚合力。女法官没有直接根据法律的规定直接宣布曹家二兄弟的行为违法,而是首先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以对他们的现实处境的关切为开端展开调解。在赢得当事人的情感认同后,女法官才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告知当事人法律的规定,以帮助其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在结果方面,她们没有径直告诉当事人处理结果,而是旋即又转到了当事人的立场,通过表明协商的可能性,对结果进行了慎重释明,以此照顾到了被告的情绪。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关怀伦理在当事人之间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合力,正是这股合力成为了纠纷解决的推动力。当事人终于相互作出让步,曹大成同意在扩建时留出2米的滴水,曹大宝和曹二宝则同意将猪圈和其他杂物撤除。两家多年累积的恩怨至此得以消除。女子法庭不仅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且用关怀修复了邻里之间的关系,用关怀修复了损坏的社会关系。
三、女法官对弱者的怜悯举措
在司法中,绝对理性强调法律的明确规定,故纠纷解决不过是一纸判决。女性的主张远非如此,它促使法官看到冰冷案卷下活生生的人的呼求。特别是在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中,它要求法官用怜悯对待当事人。
(一)女法官送法下乡
相较之城市地区贴近“陌生人社会”,乡村更接近“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对人情的看重使群众很难跳出既有的关系网络而主动接受法律规训,传统习惯和法治社会的主张之间也可能形成一定程度的对立。
就“送法下乡”而言,苏力教授将其归结于权力运作形式,即“司法下乡是为保证或促使国家权力,向农村有效渗透和控制。女子法庭的“送法下乡”与强调权力渗透不同的是,体现着对弱者的怜悯。
为解决当事人因距离较远带来的诉讼困难,女法官选择以巡回法庭的方式为偏远地区的当事人提供诉讼服务。面对辖区较广、多数乡镇距离法庭数十公里,诉讼不便的实际,三明女子法庭推出巡回法庭办案模式;面对牧民居住较远的实际,科左后旗阿都沁女子法庭的法官冒着烈日严寒,带着必要庭审设备就地开庭;邵东县法院流光岭女子法庭位于邵东县最偏僻的山区,女法官在油菜花地旁搭建简易法庭;因当事人年纪老迈,忠县人民法院第四人民法庭的女子法官选择在当事人家院坝开庭。
女子法庭普遍采用了类似于抗战时期马锡武的审判方式,她们甚至用更细致、完善的方法为偏远地区的当事人送去了法治。面对当事人不便的实际,女法官选择不辞辛苦到当事人所在地开庭,为达到“案结事了”多方奔走。从此意义上讲,女法官送的是爱与温情。
(二)女子法庭举措为民
女子法庭的便民举措也从“家文化”构建和人道主义司法两方面展开。
一方面,构建女性法庭家庭文化。以协兴女子法庭为例,该法庭走廊两边是专门设计的家文化墙,墙上粘贴着邓小平的家庭照片和习近平跟家人温馨共处的图片,及他们对家庭的论述,走廊两边还悬挂着《弟子规》和《朱子家训》。该女子法庭还设置了家事调解室,“柔和的灯光布满房间,镂空的落地纱帘、橘色的装饰画、藕荷色的桌布上摆放着粉红色的康乃馨。”“在调解离婚诉讼中,女子法官对当事人不用原、被告称呼,也不穿法袍,原被告和法官围坐平等协商”。这样的氛围更容易让双方情绪缓和,拉近彼此的距离。
另一方面,秉持人道主义司法。女子法庭充分体现司法的人道主义关怀。面对贫困的当事人,女子法庭不仅为他们争取权利,也在此过程中充分融入人道主义关怀。在恩施法院龙凤女子法庭审理的一起涉及拾荒老人的执行案件中,为拿到执行款,女法官多方调查,先后5次前往被执行人的可能居住地,最终找到被执行人,将4000多元执行款送到了老人手中。为实现每个当事人都打得起官司的目标,江宁女子法庭也出台相应举措,为特别困难的当事人解决食宿问题并提供接送服务。
女子法庭还十分关注老人和残障人的案件。在审理一起81岁老人口头起诉五个儿子的赡养案中,江宁女子法庭不仅没有收取诉讼费,还为老人代写诉状。此外,女法官还通过上门立案、上门送达、上门开庭、上门调解以及帮扶的方式,为残疾人参与诉讼提供了便利。
转型社会的现实给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给女子法庭走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遇。女子法庭的实践给我们深刻启示,女法官的爱心、细心、耐心、仁慈、怜悯等女性气质对修复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帮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