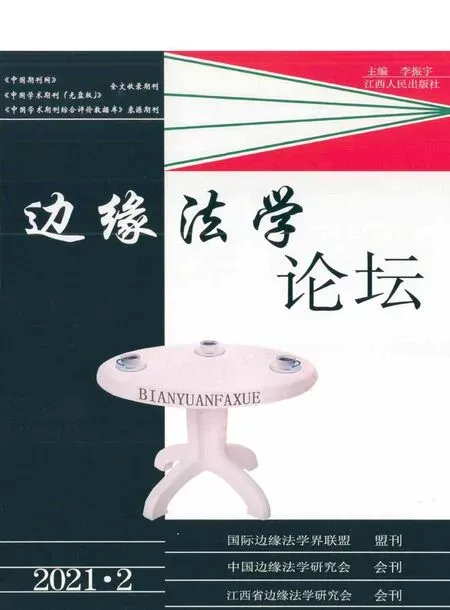德沃金与哈特关于裁判中法律解释的不同主张解析
2021-12-03郭泽宇北京海淀100088
郭泽宇 (北京 海淀 100088)
[内容提要]
裁判者应当怎样运用法律解释进行裁判,这是司法理论研究的重心之一。德沃金的理论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法律解释性的性质、实质性的内涵、整全性的特点,为我们提供了法官在裁判中正确解释法律的途径。
德沃金 建构性解释 整全性解释
在这本《法律帝国》的划时代巨著中,德沃金以内在视角的方式构建了以法官为主体的法律理论,比同样哈特以法官为主角的法律现实主义高明多了。德沃金的法律理论固然有其不足之处,但对我们思考裁判者应该如何进行法律解释这类问题极具启发意义。
一、哈特与德沃金不同法律解释观
哈特和德沃金都是20世纪英美法学世界最为声名显赫的法理学家。他们二人的论战,直接推动了整个英美法学理论的跨越式飞跃。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告诉我们,法律是社会实践规则,法律体系是由人们普遍接受终极的承认规则以及由该承认规则所衍生出来的规则组成。在哈特的法律体系中,最为关键的元命题是终极承认规则的接受,这是一个事实或描述问题,而非价值判断或者规范问题,终极的承认规则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体系的元规则,是因为人们普遍以内在视角来接受终极的承认规则,即将该规则当做自己行为的标准,并以该标准来批评他人作出违背该标准行为的理由。哈特的法律概念,是一种习惯式的法律概念,法律体系的存在,不管是西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法律体系,还是以强制与非人道为底色的法律体系,都源于该领域内的人们以内在视角的方式普遍接受终极的承认规则这一习惯。
虽然哈特也承认,法律体系事实上或多或少具备自然法的某些属性,但哈特终究是一个法律实证主义者,他所意欲构成的法律理论,就是要以客观化、事实性的习惯式法律观念,来给法律和道德划清界限,以元规则的非道德化来为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命题摇旗呐喊。哈特的理论,给整个法理世界带来了理解法律概念的新样态,以终极的承认规则为元规则的法律体系,确实给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法律体系做了一个较易接受的证成。但是,哈特的理论在宏大叙述上的成功,真的就证明它就是法理世界的真理吗?德沃金作出了否定答案。为了更好地阐明哈特与德沃金理论的差别,我们先离开美妙的理论世界,进入尘世之中。
余金平案:2019年6月5日,被告人余金平酒后驾车撞上被害人宋某并导致死亡,在审查起诉阶段,余金平认罪认罚,且门头沟区检察院提出了判三缓四的量刑建议,但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经过审理,未采纳量刑建议,判处余金平交通肇事罪有期徒刑2年。门头沟区检察院认为量刑过重,随即为了被告人的利益提起了抗诉。被告人余金平也提起上诉。经过审理,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审理的部分事实未予以合理评价,应当对其加重处罚。二审法院能否对被告人余金平加重处罚?
如若二审法院的法官是哈特之理论的信徒,是一位习惯主义者,他会首先考虑《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及其例外。但余金平案与以往其他的案子不同,以往检察机关的抗诉,绝大多数都是以被告人之不利理由进行的,这可以看成检察机关的习惯。由于认罪认罚制度是2018年刑诉法新修时才增添的制度,刑诉法对上诉制度进行制定时,刑诉法二百三十七条之上诉不加刑的例外情形应当理解为只考虑到了为被告人之不利的抗诉。
现在,摆在这个信奉哈特之习惯理论的法官面前的是,检察机关为了被告人的利益提起了抗诉,他到底能不能加重刑罚?他查阅过去的政治决定(法律),并没有显明的事实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且该案属于新增制度所衍生出来的新型疑难案件,法院也并无形成如何处理该类案件的习惯。那么,按照哈特的理论,语言天生具有开放性结构,法律作为由语言构成的规则,也不可避免得带有开放性结构。法律的开放性结构意味着,存在某些行为领域,这些领域如何规范必须由法院或官员去发展,也就是让法院或官员根据具体情况,在相互竞逐的利益间取得均衡。也就是说,疑难的法律案件是语言中核心语义之外的阴暗地带,规则在这个阴暗地带失去了魔力,取而代之的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换句话说,哈特的法律理论,并不承认这些疑难案件处于法律规则的统摄范围之下,他将这些疑难案件的规制不能看作是人类使用语言这一工具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能诉诸法官个人的良知、信念、道德进行自由裁量。
德沃金作为哈特的一生之敌,对哈特的法律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德翁认为,所谓的语言的阴暗地带,是掩盖法理学的重要问题的“语义之刺”。法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法律问题,为法律问题提供答案。真正能够揭示法律的概念,探究法律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的,正是这些疑难案件,而哈特的理论却不能辐射这些疑难案件,把案件的裁决权完全交给了自由裁量,刻意回避了能够寻求法律理论真理的绝佳材料。正是在法律的模糊地带,才是法学理论的富矿之地。
二、建构性法律解释之本质
德沃金认为,法律是建构性解释性概念。虽然在我们如今的法学教育下,法解释学、法教义学等概念我们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在德沃金那个时代,在法律实证主义所引领的法律客观化的时代,这一概念的提出可谓是提倡法律概念客观化理论的强劲对手。让我们套用下哈特所在的牛津学派所提倡的语言分析理论的惯用问法来进行论述:解释这一词是什么意思?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解释一词的出现,至少意味着存在着一个待为解释的客体,一个意欲解释客体的主体,解释正是主体对客体进行观察并阐明客体的概念、性质的主体能动过程。在德沃金的这本书中,解释的主体并不是普罗大众,而是法官。在这里,他实质上借助了哈特的“内在视角”的理论,哈特将内在视角引入到社会实践层面,即认为法律之所以能够发挥指引功能,是因为存着这样的事实,社会里大多数人将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并以该标准来评判他人之行为。德沃金更近了一步,德沃金将“内在视角”理论聚焦在了法官身上,集中到了以内在视角的形式处理疑难案件的过程中。这是德翁之理论的优势之处,但同时也是其阿喀琉斯之踵。不管怎样,德沃金将主观性因素纳入法律的理论体系,以一种新的方式对风头正盛的法律实证主义造成了冲击。
在德翁看来,揭示出法律的解释性性质还不够,因为还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理论,即主观解释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对法律的解释应当探究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意图,立法者的意图就是法律解释的金科玉律,比如在余金平案中,解释者应当探究79年刑诉法的制定者们的本意,虽然那时候的制定者们也许没有考虑到检察机关会为被告人的利益而上诉,但是解释者们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如制定该法律的会议纪要等进行假设和想象,若是制定者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会作出怎样的立法。德翁坚决反对这种意图式的解释方法,为了反驳这种完全仰仗立法者意图的解释观,他将解释分为了三种,即对话性解释、科学性解释和创造性解释,其中法律的解释应当属于创造性解释。对话性解释就是指,人与人在日常交往、在平日的交谈和对话中,当听到对方的语言时,我们确实在试图理解对方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立法者意图的解释论正是以这种对话式的解释理念为基础的。科学解释指的是科学家们通过观察客观事物的发展而作出了解释,如牛顿观察了苹果的自由下落,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建构性解释是指解释不仅仅是还原解释文本的过程,文本被创造出来之后,就有了自身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推动,文本自身的意义和实践肯定会有增添或者删减。比如,“向年老者脱帽”是一个人们表达尊敬的礼仪,并且这个礼仪得到了某一时期人们的一致接受并予以实践,时过境迁,也许对老者致敬的方式会发生变化,人们也许不再只是向老者脱帽表示尊敬,也许还会向老者挥手、鞠躬等,人们也许还会将这个将脱帽这个动作用在这样的场景,即为国奋战的老兵们载誉而归的时候,人们夹道向他们脱帽致敬。面对上述情景,我们当然可以用“向年老者脱帽是表示敬意”的规则来解释后续的向老人挥手、鞠躬或者向胜利而归的老兵们脱帽的行为同样是表达尊敬,而这种解释,是由表达敬意的向年老者脱帽这一规则解释出来了,它形构了“向年老者鞠躬、挥手或者向老兵们脱帽”这些行为的意义并同时为这些行为证成。德沃金认为,法律的解释乃至社会实践的解释,不同于对话解释和科学解释,法律的解释是建构性解释。“两者致力于解释的事物,都是人们创造出来的有别于自身的实体,而不是人们说了什么或非由人创造的事件(科学性解释)。”德沃金的建构性解释理论,实质上是借鉴了伽达默尔“效果历史”的哲学理念。根据“效果历史”的观点,文本的真正意义既不是作者的意愿也不是读者最初的理解,文本的真正意义应该是和解释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流动的运动过程中的。折射到法理学理论的结果便是,将法律这一过去的政治决定与当代解释者的视域联系起来,解释者的解释,是法律这一客体和解释者的自身视域相互交融、相互连结的结果,解释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完全主观的,是主观和客观融合的产物。所以,法律解释的目的,不能仅仅将法律的历史制定者的意图奉为圭臬,还应当把解释的重心放在解释者个人的信念上。
德翁将解释分为前解释阶段、解释阶段、后解释阶段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前理解阶段是指我们应当对实践之初步的解释内容如规则、准则等有必要的认识和共识。比如在余金平案中,对刑诉法二百三十七条上诉不加刑原则与例外及其相关的刑诉法的基本知识和理念是我们对该案件进行后续解释的基底。第二个阶段,解释阶段即是解释者为前理解阶段所确认之实践的主要组成部分,选定某个总体的证成。这个证成无需符合长期存在的实践的每个方面或特征,但其符合程度必须足以使解释者能够将自己看成是在解释那个实践,而不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实践。在余金平案中,除了上诉不加刑是法律这个形式理由之外,我们还应当思考,为什么上诉不加刑是合理的?上诉不加刑规则的背后体现的是哪些实质性的价值呢?在最后一个阶段,后解释阶段或者称为改造阶段,解释者调整自己对实践“真正”要求什么的感悟,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他在解释阶段接受的证成。也就是在这个阶段,解释者需要考虑的是,根据解释阶段所得到的信念和价值,如何对实践进行解释,才能以最佳的视角来解释和证成实践。在余金平案中,法官经过了解释阶段之后,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到底是加重刑罚抑或是恪守上诉不加刑原则符合解释阶段揭示的价值,并真正地使被解释的对象或实践成为尽可能最佳的事物。也就是说,建构性解释追求的是一种最好的解释。
德翁将怀疑论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在怀疑论,它是怀疑整个法律规则的存在,认为根本不存在好的或者坏的解释,这是典型的法律现实主义的观点。这个论战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一种是外在怀疑论,这种怀疑是一种形而上的立场,它借鉴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否认美学、道德等价值论在客观层面存在着最佳样态,认为一个观点是否绝对正确,必须要有令人接受的事实和逻辑存在。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并非是一种自然科学式的理论,而是一种信念和责任理论,比如关于奴隶制的讨论,“奴隶制是错误的存在”和“奴隶制在客观上错误的存在”这种说法不管是在相信奴隶制是原罪的群体中还是在提出若干理由支持奴隶制存在的群体中,这两种说法实质上并无多大程度的区别。“客观上或者确实”这种词语的修饰,只是起着修饰或者加强语气或者形容存在较大部分人支持该观点的作用。追究最佳解释并非是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答案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上,每个法官根据建构性解释的理论也许会得出不同于他人但能使自己完全信服的裁判。德沃金通过对外在怀疑论的驳斥,为“存在着最佳解释”这一命题廓清了认识论上的道路。
三、法律解释的整全性价值
按照德沃金的理论,既然法律是一种解释性事业,且解释并非法律制定者之附庸而是融入了解释者目的的产物,所以法律的解释势必不会是价值无涉的,相反,它必须以实质性价值理念为基础。正如德翁所言“如果法律命题出现在,为社群法律实践提供最佳建构性诠释的正义、公平、与程序性正当程序等诸原则之中,或从中推导出来,那么这些法律命题为真。”
德沃金还提出了法律的解释还应当具备“整全性”的实质价值。德沃金早期在于哈特的论战中,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批判了哈特的观点,认为法律制度不只是由单一的规则组成,还应当包括原则和政策。现在,他将这一观点融入到了法律解释理论的建构当中。德沃金将一个社群的政治实践分为三种模式:事实性偶遇模式、规则手册模式、原则模式。事实偶遇性模式描述的是一个社群之内,人与人的分工和合作完全是随机的、无规则束缚的,就如同两个毫不相干的人由于机缘巧合一起来到了一座孤岛之上,他们会因为生存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偶尔进行合作,比如合作打猎等等。这一模式显然不适合现代社会关系日渐复杂的社会。第二个较有吸引力则是规则手册模式,按着该模式,所有的社会规则都如同写在了人人都可拥有的手册一样,人们遇到任何问题,只需翻阅手册即可解决,也就是他们认为规则的内容已经穷尽了他们的义务,任何该手册未明示的内容,都不能成为指引人们行为的标准。这一模式与前述论述的习惯主义法律观念有着亲缘关系,因此也有着与习惯主义法律观念一样的弱点。第三个也即是德沃金推崇的原则模式,认为过去的政治决定(如法律、判例)等并未穷尽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规则手册记述的内容并未周延。这个社群的人们认为,统治自己的不仅是政治妥协中反复推敲确立的规则,而且包括共同的原则。原则不同于规则,规则具有相对明确的特征,而原则可以理解为规则背后的实质价值和信念,按照原则进行行动是超越了形式平等的整全性追求,它要求国家行使强制力的活动如同一个正常成年人的行动一样,保持协调和连续性。
整全性作为一项独立的实质性价值的论据,为建构性解释理论相连结提供了最佳契机。如何进行建构性解释,需要考量明确的法律规则或者判例以及正义、公平、正当程序等原则之外,还要将整全法纳入独立的考量范围之内。若是缺乏了对整全性融贯原则的考量,法官仅仅依赖自身的正义、公平等实质价值进行裁判疑难问题,那么就落入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窠臼。只有接受了解释性整全法的法官才能以融贯原则的支持下,找到对其社群之政治结构与法律教义的最佳建构性解释。同时,整全性也是区分惯习式的法律观念与法律现实主义的重要分野,它让法律陈述成为既非惯例主义回顾式的事实性报告,亦非法律实用主义前瞻式的工具性规划。整全性是一个连结过去和现在的桥梁,法官的目光应当在过去的决定如法律和判例与现在之间流连往返,不能作出死守早已失去合理性传统的决定,又要以过去作为续造法律的基础,作出既符合过去实践之原则又能体现当代追求之实质性价值的决定。整全法要求法官尽可能将法律设想成是根据一组有关正义、公平与程序性正当程序的融贯原则创制出来的;它要求他们在自己面对的新型案件中实施这些原则,从而使每个人的境况根据同一标准判断是公平而正义的。当然,整全性仅仅是法官裁判疑难案件时必须考虑的一个价值,并非是高于其他价值如公平、正义之价值。
四、裁判理想样态的体系解释
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将他理想的法官称为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取自古希腊神话,是古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力大无穷的英雄。虽然德沃金的理论是以英美法系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但对我们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司法裁判者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
一个赫拉克勒斯式的法官,首先应当具备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对显明性的历史事实,即我国的基本法律体系、基础法律规范有着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这是法律解释的前理解之必须。一个学验俱丰之法官,拥有丰富的学验,“前理解”越多,其“选择”适用各个事实关系之法律规范及淘汰不能适用的法律规范,就越为快速;其次,法官不能是适用法条的工具,他不能仅仅关注形式上的法律规定,法官的内心必须充斥着对实质价值如正义、公平、正当程序的追求,应善于对法律作出最佳的解释。德沃金的法学理论,强调法律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还不够,必须要有其他的实质价值来证成国家使用强制力。近年来,我国的基础法律规范不断得到完善,但各式各样的奇葩案件仍然层出不穷,如天津老太太气枪案、王力军收购玉米案、福建枪型钥匙扣案等。这些令人乍舌的荒谬案件的背后,折射的是某些公安司法工作人员仅仅把法律看作是一种制度性事实工具,机械适用法律的乱象。这些案件形式上当然可以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定罪量刑,但是法学的任务不应仅研究成文法,而应探寻居于指导地位之活生生的法律,据以论断成文法之善恶良窳,利用实质性价值作出符合并证成实践的最佳解释。最后,法官还应当具有整全性这一独立的价值理念,当适用某一个法律条文时,适用的法律不仅要在横切面上具有原则的一致性,比如某一涉嫌行政类犯罪的嫌疑人在行政法规范上违法的阙如,可以直接利用体系解释而为其在刑事上脱罪。而且还应当在纵切面上保持行动的原则一致性,法官的目光不仅应当放在法律规范层面上,更应当关注规范背后、证成规范的隐藏法律,即原则、政策等。德沃金主张,每一个法律规范或者判例背后,都有证成其存在意义的价值与原则。每一个疑难案件的出现,都需要法官仔细得考察法律规范背后的原则及实践,以此作出最符合过去实践并证成现在之实践的判决,使国家运用强制力如同一个整体一样协调和连续,这就是整全性的意义。
最后,再让我们回到余金平案中,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完全按照刑事诉讼法字面上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是上诉不加刑的例外,没有规定为了被告人的利益而上诉不能加重刑罚,而检察院提起了一个抗诉(不论检察机关是为了被告人的利益与否),法院都有权依据该条规定对被告人加重刑罚;第二个看法摈弃了完全按照法条的字面意思进行理解的做法,而主张去考察该制度背后的价值和原则。余金平案是发生在刑事诉讼认罪认罚制度蒸蒸日上,新的司法理念——合作正逐步融入司法制度的大背景下,该案也恰恰为认罪认罚案件。上诉不加刑设置的初衷是为了保证二审程序能够顺利起到对一审法院的监督作用,体现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过去的司法实践表明,被告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上诉而检察院没有对其作出不利抗诉的情形下,二审法院不会作出加重量刑的判决,这也同时说明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及其背后的正义价值受到整个司法界的普遍接受。现如今,被告人提起上诉,检察机关基于合作的理念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抗诉,可以理解为被告人为了自己利益上诉的强化版本(仅仅比之前多了检察机关的支持)法院基于对上诉不加刑原则与背后之实质正义以及对过去实践的遵守,且认罪认罚制度背后的合作理念,已经成为未来刑事司法不可阻挡的潮流,检察机关作出对被告人有利的抗诉,是合作理念下产生的必然衍生品,这种类型的抗诉对过去纯粹存在被告人的上诉并无本质的区别,所以法院作出不能加重刑罚决定才是最佳答案。法官若是在检察机关未提起不利抗诉的情况下,加重对被告人的刑罚,也许还涉及到了检法两机关的权力冲突,但是这并不构成一个合理的理由,因为检法两家公权力机关的权力冲突,并不是行使国家强制力,剥夺公民之权利的正当理由。两相比较,高下立判,第二种处理方式既考虑了法律规范背后的原则和价值,还关注了政治实践之贯通性和整全性,这种解释更能符合过去的实践、证成规范背后的原则和价值以及证成现在及未来的实践。
德沃金的理论是根植于美国之崇尚司法者文化中的产品,是一种司法者的自身信念和责任的法律解释理论,该理论站在自然法学派和法律实证主义下的法教义学的肩膀上,创造性地吸取两种理论的合理内核,提出了建构性解释的整全法观念。德翁之理论的确是一种较为完善和精致的司法理论,但在宏大叙事上、在放眼整个法律的基本框架上,也许哈特的理论更有魅力。但不管怎样,吾辈学人能有机会看到两位巨擘之间富有理论更有魅力。但不管怎样,吾辈学人能有机会看到两位巨擘之间富有哲思性的论战,何其幸甚!
猜你喜欢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