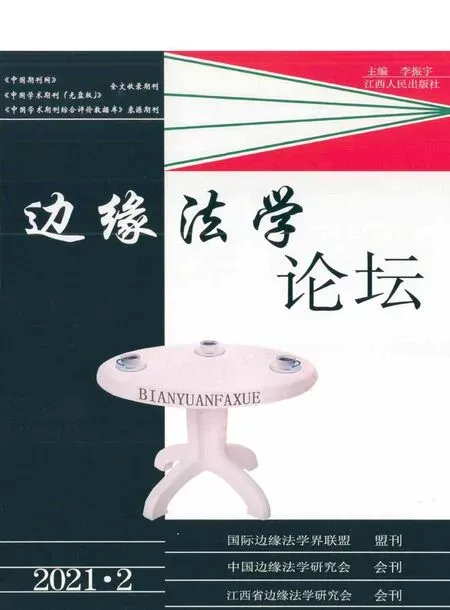弗里德里希·米勒的法律语言观建构
2021-12-03北京海淀100088
高 莉 (北京 海淀 100088)
[内容提要]
弗里德里希·米勒是德国法律语言学家,选择语言/语篇分析的方式进行法学建构,注重法律意义/法律规范生成的语境性、动态性,从而使其法学方法论具有鲜明的语用学特色,反映出语言分析与法学研究相融合的趋势。本文对米勒的法律语言观进行梳理与提炼,旨在为我国的法律语言学研究提供一些方法论创新的有益启示。
法律规范 语篇工作 语义建构
十九世纪中期,受当时社会自然科学的影响,法律实证主义者开始推崇法典至上,认为法律规范文本是语义确定的规则,在案件裁判中可以被直接适用。遇到具体案件时,法官可以通过逻辑三段论进行推导,并由法官进行宣判。事实证明,法律实证主义的许多主张过于机械化、理想化,并不符合法律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形。弗里德里希·米勒因不满实证主义法学脱离实际,提出的一系列来源于对大量真实法律实践活动的法律主张。虽然没有刻意借鉴语言学理论,但米勒的很多思想都与语用学不谋而合,因此而成为海德堡法律语言学派的主要法学理论基础,在德国法律语言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体现出德国法学与语言学研究相融合的特色。米勒的法学建构没有抽象地谈法律与语言的关系,而是将语言活动融入进了法律活动当中,是其法律语言观的体现。
一、法律规范的语义外延
在构建自己的法律方法大厦时,米勒首先区分了语言数据、事实数据和法律规范。他认为脱离了具体案件,法典/法律规范文本便没有实际的法律语义,更不是既定的法律规范,而是仅具有形式特征的语言符号串,属于法律工作中的规范语言数据。
米勒指出,法典是立法者制定的符号,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属于客观范畴。“法律意义”是法律工作者结合具体案情对法条阐释的规范观念,是司法者解释后的“法律”,属于主观范畴。众所周知,在实际案件发生时,法律的作用是定纷止争。法律人在面临具体案件时,对抽象的法律规范文本进行意义解释。米勒将法律规范生成的过程称为“法律文本的具体化”,即在法律论证的过程中,采用各种法律解释的方法,所使用的论据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具有案件针对性,直到推导出最终的法律结论。
法律文本符号和外界生活事实不再直接对接,需要经由法律人积极主动创造性地建立起关联。法律文本没有所谓固定的、能够代表立法者意志的唯一正确法律意义。在司法实践活动中,法律人在面临新的案件时,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在合理的范围内解读法律文本的意义,动态地推导出适用于个案的法律规范,并据此作出法律判决。不同法律人在不同的时空中,面临相同类型的案件或者不同类型的案件可以对同一法律文本作出不同的意义解读。这种法律活动的创造性、动态性特征使得生成的法律规范不再具有唯一性,法律人需要在多种解释可能性中选择更加具有说服力作为最终的判决依据。
二、法律文本的语篇规范
法律文本与判决文本虽是可见的、具体的,但中间历经的法律发现过程一般具有隐蔽性,米勒将其归纳为相互贯通的几个步骤:法官将案件事实转化为法律语言;寻找相关的规范文本假设;借助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将抽象规范文本的内容具体化,一般法律规范落实到具体案情上最终生成判决规范。
法律判决的起点是遇到一个法律案件,“诉讼人X是一家火葬场的职员。这家火葬场焚烧尸体需要经过三个步骤。在其中一个步骤需分拣相关物品,包括本案涉及的物品牙金。X和另外两个同事焚烧了超过600个带有牙金的尸体,他们取走和转卖了大约12公斤的黄金。......”依据该案件具体情况,法律人开始寻找相关的法律规定。由此便从事实数据转向语言数据,初步形成规范文本假设:诉讼人X有可能因为德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违反保管义务罪”、第242条规定的“盗窃罪”或者第168条规定的“死者安息妨害罪”而被处罚。确定了大致范围后法律人开始仔细考查规范方案中具体法条的内容。如:“非法夺走权利人保管的尸体、尸体的一部分或者骨灰,......构成犯罪”。这条书面规定还不具有规范性,因为它还没有引发具体的行为。只有将法律条文逐步语境化具体化,在其中加入各种解释因素,包括语法解释、历史解释、立法解释、系统解释、目的解释等等,结合案情为抽象的规范文本确定具体所指,才能生成引发判决行为的法律意义和法律规范。
在对与本案相关的法条进行语境化的过程中,适用的法律规定范围开始缩小,最终形成了具体的规范方案。如:“德国刑法典第168条第1款意义上‘死者的骨灰’包括火化后剩余的所有的残余物”。法律人在这个规范方案的指导下匹配事实中的相关要素,视角由语言数据重新转向事实数据。事实数据并非完全客观事实,而是由语言加工的事实。因此,最后得出本案的判决规范:“被告因妨碍死者安息被判处......自由刑”,促成本案判决行为的发生:逮捕本案中的X。
从上述推导法律规范的模型来看,米勒总共区分三个结构层面,即生活事实、语言数据(法条)和法律规范。领域规范、法律规范和判决规范都以语篇为载体,因而米勒称其为法律人的“语篇工作”。语篇工作模型的提出使判决行为及过程公开化、透明化。在探讨法律语言通俗化与专业化之争或法律语言的可理解性问题时,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造成法律语言可理解性差、不够大众化的原因在于立法语言的语言表述特征。因此旨在提高立法语言可理解性的尝试大多围绕着改善立法语言的语言表达,使其变得简洁明了。然而,法律只是暂时的知识,法律最终是行为。不同于传统篇章语言学认为语篇是句子序列符合语法形式的组合,米勒的“语篇”概念具有行为理论特征,他认为理解法律语言运作的方式应当是理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语篇模型解释了“法官在作出一项判决时究竟做了什么工作”,可以促进大众对法律人工作方式及法律行为模式的理解,是改善法律语言可理解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米勒法律语言观解读
如前所述,传统实证法学对法律语言过于苛求,要求精确的概念、确定的规范推导、唯一正确的规范意义。认为语言是法律内容的载体,语词具有固定的语义,可以借由形式语义学中的义素分析法确定法律概念的含义特征。米勒主张在阐释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时,将语言理论融入到法律实践当中。
(一)语言作为过程和法律作为过程
米勒主张意义并非与语言符号是固定的、唯一的。法律意义是法律人使用法律语言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创造出来的,并且依语境而变,因人而异。这些主张反映出米勒法律语言观具有鲜明的语用学特色。
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法律意义的建构还是法律人的语篇工作,都具有言语行为的特征。对于法律人/法官来说,他们并不能发现立法者的原意,而是在具体案件的语境中,对规范文本作出自己的意义解读。离开了具体案件对规范文本的意义解读,就不可能生成语义。而每一次的法律适用都是对规范文本意义的重新解读,这种意义具有动态性、不可复制性。国家可以通过特定的机构、特定的人员及法定程序来规范法律意义生成的过程,但谁也无法阻止这一进程。所有参与法律话语的人都不断地推动着这一进程向前发展。
米勒坚持法律语言使用的具体性,强调对法律文本在实际案件中的应用进行描述,主张法律意义来源于法律文本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功能,将语言作为过程和法律作为过程有机地融合了起来,为法律语言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二)法律语义的矛盾性与差异性
米勒的法律语言观同时揭示了构建法律规范/法律意义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争议。一方面,法律文本可谓是语义争斗的场所。对同一法律文本往往存在不同的,相互矛盾和竞争的诸多法律解释,这是由法律争议的根本特征所决定。案件当事人是不同利益方的代表,他们有着不同的诉讼请求,想要达到不同的诉讼目的,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寻找有利于己方的同一法律规定进行能够支撑自己观点的法律解释,从而赋予其不同的法律意义。任何以解决争端为目的的法律实践活动,如法庭上针锋相对观点表达、针对某一条文不同的法律解释、现实中“类案不同判”、“类案不同法”等等都是对法律语义争议性的印证。另一方面,法律人对法律文本的解读和意义并不是完全任意而没有边际的。作为法律实践活动的基本单位,法律人利用语篇实施判决言语行为,在判决的过程中建构法律意义。法律人在具体案件的语境中“争夺”法律文本的意义,表明语言的意义并非完全中立的现象,语言的所指存在视角化的倾向。对于法律语篇来讲,篇章理解早已不是理解法律语篇的意义,而是阐明语篇的意义,即怎样向其他人解释、阐明自己对语篇的理解。法官的任务或权力是在众多争议中决定最终采纳哪种意义解释,并将其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法律人在判决实践中清楚这一点,只是还没有反映在理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