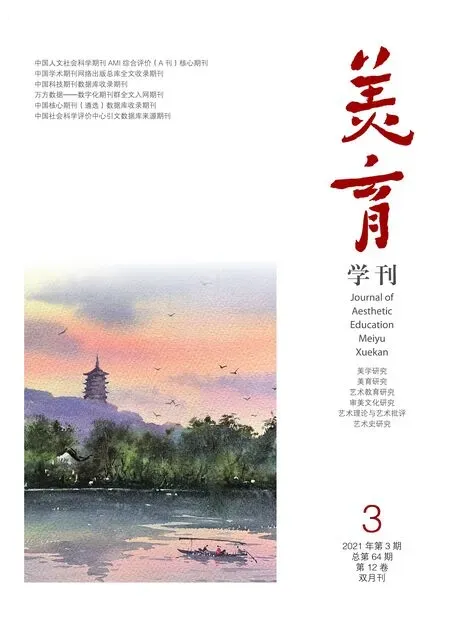中国当代艺术“中国化”问题的批评脉络
2021-12-03时胜勋
时胜勋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加强,中国当代艺术民族化、本土化、中国化诉求日益强烈,并集中体现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话语中。在历史上,陆续出现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气派”“中国化”等话语,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取代的,而是不断深化的。虽然表面看“中国化”更加科学化,更能表现出中国思想的特质,而“中国气派”则更多地侧重于外在形象[1],但是“中国化”的结果必然是“中国气派”,但不能因此就说“中国气派”仅仅是形象的,因为“中国气派”本身也包含精神性的内涵,二者不应割裂。
“中国化”的出现并不晚,毛泽东早在1938年的《论新阶段》中就提到了。在20世纪50年代也不时出现,比如潘梓年提出“哲学必须要有中国化的哲学”[2]。不过,此后关于“中国化”的讨论并不多见,直到8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才越来越多。“中国化”不仅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也发生在西方哲学领域[3],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探讨“中国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时间上看则更为后起。[4]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中的“中国化”并不局限于“中国化”这一显在的提法,也是对冠以“中国”的诸如“中国特色”“中国方式”等提法的总称,以此呈现中国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对其成因、内涵、问题的分析,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当代艺术文化与审美自觉走向深入,也有助于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话语权的提升,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当代艺术话语体系建设。
一、“中国特色”:从政治考量到学术拓展
“中国化”系列话语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特色”,与“中国化”相比,“中国特色”的“特色”就是政治性、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著名提法。在20世纪80年代,文艺界就使用“中国特色”,比如“中国特色的诗歌”。[5]这明显是受到了主流话语的影响。在文艺领域,“中国特色”一般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术”等。[6]受制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政治话语的内涵,艺术界使用“中国特色”也多着眼于意识形态方面,而单独的中国特色艺术则使用频率并不高,探讨也不深入,在学术界影响并不广泛。[7]今天也很少有“中国特色美术”这样的话题。不过,近几年“中国特色”的讨论则在更为学术化的艺术学领域有充分展开,诸如“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等。[8]这源于当代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与前述政治性的考量是一致的,不过更加偏重于学术性,尤其是相对于西方的话语权问题。
实际上,从语言使用角度而言,单纯的“中国特色”并无不可,只是在中国特定语境下,提到艺术的“中国特色”必然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批评、理论等)”,它鲜明地表达了中国艺术及其理论自身的主流性、政治性、意识形态特色。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缺乏学术性,而是意味着它自觉的意识形态以及话语权建构。不过,从内涵式发展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批评、理论)”这一称谓还有更多的内容需要加以充实,尤其需要兼顾政治性与学术性两个维度。
二、“中国方式”:策略的中国化及其争议
相比“中国特色”,“中国方式”就更为民间,也有很大争议。20世纪90年代初,栗宪庭用“中国方式”来概括当时出现的“玩世现实主义”“波普主义”。除此之外,还有“中国智慧”“中国形象”等提法,都可以归属于“中国方式”模式。但是,以“玩世现实主义”“波普主义”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在主流艺术界遭遇了持续的批评,“中国方式”的中国当代艺术是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吗?这引起了学者们的讨论。
批评者如邱志杰、王南溟等认为,“中国方式”属于“后殖民”,“中国方式”只不过是“中国符号”(“春卷”“打中国牌”等)而已,受制于西方中心论,这是在总体上否定了“中国方式”。[9]除此之外,对“中国方式”的负面评价还有“后东方主义”“细腰的国际主义”等提法,大部分将其纳入后殖民谱系加以批评。支持者有肖丰等人。2004年,肖丰、任建军将“中国方式”的技术前提概括为“借用”和“转换”。“借用”,就是“借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新的审美意象的起点或基础”。“转换”,就是“把原有文化资源中的某些具有‘符号性’特征的审美元素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视觉语言,在保留原有的审美特性的同时,显示出新的精神指向”,使人们在欣赏当代艺术的同时,又能领悟作品中文化的根源和脉络。[10]2006年,肖丰、任建军又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方式”的策略性价值,也回应了当时对“中国方式”的批评声音。[11]肖丰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也开展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国方式”的研究,有不少其指导的硕士论文涉及此问题,构成一个小型的“中国方式”研究学派。无论是批评还是支持,从学理性角度而言,“中国方式”既然已经存在,那就有其生存的某种合理性。批评家杨卫则将其与中国传统的退隐山林联系起来,区别在于前者朝向西方,但又表现了当代性,这就是当代艺术的“中国方式”,也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的“中国化”的当代艺术。[12]在笔者看来,遭遇了全球化之后,退隐山林就一定要变成“中国方式”,恐并非如此简单。
“中国方式”是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西方化之后的一种新策略,兼顾了西方当代艺术规则与中国艺术特色,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家几乎都涉足过“中国方式”,如谷文达、徐冰、蔡国强等。[13]“中国方式”就是将传统性、西方性、现代性(当代性)结合起来,其基本精神是现代性的,在其发展中,意识形态对抗性逐渐减弱,文化性、艺术性逐渐增强,因而具有较强的时代意义。可以说,“中国方式”是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与本土化阶段性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并且影响到艺术设计等领域。[14]可见,“中国方式”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与传播都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可一概否定。
此外,孙振华以吴为山的雕塑为例阐释了中国雕塑的“中国方式”,将“意”视为吴为山雕塑的核心词,通过“意”,吴为山“改变了20世纪以来中国雕塑的观念方式,使中国雕塑在重新发现传统的基础上,为建构当代的、本土的雕塑方式提供了可能”。[15]吴为山的雕塑表现将传统写意精神融入艺术实践的创作经验,体现“尚意”的中国艺术语言方式。这与当代艺术的“中国方式”(即玩世现实主义)并不完全一致,应该属于名同实异的“中国方式”。
三、“中国经验”:现代性的精神追求
如果说“中国方式”多对应于玩世现实主义、波普艺术,那么“中国经验”则对应于西南当代艺术,二者的矛盾性是比较明显的。“中国经验”原不用于艺术领域,而是指包括中国政治、社会实践在内的“中国经验”,主要是社会主义经验,后来用于艺术领域,这是王林倡导的,起始于1993年在成都举办的“90年代的中国美术:‘中国经验’画展”。这一展览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直到王林的阐释,才开始引起注意,属于典型的批评话语。
“‘中国经验’画展”共展出叶永青、张晓刚、毛旭辉、王川、周春芽五人的作品。当时展览主题定位“中国经验”。所谓“中国经验”,王林解释说就是“艺术家独立精神的体现,即对既定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现状的批判”,“是深度的批判的个人经验在艺术中的呈现”。[16]“中国经验”的提出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波普以及消费文化兴起对精神性的让渡而言的,是对不满于拷贝、复制西方当代艺术以及关注精神性、批判性的中国艺术实践的理论概括。在20世纪90年代初,艺术界已经感受到市场经济、后殖民文化带给当代艺术的挑战,提出基于批判性、现实性、精神性的“中国经验”自然是艺术界对现实的一种反应。批评家何桂彦指出,此次展览的美学诉求,“首先它力图与‘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拉开距离,拒绝调侃化、消费化的文化态度。其次,倡导‘深度绘画’,即关注艺术和人的联系性,不放弃终极理想和精神追求,把对现实情境的体验不断转换为精神发展的历史标志”。[17]显然,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始终存在着“中国经验”(西南当代艺术)与“非中国经验”(玩世现实主义等)的冲突。
1998年,王林以装置艺术为例提到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关注问题本身以及在艺术中关注中国经验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艺术的实践才具有“中国经验”的特质。“中国经验”是“当代中国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生存经验,它是局部的、具体的”,“中国经验”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强调多元性、多样性的价值。“中国经验”重视艺术家个性、个体思维、个性创造,而90年代兴起的观念艺术就是“中国经验”的一个突出体现。[18]
王林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经验”的研究与传播,进入21世纪之后也继续诠释“中国经验”。2003年,王林以西南当代艺术为例解释了“中国经验”的四个特征:一是“始终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注重生命意识、生存境遇与艺术的关系”;二是“重视内心体验和主观表现,和即时的、流行的文化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三是“看重历史性、时间性,以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个人经历作为资源”;四是“具有深度感和多义性,不以直接、表层、时尚的艺术效果为归旨”。王林理解的“中国经验”还包括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媒体变革,“90年代西南艺术家在观念艺术创作中对当代问题和媒介方式做了深入的研究,不仅扩展了西南当代艺术的领域,而且深化了西南当代艺术的人文精神”,“西南艺术家的创作不弃人文关怀、历史责任和主体追求”。在王林看来,当代艺术有很强的思想智慧与个体自由。[19]王林的“中国经验”诉求有很强的现代性内涵,与“五四”启蒙精神一脉相承,并非执着于对传统资源的恢复,注重的是当代中国艺术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复杂关系的创造性转化。
2005年,王林的文集《从中国经验开始》出版,使得“中国经验”成为一种较为系统、自觉的本土化话语。在文集前言,王林批评了东方主义,认为中国当代艺术表面繁荣的国际化可能堕入了东方主义陷阱,“西方选择和东方迎合的共谋性,将取消或改写东方文化的自身特质”。但是,王林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并不会重回传统的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而是促进文化多样性。[20]在此背景下,王林强调的是“中国经验”,是本土精神的当代阐扬,而非复古。“本土文化、中国经验和东方智慧”在东方主义视野中并没有自己的位置,有的话也只是边缘地位。王林强调的“中国经验中的文化智慧”对于回应中国当代艺术的后殖民倾向与西方中心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艺术界讨论“中国经验”,并未局限于西南当代艺术流派。比如画家杨渝诠释了90年代末以来中国艺术介入社会现实问题的“中国经验”,艺术创作也更加关注个体经验。[21]林世宾通过对“溪山引”展览作品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国经验”呈现与中国文化表达。他明确反对那种戏谑的、泼皮的、艳俗的、时尚包装的方式来进行“中国经验”呈现。关于中国文化表达,林世宾认为应该从林风眠、赵无极等人开创的道路出发,“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道路就是在现代背景下寻找中国艺术主体身份的努力,是中国开创具有人类未来文化意义在艺术上的表达”。[22]
此外,“中国经验”也溢出了艺术界,有一些学者介入“中国经验”的讨论,比如傅谨关于戏剧的“中国经验”的讨论[23],张柠关于莫言小说的“中国经验”的讨论[24],大抵都是强调中国艺术的本土性、民间性价值,但都还没有明确“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更多的只是一种口号。
“中国经验”不是一种封闭的、固定的,而是一种开放性的状态。关于“中国经验”的阶段,王岳川将其分为三大阶段:一是“纯粹古典高雅、逍遥自足的中国传统经验”;二是“经历了欧风美雨痛苦和希望交织的中国现代性经验”;三是“整合传统文化经验和百年西化经验变成自身的文化资源,纳入国际化学术文化资源和知识资源空间,用人类普世化的知识表达中国立场和中国经验”。[25]这三个阶段的“中国经验”可以概括为传统性经验、现代性经验和当代性经验。传统性经验是原汁原味的,现代性经验是西方化的,当代性经验是一种新的生成,是在西方化与中国性中找到适当的平衡。
“中国经验”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本土化的一种体现,多数并不是将其引到传统,而是更强调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与中国的现代性经验特别是特定的个体生命经验密切相关。当然,后来随着“中国经验”的泛化,一些与现代性内涵较远的内容也加入进来,比如社会主义、民族性、传统性的文学艺术本身的“中国经验”问题等。[26]这导致了“中国经验”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同时也可能意味着“中国经验”的无限扩大而面临着话语权的争夺,甚至概念本身的自我消解。
四、“中国版本”:立足文化血脉的自主性尝试
“中国版本”是2003年由陈孝信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强调传统性与当代性的融合,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方式”的升级版,但弱化了意识形态冲突的内容,相反增加了文化的内容。与这个概念相关的还有“文脉”“超写意”等词,共同构成了“中国版本”的完整内容。
在陈孝信看来,“文脉”是中国艺术实践长期积累、传承的“内核”,这一内核主要就是中国艺术精神。当然,“文脉”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诸如儒、释、道、民间等。这个“文脉”在现代中断了,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西化,二是中西融合,三是重复传统。西化自不必言,完全没有“文脉”,继承的是西方的“文脉”。中西融合也是缺乏“文脉”的,只是国际版本的“中国变体”,缺乏原创性。重复传统虽有“文脉”,但却是死的,不是开拓型的。陈孝信在否定了这三种倾向之后,提出自己的“中国版本”,所谓“中国版本”,就是对西方、传统的超越,这个超越强调创造性。这个“中国版本”的突出方面就是“文化个性”,即“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代艺术总体上的差异性和丰富多样性”。[27]即便在西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当代艺术也不一样,所以陈孝信提倡要“国别化”,而不是一味国际化,这是一种既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开放的民族主义的立场。
至于如何“国别化”,如何体现“文化个性”,陈孝信提出“扎根、利用、转换”三原则。扎根是深入传统,是前提,利用是途径、过程,关键是转换,实现对接、创化。转换就是对传统、西方的双重超越,从他策划过的“中国版本——超写意新艺术邀请展”(2003)、“中国版本——沪、宁、杭超写意艺术现象展”(2004)、“中国版本——2005北京邀请展”、“文脉当代·中国版本”大型综合艺术展(2007)等可以看出,这些展览的关键词是“中国版本”“超写意”“文脉”等。“文脉”是根,“超写意”是实践,“中国版本”是最终呈现状态。
“中国版本”是西方艺术本土化也是传统艺术精神当代化的双重体现,这种思路就是从“国际版本的中国样式”走向“中国版本的国际样式”。为了诠释这一“中国版本”,他做了很多个案的分析,比如谷文达、申伟光等,显然“中国版本”的当代性、艺术性要更强一点,而且文化性又是经过当代性、艺术性过滤的,因此才容纳了一些当代艺术类型。
五、“中国风格”:审美多样性的呈现
“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接近,但“中国风格”更加强调美学风貌,且属于后起话语。“中国风格”是2010年前后提出的概念,具有很强的主流性。2010年,“中国风格·时代丹青——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在广州艺术博物馆隆重开幕。这是首次以“中国风格”为主题的中国当代美术展。
为什么要提出“中国风格”?张晓凌认为有两个背景,一是20世纪90年代“渎神、泼皮、解构、艳俗之风广为流行”,这就是前文提及的“中国方式”,二是“晚明以来中国数代美术家所积累起来的现代性经验”,主要是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的中西融合风格。可见“中国风格”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与文化动因。“中国风格”的提出,也必然使得中国当代艺术自觉审视自我本土的现代性经验,同时应对西方化的冲击。因此,张晓凌认为在此背景下的“中国风格”其文化战略意图是明确的,一是反对后殖民风,二是总结中国百年现代性经验,三是建构有东方美学意蕴的中国当代性经验,最终“在全球化语境中,做大做强中国美术主体,并使其价值观具有普世性”。[28]
“中国风格”提出后得到了积极的学术回应,主要集中于文化立场与美学内涵两个方面。在美学立场上,卢禹舜认为“中国风格”“是美术的国家形象,体现了主流文化在当下创作上的指导意义,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在美术创作中具有主导作用,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在当代传承创新发展中纵向延伸为中国风格,有其历史意义”。张江舟认为“中国风格”“体现了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回归,是当代美术发展历程中对民族立场、国家意识的一种自觉选择,体现了一个东方大国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精神传统的尊重”。在审美内涵上,王镛认为“中国风格”体现为两类,一是写实风格,二是写意风格,抽象风格则很少。相比写实、抽象风格,王镛认为“写意精神是一种高度自由的创造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应该是构成中国风格的核心”。不过,王镛也强调不能唯写意,他认为现代艺术有两个基本特征,即“强化个性”“简化形式”,这实质上就是当代艺术的基本精神。陈池瑜则认为“中国风格”主要是写实风格,“打造中国美术的民族风格或者时代风格,现实主义是一个很好的、不可或缺的点”。尚辉认为“中国风格”就是“中国特色”,“是古今中外的一次整合,是一次新的更高程度的整合”。(1)关于“中国风格”参见《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中国风格·时代丹青——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研讨会综述》,载《美术报》,2010年6月26日。尚辉的观点应该是毛泽东“中国气派”在美术上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二者的逻辑脉络。
此外,与“中国风格”接近的是“中国风”,强调中国当代艺术要融入“中国因素”。聂琦峰将中国风分为三类,即传统观念+现代形式(如吴冠中)、非传统符号+当代社会性(如张晓刚)、传统符号的当代化(如吕胜中)。[29]由此可见,“中国风”本身就是复杂的。多数国人还处于第一类的欣赏层次,但就艺术家而言,要积极进行第二类甚至第三类的创作,这有利于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世界艺术潮流,同时又彰显了本土的创造性。
六、“中国精神”:对传统价值的艺术激活
对“中国精神”的讨论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民族精神或者“精神性”,比如文学界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30]以及油画界关于“精神性”(涉及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讨论等,[31]不过还没有上升到“中国精神”高度。21世纪初以后,“中国精神”的讨论逐渐出现,[32]也有相应的展览,比如2012年,“中国精神——油画风景学术研究展”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举行。到了2014年,情况有了显著的变化,“中国精神”成为主流话语。
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中国精神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一命题突出之处在于对文艺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维度的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中国精神”的背景是受到消费主义、全球化的挑战,本土价值观开始滑坡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关于文艺如何做到有“中国精神”,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四点,一是爱国主义,二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三是汲取传统文化资源(2)传统文化资源又集中体现在中国美学精神上:“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见习近平《在文艺座工作谈会上的讲话》,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1015/c22219-25842812.html,2014年10月15日。,四是学习借鉴西方优秀文化。由于习近平讲话是一个政治文本,因而具有很强的政策引导性,这对于扭转当前过于西方化、商业化的当代艺术趋势是非常迫切而重要的。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倡“中国精神”之后,此观念迅速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相应的展览、讨论不断涌现。“中国精神”也不再仅仅局限于风景油画,而扩展至更广泛的领域。2015年、2016年、2017年,“中国精神”第四届中国油画展分别以“心像”“真像”“抽象”为题展览,分别对应表现性、写实性、非具象性油画作品。油画三大形态与“中国精神”的关系是中国艺术对油画的百年筛选的结果,并非写实一类。杨飞云在肯定三大形态的价值之后,也反思了三大形态自身的某些问题,“写实油画泛起的图像化、精工化,媚俗(媚雅)化的实形主义,而冷静甚至缺乏真正的激情;表现性油画兴起的求怪求异的苍白表象与恣意宣泄,而弱化甚至放弃了情感的高贵而率直表达;抽象油画泥于语言之放,缺失形而上的内质追求,放言而忘意趣,空泛玄虚等,出现了在绘画语言和语言背后的文化观念、精神内涵、个人情感、民族传统积淀的关系失衡的现象”。[33]2015年,当代艺术家韦申个展举行,他也强调中国当代艺术“应该是注重中国精神的,应该注重东方文化的价值观”。(3)参见《韦申个展开幕 称中国当代艺术应注重中国精神》,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5/05-30/7311512.shtml,2015年5月30日。他的作品在荒诞怪诞、超现实主义中隐含了东方的自然自由精神。2016年,“‘中国精神’2016·中国百家金陵画展(中国画)”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彰显中国画面向现实、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艺术态度。2018年,朱乐耕在政协全国会议上提议要将“中国精神”融入当代艺术创作之中,并注重国家层面的导向机制。[34]这应该是比较明确地强调当代艺术融入“中国精神”的看法。
“中国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资源上的发扬传统。尚辉强调要“塑造当代美术的中国精神”,他认为“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有无相生、释家的虚斋坐忘,从来都是中国艺术的文化魂灵”,中国当代美术应从此再出发。[35]邵大箴强调当代油画的“中国精神”的综合路径,即“运用毛笔作画的,力图从国外艺术潮流中吸收营养,进行艺术变革;执油画笔与刮刀的,却在精神的旅途上,渴望向着民族传统回归”[36],这是中西融合的新创造。二是“中国精神”的美学内涵,邵大箴认为刘文进的“意象油画”尤其能够体现“中国精神”,使得“中国精神”更具体地落实在“写意精神”上。林笑初认为“靳尚谊探求中国画的笔墨形式与油画书写性表现,用油画语言探讨中国画的写意性与意境,对不同风格技巧和技法进行尝试,表现一种特有的‘中国写意水墨油画’”。[37]靳尚宜的“写意水墨油画”是“中国精神”的崭新体现。徐里不仅强调油画中国化的意象性、写意性实践,还吸纳了蔡国强、徐冰等人的艺术实践,放置在“中国精神”之下,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精神”的空间,也使其更具包容性、当代性、生命力。[38]
从总体上说,这些讨论都还比较笼统,都是宏观讨论,将“中国精神”引向传统、引向写意,但具体如何操作,还是缺乏细致的分析。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精神”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理论命题,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精神”的艺术化呈现也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并非一时一地所能解决。
七、结语:“中国化”话语的成绩与问题
以上对中国当代艺术“中国化”问题批评脉络的梳理,说明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都试图给中国当代艺术寻找某种“中国性”的价值,这种“中国性”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也涉及学术、审美、文化,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日益涌动的多层面的政治、学术、审美、文化自觉。在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语境中,“中国化”无疑彰显了文化的自我反思意识,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较好的批评气氛,形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中国化的时代潮流。
当然,中国化并非完美无缺,其问题也存在:第一,命名之间并不统一,关系错综复杂,比如“中国特色”的政治性如何与“中国精神”等的文化性融合为一,而“中国经验”与“中国方式”之间的明显对立如何整合,还有像“中国经验”“中国版本”的偏当代性与“中国精神”的偏传统性如何整合,等等。第二,“中国化”系列的主要问题是过于宽泛,切割不清,容易相互混淆。这些提法中的“中国”究竟是文化的中国,还是政治的中国,或者是艺术的中国?特色、方式、经验、版本、风格、精神,内部究竟有何差异?更突出的在于,这些话语几乎缺乏美学的定位,过于抽象,与“魏晋风骨”“盛唐气象”相比,特色、方式、经验、版本、风格、精神,仍然缺乏文气,灵动与韵味不足。用中国命名,更应该体现独特的审美风貌。因此,如何将“中国化”的美学内涵不断充实、完善、细化、丰富,是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第三,中国化与世界化、国际化的关系如何处理,如何克服狭隘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弊端以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寻找一种既能坚持本民族血脉,又具有跨文化性、世界性、人类性指向的中国化当代艺术,尤其是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以艺术的方式贡献自己的智慧,是中国化实践所无法忽视的问题。
无论是成绩还是问题,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走过40年的历程,中国整体的内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深化与中国当代艺术本土化诉求日益强烈的时代语境里,“中国化”对中国当代艺术内涵式发展与全球性推进都是积极而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中国化的中国当代艺术,才能以它独有的特色、精神、气韵,实现其时代性与世界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