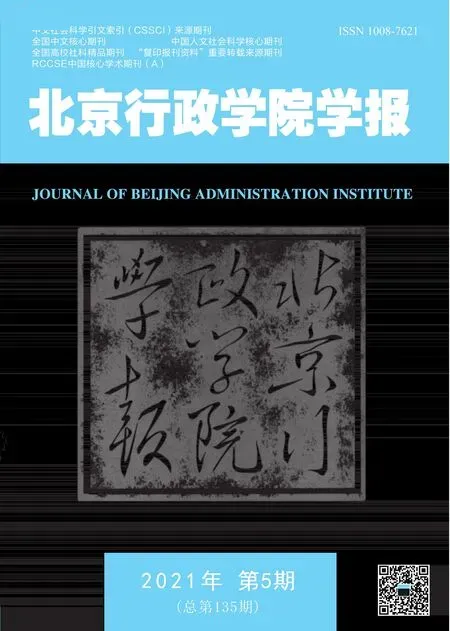中国移民历史变迁中的“新移民运动”治理: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2021-12-03陈静静
陈静静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引言
改革开放掀起了以大规模进城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移民运动”[1],体现出与中国历史上移民运动殊异的特征,又以多流动少转化的“半城市化”特征区别于世界其他城市化移民运动[2]。“中国城市新移民”也成为极具当代性和本土性的移民群体[3]。然而,主导性的移民理论及模型多建立在对西方社会少数族裔和国际移民的研究上,在分析中国新移民运动经验之时,难免有隔阂之感。因此,贴近中国经验,增强移民研究的情境性,就有必要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切入,寻找中国新移民运动及城市新移民治理的历史线索。
有研究考证,“新移民运动”开启于20世纪70年代末,流动人口增长率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达到顶峰,之后势头开始有所减缓[4]。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比2014年减少了约600万人,至2019年,再次比上年减少500万人①2015年至2019年我国的流动人口总量分别是2.47亿、2.45亿、2.44亿、2.41亿和2.36亿。数据源于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访问日期:2021年4月21日。。这一波动意味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进入调整期。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的数据显示,我国出现了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厅字〔2019〕56号),全面取消或放宽城市落户条件。中小城市户籍改革的全面推进,预示着中国的流动人口治理和城镇化政策进入全新阶段。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对于制度创新的影响。本文试图首先从历史的维度入手,在梳理中国移民群体的历史类型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新移民运动”的性质和特征进行分析;进而在移民组织形态从强制性移民、组织性移民到自发性移民的历史嬗变过程中,对所形成的移民治理制度的路径依赖予以考察;最后,结合“新移民运动”治理的制度变迁,对其打破路径依赖以实现制度创新的动因予以甄别和分析。
一、中国移民群体的历史类型及嬗变
纵观中国移民史,不同移民类型相继登场,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中国移民群体的八种历史类型
综合其迁徙动因、方向、意义及影响之不同,可将中国历史上的移民群体大体分为八种类型。
类型一:部族的整体迁徙。在华夏先民从游牧和迁移性农业转向定居性农业之前,族群迁徙现象非常频繁。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族群迁徙现象,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周时期,族群迁徙和人口流动开始频繁[5]。这一时期出现了政治和行政因素引发的整个部族的移民,如成汤八迁[6]。华夏族较大规模的早期迁移多呈现为两种路径:其一是为了追逐青铜矿源而进行的频繁性迁都[7];其二则是将所谓有“罪”的部落流放迁移到四方边远之地[8]。进入封建时代后,以汉族为主的北方人口,由北方黄河流域南迁至长江流域及南部更远地区。永嘉丧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触发的三次南迁高潮,引发了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部分从北方迁至南方的“客”户,在南宋时期逐渐形成一系,在语言与风俗习惯上,有别于当地土著居民和其他汉人,构成后来客家方言群体的主体居民。
类型二:知识阶层的流动。春秋战国时期,人口迁徙出现了新的类型。作为新兴知识阶层,士阶层不必依附土地,其求学游学,追求道统政统,本身就具有高流动性,加上各国争相罗致人才,以广纳门客食客为傲,加速了士阶层的流动。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流动,在促进学术思想空间繁荣的同时,也成为中原从割据走向统一的重要向心力量。汉代以后,流官体制和“任官回避”制度成为清晰的官员任用人事制度,进一步促进了士大夫在地域间的流动,对于文化传播,尤其是儒教扩散产生了重要影响[9]。
类型三:敌对政权之间相互的人口掳掠。游牧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战时和对峙期间对农耕人口的武力掳掠,常常让中原王朝感到困扰。秦汉时期,缘边地区被匈奴掳掠的吏民及被俘、投降的军官军士等数量的增加,使先后居于匈奴统治区的汉人总数至少有20万;鲜卑在北境崛起,数十年间掳掠不断,规模上不少于匈奴;唐代,突厥、吐蕃和南诏都曾大规模地掳掠汉民[10]。清军入关前对明数次战役,抢掠得数百万明朝官民[11]28。另一边,中原王朝也希望收编游牧民族以强固其骑兵力量。汉朝就挑选征召匈奴降兵骁勇者从军,成为精锐,拱卫京师;又置金城属国安置羌人,设羌骑校尉,统领收编羌人武装。收编后的北方游牧民族有时成为王朝重要的军事力量,可以左右王朝政局和生存,如唐代就以倚重蕃兵蕃将为著名。其后续对晚唐时期的政治局面影响至深,故而陈寅恪先生认为“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12]。
事实上,中国不过是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人口争夺战场的最东端。数千年间,生活在广袤的横贯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地区的交界地带始终处于激烈动荡的状态之中,草原征服与本地复兴之间交相轮换,构成了欧亚大陆历史进程的基础[13]。人口作为战争动乱期间愈发稀缺的资源引致各方争夺,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但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人口损失和秩序破坏,代价甚巨。
类型四:强制性内聚移民。封建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体现为强制性移民已经成为集权政权的一种制度性统治手段。秦以来,无论是统一中央王朝,还是地方割据政权,都建立和沿袭了运用行政或军事手段强制移民的政治制度。统治者将贵族、官员、一般民众——无论其来自己方,还是来自曾经的和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强行迁入新都、陵县、边疆等政治和军事要地已经成为一种统治惯例。以行政和军事手段为保障,这种强制性移民通常都能引发规模巨大、时间集中的移民行动,产生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后果。如对京畿的强制性移民自秦汉以降已然成为一个惯例。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14],刘邦采纳娄敬“强本弱末”之提议而“徙六国世家豪富10万口于关中”,刘秀强令民众东迁洛阳,董卓驱策数百万人口西迁长安,均是出于加强统治基础,增强京畿经济实力的考虑[15]。
类型五:移民实边。除京畿外,强制性移民的另一个方向是移民实边,在边疆地区施行屯垦。移民实边也是从秦汉开始成为统治常例。边疆地区缺乏农业基础,屯垦不易;外又有强敌虎伺,时有滋扰,故移民实边多少带有惩罚性和强制性。秦代开始,“迁”已经列入刑名,成为一种惩罚性的手段。公元前213年,蒙恬取河南地,军人屯垦有限,将犯官、赘婿、商人户籍者、祖父母、父母登记过商人户籍者、住在“闾左”的穷人迁往屯垦[16]。到汉代,一般类型及程度的犯官和家眷,会被判徙边,迁入地多为边疆或新设郡县。人数不够的情况下,会广泛征召平民迁入,但必须搭配奖励措施,比如拜爵或者免除徭役。西汉初年,晁错上《守边劝农疏》,其中提出的“徙民实边”之略就包括了对实边移民的种种禄利引诱,甚至丧偶者,政府也要给他们买一个配偶[17]。汉武帝时,“徙民实边”之略得以推行,从而开通了河西走廊,将中原农业带和天山以南农业区连接起来[18]。为将来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便利,对加强东方与西方的联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类型六:流民安置。妥善安置由于自然灾害、瘟疫、外敌入侵所导致的流民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安史之乱以前,中国人口重心在北方,黄河水小沙多,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民谚云“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水灾之年往往产生大量流民,如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移民。生态及瘟疫对人口及历史的影响近年来日益受到历史学界重视,极端气候导致粮食减产,社会矛盾加深,社会礼制崩坏,由此引发战乱。灾害和战乱又导致大规模人口迁徙,这时往往容易引发疫病流行,故而大的瘟疫常常爆发于王朝更替之时。而大的疫病,往往在造成人口损失的同时,也会引发人口外迁。如公元3世纪的建安大疫中,仅建安二十二年(217),建安七子中就故去了四位[19];元末,北方爆发鼠疫,也造成了华北平原,甚至波及四川的巨大的人口损失,加速了元的灭亡。
类型七:从“狭乡”往“宽乡”的经济性移民。“狭乡”指土地资源紧张的人口稠密区,当土地负荷不了人口增长的时候,人们会自发迁往“宽乡”以求生存。汉代关东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狭乡,民众自发南迁垦殖。为了缓解土地压力,维持地方稳定,拓疆辟土,开掘税源,政府也会组织民众迁往宽乡垦殖。宋以前,中国人口规模长期在七八千万上下徘徊,自发移民多缘于战乱和自然灾害,经济性移民较少。宋代,人口剧增,北宋辖境在徽宗时户数已达2000万户以上,人口总数超过1亿,出现了局部劳动力的过剩和流出。对此,政府有所体察,也会对外迁人口予以组织和调度。皇祐二年(1050),北宋朝廷就曾下达诏令迁南方狭乡人民到北方垦荒[20]。宋以后,国家组织调度“狭乡”往“宽乡”的经济性移民成为常例。经济性移民还包括了清代中后期著名的“走西口”和“闯关东”。内地土地兼并加剧,人地矛盾凸显,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故土难以生存,选择了向塞外移民,形成了清代中后期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潮。
类型八:农业时代的“乡城”移民。农业时代城市发展有限,即使地区人口不断增长,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却变化不大。除战争毁灭、迁都等特殊情况外,从汉代到清代,县级建制以上的城市基本保持在1300到1500个。虽然历代都城空间规模和人口数量在世界古代城市史上独树一帜,但是10万人以上的城市也长期只保持在十余个或稍高[21]。明代实现了产业结构的突破,长江三角洲成为棉业和蚕桑业的中心,产业突破促进了农村人口进入市镇并投身手工业,由此催生了许多专业化的新型市镇。明末江南地区的市镇数量和市镇人口都有了大幅增长。清代废除匠籍,加之实行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税制改革,产生了一些大的手工业产区。清后期,江南和广东部分地区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加之洋务运动和民族工业的推动,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加速,大批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城镇定居,成为“乡城”移民,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及其他行业。
纵观移民历史,封建时代的移民经历了从强制性移民到组织性移民,再到自发性移民的类型嬗变。到封建时代晚期,采用行政手段强制大规模移民已经不再是主流做法,而是更多体现为政府倡导、组织或招募人口从“狭乡”迁入“宽乡”和不发达地区的运动。比如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就是明清两代持续组织周边省份向四川移民的人口迁徙运动[22]。清末对明朝以羁縻形式控制的西南苗疆、川边藏区、云南展开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也在湘西、鄂西南山区、陕西南、贵州、云南形成了数百万人口西移的移民潮[23]139。
总之,封建时代晚期的移民运动呈现出一种组织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融合的特征。移民开发边疆同时实现了“狭乡—宽乡”的经济性动机和实边御侮增加政府财源的政治性动机。如果政府实施宽松的鼓励政策,又能够提供有效而持续的激励和保障,移民运动就能产生快速且强固的效果。晚清开放东北和台湾所引发的移民运动就是如此。鸦片战争后,沙俄不断侵蚀东北边境,攫取大量领土;而执行封禁政策之东北则人口空虚,清廷遂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抵御外侮,振兴关外经济,由此展开了大规模东北移民垦殖的序幕[24]。清末对台移民亦体现出民众对生存和发展机遇的追求与统治者鼓励移民之政策相配合所能迸发的活力。清代向台移民的做法,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时就已开始;乾隆二十九年(1764)取消不得携妻入台的禁令,掀起向台移民的高潮;至嘉庆时期,台湾内地移民已有长足增长。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廷采取积极经营方针,在沿海创办招垦局,招揽贫民赴台开垦[25]。
(二)封建时代移民政策的特征
我们应该看到,直至19世纪后半期之前,无论迁移是源自强制、鼓励,抑或自发流动,也无论迁移的方向为何,移民大抵不过迁移至异地务农,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业态转变。而随着近代工业化和早期城市化的进程,从20世纪上半期开始,自发性的、由乡村流向城市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的移民才成为主流。封建时代移民政策体现出三个鲜明的特征:
其一,当政者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以实现对人口流动的严密管理。农耕文明国家的收入极大依赖于田赋与丁银,户籍制度较为严格。秦自商鞅变法后就实行了户籍登记,严格控制百姓迁移[26]。由秦至汉,需要迁移的人必须向官吏申请更籍,并随身携带文书备查。战乱时,户籍隐匿严重,但新朝初立之时,往往对户籍予以整顿,限制人口流动,如洪武十四年(1381)后执行的里甲制和关津制[11]8。
其二,移民政策的制定及调整主要基于政治性考虑。在控制人口流动的大前提下,封建国家形成了管制和组织流动人口的各项制度与成规,主要服务于中央集权、开疆拓土、稳定统治等政治利益。到封建时代晚期,开发财源的经济性目的也成为主要考量。但是,即便是“湖广填四川”这样大型的开发移民运动,其中政治色彩也相当鲜明[22]。
其三,移民政策体现出超越王朝更迭、较为强固的路径依赖。如内聚性强制移民政策就延绵千年,尤其在战争和政局未平时被普遍效法。如明代对所谓地方豪强或富民的强制性迁移,就曾被称为“师古之举”。明朝初年,朱元璋在该问题上是否循例还一度有所踟蹰,称“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汉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至事有当然,不得不尔”[27]。对城市政治功能的极大重视,及对政治中心城市予以包括人口在内的资源倾斜的传统,对后世城市的治理影响深远。
又如圈地恶政,从元代到清代也体现出某种承继性。元代,虽耶律楚材否定了“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的提议,甚至拉锯之下,到忽必烈晚年,不准任意扩展牧地已为成规,也处理了一些恃势强占民田的事例,但扩展牧地事亦有存在,不断也有坚持扩展牧地的顽固派屡次请广牧地,并禁秋耕[28]。但清入关后,似乎并未考虑元代的圈地教训,顺治朝直隶各府被圈土地不少于五分之一[23]51。圈地运动导致京畿地区农民流离失所,直至康熙亲政,才下令停止圈地[29]。
上述对于移民历史政策与群体的简单回顾,对于考察“新移民运动”政策沿革具有特殊意义。
二、“新移民运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催生的移民新类型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化布局决定了中国城市移民的方向。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促使我国在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新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区,催生了一批工业城市。为此,城市人口由政府进行集中配置,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除了由原有工业基地支援新兴工业区发展带来的人才转移和输送外,也有大批农业人口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一员。
随后的“大跃进”运动中,全民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农业人口大批涌入城市。1957至1960年的三年间,农业战线的劳动力减少了4000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迁入城市。新增人口造成了城市粮食供应紧张,最紧张的时候,国家粮食收支逆差达168亿斤,全国粮食调运只能完成计划的15.3%[30]。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做出政策调整,一方面,采用下放城镇人口的方式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31],另一方面,建立收容遣送制度,限制人口自由流动。1961年,公安部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同年,国家设立了收容遣送站,先后将大约2600万进城工作的农民遣送回农村继续务农,以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和重工业发展[32]86。
改革开放开启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农村本就存在的劳动力过剩问题进一步凸显。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安排,当时普遍认为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实现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国家不支持跨省的异地流动与乡城流动。进入9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劳动力需求更加旺盛,国家准许农民在不改变身份及城市供给制度的前提下,进入城市工作,由此民工潮全面兴起。1994年,粮油定量供应制度取消,促进了随后几年远距离,以大城市为流入地的农村人口流动潮。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流动人口增加1亿有余。之后,增长的趋势明显放缓。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出现了绝对数下降,结束了流动人口连续37年的增长趋势,此后开始缓慢下降,这一趋势预示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进入调整期。应该说,这场“新移民运动”在中国移民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新类型。
首先,“城市新移民”是在和平发展时期由经济动因驱动的自发性移民,这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性移民,如强制性内聚移民、边疆移民区别开来;也与因灾害和战乱而出现的大型移民运动,如部族迁徙、人口掳掠和流民区别开来。“新移民运动”表明,人口的经济性自发流动正日益取代国家的计划安排而成为“乡城”移民的一种主要方式。
其次,“城市新移民”与历史上从“狭乡”往“宽乡”的自发或者组织性经济性移民也有所不同。“城市新移民”面临着业态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与历史上的自发经济性移民相比,承受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三重冲击。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城市新移民”与明代中晚期出现的另一种“乡城”移民亦有所不同。依照“资本主义萌芽”之成说,农民的隐性就业不足,因而转变为手工业者或工坊工人,实现了人口在农业与工业,及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迁移。以此种逻辑来看,“新移民运动”似乎是中世纪晚期的“乡城”移民传统接续后的某种“自然发展”。但是这种推断忽略了“新移民运动”出现的城市工业化和全球资本的逻辑。明清时期,在农业生产内卷化和农业商业化的影响下,乡村手工业和手工业集镇获得了发展,但无论是产业还是从业者本身,都从未获得脱离农业的独立地位[33]。乡村与手工业集镇之间的人口流动是季节性、商业性的,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历史学家刘铮云曾经在档案中发现了清代不少商贩、农人和工人的流动事迹,“与传统中国社会人们习于安定,安土重迁的观念相左”[34],从而对传统社会空间流动滞塞之说提出了质疑。明清时期乡城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人口流动迁移,仍然建立在经济作物的农业生产及手工加工业之上,后者作为农业生产的副业存在,补充农民的就业不足。即便存在相当规模的农村人口迁居集镇的现象,其生计与社会关系依然与农业和农村密切相联,这种双重联系不仅为“乡城”移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提供了甚为重要的社会支持。而工业化所驱动的“新移民运动”并不具备这些社会性因素,因此“城市新移民”在城市中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社会融入难题。
三、“新移民运动”治理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通过对移民治理制度变迁的梳理,可以看到高度依赖政治力量、带有强制性色彩的移民管理制度体现出较强固的路径依赖,其影响不仅横亘整个封建时代,其后续所及,也对当代“新移民运动”的治理乃至制度创新产生影响。
(一)硬控制:“新移民运动”前期治理及其路径依赖
既往研究多强调对流动人口的“硬管理”是计划管理政策的产物,但若结合对移民史的考察,恐怕也需要考虑到对自发性流动严格管制的政治历史传统。一些社会史学者倾向于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的叙述中寻找内在的连续性,而不仅仅是关注其断裂[35]。在这个意义上,对新中国成立后移民政策的考察,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语境性因素予以考虑之外,还有必要分析移民政策历史遗产的复杂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被纳入计划经济模式,国家曾组织农村人口迁入大中城市及新型工业城市,但因目标过高及执行操切,遭遇了挫折。改革开放催生的“新移民运动”开启后,虽然亿万农民工已经在事实上实现了跨省市流动和“乡城”流动,但这在当时仍然被认为是非常态的、短时态的,具有不稳定性和潜在社会风险,于是政府沿袭成规,实行了“硬控制”,由公安部门和(原)计生部门执行治安控制和人口控制。
以1994年(原)劳动部发布《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1995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和1997年4月成立流动人口专门管理机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为主要标志,国家逐步建立了基于暂住证、就业证、收容遣返、本地就业优先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流动管制政策。有研究统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全国每年被收容遣送的人数以百万计;收容遣送制度与暂住证制度曾经严重侵犯流动人口人身自由和人身权利甚至给许多流动人口带来巨大的痛苦,恐惧和耻辱[32]83。对流动人口的强硬管制政策受到了广泛质疑与批评。
(二)软治理:“新移民运动”治理的制度转变
2002年以后,为了统筹城乡发展,我国政府对于流动人口的管制方式开始发生转变,从部门管理转向政府管理,从控制型管理转向服务型管理,对农民外出务工采取了积极引导的政策,要求各级政府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2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首次明确了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十六字方针,并提出要纠正简单粗暴清退农民工的做法,健全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劳动合同管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2003年,因“孙志刚事件”引发巨大的社会关注和争议,收容遣送制度实施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同年,国务院以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取代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制度。2006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中央政府首次全面系统阐述涉及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变、土地承包权益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2015年以后,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相呼应,流动人口总量回落,如何促进劳动力社会性流动、稳步推进城市化成为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考量。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意见》要求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推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推动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城镇倾斜。该政策标志着流动人口宏观管理政策的重大突破。在原有的服务性政策重点,即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基础上,综合运用放松户籍制度、设计综合性财政杠杆,尤其是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等政策,鼓励输入地政府吸纳农村转移人口。
由上可知,对“新移民运动”的管控政策在2002年发生了明显转折。此前的“硬控制”,主要依托户籍制度及其他差别化制度矩阵,如社保制度、教育和医疗制度等,通过行政命令严控大规模人口流动,对流动人口市民化持保守态度。2002年后,流动人口治理模式开始了“软治理”的渐进式探索和建构。首先,在治理理念和思路上推动从管控到服务的转变;其次,对社会矛盾集中的管控制度予以废止,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在地服务和社会保障;最后,逐步清除限制人口流动的核心制度障碍,如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
(三)“新移民运动”治理的制度创新及其动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具有核心意义的制度创新的实现往往伴随着对路径依赖的突破。但试图打破路径依赖并非易事,“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36]。
“新移民运动”的治理也一度受到“硬控制”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对流动人口在制度上的严格管控和区别化对待延续达20年之久。而且,流动人口的社会问题化也进入了公共话语,如早期“盲流”这一污名化称谓的广泛流传,一方面为“硬控制”制度的延续提供了话语资源,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路径依赖在社会意识和文化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之后的流动人口治理制度创新的实现,远非单一领域的政策转向,而是一系列语境因素和制度变迁的综合结果。
首先,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流动人口体量迅速增加,流动人口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贡献获得了认可,政治地位得到确定。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外迁的冲动,共同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移民潮。随着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由流动人口所提供的低廉劳动力和国外资本、全球贸易、巨大市场一起推动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37]。
其次,在新公共管理的治理思路下,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政府职能改革的目标,整体的治理体系及话语的变迁推动了流动人口治理制度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行政学界开始对当代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新做法予以介绍,在一系列被称之为“新公共管理”的举措中,提高行政效能,改善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增强公共服务对公众需求的反应力受到普遍重视。2004年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首次在中央层面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概念;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①参见《服务型政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134999/135000/8105875.html,访问日期:2021年4月8日。。此后,服务型政府顶层规范设计,进一步推动流动人口治理政策话语从“管控”转向“服务”。
最后,流动人口主体认知的形成,在公共话语和文化层面推动了流动人口群体呈现模式的积极变化。2000年以后,第二代流动人口开始走上新世纪的历史舞台,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他们缺乏农业生产经验,对都市生活有着自己的理解,与他们父辈相比,对市民身份拥有更强烈的渴望。然而,户籍及其他社会排斥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影响下的社会偏见和污名化,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身份焦虑[38]。有学者所描述的“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的情况,在新一代流动人口中有着更为突出的体现[39]。
普遍的个体困局促进了新兴打工者主体认知的形成[40],集体意识的唤起和群体身份的确证与日益高涨的自主表达互为表里。打工文学、打工诗歌、打工戏剧与新工人摇滚等不仅记录了打工者的处境和历史经验,更在创作与表达中对造就自身经历的总体历史进程进行了反思。这种自主表达,对于改变流动人口群体一体化(unifying)与单一化(homog⁃enizing)、非历史化(dehistoricizing)与非人化(dehu⁃manizing)的阶层形象及地位[41]起到了正面作用。
新工人主体的自主表达传达了立足底层劳动者的立场和追求公平正义、捍卫劳动者尊严的价值追求,不仅推动了主体的形成,也促进了公共话语的转变。大众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取向和话语框架都发生了变化,开始有学者用“新工人阶级”替代“农民工”成为新的命名①进入新时代以来,有学者以“新工人阶级”作为取代“农民工”命名的表述。参见黄典林:《从“盲流”到“新工人阶级”——近三十年〈人民日报〉新闻话语对农民工群体的意识形态重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年第8期;潘毅:《关于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一点思考》,《人间思想》,2015年第10期。,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背景下,对社会公正的伦理追求,给予劳动者有尊严的待遇和法律保护成为社会共识。
结语
“新移民运动”治理突破“硬控制”的路径依赖以实现“软治理”的制度创新,是制度矩阵综合变革的结果。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更深刻地融入全球化经济秩序的经济背景,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政治背景;另一方面,与“新工人阶级”主体的自主表达,及其对公共话语及社会文化产生的积极影响有关。二者的合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高度连续性的移民制度传统,使路径依赖有所断裂,实现了中国移民治理的制度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争取在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所突破,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如何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实现城市新移民治理的协同创新,成为近期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焦点议题。通过从历史维度关注移民类型及其管制治理制度的变迁,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对晚近城市新移民运动治理的制度创新动因进行分析,本研究认为:一是需要继承应用新时期制度创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成果,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治理理念为基石,推进城市新移民权益保障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尤其需要考虑建构与新城市移民社会治理理念和政策相配合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意识,对“新工人阶级”主体形成所引发的公共话语和社会文化变迁予以重视,推进共建共治共享,促进广泛参与的城市新移民社会协同治理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