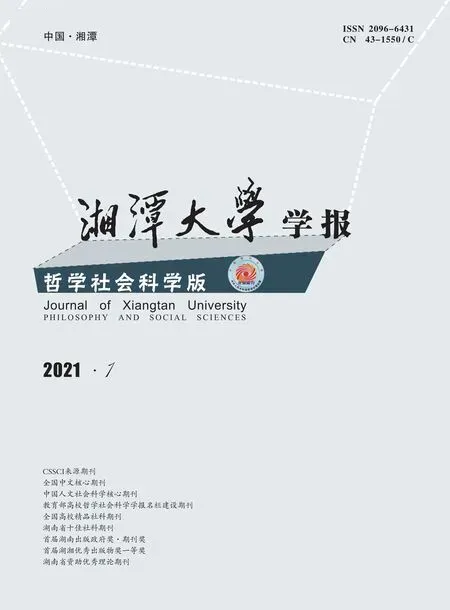黎锦明:一位中国新文学的助推者
2021-12-02陈以敏
陈以敏
(湘潭大学 图书馆,湖南 湘潭 411105)
湘中望族,湘潭长塘“黎氏八骏”中的六老爷黎锦明,在20世纪20—40年代,经常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洪水》《北新周刊》《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一般》《幻洲》《申报·自由谈》《青年界》等报刊发表大量小说、译作、时论等,出版有《烈火》《尘影》《雹》《破垒集》《马大少爷的奇迹》《蹈海》《战烟》《琼昭》《新文艺批评谈话》《文艺批评概说》等,“连理论也包括在内,前后有二十一册的数量”[1]86小说集和文学论述,颇有声名。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没有完全整理结集出版,仅仅在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黎锦明小说选》,收入中短篇小说23篇;1987年香港南方书屋出版社出版了《黎锦明中篇小说集》,收入中篇小说4篇。学界对他的研究也不够全面和深入,截至2020年5月7日在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以“篇名”为“黎锦明”,匹配方式为“精确”条件检索,仅有18条记录,文章对他的评价定位也不一。从现有知网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看,新时期最早有康咏秋1983年《试论黎锦明的思想和创作》,再主要有贾剑秋《湖湘文化的解读者:黎锦明小说地域指认性论略》,孟方《黎锦明小说艺术特色》,王吉鹏、孙晶《鲁迅与黎锦明》,硕士论文:杜悦英《走出“湖湘世界”——黎锦明小说创作特色论析》,陈丹蕾《黎锦明小说创作论》,余珊《黎锦明与革命文学的关系考察》等,都是立足于黎锦明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中篇小说《尘影》的作者,其创作得到了鲁迅的充分肯定,他是在五四新思潮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但创作思想庞杂多变。定位他为湖湘文化解读者,中国20世纪20 年代乡土文学创作中重要的作家,进步的现实主义创作者,旧中国那些热爱祖国、追求进步而未能与人民革命事业相结合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一些相关著作介绍黎锦明时,多按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把蹇先艾、裴文中、许钦文、李健吾、王鲁彦等人的作品概述为“乡土文学”。湘中作家黎锦明“很少乡土气息”,而作为乡土文学作家被简单介绍,或许是因为其“作品中有一股不可遏止的激情,或突露,或潜抑地奔涌于字里行间,写人状物,编构情节,都为激情所左右,这就是鲁迅所赞许的‘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在这一点上,黎锦明或许与田汉相类似,他们都是浪漫型的湘籍作家”[2]160。
因此,借助图书馆、文献传递、瀚堂近代报刊数字资源库等电子资源,笔者在遗散的黎锦明作品中摘取他的几篇时论、文学作品,来追踪其如何跟随新文学的前驱者呐喊助威,来感知了解其思想经历和演变,及其文学创作发生发展的情形,以历史视野解读黎锦明新文学文艺观的现代性特质,探讨他如何成了一位中国新文学的助推者。
一、黎锦明“说自己的话”的白话新文学实践得到钱玄同的支持
黎锦明(1905—1999),1924年开始发表小说《徼(侥)幸》《社交问题》,1925年一年间,在北京师范大学预读、年仅20岁的黎锦明,就在《晨报副刊》《莽原》《京报副刊》《小说月报》等发表了约50篇小说、译作、时论,准备将短篇小说结集为《烈火》出版。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广东、香港工人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举行“省港大罢工”,亲历这些事件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文化人,迫切希望创办一种进步刊物唤醒被封建专制文化荼毒而麻木、愚昧的底层民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暴行,因此1925年9月16日《洪水》半月刊自1924年8月20日创刊仅出一期停止后再次开办,第一期到第二十四期的总编辑是周全平,第二十五期后由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接手编辑。[3]关于这一事件,黎锦明在1925年10月24日、25日,11月18日《京报副刊》分别发表《阅〈洪水〉第一期后》《答二龙坑钟隐先生》《声明》,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且作出“关起门读几年再说”的决定。在《阅〈洪水〉第一期后》文章中,他对宣传创造社复活的《洪水》编辑不是郭、成、郁,没有领略到他们复新的文字感到失望,“《洪水》的精神使我太迷离惝怳了。”并认为,头一两篇文章,化名为霆声的周全平的《论是非》,是对新旧文化近乎“折衷派”;洪为法《漆黑一团》“旧话重提,拿创造社的招牌,诚心向文学研究会挑战罢了”,新旧思想夹夹杂杂。在《答二龙坑钟隐先生》文章中,黎锦明批评周全平《论是非》“霆声先生批评新旧思想说‘只有好的才是好的,坏的才是坏的’”这句话轻率、浅薄。他批评:“现在有一班所谓有大思想的刊物,——我现完全抱反感——全然是些刻薄的态度”,并说“我写文字是被理性所驱使,我虽然只有二十岁人,虽然没有学识,然而我却常时用我的思想。”在《声明》一文中,黎锦明提及他跟钱玄同一起在一次与其兄长黎锦熙聚会谈笑中误以为受到钱的嘲笑,加之发表《阅〈洪水〉第一期后》,有人说他文章吊英文尾巴,受到针对他个人的大声恶语斥骂,所以,年轻气盛的黎锦明声明,要做个小小的艺术叛徒,“现在决定不进什么学校。预备买几本原本书跑回我那故乡,关起门读几年再说”“劳北大刘握青先生慰问,我在这里声明感谢。”
黎锦明发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文章,引起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钱玄同的注意。1925年钱玄同与黎锦明的大哥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过《国语周刊》,对黎锦明自然不陌生。1925年11月23日,钱玄同先生在《京报副刊》发表了《给黎锦明先生的信》,信中钱玄同解释了在11月11日和黎锦明大哥黎锦熙、孙伏园等诸位给《儿童周报》庆祝三周岁时,跟黎锦明顽皮说笑产生的误会,这种单纯的误会解除后,因为新文学观点讨论,两人更加拉近了关系。在这封信里,钱玄同直白无忌说明了对黎锦明作品的评价,有爱读也有不爱读的,“老实说,自然也有不满意的;但是我从没有向您起过不敬(即看,起也)之意,因为您的作品,的确是黎锦明自己的话,不是学这个人学那个人的舌。”如同当世做白话新文学的文学家,只要是说自己的话的,他都是有敬意“不问其为胡适之,鲁迅,周岂明,郁达夫,叶圣陶,谢冰心,俞平伯,朱佩弦,许地山,郭沫若……”钱玄同时年39岁,长黎锦明19岁,和黎锦熙一样以语言学家见称,他在给黎锦明的信里反复强调“说自己的话”,体现了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新文学现代性,表明钱玄同对五四强调个体独立精神的坚持,[4]对青年黎锦明的爱护和援助。
钱玄同公开发表的信让黎锦明惊喜不已,作品能得到钱玄同的关注和看得起,这让他不曾想到,自然十分欣慰。1925年11月25日黎锦明在《京报副刊》发表《答疑古玄同先生》说:“我记得去年从十月到今年三月,这个时期内差不多是我全花费在写小说的时候,平均每星期有一两篇东西写成。然这也是我过于不幸的地方,我的生命力除开逼迫着我写外,曾不会教我怎样能判别一件作物是好是歹。”检讨自己花费时间写作数量多,过于急促不谨慎就发表作品,需要有人监视自己的发表动机。对编订的《烈火》集不满意,小序也写得乱,有机会还要努力写几篇凑上去。并回应有些人“学舌”“捧腿”的原因及自己的看法,指出郭沫若先生“他固然不能和鲁迅先生一样站在民众前面呐喊,然而他那自认定的sentimental的主义,当然能得到大多数的青年敬视、悦服……”这些表明黎锦明是白话新文学(化)运动中的一员猛将,富有朝气蓬勃的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精神,他做白话小说,跟随支持鲁迅、郭沫若、黎锦熙、钱玄同等新文学先驱的白话新文学倡导,反对章士钊“思想昏瞆(聩),言动疏狂”[5]的复辟文学,因为“白话文的提倡,可以直捣封建势力的壁垒”[6]1,它能充分地、自由地表达现代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表现。
二、黎锦明声讨吴稚晖
以上可以看出黎锦明有鲜明的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立场,他同样参与政论,有鲜明的政治革命意识,尽管他自称一个闲人,什么党人也不是。1928年他在潘汉年主编的创造社后期刊物《幻洲半月刊》下部“十字街头”发表署名黎君亮文章《吴稚晖与被杀青年》,“代枉死的青年们吐一口冤气”[7]351。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于1927年4月12日在蒋介石率领下,用武力“分共”,拘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会领袖。后来国民党当时的左派领导汪精卫于1927年7月15日也改变原有反对“分共”的态度,以和平方式“分共”,国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失败。 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的七一五清党行动,这两次反革命政变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政变使得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也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无数革命者不幸被捕被杀。1927年11月,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民国日报》连载长篇清党运动檄文《读了汪先生〈分共以后〉的赘言》[8]185,黎锦明冒着政治风险,不顾个人安危,给潘汉年致信——《吴稚晖与被杀青年》,文章声讨吴老文豪“骂共(产)党固来骂得痛快,但恐怕那些被冤枉杀的无辜青年鬼,要来向吴老索魂哩!”[7]350他为自己学校两个姓陈的青年学生被指是共产党,亲眼看见受酷刑后被杀,不管会骂反革命那许多,嘱汉年兄公开发表《吴稚晖与被杀青年》。自然,《幻洲半月刊》1928年1月出至第2卷第8期后被国民党以“宣传反动”之罪被迫查封停刊,共发刊20期。黎锦明和鲁迅先生一样,用自己的笔面对现实,尖锐、直接进行了新文学具体的思想政治斗争,站在民众前面为枉死的青年吐冤,为社会正义、为民众呐喊,“为民族的革命的光明做了许多宣传文字”,[1]84其思想成熟,文风凌厉,具有新文学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的现代性,且勇猛无畏,可敬可贵。
三、黎锦明的现实主义写社会新文学文艺观
对于创作,黎锦明认为作品要真实,要扫除无病呻吟。[9]436他自言他的生命都在他的文字里,如果只讲讲恋爱,一个人这样的在中国生活着,似乎不太值得。1926年3月黎锦明《让咱们来说几句和平话》[9]说:“作家先要‘固守本位’;自己没有触过农民生活的而偏要去写农民的灵魂,自然会变成庸俗;还有一种全凭空想所写的恋爱小说,如何曲折如何做作还是逃不了明眼人的认识,所以这种小说也只能给小姐少爷们‘涕泪潜(潸)然’而已”[9]436。对徐志摩的《老李的惨史》纵使成功,也不敢恭维,认为老李只是死得奇怪,并无一点惨,不真实。[9]436在《序〈青年李兰亭〉》说“我跑到什么时候,地方,就可以写出在什么时候与地方的李兰亭”。[10]事实也是这样,1926年9月,经介绍,他到了广东海丰中学任教,即以海丰农民运动为题材,1927年10月7日写成中篇小说《尘影》,这是描写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生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反映现代农民运动的小说”,鲁迅为他作《尘影序言》[11]。最为人熟知的是鲁迅序言中说“然而在结末的‘尘影’中,却也给我喝了一口好酒”,其深意用“一口好酒”表达。《尘影》与鲁迅的小说《药》比较,作品结尾有着无言而又惊心的相似之处,感觉像喝了一口好酒一样,激起清醒,令人振奋。《药》中被杀的夏瑜即是托写在绍兴轩亭口被杀、为革命献身的秋瑾女侠,以姓名夏和秋、瑜和瑾相对应。秋瑾丈夫王廷钧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家境殷实,富甲一方,秋瑾在湘潭住了8年,秋瑾一心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被清政府杀害,于1907年7月15日凌晨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在湘潭的大街小巷至今传诵“鉴湖女侠几堪豪,不惜千金买宝刀”。秋瑾后人存有同学录显示,抗战前后黎锦明父亲黎松庵曾在湘潭新群学校执教,新群学校距秋瑾故居步行距离不远,1937年8月该校增设初中部,秋瑾的儿子王沅德(重民)任校董,为躲避战乱,1941年春,这所学校搬迁到株洲大冲,校舍就设在秋瑾夫妇的槐庭别墅,是秋瑾儿子王沅德捐赠的。可以说绍兴的鲁迅和湘潭的黎锦明都对秋瑾是有深缘的,他们的小说《药》《尘影》都有秋瑾的影子。鲁迅《药》写华、夏两家,华夏就是中华民族。华大妈和夏四奶奶为儿子上坟,对比写照革命者死后未觉醒的、愚昧的亲人不能理解的痛心与悲哀,更别说看客的无情冷酷、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和“享用”牺牲。《尘影》熊履堂沉着镇定,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履堂的颈上三道血直喷了出来”,据秋瑾后人说秋瑾是惨遭刽子手挥刀三次。鲁迅《尘影序言》:“谁更为仁义和钞票写照,为三道血的‘难看’传神呢?我看见一篇尘影,他将愉快和重压留与各色的人们。”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尘影》结尾“惟(唯)死者的孩子小宝,正当那时从幼稚园放了学出来”,孩子们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12]290。强烈的反讽意味无疑非常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虽然革命者牺牲了,但这绝不意味着革命的彻底失败,[13]“花环”和“小宝”都是新的希望。熊履堂是当时小说难得的农民运动领袖形象,是为争取理想社会而参加到实际斗争而牺牲的烈士,是真正走向大时代的英雄,然而英雄就义受到“旁立者”“真难看”“猛吐了一口沫”,看客与己无关的无情唾弃,正如鲁迅曾对孙伏园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14]53《药》《尘影》有鲁迅、黎锦明共同的寄托和对生命意志深刻的体验,反对文艺脱离现实和人生的论调,文艺要参与到历史发展的必然的“大时代的时代”。黎锦明跟随鲁迅将新文学推进新的启蒙与革命现代性方向,如黎锦明说:“至少在我个人,仍然认文学为诱导一国文化向上,使一般国民的智慧增高,使社会的精神表层臻于繁荣的一种工具。我们仍然要认定现代的社会,无论那一个成份,都是异于一百年以前的情况的。这一百年来的中国进化,固未臻于理想境地,但在这进化的原律下,我们可以从无论那一个国民的心里,都存在着一点新的要求,——智慧与同情的要求。”“因为这普通的要求缺少正大的,体验的,良善的诱导……”(1934年《大上海半月刊》第3期《现代国家必需伟大文学的生长》)现代国家必需伟大文学的生长,现代文学应以其特殊地位,唤醒愚昧与麻木的国民的社会现实问题,黎锦明承鲁迅的方法,在反封建专制思想革命中,以知识分子承担着启蒙的使命,把愚昧者引上觉悟、革命的道路,其新文学文艺观具有现代性特质。
鲁迅对黎锦明的《烈火》《破垒集》小说集都有提及和评论。《烈火》分别在1926年6月初版,1927年10月再版,1928年11月三版。对于再版,黎锦明因为经历了国民党清党大屠杀,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他的心境全变了,黎锦明在《烈火重版自序》中提到,他原表明《烈火》将不出版了,但他在中山大学会见鲁迅先生,鲁迅问起并说“这可以不必,我们看过去的作品总是不好的,出了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虽觉各篇思想幼稚,艺术不成熟,“至少它不过我的一个初产出来虚弱的婴儿罢,我应该依样珍重它,决(绝)没有将其沉溺的道理”[15]。从这样的历史文字语境中,人们是能够感受黎锦明的生命现象的,即生命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以及他从白话新文学小说的“情感”“真实”走向新文学小说的“启蒙”“革命”“民族”的现代性思想演变和发展。
黎锦明1927年出版了《雹》《破垒集》小说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分析黎锦明的作品道:“……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其显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来;有时如中国的‘磊砢山房’主人的瑰奇;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cz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沈从文在1931年《论中国创作小说》指出“黎锦明承鲁迅方法,出之以粗糙的描写,尖刻的讥讽,夸张的刻画,文字的不驳杂中,却又一种豪放气派,这气派的独占,在他名为《雹》的一集中间,实很有些作品较之同时其他作家的作品更为可爱的。”[16]215文如其人,黎锦明感情敏锐,人格高洁,秉性率真热诚的不凡气质性格也在作品里有所反映。知网学术期刊以黎锦明为篇名论文作者有康咏秋、孟方、王吉鹏、孙晶、贾剑秋、杜悦英、陈丹蕾、余珊等,他们从黎锦明作品的创作思想、复仇意识、革命文学、湘楚文化、乡土地域等方面进行阐述,论证了他的小说特点。黎锦明在1928年《我所觉到过去的新文艺》[17]中,评论中国新文艺“什么主义都不会跑到中国的作品里来,除开鲁迅的作品——建筑在写实艺术上的《彷徨》与《呐喊》”。[17]19文中他还举出能写到社会的作品,如叶圣陶《线下》、许钦文《毛线袜》、许杰《惨雾》、王鲁彦《柚子》,并说“能写到社会,我想这是一宗未可限量的事”[17]19。正如鲁迅说《孔乙己》“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反映现实社会。他反对伤感或享乐、浪漫势力的蔓延,将享乐放在文学里,不会写穷人身上的破布条子,并指出如郭沫若《落叶》、田汉《咖啡店之一夜》、郁达夫《沉沦》《寒灰集》、徐志摩《志摩的诗》《翡冷翠之夜》等,作家应该给读者以社会的观念,他指出“这或许容易讨人家的嫌恶罢,可是暂且不管。如其这里面的作家——有些还是我的朋友,以后见我反(翻)了脸,我便只有道一声歉的份儿了”。[17]20他认为“只有革命才能使处处接触的忧郁、苦闷、无希望、无进步的一切改变”[1]84。黎锦明是把白话新文学作文学革命宣传,他的文字,他的生命,是为受帝国主义分子欺辱、专制势力对穷人压迫的社会而战。他是在推进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中国新文学文艺观。
黎锦明在1934年《我不愿意放弃文学》[18]74文中说,“我写了一本描绘革命的书——《尘影》……因为这书的被告发竟被监视了八天。我又不得不离去笔墨生涯,从事教书了;这教书的三年内,不能不从理论上下功夫。我对于文学更亲切的(地)认识了一些。”[18]75-76这段话说明了黎锦明的处境和他转为对文学理论的研究,显然,他的文学创作受到政治力量限制。他还说“以后我虽不时写作,但已没有早年那样的热诚和时代化了。还有些美学书和批评原理书,使我的脑子变得很执拗,几乎使我酷爱了形式主义。”[18]76但黎锦明在推进中国新文学(化)运动的努力以及他跟随新文学的前驱者呐喊助威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他在《黎锦明小说选》序中自己认可的,他不愧为一位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助推者。
1959年2月,时年53岁的黎锦明教授在湘潭大学任教生物课一学期,后来湘潭大学停办,他回到故乡湘潭县中路铺镇石潭坝乡菱角村长塘。[19]他的乡邻湘潭大学历史系副译审陈耀球常趋阶聆听他的如雷史评,如今那情景毕竟已经远去。现在的长塘是湖南省文艺联系村、文化示范村、新农村建设先进村和湖南省高校先进教学实习基地,是美丽乡村,湘潭市政府提出加快重建“黎氏八骏”故居,因此,期待在他的家乡湘潭大学图书馆也能开发建设黎锦明特色文库、数据库,乃至“黎氏八骏”、湘潭黎氏特色文库、数据库,以适应文化旅游融合、数字人文的发展形势,得到更多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传承文化,促进城乡文化、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