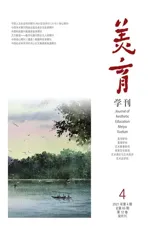试析梅洛-庞蒂如何捍卫儿童画超越线性透视法的价值
2021-12-02卫俊
卫 俊
(法国里昂第三大学 哲学系,法国 里昂 69372)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对现代绘画的思考颇受研究者关注,实际上,他对另一种绘画类型——儿童画也有考察。儿童画常常被认为是毫无章法(例如不符合线性透视法规则),因而是不值一提的,本文试图分析梅洛-庞蒂如何捍卫儿童画超越线性透视法的独特价值。
梅洛-庞蒂对儿童画比较系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处。前两处位于索邦课程笔记之中。1949年梅洛-庞蒂离开里昂大学的哲学教授讲席,来到了索邦大学,担任此处的心理学与教育学教授,一直到他1952年进入法兰西学院。在1949年到1950年的“儿童意识的结构与冲突”课程以及1951年到1952年的“儿童心理学方法”课程中,梅洛-庞蒂都集中探讨了儿童画问题。第三处有关儿童画的讨论是在《世界的散文》里。梅洛-庞蒂实际上并没有完成《世界的散文》这本书的写作,他在1951年末到1952年初左右终止了此书原本的写作计划,有关儿童画的讨论集中在目前这份未完稿的最后一部分“表达与儿童画”中。
在这三份文本中,梅洛-庞蒂有关儿童画的讨论都有一个明确的对话对象,即法国哲学家以及儿童画研究先驱吕凯(Georges-Henri Luquet)。吕凯的儿童画研究影响了皮亚杰、赫伯特·里德、阿恩海姆以及其他众多心理学家和艺术研究者,“在法国以及其它地区一直都是儿童画研究的参考书目”[1],梅洛-庞蒂从表达问题以及拓扑学存在论问题两个层面出发阐述儿童画问题时都涉及对吕凯理论的批评,下文将详细展开论述。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讨论吕凯关于儿童画的观点。
一、吕凯的儿童画研究
吕凯于1927年出版了《儿童的绘画》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将儿童的绘画描述为现实主义(réalisme)的,即把对现实的忠实再现和对线性透视法规则的掌握视为儿童绘画发展的最终指向与目标,“因为具象绘画是对于被再现物体视觉特征的图像翻译”[2]127。
根据再现的成功程度,他将儿童绘画发展依次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偶然的(fortuit)现实主义”,即儿童将偶然留下的印记称为绘画。第二个阶段是“失败的(manqué)现实主义”,这个阶段的儿童由于注意力的不集中以及综合能力的缺乏(l’incapacité synthétique)而只能画出不完整的或者并置的形象,画面元素无法协调成为一个整体。第三个阶段是“理智的(intellectuel)现实主义”,在这个阶段,儿童已经能画出完整的画面,但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透明化”(transparence)以及多个视角并存于画面中的现象。所谓“透明化”是指儿童会把原本被遮挡住、看不见的东西画出来,比如在地里埋着的植物、毯子下面的人等。同时,孩子还会把对象的多个侧面同时画在一张画上,比如画出一个正方体数个完整的正方形侧面,吕凯称这种现象为“回转迭合”(rabattement)。在吕凯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不符合线性透视法规则的错误,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不是描绘他们真正看到的东西,而是直接画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孩子知道地底下有植物、毯子下有人、正方体有数个正方形侧面,所以就把它们都画出来了。一直要等到第四个阶段即“视觉的(visuel)现实主义”阶段,以上这些错误才能得到纠正,因为此时孩子掌握了线性透视法法则以及事物之间的欧式几何学关系,不会再画看不见的东西,而只会画事物相对于自己所在视角所呈现出来的样貌,从而能够忠实地画出自己所见而非所知,实现对世界的现实主义描绘,并因此开始具有成人绘画的特征。
除了绘画发展的四阶段理论,吕凯还讨论了“图像叙事”(narration graphique)问题。所谓图像叙事是指在静态画面上对一段时间性历程如一段故事进行再现,面对这一复杂的任务,孩子们发展出了不同的应对方法。具体来说,吕凯区分了四种图像叙事模式,依次是重复型(répétition)、并列型(juxtaposition)、埃皮纳勒型(Epinal)以及象征型(symbolique)。在重复型图像叙事中,我们看到在不同时间点出现的同一个元素(包括人物和事物)在同一画面中的重复。在并列型图像叙事中,我们看到在不同时间点出现的不同元素在画面中的并列。在埃皮纳勒型图像叙事中,孩子把接续发生的多个不同场景分别画出来,互相不加融合。而在象征型图像叙事中,孩子只画在某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这四种图像叙事类型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序列,其中,重复型以及象征型图像叙事构成了这个序列的两极。重复型图像叙事对应于前述理智现实主义阶段,孩子画其所知,由于他知道故事的前后发展,所以他将在不同时间点出现的同一个事物重复地画到同一个画面上。而象征型图像叙事则对应于前述视觉现实主义阶段,孩子画其所见,在某一瞬间儿童只能看到故事的一个断面,所以他们不会重复画同一个元素,也不会把不同时间点出现的事物放在一起。从重复型到并列型,再到埃皮纳勒型以及象征型图像叙事,是孩子从画其所知到画其所见的连续发展过程。通过实验,吕凯说明这是孩子绘画发展过程的普遍模式,“在图像叙事中,如同对静态景象的再现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逐渐远离理智现实主义而走向视觉现实主义”[3]。在吕凯看来,象征型图像叙事才是正确的绘画模式,其他类型的图像叙事或多或少都有错误,错误最大的自然是重复型图像叙事,吕凯认为正是孩子综合能力的缺陷让其无法注意到画面的不同部分中存在同一个元素这一背离视觉真相的错误。
在其理论阐释中,吕凯在儿童画与成人画之间、理智现实主义与视觉现实主义之间、所知与所见之间以及非线性透视法绘画与线性透视法绘画之间建立了严格的对立关系,并且认为前者是错误的,后者才是正确的,儿童绘画发展正是从前者走向后者的连续纠错过程。
在梅洛-庞蒂看来,这种做法没有看到儿童画自身的价值,而只是站在成人画或者透视法绘画的立场上回顾性地对儿童画做一种消极的描述,因而只能看到儿童画相对于透视法绘画的不足,“孩子的绘画总是被否定式地定义,所有它的特点都被视为种种缺陷”[4]167,与之对应,儿童画的进步则被归结于它相似于透视法绘画的程度越来越高。不过,吕凯在《儿童的绘画》一书的最后部分做出了一些让步,他开始自问为何儿童画不能有其独立于透视法绘画的意义,为何儿童的综合能力不能有其独有的价值,“为何理智现实主义不能在视觉现实主义的旁边存在,就像阿拉伯语在英语旁边存在一样”[2]248。在梅洛-庞蒂看来,吕凯这种将儿童画与透视法绘画比作两种共存着的语言的让步,才稍微接近一些事情的真相,儿童画与透视画是两种各自都具有意义的表达,甚至,儿童画因为更加贴近于我们与世界的原初相遇经验,是比透视法绘画更加具有生命力的表达。
二、作为两种表达的儿童画与透视法绘画
如前所述,吕凯用注意力不集中、综合能力的缺陷等负面描述来解释儿童绘画中种种异于线性透视法之处,而梅洛-庞蒂却认为诸如画出物体不可见的侧面、将多个瞬间的景象整合在一起恰恰说明了儿童与世界维持着最原初的知觉联系。
“知觉”(perception)是梅洛-庞蒂哲学的关键词,从写作《行为的结构》和《知觉现象学》开始,梅洛-庞蒂就一直致力于恢复这个我们通过身体与世界建立的原初关联,这种关联超越所有理智主义与经验主义、主体与客体的分别,是一切文化与科学立于其上并以之为前提的前反思领域。我们可以借助“知觉”概念来解释前述儿童画中的不寻常之处。首先,关于儿童将对象的多个侧面并置在画面上的现象,在梅洛-庞蒂看来,这是因为在儿童的知觉经验中,物体是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物体的各个侧面、各种属性(例如味道、触感、颜色等)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同时存在的,它们共同呈现着物体的本质,此时尚未出现后来才有的诸多侧面与诸多属性之间的划分,因此,“回转迭合是一种将环境中互相掩映的部分之间的同时性表达出来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对于透视法的单纯无知”[4]386。其次,之所以在图像叙事中儿童会将不同时间点中发生的景象融合在一起,是因为在原初知觉经验中,时间不能被切割成一个一个连续的时间点,过去、现在和未来本来就是互相蕴含着的,“从哲学观点来看,‘连续时间’(successive time)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不可能设想一个与过去和将来无关的现在”[4]169。因此,融合多个时间点景象的图像叙事比截取一个时间断面的图像叙事更加接近我们实际的知觉经验。
在说明儿童绘画对知觉的忠实后,梅洛-庞蒂进一步将儿童绘画界定为一种“表达”(expression)。在梅洛-庞蒂看来,我们对于“表达”有一种客观主义偏见,即认为表达不过是首先想好要表达的意义,然后根据固定的语法规则为这些意义找到对应的符号,接着再将这些符号传达出来就可以了。梅洛-庞蒂提醒我们注意被言说的语言(le langage parlé)和能言说的语言(le langage parlant)两种表达之间的区别。被言说的语言是一种制度化了的、十分清楚明白但丧失生命力的语言,比如说科学或算法的语言,这种语言依据在先的法则说话。而能言说的语言则是一种处在诞生过程中、虽然模糊但却具有活力的语言,比如说诗歌或文学的语言,这种语言冲击在先的规则而建立自己的规则,新的意义即蕴含在这些新的规则之中,真正的表达指的是这种创造新意义的能言说的语言,“这与真正具有表现力的言语、因此与处于其确立阶段的整个语言并没有什么不同。言语并不仅仅为一个已经被界定的含义选择一个符号,就像某人寻找一把锤子来敲进一颗钉,或者寻找一把钳子来拔除它那样。它围绕某种意指意向进行探索,而这一意向没有任何文本可以用来指引自己,它正准备写这一文本”[5]49。能言说的言语产生新的意义,而新意义的最终来源则是前述知觉世界,知觉世界是所有文化传统与语言制度由之诞生,但同时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能言说的言语正处于从知觉世界里诞生出来的过程之中,此时它与知觉世界仍然维系着最为紧密的联系。被言说的语言虽然也是从知觉世界中产生,但由于它过分制度化,已然成为文化世界古老的沉积物,失去了最初的生命力。
吕凯把儿童画与透视法绘画比作阿拉伯语与英语的共存,对此,至少有两点可以进一步说明。首先,绘画和语言两种表达之间的关系是梅洛-庞蒂在考察“表达”问题时的一个思考点。常识中,似乎诉诸声音与文字的语言才能算作一种表达,把绘画比作语言似乎有些牵强。但在梅洛-庞蒂看来,诚然绘画不借助于语词,也不求助于声音,但这并不意味着绘画无法表达,绘画也能建立自己的规则,传达意义。而且因为绘画沉默无声,它往往更有可能挑战我们对于表达的客观主义偏见,向我们展示知觉世界的丰富性,从而启发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语言问题,“应该比较语言艺术与那些不会求助于它的其它表达艺术,并且尝试着把语言看作是这些沉默的艺术之一”[5]50。当然,问题的最紧要之处不在于在绘画和语言之间区分高低优劣,而在于在前述被言说的语言和能言说的语言之间进行区别,无论是在绘画内部还是在语言内部,我们都能发现真正的表达以及僵硬无生命力的表达。吕凯本人勉为其难地将儿童画比作与透视法绘画并列的另一种语言,因为他认为只有清晰地再现出所看之物的透视法绘画和成人画才是最合法的绘画,这显然是一种客观主义偏见。透视法的确是一种表达,它自身有一套严格的方法规则,但是当它脱离其诞生的语境而假装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时,它就变成了一种被言说的语言。反而是维系着与知觉世界紧密联系的儿童画向我们展示着意义诞生的最初过程,让我们发现透视法绘画不是表达进程的全部,“儿童画把‘客观的’绘画重新放回到表达活动系列中(这些活动没有任何保证地寻求复原世界的存在),并且使我们把客观的绘画知觉为这些活动的一个特例”[5]171。
于是,在有关表达问题的讨论中,梅洛-庞蒂实现了一次对吕凯理论的颠覆。儿童画和透视法绘画是两种表达,这不是因为儿童画最终会发展成为透视法绘画所以勉强承认儿童画也是一种表达,而是强调儿童画和透视法绘画作为能言说的语言和被言说的语言之间的区分,儿童画呈现了儿童与世界最初的相遇以及意义最初的诞生过程,它是比透视法绘画更有价值的一种表达。
三、皮亚杰:儿童画与拓扑学空间
除了有关表达问题的解释之外,梅洛-庞蒂还在有关拓扑学存在论的讨论中再次批评了以吕凯为代表的对于儿童画的消极态度,肯定了儿童画独有的价值。而有关拓扑学存在论的问题,需要联系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理论进行进一步的说明。1952年梅洛-庞蒂离开索邦大学后,正是皮亚杰接替了其在索邦的心理学与教育学教席,他是梅洛-庞蒂在讨论儿童画问题时的另外一位对话者。而且皮亚杰也同样关注吕凯的儿童画研究,他继承并发展了吕凯的儿童绘画发展理论。
在其1948年出版的《儿童的空间再现》一书中,皮亚杰将吕凯对儿童绘画发展的刻画重新阐释成儿童空间再现方式从拓扑关系模式发展到欧式几何关系模式的过程。首先,他将吕凯所述的绘画四阶段概括为三阶段,依次是综合能力缺乏的阶段、理智现实主义阶段和视觉现实主义阶段。在综合能力缺乏的阶段,儿童绘画不符合欧几里得几何学关系和射影几何学关系,但却满足拓扑几何学关系,这些拓扑学关系包括邻近(voisinage)、分离(séparation)、次序(ordre)、包裹(enveloppement)以及连续(continuité)共五种。比如儿童在此阶段尚无法准确地区分圆形、三角形与正方形,但却能够区分开放图形与封闭图形,因为圆形、三角形与正方形在欧式几何中存在差别,但是在拓扑几何学中却是等价的(都是封闭图形),而开放图形与封闭图形在拓扑几何学中却不等价。到了理智现实主义阶段,儿童对于欧式几何关系和射影几何关系开始有所了解,但拓扑几何关系还是在画面中占据上风,多个视角混合等现象说明此阶段依然是拓扑学式的空间再现。直到8到9岁儿童进入视觉现实主义阶段,他们才掌握了透视法、比例和距离的关系以及空间坐标关系等,此时他们的空间再现才是符合射影几何学以及欧式几何学的,所画之物才是从一个固定视角所看到的对象,皮亚杰说:“通过其与理智现实主义的根本差异,视觉现实主义展示了射影关系以及欧几里得关系的本质,这些关系不同于拓扑学关系。”[6]
皮亚杰的解释初听起来让人难以理解,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欧式几何学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接着到17世纪射影几何学才开始发展,然后直到19世纪拓扑学才逐渐发展起来,到20世纪初期拓扑几何学才得到严格的形式化数学描述,而在皮亚杰的解释中,“儿童在几何学方面的发展顺序似乎与历史中发现几何学的顺序正好相反”[7]。对于拓扑几何学的严格定义显然需要极高的数学能力,皮亚杰自然也不是说最小的幼儿反而具有最高的逻辑计算能力,皮亚杰的实际意思依然是最小的幼儿运算能力最差。他认为从拓扑几何学到射影几何学再到欧式几何学的过程符合演绎结构的顺序,从演绎前提到具体的演绎结果需要更多限制条件的加入,因此反而是作为演绎结果的射影几何学以及欧式几何学要求儿童有更高的逻辑与运算能力来对原初无定形的知觉进行形塑和引导,如此这般儿童才能掌握射影几何学以及欧式几何学。皮亚杰曾提出著名的儿童心理发展四阶段论,即从“感知—运动阶段”(2岁之前)开始,经过“前运算阶段”(从2岁到至7岁)以及“具体运算阶段”(从7岁到11),最后发展到“形式运算阶段”(从11岁到15岁或更大)的过程,皮亚杰将之视为儿童心理发展的普遍模式,“尽管由于个体智慧程度之间以及社会环境之间的差异,对应各个阶段的平均年龄会发生变化,但各个阶段出现的先后顺序却是不变的”[8]121。根据这一认知发生理论,儿童心理发展过程的核心是运算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的不断增强,在其运算能力不强的阶段儿童空间再现类型属于拓扑学式的,而儿童要掌握前述射影几何关系以及欧式几何关系则需要等到具体运算阶段,此时儿童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运算能力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同时知觉对其思维的支配程度则大大减弱,运算能力对知觉的影响也越来越强。
在对儿童画的解释中,皮亚杰和吕凯的立场基本一致,首先,皮亚杰非常赞同吕凯的儿童画发展阶段论,在1966年出版的《儿童心理学》中他依然说:“在吕凯关于儿童画的著名研究中,他划分了儿童画发展的各个阶段并对之进行了解释,这些理论到现在依然是正确的。”[8]50其次,皮亚杰和吕凯的解释进路相似,他们都以成人的透视法绘画为标准来评判儿童绘画的发展水平。梅洛-庞蒂批评说,虽然皮亚杰承认儿童画具有研究价值,“但是,儿童画总是作为成人画的一种功能得到研究的。儿童画被视为成人画不完美的草稿,而后者才是对物体‘真正的’再现”[4]132。在皮亚杰这里,运算能力的不断提高,对投影几何学和欧式几何学的掌握与运用,以及对透视法法则的遵从,成为儿童画发展的必然指向,如同在吕凯那里,视觉现实主义成为儿童画发展的必然归宿。
不过,在批评他的同时,梅洛-庞蒂也从皮亚杰这里获得了启发。皮亚杰将儿童最初的空间再现视为拓扑几何学式的,由此,梅洛-庞蒂发展出有关拓扑学存在论的讨论。
在1959年10月一份题为“本体论”的笔记中,梅洛-庞蒂写道:“将拓扑学空间当作存在的模式。”[9]260在梅洛-庞蒂后期讨论存在论问题的阶段,他视前述知觉的世界为大写的存在自身:“它不包括任何表达方式,可是它召唤所有的表达方式,它要求所有的表达方式,并且在每个画家那里重新激起一种新的表达努力——本质上,这个知觉世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它是比任何绘画、任何言语、任何‘立场’更多的世界。”[9]221存在是所有表达的意义源头。梅洛-庞蒂将原初知觉世界或大写存在自身进一步描述为拓扑学式的,其灵感来源正是“1948年初出版的《儿童的空间再现》一书中皮亚杰的研究”(1)见Emmanuel de Saint-Aubert, Vers une ontologie indirecte: sources et enjeux critiques de l’appel à l’ontologie chez Merleau-Ponty, Paris: Vrin,2006,p.231。作者Emmanuel de Saint-Aubert以保存、整理和研究梅洛-庞蒂的未刊稿在梅洛-庞蒂学界闻名,借助未刊稿,他判定梅洛-庞蒂有关拓扑学存在论的讨论,其源头既非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之思,也非拉康精神分析学中有关拓扑学的讨论,而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不过,他虽然指出了梅洛-庞蒂拓扑学存在之思与皮亚杰儿童心理学的关联,但却没有提及其与吕凯儿童画研究的联系。。在10月的另一份题为“原始知觉—当下—文化知觉—知识”的笔记中,梅洛-庞蒂写道:“我要说,文艺复兴的透视法是一个文化事实,知觉本身是多形态的,如果说它成为了欧几里得式的,那是因为它听任这一系统的引导。”[9]261在同一份笔记中他又写道:“在非射影的、纵向世界意义上的知觉,总是和感知、现象、沉默的超越一起被给出的。可是皮亚杰却完全不知道这一点,他将他的知觉完全变换成了文化—欧几里得式的知觉。”[9]262在此,梅洛-庞蒂用拓扑几何学与欧式几何学的差别来刻画原初知觉世界(或存在自身)与文化世界(尤指文艺复兴透视法)的对立,存在的结构对应拓扑学空间,而欧式几何学仅仅是从拓扑学演绎而来一个特例,所以透视法这一文化沉积物没有穷尽存在的深度,从拓扑几何学到欧式几何学的过程本质上是存在受困于僵死的文化制度而失去原本生命力的过程,这一解释路径显然受惠于皮亚杰对儿童空间观发展的描述,但梅洛-庞蒂在受惠于皮亚杰的同时也颠覆了皮亚杰贬低儿童画和拓扑空间的态度,儿童画非但不是失败的,反而是更接近大写存在这一意义源头的。另外,在梅洛-庞蒂谈及皮亚杰的儿童画研究时,吕凯的研究也在其视域范围之内。在为写作《存在与世界》而准备的一份草稿中,梅洛-庞蒂谈道:“关于绘画的‘阶段’,皮亚杰再次把拓扑学阶段描述为残缺的‘再现’——从中可以看出皮亚杰忽略了知觉的存在——‘理智现实主义’作为有脱漏的知识。与之相反,将拓扑学阶段描述为超越和扫除(balayage)。”(2)梅洛-庞蒂《存在与世界》(être et Monde)未刊稿:EM3[256]v(10),转引自Emmanuel de Saint-Aubert, Vers une ontologie indirecte: sources et enjeux critiques de l’appel à l’ontologie chez Merleau-Ponty,p.242。“理智现实主义”一词来源于吕凯,后被皮亚杰所沿用与发展,这两位儿童画研究者都未看到理智现实主义阶段儿童画的真正价值,而梅洛-庞蒂将之视为知觉尚未制度化的阶段,所以梅洛-庞蒂有关拓扑学存在论的思考同时构成了对吕凯与皮亚杰两人学说的批评。
由于梅洛-庞蒂在1961年突然离世,他有关存在论问题的许多研究计划与写作计划最终没有实现。有关儿童画与拓扑学存在论的讨论也仅仅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地散落在各处笔记和草稿中,而没有得到专题化的系统呈现。不过,在这些笔记和草稿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在表达问题以外,梅洛-庞蒂同样也在存在论层面上重申了儿童画独立于透视法绘画的价值,通过对皮亚杰以及吕凯的批评,梅洛-庞蒂指出,儿童画比透视法绘画更加彰显了拓扑学存在的意义厚度。
四、像看孩子一样看塞尚,像看塞尚一样看孩子
本文最后一部分试图说明梅洛-庞蒂在肯定儿童画价值时的另一个重要参照——现代绘画尤其是塞尚的绘画。“儿童心理学方法”课程中有一节标题非常耐人寻味:“成人—儿童画与意大利—现代画之间关系的比较”[4]471。将儿童画与现代画联系起来考察是梅洛-庞蒂思考绘画与透视法问题时的一个鲜明特点。在梅洛-庞蒂看来,成人画与意大利绘画都遵从线性透视法准则,而儿童画与现代绘画则对应着没有被线性透视法法则束缚的绘画表达实践,儿童画与现代绘画互相呼应,共同展示着身体与世界最初的相遇。
梅洛-庞蒂对现代绘画的关注与讨论系统而持续,早期的《塞尚的怀疑》以及晚期的《眼与心》都是他讨论现代绘画的名篇。而在众多现代画家中,塞尚是其着墨最多的,在梅洛-庞蒂的思想脉络中,塞尚与儿童在绘画与透视法问题上存在着深刻而根本的呼应,这种呼应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塞尚绘画与儿童绘画在画面表现层面呈现出类似的不符合线性透视法规则的形式与结构特征;第二个也是更为本质的方面在于,在梅洛-庞蒂看来,塞尚与儿童的绘画表达都揭示着作为文化源头的大写存在的意义厚度。
首先,如前所述,吕凯将儿童画中多个不同视角的整合以及多个瞬间景象的整合视为儿童绘画时因为不懂线性透视法而犯下的错误,梅洛-庞蒂却从“知觉”的角度给予这些特征以正面积极的解释,而我们在梅洛-庞蒂对塞尚绘画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其类似于儿童画的特征。在《塞尚的怀疑》中,梅洛-庞蒂认为塞尚实践着一种“实际的透视”(perspective vécue)或“我们知觉的透视”(perspective de notre perception)[10]10,这种透视法包括对不同视点景象的有机整合。比如在塞尚1895年所画的居斯塔夫·杰夫瓦肖像中,前景的桌子一直延伸到画面底部,而且桌子顶部高高翘起,完全不符合依据线性透视法从单一固定视点看到的景象,梅洛-庞蒂指出这是因为“当我们的眼睛扫视一个较大的表面时,它依次获得的图像取自不同的视点”[10]11,而塞尚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把这些来自不同视点的景象和谐地整合到同一个画面之中。在《漫谈》(Causeries1948)中,梅洛-庞蒂也指出:“自塞尚以来,很多画家都开始拒绝再遵从几何透视法这一规则,因为他们想要重新抓住并再现出风景在我们眼底下的诞生本身;因为他们不再满足于去做一个分析性的报告,而是想要重新融进并采用知觉经验的风格本身。”[11]21塞尚不只画在某一时间截面所看见的景象,而是将时间性纳入静态画面之中,其画面的不同部分是在不同时间里观察到的,如此这般塞尚将存在本身的时间厚度在画面中呈现出来,“在这些画中,存在不是现成地被给予了的,而是通过时间显现或浮现出来的”[11]21。所以,塞尚绘画中也有将不同视点以及不同时间点景象融合到一起的形式与结构特征。
进一步,画面形式与结构的相似指向了塞尚与儿童在绘画问题上更为本质的呼应:在梅洛-庞蒂看来,塞尚和儿童从两个角度展示着贴近知觉世界的原初表达。二者互相说明互相界定,而我们需要像看孩子一样看塞尚,也要像看塞尚一样看孩子。在《塞尚的怀疑》中,梅洛-庞蒂描述了塞尚所面对的种种误解。塞尚绘画时不断抹去重来,他失败的次数要远远多过其成功的次数,他的朋友左拉甚至以他为原型写作了一本小说,小说里的主人公,画家克洛德最终因为反复修改一件作品却又无法完成而在画架前自杀(3)1886年,塞尚因为认为这部小说在影射自己绘画上的无能而结束了和左拉的友谊。小说主人公的结局可参见左拉:《杰作:一部关于塞尚的小说》,冷杉、冷枞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333页。不过,主人公的原型也不全是塞尚,左拉笔下的画家克洛德身上还有马奈与莫奈的影子。,左拉消极地将塞尚描述为一位“夭折的天才”。但我们或许可以将塞尚的境遇理解成一个刚刚学习说话的孩子所面对的境况,“艺术家推出他的作品,就像一个人在讲第一句话时并不知晓那是否将只是一声叫喊而已”[10]17-18,塞尚拒绝套用现成的规则,同时希望表达出与世界原本的知觉联系,于是塞尚如同孩子一样面对着原初表达的困难,他有话想说但又不知如何去说,有画想画却又不知如何来画,所以塞尚才会不停尝试、不断犯错、反复修改,始终处在怀疑的状态中,而不像借助透视法规则画画的画家那样“胸有成竹”。事实上,塞尚也的确用孩子比喻自己的工作状态:“一旦一罐颜料在侧、一支画笔在手,我就仅仅是一个画家,最最单纯意义上的画家,一个小孩子。我拼命工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画着,画着,画着。”[12]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单纯的孩子反而比在文化世界里被日常习惯所驯化的成年人更能与塞尚产生共鸣,如梅洛-庞蒂所言,“成人已经被传统艺术文化所规训,孩子比他们更容易理解现代绘画”[4]258。
同样的道理,塞尚的绘画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积极地理解儿童画。如同左拉视塞尚为“夭折的天才”,吕凯和皮亚杰也因为儿童不懂得线性透视法规则而把儿童画理解成失败的成人画,但我们在塞尚这位20世纪伟大艺术家的画作中也发现了与儿童画类似的特征,塞尚和儿童一样不遵循线性透视法所规定的单一静止视角,而将不同视点以及时间的厚度纳入画面中,于是,“现代画家的努力赋予儿童绘画以新的意义。我们不再能把透视法绘画视为唯一的‘真相’”[4]132。儿童的绘画并非胡言乱语,而是儿童在尝试着记录自己与世界建立的最初联系,这种联系的确不够牢固,但却正因此而生动活泼,充满生命力,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塞尚之后的毕加索在谈论自己的画作时同样以孩子比喻自身的工作:“我是像孩子一样把它画出来的。”[13]马蒂斯更是在《用儿童的眼睛看生活》一文中写道:“希望能够不带偏见地观看事物的这种努力,需要勇气这类东西,这种勇气对于要像头一次看东西时那样看每一事物的美术家来说是根本的。他应该像他是孩子时那样去观察生活。”[14]所以,儿童的绘画努力和现代画家们一样,乃是一种真正原初的绘画表达,我们需要肯定其中的积极价值。
当然,像看孩子一样看塞尚,像看塞尚一样看孩子,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和塞尚在绘画表达上处于完全相同的位置,虽然孩子和塞尚都在实践着一种能言说的语言,都维系着与存在的密切关联,但儿童更多是因为处于个体发生时序中的初始状态,所以尚未被文化世界完全同化,而已经是成人且接受过传统艺术训练与熏陶的塞尚则是经过一番现象学还原式的努力之后才得以摆脱文化世界的束缚,重新如孩子般天真地说话。梅洛-庞蒂也指出这一差异:“当然在儿童无意而成的画与对现象的真实表达之间的确存在着区别。前者是未经分化的经验的残余,甚或是通过形体姿势获得的,是错误的绘画,就像存在着错误的书写,存在着咿呀学语时的错误的说话一样。后者不满足于利用完全现成的身体世界,而是在此基础上加进了系统表达的原则世界。”[5]170但另一方面,相较于儿童与塞尚之间的区别,梅洛-庞蒂显然更看重他们的呼应与相似之处:“但先于客观性的东西和超越客观性的东西以同样的方式象征地表达。”[5]170-171儿童与塞尚分别在各自的境遇中绕开线性透视法的束缚,同时在一种互相说明互相界定的关系中彰显着对方与自身的积极价值,在本质上,他们都实践着原初的绘画表达,展示着存在的意义深度。
五、结语
借助对吕凯和皮亚杰的反驳,以及来自塞尚和现代画家的参照,梅洛-庞蒂从现象学和拓扑学存在论两个角度肯定了儿童绘画的重要性。梅洛-庞蒂挑战线性透视法的权威性,本质上是为了敦促我们反思成人世界种种给定的规则,让我们能够从成人视角之外的其他视角去审视自身,审视成人自己构建的文化世界,去发现那些被我们自己遮蔽和掩盖的东西,去揭示真正使人成之为人的意义本源。这种反思是极其宝贵的,它永远期待并要求着更多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