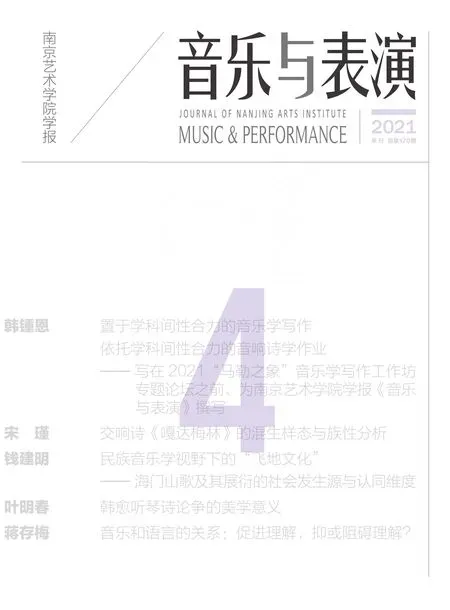“声各有形”的历史形成与理论内涵①
2021-12-01潘明栋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潘明栋(贵州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明清以来,唱论成果明显增加。其中清代乾隆年间徐大椿著《乐府传声》②《乐府传声》一书成书于乾隆年间,作者徐大椿,字灵胎,江苏吴江人。全书14,000字左右,被称为南北曲唱的集大成者。本文涉及到的唱论如《乐府传声》《唱论》《曲律》《闲情偶寄》等版本皆采用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重新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的版本。被誉为是继元代燕南芝庵《唱论》、明代魏良辅《曲律》之后的论曲唱的集大成者。“声各有形”命题是该书中众多命题之一。
“声各有形”命题里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如:1.声音是有形状的;2.声音的形状是可以改变的;3.调整歌唱口形可以达到寻找声音形状的目的。
关于这个命题的研究,当代学者多从唱字、发声、情感等方面有所引用,但都没有就命题本身进行适当研究。相对来说,刘建华教授在《“声各有形”论绎》[1]一文中结合歌唱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该文认为命题中的“形”是“人的脑际里映画出种种不同的形象”,这种形象来源于“文字的字义结合人的发声规律而形成”,需要利用“口法”的反复练习以达到声音形象的完成。该文观点合理,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但由于论述角度所限,也没有就该命题的历史形成及理论内涵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本文拟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一、从“贯珠说”到“声各有形”
“声各有形”命题的提出,首先在于认为声音有形:“凡物有气必有形,惟声无形。然声亦必有气以出之,故声亦有声之形。其形惟何?大小、阔狭、长短、尖钝、粗细、圆扁、斜正之类是也。”以中国传统的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观点,认为既然声音是由气送出,那么声音像万物一样也是有形状的这一结论。
“形”这一概念较早在绘画领域中运用较多,如“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等概念。在传统唱论中,对声音形状有较为具体描述的首先是《乐记》中的“贯珠”说。《乐记・师乙篇》中:“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蔡仲德先生的注译是:“歌声上扬时昂扬有力,如同上举;下降时沉着稳重,如同坠落;转折时棱角分明,如同折断;休止时寂然不动,如同枯树;音调千变万化都有一定之规,接连不断如同一串明珠。”[2]以接连不断形容歌唱声音的“上、下、转折、休止”等旋律形态,用珠子来形容歌唱时字音与字音的连贯与圆润。
元代《唱论》沿用了《乐记》“贯珠”说:“有字多声少,有声多字少,所谓一串骊珠也。” 书中论到善唱者、功能、场合、格调、声腔以及歌唱中出现的问题等,字数不多但内容丰富。其“一串骊珠”的“串”是指歌唱声音的连贯,“珠”则是指一个一个的歌词,第一次明确指出是字音的清晰连贯形成“串珠”般的声音形象。由于《乐记》只是说到腔的各种形态,并没有具体讲到成腔过程中字的因素。而《唱论》则指出了“一串骊珠”是歌唱中字、声关系的结果,补充、完善了《乐记》中“故歌者上如抗,……累累乎端如贯珠”中“贯珠”说的内涵。
明代魏良辅《曲律》在论初学者时说:“初学……学《桂枝香》,只唱《桂枝香》,久久成熟,移宫换吕,自然贯串。”这里的“贯串”二字是形容熟练掌握歌唱技法下的歌唱连贯性。“贯串”一词是对“贯珠”“一串骊珠”的拼凑与综合,意指歌唱声音的连贯与吐字的清晰等。《曲律》中还说:“生曲贵虚心玩味,如长腔要圆活流动。”其中“圆活流动”中的“圆”就是借珠子的形状来形容歌唱吐字运腔时的流畅状态。魏良辅所创的“水磨调”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明代王骥德在《方诸馆・论阴阳第六》中说:“既播之声音,必高下抑扬,参差相错,引如贯珠,而后可入律吕,可和管弦。”这里也是直接引用了“贯珠”一词。
从“贯珠”说的历时性发展过程来看,“贯珠”一词在明清时期的歌唱话语体系中应该已经耳熟能详,使得徐大椿能有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抽象性思考,即:声音是否有形状这一问题。
歌唱离不开歌词,歌声的形成过程就是歌词韵母声响的连接过程。在燕南芝庵《唱论》中除了提到歌声要像“一串骊珠”外,另外还有三处提到了唱字:1.歌之节奏:“……字真,句笃,依腔,贴调”提出了“字真”的审美要求;2.有“排字儿,打截儿,放褃儿,唱意儿。”; 3.“凡添字节病:则他,兀那……”[3],白宁对其中“排字儿,打截儿,放褃儿,唱意儿”的理解是“字与声表现中的不足,排字者、唱意者只注重字或词意的表达而忽视了声音的表现力,”[4]指出是歌唱中的这种现象是字、声关系问题。《唱论》全文只有1600字左右,却有四个地方讲到了唱字,可见元代唱论已经注意到字、声关系的重要性。
从绘画领域中“以形写神”等概念到“贯珠”这一具体声音形象的启发,结合燕南芝庵《唱论》中的论唱字,再到王骥德《曲律》等唱论中关于字、声关系的论述,徐大椿终于用“形状”一词把字、声、口形等关系联系在了一起,提出了“声各有形”这一命题。 从《乐记》的“贯珠”到《唱论》等著作中的字声论述,再到《乐府传声》“声各有形”命题的提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歌唱中的“字”“声”从“贯珠”论下的单一、具体的“圆”形扩展到“大、小、阔、狭、长、短、尖、钝、粗、细、斜、正、扁”等众多形状。歌唱声音形状的多样化,使得唱论传统研究发生了质的改变,因为它极大地丰富了唱论内容,表现在《乐府传声》一书中是大量围绕字的声母、韵母、四声、收音、交代等方面展开,形成了诸多的唱字“口法”,为歌唱者在理论层面打开了新的声音视野,提升了中国传统唱论的理论水平。刘承华教授认为,“对声乐演唱美学的理论化工作,是由《乐记》中的《师乙篇》开始的”[5]。纵观“贯珠”到“声各有形”这一历史发生过程,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滥觞是合乎逻辑的。“声各有形”命题的提出说明了《乐府传声》既是对历代唱论的继承过程,也是其对唱论传统的丰富与突破过程。
二、从“读字”到“唱字”的转换
“声各有形”命题的理论内涵之一是第一次明确地把读字口法借鉴为唱字口法,在理论层面提升了唱字技法的范畴。如《乐府传声・ 四呼》说:“喉舌齿牙唇,各有开齐撮合,故五音为经,四呼为纬。” 认为“喉舌齿牙唇”还有各自的四种口形, 咬字中“四呼”“五音”之间是经纬关系,在此基础上把“五音”“四呼”“归韵”“收声”“交代”等读字成果逐一单列论述其口形变化过程。下面仅以“五音”“四呼”“归韵”为例加以论述。
五音。音韵学上根据声母发音部位不同,分为喉音、牙音、舌音、齿音、唇音五类,即所谓“五音”。陈复华认为,唐代《守温韵学残卷》中就已经开始出现关于五音的整理与分类。[6]但在唐代崔令钦著《教坊记》、段安节著《乐府杂录》中两部论著中,都没有提及“五音”这一概念,说明“五音”这一概念在唐代还没有进入到唱论著作中来。明代朱权著《太和正音》一书中也出现了“五音”一词:“秦青、薛谭、韩秦娥、沈古之、石存符此五人,歌声一遏,行云不流,木叶皆坠,得其五音之正,故能感物化气故也。”这个“五音”是指“喉、牙、舌、齿、唇”五个发声部位。明代王骥德《曲律》中“又五音,宫、商宜浊,徵、羽用清。今正宫曰惆怅雄壮,近浊;越调曰陶写冷笑,近清,似矣”。这里的“五音”似乎是指“宫、商、角、徵、羽”,而不是“喉、牙、舌、齿、唇”。同一时代的两部著作却出现了对“五音”的不同用法,说明至少在明代王骥德及其以前,“五音”这一读字成果还没有真正成为唱字方法,当然不可能注意到“五音”配合时的口形变化问题。直到《乐府传声・五音》中不但提到“五音”,更是强调了“五音”的作用:“喉音之深浅不一,舌音之深浅亦不一,余三音皆然。故五音之正声皆易辨,而交界之间甚难辨。”认为五音是审字方法,丝毫不乱地掌握五音技法对于咬字十分重要。
四呼。“四呼”是真正直接讨论吐字口形的一个概念。所谓“四呼”是指发汉字韵母过程中“开、齐、撮、合”的四种口形。对于“四呼”的作用,《乐府传声》是这样认为的:“今人虽能知音之正,而呼之不清者,皆开齐撮合之法不习故也。”认为正确的“开、齐、撮、合”口形对于唱字来说关系重大。
“四呼”这个术语比五音出现得晚。陈复华认为这一概念是由清代音韵学家潘耒在《类音》中提出:“初处于喉,平舌舒唇,谓之开口;举舌对齿,声在舌颚之间,谓之齐齿;敛唇呼之,声满颐辅之间,谓之合口;蹙唇而成声,谓之撮口。”[6]16依据咬字时的口形,总结出“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种口形,被总结为“四呼”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在清代前期的唱论中没有发现使用,如清代李渔著《闲情偶寄》之《字忌模糊》中有“舌本生成,似难强造,然于开口学曲之初,先能净其齿颊,使其出口之际,字字分明”。虽然论及“舌”“开口”“齿颊”等概念,但没有提到“四呼”这一概念,清代黄图珌著《看山阁集简笔》中也没有,直到《乐府传声》才把“四呼”作为一个重要的唱字技法单列章节加以论述。
归韵。主要是指对字的韵尾的收声。韵尾属于韵母部分,韵母包括韵头、韵腹、韵尾三个部分。《乐府传声・归韵》说:“四声四呼清,则出口之字面已正,而不知归韵之法,则引长之字面,仍与箫管同,故尤以归韵为第一。”认为歌唱过程中,唱清楚字头之后还要注意归韵,不然就像管乐一样只听到声音而听不清歌词。
关于音韵的研究,元代周德清编撰的《中原音韵》和明代乐韶凤、宋濂等编撰的《洪武正韵》两本书影响最大。其中《中原音韵》以中原地区北方官话为基础写成,把字韵分成十九类,其中的韵辙是指收声时的声响,韵母是指记写的符号,这样就把语音与语言对应起来,形成各种发声与记写的对应关系。我们知道,无论是音韵学还是歌唱学,无论声母还是韵母、韵辙的发声过程都是口形变化过程。
在《乐府传声・声各有形》中:“如大字之形大,小字之形小,阔字之形阔,狭字之形狭,余数字无不皆然。”认为汉字中蕴含了每个字的读字口形,即读“大”字时口形要大,读“小”字口形要小,读“阔”字口形要开阔,读“狭”字口形要狭窄,这是“五音”“四呼”可以解决的问题。《乐府传声・归韵》篇中:“江阳,则声从两颐中出,舌根用力,渐开其口,使其声朗朗如叩金器,则江阳归韵矣。”通过详细描述口腔中的变化过程,指出“江阳”辙的发出、经过以及形成的声响过程。《乐府传声・四呼》篇指出,“有张口者,有半张者”“有闭口者,有半闭者”,还有“有先张后闭者,有先闭后张者”等细微口形差别,指出歌唱过程中口形变化的实际情况远比“四呼”复杂,这些认识以“口形”为切入点,抓住了“五音”“四呼”“归韵”等概念的主要内涵。
由于认识到读字与歌唱都涉及字形、口形与声音的内在联系,《乐府传声》细致地整理了语言学、音韵学中的读字成果,大胆地把读字成果作为唱字方法借鉴过来,形成《乐府传声》中“五音”“四呼”“四声”“宫调”“起调”“轻重”“徐疾”“出音”“句韵”等歌唱“口法”论。这些音韵学中的成果, 形成了“声各有形”命题中唱字技法的理论基础。
三、“改形”的实践意义
所谓“改形”,就是《乐府传声》中《出声口诀》篇中提出的“欲改其声,先改其形,形改而声无弗改也”的观点。从现当代唱法理论研究来看,通过调整歌唱发声管道的长短、粗细,共鸣腔体的大小、口形等是可以达到改变歌唱声音的目的。如当代唱论中“打开喉咙”“低喉位”“唱响胸腔”“口形竖起”等常用术语,就是各种描述发声形状的常用语言。所以,“欲改其声,先改其形,形改而声无弗改也”的观点, 构成了“声各有形”实践层面的内涵。
“声各有形”是命题思想,“欲改其声,先改其形”则是具体操作手段和技法原则。《乐府传声・出声口诀》中论述了这一逻辑关系中,试分析如下。第一句话:“天下有有形之声,有无形之声。”提出“声各有形”这一命题思想。第二句话:“无形之声,风雷之类是也;其声不可为而无定。有形之声,丝竹金鼓之类是也;其声可为而有定。”认为丝竹金鼓等乐器的声音是可以人为确定。第三句话:“其形何等,则其声亦从而变矣。”认为乐器形状的改变,其声响也会发生改变,从而引导出“欲改其声,先改其形,形改而声无弗改也”的结论,这是第四句话。第五句:“惟人之声亦然。”以“声”为结合点,从丝竹金鼓等乐器推导到人声,认为和乐器形状的改变导致声音改变一样,人的发声形状的改变同样也可以改变歌唱声音的形状。第六句:“喉、舌、齿、牙、唇,谓之五音;开、齐、撮、合,谓之四呼。欲正五音,而不从喉舌齿牙唇处著力,则其音必不真;欲准四呼,而不习开齐撮合之势,则其呼必不清。”改变人发声形状靠的是“五音”“四呼”。第七句:“所以欲辩真音,先学口法。口法真,则其字无不真矣。”得出第二个结论:“五音”“四呼”是唱清楚歌词的重要方法。
从“声各有形”的提出到第一个结论“欲改其声,先改其形,形改而声无弗改也”,再到第二个结论“所以欲辩真音,先学口法。口法真,则其字无不真矣”, 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过程。“口法”是解决“改形”问题,“改形”是解决具体歌唱声音的问题,所以“欲改其声,先改其形” 是对“声各有形”命题思想的具体化,是实践层面的理论内涵,两个命题之间互为表里,是现象与根源、实践与学理的关系,凸显出“声各有形”命题的内在性、根源性以及学理性地位,使得该书具有了指导歌唱实践的实用价值,奠定了该书在唱论传统中的历史地位。“欲改其声,先改其形”的“改”不是随心所欲地改。其改的依据是所唱歌词的形,改的方法是综合运用“五音、四呼、归韵、收声、交代”等系列方法,改的标准是使歌词听起来清晰,歌唱的声音圆润、好听,能够达到表情的目的。
在《乐府传声・声各有形》中以“东钟辙”“江阳辙”为例,论述了具体的改形过程:“如东钟韵,东字之声长,终字之声短,风字之声扁,宫字之声园,踪字之声尖,翁字之声钝。江阳韵,江字之声阔,臧字之声狭,堂字之声粗,将字之声细。”这段话中,首先把“东钟韵”中的声音形状分为“长”“短”“扁”“圆”“尖”“钝”“阔”“狭”“粗”“细”等几种,认为这些声音形状的形成口法很多,既有传统的“四呼”“五音”,还有“半张口”“半闭口”“喉出唇收者,有喉出舌收者”等“四呼”“五音”所没有包括进来的形状。从现代音韵学上来看,“东钟辙”中的“风”“宫”二字,都是后鼻腔归韵,但是由于声母、韵母的差异,形成不同的声响效果。如“风”字声母是“f”,采用唇、齿配合气息发音,然后迅速归到后鼻腔,在这个过程中,字音在口腔中从唇齿到后鼻腔有一个明显的后移过程,形成了文中“先闭后张”的口形状态。而“宫”字的声母是“g”,靠舌、喉配合气息发声,然后迅速归位到后鼻腔,形成口形的“半闭合”状态。这些“先闭后张”“半闭合”等状态都不是“四呼”中简单的开合状态,而是这一范畴中各种口形的变化组合。文章举例“东钟辙”是为了说明歌唱过程中口形及内部发声器官运动的复杂性,指出发声形状的细微改变对于声音形状形成的重要性,从而说明了依据歌词“改形”达到寻求歌唱声音的方法。全书中这样的例子处处可见,用各种实践的例子来说明“声各有形”命题的理论内涵。
如何解决唱字问题是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位歌唱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代也同样存在。如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土洋之争”:“一部分人强调西洋歌唱方法科学,理论体系完整,音质音色优美,表现力强;将民间唱法和戏曲与民歌结合起来的戏歌唱法斥为不科学的土唱法。认为民族唱法音域窄土气十足。”“搞民族唱法的反过来指责西洋唱法声音打颤——像打摆子,咬字不清,表情矫揉造作。”[7]“土洋之争”的焦点是民族声乐歌唱家认为美声唱法唱不清楚歌词,因此排斥。当然,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争论双方在之后的实践过程中互相学习与借鉴,形成了美声唱中国歌注意了歌词的清晰,中国民歌借鉴了美声的“低喉位”“深呼吸”等歌唱技法。美声与民族唱法的当代融合恰恰表现在歌唱发声过程中发声形状的改变:美声唱法适当进行口腔内部形状的调整,达到唱清楚汉字的目的,而民族唱法借鉴美声唱法中“打开喉咙”“低喉位”“吸着唱”技法也是发声形状改变的具体表现,这些现象都是“欲改其声,先改其形”观点的实践例证。
结 语
“贯珠”在《乐记》中是听觉形象,经过历代唱论的不断补充与完善,终于在《乐府传声》中形成“声各有形”这一命题。命题在理论层面把读字成果借鉴为唱字技法理论,在实践层面总结提炼出一个总的唱字原则与办法,即“欲改其声先改其形”的观点, 用以解决歌唱实践中各种唱字与创腔的问题。
通过梳理“声各有形”命题的历时性发展过程及两个层面的理论内涵发现,其思想内涵与现当代美声唱法中诸如“通道”“竖起”等概念内涵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有理由相信,适时地再对中国重要传统唱论进行相对深入的研究与解读,既是当代歌唱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