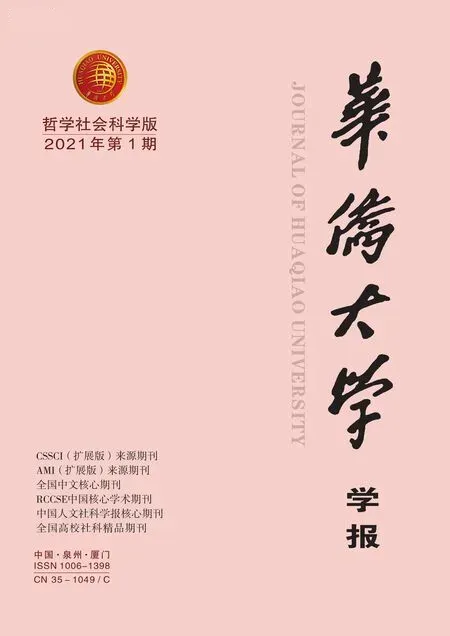妈祖信仰在日本的传播与转型
2021-12-01○林晶
○林 晶
作为“一体多元”中华文化架构下的一元,妈祖文化研究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大陆学者从妈祖文化的历史源流、妈祖文化与华人华侨、妈祖文化与一带一路等众多课题入手,构建起以“妈祖学”(1)关于“妈祖学”这一概念,参见黄瑞国:《妈祖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为代表的理论框架;我国台湾学者注重妈祖宫庙、妈祖进香仪式、妈祖与两岸认同等领域的考察,提出了具有学术史意义的“祭祀圈”(2)关于“祭祀圈”理论,参见林美容:《妈祖信仰与汉人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等研究概念;日本学者尝试探讨民间信仰与社会文化、地域建设之间的关联性,肯定了妈祖文化对振兴地域经济、促进国际性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3)参见藤田明良:《媽祖:航海信仰からみたアジア》,《季刊民族学》2010年第3期,第32—35页;松尾恒一:《清代、南シナ海の海商·海賊、漁民と媽祖信仰、歴史と伝承》,《儀礼文化学会紀要》2017第3期,第 44—62页。。虽然妈祖学研究不断升温,成果斐然,但是或许受传统研究范式的影响,上述研究成果大多以“中国”为焦点,对妈祖文化的海外传播、跨文化传播较少涉及。特别是对于与中国一衣带水、关系密切的东亚邻国——日本,妈祖文化是如何传播到这个近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妈祖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何意义?这样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
作为发端于北宋时期福建沿海的航海女神,妈祖信仰在民间崇拜与官方褒封的双重推动下,到了明代已经发展成为政府专门祭祀、国家和民间兼而有之的重要信仰之一。(4)妈祖信仰自宋宣和五年(1123)宋徽宗赐庙额“顺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正式封爵“灵惠夫人”,此后元、明、清各朝不断得到朝廷褒封。《元史》卷七十六记载:“惟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据《明史》卷五十记载:“天妃,永乐七年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康熙二十三年(1684),因佑施琅平定台湾有功,朝廷提升妈祖神格,自“天妃”诏封为“天后”。参照蒋维锬编校:《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第二辑 史摘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伴随着外交往来、海洋贸易、华人移民,妈祖信仰广泛地传播到朝鲜、日本、东南亚等海外之地,在世界各地形成一种云蒸霞蔚的妈祖文化景观。以如今的东亚日本为代表,妈祖信仰在日本的传播历经了“四传”:明洪武年间,妈祖信仰伴随朝贡贸易远渡到如今被称之为冲绳的琉球,成为“域外中华”的样本;14世纪末至17世纪前叶,妈祖信仰陆续在日本的鹿儿岛、长崎等九州各地传播开来,成为“文明互鉴”的标志;17世纪后期,妈祖信仰更向茨城县、宫城县、青森县等东日本太平洋沿岸逐渐扩散,成为“文化转型”的标志;(5)关于妈祖文化在日本传播的整体脉络,可参阅長崎県文化·スポーツ振興部:《媽祖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长崎:康真堂,2010年,第73页。20世纪之后,妈祖信仰被以长崎为代表的地域都市民众改造为文化祭祀的专门对象,成为了日本现代都市“文化符号”之一。基于妈祖信仰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本论文拟以中日历史文献的相互参照与彼此诠释为依据,探究妈祖信仰在日本传播、演绎、转型、留存的整个过程,力图论证妈祖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媒介与文化符号的本质之所在, 阐释妈祖文化在当下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之中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 文明承传:妈祖信仰“一传”琉球
将妈祖信仰在琉球的传播作为日本的“一传”,不仅是因为在近代琉球群岛被纳入日本冲绳的版图,更是源于历史上的琉球,既是从属于明清的藩属国,也是受控于日本萨摩藩的“属地”,“两属时代”的琉球作为联结中日贸易的交通要道,成为妈祖向东太平洋传播的“第一站”。围绕妈祖文化与琉球的历史研究,不少学者或是详实论述闽人赐迁琉球的历史;或是追溯中国文化深入琉球王族、乃至民间的影响。(6)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阅谢必震:《略论明代闽人移居琉球的历史作用》,《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56—69页;谢必震:《试论明清使者琉球航海中的海神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1期,第78—85页;李宏伟、阳阳:《妈祖信仰传入琉球研究》,《八侨桂刊》2016年第2期,第71—77页;张沁兰、赖正维:《明清时期闽人与琉球交往考论》,《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5—14页。但是,围绕妈祖文化是如何成为琉球的官方信仰,乃至如何定位琉球妈祖文化的问题,却鲜有涉及,因此,本部分尝试就这一段历史加以梳理。
依据《明史》记载,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派遣杨载到琉球诏谕。同年十二月,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载入朝,贡方物”(7)《明史》卷三二四,外国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61页。。这一记载落实了中国与琉球之间朝贡制度的建立。而正是为了援助琉球、推动贸易,明廷陆续派遣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这一点在《明神宗实录》中得到论证,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琉球国中山王尚宁,以洪永年间初赐闽人三十六姓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贡谢之司;习海者授通事、总管为指南之备。”(8)《明神宗实录》卷四三八,万历三十五年九月己亥。不仅如此,依据《琉球国志略》记载,自洪武朝以来,至永乐、洪熙,一直到万历朝,皆存在着闽人赐迁琉球的历史记载,“至万历中,存者止蔡、郑、梁、金、林五姓,续赐者阮、毛两姓。”(9)周煌:《琉球国志略》,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1年,第198页。由此可见,琉球成为了闽人家族迁徙、奔赴海外的重要场所之一。
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之后,妈祖信仰亦传播到了琉球。据琉球王国国师蔡温监修的编年史《球阳》一书的记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昔闽人移居中山者创建(天后)庙祠,为同祈福”(10)球陽研究会編:《球陽》,东京:角川书店,1982年,第169页。。这一官方记载也得到琉球民间史料的论证,据清代三十六姓后裔蔡世昌《久米村记》记载:“久米村,一名唐荣,即古之普门地。明太祖赐唐人三十六姓,聚族于此,故曰唐营;又以显荣者多,故曰唐荣。……自村口而入,行数十步,有神庙曰上天妃宫,嘉靖中册使郭汝霖所建。宽不过数亩,周围缭垣,殿宇宏敞。其正中为天妃神堂,其右为关帝位座,其左为久米公议地。凡中朝册使及一切渡海官民,莫不赖天妃灵佑,故累朝天使,皆谒庙行香、竖匾挂联以酬之。”(11)蔡世昌:《久米村记》,蒋维锬编:《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第一辑 散文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在此文中上天妃宫不仅“正中为天妃神堂”,还以关帝神作为从祀,更兼具唐人会馆的功能,佐证了上天妃宫乃是“唐营人信仰生活的中心”(12)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郑彭年译,澳门:海事博物馆出版,1995年,第262页。。虽然在《球阳》和《久米村记》中上天妃宫的创立者存在分歧,一说为闽人,一说为郭汝霖,但不可否认的是:聚族显荣,建庙立祠,祭祀天妃,天使拜谒,构成了琉球久米村的妈祖文化生态的一大图景。
如果说上天妃宫的建立乃是天朝上国的文化移植,那么永乐年间琉球国王、尚氏王朝开创者尚巴志(1372—1439)于那霸创建下天妃宫,成为了妈祖信仰在琉球确立正统地位的代表性事件,也展现出琉球王室对于妈祖信仰的认同与崇拜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根据琉球官方正史《中山世谱》卷四·尚巴志纪记载:“明·永乐二十年壬寅即位。二十二年甲辰春遣使,以父思绍讣闻于朝。成祖命礼部遣行人周彝赍敕至国,赐祭赙以布帛。本年,命辅臣创建下天妃庙。”(13)《中山世譜》卷四,蒋维锬编校:《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第二辑 史摘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上天妃宫和下天妃宫的相继建设,彰显了琉球王室对于妈祖信仰的虔诚态度。琉球官方正史《中山世鑑》还记载了尚泰久王在即位不久(1454年),为上天妃宫和下天妃宫敬奉梵钟一事:“琉球国王大世,[庚寅]庆生,兹现法五身,量大兹愿海。而新铸洪钟,以寄舍本州上(下)天妃宫。上祝万岁之宝位,下济三界之群生;辱命相国安潜,为其铭。铭曰:‘华钟铸就,挂着珠林。撞破昏梦,正诚天心。君臣道合,蛮夷不侵。彰凫氏德, 起追蠡吟。万古皇泽, 流妙法音’。”(14)《中山世鑑》卷三,蒋维锬编《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第二辑史摘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45页。琉球王室所书“君臣道合,蛮夷不侵”的铭文,不仅论证了明朝“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理念,也直接反映了上下天妃宫作为中华文明的承载之地而存在的历史事实,更间接佐证了琉球王国自诩为“域外中华”的文化目标。
除了闽人三十六姓、琉球王室对妈祖信仰的崇信,在此我们也不可忽略“中琉使团”在妈祖信仰传播之中的推动作用。历史上,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正使全魁、副使周煌出使琉球,行至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遭遇台风,一船触礁,一船漂回,册封使得以幸存。为了酬谢妈祖神佑,册封使奏请琉球国王建立姑米岛天后宫。副使周煌完成册封使事后撰写了《琉球国志略》一书,记载了琉球第三座天妃宫的建立始末:“天妃宫有三……一在姑米山,系新建。兹役触礁,神灯示见;且姑米为全琉门户,封、贡海道往来标准:臣煌谨同臣魁公启国王代建新宫,崇报灵迹。中山王尚穆,现在遴员卜地鸠工。”(15)周煌:《琉球国志略》卷七,蒋维锬编校:《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第一辑 散文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崇报灵迹、酬神建庙一事体现了册封使全魁、周煌对妈祖的尊崇,也反映出妈祖作为海神信仰的实质之所在。该年九月十五日,使者在首里王城举行册封仪式,至次年三月十七日登舟候风,而后放洋归棹,在琉球滞留二百二十七日。整个过程中,祭祀海神的文化活动贯穿于册封使事之始终,构成清代中国使者册封琉球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16)谢必震:《试论明清使者琉球航海中的海神信仰》,第169页。与此同时,中国册封使团的文化活动也深刻地影响了到大陆进行朝贡活动的琉球进贡使团。据《球阳》记载:“自往昔时,进贡船奉安天后菩萨,以便往来,即设立总管职,令他朝夕焚香,以祈神庇。”(17)球陽研究会編:《球陽》,东京:角川书店,1982年,第259页。妈祖信仰成为了中国与琉球官方共通的一大信仰。
追溯妈祖信仰在琉球的“一传”,首先,作为宏大背景,中国与琉球之间的朝贡体系的确立,尤其是闽人三十六姓、琉球王室、中琉使团的共同努力,构建起祭祀海神妈祖的信仰共同体,从而使妈祖信仰成为中琉两国共通的官方信仰。这一点成为妈祖信仰传播到琉球的基本前提,既确立了妈祖信仰在琉球传播的正统性,也奠定了妈祖信仰作为“官方信仰”的基调。(18)相较于琉球的妈祖文化多见于《中山世鑑》《中山世谱》《球阳》等官方性的文献记载,其在民间史料的留存则极为稀少。林国平教授曾利用琉球土著居民家文书(道光年间至昭和年间)收集170篇祈愿文和结愿文,广泛讨论了琉球的本土神灵,该研究未见妈祖信仰对于琉球民间的影响痕迹。目前学界掌握的妈祖信仰在琉球的民间史料,散见于部分中琉船员的漂流日记中,进一步挖掘妈祖在琉球民间的影响乃是未来一大课题。林国平:《琉球家族的宗教观与宗教生活——以祈愿文、结愿文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2期,第77—88页。其次,不管是本文提到的闽人聚居之地——久米村创建的上天妃宫,还是琉球王室所创建的下天妃宫,这一系列史实不仅反映出妈祖文化自民间信仰走向世界性的海洋文化的渐变经纬,也反过来论证了琉球将自身融入到中华文化体系之下、成为“域外中华”的承袭者。一言蔽之,就妈祖信仰“一传”琉球而言,藉由中华册封活动、朝贡贸易的方式,妈祖信仰得以传播到琉球,不仅树立了妈祖作为航海女神的官方地位,还彰示出琉球作为“域外中华”的身份认同,突出了以妈祖信仰为代表的东亚一隅“和平交往、共同发展”(19)围绕明朝初年与东亚的政治关系,万明研究员认为,明太祖以“不征”和“薄来厚往”为外交政策,通过“册封”体系和“朝贡”体系积极与周边的海陆各国拓展外交关系,推动东亚区域出现了政治上国家权力的整体上扬、经济上官方贸易的鼎盛合作、文化上区域国家间的广泛认同的新局面。参考万明:《明代初年中国与东亚关系新审视》,《学术月刊》2009年第8期,第127—134页。的格局,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论证了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呈现。
二 文明互鉴:妈祖信仰“二传”长崎
如果说妈祖信仰在琉球的传播带有朝贡体系下的官方支持、“域外中华”的身份认同、共同发展的思想理念的话,那么妈祖信仰在长崎的传播则带有明末清初时代背景下以“唐船”贸易为核心,以商人和佛教僧侣所代表的“唐人”(20)明清时代,日本人将中华称为“唐土”,华人称为“唐人”,将来自“唐土”的商船称为“唐船”。为主体的民间文化传播的浓厚色彩。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注重朝贡体系趋于式微下的东亚海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与民间贸易往来——1613年,日本开始施行“闭关锁国”,长崎港成为幕府仅向中国和荷兰开放的唯一港口。(21)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阅赵德宇:《日本南蛮时代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2期,第93—102页;高薇:《清朝商人与江户时期中日文化交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25—130页。不过,妈祖文化是如何在长崎演绎、扎根的过程,基本上没有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借助“锁国”这一特殊时代的唐船贸易与人员往来,妈祖信仰成为中国与日本之间展开“文明互鉴”的一大标志。
妈祖信仰在长崎的传播具有“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第一,唐船贸易、人员往来构成了妈祖文化传播到日本本土的宏大背景。庆长八年(1603),江户幕府成立之后,实行本质上鼓励中国商人的“朱印船贸易法”(22)朱印状明文写道:“任何郡县岛屿,商主均可随意交易。如奸谋之妄徒行不义,可据商主控诉,立处斩刑。”,中国商船开始逐渐增加。康熙二十三年(1683),清政府收复台湾之后颁布了“展海令”,为中日民间贸易带来新的契机。据统计,“展海令”颁布的第二年,中国来航长崎的船只达85艘,是以往的3.5倍。(23)《长崎志》卷11,中国船入港并杂事之部。转引自[日]松浦章著:《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上)》,李小林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伴随唐船贸易的繁盛,长崎的华人社会日益形成,各地商帮船主相继创立唐寺。首先是元和六年(1620)的南京寺,随后宽永六年(1629)漳州寺和福州寺也陆续建立。(24)《长崎实录大成正编》,《长崎文献丛书》第一集第二卷,长崎:长崎文献社,1973年,第242页。依照《长崎图志》的记载:“福济寺,……庆安三年,檀首陈道隆泉南父老改建,遂以分紫山名之。……(青莲堂)右奠天妃,左奉关帝。”“兴福寺,……宽永中,僧默子募建。傍奠天妃,以使市舶祝祷。……宽文三年邑大火,寺宇烬毁。僧道亮重建,元禄十五年住持悦峰修复。……海天司命堂,中央祀天妃及千里眼、顺风耳二鬼。”“崇福寺,……宽永九年,明人王、何、林、魏诸大商施,僧超然建。即祀天妃。”(25)《長崎図志》,引自蒋维锬编校:《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第二辑 史摘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99页。换言之,长崎的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即“唐三寺”经由渡航到长崎的中国船主捐资创建而成,且都奉祀妈祖。长崎不仅成为了海外华人最为重要的聚散地,也成为日本本土的“妈祖信仰”最具代表性的承载地。
不过,探究“唐人”兴建唐三寺的目的,开展贸易、推崇信仰的直接缘由固然重要,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或者说东亚内部的文明互鉴的根本事实。根据《长崎市史·地志编佛寺部》之“兴福寺”条记载,这一时期日本处在禁止天主教的一个阶段,长崎奉行秉持江户幕府之命,严格调查华人,因此,寓居长崎的南京船主一方面出于祈求海上平安的直接诉求,一方面为了应对政府要求而进行宗教甄别,“故而共同出资在真円小庵处建立了佛殿与妈祖堂,真円成为开山。”(26)長崎市役所:《長崎市史·地誌編仏寺部(下)》,长崎:重城舍,1927年,第151页。事实上,正如《长崎市史》所概述的:“唐人无暇听取佛教高远教义,纯粹是为了祈祷海上安全,举行各个宗教仪式,并为了得到寺庙提供的墓地。最为重要的,就是为了寻找办法证明自己绝非基督教徒。”(27)長崎市役所:《長崎市史·地誌編仏寺部(下)》,第250—251页。在此,妈祖信仰在长崎最初的文化传播,应该说就隐藏在这样一个东西间的文明冲突、中日间的文明对话的时代语境下。
第二,妈祖信仰在长崎的传播,离不开妈祖信仰的主体——“唐人”维护与继承这一文化的努力。作为唐人来航长崎、崇祀妈祖的场所,唐三寺一开始就是以妈祖堂、关帝庙为主体而构筑起来的。(28)内田直作:《日本華僑社会の研究》,东京:同文馆,1949年,第68页。唐三寺创建初期,就是以建造佛寺为名而行崇祀天后妈祖之实,实质上就是以妈祖信仰为核心的妈祖庙。(29)童家州:《日本华侨的妈祖信仰及其与新、马的比较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33页。依照绕田喻义《长崎名胜图绘》描述,“(福济寺)……妈祖坛,天妃像(海神也。女子像,旁侍女两人。在大士之左坛祭之)……封锁天妃坛的左傍,另辟一殿,唐船在港期间把船上礼拜奉祀的天妃像(寄存菩萨)存放于此。”(30)繞田喻義:《長崎名勝図絵》,引自蒋维锬编校:《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第二辑 史摘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160—161页。又依据《长崎实录大成》记载,“每年三月二十三日是船神天后的祭礼,允许滞留长崎港的唐人出馆到兴福寺祭祀参拜妈祖。待福济寺、崇福寺相继建成后,三寺同格并立,每年三月、七月、九月的二十三日轮流举行妈祖祭,在长崎港的唐人前往祭祀。”(31)《長崎実録大成》,引自长崎県文化·スポーツ振興部:《媽祖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第8页。由此可见,唐三寺不仅是唐人寄存唐船携来的妈祖神像的重要场所,更是唐人崇祀海神、举行妈祖祭的神圣空间。长崎的唐人通过唐三寺这一实存的载体,彼此配合、轮流祭祀,发挥出了承载妈祖文化的一大使命。
妈祖信仰在长崎之所以不断传播下去,也得益于“唐人”活动空间的持续扩大,尤其是佛教活动的兴盛与传播。以福州府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的高僧——隐元隆琦(1592—1673)为例证,1654年,应崇福寺僧超然的邀请,隐元自厦门启航东渡日本,先后在长崎的兴福寺、崇福寺开坛讲经说法,传授禅门大戒。1661年,隐元获得江户幕府赏识,于京都宇治开创了黄檗山万福寺,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之祖。1657年,隐元禅师的法嗣、福清人即非如一(1616—1671)应邀东渡,住持长崎崇福寺,留下了著名的《镇山门法度六则》。《镇山门法度六则》第一则就规定: “三宝伽蓝妈祖香灯及旦辰年度供养如常”(32)内田直作:《日本華僑社会の研究》,第67—68页。在此,祭祀妈祖、供养香灯成为在日黄檗禅宗的第一“法度”。以隐元开创的日本黄檗宗为标志,中国僧侣往来于京都与长崎之间,也就是日本文化的中心与边缘之间,不仅有效地发挥出传播中华佛教、引导日本信众的功能,还令与佛教文化融聚在一起的妈祖文化得以进一步传播到东日本。
第三,长崎的妈祖祭祀活动逐渐将日本的本土人士带入进来,成为中华文化深入日本民间、不断扩散的一大标志。依据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卷二记载:“来长崎的唐人,号为船菩萨的,第一就是妈祖,也号姥妈。……航来长崎的唐船,必有港口放石火矢;抛锚必鸣金鼓祝贺。……又在同一港中,当一船货物装卸完毕之后把菩萨从船上卸下,或返航让菩萨乘船的时候,沿途始终鸣金鼓吹喇叭。到达其船则港中同类船只鸣金鼓三三九遍。”(33)西川如見:《華夷通商考》卷二,引自蒋维锬编校:《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第二辑 史摘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53页。西川如见描述的,就是被称为“菩萨扬”和“菩萨乘”的,象征“唐船”入港与出港的妈祖祭祀活动,且这一活动主要由“唐人”来支配进行,成为凝聚中华文化共识的重要纽带。不过,随着时代的迁变,这一祭祀活动的参与者也不断渗透到日本民众之中。据《唐通事会所日录》描述,元禄2年(1689),为了在兴福寺举行妈祖祭,唐通事将妈祖祭中吹奏唢呐的事宜委托给下筑后町庄左卫門等四人,并雇佣本地太鼓铜锣乐手参与。乐队自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祭日清晨就守候于兴福寺,昼夜演奏。对此,唢呐手庄左卫門曾感叹道:“市町中若无妈祖祭,我将难以维持生计。”(34)《唐通事会所日録》巻一。转引自深瀬公一:《唐人屋敷設置期の唐寺と媽祖》,《長崎歴史文化博物館研究紀要》2009年总第4期,第77页。在此,妈祖祭祀活动不再只是唐人的文化输出,更在与长崎本土居民进行文化交涉、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融入地域社会,构成东亚内部文明互鉴的历史见证。
探究文明互鉴背景下妈祖信仰“二传”长崎这一主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梳理出妈祖文化以唐船贸易、人员往来为背景而传播到长崎,处在日本“扬佛抑耶”与“闭关锁国”的历史夹缝之中,彰显出一个文明间的冲突、融合、对话的宏大叙事;一方面,妈祖文化作为融合民间文化、华人文化、佛教文化、海洋文化等为一体的“共同体”的存在,以强大的生命力适应日本的文化土壤和历史环境,并不断地扩大生存空间,自唐人信仰而深入到日本民众之中,自长崎一地而散落到九州地区进而扩展到了京都地区,从而构筑起文明互鉴格式的一大典范。
三 文化转型:妈祖信仰“三传”东日本
如果说琉球的妈祖信仰是朝贡体系格局下的官方信仰,长崎的妈祖信仰是文明互鉴模式下的唐人信仰,那么“东日本”的妈祖信仰则象征着妈祖信仰真正走向日本民间,实现了“文化转型”的本土化。不过,迄今为止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学术界或是关注水户藩主(今茨城县中部及北部)德川光国(1628—1701)在矶原、矶浜两地创建天妃祠的事件记载;或是探究渡日学者或者著名僧侣,尤其是禅僧东皋心越(1639—1695)在日本的思想传承,(35)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阅张丽娟、高致华:《中国天妃信仰和日本弟橘媛信仰的关联与连结 》,《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269—271页;李宏伟、阳阳:《妈祖信仰传入日本路径研究》,《八侨桂刊》2018年第2期,第21页;谢孝萍:《旅日琴僧东皋心越》,《音乐研究》1993年第4期,第75—82页;敖运梅、赵元云:《论明末东渡僧人心越诗歌的禅理与画意》,《文艺评论》2013年第8期,第20—24页。基本忽略了妈祖文化在东日本传承之际的“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的问题。如果说日本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以外来文化为对象的“从受容到变容”(受容から変容へ)的过程的话,那么妈祖文化在东日本的传播也就具有与这样的日本文化的“文化模式”相契合的一大特征,也就成为了日本文化接受外来文化,构筑文化自觉,形成本土文化的一大转型标志。
第一,探究妈祖信仰在东日本的传播,首先需要梳理历史线索,探究妈祖信仰是如何进入东日本的传播经纬。江户时代初期,时值中国明末清初,为了抵制清朝的统治和躲避战乱,大批明代遗民流寓日本。心越(1639—1695),别号东皋,浙江浦江人,入日前驻杭州永福禅寺。1676年8月,由于谋事抗清失败,心越避难日本,翌年正月抵长崎,驻锡于长崎兴福寺。据李献璋的研究,水户藩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国尊崇中国文化,应德川光国的邀请心越于1690年移居水户,驻锡天德寺,并把自“唐土”带来的妈祖像作为伽蓝神之一祭祀于天德寺之内。(36)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第265页。1712年,天德寺改名为“寿昌山袛园寺”(现水户市八幡町),心越被尊为曹洞宗寿昌派的开山鼻祖。换言之,东皋心越自唐土携来妈祖像,驻足长崎兴福寺,再经德川光国迎至水户寿昌山袛园寺,开启了以水户为核心的东日本的妈祖信仰。
在天德寺成为水户妈祖信仰的第一站后,德川光国进一步采取“分灵”(37)据矶原天妃祠旧别当行藏院所藏古文书记载,矶原天妃祠被称为渡海第一宫,矶浜天妃祠被称为渡海第二宫,矶浜天妃祠略晚于矶原天妃祠,乃是作为矶原天妃祠的“御影”(影子)建立。事实上,“御影”和“分体”相呼应,间接论证了水户天妃祠采用“分灵”形式来加以祭祀的形式。参照[日]秋月観暎:《東日本における天妃信仰の伝播——東北地方に残る道教的信仰の調査報告》,《歴史》1962年第4期,第21页。的形式在水户的矶原和矶浜两地分别安置妈祖分灵、创建天妃祠,从而使妈祖信仰成为了水户的地域性的民间信仰。这一段历史在明治末年斧山和尚编撰的《寿昌山衹园寺缘起》中留下了记载:“(海上守护)天妃尊……开山禅师亲自把西湖永福寺祭祀的天妃尊奉来。元禄三庚午年(1690),奉源义公之命将其分体安置于祝町及矶原村两地,本体安置于本山。晨昏,祈求人民海上不遭风波之难。”(38)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第265页。矶原(现茨城县北茨城市矶原)和矶浜(现茨城县东茨城郡大洗町矶浜町祝町)作为毗邻水户城的两大姐妹港口,契合了妈祖信仰作为海神信仰的根本指向。据《水户纪年》卷二“元禄三年庚午四月六日”条记载:“海滨创立天妃祠,每夜举灯,以便海舶渔船夜行。”(39)蒋维锬编校:《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第二辑 史摘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由此可见,两地的天妃祠面朝大海、每夜举灯,发挥出航海女神指明方向的作用。《寿昌山衹园寺缘起》的一段文字亦对此进行论证:“据说此后三滨海上风波之难少,年年大祭参诣本山者云集。今复古例分给守护符,信者接受矣。”(40)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第266页。就这样,两地天妃祠的建立,令作为航海守护神的妈祖直接服务于水户本土的渔民船员,故而也就集结了一大批民间人士的信仰者。(41)日本妈祖信仰的特色不仅在于以华人为主体,亦扩散到了日本船员之中。参阅藤田明良:《媽祖―航海信仰からみたアジア》,《季刊民族学》2010年(通号133),第32—35页。
第二,妈祖信仰在东日本的传播,是否具有“东日本”的地域性格,或者说是否趋向本土化,就此也需要深入到妈祖信仰的内部来加以论证。根据李献璋的研究,矶原天妃山行藏院的现存档案保留了妈祖祭祀活动的历史记录,其一,“水户袛园寺天妃宫之事·三月二十三日天妃祭:(供饭、酒和鱼。三月三日节句献桃花一瓶。五月献菖蒲一瓶。九月九日献菊花一瓶。十月十日献稻穗)……”其二,“矶原的天妃山天妃神,三月二十三日为缘日。此日,船山立小旗,吹打笛、钟、小鼓、大鼓,群集跳□祭祀,取名为菩萨祭。”(42)蒋维锬编校:《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第二辑 史摘卷》,第159页。审视两则文献,“天妃神,三月二十三日为缘日”的记录直接呼应了“三月二十三日乃是妈祖——林默的诞辰日”这一中国妈祖信仰的原典。“菩萨祭”之名亦与长崎妈祖信仰的“菩萨”称谓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关联性,由此也就呈现出日本承袭中国文化、对之原封不动地进行移植的格局。
不过,这一记载到了江户幕府文政年间(1818—1830)则出现不小的转型,尤其是针对“妈祖”的称谓。依照这一时期中山信名纂修的《新编常陆国志》卷五“(鹿岛郡)矶原天妃祠”条记载:“(天妃山姨祖权现)神殿萱葺,方两间。神体木像,长六寸五分。肋立两躯,女体。前殿长五门半,横两间。……祭礼是三月二十三日。寿昌派幡二流所建,一流西方记为鹿岛郡,一流东方记为那珂郡。”(43)蒋维锬编校:《妈祖文献史料汇编 第二辑 史摘卷》,第159页。在此,“姨祖”应该是“妈祖”之讹误,“权现”乃是出自日本神道“本地垂迹”论的神号,源于日本历史上“神佛习合”的文化传统。(44)林晶、陈凌菁、吴光辉:《文化传承的融离与回眸——以日本长崎的“妈祖信仰”为对象》,《东南学术》2015年第6期,第261页。不言而喻,水户藩妈祖祭祀的兴盛景象进一步论证了妈祖信仰在水户藩获得广泛认同的事实,“姨祖权现”这一表述则显示出水户藩信众并不是将妈祖视为来自中国的神灵,而是作为本土的神道教的神明之一来崇拜之。水户藩的妈祖信仰直接传承来自中国民间的文化信仰,且随着历史的演绎被逐渐赋予了日本神道教的新内涵。
事实上,探究妈祖文化在东日本的传播与转型,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是与这一时期日益突出的所谓日本“文化自觉”的思潮密不可分。据李献璋的考证,旧矶浜町记录 <矶浜町事迹簿》之“弟橘比卖(45)《古事记》记载为“弟橘比卖命”,《日本书纪》记载为“弟橘媛”,为日本武尊(倭建命)之妃,神道教的海神之一。神社”条提到:“俗称天妃姨祖权现,但源烈公时把祭神换为弟橘比卖。”矶原天妃山别当的《株格之仪书上》亦提到:“水户齐昭,天保中……下令换成和天妃神业绩相同的弟橘媛——笠原明神和社号。”(46)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第267页。天保年间( 1830—1844),即德川齐昭担任藩主之际,水户藩兴起了一股以“神国”自居、进而“尊王攘夷”的国粹主义风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妈祖信仰出现了一个趋向在日本土化的“文化变异”,矶浜与矶原两地的妈祖神像被替换为日本本土神道教的神明——弟橘媛,即笠原明神。但是,妈祖信仰在水户藩并没有就此消失。天保四年(1833),矶原和大津两村的村长、船庄和村民代表共十四人联名向寺社奉行提交请愿书,请求归还撤下的天妃神像,这一请求终于在弘化年间(1844—1847)得以实现,也促成了天妃像的传统复原,与弟橘媛共同祭祀,史称“天妃像返还运动”(47)长崎県文化·スポーツ振興部:《媽祖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第72页。。这一请愿活动,成为确认妈祖信仰在东日本传播、变异乃至走向“还原”的一大佐证。
探究文化转型背景下妈祖信仰“三传”东日本的整个过程,可以梳理出一条逻辑性的轨迹,即东日本这一地区既存在着依照中国“原型”来接受妈祖信仰的事例,也存在着相互融合乃至共同祭祀的事例,更出现了基于日本自身的“文化自觉”使妈祖信仰发生“变异”的本土化事例。就在这样的演绎过程中,妈祖信仰的原型(中国型)—融合型(中日兼具型)—变异型(日本型)呈现为“东日本”这一独特时空下的“古层结构”(48)“古层论”是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对于把握日本思想文化的特征而提出的方法论之一。参阅[日]饭田泰三:《丸山真男的文化接触论、古层论探析》,陈毅立译,《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第136页。,也就是各个阶段逐层累积而构筑起来的犹如历史的“横切面”的存在样态,因而具有了多样化、重层性的基本特征。尤为重要的是,“天妃像返还”这一历史事件提示了我们,与其去探索所谓日本的“文化自觉”,倒不如说更为直接地证明了中华文化内在的“共生”性格,体现出以妈祖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包容力(49)林晶:《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研究:从变异体到共生》,《福建论坛》2019年第2期,第103—108页。,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逻辑和根本原理的重要见证。
四 祭祀文明:妈祖信仰“四传”现代都市
迄今为止,现代视域下的妈祖信仰研究大多集中在以海外华侨华人为主体的研究,或是侧重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论证(50)林明太、连晨曦:《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研究》,《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1期,第89—99页。,或是关注祭祀活动的组织变迁(51)小林康正、安田广美:《横滨中华街妈祖庙与东京妈祖庙——观光地中的信仰行为》,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院:《2019年国际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19年,第163—174页。,而忽略了妈祖信仰为什么会延续到当下,对于日本人而言,妈祖信仰究竟具有什么样的“魅力”?借鉴人类学视野下的“祭祀研究”与“城市观光”的理论成果,我们可以重新把握妈祖信仰的现代价值。作为理论建构,米山俊直的著作《都市与祭祀的人类学》以世界都市人类学与祭祀研究的文献资料为原点,探讨了都市人类学框架下的祭祀研究的意义,即探究祭祀活动之中的“人际关系与集团结构”,寻找其“内在的人物纠葛与紧张关系”,进而为日本人的宗教仪式、礼仪文化、祭祀观念来提供合理的、合法的证明。(52)米山俊直:《都市と祭祀の人類学》,东京:河出书房,1986年,第17页。与这一理论相呼应,则是日本学者提出的“观光学”的立场。2003年,堀川纪年、石井雄二、前田弘编撰的《为学习国际观光学的人们》提示了“21世纪是观光的世纪”,“观光改变地域,观光改变人”的论断。(53)堀川紀年、石井雄二、前田弘:《国際観光学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东京:世界思想社,2003年,扉页。换言之,若是结合人类学立场下的“祭祀研究”与“城市观光”的两大理论,由此来整理妈祖信仰在日本的再度转型,或许可以令妈祖信仰的研究获得一种新的“解放”,也可以令妈祖信仰本身朝着这样的新方向前进,从而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借助这样的理论框架,来进一步审视妈祖信仰的时代定位,我们可以站在一个传统与现代、内容与形式、价值与表征的视角下来对妈祖信仰进行重新评价。
首先,站在传统与现代的视角,妈祖文化作为日本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在冲绳,清代册封使奏请琉球国王建立的久米岛“天后宫”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妈祖圣像保存完整,并配祀千里眼、顺风耳和侍女,成为日本冲绳县的“重要文化财”;在长崎,唐三寺妈祖堂亦完好地保存下来,特别是崇福寺妈祖堂、妈祖门楼等被指定为日本国“重要文化财”,兴福寺妈祖堂被指定为“长崎有形文化财”;在水户,寿昌山袛园寺的妈祖像作为该寺的守护神而祭祀于本堂右侧,这一神像传闻由心越禅师从杭州永福寺奉请而来,一直传承至今(54)根据漥德忠教授的研究,该座像高约17厘米,头戴园冠,手持玉圭,配侍千里眼和顺风眼,三尊神像共同安置于一神龛内。不过,漥德忠教授认为该神像是否是心越携带而来还有待考证。窪德忠:《媽祖信仰(5)東日本の媽祖信仰》,《アジア遊学》2002年第8期,第147页。;在矶原,矶原天妃神社在大殿牌匾上书写了“天妃姬、弟橘媛、堆都嘉”的神灵之名,并收藏了和式风格的妈祖神像,(55)根据藤田良明教授的田野调查,该神社所藏天妃神像不轻易开账示人,根据该神社提供的神像照片资料可见,天妃像面部呈黑色,冠冕上的珠帘与中国传统的前后悬挂样式不同,呈左右悬挂,且身披和式神衣。配侍的两尊侍女手持日月扇,身披和式神衣。长崎県文化·スポーツ振興部:《媽祖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第73页。成为妈祖信仰走向日本化的标志。依据长崎文化·体育振兴部的调查,目前全日本保存古代妈祖像或持有祭祀传统的场所累计43处,(56)长崎県文化·スポーツ振興部:《媽祖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第15—17页。乃是妈祖信仰在日本传播的最大证明。换言之,作为文化传播的历史性存在,妈祖文化成为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极为显著的观光价值,也间接地成为日本多元文化性格的一大表征。
其次,站在内容与形式的视角,妈祖文化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性存在,通过有形化的祭祀活动得以传承下来,并复兴于现代日本都市的祭祀文化之中。妈祖文化的本质乃是航海女神信仰,历史上“菩萨扬”与“菩萨乘”的祭祀活动是以祈祷海上航行安全为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推演,这一祭祀活动的“原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作为全日本最为著名的妈祖祭典活动,现代长崎春节灯会的“妈祖巡行”起源于1987年,由长崎市观光局与新地中华街振兴组合共同举办。作为都市振兴的重要一环,巡行活动在春节灯会的正月初一到十五日举行,与过去的妈祖祭祀时间截然不同。在此期间,全市开始装饰中国式的灯笼,以中华街为主会场,表演舞狮子、舞龙、杂技等中国传统节目,且模仿江户时代“唐船”停靠、离开长崎港的情景,进行两次“妈祖巡行”活动。根据实地考察,巡游队伍前方由演绎千里眼、顺风耳、直库、侍女等的人员开道,队伍中间由“船主”夫妇携8名“船员”肩抬妈祖神舆,一人手持护神凉伞紧密跟随,力图再现历史上的“菩萨扬”“菩萨乘”的盛景。整个巡游队伍自长崎孔子庙出发,途经唐人屋敷、眼镜桥等长崎名胜古迹,最后到达巡行终点——兴福寺。这一巡游队伍得到沿途数以万计的长崎市民与观光游客的争相赏阅,成为长崎市地方振兴的一大文化符号。
站在价值与表征的视角,就日本或者日本人而言,妈祖文化的价值不在于传承中国文化,而在于树立日本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持续努力”;妈祖文化的表征也不在于坚持中国文化的本源性,而在于认识到它是作为日常生活的场所性存在,且完全融入于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就此而言,现代日本推崇的妈祖信仰,存在着与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与长崎的妈祖巡游兼顾了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因子不同,矶原天妃神社的祭祀活动则是凸显了日本文化的日常性与生活性。承前所述,矶原天妃神社将天妃神与“弟橘媛”“堆都嘉”等神道教神灵合祀在一道,自昭和三十六年(1961)以后,神社祭礼统一在1月23日和11月23日举行,这一时间设定完全迥异于妈祖传统的祭拜时间。最为令人惊诧的是,神社的“氏子”们,即祭祀信奉某一地区保护神、地方神的地方居民每逢家族出嫁前夕、结婚、孩子诞生之际,皆会到神社再度参拜,将妈祖信仰作为了绝对的依靠。不过,大津市造船厂在新船竣工之后,总是环绕矶原天妃山行驶三圈,喷射水柱以祈祷航海安全(57)松本浩一:《船人たちが伝えた海の神——媽祖信仰とその広がり》,《アジア遊学》2004年总第70期,第173页。,可见妈祖的海神性格亦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下来。这样的一系列表征,一方面演绎出了妈祖文化成为日本本土神道信仰的“转型”,体现出妈祖文化的日常性与生活性;一方面则依旧不曾脱离传统的“天妃信仰”的原初性,喻示着中国传统信仰在日本的传承与保留。不管如何,妈祖信仰在此作为了地域性的、场所性的存在,尤其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完全融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如果说妈祖文化以历史性的存在、媒介性的存在、场所性的存在等表现形式构成了日本的“都市祭祀文明”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一架构。一方面,站在“祭祀研究”的视角,或许可以梳理出妈祖信仰的祭祀活动如何彰显现代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与集团结构”,探究华人华侨是如何融入日本社会,进而日本大众是如何接受妈祖信仰的心理过程,从而为这一祭祀活动的宗教仪式、祭祀观念来提供现代性的证明;一方面,站在“城市观光”的视角,或许可以探讨“妈祖巡行”是如何推动长崎城市改造,改变世界人的长崎印象,进而与地域开发、城市振兴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以妈祖文化的海外传播为镜像,由此反观中国自身,从而可以审视妈祖文化是否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嫁接、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契合、实现了价值与表征的共生,这是当下尤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结 语
站在中日文化交流的立场,审视妈祖信仰在整个日本的传播,一传琉球官方信仰,二传长崎唐人信仰,三传东日本本土信仰,妈祖信仰在日本经历了一个自官方信仰,逐渐融入本土地域,且进一步扎根于民间的曲折经历。无论是在被奉为官方祭祀的琉球,还是处在锁国状态下的长崎,或是在奉行国粹主义的茨城,妈祖信仰既维持着自身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格,也与日本的本土文化共存共融,成为中国文化走向海外、走向世界的一大标志。尤其是到了当下,妈祖文化作为文化传播的历史性存在,构成了日本社会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文化传承的媒介性存在,复兴于日本都市祭祀文化之中;作为日常生活的场所性存在,融入于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妈祖文化在现代日本的再度转型,既表现了日本文化的多元化、多样性的存在样态,也潜在地提示了妈祖信仰作为现代都市祭祀文明的无限生机与再生价值。
2009年9月,“妈祖信俗”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妈祖信仰具有了世界性的价值与现实性的意义。正如2019年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参加第四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时所发出倡议:“让我们在妈祖海神的呵护下,推动人员与文化的密切交流,创造彼此更多的利益与合作的成长点,培育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58)《第四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之专家主旨演讲》,莆田文化网,2019年11月7日,http://www.ptwhw.com/?post=23340。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21世纪,作为一个历史的、实存的文化媒介,妈祖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共生共长,沟通了人与人的和谐交往。作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成功案例,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转型,彰显出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持续的包容力,为当下中国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构筑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与历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