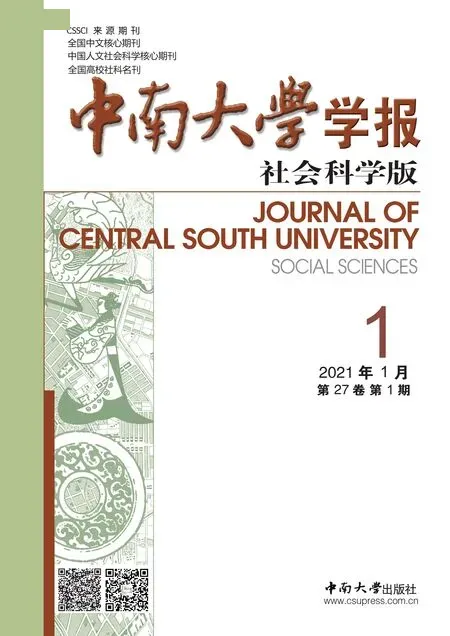返璞归真:中国常态环境史研究刍议
2021-12-01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自环境史诞生以来,探究环境史理论者,大都对环境史中“环境”的意蕴进行过思考。向国内大力介绍环境史的世界史学者,如侯文蕙[1-3]、包茂红[4]、梅雪芹[5-6]、高国荣[7]等人,大都从环境史的定义、研究方法、价值取向等方面切入剖析环境问题。而中国史学者,如刘翠溶[8]、李根蟠[9]、王利华[10-11]、景爱[12-13]、侯甬坚[14]、钞晓鸿[15-16]、蓝勇[17]等人,在探究中国环境史研究思路与方法时,也往往从上述几个方面关照环境问题。相关成果极大地拓展了环境史研究的疆域,也加深了人们对“环境”内涵的认识。不过,以上研究多着眼于“变态环境”,除笔者曾撰文从“变态”与“常态”两种状态的角度思考过环境问题外[18],尚无人对“常态环境”有过探讨。笔者不揣浅陋,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一、常态环境与变态环境
就环境的存在状态来看,环境史所探究之环境,或者说与人类彼此因应之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大致分两种,一为常态环境,一为变态环境。美国学者沃斯特和休斯都将环境史的研究主题划分成三大类:环境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人类行为造成的环境变化以及该变化对人类的反作用,环境思想史[19]。他们虽没有对环境的状态作出界定,但划定的第一大类主题更接近于常态环境,而第二大类主题则比较契合变态环境。
笔者以为,常态环境是指在较长时间内稳定存在的环境状况,虽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但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不易为人所察觉。人类长期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某地是山地还是平原,位于内陆还是滨海,土壤是肥沃还是贫瘠,植被是丰茂还是稀疏,水文条件是水域辽阔还是河流湖泊稀少,气温是温暖还是寒冷,降水是丰沛还是稀少,矿产资源是丰富还是匮乏等,这些环境特质都有较稳定的特征,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会形成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与思想观念。古希腊人与古代中国人的社会风貌、风俗习惯与思想风格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与他们生活环境的不同有很大关系。狂热的环境决定论当然不可取,但“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深刻地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变态环境是指突然发生剧烈的变化但持续时间却很短的环境状况,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极为惊人。在此类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会遭受剧烈冲击并发生诸多变化。如某地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重大灾变时,出现气候变动导致旱灾、水灾、风灾、蝗灾等农业灾害时,天花、鼠疫、霍乱、流感等瘟疫流行时,地方叛乱、民众造反、异族入侵等社会变乱发生时,原有的社会组织、规范秩序、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等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严格来说,没有绝对静止的环境状态,所谓的常态是就相对意义而言,其实也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常态环境与变态环境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发生和缓的、渐进式的量变,而后者则主要发生猛烈的、短促的质变。量变通过较长时间来形塑某一区域社会的整体风貌,而质变则会迅速瓦解原有的社会格局并改绘该区域的社会风貌。
在前工业时代,绝大部分的变态环境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人类导致的环境巨变,则往往是工业社会造成的。历史学者一再强调传统社会人类对自然干预力量之强大。如伊懋可即认为,中国当代环境问题并非发端于近代,而是有着至少三千年的漫长历程,这一过程是“慢慢进行的灾难”,“不可阻挡的导致生命支持体系之衰弱甚至破坏”[20]。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历经数千年的改变远不如工业社会几百年来对环境的影响大。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巨大发展时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1]这段话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揭示出人类对环境影响的巨大差异。毋庸置疑的是,在工业社会,人类引发了真正意义上的环境质变。
学者对此早有认识。如老麦克尼尔在探究传统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时,将对环境质变起因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自然因素上,比如瘟疫的流行[22]。国内学者探究灾荒史、疾病医疗史时也是如此。而关注人类导致环境巨变的学者往往将视野投向了工业社会,特别是在20世纪。小麦克尼尔对20世纪的全球环境史作了全景式的阐释,展示了人类在扰动全球岩石圈、土壤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及人造生态系统方面的惊人威力[23]。沃斯特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尘暴的深入研究,同样揭示了人类对环境的巨大影响力[24]。在其他国家或区域环境史研究中,凡关注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变问题者,也大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业社会[25]。
在环境史研究中,我们需要避免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本身是流动不居的,有史以来的自然环境巨变往往是由自身变化引发的。如太阳辐射的周期性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磁场反转、洋流与大气环流异动等自然现象,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传统时代,人们无力应对;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依然束手无策。如导致全球气候异常的厄尔尼诺现象与拉尼娜现象,虽然学界已对其成因机理及影响气候的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得出了准确的结论,但迄今尚无可行的技术手段对其进行干预[26-27]。又如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的大爆发,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无夏之年”,不少国家发生的政治动荡与此有关,我国也被卷入其中,农业与渔业收成均遭受重创[28-32]。诸如此类自然灾害,人类都只能听天由命。
无论是探究变态环境还是常态环境,我们都应重视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逻辑,不必将一切变化过程都打上人的印记。没有人,自然照样有沧桑巨变。
变态是暂时的,而常态则是长久持续的,我们朝夕相伴的是常态环境而非变态环境。变态环境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留下浓重的印记,但常态环境更能发挥“润物细无声”的功效,对社会的影响也往往更为深远。即使是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以后,过往的环境特质依旧会深刻地影响我们。
族群会因所处环境不同而呈现浓重的地域特色。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环境会显著地影响人的身体和性格,“居住在雨量丰富、气候多变的高山地区的民族,身材高大、勤劳勇敢、粗鲁彪悍;居住在气闷的低平原的民族,爱饮热水、身体肥胖多肉、头发皮肤呈棕色,缺乏耐力和勇敢精神”[33]。同样地,中国古人也有类似论述。《管子》认为水土皆万物之本原,地为“诸生之根菀”,水为“诸生之宗室”,皆为“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而齐、楚、越、秦、晋、燕、宋诸国民风之不同皆与水有关[34]。孟德斯鸠详细地剖析了当时世界主要民族的特点,指出以气候、土壤为代表的环境特质对人的体质与社会制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35]。一百年前,埃尔斯沃斯·亨廷顿即指出气候在塑造文化面貌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印象作用,而南茜·兰斯顿则在环境史的范畴内进一步强调了气候问题的重要性[36]。
就个人而言,长期置身于其中或居住过的环境(特别是婴幼儿到青少年阶段)会深刻地影响我们,语言、思想、价值取向、饮食习惯也往往会为其所塑造,而之后无论所处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都难以撼动我们形成的文化习性。所以,一个山东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对煎饼与大葱情有独钟[37]。一个天津人即使来到内陆地区,其滨海习性也会顽强地保留下来,“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依旧会是他的生活理念。而清代文人对于如何发展畿辅地区水利的见解,也因其籍贯在南方还是北方而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也是由其常年生活过的环境特质所促成的[38]。
就全人类而言,虽然我们所居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但远古祖先所生活过的环境状态在历经数百万年以后依然在影响着我们。比如,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丛林之中,但对丛林的向往依旧存在于我们的血脉里,钢筋混凝土组成的高楼大厦无法遮蔽我们对满眼苍翠与鸟语花香的喜好。又比如,我们的食物获取方式已经与远古时期有着质的差异,但祖先的饮食风格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男性喜欢大鱼大肉而女性偏爱吃零食的特征,即与我们祖先的两性社会分工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男性主要负责狩猎,而女性负责采集,狩猎过程中未捕获猎物时无法进食,而采集过程中则可以不时地将草籽、果实放入口中。远古祖先的生活习性建立在当时的环境基础之上,至今顽强地影响着我们[39-40]。
要之,常态环境与变态环境同样值得我们下大功夫、花大力气去探究,两者兼顾,方能更好地彰显环境史的独特魅力。
二、常态环境史研究的滞后性
如前所述,常态与变态之环境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然也都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不过就目前的情形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是关注剧烈的环境变动之下人类社会的反响与应对,或者是关注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急剧的环境变动。常态环境下的人与自然间的故事,历来关注者甚少。
诸多学者对环境史的环境问题作出预判时都突出了“变”字,在有意无意间,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变态环境上。如休斯认为,“起因上通常被视为非人为、至少主要部分不是人力所致的变化”的环境因素与“人类活动引起的变化在自然环境中的影响”,均是环境史的重要关注对象[25]。伊懋可在构设中国环境史研究版图时,指出重要的研究取向是以技术为中心,探讨气候、地貌、海洋、植物、动物等环境因素的变化轨迹[41]。刘翠溶为中国环境史研究开具的10 组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中,有4 组涉及变迁问题,分别是“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其余6 组课题中也大都与“变”密切相关[42](9-11,14)。王利华认为,环境史在对不同时空中人类生态系统特质进行探究时,“从时空经纬中把握它们的历史变化,乃是揭示人类与环境双向互动关系的关键”[43]。梅雪芹追溯中国环境史发展历程时曾指出,环境史“具有将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类历史发展联结起来的学术品格”,开展研究时格外关注“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影响及其历史变化研究的众多成果”[44]。景爱则认为环境史研究的是人类的生产生活“所引起的自然变化的过程和结果,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42](41)。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学界之所以忽视常态环境,原因有三。其一,从资料选取与操作难度来看,研究变态环境较常态环境为易。变态环境之变化显著,因而更有戏剧性,容易为普通人所感知并留下较详细的记录,历史学家可以较为便捷地捕捉相关信息并加以梳理。而研究常态环境,因其变化并不明显,故而缺少戏剧性,资料留存反倒较少,从而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难题。不论是传统史学,还是环境史学,都面临同样的资料瓶颈,越是特异的人物、事件与现象,人们越是会留下大量的记载,而越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人们越容易选择性失明。正因为如此,一部人类历史,乱世所留下的记载远多于治世,而且记载丰度与两者的实际时长严重不成比例。史料限制是史家关注变化的重要原因,研究晚近历史如此,研究古代历史更是如此。
试以《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为例。自李渊称帝至唐朝初步扫平天下共有9年时间,却用了8 卷的篇幅(卷185~192),约合1年用0.88卷;而整个唐朝历时289年,共有81 卷(卷185~265),约合1年用0.28 卷,这其中还包括了安史之乱(8年,卷217~224)和黄巢之乱(8年,卷251~255)两个动乱期,若将乱世都剔除掉,则264年共有60 卷,1年折合的卷数只有0.23。乱世的记载更为详细,于此可见一斑[45]。环境史的记载也有类似问题,重大的气候异常、地震、火山爆发、灾荒、瘟疫流行等事项的记述远比正常环境状况的记述要丰富。
其二,与史料问题相对应,社会大众与史家对日常的历史事件不敏感,对非同寻常的剧烈变动更感兴趣。这也是变态环境问题相关研究远比常态环境问题更丰硕的重要原因。超乎日常生活之外的战争、灾难、改朝换代、政治斗争等,显然更受大众的青睐,而反映日常生活的历史问题并不能激发大众的兴趣。需求决定供给,史家之论著不能完全与社会的需求脱节,自然也会在著史时向大众兴趣靠拢。我们在翻检传统史籍时会发现,每一时代之史书,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该时代社会风潮之印记。
而作为社会大众之一的史家,自身的兴趣也往往与大众趋同。人多有猎奇心理,历史学者也不例外,他们对于有张力的历史情境自然会给予更多的关照。司马迁发愤著史,即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最主要的宗旨[46],《史记》最精彩的篇章也多是对充满变数的征战杀伐与运筹帷幄的描述。J·R·麦克尼尔也指出,“历史学家主要对变化有兴趣”,他在探究20世纪环境问题时只“关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间与地区,对无数持续不变的例子略而不计”[47]。
其三,其他史学分支与环境史的交错与融合,也使得环境史学者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变态环境,而影响极大的则是历史地理学、灾荒史与疾病医疗史。这些史学分支都有独立的发展历程,只是后起的环境史试图将它们整合到自己的旗帜下,以构建更宽阔的学术疆域。这一整合既壮大了环境史研究的队伍,又为相关研究打开了全新的局面。早在环境史理念兴起之前,相关学科对变态环境之研究就已经较为深入了。
历史地理学者非常重视人地关系,当历史地理学者切入环境史研究时,自然会格外关注环境变迁问题。朱士光认为,“人类活动影响而产生的人类历史时期生态环境之变化,即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47]。邹逸麟认为环境史探讨的问题也都应该围绕着“变化”展开,分别是我国的环境演变脉络、演变原因、演变的必然性与或然性、演变给我们的启示[48]。侯甬坚指出,由侯仁之、史念海等人关注的历史时期植被破坏问题揭开了中国环境变迁研究的大幕,研究对象从黄土高原推向全国,流风余韵影响至今,而环境破坏论理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新型的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理念与价值取向[14](26-27)。韩昭庆认为,虽然研究的目的与时间侧重有不同,但历史地理和环境史关注的重点都是人地关系与环境变迁[49]。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者继续经营人地关系理念,关注人与自然互动所导致的环境变迁问题,在历史地理与环境史的交错地带辛勤耕耘,推出了一大批环境史论著,极大地促进了环境史研究的发展。但是在原有的学术理念与思维惯性影响之下,他们的注意点过多地集中在环境的变迁与环境的破坏上,对人为因素的关注相对较为薄弱。王利华曾指出,对于气候、森林、动物、水文、土壤、疾病等问题的研究虽然较多,但对这些环境因素“与社会系统诸要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彼此反馈进而引发或促进系统变迁”的研究还不够,有待进一步推进[43](34)。
灾荒史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变态环境问题,因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才会导致重要的自然灾害,重创生产秩序,并严重威胁民众的正常生活。因其影响巨大,故而古人极为重视,正史中但凡立志多有《五行志》,详细记录历代的灾异事件。而应对灾荒同样受古人重视,如宋代董煟著有《救荒活民书》,明代朱橚编有《救荒本草》。民国以来,渐有对灾荒的系统研究,其中较重要的有邓云特(即邓拓)、竺可桢、潘光旦、蒋杰、陈高庸、李文海等人[50]。灾荒为我们打开了研究的另一扇窗,因其来势汹汹,人与自然激烈交锋,彼此因应与相互制约关系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近距离地窥探人与自然彼此因应的过程。当环境史学者将灾荒史纳入旗下并梳理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时,势不能亦步亦趋,还需很好地区分“灾”与“非灾”两种情形。
环境史对疾病医疗问题的关注同样使得变态环境问题更加光彩夺目。伊懋可在开展中国环境史研究时,虽未涉及疾病医疗问题,但显然认为这是极重要的领域,他指出自己没有时间对相关问题进行探究是“最主要的缺憾与空白”[51]。与灾荒不同,疾病既有与变态环境相关的流行病或称之为瘟疫,也有与常态环境相关的非流行病。一如前文所述,史家对非常规现象更感兴趣,传统的疾病医疗史家已然对流行病有着更大的兴趣,为大家所熟知的重要论著几乎都集中在传染病方面。
威廉·H·麦克尼尔采用宏观视野审视了瘟疫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得出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的结论,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瘟疫塑造了人类社会[22]。国内学者王旭东、孟庆龙也对全球范围内的传染病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揭示了瘟疫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52]。对于特定的瘟疫,国内外对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的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硕[53-55]。此外,美国学者霍普金斯对天花的研究,曹树基、李玉尚等人对鼠疫在中国大流行的研究,余新忠对清代江南传染病流行的研究,梁其姿对麻风病的研究,也较为典型[56-60]。
当环境史学大力介入疾病医疗领域后,受原有学术理念的影响,对流行病的关注也远胜非流行病。试以1993年和2005年在香港和天津召开的两次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最终形成的论文集中反映的情况为例来分析。前者的中文文集一共收录了3 篇与疾病有关的文章,涉及的主题全部是流行病[20];后者一共收录了4 篇疾病医疗方面的文章,也都与瘟疫有关[42]。可见,环境史领域对非传染病的研究亟待加强。
要之,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在已有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之中,都对变态环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常态环境问题则遭到了冷落。变态环境与常态环境是环境史中有关环境问题的一体两翼,目前的情形是厚此而薄彼。未来倘能实现平衡,更广阔的学术疆域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三、常态环境问题研究的理念与取向
如上文所述,学界多重视变态环境而忽视常态环境,是因为变态环境问题在资料、操作及学术积淀等方面都有着先天的优势。如果要推动常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势必要采取全新的视角与方法。
有学者指出,为了更好地探究环境状态的问题,有必要在环境史研究过程中引入“准静态”的视角。这是一个“动中有静,静中又有动”的相对的概念,并不是不承认变化,只是认为变化缓慢且幅度很小,呈现近似停滞的状态。古人所谓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颇能反映准静态的真谛[61]。在准静态视野下,我们可以深入探究常态环境下各种生态因素的状况,思考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进而审视人们如何调适自己的生计方式并形成特定的环境意识来适应特定的生态状况[62]。
可以数学上的函数理念与极值分析方法来帮助我们理解准静态视角的奥义。在进行数理分析时,人们常采用极端假设,将某一变量取极值,把抽象、复杂的问题具象化、简单化,从而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数量关系。我们在探究天人关系时,近似于要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函数关系,则变态环境的研究即相当于将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某一自然因素的作用视作一变量并取极大值,撇开其他变量不论,则自然因素对人的影响一目了然。如此论畸轻畸重,过分重视变态环境而忽视更为常态化的环境情形,显然无法真正参透人与自然互动的奥妙。很多时候,环境因素的变化不明显,我们将其视作一个常量去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许更为可取。
常态环境理念与准静态视角主要适用于四种状况。其一,探究长时间变化不明显的环境问题。比如史前环境史,长达百万年的时间里,环境状况虽也在不断变化,相当多的大型哺乳动物因人类而亡,冰河期逐渐消退,但整体而言根本性的变化并不明显。比如欧洲的中世纪环境史,社会生产、生活、思想观念等无本质的变化,生态状况亦缺少根本性的变化。探究类似的一些问题时,可从常态环境的角度切入进行思考,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皆是如此。比如布罗代尔在探究地中海世界的历史时,既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其总体史理念,又用相当大的篇幅强调了近乎静止的长时段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制约作用[63]。而勒华拉杜里在探究蒙塔尤这样一个小村庄的历史时,他的分析与论述更是立足于近乎凝固不变的环境基础之上[64]。
其二,探究某一时代(特别是前工业时代)的环境史。这相当于从历史演进的时间流中切下某一横截面,这一断面上的环境状态可以视作“准静态”。以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平原地区为例,当天然植被开发殆尽且沼泽、湖泊大都淤塞以后,明清时期的环境状况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呈现出近乎凝固的状态,我们在探究这一时期的环境史时,应关注常态环境下的人与自然之互动关系。同样地,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漠北草原地区,也可用类似的视角去审视。黄宗智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农经济的研究,王建革对明清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和华北社会生态问题的研究,不管其是否承认“内卷化”,其实都是以准静态的环境为立论基础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65-68]。
其三,探究某些特定区域的环境史。在若干与欧亚大陆隔绝的大陆与岛屿地区,近一万年来社会风貌发生变化的幅度较小。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他太平洋岛屿地区即是如此,而大陆主轴呈南北走向的美洲、非洲地区变化的幅度也相对较小。亚欧大陆上的某些特定区域也在传统时期缺少变化,如高山冰川地区、西伯利亚地区、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环境史,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人与自然的交互方式也较少发生质的改变。这些地区的环境特质亦更接近于常态环境,可采用相关理念进行探讨。贾雷德·戴蒙德在阐释一万年以来世界各民族历史进程的巨大差异问题时,认为各自所处环境的气候特质、动植物资源、矿产、致病微生物状况、大陆轴向等因素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69-71]。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探究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历史时,同样认为常规的生态环境因素如信风、洋流等是欧洲人最后获胜的至关重要的因素[72-73]。
其四,探究环境思想史。唐纳德·休斯在《什么是环境史》中用了1 章的篇幅梳理了古代世界环境思想的流变,对古希腊与古代中国先哲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予以了较高的评价[25]。伊懋可同样特别关注环境思想,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用了3 章的篇幅来专门探究中国人的环境观念问题[52]。王利华则特别重视“生态认知系统”,探究了人们对环境的认知方式与知识体系如何形成又如何影响人们同环境的交往模式[74-76]。他们虽然并未刻意强调环境思想的“准静态”问题,但他们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证明了每一特定族群或特定文化的认知与思维模式都有着极强的稳定性与保守性。我们并不否认思想在不断地变化,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观察与阐释自然事物的方法与理念在传统社会的几千年发展历程中,并无本质的变化。
在“准静态”理念的指引下,环境史将实现“动静兼备”,过分关注变态环境的倾向将得以矫正,环境史的特色也将得到极大的彰显。
探究常态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学术积淀不足的短板,这就需要环境史学者具备更强烈的跨学科研究的觉悟。对静态有较多关照的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相关理念、方法,都值得我们借鉴。而这些学科与环境史交错的地带,更是我们探究常态环境问题时需用心开拓的疆域。
民俗学特别注重文化事项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前者指民俗“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即历时的纵向延续性”,后者则指民俗“会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长期相对地固定下来”[77]。民俗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又与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与环境史从最基本的资源利用与生计层面出发去探究社会状况的诉求是相契合的。王利华指出,活命和保命是人类生存的两个基本层面,将人类社会放置于环境系统之中,研究其“应该怎样延续下去、怎样演化发展”[78]。王氏透过对端午风俗的考察,深入考究节日背后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更是环境史与民俗学交融的经典范例[79]。从某种程度上说,环境史也是资源史与生计史。资源与生计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塑造作用,人们对环境的适应、改造与突破,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观念与仪式活动等,既是民俗学关注的范畴,也是开展常态环境研究的重要方向。
人类学并不刻意推动定量研究,而是更强调定性研究。人类学家认为前者往往会带来“非人化的”效果,因为人们过多关注数字可能会忽略“血肉之躯的人类所关切的事情”,也不利于学者探讨不太容易数字化的重要问题[80]。这一特质决定了人类学家少用类似的函数理念去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更偏向于“常量”而非“变量”的思维方式,他们在考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更多地关照了常态环境。如尹绍亭对云南少数民族刀耕火种问题的研究,探究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稳定传承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强调了常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推广现代耕作方式导致的环境巨变持批判态度[81]。近年来,人类学家也积极地介入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对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下的资源利用、思想观念与社会组织等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相关观察角度与思维方式对我们开展常态环境问题研究也是极具启发意义的[82-85]。
考古学对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遗存做了大量研究,其中对动物遗骸、植物籽粒、孢粉等事物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古代的环境特质与生态系统运行状况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环境史学者大都将考古学视为中国环境史的重要本土渊源之一[10,44,86]。而由考古学衍生出来的环境考古学更是与环境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学术诉求为“环境因素对人类生活场所的选择、变更、迁徙所造成的影响,以及环境与人类自身及其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等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87]。考古学主要利用出土的人类实物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而环境考古学则更加关注自然环境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整体而言,虽然环境考古学比传统考古学有更多动态的考量,但依旧是通过对静态样本的分析来探究人与环境之关系,关照的也多是常态环境问题。环境考古学的关注对象主要有四部分,即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古代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和古代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88]。这几个层面均与环境史的研究旨趣高度契合,故而相关研究理念对我们开展常态环境问题研究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
关于常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取向,笔者酝酿的研究构想包括六个方面,即饮食、水资源、能源、人居环境、礼仪习惯、环境思想,并分别做了初步分析[18]。除此之外,还可加上疾病医疗问题。
在历史上,究竟是传染病还是非传染疾病对人的影响更大,这恐怕是个难以争论清楚的问题。但正如前文所述,因瘟疫会在极短时间内重创某一地区甚至全球,又极富戏剧性,故而人们对其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其实,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非传染病的影响并未被忽视,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颇多。如李建民对古代医疗知识体系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生命史学的理念[89]。李贞德对性别与医疗之关联进行了解构,对女性医疗问题有较精辟的分析[90-91]。而于赓哲对唐代疾病医疗的研究也较为突出,对医学体系与医疗观念的研究发人深思,对唐与吐蕃战争中高原疾病影响的探究更是令人耳目一新[92]。唐代风疾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其相关研究有助于理解唐代的政治史与风俗史[93-94]。余新忠对疾病医疗史的研究成果做了细致的分析,其中不少涉及非传染病与医学、疾病观等问题[95]。但整体而言,非传染病方面的论著远没有传染病方面的研究引人注目。笔者以为,在关注某一区域的环境史时,历史上发病率极高的非传染病往往深刻地影响着民众健康、社会风俗和思想观念,若不探究这些疾病,就不能真正理解该区域内人与自然互动的丰富内涵。所以笔者以为,关注常规疾病的意义极为重大。
要之,对常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不够,是当今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学界过多关注变态环境,既与文献丰寡有关,又与史家偏好有关,更与相关学科的惯性思维有关。要推进常态环境问题研究,就必须引入准静态视角,采用跨学科方法,对若干特定领域进行深入探究。开展常态环境问题研究,将极大地丰富环境史的内涵,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帮助我们更全面地审视人与自然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