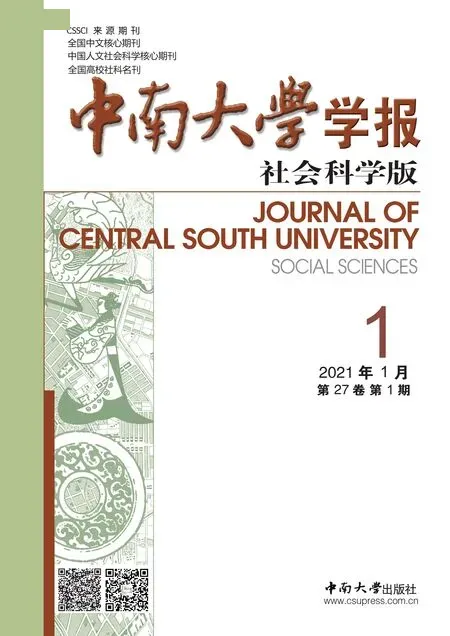《全明词》所收明太祖、建文帝词辨伪
2021-12-01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明清时的词选、词话、方志与笔记中所载的明初君臣所作的词作,往往出自伪托。如清人徐釚《词苑丛谈》卷八所收刘基《沁园春》(生天地间)、《明词综》卷一所收铁铉《浣溪沙》(晚出闲庭看海棠),均已有人作过辨伪①。而《全明词》第一册所收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的词作各一首,分别出自方志及词话,也是疑点重重。现试作辨伪。
一、明太祖《折桂令》辨伪
《全明词》第一册收录明太祖朱元璋“阙调名”词一首:“望东南、隐隐神坛。独跨征车,信步登山。烟寺迂迂,云林郁郁,风竹姗姗。尘不染,浮生九寰。客中有、僧舍三间。他日偷闲,花鸟娱情,山水相看。”[1](112-113)经查《词谱》,此首实为《折桂令》。
此首《折桂令》,编者辑自《金坛县志》卷二,但未附上相应的版本信息。查阅《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可知[2](342-343),现存《金坛县志》共四种,分别修于康熙、乾隆、光绪和民国时期。经核查,此词在上述几种县志中均有记载,现录《(康熙)金坛县志》卷一“山川”:
顾龙山,在县治南五里。前望白龙荡,故名。一名乌龙山,俗呼为土山。平湖澄碧,远山环秀,上有敕建圆通庵、大圣塔、五显灵官庙、季子庙、关帝庙、修真观。左有茅山书院旧基,山地周回一百四十亩。岁丁酉十一月,明太祖东征,尝驻跸于此,题乐府一阕于寺壁,云:“望东南、隐隐神坛。独跨征车,信步登山。烟寺迂迂,云林郁郁,风竹珊珊。尘不染、浮生九寰。客中有、僧舍三间。他日偷闲,花鸟娱情,山水相看。”今勒碑建御亭于其上(知县刘美书)。洪武中有傅敬者,初授金坛尹,陛辞,上谕之曰:“金坛有横山一座,朕曾临幸。”即此山也。御书、僧舍在今圆通庵。[3](99-100)
后续修的几种县志所记与此大致相同。除以上四种县志外,据《(康熙)金坛县志》卷首所收录的分别由王守仁、刘美撰写的《金坛县志序》可知[3](31-37),明代正德、万历年间金坛县均修纂有县志,惜两种书今已不见。《全明词》第一册从《金坛县志》卷二收录此词,经核对卷次,编者应是辑自民国十五年修撰的《金坛县志》。又从《(乾隆)镇江府志》卷首所收录的前志序文内容可知[4](19-20),明代曾在永乐、成化、正德、万历年间分别修纂了府志,惜前三种已佚,仅存《(万历)镇江府志》。清代则有康熙、乾隆所修的两种。现存的三种府志中均有明太祖题乐府于顾龙山寺壁的记载,所记文字俱同,可知后两种是沿袭了《(万历)镇江府志》而来。今录《(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山川下”的文字如下:
顾龙山,在县南五里。前望白龙荡,故名。一名乌龙山,俗呼土山。山上有圆通庵、大圣塔、五显灵官庙、季子庙、汉寿亭侯祠、修真观。丁酉年十一月,明太祖东征,尝驻跸焉,题乐府于寺壁,云:“望西南、隐隐神坛。独跨征车,信步登山。”命词臣续之,曰:“烟寺迂迂,云林郁郁,风竹珊珊。尘不染、浮生九寰。客中有、僧舍三间。他日偷闲,花鸟娱情,山水相看。”今勒碑亭中(知县刘美书)。有傅敬者,初授金坛令,陛辞太祖,谕之曰:“金坛有横山一座,朕曾临幸。”即此山也。[5](539)
将《(康熙)金坛县志》与《(万历)镇江府志》的相关记载相对照,有同有异。所同者,两种方志皆谓丁酉年十一月明太祖东征时曾登临金坛县治南五里之顾龙山,并题乐府于寺壁;所异者,《(康熙)金坛县志》谓整首词为明太祖所作,而《(万历)镇江府志》则谓明太祖仅作了开头数句,后面大部分为词臣所续。所录词作也有个别异文,首句《金坛县志》作“望东南”,《镇江府志》作“望西南”。
又明人邓伯羔《艺彀》卷中有“顾龙山乐府”词条,其文云:
邑有顾龙山,山有御制乐府碑:“望东南、隐隐神坛。独跨征车,信步登山。”此下《县志》直谓高皇帝自为之,《府志》《南畿志》谓词臣续之。此以词臣续之为是,“他日偷闲,花鸟娱情,山水相看”,大哉皇言,曷宜有此。[6](26)
邓伯羔,《(康熙)金坛县志》卷十二有传,“邓伯羔,字孺孝,少即谢去诸生,隐天湖之铜马池,博学洽闻,撰著甚富。郡守王公应麟聘修《镇江府志》,捃摭独详。柯御史督学南中,召为记室,不就,巡抚某以行修学博闻于朝,亦不赴。日徜徉钓雪亭,综述文史,乘兴往来两浙,与诸名流唱和。上下古今,笔无停涉,有《卧游集》四卷藏于家,其《古易诠》二十九卷、《今易诠》二十四卷已行世”[7](312-313)。小传中所提及的郡守王应麟,字仁卿,福建龙溪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知镇江府,任间聘诸名士修府志,府志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付梓,即我们现在所见的《(万历)镇江府志》。又汤宾尹有诗《寄寿邓山人》追怀邓氏,诗曰:“每恨生较晚,不及与同朝。……崛起嘉隆间,身存道独韬。”[8](444-445)据以上材料可知,邓伯羔主要生活于嘉靖至万历年间。其在《艺彀》言“《县志》直谓髙皇帝自为之”,此县志当指现已失传的《(正德)金坛县志》或《(万历)金坛县志》。则至迟在正德至万历年间,已有明太祖登顾龙山并御作乐府的记载;《府志》或指邓伯羔所参与纂修的《(万历)镇江府志》,或指万历以前所作的府志,而《南畿志》当指闻人铨、陈沂所纂,刻于嘉靖十三年的《(嘉靖)南畿志》。
《(嘉靖)南畿志》卷二十四:“顾龙山,在县南五里。前望白龙荡,故名。又名乌龙山。高皇东征,尝驻跸,题乐府于寺壁,命词臣续之,今建御亭于上。”[9](413)此志已经认为现在所见的《折桂令》乐府之开头为明太祖御制,而后面部分为词臣所续。而邓伯羔赞成这一说法,并且进一步从词作内容上进行论证,认为“他日偷闲,花鸟娱情,山水相看”这样的表述,不是皇帝所说的话。看来,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认为朱元璋曾经登临顾龙山,并作乐府开头,词臣续成的观点,已经成为主流观点。
《折桂令》一词,除以上几种记载外,由于早期的几种明代所修纂的《金坛县志》《镇江府志》的亡佚,我们已经无法更详细地考知是否还有更早的文献来源,但从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这些材料来看,此词很可能是假托之作,与朱元璋及词臣并无关系。
首先,几种方志中所记载的明太祖登临顾龙山及题写乐府的时间与史实不合。无论是记明太祖独创的《金坛县志》还是记君臣合作的《镇江府志》,一致认为此词作于丁酉年十一月明太祖东征驻跸于金坛顾龙山时。丁酉十一年即元至正十七年(1357),该年十一月朱元璋未尝东征,亦未取道金坛。据《明太祖实录》卷四记载,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应天府,同年四月“乙丑克金坛县”,至此,金坛县纳入朱元璋辖内。《明太祖实录》也未记录至正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月朱元璋集团的军事活动,但记载有同年十月的战事:
冬十月辛未朔。壬申,中翼大元帅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铜陵进攻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军。遇春及吴国宝帅舟师抵城下,合攻之,自辰至巳,已破其北门,遂入其城,执元帅洪某,斩之,禽别将魏寿、徐天麟等。敌众败走,得粮九千余石。薄暮,敌复以战,船百余艘来,逆战,复大败之。甲申,上阅军于大通江,遂命元帅缪大亨率师取扬州,克之。青军元帅张明鉴以其众降。……至是,大亨攻之,明鉴等不支,乃出降,得其众数万,战马二千余匹,报至上,命悉送其将校妻子至建康,赈给之,置淮海翼元帅府,命元帅张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扬州路为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按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德林以旧城虚旷难守,乃截城西南隅,筑而守之。[10](57-58)
上文中的“壬申”即十月初二,“甲申”即十月十四日,“大通江”在铜陵县境內。十月十四日朱元璋于铜陵大通江阅兵,从地理方位看,铜陵、池州在应天府西北方位,并不需要经过远在东南面的金坛。从“上阅军于大通江,遂命元帅缪大亨率师取扬州”可知,朱元璋并未亲临扬州战役现场,况且自池州出发进军扬州,也无须经过金坛。
方志记载的东征战事,在翌年即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底至十二月之间实有发生。据《明太祖实录》卷六:
十一月乙未朔……甲子,上以枢密院判胡大海兵攻婺州不克,乃自将亲军副都指挥使杨璟等师十万往征之。
十二月乙丑朔,命籍户口。庚午,遣主簿蔡元刚往东阳招长枪元帅谢国玺,不从。其部将何同佥阴遣其属龚敬赍书,以所部兵来降。庚辰,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访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实、姚琏者来见。……乃赐诸父老布帛,抚慰之而去。至德兴,闻张士诚兵据绍兴之诸暨,乃引兵道兰溪,壬午至婺。……甲申,上入婺州,下令禁戢军士剽掠,有亲随知印黄某取民财,即斩以徇。[10](70-72)
以上引文中的甲子即十一月三十日,庚辰即十二月十六日,壬午即十二月十八日,甲申即十二月二十日。那么是否方志混淆了年份,将1358年11月朱元璋亲征误记成1357年11月呢?根据朱元璋南下进军的线路,也排除了这个可能。朱元璋率军十万亲征婺州,自应天经宣城南下,经徽州、德兴、兰溪,依此行军路线,根本无须经过东面的金坛。何况战事危急,朱元璋率领十万大军,更不可能行南辕北辙之事。为防疏漏,笔者一并查阅了《昭代典则》《国榷》《明史纪事本末》等各类史书和今人所撰《朱元璋系年要录》《朱元璋传》《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诸书,但均未能找到与方志记载内容相合的事件,故方志记载丁酉年十一月朱元璋东征驻跸金坛顾龙山并题词之事很可能是虚构的,历史上并无此事。
相关县志、府志“顾龙山”词条下记洪武中傅敬授金坛知县,陛辞时明太祖谓“金坛有横山一座,朕曾临幸”。明太祖是否到过金坛,是何时及什么情况下去的,囿于文献失征,现在已经无法考知了。即使明太祖到过金坛,他所说的“有横山一座”,这座横山是否就是顾龙山,也大有疑问。而且“临幸”与“驻跸”也不完全相同,“临幸”即曾经到过,“驻跸”则是暂住下来的意思。目前所见的《镇江府志》《金坛县志》也没有说明明太祖所说的“有横山一座”,为何就是顾龙山。又考傅敬其人,史料记载甚少,方志中有寥寥数语,《(康熙)金坛县志》卷七《职官志》“明知县”:“傅敬,江西新喻人,洪武中任。”[3](568)《(万历)镇江府志》卷十六记载相同[5](694)。明太祖是否对傅敬说过那番话,其史料来源及其真伪也已无从考究。
另有《大明一统志》《广舆记》二书认为朱元璋驻跸顾龙山的时间为洪武初。《大明一统志》卷十一云:“御亭:在顾龙山。洪武初,车驾驻跸于此,有宝床及御题乐府碑、万岁碑焉。”[11](269)陆应阳《广舆记》卷三云:“御亭:顾龙山。洪武初,车驾驻跸于此,有御题乐府碑。”[12](111)二书的材料来源已无从考知,笔者查阅《明实录》在内的上述诸书,没有记载入明后朱元璋到过金坛,该说亦不可靠。我们现在所见的《大明一统志》系万历年间所刻,已增入隆庆、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内容,而陆应阳也是嘉靖至万历年间的人,这两部书中所记顾龙山有御题乐府碑,可知成书于御碑兴建之后。
其次,御碑当为明太祖作乐府的传说出现并流传之后,万历年间金坛知县刘美所建。《(康熙)金坛县志》卷一“山川志”谓“御书、僧舍在今圆通庵”,该志卷十“寺观”谓:
敕赐圆通庵,在顾龙山,旧名新兴院。梁大同间僧妙高创造。元延祐间重修,有四佛殿、大悲殿,宋元间画笔尚存弥勒殿塔。明太祖东征,尝驻跸于此,赐名圆通庵,其御亭三间,正统十四年二月僧道颖奉旨重修。僧道颖疏称:“切思本庵原系太祖高皇帝驻跸处,所有御床、御亭见在供奉。臣先于正统十二年二月内奉请本庵名额,已蒙敕赐圆通庵外,今臣又思得本庵御亭三间,年深朽坏,欲将自己衣钵收买木料,重新修盖。缘系御亭,未敢擅便,伏望圣恩怜悯,敕部允臣修盖完固,朝夕焚修,祝延圣寿,永图补报。便益谨具奏闻。”奉圣旨:“准他修盖,工部知道。”[7](148-149)
据上文所述,以太祖驻跸为由,新兴院于正统十二年(1447)得赐圆通庵名,因庵中御亭年久失修,僧道颖上疏重修,疏中提太祖驻跸而未言题词之事,述庵中情况时,列御床、御亭,但并没有提到题词寺壁和御碑。由是观之,在正统年间,顾龙山有御亭但无御碑,太祖顾龙山驻跸的故事雏形已经出现,但似乎还没有衍生为太祖驻跸并题词的完整传说。
刻有传为明太祖所作的《折桂令》词的御碑当为万历年间所建。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顾龙山”词条“今勒碑亭中(知县刘美书)”、《(康熙)金坛县志》卷一“顾龙山”词条“今勒碑建御亭于其上(知县刘美书)”等记载可知,御碑为金坛知县刘美所建。《(康熙)金坛县志》卷七“明知县”条目下有言:“刘美,万历四年由洋县任。”[3](570)可知御碑修建于万历四年(1576)后。除建置御碑外,为自圆其说,刘美在顾龙山一带建造了相关的建筑,并以“龙”“蛟”这些象征帝王的文字命名,与高祖驻跸题词传说桴鼓相应。《(康熙)金坛县志》卷二“津梁”:“见龙桥,在顾龙山南,俗名九里桥,明万历八年知县刘美建,自为记,今圮。”“腾蛟桥,在见龙桥西,明万历八年知县刘美建,有记,今圮。”[3](188)
依上文《(嘉靖)南畿志》《艺彀》二书所叙,至迟在正德至嘉靖年间,已有明太祖驻跸顾龙山并题乐府的记载。相较而言,御碑修建时间很晚,御碑的建造应该与知县刘美好大喜功的个性相关。刘美喜立碑撰文,据《(光绪)金坛县志》卷十五“碑碣”记载,刘美在任期内俢撰了县志碑、题名碑和义成广泽二闸碑[13](1248)。另据《(康熙)金坛县志》卷十记载,刘美还重修了县东的龙兴庵并撰碑[3](151)。
最后,从词作内容本身分析,《折桂令》作伪嫌疑很大。从整首词中可以看出,词作者歆羡僧舍生活明净无染,山水之间悠闲淡然,萌生隐居消遣之意,希冀栖身于庙宇山林。观照朱元璋的生平经历,他是不大可能创作出这首词的。朱元璋出生于贫困农民家庭,幼时为地主放牛,十七岁入皇觉寺为僧,是年僧舍乏食,只得托钵流浪,乞食四方,后又返寺。朱元璋出家是为求生计温饱,绝非追寻词中所述“尘不染”“花鸟娱情,山水相看”的超然境界。况且丁酉年十一月东征期间,朱元璋秉钺于身,统率万军,不大可能去怀念过去的苦难生活,更遑论题壁示众。与此同时,当时朱元璋周遭强敌如林,出征途中亦不应有隐退闲居的心境与表述。倘若如《府志》和《南畿志》所言,该部分为词臣所续,作为朱元璋属下,不应不知道其有多年出家经历,续作部分两处提及“烟寺”“僧舍”,下阕有功成身退,回归山中庙宇之意,文字僭越,也不合情理。
除以上的方志等记载外,明代有关朱元璋驻跸金坛顾龙山并创作乐府的故事,另有一个版本。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言:“金坛城外顾龙山,太祖高皇帝时,有于高五郎作乱,亲征,曾驻跸于此,今有御制词刻石碑。”[14](4)
李诩,生于弘治十八年(1505),卒于万历二十三年(1593),字厚德,自号戒庵老人,南直隶江阴人(今江苏属县)。一生坎坷不遇,七试均落第,后淡于仕进,居家读书著述自娱。《戒庵老人漫笔》是李诩晚年的笔记,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由李诩孙李如一初刻。该书记录相关的典章制度、遗闻轶事,兼及学术辨析,内容芜杂,可信度低。《四库全书总目》谓该书“其间多志朝野典故及诗文琐语,而叙次烦猥,短于持择,于凡谐谑鄙俗之事,兼收并载,乃流于小说家言”[15](1105)。《戒庵老人漫笔》今有魏连科的点校整理本,魏氏在篇前《点校说明》直言“有些荒诞不经的异闻,也必一一载入,这些糟粕成为本书之累”[14]。尽管《戒庵老人漫笔》内容真假混杂,难补史书之未备,但该书是唯一记载明太祖征伐对象的文献,我们仍然需要进行覆按。
《戒庵老人漫笔》记载甚为简略,片言只语中唯一有用的信息是“于高五郎作乱”。从称谓上看,“于高五郎”应是其别称而非真名,仅凭《戒庵老人漫笔》的寥寥数语,笔者在各类史书中按图索骥,皆未能找到相对应的人物,所幸最终还是在《(康熙)金坛县志》中发现了线索。《(康熙)金坛县志》卷一“兵事”:“丁酉年,太祖东征,驻跸顾龙山时,县南有余皋五者,拳勇好斗。太祖率□亲征至顾龙山,勒兵□□掩至林中烧杀之。”[3](88)比对《戒庵老人漫笔》《(康熙)金坛县志》二书,“于高五”与“余皋五”音同,可以判定《戒庵老人漫笔》中的“于高五郎”即是《(康熙)金坛县志》中的“余皋五”。时间与方志记载吻合,俱是丁酉年东征,太祖东征事件在前文已证伪。同时,二书在叙事的逻辑关系上相抵牾,依《戒庵老人漫笔》所叙,于高五郎作乱是太祖东征的原因;而在《县志》中,剿灭余皋五只是太祖东征途中为民除害的小插曲。在史书和其他文献中,笔者依旧未能找到“余皋五”的踪迹。退一步讲,若确如《戒庵老人漫笔》所言,明太祖东征“余皋五”或“于高五”,史书中怎会没有任何记载?且太祖为金坛县内一个“拳勇好斗”的地痞流氓而亲自东征,显然不合常理,故《戒庵老人漫笔》乃伪说无疑。
通过对上述材料的梳理辨析,我们可以推测,在李诩生活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朱元璋驻跸题词的传说可能已经衍生为多个版本。李诩为南直隶常州府江阴人,常州府与镇江府相邻,金坛、江阴两县虽未接壤,但相距不远。李如一在《戒庵老人漫笔》的序中称李诩“晚乃纪岁月阴晴、里闬人事”“上搜国家之逸载,下收乡邑之阙闻”[14],明太祖顾龙山题词事应属于“里闬人事”“乡邑之阙闻”之类。书中的“于高五”与县志中“余皋五”音同,应是口耳相传所致。《戒庵老人漫笔》所收的明太祖事,是由东征于高五郎与顾龙山题词两个故事杂糅而成,属于民间流传的故事版本之一。
另,将故事发生地设在顾龙山,可能与“顾龙”之名有关。其实,“顾龙山”的名称并不是依据明太祖驻跸的传说而来的,早在南宋就有顾龙山的记载。《(嘉定)镇江志》卷六《地理志》记载:“顾龙山,在金坛县五里,俗呼土山。下瞰思湖、龙荡,高不能五六丈,而巨石盘亘,瞰平湖数千顷,湖之旁山者,居民占植芙蕖,界以菰蒲,如错锦绣。暑风至则荷香,与偕若非凡境。”[16](418)又《(万历)镇江府志》《(康熙)金坛县志》等书谓顾龙山取名来自“前望白龙荡,故名”,此山因“下瞰思湖、龙荡”“前望白龙荡”而得名,而后人可能望文生义,引申为见龙之意,附会出明太祖曾驻跸于此的传说。
综上所述,《全明词》所收的《折桂令》词乃假托朱元璋所作。太祖因东征而驻跸顾龙山并题词是层累地造成的民间传说:先是明太祖可能对即将赴任金坛知县的傅敬说过自己曾经临幸过金坛一横山,后来好事者因为“顾龙山”的山名附会出太祖所临幸的横山即是此山,并有了驻跸于此的传说。到了正统年间,和尚据此重修寺院并建御亭。在这之后又附会出太祖驻跸于此并题乐府于寺壁的传说。到了万历年间金坛知县又建造了御碑亭,而当地的志书不仅将太祖驻跸于顾龙山当作信史载入志书,而且将该乐府收录其中,或谓太祖御制或谓君臣合作。而后世修撰的志书则陈陈相因,明人笔记也以讹传讹,而《全明词》未加辨析,导致错收。
二、建文帝《满江红》辨伪
《全明词》第一册收录建文帝朱允炆《满江红》一首[1](231),词曰:“三过吴江,又添得、一亭清绝。□占断、水光多处,巧依林樾。漠漠云烟春昼雨,寥寥天地秋宵月。更冰壶、玉鉴暑宜风,寒宜雪。曜庵右,山岚缺。虹桥左,波涛截。正三高堂畔,旧规今别。何□渔翁垂钓好,漫将柳子新吟揭。信登临、佳兴属彭宣,能挥发。”并注辑自《莲子居词话》。此词本为宋代无名氏所作,而归入建文帝名下,当肇始于清人褚人获纂辑的笔记小说《坚瓠集》。该书补集卷二首篇《建文帝诗词》云:
建文帝首至吴江史仲彬家,题诗《清远轩》云:“玉蟾飞入水晶宫,万顷琉璃破晓风。诗就云归不知处,断山零落有无中。”“画鹢高飞江水涨,老渔亟唱夕阳斜。秋来客子兴归思,船到吴江即是家。”又三至吴江,题《满江红》词云:“三过吴江,又添得、一亭清绝。刚占断、水光多处,巧依林樾。漠漠云烟春昼雨,寥寥天地秋宵月。更冰壶、玉鉴暑宜风,寒宜雪。臞庵右,山依缺。垂虹左,波涛截。正三高堂畔,旧规今别。何但渔翁垂钓好,谩将柳子新吟揭。信登临、佳兴属彭宣,能挥发。”又《观竞渡》词云:“梅霖初歇。正绛色海榴,初开佳节。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处玳筵罗列。斗巧尽输年少,玉腕彩纱双结。舣彩舫,龙舟两两,波心齐发。奇绝处,激起浪花,翻作湖间雪。画鼓轰雷,红旗掣电,夺罢锦标方彻。望水中天日暮,犹是珠帘高揭。归棹晚,载荷香十里,一钩新月。”[17](24-25)
《坚瓠集》多取历代逸闻轶事,兼及诗词文章,失实处甚多。记建文故事者,有《半边月》《建文云游》《水月观》《逊国诗纪》等,内容怪诞不经,取材自明以来的各种野言稗史。如《坚瓠集》丙集卷一《半边月》篇载:“建文帝初生,顶颅颇偏高,高皇视之心甚不悦,尝抚而名之曰:‘半边月儿。’每虑其不克终,或以诗对试之。一夕,与懿文同侍高皇侧,命咏新月。懿文云:‘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不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建文云:‘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高皇览之不悦。未几,懿文薨,建文帝又出亡,皆应其语。”[17](589)此事亦见于明人黄瑜《双槐岁钞》卷二[18](35-36)、陈师《禅寄笔谈》卷二[19](603)、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十九[20](380-381)、吕毖《明朝小史》卷三等处[21](499)。《咏新月诗》实为元顺帝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所作,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引叶子奇《草木子》为之辨伪[22](370)。胡丹在《“神奇其说”:建文传说的神秘性探析》一文中也对偏颅之说和《咏新月诗》进行了证伪[23]。
《建文帝诗词》所载建文帝出亡诸事始见于《致身录》。此书于万历后期流传于吴中,托名史仲彬所著,在承袭先前建文传奇的基础上,以第一人称讲述自身得建文帝慧眼赏识,靖难时助其水关出亡,后建文帝三过吴江等事。现引《致身录》建文帝首至吴江片段于下:
彬曰:“大家势盛,耳目众多,况新主谅不释然,能无见告,不若往来名胜,东南西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给而足备一夕者,驻锡于兹,有何不可?”师曰:“良是。”(笔者注:师即建文帝)于是更举七家:廖平、王良、郑洽、郭节、王资、史仲彬、梁良玉。师曰:“此可暂,不可久。”况郊坛所在,明旦必行,将何所之,众议浦江。郑亦曰:“族俱忠孝,可居也。”夜分师足骨度不能行,微明牛景先与彬步至中河桥畔,谋所以载者,有一艇来焉,闻声为吾乡,急叩之,则彬家所遗以侦彬吉凶者也。与牛大快,亟迎师,且至彬家,诸人闻之,且喜且悲,同载八人,为程、为叶、为杨、为牛、为冯、为宋,余俱走散,期以月终更晤。取道溧阳,依叔松隐所,不纳。八日始至吴江之黄溪,奉师居之西偏,曰“清远轩”,众出拜,师亦大适。[24](5)
后两至吴江部分,笔者惮烦不引。《建文帝诗词》载诗、词各二首,其中《清远轩》一诗,取名应源自上文《致身录》中的居所名“清远轩”。《致身录》来历可疑,情节怪诞,问世以来屡遭辨伪,诸多学者进行了文献翔实的考证,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云:
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录》者,谓其先世曾为建文功臣,因侍从潜遁为僧,假称师徒,遍历海内,且幸其家数度。此时苏、嘉二府逼近金陵,何以往来自由? 又赓和篇什,徜徉山水,无一讥察者?况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报命。观《忠安传》中云:“穷乡下邑。无不毕至。”胡为常州人,去此地仅三舍,且往来孔道也,岂建文君臣,能罗公远隐身法耶?所幸伪撰之人,不晓本期典制,所称官秩,皆国初所无。且妄创俚谈,自呈败缺。[25](9)
对此书考辨最有力者当属钱谦益。钱氏作《〈致身录〉考》,分析吴宽为史仲彬所作墓表等材料,列十条“必无”证据,判定《致身录》为后人伪造[26](755-758)。钱氏十论,理据皎然,《致身录》之伪庶几定谳,其后潘柽章、潘耒等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考证,笔者不再一一详说。《致身录》既伪,《坚瓠集》中的《建文帝诗词》以《致身录》为背景,亦应是伪造而成。
现从《(弘治)吴江志》卷十九、卷二十二“集诗”中发现了《建文帝诗词》所载二诗、二词,俱标为无名氏所作。经核对,《(弘治)吴江志》卷十九收录的七言绝句《适吴江》(二首)即为《建文帝诗词》中的《清远轩》(二首)[27](443),卷二十二收录的失调名二词《钓雪亭》《吴江观竞渡》则为《建文帝诗词》中的《满江红》《观竞渡》[27](597-598)。比对二书,除题目不同外,内容亦稍有删改。《(弘治)吴江志》中《钓雪亭》词上片首句为“三过松江”,下片第六句为“旧观新别”,而《建文帝诗词》则是“三过吴江”“旧规新别”。又如《适吴江》(其二)末句为“船到松陵即是家”,《建文帝诗词》改为“船到吴兴即是家”,显系迎合建文出亡故事背景而有意篡改。现经查证,《适吴江》(玉蟾飞入水晶宫)为南宋苏庠所作,《全宋诗》卷一二八八据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十四收录[28](14605)。另一首《适吴江》(画鹢高飞江水涨)未见于其他文献。在《(弘治)吴江志》卷十九中,二首《适吴江》系于同一无名氏名下,前者为苏庠所作,《适吴江》(画鹢高飞江水涨)也当判为苏庠佚作。《吴江观竞渡》一词即为北宋黄裳词作《喜迁莺·端午泛湖》,见于黄裳《演山集》卷三十一[29](209),《全宋词》第一册收录[30](378)。而《钓雪亭》,即《全明词》收录的建文帝《满江红》词,现无法找到其他文献来源,《(弘治)吴江志》卷二十二该词之前有言“此后俱宋人”,故仅知此词为宋代无名氏所作。综上所论,《坚瓢集》补集卷二首篇《建文帝诗词》所载建文帝诗词四首均为宋人所作,《建文帝诗词》或摘录自《(弘治)吴江志》,或出自同一来源。
《坚瓢集》误收在先,后人词集相继因袭。清人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十六选建文帝《满江红》词,于词末标注《坚瓠集》[31](2089)。清人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八摘录此词,词后疑其真伪,作者注云:“余谓老还大内,死葬西山之说,断不足信。若《致身》《从亡》等录,与《坚瓠》所载诗词,咸具不忍死其君之心,疑以存疑可耳。”[32](2675-2676)而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三著录此词[33](2642),未标明出处,《全明词》据此收录,未考镜源流,以致错收。
三、结语
《全明词》收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词各一首,经过对文献材料的发掘、稽考、释证,二词皆系伪作的事实彰明较著,因此笔者在重编《全明词》时,将二词剔除不录。
据《全明词》记载,这两首词分别辑录自清代以后的《金坛县志》与《莲子居词话》。推而广之,在从事文献辑佚和采录工作时,当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与追本溯源的方法。就明代而言,对于汤显祖、李贽这类著名文学家和朱元璋、朱允炆这类带有传奇色彩的帝王,被后人伪托的概率是非常高的②,因此,在文献整理出版如火如荼、古籍数字化蔚为大观的今日,采录佚作时更要谨慎。
注释:
①刘基词辨伪见周明初《刘基佚词四首小考》,原载《刘基文化论丛》第2 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今已收入《明清文学考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61—364页;吴留营《有关刘伯温的诗词考述二则》,载《文献》2018年第5 期;而铁铉之词实为五代李珣所作,清人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九已经指出,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73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王兆鹏进一步指出此词已见于《花间集》卷十,见王兆鹏点校《明词综》,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②关于明清文献辑佚与整理时材料采录的可靠性问题,笔者在《〈汤显祖集全编·诗文续补遗〉辨伪》一文中已指出。(《文献》2017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