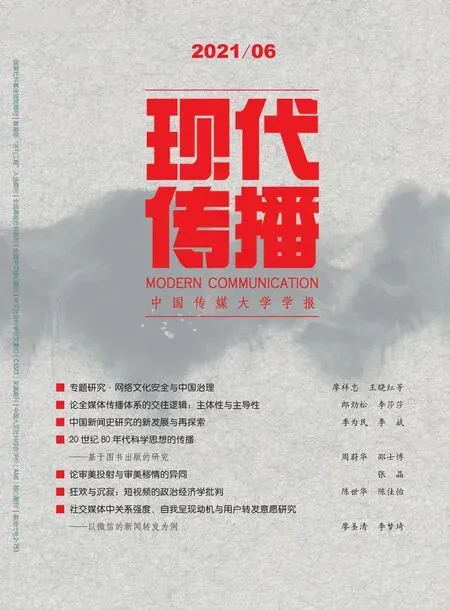论审美投射与审美移情的异同
2021-12-01■张晶
■ 张 晶
稍通美学的人对于审美移情都不会感到陌生,这是西方美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从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康德,到19世纪的费肖尔父子、立普斯、谷鲁斯等,都是将移情作为最根本的审美心理机制。其中在理论上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立普斯。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史》这部名著中,对移情说有系统的评述。而关于“审美投射”这个范畴,在国内学术界就罕有深入的讨论。据笔者所了解的,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中华书局2013年版)中,有《心理定向与美的幻觉——谈审美投射》的专章,笔者则有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上的《论审美投射与审美构形》一文。而在西方学术界,英国著名的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则是投射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笔者关于投射的观点,也多半是借鉴于贡布里希的投射理论的。现在的问题是,移情与投射都是审美主体对于客体的外倾,移情的方式多处被译为“外射”。就其共同之处而言,移情与投射,都是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交融过程,而且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倾。但是,投射与移情是否就是同样的心理机制?是否有必要将“投射”作为一个审美心理问题加以深化研究?质而言之,投射与移情的差异之处究竟何在?这是本文的论旨所在。
一
移情的内容主要是主体的感觉、情感、意志等,而所移入的对象,主要是无生命之物;投射则是将主体积淀的内在图式贯注到客体中去,又以客体的原初形态作为对图式的矫正和生成的契机,从而生成新的审美知觉。主张移情说的美学家以移情作为审美经验的本质特征,而主张投射的美学家,则以投射作为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的必经之途。
关于移情,朱光潜先生在西方美学家移情说的基础上,有这样的概括:“什么是移情作用?用简单的话来说,它就是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同时,人自己也受到对事物的这种错觉影响,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和共鸣。”①这个阐述是颇为简明而清晰的,凝缩了西方近代美学中移情理论的传统。康德在论述崇高感时分析了人在自然中感受到的“崇高”,认为:“所以那对于自然界里的崇高的感觉就是对于自己本身的使命的崇敬,而经由某一种暗换付予了一自然界的对象(把这对于主体里的人类观念的崇敬变换为对于客体),这样就像似把我们的认识机能里的理性使命对于感性里最大机能的优越性形象化地表达出来了。”②这里的“暗换”,朱光潜译为“偷换”,意思完全一样。康德在美学方面的一个基本命题是:“美是道德精神的象征”,而对于其间的联系,康德也是通过移情现象来说明的。作为移情说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弗里德里希·费肖尔,将移情作用称为“审美的象征作用”,指出:“这种对每一个对象的人化可以采取很多的不同的方式,要看是对象属于自然界无意识的东西,属于人类,还是属于无生命或有生命的自然。通过常提到的紧密的象征作用,人把他自己外射到或感入到(fuhlt sich hinein)自然界事物里去,艺术家或诗人则把我们外射或感入到(fuhlt sich hinein)自然界事物里去。”③费肖尔所说的“象征作用”,就是美学界确认的移情作用,他的儿子劳伯特·费肖尔,就把这种“审美的象征作用”,改称为“移情作用”。与其父相比,劳伯特·费肖尔把这种“自然的人化”的性质,从“移入感觉”转为“移入情感”,因为情感比起感觉来,是更深刻更亲切的心理活动。我们通过朱光潜先生的阐述来理解劳伯特·费肖尔在移情理论发展中的地位,“到了‘移入情感’(即移情作用),审美的活动才达到最完满的阶段,‘我们把自己已完全沉没到事物里去,并且也把事物沉没到自我里去,我们同高榆一起昂然挺立,同大风一起狂吼,和波浪一起拍打岸石。’费肖尔反对用记忆或联想来解释这种移情现象,因为移情现象是直接随着知觉来的物我同一,中间没有时间的间隔可容许记忆或联想起作用。”④里普斯作为移情说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以移情作用来解释审美快感,他认为审美快感是由于主体看到对象而产生的,而在对象中所感受到的快感,其实是主体的“自我”。他说:“审美的欣赏是一种愉快或欣喜的情感,随着每次个别情况带有独特的色调,也随着每个新的审美对象而时时不同——这种情感是由看到对象所产生的……审美欣赏的‘对象’是一个问题,审美欣赏的原因却另是一个问题。美的事物的感性形状当然是审美欣赏的对象,但也当然不是审美欣赏的原因。无宁说,审美欣赏的原因就在我自己,或自我,也就是‘看到’‘对立的’对象而感到欢乐或愉快的那个自我。”⑤里普斯更为明确地认为:“移情作用所指的不是一种身体感觉,而是把自己‘感’到审美对象里面去。”⑥里普斯以雕像为例,说明移情作用在雕像身上的产生,并与真人比较:“我在看到一座表现一个人正在起立的雕像时,一个实在的人在起立时所例有的器官感觉,和我自己的器官感觉一样,对于我的审美观照都是不存在的。我从那座雕刻形象里所立刻直觉到的是它的发动意志,它的力量,它的自豪。只有这个对于我的观照才是直接现在所观照的对象上面的。除直接现在观照对象上的东西以外,就绝对没有什么是属于审美对象的。”⑦里普斯是将移情作用作为审美快感的本质,在他看来,只要是审美对象,对于主体而言移情作用是必定存在的。在《再论“移情作用”》这篇经典文章中,里普斯又作了这样一个区分,即移情作用的情感和“我对一个对象的情感”之不同,他说:“移情的情感还有一个分别,即‘我在对象里面’所感觉到的那类情感和我对一个对象所生的那类情感不同。……如果我在一根石柱里面感觉到自己的出力使劲,这和我要竖立石柱或毁坏石柱的出力使劲是不大相同的。再如我在蔚蓝的天空里面以移情的方式感觉到我的喜悦,那蔚蓝的天空就微笑起来。我的喜悦是在天空里面的,属于天空的。这和对某一个对象微笑却不同。……移情作用的意义是这样:我对一个感性对象的知觉直接地引起在我身上的要发生某种特殊心理活动的倾向,由于一种本能,这种知觉和这种心理活动二者形成一个不可分裂的活动。……对这个关系的意识就是对一个对象所生的快感的意识,必以对那对象的知觉为先行条件。这就是移情作用。”⑧里普斯所作的这个“分别”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它进一步指出了移情作用的本质特征。它并非我们对一个对象的感觉,而是一种在对象中所知觉到的主体的情感,于是对象也就如同有了和主体一样的情感。里普斯的移情理论并非泛化于一般的心理活动,而是以文艺创作和欣赏的心理为基本内涵的。乃如英国著名美学家李斯托威尔的评价所说:“移情论的权威倡导人是里普斯。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为详尽地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艺术和审美鉴赏的每一个方面去。”⑨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别,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人间词话》)静安先生所说的“有我之境”,其实正是“移情作用”,“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就是主体将情感移入到对象中去,使之有了与主体一样的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移情”现象颇多,略举一二,如“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天涯离恨江声咽,啼猿切,此意向谁说?”(顾夐:《河传》)“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李煜:《临江仙》)“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张昇:《离亭燕》)“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苏轼:《赠刘景文》)“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柳永:《八声甘州》)“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姜夔:《点绛唇》)“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姜夔:《扬州慢》)“一个幽禽缘底事,苦来醉耳边啼?月斜西院愈声悲。”(晁补之:《临江仙》)“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毛滂:《惜分飞》)等等。诗人将自己的情感意绪移入到对象中去,使所描写的物象,都浸透着诗人的情感意绪。
再看我们所说的审美投射。这种投射,我们也主要是将其置于艺术创作与欣赏的范围内来理解的。投射与移情都有外倾的过程,因而使人感到相当接近,以至于难以区分。但笔者以为,移情顾名思义,其内涵是主体的审美情感,而投射则不然。笔者以为审美投射的内容是艺术家主体内心持存的艺术图式。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对投射的界定是:“投射是人的一种心理能力,是主体将自己的记忆、知识、期待所形成的心理定向,化为一种主观图式,投射到特定的客体上,使客体符合主观图式,促成幻觉的产生的心理过程。”⑩童先生是以投射为一种普遍性的审美心理能力,而笔者所论,主要在于艺术创作和欣赏过程中的审美投射。
二
在著名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的理论体系中,“投射”这个范畴的重要性是贯穿始终的,也可以认为是贡布里希艺术理论的逻辑起点。在《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这部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中,“投射”是艺术创造的心理依据。贡布里希以心理学试验的著名案例“罗夏测验”来说明投射的一般性心理学机能。“在所谓的‘罗夏测验’(Rorschach test)中,把一批标准墨迹(standard inkdlot)交给受试者进行解释,同一块墨迹会被解释成蝙蝠或蝴蝶,更不用说在用这种测验方法所积累的浩瀚文献中我们所发现的无数其他可能情况了。罗夏本人强调说,在正常知觉即我们心灵中的印象归档跟由‘投射’引起的种种解释之间,只有程度的差异。”艺术史家用“投射”理论来解释起源问题,贡布里希是深以为然的。投射是一种心理定向,而且是图式化的心理定向,这是一种错觉产生的必要机制,而所谓错觉,乃是艺术创作的原始动力。贡布里希指出:“我们所说的‘心理定向’,可能正是指准备开始投射的就绪状态,指准备把那些总是在我们知觉周围闪烁不定的虚幻色彩(phantom colour)和虚幻物像(phantom image)的触角伸出去的就绪状态。——一种投射,即一种读解,一旦在我们面前的物像中找到锚地,要把它去掉就困难多了。这在读解画谜时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经验。”对于绘画艺术而言,没有图式的投射,就不会有创作的开始。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所举的关于投射最经典的例子,竟然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段趣事。即宋代画家宋迪指点陈用之作山水画方法的记载。宋代著名科学家及艺术评论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往岁小窑村陈用之善画,迪见其画山水,谓用之曰:‘汝画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迪曰:‘此不难耳,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其有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用之自此画格得进。”在贡布里希看来,宋迪的这种方法,正是投射的经典之用,这当然也是一种艺术创作方法的训练。在绢素复盖于败墙的隐约图形中,引发了主体的艺术错觉,又将它们投射到这个“屏幕”之上,从而形成了种种山水之象。当我们面对一个自然物像,准备进行摹写或加以改造而成为画面时,投射就已经进行了。贡布里希解析了这个过程:“即使承认我们的预测在知觉中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已使一位心理学者及运动和知觉二者的统一——这种眼光难道不妨碍对读解绘画和生活情境中观察世界这二者进行什么比较吗?在某种程度上讲,确有妨碍。世界决不会向我们呈现中性的画面;意识到世界就是意识到我们能够试验并检验其有效性的那些可能情境。艺术的奇迹之一,就是它能够迫使我们把这种态度、这种检验应用于一件大自然的模仿之作,一个静止的物像。在上一章我们已看到,这样一件模仿之作的的确确激励着我们进行探查和预期,投射我们的预测,从而建立起一个想象中的错觉世界。”贡布里希在论述投射时针对的是绘画创作的心理过程。艺术家必须学习和掌握传统的图式,而在临机面对自然时,就会将图式投射到所要表现的对象中去,然后,再从艺术表现对象中获取当下的契机,对原有的图式进行矫正,从而产生新的图式。贡布里希在另一本书里更明确地指出:“画家的起点决不可能是对自然的观察和模仿;一切艺术都是所谓的概念性艺术,即对一种语汇的掌握;甚至最自然主义的艺术一般也都以我所说的某个‘图式’为起点,接着是对这个‘图式’进行修正和调整,直到使它看上去与可见世界相匹配。”从中也可以得知,与投射密切相关的乃是图式,而非情感。在此一点上,投射与移情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谈及投射就不能不讲到图式,那么图式又是什么?这在贡布里希的理论体系中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实体性范畴。图式本来是有着心理学的根源的,在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理论中,图式是一个源初性的范畴。贡布里希在绘画心理学的角度上所用的“图式”,当然也有着深厚的心理学背景,但它的语境却是绘画艺术创作。贡布里希正面回答了图式这个范畴的涵义,他说:“我们从这些实验中得知,摹写是以图式和矫正的节律(rhythms and correction)进行的。图式并不是一种‘抽象’(abstraction)过程的产物,也不是一种‘简化’(simplity)倾向的产物;图式代表那首次近似的、松散的类目(category),这个类目逐渐地加紧以适合那应复现出来的形状。”容我在这里加一点个人的理解:图式不同于柏拉图的“理式”,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它是艺术家内心中持存着的某类艺术品的框架,在造型艺术中当然就更为直观,而如文学作品,则是以语言媒介勾勒出的内在直观。现象学美学家茵加登将“图式化外观”作为文学作品的内在层面,笔者认为这是本质性的东西。贡布里希在谈到希腊艺术时指出:“希腊革新可能已经改变了艺术的功能和形式,但它并不能改变制像的逻辑,不能改变这个简单的事实:没有一种媒介,没有一个能够加以塑造和矫正的图式,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能模仿现实。”贡布里希援引心理学家艾尔在实验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说:“训练有素的画家学会大量图式,依照这些图式他可以在纸上迅速地画出一只动物、一朵花或一所房屋的图式。这可以用作再现他的记忆图像的支点,然后他逐渐矫正这个图式,直到符合他要表达的东西为止。”图式与矫正是贡布里希的绘画心理学的基本逻辑。
图式究竟是个性化的抑或是一种原型?笔者以为,贡布里希所讲的“图式”,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平衡。图式的获得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是传统的学习中习得的产物,同时,又通过心灵与外物相接而注入了新的生命。在这里,不妨参照英国学者诺曼·布列逊在他的“新艺术史”三部曲之二《视觉与绘画:注视的逻辑》一书中的细致分析来表明笔者的理解,布列逊指出:“可以相信,贡布里希内心所具有的图式目标不只是一个归因问题:其口径大大超过了莫雷利(1816—1891,意大利美术评论家,其直接研究方法为以后的艺术批评奠定了基础。)那种只针对个别画家的狭窄性。在莫雷利视图式为个人特征的标签而加以研究之处,恰恰正是图式的超个性本性亦即贡布里希的兴趣所在。历史是被认可为比个人化的传记更高水准上起作用的一种力量:图式被视为一种普遍文化遗产,就像一份潜移默化的汇集的总目有效地为个别艺术家所用,并在绘画实践的直接环境中由个体的画家加以地域化与修正。反之,我们可以说,莫雷利却因图式具有的超个性范围,认为对确定归属的科学不起作用,就将其从普遍文化遗产中排除了出去,也因此他独独关注于图式的个性变化,而贡布里希则两者兼顾。”布列逊是在客观的立场上分析了贡布里希与莫雷利在图式问题上的不同理论观点。笔者以为布列逊的阐述是能给我们对图式问题以一个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认识角度的。莫雷利的看法是认为图式是个性化的,而全然不顾及它的传承性因素;而贡布里希则主张,图式是艺术家从传承中获得的,具有原型的性质;但它又在艺术家的具体艺术经验中与鲜活的当下对象相交接,使既有的图式得到矫正,从而获得属于该艺术家个人所亲自建构的新的图式。布列逊进而谈到贡布里希所说的“图式”的传承性质:“根据贡布里希的观点,画家并不是以纯朴或自然的眼光注视着这个世界,并用画笔照录出在其目光中显示的东西。在画家与眼睛之间,介入的是根据画家的特定艺术传统所打造的一整套图式体系。画家所做的,科学家所做的,都是任经验的观测去测试这些图式:他们的产品不可能是一种用转录真实的方式反映宇宙的本质的复制;它将是一种对现有假说或图式汇总的暂时与临时的改进,是因为面对世界通过证伪的测试而被改进的。”不仅在绘画中,在其他艺术门类中,如戏剧戏曲、音乐、舞蹈、书法等,图式体系都是艺术传承的链条。中国山水画论中所说的“丘壑”,其实就是这样的图式体系。“丘壑”在画论中一般并非指自然界的丘壑山岭,而是指画家内心持存的内在山水图式。因而,又被称为“胸中丘壑”。黄庭坚称赞苏轼所画枯木:“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题子瞻枯木》)明代大画家董其昌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都标示出了“丘壑”是内在于画家内心的。“丘壑”是画家从前人的名迹那里习得的山水图式。清代画家笪重光说:“凡作画者,多究心笔墨,而于章法位置,往往忽之,不知古人丘壑生发不已,时出新意,别开生面,皆胸中先成章法位置之妙也。”清代画家华琳主张从临古人成稿以养成丘壑,他说:“作画惟以丘壑为难,过庸不可,过奇不可。古人作画,于通幅之屈伸变换,穿插映带,蜿蜒曲折,皆惨淡经营,然后落笔。故文心俶诡而不平,理境幽深而不晦。使人观之,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而又一气婉转,非堆砌成稿,乃得山川真正灵秀之气。初学之士,固不能如吴道子粉本在胸,一夕脱手。惟须多临成篇,使胸有成竹,然后陶铸古人,自出机杼,方成佳制。不然师心自用,非痴呆无心思,即乖戾无理法。如文家之不善谋篇,虽有绮语,位置失所,翻多疵谬。且成稿亦岂易办,其笔墨佳而丘壑佳者无论矣,其笔墨不佳而丘壑不佳者亦无论矣,间有笔墨殊无可取,而丘壑甚佳,此临前人成稿,而欲作伪者。遇此等画,亦不得率然弃之,取其丘壑,运以自己之笔墨,安见不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至于成稿临熟,欲自成丘壑,则当于画出主树之后,先落一二笔以取其势,次定宾主,次分阴阳,类医家之立方,有君而后有臣,有佐使也。”姑且置那些专业性的问题不论,由中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丘壑”,是画家由古人成稿中习得的。同类的画材,大致会有相应的“丘壑”,而经过历代画家的踵事增华,丘壑也就成一体系了。贡布里希谈到图式的预期性时就举了中国绘画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固定的中国传统语汇是怎样像筛子一样只允许已有图式的那些特征进入画面。艺术家会被可能用他的惯用手法去描绘的那些母题所吸引。他审视风景时,那些能够成功地跟他业已掌握的图式相匹配的景象跃然而出,成为注意的中心。风格和手段一样,也创造了一种心理定向,使得艺术家在四周的景色中寻找一些他能够描绘的方面。”以这里的论述来看中国山水画论中的“丘壑”,还是颇为客观的。由此可见,“胸中丘壑”的养成,就一定是向前人学习的结果。清代画家唐岱也明确指出:“俟皴染纯熟,心手相应,则摹仿旧画,多临多记,古人丘壑,融会胸中,自得六法三品之妙。落笔腕下眼底,一片空明,山高水长,气韵生动矣。”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翚主张:“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都是认为,丘壑是传承前代画家的山水图式。仅有前人留下来的“丘壑”,就能画出佳品杰作了吗?当然不是。胸中丘壑是画家的审美预期,是通过它来把握当前山水物象的尺度;真正要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杰作,必然是画家面对当下的山水物象,以自己的独特感兴契合之,这样,也使“丘壑”焕发出新的生机。亦如董其昌所说的“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化为师。”(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以造化为师”,即是以活泼的当下自然为师。在唐代大画家张璪的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心源”就包括了艺术图式的传承习得,而师造化,就是在当下的自然物象中产生感兴。宋代画论家董逌评画,特重“天机”,也即当下的审美感兴。如评燕肃的《写蜀图》说:“然平生不妄落笔,登临探索,遇物兴怀,胸中磊落,自成丘壑。至于意好已传,然后发之。”“想其解衣磅礴,心游神放,群山万水,冷然有感而应者。”这种因面对当下的山水物象而生成的意象之美,是与所学前人的“丘壑”相融会的。如果只是临仿前人,而无自己的当下审美感兴,则只是泥古的套路,而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绘画创作。清代画家盛大士便说:“画中丘壑位置,俱要从肺腑中自然流出,则笔墨间自有神味也。若从应酬起见,终日搦管,但求蹊径而不参以心思,不过是土木形骸耳。”这种以当下的自然物象为契机而形成的自己的“丘壑”,是对前人图式的矫正。这也就应了贡布里希所说的“我们的图式与矫正和先制作后匹配的公式”。
投射不仅关乎到艺术创作,也关乎到艺术欣赏。而成熟的艺术家在创作时,已将这种审美预期作为自己的创作策略了。贡布里希认为,“辨认物像全都离不开投射与视觉预期”,“这种投射需要一个‘屏幕’,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跟我们的预期相抵触的空白区域。这个道理就说明为什么创造运动感和由之而来的生命感的效果,求之于有力的寥寥几笔,比求之于精雕细刻要远为容易。”文学艺术创作中的“计虚当实”“计白当黑”等观念,都需要审美投射的帮助。刘勰在谈到文学创作中面对自然物色时要“析辞尚简”:“皎日彗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论诗画时则说:“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且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墨气四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等等,在诗学中不一而足。中国画讲求笔墨简省,是要在简中获得更多的意蕴和审美享受。这就尤为需要鉴画者的投射加配合。文人画尤其重“简”,但简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要以笔墨之简淡来蕴含更多的意趣。宋人葛守昌认为:“大抵形似少精,则失之整齐;笔墨太简,则失之阔略。精而造疏,简则意足,惟得于笔墨之外者知之。”“简”的是笔墨不是意涵,如果笔墨过于简省,也易于失之“阔略”,只有“简而意足”,才是理想之境。清代画家王昱指出:“写意画落笔须简净,布局布景,务须笔有尽而意无穷。”何以能够做到笔简而意丰?是要靠鉴赏者的审美投射作用的。投射对于鉴赏者而言,所发挥的作用如贡布里希所说的:“观看者必须在没有任何结构辅助的情况下调动他对于可见世界的记忆,并且把它投射到面前的画布上由点点划划构成的镶嵌图案之中。因此,制导投射的原则正是在此发挥到极致。不妨说,物像并没有在画布上留下稳固的锚地,只是在我们心中‘唤起’(conjured up)而已。观看者心甘情愿地对艺术家的暗示(suggestion)作出反应,因为他欣赏眼前出现的这种变形转化。正是在这种乐趣中,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期中,逐渐地、几乎无人注意地出现了艺术的一个新功能。艺术家越来越给观看者‘更多的事情做’,把他拉入创作这个魔法圈子,使他得以体验曾是艺术家特权的‘制作’活动的几分激动。”观赏者之所以能够参与到艺术创作中来,是因其以投射作为反应艺术家暗示的功能。这就从心理学的意义上阐发了作为鉴赏者的审美活动的奥秘。
三
本文所关心的则是,审美投射和审美移情是否都关涉到知觉?如果是,知觉在投射与移情中的功能是一样的吗?笔者以为,移情与投射都离不开知觉的作用,但知觉在移情和投射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
在审美移情的过程中,主体对于外在物象的情感移入或感入,是以对于物象的知觉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以知觉作为“助推器”的。里普斯在谈到移情作用时以道芮式石柱作为典型的例子。道芮式石柱本是一个无生命的建筑物,而在面对它的主体的感知中,它却体现出“耸立上腾”的力量。里普斯这样分析:“这种情况发生并不经过任何反思。正如我们并非先看到石柱而后按照机械的方式去解释它,那第二种方式的解释,即‘人格化’的解释,亦即按照我们自己的动作来测度客观事件的方式,也并非跟着机械的解释之后才来的。石柱的存在本身,就我所知觉到的来说,像是直接的,就在我知觉到它那一顷刻中,它已显得是由机械的原因决定的,而这些机械的原因又显得是直接从和人的动作的类比来体会的。在我的眼前,石柱仿佛自己在凝成整体和耸立上腾,就像我自己在镇定自持和昂然挺立,或是抗拒自己身体重量压力而继续维持这种镇定挺立时所做的一样。我简直无法对石柱起知觉,除非这种活动像是存在于所知觉的对象里。”里普斯通过这里所做的详细分析,呈现给我们移情作用的基本情形。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移情与知觉的关系是里普斯加以说明了的。知觉是移情的前提条件。所谓“机械的解释”,其实是动力性的介入。朱光潜先生的译注颇为值得注意:“里普斯在本书中所用的‘机械的’一词都应理解为‘动力的’。‘机械的解释’即把石柱的形象看成仿佛是有生命的,能进行各种活动的。虽叫做‘解释’,其实是在无意中进行的。机械的(动力的)解释和下文所说的‘人格化的解释’,是相辅相成的。”知觉本身就是活动着的,是充满张力的。著名心理学美学家阿恩海姆就曾指出:“一旦我们考察了人们在理解表现时所做的是什么时,那么,显而易见,他们使用的机制是知觉而不是某种别的神秘认知能力。这一点,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这不是可以用某种标准加以衡量的形状、大小、色彩或音乐的静力学方面的知觉,而是由同一刺激所传递的直接张力的知觉。”知觉本身就带着一种动能,带着张力,而非静止的。里普斯又讲:“我感到这种情感,是当我观看这个对象,也就是对它注意得很清楚而把它一眼摄进知觉里的时候。但是在审美的观照里,只有审美对象(例如艺术作品)的感性形状才是被注意到的。只有这感性形状才是审美欣赏的‘对象’(客体);只有它才和我‘对立’,显得是和我自己不同的一种东西,对这种东西,我以及我的愉快的情感发生了某种‘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我才感到欣喜或愉快,总之,才在欣赏。”进入了主体的知觉,移情的过程才得以发生。然而,知觉并非移情本身,而是引发移情的前奏,是移情发生的契机。英国美学家李斯托威尔在谈“移情”时说:“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审美观照,其基本的特点是一种自发的外射作用。那就是说,它不仅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把真正的心灵的感情投射到我们的眼睛所感知到的人物和事物中去。一句话,它不是‘Einnempfindung’(感受),而是‘Einfuhlung’(移情)。外射的动作是紧接着知觉而来的,并且把我们的人格融合到对象中去,因此,它不可能被说成是一种联想或回忆。在这种情形下,光线和颜色,看起来不是欢乐的,就是悲哀的。当移情作用完成时,我们自己的人格就与对象完全融合一致了。”李斯托威尔的论述,是符合移情理论内涵的,移情是跟随知觉后面的。
投射更离不开知觉,因为投射的内容就是图式,而图式本身就是一种知觉的样式,或许也可以认为,图式是一种审美知觉的存在形式。图式不可能缺少结构的要素,没有结构也就谈不到图式。布列逊对此有过较为深入的探讨,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有关图式的重要问题:我们是否想过,图式作为一种客观结构,就像介于视网膜和画笔之间的一块模板,这么说的话,它是用画家的手和肌肉独特地操作一种接受程式的装置呢,抑或是一种类似格式塔的精神结构,使艺术家的形相的知觉呈现出显著的历史化的局部形式?换种方式说:图式是一种限于在画家手部惯常的肌肉训练中存在的手工的实体呢,抑或是一种隐身于画家意识领域之内的精神的实体?”布列逊的问题提得颇中肯綮,其实,具体到画家所接受的图式层面,就是包含了这两种实体,或者可以认为是这两种实体的重合叠加。布列逊也主张“具有手工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双重性质:图式的一部分为格式塔形态,用一定的方法过滤掉感官刺激的内容,排除掉一部分,突出另一部分,从而在画家的知觉意识里构成一个清晰图像。”相对来说,笔者则是更为倾向于画家在当下的审美感兴中所生成的新的图式。五代画家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的“六要”,其三是思,其四是景,二者连通,乃成佳制。所谓“思”,“思者,删拨大要,凝想形物”,所谓“景”,“景者,制度时因,搜妙创真。”可以将其理解为当下之景与胸中丘壑的融合。当下的知觉,应该是画家创作的着眼点。
再有一个问题是,移情和投射与抽象是什么关系?这涉及到审美投射的性质与功能。移情作用是以感性的因素作为主导,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费肖尔还是里普斯,都有清晰的认识。里普斯的相关看法已如上述,而费肖尔也将移情中的主客体关系,置于感性的轨道之上。费肖尔指出:“所以这里就要单纯从现象的概念推论出主观环节一同被提出的必然性。在现象概念中,主体已经一同包括在内了,某种事物是对主体出现的。同一感性的东西,在对象中,它便作为纯粹形象起作用,在广泛世界中到处都是;而在主体中,则作为器官,作为感性,通过这种器官,那个在主体以外存在的感性的东西便成了主体的对象。”投射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投射的内容是图式,图式是与抽象难以撇清关系的。尽管贡布里希指出“图式并不是一种抽象(abstractlion)的产物”,但笔者要指出的则是,这里所说的“抽象”是概念性的抽象,而非审美性的抽象。阿恩海姆认为:“一切知觉都是象征性的。严格地说,人们从不与独一无二的个别性打交道,他们是依照所传达出来的普遍性质和作为某种存在的特定事物或人打交道。这种人类把握经验的基本方式与另一种能力互补,即以替代物来取代现实情况并把握它的能力。”阿恩海姆所说的知觉,其实是可以用来理解图式的,这里已经包含了“共相”。笔者曾对审美抽象作过专门的论述,并就审美抽象作过这样的概括性阐述:“审美抽象指审美主体在对审美客体进行直觉观照时所作的从个案形象到普遍价值的概括与提升。审美抽象与逻辑抽象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它们都是从具体事物上升到普遍的意义,但逻辑思维的抽象是以语言概念为工具,通过舍弃对象的偶然的、感性的、枝节的因素,以概念的形式抽出对象主要的、必然的、一般的属性和关系;审美抽象则通过知觉的途径,以感性直观的方式使对象中的普遍意义呈现出来,在艺术创作领域中表现为符号的形式。”笔者认为,审美抽象是在艺术领域中的普遍存在,它的操作过程是以知觉尤其是视知觉为中介的。审美抽象不是以牺牲作品的生动与细节作为代价,恰恰是以其整体性与生动性突显了对象的本质特征。阿恩海姆举中国画家谢赫的“绘画六法”为例,说明审美抽象的这种特征,他说:“我们只需注意到公元500年左右南朝谢赫提出的关于中国绘画‘六法’中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气韵生动’,即生命之气回荡于其中。通过这种可以由笔触中察觉得到的性质,上天的呼吸赋予自然中一切事物以生命,并一直支持着运动和变化的永恒进程,……如果艺术作品包含‘气’于其中,它必然反映出一种精神的活力,这种活力正是生命的本质之所在。”阿恩海姆更为明确地揭示了抽象在艺术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抽象是将一切可见形象感知、确定和发现为具有一般性和象征意义时所使用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或许我可以将康德的论断作另一种表述:视觉没有抽象是盲目的;抽象没有视觉是空洞的。”笔者认为,阿恩海姆对艺术中抽象所作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颇能说明艺术创作揭示生活本质的审美之途的。投射的艺术图式,究其实质,是包含着审美抽象的内在方式的。从艺术的角度讲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深入到创作心理层面,图式的投射与矫正,其实是艺术传统的内在线索。这样看来,投射与移情的同与异,就是不可不辨的。
注释:
①④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597、604页。
②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7页。
③ [德]费肖尔:《批评论丛》第五卷,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601页。
⑤⑥⑦ [德]里普斯:《移情作用:内摹仿和器官感觉》,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8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3、52、52页。
⑧ [德]里普斯:《再论移情作用》,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8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年版,第55页。
⑩ 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