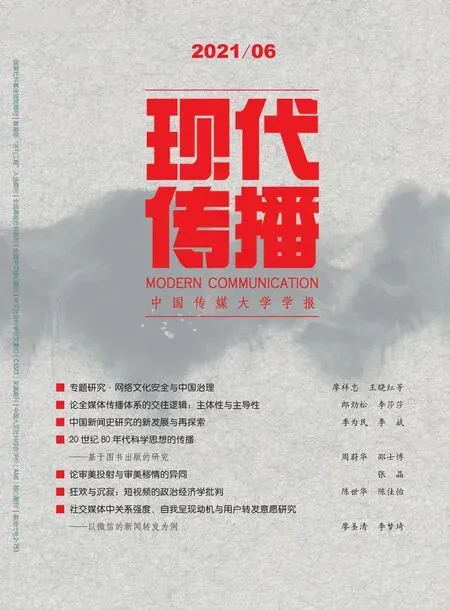论共情传播
2021-12-01赵建国
■ 赵建国
共情传播研究在最近几年刚刚起步,而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成功实践又推进了这个研究。但在为数不算少的有关文章中,多数停留于直接搬用共情的心理学概念,来阐释抗击新冠疫情和其他社会活动的传播问题。只有吴飞的《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①一篇文章是较全面的基础理论研究,这也是发表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国最早研究共情传播的论文之一。遗憾的是,这篇论文依然在心理学框架下阐释共情,只是在为共情传播提供“理论基础”,并没有给出共情传播的有效概念。从该篇论文的三个关键词“理性”“共情”“人类命运共同体”便可看出端倪。这篇文章涉及共情传播的内容是第三个小标题“通过沟通提升共情力”,在这个小标题下的三个次级小标题是:“爱”是共情的基础;沟通能够促进共情;共情因对象、因情境而变。倒是另外两篇并非专门研究共情传播基础理论的论文:刘海明、宋婷的《共情传播的量度: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共振与纠偏》②和李玲的《民族互嵌与共情传播——一个文化社会心理学的视角》③,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这两篇文章的有关见解我们将要在本文中引述。由于这两篇论文都不是专门探讨共情传播基础理论的,我们不能要求其提供更多的关于共情传播的基础理论。
鉴于以上所述,在共情传播研究正在起步的时候,有必要筑牢其基础理论,为其发展拓宽道路。抗击新冠疫情等重大社会实践也呼唤共情传播基础理论及时跟进。
一、共情和共情传播的概念
(一)共情
共情(empathy,也有人译作“移情”)作为心理学术语,通常解释为“个体基于对另一个人情绪状态或状况的理解所做出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等同或类似于他人正在体验的感受或可能体验的感受”(Damon,Lerner,& Eisenberg,2006)。有人更简洁地把共情概括为体验别人内心世界的能力。这里所说的共情,其含义与中国成语“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将心比心”等比较接近。
与上述解释基本一致,中国有心理学者说,“共情指的是个体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共享并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的倾向。”④另有一些中国的心理学者力求把共情阐释得更全面:个体面对(或想象)一个或多个个体的情绪情景时,首先产生与他人情绪情感的共享,而后在认知到自我与他人有区别的前提下,对其总体状况进行认知评估,从而产生的一种伴有相应行为(外显或内隐行为)的情绪情感反应,且主体将这种情绪情感和行为指向客体的心理过程。⑤
从上述介绍中可以看出,情绪分享或共享处于共情的核心地位,共情的基础是个体与他人之间的情绪共享。还可以看出,共情主要是个体间的情绪情感分享或共享。在此意义上,多数心理学研究者赋予共情积极的、正面的意义。
有必要指出,共情的定义一直有争议,还处于不断探索中。比如,“目前在心理学领域中大部分研究者都将同情包含在了共情之中,特指他人定向的共情。”“我们查阅了相关文献,发现共情和同情在许多研究中其实一直处于混用的状态。”“甚至直接把共情和同情当作一个概念。”“同情由于在词源和翻译上在一段时间内和共情存在一致,从而也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之后的研究者。”⑥共情有时候包含同情的成分,但如果把共情等同于同情那就大大限制了共情的内涵和意义。特别是在共情传播研究中,如果把共情等同于同情那就把共情传播限制在极小的圈子里了。
(二)共情与传播的内在联系
在人际沟通或互动过程中对他人的知觉和理解形成共情,而且共情主要是个体间的情绪、情感分享或共享,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共情与传播有着天然的、内在的联系。共情传播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内在联系的理论揭示,更是对共情传播社会实践的理论呼应。
共情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交流、沟通、传播过程,离开了交流、沟通、传播就难以形成共情,而共情的表达更是一种传播过程。研究探讨共情,实际上也是在研究探讨情感、情绪的交流传播。其实,心理学对共情的研究也在为共情传播研究开辟道路,更显在为心理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开拓新的疆域;反之亦然。
(三)共情传播
现有的共情传播概念是在共情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共情这个概念主要是在心理学领域里使用。把它直接移植到传播学和新闻学中,可能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要实现共情概念传播化,有必要改造现有的共情传播概念。传播学对共情概念扩展应该有自己的贡献。在这方面,研究者刘海明、宋婷等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将共情传播界定为“个体在面对群体的情绪情景时参与信息接收、感染和表达以及传递分享的过程。”两位研究者还指出,公众在“新冠”疫情构建出的各类情绪场景中积极地参与共情传播。⑦在这个界定中,至少有两点重要拓展值得注意。一是共情和共情传播不再局限于个体与个体之间,而是“个体在面对群体的情绪情景时”产生的情感反应。二是这种情绪情景不再是单一的,比如痛苦、受难,而是“各类情绪场景”。
在上述刘海明、宋婷等对共情传播的界定基础上,本文将共情传播进一步界定为:共情传播就是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这个界定没有提“群体的情绪”,但“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与“群体的情绪”是相呼应的。而“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则与“接收、感染和表达以及传递分享的过程”更是基本一致的。这个界定没有提“个体在面对群体的情绪情景时”,是想为共情传播留下更大的空间,它既可以包括个体对群体,也可以包括个体对个体,还可以包括群体对群体等。正如研究者李玲所说:
如果说心理学上的共情仍然是在描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传播学上所要说的“共情传播”,则是要在此基础上,说明在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新关系模式。⑧
包括了个体对个体,就接纳了心理学对共情通常意义上的阐释,即共情是“个体基于对另一个人情绪状态或状况的理解所做出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等同或类似于他人正在体验的感受或可能体验的感受”。
有必要指出,上述界定并没有脱离心理学意义和传统意义上对共情的阐释。Empathy源自1873年德国哲学家Robert Vischer在其著作《Uber das optische Formgefuhl:Ein Beitrag zu Aesthetik》中所提到的“Einfuhling”一词,这是对希腊语“empatheia”的音译,最初被用于描述个体对艺术作品的共鸣(见 Gladstein,1984)。另外一些心理学研究者也指出:理论心理学家一般认为Titchener是在1909年的“关于思维过程的实验心理学的讲稿”中首次提到英文“empathy”,后来,不同研究者曾用同感、共感、共鸣、替代内省、社会敏锐性等概念来概括这种心理现象。⑨
我们正是继承了这些学者所赋予共情的“同感”“共感”“共鸣”等内涵,来界定共情传播的。我们所说的“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正是以“同感”“共感”“共鸣”为依据的,同时“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也可以包容心理学者对共情界定中的“情绪情感的共享”。
本文所说的共情传播中的共情,更接近于情感共振、情感共鸣,即是产生了相同或相似的情感、情绪。我们中国人日常的惯用语或成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戮力同心”“群情激奋”“引起公愤”“天人共怒”“天怒人怨”“人神共愤”“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等,与我们所说的共情相通或相近。相同或相似的情感、情绪也更接近于共情的字面意义,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更有普适性。当然,这里所说的共情包含心理学所说的移情,包含对他人情绪状态或状况的理解所做出的情感反应,也包含与他人正在体验的感受或可能体验的感受相同或近似的情感反应。无疑,我们把共情传播界定为“共同、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也是呼应了社会传播实践的需要和传播学发展的需要。
共情传播有两种情形。通过信息的传递、扩散和共享,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情感共鸣、共振,产生了相同或相近的情感或情绪,这就是共情传播。当然,相同或相近的情感或情绪的传递和扩散,或者说群体情感或群体情绪的传递和扩散也属于共情传播。应当指出,这两种情形不可能截然分开。共情传播的结果是形成情感共同体,也就是形成一种群体情感或群体情绪。
经过比较发现,传播学研究者在使用共情传播时,共情并不是总在积极的、正面的意义上使用,也包括消极的、负面的意义,这一点与心理学界的情况有所不同。比如刘海明、宋婷的论文题目《共情传播的量度: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共振与纠偏》,所谓“纠偏”正是针对共情的消极、负面意义而言的。
(四)共情与传播效果的三个层面
传播追求的是传播效果。传播效果通常分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上的效果,情感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行动层面上的效果。
共情表现为共同或相近的情绪或情感,这与传播效果的情感和态度层面是吻合的。交流和传播所追求的效果,相当程度上就是使情绪或情感接近或趋同,使态度接近或基本一致。传播所达到的情感和态度趋同效果,与我们所说的共情大致是一回事。共情传播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人的情感、态度层面的趋同或相近。
传播活动能够强化或改变人们对社会问题、政治观念的看法和态度,能够引起多数受众在情感上向相同或相近的方向上起伏变化,也能够强化人们相似的动机,坚定人们的共同意志。这些都属于传播的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
传播效果虽然分为三个层面,但这三个层面不可能截然分开。如果认知层面发生了变化,情感、态度层面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同样,如果情感和态度有了新的认同,认知的认同度也会更高。如果传播活动使人在认知层面上接近或一致,并且实现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认同,那么或迟或早会采取一致行动。相比较而言,传播在情感、态度层面引起的认同,比认知层面引起的认同更容易引起一致的行动,而且力度更大。
二、共情传播与共识传播比较分析
传播活动所承载的内容可以分为认知信息和情感信息两大类;认知信息与共识传播对接,情感信息与共情传播对接。共识传播依赖于认知信息,共情传播依赖于情感信息。因此,共情传播与共识传播是传播活动的双翼。同时,从传播效果角度看,共情与共识都是传播活动所追求的理想效果。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可以看作拙作《论共识传播》⑩的姊妹篇。
(一)共情传播与共识传播的内在关联
众多心理学研究者已经指出,共情是自下而上的情绪分享过程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互相作用的结果。如Davis通过因素分析指出共情有四种基本成分: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个人悲伤(personal distress)、共情想象(empathic fantacy)和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前三个是共情的情绪成分,而观点采择是共情的认知成分。“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不是静态和孤立的,二者彼此独立但互相补充。”也就是说,共情中包含着相关的共识成分。正因为如此,有心理学者将共情划分为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情绪共情(affective empathy)和行为共情(behavioural empathy)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把共情传播与共识传播作为一对概念分别来考察。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共识传播不可能完全没有相应的共情因素(也许自然科学共识传播是个例外),共情传播一般也以特定的共识为基础。我们只是把以形成共识为主要目标的传播活动称之为共识传播,而把共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沟通交流活动叫做共情传播。共情侧重情绪、情感,共识侧重理性、理智。以情感人更有激发力,但不易控制。以理服人更持久,较易控制。传播学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以情感人往往比以理服人更有效果。
共情是一个包含认知、情绪情感和行为的多重心理活动过程。一个完整的共情过程包含知、情、行。认知—情感—行动,构成一个共情过程的完整链条。读过《论共识传播》的读者一定还会有印象,真正的共识一定包含有共识所导致的相应行动。由此看来,共情与共识都包含行动,都指向社会效果。
(二)共情传播的优势和特征
与共识传播相比,共情传播的优势在于:一是共情一旦形成,多数情况下其动能要比共识大且强烈;二是共情传播的门槛要比共识传播低。共识的形成需要讲道理,有些道理没有一定的社会经历和理论基础就弄不懂。而本能性情绪则特别容易相互感染,共情只需要一个事件、一个案例甚至一段视频或一句口号就能被唤起。理智的、冷静的情感、意识在群体中起作用的难度极大,多数人往往沉溺于“集体情感”的旋涡之中。
共情传播凝聚力大、合力大。大规模、强烈的共情一旦形成,其建设力和破坏力一样强大,相互感染的群体情绪,决定群体行为的选择,不少情形下即使是共情传播的发起者、组织者也难于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共情效应会使公众心理失衡和心态偏激,表现出非理性的情绪发泄。对于共情传播的这一特征,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还有一点同样需要充分关注。由于社会状况复杂,可能会有不同性质的共情在传播,其结果是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情群体,也就是形成不同的情感共同体或若干类庞大的情感共同体。尤其是如果出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对抗的情感共同体,那么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会非常棘手和危险。美国总统大选中形成的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阵营和以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阵营,就是两个对立、对抗的情感共同体。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压颈致死,引发全美范围内示威抗议,“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多次抗争也是对抗性的情感共同体。战场上作战双方则是极端的、你死我活的共情对抗。
(三)共情与共识有机结合
如果从传播效果方面考察,共情与共识有机结合并达到足够力度和规模时,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能量——无论这是一种正能量还是负能量,都能更有效地推进社会变革或变化。共情与共识若能够有机结合在一起,往往会实现令人满意的传播效果。
我们经常谈论的社会舆论,表面看是多数人相近或一致看法的公开表达,与社会共识很接近。但仔细考察,社会舆论也蕴含着相同或相近的情感和情绪,多数情形下社会舆论其实是共识与共情的复合体。比如,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腐败问题社会舆论反映强烈,但谁能说在这种社会舆论中没有强烈的不满、愤怒情绪呢?因此,仅从思想、意见、看法角度认识和理解社会舆论还不够全面。从共识与共情复合体角度理解和把握社会舆论,就会使我们对社会舆论的重要性有进一步认识。
三、共情传播的条件和途径
许许多多的不同个体怎样才能够产生相同或相近的情感、情绪?这是共情传播更关注的一个问题。
众多个体共情的形成需要一个大的环境条件。心理学界把这个大的环境条件概括为情境。情境就是在一个给定的时空场域中所展现出来的整体境况和环境条件,包括所有事物或信息,它能够影响或决定个体的情感、情绪及认识、判断。“情境理解系统是一个领域普遍性的评价系统,提供了一个基础,用来估计他人的情绪状态是处于怎样的具体情境中。……这一系统可以直接影响到共情者自身的情绪状态,使之向共情的方向靠近。”在1931年“9·18事变”、1932年“1·28事变”和1937年“7·7事变”后民族危亡的大环境中,所有具有民族感情的中国人都会生发抗日救亡的共同情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表达的正是这种共情。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爱国主义是一种共同的感情,是中华民族的共情。
从传播内容考察,情感要靠情感来催生。文学艺术作品包含情感,可以催生和传播共情,但学术理论文章很难催生共情。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与《松花江上》等作品在抗日战争时期唤起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共情,多少战士正是在《义勇军进行曲》等感召下奔赴抗日战场,冲向日军阵地。
新闻报道真人真事,报道真实事件也可以催生共情。人物的悲欢离合、事件的跌宕起伏都会引起人们的同情或共鸣。比如,通过“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群体的公共卫生意识被唤醒,在网络舆论场形成的共情呈现出易感染性、对象集中性和评估复杂性以及共情表达强烈性等特点。
从传播方式来考察,演讲、集会等身体共在的情况下更容易激发共情。演讲、游行、集会本身就是一种共情传播,通常,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往往都伴随着强烈的共情传播。群体性事件必定伴随着对立性共情传播。扩而言之,若想尽快有效地实现共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通常是最佳选择。因为它往往具备产生强烈群发共情的两个必备条件:第一,能够激起群体共情的情境;第二,大规模的身体共在。身体共在会使情感、情绪急速互相传染。若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并且多数个体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情感、情绪基础,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会产生一呼百应的共情效果。战前动员的最佳效果就是使全体战士产生拼死必胜的激越共情。1941年,在德国军队随时可能攻入苏联首都莫斯科的危急关头,莫斯科红场大阅兵之后受阅部队直接奔赴战场,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军队和人民抵抗德军入侵的士气并激发了同仇敌忾的共情。这是一个共情传播成功的典型案例。
散在的相同或近似的情感和情绪,需要一种情境或场合以便使这种情感和情绪聚合、展现甚至爆发。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播可以为形成共情传播打下基础,但还与共情传播有一步之遥,它需要一个身体共在的场合,至少需要一个虚拟的身体共在情境,如互联网的跟帖、微信群等。比如,10天建成1000张床位的负气压传染病医院——武汉火神山医院是吸引全球受众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央视频”客户端以5G+光纤双千兆网络技术进行全程慢直播,同时提供评论专区,为网民讨论交流提供云平台,通过连续600小时超长直播的方式,让受众体验身临其境的沉浸感,全程见证、参与医院建设,相关报道累计在线观看的国内外受众达到1.7亿人次,点赞数超221万人次,创造了5700万人同时在线观看的纪录。为网民讨论交流提供云平台营造了一个虚拟的身体共在情境氛围,对于聚拢人气共情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共情传播在国内外重大事务中的实践
共情传播在日常生活和重大事务中都有广泛应用,研究共情传播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下面分别以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和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为例进行探讨。
(一)共情传播在中国抗击新冠疫情中的成功实践
这次以武汉为主战场的中国抗击新冠疫情攻坚战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新闻传播和舆论氛围营造角度看,共情传播的成功实践是重要经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记者唐颖总结说:共情传播,是武汉前方报道组抗“疫”报道电视新闻语境的重要实践和创新。
其实,不光是电视新闻,其他各种媒体及其报道都在共情传播方面做出了贡献。正因为如此,抗击新冠疫情以来,出现了多篇探讨与疫情相关的共情传播的文章。抗击新冠疫情的实践推动了共情传播的研究,也拓展了心理学的共情概念。
疫情骤起后,“武汉加油”“中国加油”“隔离但不隔绝爱”等口号响彻中华大地,调动和凝聚起万众团结一心、共同抗疫的决心和情绪。
疫情期间,一线的白衣天使夜以继日、连续奋战,解放军官兵、公安干警时刻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社区工作者、基层干部、志愿者们不辞辛劳、尽心竭力。这些平凡英雄的事迹通过各种媒体广泛传播,一股无坚不摧、全民抗疫、武汉必胜的中国抗疫精神回荡在大江南北、充盈在长城内外!
时隔一年,中国抗疫故事再次在石家庄上演。2021年1月6日是支援石家庄的护士张丽芳人生中最纠结、最难熬的一天。当她与河北省辛集市中医院的10多名同事冒着零下17摄氏度的严寒,在全国唯一高风险地区石家庄市藁城区防疫一线连续作战,完成该区廉州镇五里庄村3317名群众的核酸检测样本采集工作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时,接到了母亲突发疾病去世的消息。当晚,她穿着工作服缓缓走到院里,向着家的方向鞠躬遥祭、泪别娘亲。这段视频传到网上感动了无数人,白衣天使的家国情怀和各行各业无数无私奉献的事迹,再次激发和凝聚起众志成城的抗疫共情。很快,石家庄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行!
(二)中国抗疫精神中的共情和共识
在这次抗击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二十字抗疫精神凝聚了中国政府和全国同胞的共识和共情。“生命至上”“尊重科学”“命运与共”更多体现了抗疫共识的核心思想,“举国同心”“舍生忘死”更多体现了抗疫共情的核心情感和意志。二十字抗疫精神是中国人民共识和共情的有机凝聚,是科学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有机融汇,这种共识和共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中国人民取得抗击新冠疫情的伟大胜利,共识和共情缺一不可。
(三)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对抗性共情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过程一直伴随着对立共情传播,而对选举结果的最终确认,使原本严重对立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对抗性共情激化。
11月7日大选之后,特朗普及其团队发起了50多起质疑和否定大选结果的司法诉讼,制造了上百个民主党“偷走”大选结果的阴谋论,并号召支持者上街抗议。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甚至这样不断煽动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你们愿意为实现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而去死吗?特朗普向他的支持者承诺,周三(1月6日)将是“疯狂的一天”。就在1月6日中午,特朗普专门向会集到华盛顿的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发表煽动性演讲,再次宣称民主党“偷走了”原本属于他的大选胜利,坚决不接受选举结果,不会让步,煽动支持者“挺身而出维护美国的公正”。敦促支持者“拼命战斗”,前往国会大厦游行,并称“一会儿我会跟你们一起去国会山”。结果,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冲击国会山流血事件。前总统奥巴马指出这“是一位对合法选举结果毫无根据撒谎的在任总统煽动的。”
暴力冲击国会山事件之所以发生,有两个关键环节需要注意。一是特朗普利用社交媒体推特等平台将支持者散在的对立、对抗情绪汇聚起来,形成激烈的共情,他的推特“粉丝”高达8800多万。正因为如此,推特公司8日宣布,“永久封禁”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个人账户,理由是“存在进一步煽动暴力行为的风险”。推特公司在一篇博客帖文中详细解释“销号”理由,认为在国会大厦骚乱以及网络上流传一些针对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就职的武装抗议计划背景下,特朗普8日所发两条推文构成“美化暴力”。与此同时,其他媒体也有类似跟进封禁。二是特朗普鼓动支持者汇聚华盛顿,尤其是1月6日中午特朗普向集会抗议的人群发表演讲,点燃了冲击国会山的导火索。事实上,特朗普的演讲还未结束,有人就迫不及待向国会山进发了。以上两个要素满足了激烈共情形成和爆发的条件。
(四)“后真相”现象助推对抗性共情
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和过于无视真相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后真相”时代到来的两大标志性事件。所谓“后真相”(post-truth)是指“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对于许多特朗普支持者来说,特朗普当年当选是客观事实,如今的败选就不是客观事实,因为对于特朗普败选他们在情感和信念上无法接受,只有他们自我认定和接受的事实才是唯一的“真相”。正如《环球时报》社评所说:“特朗普在败选之后一直拒绝认输,在他的大量支持者中引起共鸣”,难以化解。“这次大选留给失败一方和支持者巨大情绪的力量”,“只要涉及政治,美国政坛乃至舆论场上近乎只剩下立场,不再有是非。”即使国会确认特朗普败选后,一份报告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相信选举结果。据《迈阿密先驱报》16日报道,当天迈阿密市中心数十名特朗普的粉丝举行和平集会。他们挥舞着旗帜,高喊“选举欺诈”。80岁的罗克说:“我爱我的总统。这次选举完全是一场骗局。”另一名支持者佩雷斯则表示,他还不准备承认特朗普总统任期将于1月20日结束:“那是你的看法。毫无疑问,特朗普赢得了第二任期。”《南佛罗里达太阳哨兵报》16日称,悲伤,愤怒,厌恶——特朗普的南佛罗里达支持者表示,面对特朗普任期结束、拜登即将就职,他们有这样的感受。一些人在哀悼,表达了绝望的情绪,甚至不愿在电视上观看新总统的就职典礼——“我绝不会看,他不是我的总统。”支持者计划在特朗普抵达棕榈滩时到机场迎接他,表示声援。
当对立双方的情感、信念、立场无视或藐视事实时,这种对立或对抗性共情就很难化解,给双方共处的社会带来巨大的隐患和难题。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势均力敌的分化阵营相互角力,使美国社会深层撕裂,有人称之为“愤怒政治”。这就是新任总统拜登面对的困境。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难题:当民主遭遇势均力敌的对立双方时该怎么办?
(五)“后真相”和对抗性共情留给我们的思考
美国等国出现的“后真相”现象和对抗性共情,留给世界诸多镜鉴和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也不能置身其外,我们必须正视和重视,并对其深入研究。有中国学者已经指出:当下中国的网络舆论场体现出“后真相”的特征: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于是,公共事件每每成为群体、派系对立的话语载体,“话语政治”不断撕裂着社会。
与上述现象相伴,对抗性共情也不能说与中国社会完全绝缘。由于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利益分化、贫富悬殊、腐败多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社会怨恨情绪不断积累等诸多挑战,导致负面情绪产生,并沉淀为负面集体记忆,当这种情感记忆被一个“突发事件所唤起时,藉着信息的快速传播,大规模的群体性不满和怨恨性情感就会在一定地域甚至是跨地区内迅速蔓延,形成对事件的怨恨式解释,由此可能导致群体性情感宣泄的极端后果,即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对于“后真相”和对抗性共情,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引导人们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力避“后真相”心态,解决社会矛盾,化解对抗性情绪,聚拢和形成最大程度的积极性社会共识和共情,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任重道远,不可懈怠。
注释:
① 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5期,第59-76页。
③⑧ 李玲:《民族互嵌与共情传播——一个文化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文化与传播》,2019年第3期,第31页。
④ 陈武英、刘连启:《情境对共情的影响》,《心理科学进展》,2016年第1期,第91、95页。
⑤ 刘聪慧、王永梅、俞国良等:《共情的相关理论评述及动态模型探新》,《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5期,第965页。
⑥ 颜志强、苏金龙、苏彦捷:《共情与同情:词源、概念和测量》,《心理与行为研究》,2018年第4期,第436页。
⑨ 陈晶、史占彪、张建新:《共情概念的演变》,《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年第6期,第664-666页。
⑩ 赵建国:《论共识传播》,《现代传播》,2019年第5期,第36-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