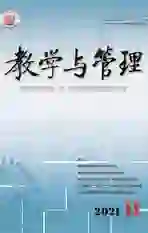解释学观照下教师教学评价素养实践的表征与机理
2021-11-30张瑞覃千钟
张瑞 覃千钟
摘 要
在解释学语境下,教师教学评价素养实践表征于“理解”规定着评价意识存在,“文本”是评价知能实践的载体,“对话”作为评价行为表现机制,“意义”是情境适应性评价的产物;教师教学评价素养实践的机理内在于评价意识强化是一种“循环”进程,“先见”是评价知能转化的实践基础,“预期”驱动评价行为的反思和改进,“时间间距”是深化评价意义的媒介,教学评价素养实践的实质是“视域融合”。
关键词 教学评价素养 解释学表征 实践表征 视域融合
“评价素养”是针对教师群体的一种专业性素养,在我国是作为西方学术概念的舶来品,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评估专家斯蒂金斯提出[1]。教师之于评价素养的实践范畴通常是在课堂教学领域当中,因此教师的评价素养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教学评价的素养。根据相关学者定义,教师的教学评价素养一般包含评价知识、评价能力和评价态度等要素。但从“素养”本身来说,素养遵循实践逻辑,是知识能力、思想意识、行为气质的综合反映,涉及人的内在心理、动机,包含人的情感,产生于一定的文化组织、社会机制环境中,并且教学评价本身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活动,这意味着教师教学评价素养在实践层面有着更宽泛的内涵和外延[2]。
一、教学评价的“解释学”蕴涵
解释学是一项专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说。本文所指的解释学是由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在继承和批判传统解释学观点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新解释学,它和传统解释学一样认为“文本”是作为解释和揭示的工具和载体,但并非要对事物进行科学的说明和确证。解释学以研究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为主要目标,以问答对话为理解的媒介,证实理解是存在的基本特性,而不是发展某种技艺或提供方法论基础。因此,在哲学解释学的要素框架中,对教学评价的解释要以“理解”为基点、“对话”为媒介、“文本”为工具,将教学评价还原为一种教育价值判断活动,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3],进而澄清教学评价的存在意义。
1.教学评价的基点是“课程理解”
解释学的核心话语是“理解”,在教育关系活动中,常伴随着理解现象的生发。教学评价作为一种从属于教师与学生的教育关系活动,在课堂场域中,此种关系活动构成了课程、教学与评价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磁力场,课程应然制约着教学评价,教学评价实然影响着课程[4]。教学评价本质上是对教学系统的构成要素即教材资源、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学媒体等进行诊断分析,以反馈教学信息从而达到为优化教学配置决策的目的和过程,而教学系统是课程外显化的载体,教学评价的设计与实施就势必涉及对课程转化的理解。解释学的基本观点认为理解建构着与被理解事物的关系和意义。教师对课程与教学关系的理解表征为教学评价实践,教学评价是对课程评价意义的深化。
2.教学评价遵循“文本诠释”精神
在解释学中,文本诠释象征着文本精神,意指读者对文本内容背后的作者意图和思想的解读。教学文本是在具体教学情境中生产和接受的动态文本,其文本精神在于教师对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文本的诠释。教学文本是课堂教学评价的依据和媒介,评价实践遵循文本诠释的内在逻辑,并基于对文本背后的“促进教学”意涵的解读来落实。促进教学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通过测验来探察认知水平,而是将评价定位成对学习者信息持续推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更多依赖于对文本中教学事件、案例等事项的组织、整合、探究,捕捉或生成真实的评价信息来检测与改善学习,对呈现的评价结果作出合理的解释,以此形成为课程和教学服务的评价模型。在文本诠释中,无论是对课标、课本等规范性的课程教材文本的考察还是对在授课实录中演绎的文本如教案、会话记录、课后作业的审思,都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创造的文本系统,融合了学生的视域,隐含了学生不同阶段的学习行为与特征,对文本的分析能够获取这些信息,并以此设计课堂教学评价指标[5]。
3.教学评价存在“师生对话”属性
在解释学中,对话是理解的途径,而理解发生于人的关系性活动中。从这点上看,教学评价的主体是师生,必然伴随着理解的萌生,进而产生对话。首先从课堂教学本身来讲,课堂互动的核心是师生间的对话关系,互动性是一堂好课的基本特征和先决条件。单就教学而言,改变过去机械授受恒定公式和定理的教学方法,转以灵活对话的方式纠正原有的认知偏差和错误概念从而加深教学理解、建构教学意义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教改共识,对教学偏差与错误的诊改正是教学评价存在本身。教学评价是课堂教学的“心理诊所”,贯穿课堂教学过程,不可否认其在具体教学实践上有着深刻的“对话”逻辑。其次,从教学评价的性质来看,其价值判断准则之一是教学活动满足个体需要的程度,课堂教学评价要客观地衡量学生的综合素质,那么对德智体美劳各项变量的评价就决定了它不是一种简单的以实证测量为基本范式的量化评价,对评价对象和内容的阶段性、持续性、形成性的诊断和评测遵循的是对话式问答逻辑,收集评价信息更多是以文本叙事、观察记录、描述取向为本的质性评价,语言是必要的评估手法,课堂对话也就呼之欲出。
4.教学评价承载“育人意义”
传统教学评价遵循课程本位,多围绕教科书展开,反映在课堂中是對学习任务的程序化拆解,是基于心理测量的技术选择而非育人向度的价值判断。评价的范畴倾向于以认知、技能领域为中心,意义在于短期教学目标的达成,即便在三维目标导向下,一些更深入的能力或心理素质,比如高级信息处理、情感意志也难以被信度、效度、区分度等技术指标评估,不符合课堂教学情境的实际。教学情境的本质是变化,教学评价理应是对变化的评价,是一种理解教学情境的评价。现代教学观倡导教学应“为理解而教”,学生学习“随理解而学”,且解释学主张在理解社会和历史情境中考察人的意义,因此教学理解要关注到教学情境背后教师与学生的文化心理、社会经验,评价要落地于情境化的课堂实践中,使课程评价让渡课堂评价,收集学生知识探究、素养培育过程的信息,以作为判断课程育人价值的信息媒介,建构从理解课程到理解人的价值的评价意义,此种意义是对当下课程改革中“培养什么人”问题的回答,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学追求。
二、教师教学评价素养实践的表征
现代教学评价观倡导教育者应发展一种非技术理性的评价素养,这种素养的功用不是作为实证测量和总结评估的手段,而是为了在实践中加深对评价的理解和为改善教学服务。在解释学语境下,教师教学评价素养实践有其独特的“解释”维度。
1.“理解”规定着教师的评价意识存在
解释学家认为,人因为理解而存在[6]。教学评价从属于人的教育活动范畴,是教育理解的过程,教师对评价的“理解”规定着评价意识的存在。从评价素养的涵义和结构来看,一者评价素养是指“个人对评价基本概念和程序的理解,并对教学决策产生可能的影响”[7]。其规定性体现在对教育教学与评价的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解,这种关系在于证明评价是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教学离不开评价,评价亦离不开教学[8]。指向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建构一种具体的“理解”框架,以解释教学过程中的问题。狄尔泰认为,解释问题应该被融入到更广阔的历史视域中。理解教学与评价的关系或者说理解评价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形式,应将其纳入更广阔的教育情境,通过考察课程、教学、评价的互动关系,培育教师的评价意识。二者评价意识是评价素养的基础,教学评价素养实践是对教学评价活动整体的关注与局部要素的察觉,其意识规定性反映在教师对单一的评价行为、语言到复杂的评價目标设计、评价过程观察、评价结果分析等评价技术实践的理解,以使教师在实际的评价活动中保持评价意识的基本方位。
2.“文本”是教师评价知能的实践载体
伽达默尔说:“我们通过解释让文本说话。”解释总是以文本为依托,教师通过文本分析和解释教学信息,以此作为教学评价的根据。教师建构教学评价的文本有两类。一类是现成的、正式的评价文本,主要为学业评价政策和课程标准、纲要等。此类文本提供宏观和总体的评价要求和规则,就学业评价政策而言,评价政策过于理论化和抽象化,无法直接为教学提供示范性、操作性指导。另一类文本是生成的、非正式的评价文本。这类文本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创造的文本,如试卷、教学档案袋、作文、教师日志等,是使评价政策、课程标准落地于情境化、具象化的课堂评价的抓手。教师借助政策条例和纲要将评价要求和标准运用到教学中,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文本的融合,将“文本式”的教学评价理论、范型转化为教师教学评价素养中的评价知识与能力,遵循的是实践逻辑而非文本逻辑,因此教师教学评价素养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做好从教育政策到教学实践之间的转化[9]。
3.“对话”作为教师的评价行为表现机制
在解释学语境下,语言是理解的技艺,“在关于我们和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被语言包容”[10]。借助语言,教师在课堂中的评价行为以一种“师生对话”的规则上演,表现为涵括三种实践要素的评价机制:一是基于课堂情境的行动,对话使教学语言情境化进而阐明学习的现象和因果,并以对话的形式将评价的结果反馈给对方,这种教学语言具有生成性的特点,包括形成性的课堂评价、解释、交流和报告[11]。二是对话重置了评价主客体身份,构建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合法的边缘参与,打破了教师作为评价者“话语专权”与学生“话语孤岛”的局面,使教师的评价行为从主导向协商转变。三是评价共同体的建构,这意味着一种对话系统的形成。这种对话系统以“回应—协商—共识”为基本模式,在回应教学问题、协商评价方案、达成教学共识的对话三部曲中,蕴涵着相应的评价行为及尺度:沟通学习目标;协调表现性任务、标准;在理解中开发焦点;试图调动学生的好奇心,为激励学生思考提出高质量的问题;让学生有效参与课堂讨论;从学生对教师的反馈中获得信息;教师对学习质量给出定期的反馈[12]。
4.“意义”是教师在情境适应性评价中的产物
哲学解释学重视对历史情境的理解以阐明“人”的意义。重视“人”的意义的课堂教学评价是一种情境适应性评价。情境适应性评价是一种质性评价范式,是特定课堂情境中的表现性评价实践,与基于传统心理测量学的量化评价不同,其价值不是“我们如何知道”,而在于澄清被测量技术裹挟的人本意义,是“通过理解而存在的意义”。评价的“情境性”扩展了评价的视界再次呈现教学内容产生的历史情境,唤醒学生已有体验进而助益学生发展,克服了教学评价中去背景化、去时间化、去个性化和去整体化的弊端[13]。这体现在作为评价者的教师在情境适应性评价实践中一来重视评价对象的知识背景、兴趣偏好,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个体差异性,向学生开放评价过程,引导学生参与评价[14];二来强调评价关注的长时性,通过多次课堂对话、多类教学案例的分析,教师能关注到学生更多的表现细节,包含着教师能区分教学情境中什么是重要的,充分运用自己所知道的去解释课堂情境产生的原因,并将这种情境与评价结果或更广泛的学习建立关联[15]。因此,情境适应性评价实践产生的意义有四点:构建师生关系;在理解中遵循个性和情感的共鸣;形成“以学评教”的思维;构成“因材施教”的基础。
三、教师教学评价素养实践的机理
教师教学评价素养实践不仅表征于解释学的实践形式,其实践机理更内在于解释学存在的要素之中。从解释学视角诠释教师教学评价素养实践的机理,也为澄明教师评价素养发展理路提供了视野。
1.教师的评价意识强化是一种“循环”进程
在解释学中,理解是一种循环进程,这种进程称为“解释学循环”,其本质是整体与局部的相互循环运动。从评价素养的作用机制和形式来看,教师评价素养内隐于“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结果”的整体教学实践系统中,包括四个环节:“理解评价—使用评价—管理评价—元评价”。表面上,理解只是初始的局部活动,实际上理解发生在所有环节,如元评价就是对评价过程和结果的再次理解,旨在厘清“目标—教学—学习—评价”的矛盾关系。理解过程中循环着三种评价意识要素:一是对象意识。对象意识强调明确的评价目标,课堂教学评价的对象包括学生表现、教师导引、学科内容,因此理解对象并非单一的主体性行为,对目标的验证需要学生和同行的参与,与他人共同实践与研究评价的意愿。二是反思意识。解释学认为理解是人的自我理解,教学评价中的反思是理解自身的一种回顾传统的行动,使教师获得学生反馈的同时更新自我认知,不仅益于教师在意识层面再造教学理解,还有助于教师保持考察教学内部要素的意识状态。三是自身意识。这种意识重在构建评价的态度,态度是学习的心理成分,包含观点、倾向和信念[15]。当教师形塑自身意识时,其对教学的理解就内化为一种教学倾向或信念,并使评价意识在遵循和违背这种倾向或信念的循环中生长。
2.“先见”是教师评价知能转化的实践基础
解释学认为,理解事物需要一定的前理解结构,即所谓的“先见”。教师的先见是建构专业知识、延伸教学能力的实践起点,而任何知识与能力转化为素养的实践都是“心灵先天力量与环境后天互动演化的积淀”[16]。教师的先见表征为一种实践性知识,这种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应对课堂变化的内在经验,揭示了隐藏在课堂表象背后的背景性知识。这种背景性知识内塑了教师在教学生活中的前理解进而造就了新的教学理解,使教师能够在评价学生学习之前获得相关信息,成为教师诊断和评估教学、呈现评价素养高效教学实践特征的关联点。它构成了理解者与理解对象的历史性关联,使得作为理解主体的教师在不同历史环境、条件下,重塑教学文本的意涵。但教师不能只是参照教材文本、课程纲要的标准来评价课堂教学,文本式课堂只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隐于水下的“冰山”才是真正的课堂,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来源于也作用于深度的课堂文化。譬如在伦理层面,教师实践评价前要对学生的心理状态、学业表现有先行概念和经验认知,使评价结果能在遵循客观性和规律性的基础上,保证教师公正、平等、民主地对待学生,而非视学生为教学附庸,在各种评价情境中加以贬抑[17]。
3.“預期”驱动教师评价行为的反思和改进
在解释学中,理解需要做出“预备规划”,是对于理解事物的一种“预期”。在教学实践中,教师的教学行动都是基于预设的教学目标展开,诚如泰勒所言“我们试图让学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是一种宏观的教学预期。教学预期是对课程目标落实的预估,目标具有引导评价的主要功能,因此对教学预期的检验通常是取向于评价的教学行动选择。而课程目标来源于学习者、社会生活和学科本身,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文化和社会结构图式,教学预期不仅是对技术的预期,更是对意义的预期,这就内在决定了课堂教学评价不只是具有诊断、证伪和测量的技术操作,更重要的是使评价对象“向善”的属性,这种向善的属性在具体的评价技术指标上负载着对人的心理、社会和文化的价值预期,包括学生学习经验分析、课程资源的转化、学科内容及标准等,可见教师建构评价的障碍更多来自于心理和社会层面,而不单是技术层面[18]。教师要“预先评估学习目标,运用评估信息指导教学”来界定教学的预期值,反思在评价中是否促进了学习经验提供给学习者去实践目标所含内容的机会,是否由于实践目标而获得满足感,是否使学生在能力范围内回应了学习经验的期望,对教学的预期驱动着教师诘问教学进程来反思和改进具体的评价行为:(1)缘何评价?评价的过程、结果倾向于清晰恰当的目标;(2)评价什么?要呈现有价值的学习目标;(3)怎样评价?目标要转化成精确的结果;(4)怎样沟通?评价结果能改善教学管理和促进师生交流;(5)学生何为?学生参与和建构自我评价[19]。
4.“时间间距”是教师深化评价意义的媒介
任何教学实践活动的意义延伸都需要历经一定周期,这种周期在解释学中被称为“时间间距”。教学的时间间距是使教学文本创作时间背后的思想、信念、精神和空间等方面的差异得以被理解的时间距离,充斥着各种教学传统、习俗观念的意义延续。教师的教学评价素养作为一种实践性素养,在教学实践中不是简单地呈现为编撰评价素材来评价教学内容、对象的过程,而是不断反思、批判教学,通过阐明教学文本来理解教与学的实际差异,并由教师和学生共同诠释意义的过程。从这点上看,教学评价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依托教学文本建构意义的时间间距,时间间距是教学评价意义得以深化的媒介。时间间距的媒介功能发挥依赖于在过程中创设教学情境,展开情境适应性评价。情境适应性评价中的教学文本诠释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时间性特征。其一,文本诠释的共时性是指在评价活动中师生共同参与文本建构,体现出对话、协商、沟通的精神,借由对话协商的方式了解相关利益主体的观点、需求和关注的问题,达成对评价意义的共同理解的开放性过程[20]。其二,文本诠释的历时性是指教师和学生与文本背后的作者之间交流,根植于“教学前期文本—教学中期文本—教学后期文本”的历史间隔,在“学情诊断—中期评估—信息传递—结果呈现—信息回馈—改善教学”的评价过程中揭示文本意义。
5.教学评价素养实践的实质是“视域融合”
教师的教学评价素养实践是教师根据自身前有的知识经验作用于理解对象的主客关系活动,解释学将这种理解活动的过程称之为“视域融合”,视域融合以理解为核心,以对话、接纳、相互作用为条件,使理解者与被理解者双方的视域不断扩大、丰富,从而融合成新的视域。教师教学评价素养实践主要围绕课程和学生架构视域空间,课程的视域以学科文化和课程编制者的要求为纲,学生的视域则由涵括其学习经验、生活观念的先见而衍生。一方面,教师在理解教材的基础上对课程落地课堂的检验和修缮,是对课程评价的拆分、深化和改进,提供了将课程文本解构为教学文本的信息。另一方面,教师在课堂师生交往的情境中,以教学文本为单元,以课堂对话为要素,将作为教师“先见”的实践性知识编码和外显化,借以辅助教师诊断学生学情并为改进学业成就提供参考信息,教师在获得学生反馈的同时也能获得来自学生的评价。无论是课程的视域还是学生的视域,都是构成教学理解进而使双方视域融合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促成教学理解的过程中,教师教学评价素养并非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一种运动的精神状态,直接或间接、完全或不完全的融入到“检测”“监控”“反馈”“支持”理解教学目标、过程、结果和“沟通”“适应”“参与”理解教学对象、内容、方法的实践场域中,驱动教师的一般能力向评价素养迁移,保持着教学评价素养的实践平衡[21]。
参考文献
[1] Stiggins,R.J.Assessment literacy[J].Phi Delta Kappan,1991(72):534-539.
[2] 张瑞.情境适应性教学评价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8.
[3]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3.
[4] 王少非.课堂需要什么样的评价[J].当代教育科学,2015(18):17-21+26.
[5] 陳佑清,陶涛.“以学评教”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设计[J].课程·教材·教法,2016(01):45-52.
[6] 金生鈜.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42.
[7] Popham,W.J.Assessment literacy overlooked:A teacher educators confession[J].The Teacher Educator,2011(46):265-273.
[8] 赵德成.促进教学的测验与评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8.
[9][22] 余闻婧,吴刚平.教师教学评价素养的形态及其意义[J].全球教育展望,2014(11):52-61.
[10]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62.
[11] Stiggins,R.,&Duke,D.Effective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requires assessment leadership[J].Phi Delta Kappan,2008(90):285-291.
[12] David,H.,Melvin,C.,Ridzuan,R.,Dennis,K.,Khin,M.A.,Siok,C.L.,Yee,Z.S.,& Wenshu,L.Assessment and the logic of instructional practice in Secondary 3 English and mathematics classrooms in Singapore[J].Review of Education,2013(01):57-106.
[13] 张瑞,朱德全.情境适应性课堂教学评价[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13):61-64.
[14] 郑东辉.教师需要怎样的评价知识[J].教师教育研究,2010(05):48-52.
[15] Erin,M.F.Linking a learning progression for natural selection to teachersenactment of formative assessment[J].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012(49):1181-1210.
[16] Mason,J.Being mathematical with and in front of learners[A].In B.Jaworski&T.Wood(Eds.),The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or as a developing professional[C].Rotterdam,The Netherlands:Sense Publishers,2008:31-35.
[17] 李伟斌,张李娜.休谟道德哲学新论[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2):68-72.
[18] 王帅.教师评价偏见与反偏见评价建构[J].中国教育学刊,2013(06):81-84.
[19] Dwyer,C.A.Assessment and classroom learning:Theory and practice[J].Assessment in Education,1998(05):131-136.
[20] Francesca,C.Teacher competence frameworks in europe:policy-as-discourse and policy -as-practice[J].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2014(02):1-21.
[21] 刘志军.教育评价的反思和建构[J].教育研究,2004(02):59-64.
[作者:张瑞(1980-),女,河南项城人,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覃千钟(1994-),广西玉林人,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科研助理,硕士。]
【责任编辑 郑雪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