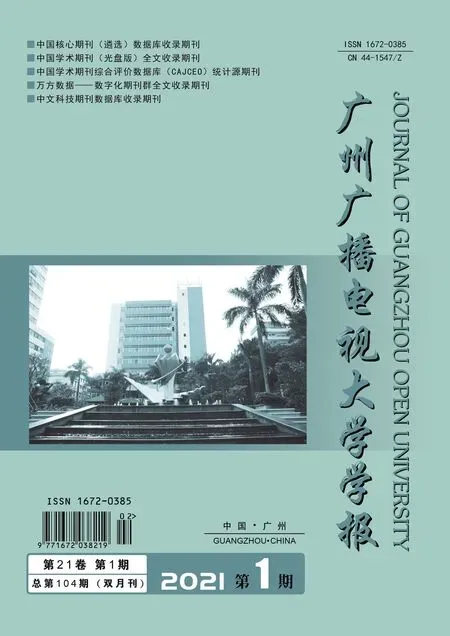论中国写意小说之流变
2021-11-30陈闽燕
陈闽燕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写意精神是中国古典艺术最主要的精神,在“小说界革命”以前,这种精神一直存在于古典诗文和书画之中,并没有对小说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直到晚晴“小说界革命”一改小说“街谈巷议”、文学末流的地位,将小说捧进文字正宗的殿堂,并尊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是“改良群治”之良方,写意精神也开始进入小说艺术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小说文类地位的提高改变了人们的文化心态,越来越多的高素质文人开始加入小说创作,他们积极为小说艺术的发展寻求新的审美素质,而他们身上积淀的深厚的诗文书画艺术素质很自然地成了推动小说艺术现代化的重要资源,写意精神因之进入小说,写意小说由此诞生。
一、写意小说概念辨析
不同于写实小说以情节或人物为内容核心,写意小说以意绪或情趣为内容核心,注重意境营造和氛围渲染,以“写意”为独特的美学追求,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小说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继承与延续,又开拓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另一途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废名、沈从文、萧红、萧乾、孙犁、汪曾祺、林斤澜、何立伟等作家创作的写意小说给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清新淡远的风致,在一众描绘复杂人性与苦难现实的小说中呈现出梦幻的色彩和诗意的美感。
写意小说旨在表现作者的情绪或理念,这与以情感抒发为目的抒情小说有相通之处,因而也有“诗化小说”之称。但细究之下,还是可以发现二者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不同于主要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因而追求情感不受拘束地释放的抒情小说,写意小说更多表现出对古代诗文传统的继承意向,强调情感表达含蓄节制。此外,抒情小说为了方便情感抒发,叙述视角往往选择“内转”,以主体的情绪来辐射外界事物,使之“皆着我之色彩”,而写意小说更关注的是如何将自己的情感客观化,通过营造意境来达到一种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
读写意小说,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一种近似于散文的“散漫”之感,有时甚至无法分辨二者的区别,周作人就曾将废名的一些小说作品收进了《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中,并认为这些小说与小品散文无异。汪曾祺的小说也突出表现出“信马由缰,为文无法”的“散文化”特征,他的小说《戴车匠》仅描写了戴车匠一年到头的活计,可以说是平静无波,也没有什么小说的结构技巧,就像是篇记人的抒情散文,仅留给我们一种安宁温暖的感受,一种哀婉和谐的情调。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家正是用“散文化小说”来命名写意小说。写意小说和散文都注重通过营造意境和渲染氛围来传达作者的某种情绪或意念,但是文体的区别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不能混为一谈,写意小说往往具有较多的虚构性内容,这与散文的文类要求相悖。因此,相较于“诗化小说”和“散文化小说”,本文选择“写意小说”这一命名。
二、写意小说之流变历程
纵观中国现代小说史,代表启蒙现代性追求的写实小说始终居于小说发展的主流位置,而追求审美现代性的写意小说稍显无人问津,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在某些时期甚至被认为是异端)位置。虽然地位尴尬,但每个时期都有一批文人以写意精神为自己艺术创作的底色和基质,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默默耕耘着一块平淡静穆的小说园地,在炮火哭喊中以舒缓安宁的调子奏出一曲安息曲。
意境是中国古典艺术的重要素质,它是审美主体通过将内在的情感理念与外在的客观事物相交融的方式,创造一个富有韵味和张力的审美空间。在古典文论中,意境的有无是评判文学作品好坏的重要尺度。对于写意小说而言,意境的营造处于重要的地位,而处于写实小说核心的人物、情节在写意小说中仅作为意境的营造工具而存在,优秀的写意小说必须拥有圆融的意境,并由此传递出作者特定的情绪、理念和意味。写意小说在理论上可追溯到王国维的“境界说”,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的观点,虽然他并非“境界”一词的首创者,但他对“境界”融贯中西的系统论述使“境界”或“意境”成为中国文人创作的重要追求,同时也为将意境作为小说艺术因素提供了理论前提,为写意小说的出现洞开了光明前景。真正将“意境”引入小说创作领域的是周作人,他在为废名小说作的序中肯定了废名在文章中创造的独特意境,并从文体变迁的角度对此表示欣赏。在这里,周作人正式把意境这一范畴引入到小说中来,并且从小说文体的高度揭示了这种造“境”的小说的重要性与可能性。[1]在王国维和周作人的理论倡导下,一批作家开始有意在小说中营造意境,探索小说写意的可能性。
废名是20年代写意小说的代表作家,他化古典诗词意境于小说之中,打造出一个宛如唐人绝句般的静穆空灵的小说境界。他笔下质朴而恬静的田园生活与他对人生的诗意感受水乳交融,他的小说与其说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不如说是在谱写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在《菱荡》中,废名没有设置情节波澜和人物矛盾,而专注于描绘陶家村的景致,勾勒这里的深山绿水,翠竹菱荡,清幽的环境与静默的人物和谐交融一同构筑出一种冲淡幽远的禅境,这一禅境正是作者的美学理想的具象化。废名独具特色的写意小说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小说创作,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作家在废名的熏陶下在小说中追求写意美。
30年代,京派作家群以废名为导师,继续进行写意小说的创作和艺术探索。这一作家群包含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李健吾、何其芳、林徽因等成员,他们自觉与时代政治保持距离,高蹈于现实功利之上,虔诚而执着地追求艺术美,讲求一种“纯正的文学趣味”,注意节制情感,营造一种“和谐”的艺术境界,从而达到“美化人生”“净化人心”的目的。这种人生的艺术化的立场注定了京派作家会采取一种与现实主义小说截然不同的创作法则,他们摆脱情节、人物要素对小说的桎梏,力求构筑一个“和谐”“圆融”“精粹”的意境,正如沈从文所说的:“重要的,也许还是培养手与心那个‘境’。一个比较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2]在《边城》中那个古朴纯净、爱无等差的湘西世界,人、景、物等呈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神性光辉,这是现代的桃花源、民族的乌托邦。小说在叙述翠翠的爱情悲剧的同时,运用了大量笔墨描绘湘西地区优美的自然风光、淳朴原始的民风、真诚善良的人性和简单纯粹的人生,人性的美好与自然的秀丽交织成一个寄寓着作者理想人生形式的意境。这时期的写意小说虽然以京派作家的创作最为引人注意,但其他一些作家也创作了不少出色的写意小说,为写意小说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这一时期,写意小说的创作还较为普遍。其中,萧红作品中的写意性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她的小说呈现出明显的“散文化”倾向,《呼兰河传》没有统一的情节线索,只有零零碎碎的故事和形形色色的人物轮番上场,因此读来“不像一部小说”,但是它却有“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其实,这些“诱人的东西”就来自于它的写意美。小说以回忆的方式和情绪的线索,将童年记忆中的零散片断用情绪缀合起来,用散文笔法淡化故事性,强化抒情性,整部小说笼罩着作者淡淡的忧伤和愁绪,传达出她对童年的缅怀和对人生的感悟。在这种情绪的统摄下,呼兰河城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弥漫着浓厚的人文气息的文化空间,是具有无限张力、蕴藉着丰富寓意的小说意境。
到了40年代,复杂的政治形势影响着文学创作,此前较为宽松自由的创作空间开始紧缩,写实小说完全占据了小说创作的统治地位,而写意小说因其疏离于时代政治而遭到主流的排斥,这一时期,除了此前钟情于写意小说的作家的坚守外,仍有一些作家被写意小说的魅力所吸引。沦陷区的张爱玲创作的新旧意境交融的小说成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傅雷语)。她的小说总是充满了纷繁的意象,共同形成一个独属于张爱玲的苍凉意境。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在描写长安与世舫分手的场景时,没有让人物老套地哭哭啼啼、絮絮叨叨,而是冷静地择取几个富有象征性的事物,如“一树的枯枝”“瓷上的冰纹”“淡黄的雏菊”“水晶瓶”等,这些意象包孕着丰富的意味,筑成一个沉郁苍凉的意境。读者就在这意境中体味人生的悲凉无奈。解放区虽然大力提倡小说艺术的民族化与通俗化,但写意小说依旧占有一席之地。孙犁的小说同废名和京派的写意小说有相通之处,不过在解放区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孙犁的小说克服了此前写意小说过于文人化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吸收了一些写实小说的因素,推动写意小说走向通俗化、平民化。二三十年代的写意小说注重的是渲染氛围、营造意境和寄寓理念,人物、情节都是围绕着意境创造和意绪传达而存在,因此,写意小说通常没有复杂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而解放区文艺政策对小说创作的“硬性”要求使得孙犁不得不吸收写实小说塑造人物形象和设置情节波澜的方法,对写意小说进行“改良”。[4]他的小说既描绘白洋淀地区美丽的自然风光,营造了一个灵秀温馨的荷花世界,又塑造了一批善良坚韧的劳动妇女形象,自然美与人性美共同交织成一个清新明丽的小说意境,但激烈的敌我斗争描写和细腻的人物刻画又让人们没有沉浸其中,而是清醒地意识到现实战况的惨烈。因此,较此前的写意小说,孙犁的小说更加通俗质朴,体现了写意小说在解放区的新的艺术探索。
建国后的小说文体意识和小说体式原则脱胎于解放区小说,仍表现出向传统体式回归和向民族化大众化靠拢的趋向。这一趋向在国家有意的推动下,在五六十年代更加定型化和教条化。五四以来形成的小说艺术自由发展,体式多样的格局被打破,性格、情节类小说牢牢占据建国后小说的统治地位,抒情小说也被迫掺入大量情节性因素,而写意小说则被冷落,不得不退出人们的视野。在50年代中期,“双百”政策让作家们紧张的心态有所放松,不仅在内容上开始涉及一些曾经的禁区,在艺术上也进行了一些富有探索性的尝试。茹志鹃、陆文夫、宗璞、汪曾祺等作家创作了一批迥异于此前故事型小说的作品,这些小说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写意精神的复苏,这种写意美在千篇一律、展现路线斗争的小说中犹如一阵温和湿润的清风,使人们如临春天。但好景不长,很快这种探索就被迫中断了,写意小说又重新陷入沉滞,这种“冰封”局面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文革结束后,国家拨乱反正,局势趋于稳定,经济也得到发展,各种思潮的涌入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作家有了余裕和从容的心态从事符合自己审美趋向的创作活动,人们也有了条件追求多元的审美旨趣,尤其是文革带来的种种“后遗症”,让人们更加崇尚才情、风骨和品格,这些都支持和鼓励着作家在创作中释放个人的意绪和情趣。80年代,作家的创作从政治历史的确证过渡到文化审美的选择上,他们身上积淀的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很自然地使他们转向了写意小说。因此,这时期写意小说又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在一众富有西方现代意味的小说中显现出中国古典文学的雅致。这时期汪曾祺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小说的出现为写意小说的回归发出了一个醒目的信号,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他的影响下,阿城、何立伟、贾平凹等作家也开始有意传承传统文化的血脉,在小说中展现古典美学的风韵。新时期写意小说的突出特征是表现出一种“士大夫情调”,这种情调体现为“亲近自然,崇尚平淡,超脱名利,去动适静,唯性是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气质秉性。这时期文人精神气度的复归与重振,是一些作家应对社会变革和重建精神家园所选择的策略和姿态。[5]因此,当代写意小说家总是以舒缓平易的笔调勾勒着世间百态,他们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天人合一、情理交融的达到超逸明净的艺术境界,只有人间烟火气的温馨,没有世俗的蝇营狗苟,一切都温柔似水、轻淡如烟,充盈着文人的人格修养和精神品性。《受戒》是汪曾祺的一个美梦,这里没有俗世的纷扰和俗人的机心,少男少女的纯洁爱情与水乡的温馨古朴相互映衬、浑然天成,俨然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化境。
90年代是一个精英文化让位于大众文化的时代,写意小说的热度在市场经济和影视文化的双重夹击下逐渐降温,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立场也随之向大众文化立场位移。一部分作家放弃了写意小说的创作而转向更适应市场需求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一部分作家投入影视剧本的创作之中,更甚者一些作家在市场经济浪潮的裹挟下停止创作,转行经商或是出国发展。[6]兴盛一时的写意小说创作骤然冷清下来,再也没有形成80年代那样备受瞩目的气势。尽管新时期写意小说的“领头羊”汪曾祺仍然坚持创作,他在这一时期笔耕不辍,创作了《捡烂纸的老头》《明白官》《护秋》《鹿井丹泉》《梦》等作品,虽然数量可观,但从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上却没能超越他在80年代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值得欣慰的是,除了汪曾祺的坚守之外,迟子建、曹文轩还有一些九十年代新晋的青年作家依旧埋首于写意小说的园地,默默耕耘,为这一小说体式的发展苦心经营着。也正是这些作家的努力,写意小说得以进入新世纪文坛,并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相比于此前的写意小说,还孕育出了一些新的因素。
写意小说的命运虽然多舛,但对于它的未来,我们大可以放心。写意小说虽说从未取得主流的地位,在一些时期还被封锁雪藏过,但它永远不会消失。就像我们的古典文化不会消失一样,对写意美的追求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因此不管它是暂时的“走红”,还是突然的“遇冷”,我们只需以平常心待之,正如汪曾祺早已洞悉的——写意小说“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在新世纪,网络小说的崛起成为一道新的景观,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而写意小说在一方静穆的小天地依然为人们提供着一个诗意的心灵栖息地。
三、结语
纵观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史,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转型是在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学冲击下开始的,因此,现代小说在艺术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反传统性和西化倾向。然而,除了西方文化因素的促动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古典美学传统犹如一脉地下泉水默默滋养着小说艺术,孕育出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的写意小说,一代代作家文人的创作实践又使写意小说走向成熟壮大。在西方文明占据话语权的当下,这种写意性对保持中国小说的独立品格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