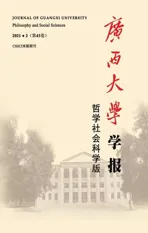论清初的华夷之辨与王朝认同
2021-11-30姜维枫
姜维枫
华夷之辨即辨别华夏与夷狄,为传统中国的民族关系理论之一。华夷观形成于春秋,后世每临夷狄交侵,华夷之辨常常被加以强调。明清易代,满族入主中原,华夷之辨对清初不同阶层、人群的心理与行为均产生深刻影响。华夷观成为清初令出之基础,如“剃发易服”“文字狱”“博学鸿词”“修明史”“纂图书”“移风俗”“兴文教”等,可视为清廷于华夷观之下执政的若干步骤。高压与怀柔或两相交融,或“辨”或“融”的华夷之策,是清初帝王不遗余力的王朝治理技术。如何认知清初不同群体之华夷观,对其做“辨”或“融”的论断,均会失之偏颇。本文从帝王、仕清者、遗民三类群体出发,对清初社会的华夷观及其流衍加以梳理,揭析清初华夷之辨的内涵与走向,希冀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一、清初帝王之华夷观
本文所谓“清初”,特指顺康两朝。鉴于思想形成流衍的纵向性,故对顺康前后之华夷观亦稍加综括,以见清初华夷观之大旨。
清初“辨华夷”必言“大一统”。清入关前,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代“大一统”思想的基本理路是奉明朝为“中国”,自视可与“中国”共同构成“天下”,而一旦天命归之,则“我”可为天下之主。努尔哈赤曾言:“天降大国之君,以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1]339“我本大金之裔,曷尝受制于人,或天命有归,即国之寡小勿论,天自扶而成之也。”[1]377-378皇太极认为:“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2]努尔哈赤与皇太极虽未明言“大一统”与华夷,然均认同明乃天下之共主,而非一国之主,大金与昔日之辽金元一样,均足以与“中国”抗衡,有朝一日天命归大金,则大金即为天下之共主。
顺治年间,摄政王多尔衮与顺治帝均倡疆域与文化“一统”,并自列正统。顺治元年(1644)十月,帝告祭天地,称“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3]91,同年南明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致书史可法,称“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4]。一国难容二主,表达了统一国家主权不容分割的意愿。顺治二年(1645),清廷举行入关以来首次历代帝王庙祀典,如何论列前代具有“夷狄”身份的帝王,关乎大清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按故明洪武初年立庙,将元世祖入庙享祀,而辽、金各帝皆不与焉。但稽:大辽,则宋曾纳贡;大金,则宋曾称侄。当日宋之天下,辽金分统南北之天下也。今帝王庙祀,似不得独遗。应将辽太祖,并功臣耶律曷鲁,金太祖、金世宗,并功臣完颜粘没罕、完颜斡离不,俱入庙享祀。元世祖之有天下,功因太祖,未有世祖入庙,而可遗太祖者。则元世祖之上,乃应追崇元太祖一位。其功臣木华黎、伯颜、应从祀焉。至明太祖,并功臣徐达、刘基、各宜增入。照次享祀,以昭帝王功业之隆。用彰皇上追崇往哲至意。[3]130
礼部奏请充分论证了历代“夷狄”之君的正统性,无论“分统”天下如“辽金”,亦或“有天下”之元世祖,均视为正统,入庙享祀,将元辽金国君均列正统。世祖“一视华夷”的倡导得到了圣祖呼应,康熙六十一年(1722),圣祖诏令“凡为天下主,除亡国暨无道被弑,悉当庙祀”[5]2526,昌明其“华夷一家”之立场。
论者通常将血缘、地缘、文化视为“华夷之辨”三义。对清帝而言,血缘不可改变,彼时已居中原,文化的同源则是可论证的。康熙帝很清楚如何将王朝纳入华夏统绪、编入治道正统,以拥有统御天下的合法性。康熙帝不仅从知识、制度、思想等层面主动接纳学习宣扬汉文化,以阐述满汉夷夏关系,还炮制了泰山与长白山的地缘政治论,其刊布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云:
古今论九州山脉,但言华山为虎,泰山为龙。地理家亦仅云泰山特起东方,张左右翼为障,未根究泰山之龙于何处发脉。朕细考形势,深究地络,遣人航海测量,知泰山实发龙于长白山也。长白绵亘乌喇之南……于是乎,陆起西南行八百余里,结而为泰山,穹崇盘屈,为五岳首。此论虽古人所未及,而形理有确然可据者。[6]
泰山自古被奉为华夏至尊正统,“泰山,五岳之长,群神之宗,故独封泰山,告平于天,报神功也”[7],“泰山岱宗,五岳之长,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也”[8]。唐苏颋《大唐封东岳朝觐颂》云:“封祀之山,五在中国,泰岳首之;昊穹之命,再集巨唐,皇帝受之。”[9]元郝经认为“孰如兹山,中华正朔”[10]。明遗民阎尔梅称咏泰山“光伟如君子,尊严若老师。垂绅云汉上,华夏古威仪”[11]。封禅泰山乃历代帝王宣示一统、正统与合法性的最佳方式,泰山进入国家政治核心,即借助封禅仪典。因此,封禅虽绝响于宋真宗朝,然清康熙朝仍有曹禾上《封禅祀》“恭请皇上登封岱宗以告成功以昭盛德事”[12]52-53,熟稔汉文化的康熙帝自然知晓泰山在华夏文化的隆盛地位与象征意蕴。与之相应的是长白山,长白山是满族的政治文化符号,“乃祖宗发祥之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以昭国家茂膺神贶之意”[13]。故此,两山在清代政治、文化层面的特殊性可见一斑。文中所谓泰山为长白山同脉一说,章太炎与张相文均撰文考辨其“大谬不然”。然如从文题与国初治政需要看,“泰山实发龙于长白山”一说,实为康熙帝借助两山的族群与王朝象征,论证清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从族源融合与王朝认同的角度来看,借两山同脉以表达“华夷一家”“满汉合一”的族群与王朝认同观亦十分明晰。
问题的关键是泰山与长白山在清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如检阅康熙帝祭祀泰山与长白及论列两山地位,则或有新的认知。康熙帝一生到泰山六次,登顶亲祀四次①康熙帝亲祀泰山四次,见于史档者三次,分别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帝另一次亲祀泰山发生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见周郢:《〈南巡惠爱录〉中康熙泰山之行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3-27)。,每年命有司致祭为常例。康熙皇帝首次遣官致祭泰山在康熙六年(1667)八月十七日,首次登顶亲祀泰山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康熙帝命臣初祭长白山为康熙十六年(1677)丁巳九月,晚于遣官致祭泰山十年;自此之后,命宁古塔官员每年春秋二祭在大乌拉设坛望祭,是为惯例;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又“遣内大臣觉罗武默纳、一等侍卫对秦,赍敕封长白山之神,祀典如五岳”[12]909。可知泰白两山之祀典同。康熙帝未曾登顶长白山,所谓亲祭均为在长白山近处设坛望祭:一次为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皇帝于松花江畔温德亨山设坛望祭长白山;一次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二十五日,吉林望祭长白山神,并作望祭长白山诗文。由此观之,泰白两山于康熙一朝处伯仲之间。研究者认为,“祖先的原住地和迁移经由地等是与子孙现在的身份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正如牧野所说,这是与周围的同盟者形成‘同乡观念’等连带意识的重要基础。……这已成为将自己的来历与中华文明的中心地连接起来、主张正统汉族后裔身份的最明确的依据之一”[14]。通观历史,从四夷族群不断融入华夏共同体的角度看,康熙帝关于“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何尝不是在寻求融入华夏正统族源、宣称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呢?可是问题往往没有这样简单,《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康熙年间的山岳祀典:“皇清国朝详定《岳镇祀典》《大清会典》,凡各处岳镇恭遇登极亲政、尊加徽号、册立东宫,一应庆贺大典、颁布恩诏,必遣官分行祭吿,每年仍令有司以时致祭。现在举行者:东岳泰山,山东泰安州祭;西岳华山,陕西华阴县祭;中岳嵩山,河南登封县祭;……”[15]38泰山为国朝登极亲政等大典之首告者,其地位之首出可以坐实。再以两山入编《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排序为例,在山川典之下分别为:山川总部-山总部-五岳总部-长白山部。由此观之,五岳位于长白山之前,而泰山居五岳之首。然同书《山川典》第九卷《长白山部汇考一》之《奉天府东北之长白山》又云:“长白山在今船厂东南一千三百余里,古名不咸山,又名太白山,又名白山。旧志称横亘千里、高二百里,……体势高大,支裔绵远,洵足雄冠五岳,俯视万山。”[15]43要之,据康熙朝关于泰白两山祭祀、位次、发脉等综合情况,两山在康熙朝政治格局中均举足轻重,泰山是统治合法性与王道的符号,长白山是政权神圣性的象征。基于此,康熙帝的华夷观可概括为基于本民族(满族)主体性的满汉融合、华夷一家。
雍乾两朝持守“天下一统、中外一家”和“奄有中原”即为正统观。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借曾静案之机,主动开启“华夷之辨”。十一年(1733)雍正帝又因“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指出“然则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16]696。雍正帝不讳言满洲为夷狄,其高标“一统”“中外一家”以对抗带有遗民情绪的“华夷之辨”。与祖父辈不同,乾隆帝从“奄有中原”的角度论列正统:“曩时皇祖敕议增祀,圣训至公,而陈议者未能曲体,乃列辽、金二朝,而遗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谓南北朝偏安,则辽、金亦未奄有中夏。即两晋诸代,因篡而斥,不知三国正统,本在昭烈。……昔杨维桢著《正统辨》,谓正统在宋,不在辽、金、元,其说甚当。”[5]2528乾隆帝认为“正统”的标准为“奄有中原”,并认为“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17],本朝正统并非来自北方的辽、金,清王朝为明复仇乃定鼎中原,其政统的合法性乃承继中原明朝正统而来。另外,高宗的《重建泰山神庙碑文》亦赋予泰山极其显赫尊崇的地位:“国家秩祀之典,方望实惟最重。而泰山为五岳宗长,功用显彰,为德尤盛。”[18]
此外,作为征服者与统治者能够认同华夏文化,主张华夷一家,还有基于统治技术的考量。雍正帝云:“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19]普通人与帝王言行之立足点不同,前者在于建立道统以维持家国人伦,后者则借道统为治统工具,以利家天下。
概言之,清初帝王的华夷观可概括为大一统、自视正统和基于本民族(满族)主体性的华夷一家。综括清初统治者的华夷观,不仅可见顺康雍乾四帝华夷观之变化,亦可窥见民族与王朝文化自信的曲折脉络。顺治朝增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入庙祀,流露出第一代帝王为自身争地位的心理倾向;康熙帝的“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论,无论是有意融入亦或强调本民族主体性的华夷一家,依然流露出自信之不足;至雍正帝始一变,雍正帝不讳言华夷,主动开启华夷辩论,呈现基于华夷一家与王朝认同的自信;乾隆帝认为“奄有中原”即为正统,且不因出身而偏袒辽金,政权与王朝的自信与认同愈发鲜明。
二、清初仕清群体之华夷观
清初仕清群体分为两类——由明入清者与生于新朝者。概言之,仕清群体普遍回避华夷之辨,其“正统论”也往往回避“夷狄”统绪,不辨华夷、主张华夷一家为此群体普遍之华夷观。
钱谦益为开清初文学之风气者,兼具“一身两姓之惭”的独特经历。就笔者目力所及,钱谦益诗文中未见直言“辨华夷”“论正统”之作。钱谦益入清后分为降清与反清两个阶段,前期当然不便做此论辩,后期诗文更多注重形塑“遗民”形象与心态。如其借议元明之际刘基做“忠贰之辩”为自己辩护,关于其降而又反的动因,学者多有分析,笔者以为华夷之辨的潜在意识则不可忽略。其《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其四)》云:“九州一失算残棋,幅裂区分信可悲。局内正当侵劫后,人间都道烂柯时。住山师子频申久,起陆龙蛇撇捩迟。杀尽羯奴才敛手,推枰何用更寻思。”[20]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1659),是年清廷派军南下围剿永历小朝廷,郑成功、张煌言趁机北伐,诗中以棋为喻,首尾以“九州”与“羯奴”对举,流露出自恃华夏鄙薄夷狄的心态,末联更见驱除夷狄之心。魏裔介为顺治三年(1646)进士,其《三国论》借论三国实辨正统,作者行文不言华夷,而是传达了“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儒家治道伦理:“取天下以德与才”“曹与孙,其才与德既无足取。昭烈仗义讨贼,屡经挫衄,志气不衰,卒以郁郁而死,才虽不足,其义则正矣。是以君子取之,以续汉统”[21]。作者首先将才德不足取的曹与孙排除在正统之外,认为刘才虽不足,然“正义”可取,“正义”即“仗义讨贼”,可谓“忠君”,“忠君”则为正统,这一理路契合了清初思想秩序的王朝意识。叶燮为康熙九年(1670)进士,其《正统论》同样不言“华夷”,认为德者、位者、作礼乐者方可称正统:“正统者,即夫子所云:三重寡过之君子也。……夫德者正也,位者统也。不敢作礼乐,虽王天下,不得称为寡过之君子。……未有德位不兼,而可称正统者也。”叶燮尤其强调道德仁义对于正统之重要,认为名实相符方为正统:“正统者,名不可以虚假乎实,而实不可以冒袭乎名,要使天下后世,知道德仁义之有常尊,而贼乱篡弑之足为诫也。”叶燮还进一步否定了遗民魏禧的“偏统”“窃统”说,认为:“统者,合天下之不一,既已偏矣,安得称统?”[22]209-210这实际上为王朝排除了“偏统”与“窃统”两种可能。魏裔介与叶燮的正统论均未论及具有“夷狄”身份的元朝,流露出仕清者有意回避“华夷之辨”的伦理意识。仕清群体对“道德”“仁义”的提倡正与其辞赋创作——《璇玑玉衡赋》《南郊赋》《皇京赋》《瀛台赋》《南苑赋》《帝京元夕赋》——相呼应:颂扬盛世仁德、倡扬天下一家,治国之道具有正确性,因而入主中原具有合法性。
仕清群体的华夷一家观在辞赋创作中多有呈现。彭孙遹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存赋17 篇,其赋借体物以颂美,推尊仁德政治,倡言天下一家。《帝京元夕赋》以元夕节为背景,描绘民物恬熙的世俗繁华,歌咏“合天下为一家,引六合为一身”,颂扬仁德之治:“知皇仁之溥遍。盖惟弘基积累,醲化奫沦。懿以文德,洽以深仁。”[23]8931《南郊赋》借玉杓北指,摹写行祭天大典,恭颂天地圣君,倡修儒家仁义道德、儒雅艺文;《白鹦鹉赋》借祥瑞而颂圣。李雯《琵琶赋》云“散钧天于华夷”[23]8579。尤侗《长白山赋》称扬“若我皇清之受命也,爰自朔方,始开大漠。函盖穹窿,广轮寥廓。上帝乃眷,名山斯托。睥睨三壶,凭陵五岳”[23]8666。汤斌《懋勤殿赋》称颂皇帝勤读兴儒、重实政轻嘉名,推重经世致用、尊崇制度文教、倡导礼乐、薄赋宽徭;天下弃伪返本、敦朴去浇;着意树立王朝与清帝兴儒重道的正统形象。其《长白山赋》以论证王朝正统、消弭华夷之辩为旨归,以长白山象征清廷帝王,实现国家一统,南北西东,“陆詟水慄,无不奔走而来宾”[23]8846,皇帝则耀德布恩,实行书礼教化。叶方蔼《进呈后瀛台赋》颂扬圣祖“遏乱取残,我武斯赫”“励精出治,不遑暇食”“文谟武烈”兢兢业业,而今“固已胥天下为一家,延八荒于我闼”[23]8862-8863。魏际瑞《登楼赋》以秦末南越王赵佗融合汉越文化的故典和冯盎由隋入唐治理岭南社会安定的典实,表达自己由明入清担当文化传承融合之责以及对王朝与社会安定的期待。总之,倡言一统、华夷一家,不一而足。
第一代仕清群体主观上呼应王朝治道,消弭华夷之辨,与帝王一起强化华夷一家的意识形态,传达出与清初遗民完全不同的华夷观,亦开启了第二代仕清者之华夷观。邵廷采生于顺治五年(1648),因屡试不第遂弃举业,其非遗非仕的特殊身份,有助于从另外的视角认识清初社会之华夷与正统观。《正统论》云:“其开地大而享国长久,守之以仁义,吾取汉唐及明而已。”[22]203表达了秉道德仁义而定是非的观念,其论列“正统”依据的是儒家道德仁义等君子规范,回避了华夷正统。黄中坚为顺治间贡生,后弃举子业,致力古文,其《正统论》开篇即重修“正统”之义:“统者何?帝王相承之绪也。正者何?不偏之谓也。合天下于一,而无有与之并立者,统斯正矣。”[24]同样不从“华夷”角度论正统,“无有与之并立者”斯为正统。由此观之,出生于新朝之士人已完全接受清之正统,至于更晚之士人如乾隆朝之章学诚,更直言大清为正统,其意又远非前之邵廷采、黄中坚可比:“自唐虞三代以还,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25]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帝王与仕清群体在共同的不辨(言)华夷观之外,还出现“以夷为正”观。仅以辞赋为例,清代赋家以长白山为题,表达满族正统的赋作达10 篇之多,而以“泰山”命篇的辞赋仅有两篇。其中尤侗《长白山赋》以议论之笔敦免清帝封禅长白:“古之封禅者,皆封泰山,禅梁甫。云云亭亭,不可胜数。而臣独谓百年不同时,千年不同士。天地循环,各从其主。惟兹长白,启我列祖。肇基王迹,削平险阻。崇德报功,允宜首举……”[23]8667晚清周沐润《长白山赋》更直言“大清受命,长白发祥”,“盖泰岱乃寰中之望,而长白为泰岱所宗”[23]15990-15991。要之,清初仕清群体的华夷观为不言华夷,天下一家,充分传达了王朝政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甚至出现满族正统观念。
三、清初遗民群体之华夷观
清初遗民华夷观在历时与共时层面均有呈现,前者呈现为由“辨华夷”到“不辨华夷”的衍化,后者呈现出保守与开放的异质性。
明亡于李闯,多尔衮入关前采纳范文程、洪承畴谏言并誓约“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违者罪之”[26],入京后又招抚亡明遗臣,为明帝发丧。对此,孟森先生认为:“覇者假借仁义,亦可与王者同功。要其优礼前代之意虽假,而于宽恤民生,使久罹水火之人倚我以图苏息,则事实不可诬也。”[26]清兵入关之初并未遇到太多的武力对抗,其初定江南时,汉族士民的排夷情绪与武力对抗亦不激烈,有史可查。所谓“东南郡邑一时帖然,犹若不知有鼎革之事者。自薙发令下,而人心始摇”[27]。《江阴城守纪》载,顺治二年(1645),六月“大清特授知县方亨到任”,“闰六月初一,江阴倡义守城。清晨,亨行香,诸生百余人及耆老百姓从至文庙。众问曰:今江阴已顺,想无他事矣。亨曰:止有薙发尔。前所差四兵,为押薙发故也。众曰:发可薙乎?亨曰:此清律,不可违。遂回衙。诸生许用等大言于明伦堂曰:头可断,发决不可薙也。适府中檄下,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亨命吏书示此言,吏掷笔于地曰:就死也罢。享欲笞之,共哗而出”。最终,是役“凡攻守八十一日,……然竟无一人降者”[28]。
中土儒士向来珍视自己的发肤,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29]。因此,清初行“薙发令”以来,以“藏发”“断发”“薙发”为题之作甚多。归庄云“发乃父母生,毁伤贻大辱,弃华而从夷,我罪今莫赎”“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30]。清人强行薙发易服等暴政本欲向汉人宣示可以通过武力强权等迫使他们屈服,乃至忘掉自己的文化习俗;然薙发易服令一出反激起广大汉人的民族情绪与抗清意志,同时亦唤醒了遗民心底的“华夷”之思,继而引发对清廷正统性与合法性的反抗及质疑。“清初三大家”均表达了严防夷夏的主张,王夫之云:“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呜呼!小人之乱君子,无殊于夷狄之乱华夏。……而夷夏分,以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类防之不可不严也。夫夷之乱华久矣,狎而召之、利而安之者,嗜利之小人也。”[31]黄宗羲认为:“中国之与夷狄也,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于人也。”[32]顾炎武则认为:“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33]卷七又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33]卷一三顾黄王的华夷观可视为清初遗民群体的主流意识,华夷之间不仅是内外之辨,而犹如君子小人、人兽之别,失于华夷之防,则天下亡,天下亡则华夏文化亡。站在今天的历史节点,反观遗民华夷之辨的某些表达,其中固然不无激烈或非理智的成分,然后人对其认识应不脱离清初高压与暴政的具体语境。
三大思想家之外,清初遗民辨“华夷”论“正统”,通常将“施暴”“弑杀”作为论辩的焦点。甘京《正统论》提出“正统”“篡统”“攘统”说,认为:“子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统,器也;正,名也。禅者,正统也。诛君吊民者,正统也……”甘京认为以禅让得君位、诛杀暴君抚慰百姓均可称正统,而“……宋赵匡胤、元忽必烈,此皆绝人之国,弑君、父、兄而自立为君,夺天子土宇而据之。万世而下,声其罪为篡”[22]206。其否定了元朝之正统,将其列为篡统,因其“弑杀”。甘京虽未论清之统绪,而其非正统之绪已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初遗民严防华夷观出现转圜。梁启超曾将清初分作三期,即所谓“利用政策”“高压政策”“怀柔政策”,遗民激烈的华夷之辨多处于前两期,“到第三期,值康熙帝亲政后数年……他的怀柔政策,分三着实施。第一着,为康熙十二年之荐举山林隐逸。第二着,为康熙十七年之荐举博学鸿儒。……第三着为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34]。三着过后,尤其是撰修“明史”,汉族读书人包括遗民的华夷之辨出现明显转换——由严防到边缘化乃至消解。时间是医治心灵、冲淡仇恨的最好良方,如黄宗羲于康熙十年(1671)开始使用清朝年号,并称康熙“圣天子”:“圣天子崇儒尚文”[35]116,“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礼教,不因之而益重乎?”[35]262康熙十九年(1680)明史馆聘黄宗羲进京与修明史,黄宗羲以年老辞,但未阻止儿子黄百家与弟子万斯同入馆。顾炎武不仅晚年交游降清明臣曹溶、程先贞、史可程等人[36],而且其外甥徐乾学与徐元文均出仕清朝,顾炎武鼓励他们“以道事君”。康熙二十年(1681)之后,随着遗民界大师渐趋凋谢略尽,其后人则逐渐能够接受满蒙汉共同体的大清帝国,华夷之辨更趋边缘化。
如从横向角度看,同为遗民,其华夷观亦不尽一致。遗民金堡对夷夏之辨即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华夷二字,乃人间自家分经立界,若同一天覆,则上帝必无此说,亦但论其所行之善恶耳。……人着实干些济人利物之事。”[37]金堡此论可谓对孔孟“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说的突破。不辨华夷而辨善恶、倡经世致用,代表了清初遗民群体华夷观开放的一面。
要言之,开放与保守两种华夷观于先秦儒家思想体系生成之后,后世不同族群基于自身政治或文化立场,进行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论辩从未中断。华夷之辨的根本为文化主体性优劣辨,然“华夷二字,乃人间自家分经立界,若同一天覆,则上帝必无此说”[37],金堡所言甚是。清初三类群体,虽有以严防华夷者始,然不辨华夷为共同趋向。而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不辨华夷、华夷一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向心力与趋势,中华民族能不断走向融合与统一正是这一强大的文化向心力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