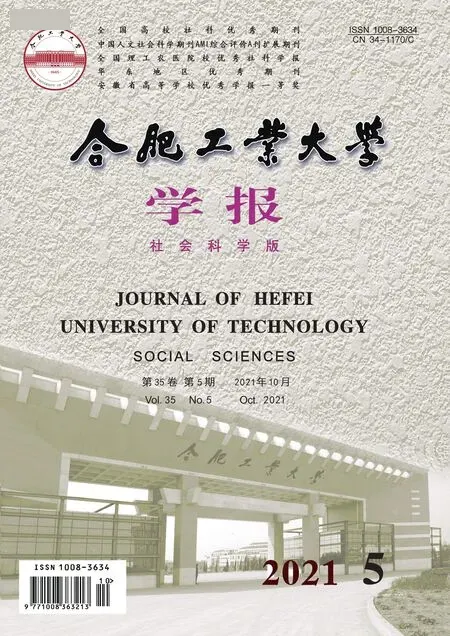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杯酒留痕》精神共同体的三重功能
2021-11-30杜志梅
陈 曦, 杜志梅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61)
一、引 言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1996年的布克奖获奖作品《杯酒留痕》(LastOrders)是一部以死亡为主题的小说。为实现屠夫杰克的遗愿,他的养子以及他的老友们一起踏上了前往马盖特的旅程。这场旅行不仅唤醒了人物内对于亲情与友情的深刻记忆,化解了人际关系中暗含的矛盾与隔阂,更强化了人物之间命运与情感的紧密联系。作为经久不衰的文学母题,旅行展现的是“人从文学意义上的旧身份出发寻找新身份,却恰在对远方的向往中不自觉地完成了对旧身份的重新建构而获得了新生”[1]。
《杯酒留痕》的送葬之旅如何将纹理细密的人文关怀融入人物新旧身份的转变之中,值得细细品读分析。本文从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切入,按照爱情、亲情和友情三个伦理维度的次序,探究小说如何通过人物的回忆和互动构建一个有机的精神共同体,以及人物身份如何在共同体内部重新生成,从而实现个体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哲学转变。
二、《杯酒留痕》中的精神共同体
在送葬之旅中,文斯养父杰克的三位老友形成了共同体。广义上的“共同体”(community)可以泛指一切具有共同目标或特征的群体。该词源于拉丁文communis,原义为“共同的”(common)[2],通常用来区别于个体。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共同体理论发端于古希腊哲学,在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TheRepublic)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Politics)中均有提及。虽然共同体概念早已有之,但在19世纪中后期前未曾受到重视。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将共同体概念引入社会文化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在1887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滕尼斯将共同体定义为“人类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3]。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将共同体分为三种类型,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4]53。滕尼斯认为,与“社会”包罗万象的丰富内涵不同,“共同体”是一个有机体,蕴含了人与人之间纯朴、亲密的感情,“相互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这是一种有机的联系”[5]。
作为共同体的一种类型,精神共同体特指“具有共同信仰、共同价值追求的人们为了满足主体心理、情感、意志等精神方面的需要所结合起来的共同体”[6]。成员之间在精神、情感与伦理等层面上强烈依存的有机联系是维系精神共同体的纽带。精神共同体中自然本性与心灵生活的联系是成员相互合作的基础。
小说中的共同体建立在杰克之死的基础上,送葬成为文斯与养父好友共同的目标,他们以杰克为中心,以友情、亲情与责任为联系,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共同体。法国哲学家南希(Jean Luc Nancy)指出:“共同体在他人的死亡中得以显现”[7]15。《杯酒留痕》精神共同体肩负杰克的遗愿,从博蒙德赛前往马盖特,成员之间的情谊不断加深,正如滕尼斯所言:“精神共同体是由地缘共同体发展而来,其基本表现形式为友谊”[8]。
关于共同体成立的条件,滕尼斯有明确的表述:一是共同体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作为一个共同体自己的意志[4]58,这种意志被理解为成员彼此之间的默认一致(consensus);二是默认一致的语言基础是共同体成立的关键,通过语言上的交流,成员告知和感受到痛苦、欢乐、惧怕和所有其他的情感;三是“共同体的生活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是占有和享受共同财产”[4]62。同样,情感归属的一致性正是精神共同体得以建立的首要条件,成员必须具备“共同的目标、志趣或利益,及由此而产生的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性”[9]。
小说中,实现杰克的遗言是送葬共同体的一致目标,一路上他们彼此合作,表现出强烈的相互依存性。四个男人对杰克遗愿怀有很强的责任感,都心甘情愿地踏上了这次旅程。用养子文斯的话来说,他们几个人便是此次旅行的最佳组合。“我们四个就很舒服。也许这只是男人的事。”[10]23文斯主动驾车,是启动旅程的直接推动力。殡葬师维克在送葬之旅中是维持仪式与秩序的关键人物,他的存在令人心安,确保了仪式的规范,以至于雷感叹道:“知道你的至交会给你做好敛葬准备,装好骨灰,并安排好一切后事真是一种慰藉。”[10]4雷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是主要的叙事者,在旅行中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他“连接着破碎的家庭与相互憎恨的朋友,并维持他们之间的友谊”[11]56。伦尼虽然常常惹是生非,但他的健谈消除了旅途的沉闷,是不可或缺的一员。
精神共同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成员之间的内部公约。精神共同体不能仅凭借情感来维系,情感会造成内部秩序混乱。因此,情感之外,还要有公约,“具有共同的规范和价值准则,这是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和配合的关键”[9]。共同的价值规范维持共同体内部秩序稳定,促进成员间相互配合,是构建精神共同体的第二要义。在送葬旅程中,杰克虽已辞世却始终在场,他在成员们的回忆中不断被赋予生命,他的话语回荡在其他人的耳边,甚至对成员们起到了“监督”作用。可以说,杰克也是这个共同体超越现实层面上的成员,“死者的声音尤为重要,因为它极大地影响着其他主人公的生活。”[11]62尊重杰克为“鲜活的个体”这一共同意识,成为送葬共同体的统一规约,并通过共同回忆逐渐被巩固。正如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所言:“人类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改变或掌握世界的权力,也是在叙事话语中被记住、被回忆的能力。”[12]旅途中,杰克一次次被大家回忆起,他的声音始终萦绕在送葬成员的耳边,使成员们在尊重杰克的骨灰这件事上形成统一的价值认同。
精神共同体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可以升华成员们的精神,能够实现成员间情感需求的满足与共鸣,促使个体发挥自身独特的价值。每个成员进入精神共同体,就放弃了一部分自我,开始了自我主体性的重建过程。小说中的送葬旅途包含了社会仪式的三个阈限(1)“阈限”是文化人类学中的概念,指一种社会文化结构向待建立的社会文化结构过渡的状态或过程。旅游“有着一个三段式的仪式程序结构:1.阈限前阶段(分离:离家出行);2.阈限期阶段(过渡:朝圣与旅游过程);3.阈限后阶段(交融:回归生活)”[13]。阶段,是成员主体之间深度交流甚至冲突的过程,也是成员获得精神满足的来源。阈限阶段的交流和思考有助于成员超越自身局限,跨越主体性的边界,实现主体间性的突破,塑造新的自我。
三、爱情维度下责任性伦理的重构
作为一个成员间相互依存的伦理实体,精神共同体重要的伦理意义在于“它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符合时代精神要求的新伦理——责任性伦理”[9]。责任性伦理是一种强调道德要求的伦理形式,认为人作为道德主体应该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并将无私奉献作为个体在道德上的追求。小说中,杰克与埃米的夫妻矛盾在精神共同体责任性伦理的重构过程中得以化解。
杰克与埃米看似夫妻关系和谐,实际上二人关系却包含着双重矛盾。第一重是经济层面的矛盾。杰克生前为了还清贷款,变卖了自家祖传的肉铺,还未还清欠款就因病去世,给妻子留下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造成了后者生存困难。第二重矛盾关乎权力,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两人对待女儿琼的不同态度之中。琼在小说中没有直接登场,看似可有可无,但她的存在反映了杰克与埃米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在埃米看来,杰克给她留下了一个难以收拾的残局。琼天生智障,在杰克看来,这似乎是对他与埃米婚前行为不端的惩罚。杰克在情感上排斥琼,拒绝探视女儿,并认为埃米每周对琼的探望既愚蠢又徒劳。他说,“如果我能放弃杰克·道兹家庭屠夫的身份,你也应该放弃每周愚蠢的旅途。”[10]16夫妻对女儿的不同态度造成了两人之间深刻的隔阂。
精神共同体内部形成新的责任性伦理,重构了两人的关系,彻底化解了夫妻间的双重矛盾。精神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是杰克的遗言,遗言中明确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洒在马盖特码头。生活在博蒙德赛的杰克为何要将骨灰撒在马盖特呢?这一看似与他们毫无关系的地点,事实上是杰克与埃米关系的重要纽带。在旅程即将结束时,雷回想起自己曾问杰克为何选择马盖特,杰克说;“‘我不想抛下她不管,我只想她好好地活着。’这时他突然闭上了眼睛,眼皮沉沉地耷拉下来,仿佛他的眼睛有难以承受之重。”[10]216对话以雷的视角对行将就木的杰克进行了细致描写,伴随雷的猜测与杰克留下的悬念,充分表现了在生命最后阶段,杰克内心对艾米的愧疚之情。这也揭示了杰克选择马盖特作为人生终点的真正原因——这里是他与妻子埃米的蜜月之地,亦是重新开始的希望之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杰克想通过遗言完成对妻子未兑现的承诺,弥补自己曾犯下的过失,履行丈夫的责任,演好爱情维度下自己的伦理角色。
精神共同体实现了杰克的道德责任,重构了两人的责任性伦理。责任性伦理表现了精神共同体的道德功能,其中衡量道德的起点不从个人出发,也不由个人的权力或需要决定,“而是在各种人伦关系、在人与人、人与周围环境的社会联系之中”[9]。杰克选择马盖特码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表达了他对埃米深深的关心和歉意,表现出对埃米源自生命深处的爱。此外,他的辞世为埃米提供了思考未来生活的契机,体现了责任性伦理强调的人际关系奉献精神。这种责任性伦理关系的建立,使埃米与杰克的矛盾得以化解,埃米摆脱了过去生活的阴影,结束了长达五十年的探望女儿的习惯,换上崭新的面貌追逐新的生活,成为一名独立的女性。
四、亲情维度下情感缺憾的弥补
除了在夫妻关系维度中建立责任性伦理之外,精神共同体在化解杰克与文斯养父子之间的代际矛盾、调和父子关系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精神共同体有满足情感需求的功能,能够弥补成员情感经验上的缺憾,提升个体精神世界的品质,促使个体发展健全的性格。
杰克与养子文斯之间存在代沟,这种冲突从本质上讲是“社会文化变迁和抗争性的文化隐喻,再现了自由意志抗争下的伦理冲突”[14]。杰克与文斯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加上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导致了父子关系的紧张。文斯对其作为杰克养子身份感到羞愧,同时还表现出对杰克意志的抗拒和对养父母的敌意,这是他情感需求长期被忽视的结果。虽然文斯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但他仍缺乏明确的归属感,这导致父子之间形成了典型的代际冲突。代际冲突理论认为:“处在特定家庭代际关系中的个体常会经历一种矛盾的心理体验——既想独立,又不得不延续家庭承上启下的角色需要;既考虑个人的利益,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道德责任或在社会环境中的具体表现;既爱对方,但同时又感到为维系情感而不得不付出的压力和承受精神上的疲惫;渴望行动自由,同时又期望得到源于家庭制度的支持。”[15]
作为年轻一代,文斯在家庭生活中体验同样的代际冲突,造成他在情感上与养父母疏远。他渴望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却一直受到子承父业思想的束缚。矛盾重重的父子关系令缺乏家庭身份认同的文斯倍感疲惫,他想为自己而活,不愿像杰克那一代人一样单纯地子承父业,被动地接受安排。在他看来,杰克与“历史上的英国劳工阶层一样,他们需要完成责任,对各自的工作尽责,减缓改变和自我实现”[16]。文斯在职业上有清晰的目标,梦想成为一名车商,只有与车打交道才能充分发挥他的主体性,得到自我实现与精神满足。精神共同体成立之前,杰克与文斯之间属于“主客体”关系,文斯被养父“视为我的工具,我的客体”[17]。作为父亲,杰克仅将文斯视为继承家族职业的工具,无视文斯的主体性,给文斯内心留下了创伤。正如朱蒂思·赫曼(Judith Herman)指出的那样,心灵受到创伤的文斯“既想让别人注意到那难以启齿的创伤秘密,又想极力隐藏它的存在”[18]。渴望得到杰克的尊重与家庭关怀的文斯始终不能直面内心想法,隐藏情感缺失和参军逃避成为其无奈的选择。亲情关怀与价值肯定的缺失是构成杰克与文斯代际矛盾的主要原因。
但是,文斯主动驾驶奔驰车带领其他成员为杰克送葬,以实际行动发挥自身价值,重获情感满足。“满足个体的精神情感需要是精神共同体最主要的功能和作用,也是精神共同体存在的根本动因。”[6]奔驰车是文斯最珍贵的物品,代表了他对梦想的追求,象征着文斯“试图摆脱本地的忠诚度和价值传统”[13]。路过黑荒原时,被问到为什么要借一辆奔驰车,文斯意味深长地说:“这可不是一辆运肉的货车”[10]134。虽然文斯没有直接承认自己相信杰克一直“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但他内心却一直深信他的存在。拿出爱车为杰克送葬,文斯向杰克证明了自己的职业是有价值的,为实现精神共同体的使命发挥了关键作用。
精神共同体使个人与集体关系更加密切,个体成员在集体中得到了全面而充分的发展。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只有在共同体内,个体才有机会全面发展才能;因此,只有在共同体中,人的自由才有可能……个人通过相互联系获得真正的自由。”[19]在送葬之旅中形成的精神共同体为文斯获得精神满足提供了稳定的关系网。在关系网内,文斯与其他成员共同回忆杰克,获得他人对自己职业的认可,这反过来强化了他和杰克之间的父子关系:文斯开始正式认同自己的养子身份,并履行作为儿子的责任,弥补父亲的缺憾。途中,文斯改变计划驶向维克农场,在那里抛洒了父亲的骨灰。他知道那里是养父母相识的地方,在那里抛洒骨灰,既是对杰克与埃米夫妻关系的尊重,也标志着文斯内心对养父的正式接受。当旅途到达终点时,两人的代际矛盾在精神共同体的作用下得到化解。精神共同体使文斯与其他成员产生了共鸣,明确了他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个人选择自由,使文斯感知到生存意义,收获了精神情感的满足。
五、友情维度下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在家庭关系之外,精神共同体同样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和谐,尤其是友情的融洽。个体在精神共同体的生活中,通过对社会价值的认同,“逐步实现共同体价值的内在化和人格的同一性,促进个体道德人格的发展”[6]。《杯酒留痕》里,雷与杰克这对老朋友之间也存在深层次的矛盾,矛盾源自雷的道德过失。通过送葬之旅,雷的道德人格在精神共同体中得到了完善,他与杰克的矛盾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化解。
雷与杰克表面上十分友好。雷的穿着、对待杰克骨灰的态度无一不体现他对老友的尊敬,但友好关系的表象背后却隐含了双重矛盾。两人结识于战场,在战火中成为挚友,情同手足。然而,雷对杰克的妻子埃米却抱有不合乎道德的爱慕之心。杰克拒绝陪同埃米看望女儿时,“雷表现出自由意志的膨胀,他不顾社会伦理规约,试图达到接近埃米、插足朋友夫妻关系的非理性意志目的,做出了违背友情的伦理选择。”[20]雷与埃米的暧昧是他与杰克的第一重矛盾。此外,雷是一位赌马高手。有一次,受杰克的委托,雷替杰克投注,大获成功,赢下了丰厚的回报。面对利益,雷犹豫再三后选择隐瞒奖金的事实,仅将本金退还给杰克,还自我安慰这是对得起良心的做法。“他的见利忘义再次辜负了杰克对他的信任,从而进一步背弃他与杰克之间深厚的朋友伦理关系,也极大地降格了雷的理性和道德形象建构。”[19]这成为两人的第二重矛盾。
旅途中,雷多次回忆起与杰克共处的往事,每一次回忆都强化了他对两人友谊的认可,逐渐引起其内心的道德反省。经过坎特伯雷大教堂时,神圣庄严的大教堂促使雷反思自己,他说:“我可以感觉到教堂就在我身后,盯着我,似乎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阿雷拿了很多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10]219雷在这里感到自己被其他成员“监视”——这正是精神共同体对他的督促作用。被“监视”的感觉来源于他对好友杰克深深的内疚。精神共同体给了雷无形的压力,促使他拿出行动来完善自身的道德人格。杰克作为精神共同体的一员,也发挥了无形的督促作用。到达终点后,雷自述“我觉得自己无法说话,因为一股冲动在我体内油然升起,从胸膛那儿,杰克正在我胸前,包在我的大衣下,就像海浪在拍打着我的胸膛”[10]278。最终在道德与情感的双重拷问下,雷向文斯坦白了真相。道德自省,使雷直面内心、追求诚信,摆脱了自私自利的局限。人格升华后的雷终于能够用坦诚的心情完成杰克的遗愿。这场送葬之旅见证了雷从撒谎逃避到坦然面对过错的转变。道德人格的提升成为修补他与杰克之间友谊裂痕的关键,也是在旅途过后他决定与埃米开始新生活的基石。雷的决定是对杰克最好的补偿,他为自己曾经的伦理过失负责,兑现了对杰克的诺言。
六、结语: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飞跃
作为一部伦理道德小说,《杯酒留痕》深入家庭伦理与友情道德的纹理之中,从爱情、亲情与友情三重伦理维度出发,展现了精神共同体化解内部矛盾、实现伦理和谐的三重功能。小说从主体性哲学的高度观照社会现实问题,即被资本主义文化割裂的主体性如何在共同体内部实现超越,形成和谐共生的主体间性 。
“主体既是以主体间的方式存在,其本质又是个体性的,主体间性就是个性间的共在。”[21]主体间性作用下不同个体的交往,一方面带来对自身的重新认识与超越,在社会关系中找回个性;另一方面拉近主体间的距离,重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社会和谐。
精神共同体内部交往构成了主体间性的基础。原先分散的个体在精神共同体的作用下结成以杰克为中心的关系网,并在主体间的交往中找回真正的自我,验证了齐泽克所说的“如果没有主体间性,作为主体的‘我’是没法生成的”[17]。
约而言之,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飞跃化解了精神共同体内部诸多矛盾,使旧主体的“死亡”成为新生活的起点。